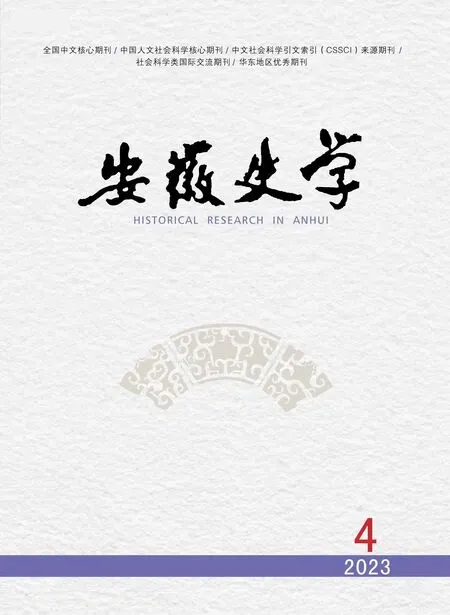明清时期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路径研究
——以祁州药市为中心
程立中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关于中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否形成于清代中期的争论由来已久。施坚雅所提的著名大区理论(Macroregion),按照空间地理维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且“每区最后都发展成为单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经济”。(1)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页。该理论不仅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如罗威廉认为前工业化时期,中国发达的水运系统和特殊的商业手段,抵消了长距离和低技术的制约,“在清朝中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2)[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作者认为“如果说中国国内市场有一个惟一的集散中心的话,它就应当是汉口”。罗威廉所强调的“汉口”集散中心,是综合性的集散市场,并非本文所研究的全国性专业市场。也遭到中国学界的反驳,李伯重则认为,1840年以前“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3)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邓亦兵的研究显示,“全国商品流通网络”(4)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在清代前期就已形成。许檀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5)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几乎全国大部分州县、村落均可进行经济联系。
西方话语主导下的世界史研究认为,非西方地区的全国市场形成,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结果,该观点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如中国,更不能简单笼统地套用在各地特殊专业市场的形成上。如明清时期中国传统药材市场的形成问题,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6)朱绍祖、吴寰:《清代重庆药材市场的形成问题探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清代药材市场的形成原因、发展变迁、药商信仰及经营活动等内容,至于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路径问题,并未给予充分关注。(7)相关研究成果如牛良臣:《祁州药都形成的原因》,《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留文:《洪山信仰与明清时期中原药材市场的变迁》,《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等。按照卡尔·波兰尼的市场理论,“排除任何干涉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8)李拂尘:《制度、选择与市场形成:一个理论框架》,《学术界》2015年第4期;[英]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而清代全国性药材市场又通过哪些路径形成?本文以“祁州药市”为中心探讨此问题,不仅对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全国市场形成”观点给予回应,还可为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家战略提供历史借鉴。
一、传布:“药会”活动的兴办
随着城乡药业的快速发展和药材出口的增加,以祁州、百泉、樟树等为代表的区域性药材市场,在清代中期呈现出定期集市和跨区贸易共生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9)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尤其祁州药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药材市场,“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的时间,应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10)牛良臣:《祁州药都形成的原因》,《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而这种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则得益于早期的“药王庙会”。
祁州药王庙会,最早形成于“南宋咸淳年间”(11)杨见瑞主编:《祁州中药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初期由药王庙的“香火会”(12)河北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演变而来。祁州土神庙在南城门外,自宋代以来,以医显灵,故“四方赛祷无虚日”。(13)康熙《祁州志》卷3《祀典志·皮场王庙》,清康熙十九年增刻本。明成化二十年,州守童潮《皮场王庙》诗曾言“礼祷纷如蚁,常闻萧鼓音”。(14)乾隆《祁州志》卷7《艺文志·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660页。药王庙又称为皮场庙,初期仅为一座“不知名的地方庙宇”(15)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庙会期间的四方民众,多为祷礼祈福而来。
明代祁州药王庙会迅速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成化二十三年二月,知州童潮请命新修庙宇,于清明节期间,举行“酬神”活动,演奏“迎神曲”“送神曲”(16)成化丙午《重修皮场祠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曲词内容突出“庙神”的医药色彩,如“蓬莱之药贮满囊”“龙虎之药留丹房”等。随后,祁州药王庙会的影响开始达于四郡,收到名遂扬、车相望的效果。
万历年间朝廷因之敕封重修药王庙,庙会的影响随之倍增,“倾动远迩,齐沐仰瞻,奔走一时”。(17)万历《敕封重修明灵昭惠显佑王新碑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尤其在清明寒食之际,“赛祷于祠下,车榖填门”(18)万历二十六年《重修明灵昭惠显佑王祠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环境,“轮蹄辐辏尤甚,或辇金钱,或输诸币”。(19)天启二年《新建皮王神阁碑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药王庙会原为“民俗信仰”活动,客观上为产品交易提供了空间,从而演进为“信仰与经济形成相互纠缠的态势”。(20)张海岚:《民俗经济视角下都市传统庙会市场空间变迁研究——以上海龙华庙会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随着时间的发展,药王庙会的平台聚集属性日益凸显,其平台经济功能得以发挥,“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21)李育冬、张荣佳:《商务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6页。
至清代,这种平台经济规模进一步发展。康熙时期:“清明时人以万计,车载填门。”(22)康熙《祁州志》卷3《祀典志·皮场王庙》,清康熙十九年增刻本。雍正年间,刁显祖的《祁阳赋》云:“年年两会,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23)乾隆《祁州志》卷7《艺文志·赋》,第648页。药王庙会突破了每年一次的局限,改为冬、春两次。“药材”(24)据刁显祖在《祁阳赋》中言:“药材极山海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皮服来岛夷而贩口西,名驹竭秦晋而空冀北。”可见此时“药材”作为祁州药王庙会上的交易商品,其地位开始逐渐显现。作为主要商品,进入庙会大宗交易商品行列。乾隆年间,祁州药王庙会的中药材交易量逐年增加,每年清明及十月十五日,“商贾辐辏,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云”。(25)乾隆《祁州志》卷2《建置志·坛庙》,第145页。至此,祁州药王庙会作为区域性药材交易平台基本成形。
祁州药王庙会吸引了更多药商前来“平台”交易,因“平台上卖方越多,对买方的吸引力越大”(26)徐晋、张祥建:《平台经济学初探》,《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5期。,形成良性互动模式。来自各地的药商,有交易的,有“了解行情、搜罗信息的”(27)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7页。,更大规模的庙会“则吸引了更大范围的商业往来”。(28)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4页。故清代中叶发展中的祁州药市,需要借助更大规模的庙会活动,以扩大影响。
作为商业附属的地方景观建设,也被纳入庙会“平台”体系之中。嘉庆年间,祁州药王庙中自宫殿至墙垣、门坊,靡不修葺,彩画维新,可谓“祁郡一大观”。(29)嘉庆九年《重修皮王阁神碑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嘉庆二十三年,经本地药商卜中节等劝募,增修名医殿、碑楼、钟鼓楼,以及牌坊、戏楼等药王庙的相关建筑,“规模始大”。(30)光绪《祁州续志》卷1《建置志·祠庙》,(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6页。位于药王庙右后之偏南向的皮王阁,也被集资重建,“以壮观瞻者”。
至道光年间,祁州药王庙再次重修,“药王神庙已更旧址,尽焕新规”。(31)《南旗杆底座铭文》,现存安国药王庙门前。在药王庙山门外,有铁旗杆二根,始铸于道光九年,资金源于商业捐助,其中药商占比较大,如“大药市、陕西帮、京通卫、杂货行、山东帮、山西帮、黄芪帮、关东帮”(32)《北旗杆底座铭文》,现存安国药王庙门前。等。此铁旗杆“高七丈二尺”(33)光绪《祁州续志》卷1《建置志·祠庙》,(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6页。,上干云霄,塑有龙凤,悬旗于上,格外醒目,“无疑可以成为商人最精彩的广告”(34)徐春燕:《古代铁旗杆考》,《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对于当时祁州药王庙会以及药材市场的声名传布,无疑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祁州药王庙会影响的扩大,同治年间的药材交易较往昔更为繁盛,“商贾云集,称盛会焉,而药行尤巨”。(35)同治四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光绪六年,以卜凤鸣、卜兆晋为首的地方药商,复议捐资增修药王庙,此次增修前后历时八载,“共支京钱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千六百五十六文”(36)光绪六年《同治十二年春会至光绪五年冬会客帮银钱捐项碑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又以药商捐资较大。增修之后的祁州药王庙规模愈为宏壮,药材市场也极为繁盛,“故春秋两季,南北药贾,奔走而来遍海内”。(37)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现存安国药王庙内。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药商,不仅主导药王庙的修建,“三次庙宇修缮均为卜氏主持”(38)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还主导药王庙会的兴办,如卜中节经办庙会,“南关春冬两会,商贾云集,事无巨细,皆倚赖之”。(39)光绪《祁州续志》卷2《人物志上·义行》,第143页。
总之,在官府和药商的共同助推下,祁州药王庙会实现由信仰向商业空间的转化,并依托庙会的平台经济功能,吸引各地药商汇集于此,祁州药市得以迅速发展,最终于清代中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地。
二、共识:“药王”形象的建构
祁州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药材市场的重镇,据说与“药王”的作用“有偌大的关系”(40)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上)》,《社会科学杂志》1932年第3卷第1期。,因此探讨祁州药市的演进路径,“药王”提供了理想的视角。
祁州地方文献中,较早论及“药王”内容的,为《重修皮场祠记》:“祁之土神兮,曰皮场”。(41)成化丙午《重修皮场祠记》。此处的“皮场”,应为“皮场王”。宋建中靖国元年,获朝廷封赐,“敕皮场土地……爰视侯封,褒锡美号”(42)邹浩:《道乡集》卷16《皮场土地封灵贶侯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3页。,因愈之难疗,显济一方,故“特封灵贶侯”。(43)司仪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137《礼典二十二·地示、山川、杂记·皮场土地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6页。崇宁四年,又被朝廷加封为“灵惠王”。(44)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10、4011、4011页。原为普通的皮场土地,通过朝廷的连续封赐,获得“王”的称号,从而进入国家祀典体系。但皮场王身份并不清晰,未被赋予具体的神祇形象。直到政和年间,周秋在皮场王《记文》中借耆老之言,最早建构出皮场王为“神农”(45)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10、4011、4011页。之说。此外,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席旦”(46)洪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5《皮场大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郑信”(47)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67页。“张森”(48)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卷12《南山城内胜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155页。等诸多形象,大都影响甚微。
获得国家祀典资格的“皮场王”,一旦进入地方祭祀系统,其神祇色彩与历史情境,势必会被本土化重构,以便满足地方话语权力表达的需要。明朝初年,朝廷禁止地方以“三皇”为医药之祖进行祭祀,“三皇继天立极,以开万世教化之源,而汩于医师,其可乎?”(49)《明太祖实录》卷62,洪武四年三月乙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明实录》校印本,第1200页。故成化年间祁州州牧童潮在《重修皮场祠记》中,未承袭皮场王为“神农”之说,仅言“皮场为州之灵神”,皮场王的具体形象依然模糊不清。该碑文记载的皮场王医秦王疡疾之事,“神忽感于梦寝兮……药其疮。厥疾遂愈兮,安且康”,其实是对政和年间皮场王《记文》中“应梦见祥”(50)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10、4011、4011页。的挪用。祁州本土所建构的皮场王历史“灵迹”,与宋代的朝廷叙事,存在明显差异,后者仅有“香火辄愈”(51)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88页。的记载,未见“梦寝”“遂愈”之事。皮场王的地方书写,虽然还未与“祁州风物相结合”(52)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但已为皮场王的本土化建构,作了较好的铺垫。
将皮场王叙事与祁州风物相结合,初见于万历二十六年的《重修明灵昭惠显佑王祠记》。该碑文将宋代朝廷封赐制文与周秋《记文》、“医治秦王”等内容附会整合,并借父老传言,完成皮场王为“祁州南关人也”的建构。皮场王由成化丙午碑中的“祁之土神”,演进为“南关人也”,实现了由“神”到“人”的形象转变,意在皮场王的本土化。天启二年《新建皮王神阁碑记》摒弃了“明灵昭惠显佑王”称谓,改以“皮王”称之,再次突出皮场王的医疾灵验形象,“梦神授之剂,觉而陈疴顿减,厥明乃疗”。“梦寐疗疾”传说母题再次呈现,但医疗对象由“秦王”转变成“居民”,皮场王形象“完成了在祁州地方社会的在地化过程”。(53)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
清朝时期,在四方药贾竞相奔祁的形势下,药王形象的建构起着提升药商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康熙《祁州志》所载皮场王医疾灵验之内容,主要承袭宋代旧文与前明碑辞,并言皮场王为“祁州南门人也”。(54)康熙《祁州志》卷3《祀典志·皮场王庙》。乾隆《祁州志》载:“汉将邳彤王庙,俗呼为皮场王,即药王也”(55)乾隆《祁州志》卷2《建置·坛庙》,第145页。,祁州皮场王首次以“邳彤”“药王”形象,出现于地方志书之中。“药王”的地方史志书写,应当是祁州发展为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所需。而汉代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也”(56)《后汉书》卷20《邳彤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57页。,王莽时分钜鹿为“和成郡”(57)袁宏:《后汉纪》卷2《光武皇帝纪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03册,第506页。,居下曲阳,以邳彤为“卒正”。(58)刘珍等:《东观汉记》卷10《邳彤列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0册,第127页。后归顺光武帝,战功显赫,被封灵寿侯,官至太常少府。史书关于汉将邳彤的叙事内容,与祁州地方志书的书写,存在较大的差异,志书所言秦王得疾,药王“进药数丸,立愈”(59)乾隆《祁州志》卷2《建置·坛庙》,第145页。之事,而史书未载。乾隆《祁州志》有将邳彤、皮场王与药王,“糅合成一体”(60)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的趋势,并且将“汉邳彤王庙”作为标题,改变以往旧志惯例(61)康熙《祁州志》卷3《祀典志》。该志以前旧志,大都将“皮场王庙”作为标题。,由此可知乾隆年间,邳彤作为祁州之药王,已在本地形成共识。
嘉庆九年《重修皮王阁神碑记》中,仅有“皮王明灵昭惠显佑”之记载,未有出现“邳彤”“药王”之称,可见三者杂糅,碑刻文献迟于官方志书。道光二十二年,祁州卜中节所撰的《重修皮王阁神碑记》载:“皮王,浑名也。……此处旧有神农庙”(62)道光二十二年《重修皮王神阁碑记》,《安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4页。,凡四方远近士农工商祈医屡应。乾隆年间祁州志中邳彤的书写,已有影响,而为何至道光年间,地方碑刻又出现神农形象,祁州皮场王与“神农”的关涉,应非随意而为。嘉庆年间,祁州南关药会,就已“天下驰名久矣”(63)嘉庆九年《重修皮王阁神碑记》。,而道光年间临近鄚州药市的衰落,又为祁州药市的繁盛提供了“极好的契机”。(64)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鄚州药市曾为明代华北地区较为繁盛的药市之一,“城外有药王庙,专祀扁鹊”(6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外郡·鄚州》,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6页。,由于乾隆、道光年间,连遭火灾,“景物消歇,不似从前云集矣”。(66)道光《任邱县志续编》卷下《绪言志·余录》,清道光十七年刻本。随着鄚州药商向祁州的转移,相邻的两个药市,自然存在彼消此长的竞争,无论是形象模糊的“皮场王”,还是毫无医药历史背景的“邳彤”,均难以抗衡古代名医“扁鹊”的影响。在此形势下,以卜氏为代表的地方药贾,借助“神农”凝聚共识,扩大祁州药市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在清代国家医药祀典体系中,处于从祀地位的“扁鹊”,远低于主祀地位的“神农”(67)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49《礼部·祠祭清吏司·群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427页。,这或许是道光年间卜中节建构祁州药王“神农”的主要原因。但“其神农之说,似不可信”(68)(伪)河北省公署秘书处情报室:《安国县药王庙事迹》,《民国文献类编·历史地理卷》第968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可能是神农非出自本地,难以令众药商信服。光绪年间祁州又曾出现皮场王“张森说”(69)《祁州乡土志》,清光绪二十七年抄本,天津市图书馆藏。,也影响甚微。
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云:“祁之崇祀药王也……邳姓彤名”,为光武二十八将之一,南关有其故墓。该碑记的作者是户部山西司主政沈鸣珂,再次将祁州药王与汉代邳彤进行关联,可能是受卜凤鸣、卜兆晋之请,“函致京师嘱为文”,自然要体现请托人的意图。但难免有人疑问,邳彤不以医名而祠以药王祀之,难免牵强,故解释“其王固精于医而史乘未记”(70)万历二十六年《重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且言史乘所记称其大而略其细欤。这种归为史家之失的想象性发挥,反映了卜氏后代为凝聚南北药贾之共识,不惜抛弃祖辈的“神农”之说,而把“吾祁为桑梓之乡”的邳彤,再次建构成祁州药王形象,客观上扩大了祁州药市的影响。
三、规训:“药市”礼约的形塑
在祁州药王庙会平台上,组织者及买卖双方,在信仰、经济的纠缠中,“在达成不同认同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庙会商贸习俗’建构的合谋者”。(71)张海岚:《民俗经济视角下都市传统庙会市场空间变迁研究——以上海龙华庙会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他们以各自形式获取收益,并在获益的“过程”中,体现着相关制度的“安排、习俗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塑造”(72)金晓瑜、沈卫平:《企业·市场与制度——关于企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制度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这种相互守信遵约的社会习惯,保证了交易活动的稳定性。
明清时期,随着祁州药材市场的日益兴盛,全国各地药商纷至沓来,来自不同区域的药商,思想观点、生活习俗等均有差异,势必需要系统性“塑造”和“规训”(73)[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197、155、201、216页。,以便稳定商贾,繁荣贸易。
道光年间,祁州药材市场中的“安客堂”(74)刘铁梁:《安国药王庙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便是在稳定商贾、繁荣贸易的目的下成立,其宗旨是“保障客商利益”(75)安庆昌:《安客堂和十三帮五大会》,《安国县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安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第67、68页。,办理药材市场的一切事宜,可谓是全行业的“总组织”。(76)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351、352页。而安客堂可视为一种“规训”场所,是一切需要被了解事情的“汇聚点”(77)[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197、155、201、216页。,各地商帮之间发生贷款纠纷,不是到官府解决,而是到“安客堂”进行调解。
为确保公平交易,安客堂起草了“药材地道、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一诺千金”(78)安国中医药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国中医药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页。的庙会公约。福柯认为这种公约性“纪律”,其高雅性在于无需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79)[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197、155、201、216页。安客堂内还设有“标准称”,用来解决争称问题,经手人如有吃称,安客堂便惩罚当事人出钱演戏,以示警戒;祁州本地药商如与客商发生纠纷,即使本地药商有理,安客堂也要求向客商赔礼,以示尊敬。由此可知,祁州药市更趋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80)安庆昌:《安客堂和十三帮五大会》,《安国县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安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第67、68页。,便得益于这种按章办事的“礼约”。“安客堂”可谓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81)[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197、155、201、216页。,享有某种司法特权。“安客堂”实际上成为整个祁州药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清朝末年,其直接更名为“商务分会”。(82)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351、352页。
药市交易活动构成了祁州庙会的主体,以卜、崔、张、党为首的四大家族,不仅掌控着庙会的主办权,还轮流把控着“安客堂”,为本家族商业谋取最大的利益。如卜中节掌管庙会,“事无巨细,皆倚赖之”,其孙卜兆晋继其后,“亦颇能绳其祖武”。(83)光绪《祁州续志》卷2《人物志上·义行》,第143页。而安客堂的主管,“历任总不出崔、卜两家”(84)刘铁梁:《安国药王庙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崔家先后有崔洛朝、崔子舆、崔志远等,而卜家则先后有卜庆甫、卜继彬、卜继荣等。
卜、崔、张、党等家族之间也存在合作与竞争关系,共同主导着祁州药市的经营。卜家主营永德裕、永和堂、全记等药材商号;崔家主营瑞盛永、德行永等熟药行;张家主营拆货棚、行栈,兼有义盛和、万盛魁等商号;党家则以药铺经营为主。祁州“四大家族”分居于药王庙周围,“形成了四大家族对药市的环抱型分布”(85)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共同维护祁州药市“礼约”的实施。
同治、光绪年间祁州药王庙曾进行大规模重修,“增其式廓,而规模愈宏壮矣”。(86)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而重修费用则主要来源于药商的义捐,已有的研究显示“药商捐款可能超过90%”。(87)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绪五年众商义捐布施碑记》将这些药商的捐款数额、所属商帮、商号名称和起源地名等,均刻于石碑之上。这种“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88)[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4、197、155、201、216页。,则把个体纳入整体,既是功德展示,又是比较领域和区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度量差距和决定水准的作用,从而导致个体差异的显现。又如《经纪捐款碑》记载,同治十二年春会共176名,“共捐钱五百七十七千”(89)许檀:《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该碑把捐款人姓名和数额一同公布于众,或许主导者认为,让个体感受“压力”愈强,“规训”效果愈佳。
祁州药材市场中“安客堂”和药商“捐款碑”,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特定“空间”,发挥着“规训”的效能。而作为“空间规训”,主要“通过对空间的刻意为之的筹划、设置与构造”(90)李赛乔、庞弘:《空间规训——理解米歇尔·福柯空间理论的关键概念》,《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年第1期。,从而对个体产生某种影响,使之遵从于既有秩序。就祁州“药王庙”的建造历程而言,自明代成化年间的“皮场祠”(91)成化丙午《重修皮场祠记》。,到清康乾时期的“皮场庙”(92)康熙《祁州志》卷3《祀典志·皮场王庙》。与“邳彤王庙”(93)乾隆《祁州志》卷2《建置·坛庙》,第145页。,未载空间设置。至嘉庆二十三年,经卜中节等劝募,“增修名医殿十楹”。(94)光绪《祁州续志》卷1《建置志·祠庙》,第55页。名医殿建于主殿之前两庑,“以历代名医配之”(95)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其左依次为华佗、孙林、刘河间、张子和、张惠卿,其右为皇甫谧、扁鹊、张仲景、孙思邈、徐文伯。令人疑惑的是,祁州名医殿所祀名医,并非完全按当时国家从祀名医礼制执行,即不同于明代从祀的“十大名医”(96)《明史》卷50《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94页。,也有别于清代从祀的二十八“配位”(97)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49《礼部·祠祭清吏司·群祀三》,第427页。除华佗、皇甫谧、刘完素、扁鹊、张仲景、孙思邈六位名医在列外,其余四位均不在列。诸医。
祁州药王庙在祀典名医选择上,名医殿建造者有其自身考量,把部分药材商帮故乡名医纳入从祀之列,让各地药商祭祀、瞻仰药王时,形成特定的等级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思想,从而遵从既定的商业秩序,实现规训的目的。建造名医殿“盖愈抬高药王之神位及表显其灵应有过于十大名医耳”(98)(伪)河北省公署秘书处情报室:《安国县药王庙事迹》,《民国文献类编·历史地理卷》第968册,第214页。,在这种设置、构造分类等级中,规训权力“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99)[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第211页。,由支配空间进而影响个体,从而实现更宽范围的“掌控”与“规范”。
四、协作:“药帮”利益的调适
在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药商“团体”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各地药材商帮的协作,共同推动了明清祁州药材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最终演进为“全国药材集散地”(100)河北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河北名胜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101)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前言》,黄山书社1993年版。同治、光绪年间祁州“十三帮”的出现,被视为全国性药材市场形成的重要“标志”。(102)牛良臣:《祁州药都形成的原因》,《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祁州“十三帮”之名,最早出现在同治四年,凡药商载药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103)同治四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祁州药王庙山门前所铸铁旗杆底座铭文,就刻有捐款药材商帮的名称,如“山西帮、黄芪帮、关东帮”(104)《北旗杆底座铭文》。等。所谓的“帮”,就是一班做买卖的人,或因来自同一地域,或因交易同一种类的货品,而组成的“一种特殊团体”(105)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下)》,《社会科学杂志》1932年第3卷第2期。,多取友助之义,“商家同行同省谓之帮”(106)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校注本)卷14《人物志八》,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721页。,“地域”与“行业”是清代祁州药材商帮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
“十三帮”中的“黄芪帮”,在祁州本地常驻,是“专门从事黄芪运输加工的药商”。(107)刘铁梁:《安国药王庙会》,第32页。清代前期祁州所产药材主要有“枸杞、黑白丑、紫苏……王不留行”(108)乾隆《祁州志》卷3《赋役·物产·药属》,第248—249页。等34种,并未有“黄芪”的记载,“祁州并不产黄芪,市售各种黄芪均来自外地”。(109)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240页。内蒙古的黑皮黄芪,因内色鲜黄、品质优良,为在祁州经营的浑源黄芪药商所重视,故纷纷仿制加工。当黄芪产新之季,运输的马车骡队,往返于浑源与祁州间,获利颇丰。“黄芪帮”也成为祁州本地药帮中规模最大者,主要对来自山西和关外的黄芪进行加工和销售。(110)由于黄芪主要产自山西、内蒙古和黑龙江一带,故黄芪为山西帮和关东帮主营药材之一,而祁州黄芪帮则侧重于加工销售,各药帮之间的密切配合,共同推动黄芪的全国性流通。祁州黄芪、甘草等药材多以浸润、切制方式加工,技术讲究,经“数百年的加工实践,形成独特技艺”(111)河北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国县志》,第364页。,所加工药材均匀美观、药效提高。据《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绪五年众商义捐布施碑记》可知,黄芪帮位列第五,捐钱“占各帮捐款总额的8.1%,实力亦属不凡”。(112)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除从事黄芪加工、销售外,部分土著居民则以药行经纪人的身份活跃于祁州药市,游走于买卖双方之间,以促成双方交易为目的,并抽取一定佣金。即使买卖双方不到祁州现场,也可完成交易,其关键“完全在经纪人”。(113)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下)》,《社会科学杂志》1932年第3卷第2期。经纪人以自身信用担保达成交易,并以绝对公信力保障着“自身利益及市场金融的稳定”(114)杨小敏:《论祁州药市金融》,《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促进药市的繁荣和发展。可见,以祁州本地人为主的“黄芪帮”和药行经纪人,对祁州药市的兴盛,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祁州药市上还有许多药材来自外地,“东购辽沈,西接川陕,南交云贵,北来塞外,云屯物集”。(115)《祁州乡土志》。其中源自“辽沈”的药材为祁州药市之大宗,主要为“关东帮”所经营。关东帮为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一带的药商所组成(116)刘铁梁:《安国药王庙会》,第32页。,大多以“吉林”“营口”为集散地,在祁州各药材商帮中“占首位”(117)安庆昌:《安客堂和十三帮五大会》,第69、70页。,经济实力最强。在《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绪五年众商义捐布施碑记》中,该帮捐款数额高居榜首,接近总捐款额的四分之一。每届祁州药会期间,来自关外的镖车绵延数里,享有“关东大军”之称。其所贩药材总额,几乎占当届药会“全部来货的大半”。(118)政协安国市委员会编:《千年药都》,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页。“关东帮”在清乾隆年间就已见雏形(119)民国《武安县志》卷10《实业志·商业》,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主营人参、鹿茸、黄芪、虎骨等“关外药材”。(120)黄璐琦、张瑞贤主编:《道地药材理论与文献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关东帮所贩药材大多“由北宁转平汉至定县”(121)郑合成:《关于“安国县药市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后至祁州,约二三千里。
祁州药材市场的兴盛,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活跃在祁州药材市场的山西帮,既从事药材交易,又“垄断了市场的金融发展”。(122)政协安国市委员会编:《千年药都》,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页。山西帮主要由山西和部分陕西药商组成,多零散小型,以经营“枸杞……小茴香、西贝母”(123)安庆昌:《安客堂和十三帮五大会》,第69、70页。等药材为主。明清时期,山西商业繁盛,资本雄厚,“江北则推山右……其富甚于新安”。(124)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清代山西的曲沃、潞州、泽州、汾州等地,经商风气盛行,商业资本雄厚。山西之平阳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125)《平阳府志》卷20《宦绩》,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所辖曲沃县,土狭人满,“每挟资走四方”(126)《续修曲沃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清嘉庆二年刻本。,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而“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127)顾炎武著、谭其骧等点校:《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5页。,非数十万不称富,“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128)《清高宗实录》卷1257,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下,《清实录》第2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9页。,可见山西富贾财资之巨。
清代山西帮凭借雄厚资本,逐渐向金融业发展,经营票号。清朝徐柯《清稗类钞》记载,所谓票号,以汇款及放债为业者,“其始多山西人为之”(129)徐柯:《清稗类钞·农商类·山西票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7页。,分号遍各省,当未设银行时,全恃此以为汇兑,清季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汇兑业务”。(130)陈绍闻主编:《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清代祁州药材市场最早的金融机构,为道光年间山西人开设的“兴盛”银号,众多药商的药材交易,“主要靠银号大量银钱码子的周转”(131)河北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国县志》,第377页。,为各地药商资金调剂和药材贸易提供方便。
明清时期,各地药帮通过“南药换北药,东西拆兑”(132)刘华圃、许子素:《祁州庙会——药材市场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使祁州形成药材发兑的总汇之地。清代祁州药帮,尚有“京通卫帮”“陕西帮”“彰武帮”“山东帮”“浙宁帮”“禹州帮”“江西帮”“亳州帮”“怀邦”“广帮”等。(133)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352页。祁州药材因药帮巨贾的协作,才有“各省皆至,南北俱备”(134)赵燏黄著、樊菊芬点校:《祁州药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又因各地药帮奔驰辐辏,发兑远销,祁州药市才人山药海,益形发达。各地药帮,因利益而汇聚,“为祁州药市的繁盛助以肱骨之力”(135)政协安国市委员会编:《千年药都》,第185页。,才能成就其集全国药材贸易之大成。
各地药帮因同乡或同行联合而成,“有明显的竞争和垄断性质”(136)傅立民、贺名仑主编:《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难免有利益摩擦。如关东帮因东北地方人稀,“消费有限”(137)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历年运大批人参、黄芪等药而来,而运去的药“却寥寥无几”。(138)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下)》,《社会科学杂志》1932年第3卷第2期。又因清代江南温补之风盛行,“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139)徐灵胎著、刘洋校注:《医学源流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而关外所产人参又是温补上药,甚至出现“富贵之人不死于参者鲜矣”(140)王士雄著,苗彦霞、耿荣安注释:《三家医话》,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的程度。故祁州药市中南北“药帮”之间商业关系存在竞争性,而当地“箭射龙头”(141)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的传说,折射出祁州药市对利益冲突的平衡,为南北药帮持续协作,保持药市的长期繁荣发挥着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本土药帮凭借地理优势,从事黄芪的加工销售,兼营中介、代购等药材贸易服务,为祁州药市发展提供宽敞的交易场地和良好的经营环境。关东帮为祁州药市提供的货源,占据祁州药材总量的半壁江山。财力雄厚的山西帮,则为祁州药材贸易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其他各地药帮,在药材的对外购入、销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代汇聚祁州的各地“药帮”之间,在合作与竞争中,不断调适各自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协作共同推动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与繁荣。
结 语
明清时期,随着药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药材交易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大,部分区域性药材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向全国性药材市场演进。祁州药市至清代中期已形成全国性药材市场。就其形成路径而论,以药会活动为“平台”,使祁州成为群集聚会之地,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中心”(142)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促进了祁州药材市场声名的传布,在各级官府和地方药商的推动下,祁州药会“天下驰名”(143)嘉庆九年《重修皮王阁神碑记》。,从而吸引更多各地药商巨贾汇集于此。为凝聚各地药商共识,明清时期祁州地方官员和本土药商,对“药王”形象展开了持续性建构,最初由地方州牧借助皮场王“医秦王”之事,为药王的本土化建构作了较好的铺垫,并于明万历年间完成了药王的“在地化过程”(144)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为与鄚州药市竞争,清代道光年间地方药贾,把药王视为“神农”(145)道光二十二年《重修皮王阁神碑记》,《安国县志》,第1034页。,而光绪年间再次搬出汉将“邳彤”(146)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药王形象的持续化建构,大都以凝聚药商、发展药市为目的。
不同区域的药业商贾,在思想、习俗等方面互有差异。为稳定商贾,繁荣贸易,清代祁州本土药商凭借家族势力,充分利用“安客堂”“捐款碑”和“名医殿”等场所,进行全方位的“规训”,借助支配空间进而影响个体,从而实现对整个药市发展的“掌控”和“规范”。明清时期各地“药帮”,对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祁州本土药帮和经纪人在药材交易场地和经营环境、中介服务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关东帮所贩运的关外药材和山西帮的金融优势,解决了祁州药市的货源和资金问题,而其他各地药帮,在各地药材的购入和分销方面作用显著。汇聚祁州的各地“药帮”,在合作与竞争中,共同推动了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