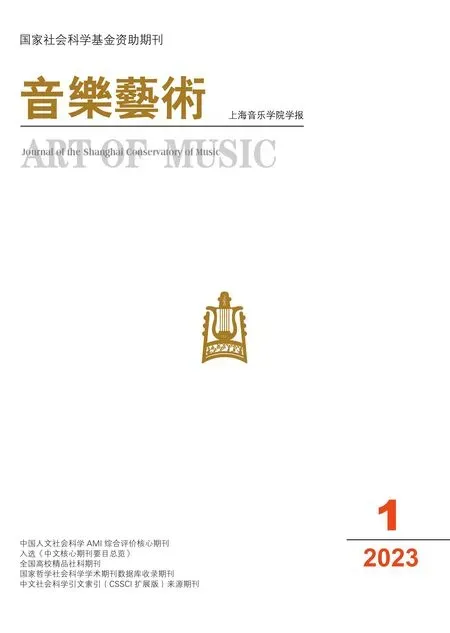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与儒墨音乐思想
方建军
内容提要: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涉及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和楚国礼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文为范戊答楚王所问,其间以白玉为譬喻、以音乐事例向楚王进谏。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知,范戊主张维护传统礼乐等级制度,按个人身份地位享用相应的乐器配置或乐队构成,其音乐思想应属儒家学派。楚王并不尊奉传统礼乐规范,重鬼神而轻人事,其思想和主张应属墨家一系。既有楚地出土战国文献,所展露的音乐思想多属儒道,但《君人者何必安哉》说明战国时期墨家音乐思想在楚地也有流传,这为先秦时期诸子音乐思想在楚国得以交流发展的论断增添了新的例证。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辑中,有一篇题名为《君人者何必安哉》①的简文,内容涉及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和楚国的礼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篇出土文献共有九支竹简,分为甲、乙两本,文字基本相同。简文主要以君臣对话的形式,叙述范戊(范乘)答楚王所问,其间以白玉作为譬喻,举音乐事例向楚王进谏。目前学术界对此已有较全面的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仔细绎读这篇文献,可以发现其中蕴含儒墨两家之音乐思想。本文补释简文的有关字词,结合传世文献,探究简文所反映的儒墨音乐思想。
一
关于简文《君人者何必安哉》的隶定和读释,黄蓓②、蔡树才③、米雁④、曹方向⑤等多位学者均撰有论文予以综述和集释,并均有十分精当的见解。
《君人者何必安哉》全文如下:
范戊曰:“君王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命为君王戋之,敢告于见(视)日。”王乃出而见之。王曰:“范乘,吾倝(曷)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哉?”范乘曰:“楚邦之中,有食田五贞(顷),竽瑟衡于前,君王有楚,不听鼓钟之声,此其一回也;珪玉之君,百贞(顷)之主,宫妾以十百数,君王有楚,侯子三人,一人杜门而不出,此其二回也;州徒(土)之乐,而天下莫不语,先王之所以为目观也,君王龙(隆)其祭而不为其乐,此其三回也。先王为此,人谓之安邦,谓之利民。今君王尽去耳目之欲,人以君王为驭以嚣,民有不能也,鬼无不能也。民乍(作)而甶讙之,王虽不长年,可也。戊行年七十矣,言(然)不敢睪身,君人者何必安哉?桀、受(纣)、幽、厉戮死于人手,先君灵王乾溪云(殒)尔,君人者何必安(然)哉?”
以下对简文中的部分字句进行说明和解释。
(1)“君王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其中的“回”,濮茅左认为是量词,意同“块”⑥。其中的“戋”见于楚简,如1957年发掘的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所出竹简中有“戋人”一词(简1—01、1—02)⑦。“戋”读为“贱”,“戋人”即“贱人”。本简中“戋”字读为“践”,与“贱”同音;“践”与“残”亦通⑧,因此两者均有残伤之意。如《释名· 释姿容》曰:“践,残也,使残坏也。”⑨《庄子· 马蹄》云:“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⑩其中“残”“毁”对文,文义近同。《说文》训“毁”为“缺”,段注:“缺者,器破也。”⑪此句大概意思是,楚王有白玉三块,但未加工制成礼器。范戊所言楚王有白玉三“回”,但并非实有白玉,而是以白玉比喻楚王所具备的三重美德。古人常以玉喻德,如西汉贾谊所讲:“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象德体六理,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⑫不过,范戊虽然称赞楚王有白玉般的美德,但转而指出白玉只是制器的良材,需“践之”(即加工)才能成为礼器,随后又列举楚王的美中不足,以委婉的方式讽谏。
(2)“竽瑟衡于前”。“竽瑟”联为一词,传世文献屡见,如“竽瑟狂会”(《楚辞· 招魂》)⑬、“陈竽瑟兮浩倡”(《楚辞· 九歌· 东皇太一》)⑭、“竽瑟之乐”(《墨子· 三辩》)⑮、“铄绝竽瑟”(《庄子· 胠箧》)⑯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遣策亦记有“楚竽瑟”和“郑竽瑟”⑰,均在乐器名称前冠以国(地)名。
(3)“不听鼓钟之声”。“鼓”是动词,意为演奏、敲击。如《诗经· 小雅· 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⑱又如编钟铭文中常见的“永保鼓之”“其永鼓之”。1984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出土的西周晚期井叔采钟,铭文也有“永日鼓乐兹钟”⑲,此处的“鼓”,应仅就击奏编钟而言,非指“鼓”和“钟”两种乐器。简文中的“鼓钟”,当为“钟鼓”之倒置。《诗经》《楚辞》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诗经· 周南· 关睢》:“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⑳《诗经· 唐风· 山有枢》:“子有钟鼓,弗鼓弗考。”㉑《楚辞· 招魂》:“陈钟按鼓,造新歌些。”㉒因此,简文中的“鼓钟之声”与《孟子· 梁惠王下》中“钟鼓之声”㉓和《墨子· 三辩》中“钟鼓之乐”㉔的文义相同。
(4)“州徒之乐”。“徒”读作“土”,“州徒”即“州土”,孟蓬生㉕、林文华㉖、周凤五㉗、黄人二㉘等均曾提出。《楚辞· 哀郢》:“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㉙其中的“州土”与简文相同,均指楚国本土。“州土之乐”即楚国当地的民间音乐。《左传》成公九年记述楚国乐官锺仪抚琴奏乐时“操南音”,且“乐操土风”㉚,其演奏的乐曲呈现出楚国的本土音乐风格。
(5)“而天下莫不语”。董珊先生认为,“语”读作“娱”㉛,有娱乐之意。笔者私见,“语”如《说文》,训为“论”㉜,有谈论之意。此句大意为,“州土之乐”这类地方性的民间音乐,大家都知晓且耳熟能详。
(6)“先王之所以为目观也”。“目观”不仅是观看“州土之乐”,其中还有体察风土民情之意。周代有采风制度,即从民间采集歌谣,体察风俗民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先王要通过“州土之乐”,了解和体察民众的状况。
(7)“君王龙(隆)其祭而不为其乐”。“隆”有丰盛之意,《说文》:“隆,丰大也。”㉝《礼记· 经解》:“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郑玄注:“隆礼,谓盛行礼也”㉞。“乐”指祭祀中的奏乐。此句大意为楚王盛其祭祀,但并非为了祭祀仪式中的音乐表演。
(8)“人以君王为驭以嚣”。张崇礼先生认为,“驭”是“驭人”之“驭”的专字㉟,可从。《说文》未收“驭”字,但在“御”下有云:“驭,古文御”㊱。“御,治也”,见《国语· 周语上》“百官御事”三国韦昭注。㊲《周礼· 天官· 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㊳。“驭”有统治之意,“以”意为“而”。3“9嚣”有“自得无欲之貌”之意,见《孟子· 尽心上》“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之注疏。㊵此句简文的大意是,人们会认为,君王为了控制民众而故作寡欲。
(9)“民乍(作)而甶讙之”。“乍”读为“作”,指“劳于农事”。㊶如《商君书· 算地》:“兵休,民作而畜长足”㊷。“甶”读为“使”㊸,“讙”读为“欢”㊹。此句意思是,让人民劳作,并使之得到欢乐。
(10)“ 王虽不长年,可也”。“长年”意为高龄㊺或长寿㊻。此句意为王虽没有长寿,也不必在意。《墨子· 明鬼下》认为,鬼神可以“赏贤而罚暴”,因而祭祀诸神能够“以延年寿”,“若无鬼神,彼岂有所延年寿哉”㊼。范戊的真实用意是奉劝楚王不必“隆其祭”而祈求长寿,忽视民众的需求。上博五《鬼神之明》云:“昔者尧舜禹汤,仁义圣智,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长年有誉㊽,后世遂之。”又云“:荣夷公㊾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㊿其中的“长年”均有长寿之意。
(11)“戊行年七十矣,言(然)不敢睪身”。“言”读为“然”,“睪”读为“斁”,训为“厌弃”51。如《诗经· 周南· 葛覃》中的“服之无斁”,郑玄笺:“斁,厌也”,“乃能整治之,无厌倦”52。这句的大意是,范戊虽年届七十,但仍不敢放逐自身应遵循的礼乐规范。
根据上述字句释义,将简文试译如下:
范戊说:“君王您有白玉三块而没有加工成器,今请为君王加工成器并告知您。”于是楚王就召见他。楚王说:“范乘,我哪里有白玉三块而没有加工成器呢?”范戊答道:“楚国之内有田亩五顷者,有乐人将竽瑟置于座前为其演奏;君王您拥有楚国,却不听钟鼓之乐,这是第一块。拥有珪玉和田亩百顷的君主,宫内妻妾几十上百;您作为楚国君王,仅有妻妾三人,且一人闭门不出,这是第二块。楚国本土的民间音乐,为民众所熟知,先王也以此来体察风土民情;但君王用乐只为祭祀而不为其中所奏之乐,这是第三块。先王所为,人们称其为国家安定和人民获利,如今您全然去除声色之欲,人们便会认为您是为了控制民众而故作寡欲,并认为民众有所不能,而鬼神则无所不能。人民劳作并从中得到快乐,王虽然没有长寿,也不必在意。我范戊已经七十岁了,尚且不敢放弃自身应遵循的礼乐规范,作为统治人民的君王,又何必如此呢?夏桀、商纣、西周幽王和厉王均为人所杀,楚国的祖先楚灵王死于乾溪之地,作为统治人民的君王,又何必像他们那样呢?”
二
《君人者何必安哉》虽为范戊与楚王的对答,但其中楚王仅有一问,其余皆为范戊自述。
范戊所称楚王白玉般的三重美德,一是指拥有“食田五顷”者享受竽瑟之乐,而楚王乃一国之君,却不听钟鼓之乐。二是指拥有珪玉和百顷之田的诸侯国君都妻妾成群,而楚王仅有妻妾三人,且有一人杜门不出,说明楚王不沉迷女色。三是指作为地方民间音乐的“州土之乐”,不仅为民众喜闻乐见,而且先王也参与“目观”,以此体察风俗民情,但楚王用乐只重其祭祀仪式,而不关注其奏乐。范戊所言“鼓钟之声”“竽瑟衡于前”“州土之乐”,遵循基于等级制度的传统礼乐规范,但楚王则反其道而行。
类似的记述见于《墨子 · 三辩》: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53
文中也有三种不同层次的音乐。前两种按官职大小和地位高低,由诸侯至士大夫逐次享有礼乐制度所规定的乐器配置,即是程繁所说诸侯级的“钟鼓之乐”和士大夫级的“竽瑟之乐”。至农夫阶层,限于财力和身份,只能以“瓴缶之乐”作为娱乐手段。
《墨子· 三辩》中的三种音乐,与范戊所谓“鼓钟”“竽瑟”和“州土之乐”相对应。简文中“食田五顷”者,享有士大夫级的“竽瑟之乐”;拥有“珪玉”和“百顷之田”者,虽未明示其职官和所享用的音乐,但实际应为诸侯一级,着重说明其妻妾“以十百数”计。《淮南子· 道应》:“子发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54这与简文“百顷之主”和“珪玉之君”相对应。程繁和范戊谈论的三种音乐,包含相应的乐器配置或乐队构成,均为儒家所尊奉的礼乐规范,也是简文中范戊的主张和倾向。乐器作为礼乐制度的物化形态,并非人人皆可得到并享有,而是要与个人的身份、等级相对应。这种思想观念与孔子“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55的儒家学说吻合。
范戊和程繁所说的“钟鼓之乐”,是以钟、鼓两种乐器为表征,而实际所用乐器并非仅此两种。考古发现表明,东周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一般都有编钟和编磬随葬,形成礼乐制度的最高物质形态—金石之乐。此外,墓葬中还有不同种类的弹弦乐器和吹奏乐器,著名实例当属楚地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
同样,“竽瑟之乐”也以竽、瑟作为标志性乐器。竽和笙同属自由簧编管气鸣吹奏乐器,如《吕氏春秋· 仲夏纪》高诱注:“竽,笙之大者,古皆以瓠为之。”56因此“竽瑟之乐”中的竽有时用笙代替。战国时期大夫级的楚墓,少见仅随葬竽、瑟两种乐器者,一般有其他乐器随葬,可见“竽瑟之乐”的乐队编制和规模较为可观。如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墓主人为大夫,出土乐器有编钟、瑟和鼓,同墓所出遣策还有“二笙,一竽”(2—03简)的记录。57又如,1971年湖南长沙浏城桥战国楚墓M1,出土有笙、瑟、鼓、木角等乐器,墓主人为下大夫。58
《墨子· 三辩》所言农夫阶层的“瓴缶之乐”,是以瓴、缶之类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作为乐器。这与范戊所言“州土之乐”一样,同属民间音乐。《说文》曰“:瓴,瓮,似瓶也。”“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59《史记· 李斯列传》云“: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60由此可知,缶确曾作为击奏乐器流行于民间。2004年,江苏无锡鸿山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墓出土有瓷缶,同出土的乐器还有瓷制的编钟、编镈、编磬、句鑃、錞于、钲、鼓(座)等。61这也说明,缶不仅流行于北方秦国民间,也被用于南方古越国贵族阶层的音乐表演。
诸侯国君享用的钟鼓之乐,在乐器配置和乐队规模上优于大夫。诸侯所用乐器除钟磬外,可向下兼容,包含多种乐器,而低职级者可享用的乐器则依次递减。如大夫一级所用乐器品种和数量比诸侯少,士一级仅有琴瑟之类的弹弦乐器。目前发现的墓主身份相当于士人的墓葬,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中期楚墓,62该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底部铭文“东宫之师”,即楚太子之师,63同出土的竹简,可能是供其教学所用。该墓出土乐器仅有一张七弦琴,未见其他乐器随葬,可见士大夫级的“竽瑟之乐”是泛称,具体到士人可能仅有琴瑟之类的弹弦乐器。
据《礼记· 曲礼下》记载,“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64所谓“君无故玉不去身”,与范戊所说的“珪玉之君”似可比附;“大夫无故不彻悬”,“悬”是由编钟和编磬构成的“乐悬”;“士无故不彻琴瑟”,大约是说士人将琴或瑟作为独奏乐器,其主要功能当如《庄子· 让王》所说,“鼓琴,足以自娱。”65可见,士人弹奏琴瑟的主要目的是娱己,其次才是娱人。
三
由范戊所述楚王的行事不难看出,楚王并非遵守传统的礼乐等级制度,而是“不听鼓钟之声”,这与《墨子· 非乐上》所言“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66相符,可见楚王受墨家“非乐”音乐思想影响之深厚。
范戊说楚王“隆其祭而不为其乐”,并不是说祭祀仪式中没有音乐,周代祭祀中均用乐,楚王也不例外,但其重祭祀本身,即“隆其祭”,将音乐置于次要地位,但并未尽弃音乐。这里的“不为其乐”,与《墨子· 三辩》反复强调的“圣王不为乐”相当。在《墨子· 三辩》末章,墨子分别列举尧舜、商汤和西周武王、成王时代的礼乐,并以《濩》《韶》《象》《驺虞》等具体曲目为例,说明“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由此得出结论,圣王“有乐而少,此亦无也”67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乐非所以治天下”,楚王不听钟鼓之乐,恐怕是受墨家音乐思想的影响,进而与《乐记· 乐本》“声音之道与政通矣”68的儒家音乐观相对立;二是先王并非没有音乐,只是“有乐而少”,即便是“无乐”,也从另一面体现出了“圣王不为乐”的思想。因此,简文中的楚王,盛其祭祀而“不为其乐”,与墨家“圣王不为乐”和“有乐而少”的观念一致。
正如《左传· 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9,祭祀和战争同为国家的头等大事。由此可知,楚王的“隆其祭”固然无错,但范戊的意思是,虽然盛大的祭祀仪式很好,但也不要忽略其中的音乐。在先秦传统礼乐观中,制作乐器的目的除祭祀祖先神明之外,还有娱乐众生。如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M2出土的王孙诰编钟,其铭文便有“王孙诰择其吉金,自作和钟……用宴以喜,以乐楚王、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70。因此,祭祀仪式中的音乐,不仅能娱神,也可娱人。
范戊还指出,楚王只重视祭祀,而忽略祭祀中的音乐,人们会认为“民有不能”,而“鬼无不能”,这会导致楚王与民众疏离。楚王的行为与《墨子· 公孟》所批评的“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的儒家鬼神观不同,而与同篇所说的“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71和《墨子· 明鬼下》中的“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72相合,反映出楚王的墨家鬼神观。
楚王重鬼神而轻人事,希望通过祭祀鬼神而延年益寿,这属于墨子的鬼神观。墨子认为,鬼神能够赏善罚暴,善者可以长寿。但范戊提倡儒学思想,主张重民生尽人事,故言王虽不长寿,却可得到人民的尊重爱戴。其见解在简文中体现为“民作而使欢之,王虽不长年,可也”。这与《墨子· 三辩》中“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的表述相通。
在简文中,范戊将楚国先王与当世楚王作比较,认为先王所为是“安邦”和“利民”,为世人所称道;而楚王“尽去耳目之欲”,不近声色,人们会认为楚王是为了控制民众而有意为之。所言“尽去耳目之欲”,初看似与老庄音乐思想接近,如《老子》十二章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73,以及《庄子· 天地》中的“五色乱目”和“五声乱耳”74。但这只是范戊的看法,实际上楚王并非禁欲,而是寡欲,并未尽弃声色,而是“有侯子三人”,且在祭祀仪式中有音乐伴随,表明其音乐思想不是道家所奉行的“虚静”,而是墨家一系。
简文末尾,范戊还以桀、纣、幽、厉被人所杀为警戒,重申作为统治者的君王,其行为必须合乎传统的礼乐行为规范,但不可纵情声色。范戊所说的夏商周三代暴君,在音乐上均极尽奢靡荒淫。如《墨子· 公孟》所说,“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戮。”75其中尤以桀、纣为甚,如《吕氏春秋· 侈乐篇》曰,“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76《管子· 轻重甲》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譟于端门77,乐闻于三衢。”78《新序· 刺奢》曰:“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隄,纵靡靡之乐。”79《史记· 殷本记》也记述了商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80。
楚国的先君灵王,同样极尽声色之欲,筑章华之台,“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81。不仅如此,其“视侈、淫色”“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82,后败绩于乾溪而丧命。范戊以三代暴王和楚灵王为反例,劝谏当世楚王,言下之意为:君王您不必如此寡欲,要奉行符合等级制度的礼乐规范,这样才不会脱离民众,避免落得被戮死的下场。
全篇简文,范戊对楚王先颂后谏,奉劝楚王维护传统礼乐制度,体察风土民情,与民同乐。《孟子· 梁惠王上》云:“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又有《孟子· 梁惠王下》云:“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83以此对照,范戊应是儒家礼乐思想的维护和倡导者,而楚王则奉行墨子“非乐”“圣王不为乐”“有乐而少”的音乐思想。综而观之,范戊是兼通儒墨思想且富有学识的人物。孙诒让曾指出,《墨子· 三辩》中的程繁“盖兼治儒墨之学者”84。这与简文中范戊的情形十分相似,但两人都倾向于维护儒家的礼乐传统。
以往楚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文献,如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主要是关于儒道音乐思想的典籍。85但上海博物馆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的记述表明,墨家音乐思想在楚地也有影响和流传。墨子曾到楚国向楚惠王献书,传播其思想学说。《文选注》(卷三)十引《墨子》佚文:“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86由此可知,在楚地发现包含墨学音乐思想的简册佚籍并非偶然,这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在南方楚国交流发展的论断增添了新的例证。
注释: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89—218页。
② 黄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七)文字集释评述》,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③蔡树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文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④ 米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综合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⑤ 曹方向:《上博简所见楚国故事类文献校释与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⑥ 同①,第194页。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第125页。
⑧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上博七· 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见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80,浏览时间:2022—09—08。陈伟:《君人者何必安哉初读》,见简帛网,http://www.bsm.org.cn/?chujian/5123.html,浏览时间:2022—09—08。
⑨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第118页。
⑩ 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第333页。
1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25页。
12 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18页。
13 王泗原:《楚辞校释》,中华书局,2014,第146页。
14 同13,第221页。
15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第35页。
16 同10,第355页。
17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第51页。
1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467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86年第1期。
20 同18,第274页。
21 同18,第362页。
22 同13,第145页。
23 同18,第2673页。
24 同15,第35页。
25 孟蓬生:《〈君人者何必安哉〉賸义掇拾》,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见http://www.fdgwz.org.cn/Web/Show/611,浏览时间:2022—09—10。
26 林文华:《〈君人者何必安哉〉“州徒之乐”考》,简帛网,见http://www.bsm.org.cn/?chujian/5178.html,浏览时间:2022—09—09。
27 周凤五:《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新探》,载《台大中文学报》,2009年第30期。
28 黄人二:《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试释》,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6期。
29 同13,第169页。
30 同18,第1905—1906页。
31 董珊:《读〈上博七〉杂记(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见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85,浏览时间:2022—09—09。
32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1963,第51页。
33 同32,第127页。
34 同18,第1610页。
35 张崇礼:《〈君人者何必安哉〉释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见http://www.fdgwz.org.cn/Web/Show/651,浏览时间:2022—09—07。
36 同32,第43页。
37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第18页。
38 同18,第646页。
39 同31。
40 同18,第2764页。
41 苏建洲:《〈君人者何必然哉〉劄記一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见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91,浏览时间:2022—09—07。
42 石磊译注:《商君书》,中华书局,2011,第57页。
43 同31。
44 季旭昇:《上博七刍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见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88,浏览时间:2022—09—07。
45 单育辰:《占毕随录之七》,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90,浏览时间:2022—09—07。
46 同28。
47 同15,第219页。
48“ 誉”字原释“举”,此从廖明春所释,详参廖名春《读〈上博五· 鬼神之明〉篇札记》,载孔子2000网“清华简帛研究”专栏,发布时间:2006年2月19日。
49 李家浩、杨泽生释“荣夷公”为“秦穆公”,见其所著《谈上博竹书〈鬼神之明〉中的“送矛公”》,载《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77—185页。
50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16页。
51 林文华:《〈君人者何必安哉〉“言不敢睪身”考》,简帛网,http://www.bsm.org.cn/?chujian/5180.html,浏览时间:2022—09—07。
52 同18,第276页。
53 同15,第35—36页。
54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298页。
55 同18,第1894页。
56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49页。
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第128页。
58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59 同32,第269、109页。
60 司马迁:《史记》(卷87),中华书局,1959,第2543—2544页。
61 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第276—279页。
62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载《文物》,1997年第7期。
63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4—186页。
64 同18,第1259页。
65 同10,第1143页。
66 同15,第227页。
67 同15,第36—38页。
68 同18,第1527页。
69 同18,第1911页。
7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第142页。
71 同15,第417、421页。
72 同15,第214页。
73 辛占军:《老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第46页。
74 同10,第462页。
75 同15,第418页。
76 同56,第269页。
77 郭沫若等:《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第1186页。
78 《管子》卷二十三,载《四部备要》第52册,中华书局,1936,第198页。
79 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第790页。
80 同60,第105页。
81 范晔:《后汉书》(卷80下),中华书局,1965,第2640页。
82 同37,第493—494页。
83 同18,第2666、2674页。
84 同15,第35页。
85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86 李善等:《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第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