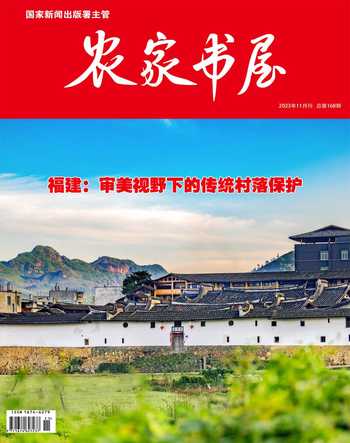《1937,延安对话》: 延安的国际交往
张洪
80多年前,斯诺、史沫特莱等访问延安,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笔录《毛泽东自传》在《亚细亚》月刊连载,1937年出版了《西行漫记》,两个月内印行五次,东方革命广为传播。域外记者、作家的大胆举动和健笔所书,点染出中华民族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彩画卷,一直为读者追捧研读。《西行漫记》第一个中文译本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距离其纽约版问世只有一个月时间。胡愈之策划组织林淡秋、梅益等十余人精诚合作,以复社名义出版,半年内连印五次,销量近十万册。新加坡、菲律宾等华人聚居地也出现了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进入新时代,董乐山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推出,几年内创下销售1400万册的斐然业绩。
红色心脏延安,当年“中国特区”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总后方,企盼亲眼目睹甚至投身根据地洪流之中的中外人士何其多也,圣地让人朝思暮想,代表希望,充满神秘,象征未来,期待走出新路的英才俊杰将雄心壮志托付其间,长啸高唱,慨当以慷,奔向光明。两位来自美、苏的30多岁年轻人托马斯·亚瑟·毕森和罗曼·卡尔曼,分别于1937年、1939年到访延安和边区。虽然不到一周和一个月时间,他们用文字和影像描摹所见所闻,后来发行了英文、俄文专著。如此珍贵的图书,直到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上半年才与中文读者见面,比当年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化名《西行漫记》,由胡愈之等人翻译出版整整晚了八十多个春秋。
《1937,延安对话》和《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1938—1939)》两部作品,字数一二十万字,图片几十幅,看似寻常,却内涵厚重。前者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陈晋作序推荐,后者由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独立译出。好书为庆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它们在国际标准书号检索体系下,代码分别为中国的01和02号,当此盛时,位置、分量可见一斑。
独家现场采访,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延安保育院、鲁迅艺术学院,这些“标配式”安排应该是外访者必到之地,“昔日文小姐”丁玲和她的女儿也是频繁上镜的明星。卡尔曼和毕森的神来之笔妙手偶得,留下了路边农民扛着锄头与毛泽东聊天侃笑的镜头,记录下朱德主持指挥员培训时邀请几位美国友人当众演讲。毕森终生难忘,当时面对数百名军人说过一句话:“在延安,我们是站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心。”
两本著作中的领袖群像,最为聚焦的是毛泽东讲述的话题与故事,预见远见,剖析解析,谈笑风生中,边区政治与天下大势系于一处,遥相呼应,生死攸关。中外双方关注的不只是国共和中日间的纷争,还有英法德美苏联西班牙诸多全球背景与格局。“笼罩着勇敢、不屈不挠意志、英雄主义、最平易近人等传奇光环”的毛泽东坚信,“不应孤立地看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阅读原始文献,追忆过往,延安与领袖、边区和世界的景象视野变得立体丰盈,大道多维。
陳晋将毛泽东的身份跨越锁定在三个时间点上,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冯友兰从中国历史大背景下概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后来成“君”成“师”。龚育之介绍毛泽东写作和读书时得出的观点,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在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斯诺和毕森、卡尔曼大感兴趣那些马克思主义词汇。部队和后方中大胆从事军事工作的红小鬼,“从遥远的延安窑洞里面,毛泽东甚至变成了一位世界人物”,他的论断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更有如上评估。从斯诺镜头中的红小鬼,到斯特朗笔下的“纸老虎”,延安和毛泽东创造的新奇词汇,看似小品,实乃大作,终成通行畅达的全球话语。
延安十余年,外访者刊行的篇章历历在目,臻妙入胜,洵为依据。不管是惊鸿一瞥,还是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撰写了多篇文章的爱泼斯坦那样与中国永远不离不弃,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与领袖们对话之后,他们大都成为亲华爱华人士、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者。无论身处顺境逆势,矢志不渝促进中外交流国际友谊成为共同的信念和坚实行动。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女记者史莱特莱深入采访朱德,写出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美国记者福尔曼原本对国共不持明确立场,去延安后改变了原先对中共的怀疑看法,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对外声明中大力称颂中共抗战出色表现及其与人民的亲密关系。1938年3月28日,白求恩和护士尤恩到达延安。当日午夜,毛泽东与其会见。三天后,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会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与毛泽东长谈八小时,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提出的“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印象尤深,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次受到积极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中共中央对这些外国记者和人员来访高度重视,不是把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动,而应当把这看成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1960年,斯特朗回忆,十几年前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休息时,毛泽东与美方记者汉森聊起美国大选的可能结果,回答中共要实现什么形态的民主时,深谙西方观点的他从理论上阐述:“中国民主政府将与西方四个民主国家(英、法、苏、美)非常类似,但政策必须有利于中国广大人民,这种政策必须要比英美更开明。”一切工作的试验在延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从这里开始建立。
毕森和卡尔曼作品中的细节耐人寻味,他们观察中外两位司机与毛泽东同桌吃饭,共同交谈的实景:江西小伙子顾保申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激动得无法抑制忐忑不安的内心;瑞典的“中国通”艾飞·希尔被毛泽东盛邀留延安工作,他在中国出生长大,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正如卡尔曼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和朗诵词杂糅到一处,怒吼咆哮“发出英勇的叫啸”,呐喊与歌唱难能可贵地水乳交融,力道、强度,与雄奇壮美集于一身,永远向着全中国,向着全世界。斯诺和卡尔曼都得到了毛泽东手书的七律《长征》,人民领袖讴歌一个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歌,“将是我从中国带回的最珍贵礼物”。
(来源:《沈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