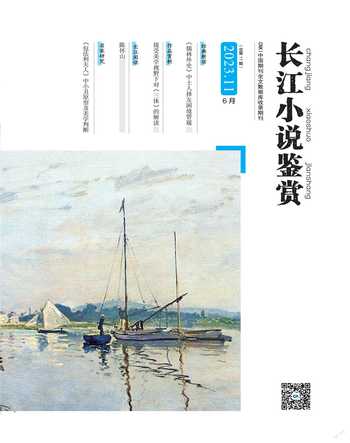以福柯的空间理论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摘 要] 《霍乱时期的爱情》作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小说,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关注。这部小说不仅有常规的时间叙事手法,还利用空间转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本文运用福柯异质空间理论分析在妓院、镜子前以及“新忠诚号”轮船里人物情感的转变;运用空间规训理论分析主人公在不同空间下受到的规训;运用权力空间理论分析作品中空间的转换给人物权力带来的变化,进而分析主人公的性格形象,深入挖掘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方式以及寄托的情感。
[关键词] 异质空间 空间规训 权力空间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28-05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时间和空间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同,流动且灵活的时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而空间则被认为是刻板静止的,学界忽略了对空间的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空间都受到时间的束缚和压制,难以显示出自身的魅力和价值。直到20世纪,空间才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被纳入新的研究视野中。理论界对空间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多样,其中,福柯的“空间规训”和“异质空间”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等都在空间理论的建构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福柯在《关于其他空间》中曾断言:“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基本上主要与空间相关,而与时间无甚关联。”[1]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越来越重视对空间的研究,文学领域的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将空间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小说创作中经常将时间进行碎片化处理,他并不按照常规的叙事时间来写作,而是通过模糊或淡化时间来凸显空间的重要性,用空间的转化推动叙事进程。《霍乱时期的爱情》作为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叙事作品,受到了世界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小说将时间设定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并以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间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永恒爱情故事。在小说叙述的时间顺序上,马尔克斯采用倒叙加顺叙的写作手法,但他有意淡化时间信息,用人物视角转变以及空间转换的叙事手段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使整部小说带有很强的空间叙事色彩。
本文试图以福柯的异质空间、空间规训和权力空间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来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异质空间、空间规训和权力空间都是社会真实存在的现象,本文用真实存在的异质空间来分析主人公乌托邦似的幻想,真实中存在着某种不真实的因素;用空间规训和权力空间分析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发现小说中的真实与虚幻形成了呼应,从而更加深入理解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以及寄托的情感。
一、异质空间中的绝望与希望
福柯在1967年的演講稿《不同的空间》中提出了“异质空间” 这一概念。异质空间又称为“异托邦”。异质空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空间,在社会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相对其他空间来说是较为特殊的社会空间。福柯认为异质空间对其他空间有幻觉性和补偿性。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妓院作为一个异质空间,对于弗洛伦蒂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妓院是他认知爱情和渴望得到美好爱情的一个幻想空间。在他看来,妓院不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那些裸着身子的女人也不是一群没有良知的人。妓院反而是他摆脱孤独的一片净土,那些女人甚至可以算他的知心朋友。“自从认识费尔明娜·达萨以来,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自在了,因为这儿是唯一不让他觉得孤独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最终成了唯一能让他感到仿佛和她待在一起的地方。”[2]可以看出,虽然当时他对爱的理解还处于朦胧状态,但他认为爱情是美好且纯真的,即使身处在混乱不堪的妓院中,他也同样对纯洁的爱情抱有强烈幻想。其次,对于青年时期的弗洛伦蒂诺来说,妓院不是他人认为的寻欢作乐、放纵自我的场所,而是一个将自己封闭起来疗伤的异质空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呢,由于他沉默寡言,且性格难以捉摸,也受到旅馆主人的青睐。在那些最痛苦艰难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旅馆闷热的房间中,朗读催人泪下的诗歌或连载的爱情小说。他的梦幻在阳台上筑起黑燕子的巢穴,在午睡的昏沉中留下亲吻和扇动翅膀的窸窣。”[2]在妓院这一充满幻想的异质空间里,他反而更能直面自己的内心,而且在这样的空间下,他不仅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来这里的其他人也可以将秘密说给别人听,毫无避讳。因此,妓院相较于其他现实空间来说更为真实,更能让人直面人与事,相反,真实空间却充满了谎言与虚幻。
“福柯认为,异质空间通常和时间的片段性相关。这样就将异质空间和异质时间联系在一起……在某些异质空间形态中,时间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动。时间或加速推进或倒转回溯或凝滞悬停,呈现出与异质空间相应的不同形态。”[3]在小说中,“镜子”便是这样一个将异质时间与异质空间联系起来的意象。在镜子中,弗洛伦蒂诺将转瞬即逝的美好时间状态凝滞成为永恒。“他在餐厅尽头的大镜子中看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和丈夫以及另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边,从他这个角度正好能在境中欣赏她那迷人的风姿。她举止自如,优雅地与众人交谈,笑声就像烟火一样,在晶莹的大吊灯下,她的美更加光彩夺目:爱丽丝再次走入了镜中。”“他坐在自己孤独的桌子前,和她共度她人生的片刻。”[2]对于费尔明娜来说,那不过是片刻的停留,而对于弗洛伦蒂诺来说,便足以成为永恒。在镜子中,他忽视了周围的一切,只将心爱之人的一颦一笑珍藏于镜中。在镜子中,时间仿佛暂停,世界只剩彼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镜子挂到了自己家中,却并不是因为那镜框的精雕细琢,而是因为镜子里的那片天地,他爱恋的形象曾在那里占据了两个小时之久。”[2]可以说,等待费尔明娜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的半个世纪中,她是弗洛伦蒂诺精神的寄托,甚至是灵魂所在。所以,虽然镜子中不再出现费尔明娜的身影,但是在他看来,那面镜子里的世界也足以使他“狂欢”。
福柯从乌托邦的角度阐释“异托邦”。福柯认为乌托邦是不真实在场的空间,但是,在一切文化或文明中, 有一些真实而有效的场所却是非场所的, 或者说, 是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即为“异托邦”。弗洛伦蒂诺在镜子里,在一个非实在的空间里看费尔明娜,此时的费尔明娜处在并不真实在场的地方,即镜子里的乌托邦。但镜子也是一个“异托邦”,因为镜子是真实存在的。镜子里的费尔明娜在镜子平面上占据了一个位置,镜子为弗洛伦蒂诺提供了一个占据费尔明娜的场所,这是绝对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镜子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异托邦”。镜子既为弗洛伦蒂诺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世界,又提供了真实的空间。因此,镜子具有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双重属性。
“福柯认为在幻觉性和补偿性的两个极端的异质空间中存在着一些中间状态的空间形式,一些不断流动着的‘空间片段(比如船)。在福柯看来,船‘只是一个漂移的空间,一个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地方,它孤独地存在着,自我封闭着,而且与此同时,还放任自己漫游于大海的无限之中。”[1]“船”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得知费尔明娜将嫁给乌尔比诺医生后,弗洛伦蒂诺心灰意冷,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在母亲和叔父的干预下,他踏上了疗伤之旅,此时的航船将弗洛伦蒂诺带到远离伤痛的地方。他将自己封闭起来,孤独又疯狂地想念着费尔明娜。“他会给她写下一封封伤心欲绝的信,而后,任它们的碎片飘散在那一刻不停地向着她的方向奔流而去的河水之中。”“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的恋人。”[2]在疗伤之旅的航船上,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在这里他是孤独的。虽然轮船这个异质空间在不同的情节中依旧是封闭的,但它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他迟暮之年得到费尔明娜的爱时,流动的航船便不再是孤独的、封闭的,而是具有无限可能的、开放的和自由的。“新忠诚号”是弗洛伦蒂诺和费尔明娜新婚旅行的见证,船舱内的“总统舱”是他们新婚旅行中幸福的世外桃源。小说中的“新忠诚号”轮船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第三空间,是两位老人生命最后阶段全部的感情寄托,更充满着对彼此永恒的爱。当弗洛伦蒂诺为了费尔明娜不被外界所打扰,将轮船升起霍乱的黄旗时,他将“新忠诚号”变成了封闭、流动的“第三空间”。在这里,弗洛伦蒂诺丝毫没有之前旅行的绝望与消极的封闭自我,反而这里的封闭是积极的、充满爱与希望的。他们在无人打扰的轮船上,过着欢乐幸福的时光。当这异质空间即将返回现实空间时,弗洛伦蒂诺选择永远前行。“我们走,一直走,一直走,重回黄金港!”[2]他选择将这一空间保留下去直至永远。此时,“新忠诚号”轮船这一封闭的“第三空间”传达了马尔克斯的思考,即永恒爱情可包容一切。
无论是处于绝望的空间中还是处于希望空间中,都是弗洛伦蒂诺自己真实的体验与感受。即使处于像镜子这样的幻想空间中,他的绝望是真实的,希望也是真实的。因此,无论是妓院、镜子还是航船都是弗洛伦蒂诺的“异托邦”。
二、空间规训中的约束与自由
“在福柯笔下,‘规训一词被赋予特殊内涵,意指使用技术手段对个体加以干预、操控与塑造,使之变得恭顺而驯服。所谓‘空间规训,意指通过对空间的刻意为之的筹划、设置与构造,对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心悦诚服地屈从于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并逐渐蜕变为驯顺而高效的‘被规训的物种。”[4]也就是说,空间规训需要以具体的空间作为基点,来对个体的个性特点、情感思想以及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影响。空间规训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影响。《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无论是福音公园的老宅还是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对费尔明娜身心的管控与束缚都是毋庸置疑的。
生活在福音公园的老房子里,费尔明娜受到父亲对她生活和思想的约束与管控。父亲为了让女儿成为贵夫人,将自己的心愿和想法強加给费尔明娜,让她去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两个世纪以来,上流社会的小姐们都会到那里去学习相夫教子的艺术和职责”[2]。父亲不仅干预她学习的环境,还对她的言行举止甚至行为活动严加干涉,“她的身边总跟着那位独身的姑妈,而且她的言行举止处处表明,她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娱乐活动”[2]。在得知费尔明娜和弗洛伦蒂诺交往时,父亲更是强硬地阻止两人来往,“他说尽了各种好话来打动她,试图让她明白她这个年龄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厢情愿地希望能说服她退回那些情书,回到学校去,跪下来求得校方原谅。他还许诺说,到时他会第一个为女儿找一位配得上她的求婚者,让她得到幸福”[2]。虽然费尔明娜在身体上受到了父亲的规训,举止端庄得体,但在灵魂深处,她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但她最后还是接受了乌尔比诺医生的追求,听从父亲的安排,成为一名贵夫人。可以看出,在最后婚姻生活的选择上,费尔明娜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规训的影响。
在嫁到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后,费尔明娜受到了来自封建贵族礼教更严格的约束和规训,只能屈从于家族礼教。她被侯爵府各种规矩束缚着,甚至承受着人们对她不合规矩的行为的批评。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使她诅咒一切,家里的规矩习惯也让她无法适应。面对婆婆用“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2]等话语规训她时,她只能顺从,唯一争取到的也不过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费尔明娜不仅被侯爵府的各种规矩束缚着,在社会中,她同样被束缚着。她被封建礼教规训成一位举止优雅端庄的贵夫人。在外人面前,即使对婚姻不满,她也表现得和丈夫十分恩爱。在她看来世俗生活“其实不过是一套延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礼仪”[2]。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她的言行都符合规矩和礼仪,给外人留下幸福美好的印象。费尔明娜被贵族圈子约束着,即使最后她突破自我,与弗洛伦蒂诺踏上了新生活的旅程,但她依旧在乎别人的目光和想法,“她宁愿死,也不愿被那个圈子中的人发现她在丈夫刚去世不久就愉快地出门旅行”[2],只有在“新忠诚号”船升起霍乱黄旗后,她才感到安全。
因此,即使费尔明娜是一个充满个性、有着强烈叛逆性格的人,可无论是在修道院的老房子里、侯爵府中还是在公众面前甚至是在轮船上,她都无形中受到了传统道德、封建礼仪甚至社会流言蜚语的规训。
三、权力空间下的无权与掌权
“在福柯看来,权力既不在空间之外,也不在空间之内。权力决定人们处于怎样的生活空间之中,换言之,权力为人的现实生活定位。可见,权力始终是与空间相结合的,世界上不存在无权力的空间,也不存在无空间的权力。所以福柯说:‘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5]空间与权力相辅相成,只要有空间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空间是权力运行其中的场所,权力又能够对空间进行布置与安排,权力既凌驾于空间之上,又贯穿于空间之中。空间的存在,能够使权力更好地运作;同时空间中的权力也体现在对人的制约上。《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在不同的空间中受到不同权力的制约,同时在其他空间中,她又是有权力的统治者。因此,费尔明娜的身上更好地体现了空间与权力关系。
费尔明娜起初和父亲、姑母生活在福音公园的老房子里。在这座房子里,她的父亲是绝对的权力统治者。费尔明娜对父亲权力的反抗都无功而返,她在家中没有真正的权力。“而自从费尔明娜来到巴耶杜帕尔镇,弗洛伦蒂诺便得以和她频繁通信。”[2]在这里,“费尔明娜·达萨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成为自己的主人”[2]。在不同空间下,费尔明娜完成了从无权向有权的转换。直到重新返回老房子后,“费尔明娜·达萨已经不再是那个既受父亲宠爱又受他严加管束的独生女了,而变成了这个满是尘土和蛛网的王国真正的女主人”[2]。父亲将权力转交给费尔明娜,此时无论是话语还是权力在空间中都完成了一次转换,拥有权力也使费尔明娜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不同的定位。从老房子到巴耶杜帕尔镇再回到老房子,空间的转换更好地展现了权力的转换。
嫁给乌尔比诺医生后,费尔明娜再一次被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所束缚。“她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人家。”[2]面对刻薄的婆婆布兰卡夫人和无能的丈夫,她只能屈从于家族礼教,生活在婆婆权力的束缚下。布兰卡夫人的独裁与威严使费尔明娜内心更加孤独,被约束的生活使她窒息。在侯爵府,她没有权力展现个性,只能表明顺从。费尔明娜在侯爵府没有权力,直到“她住进拉曼加的新房子里,成了自己命运的绝对主人”[2]时,她才重新获得主导权。她对家里的各种事都有绝对权力,甚至在丈夫去世后,为了不在痛苦中沉迷,她极端地“将所有能让她想起亡夫的东西全部清出家门”[2],甚至不惜将贵重物品烧毁。虽然在拉曼加的新房子里,费尔明娜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她的生活也受到了丈夫的羁绊,没有自由。只有当费尔明娜准备离开现实的束缚前往“新忠诚号”时,她才真正实现了权力的自由。在上船之前,“她亲自安排了这次旅行的细节……半打棉制衣服、梳妆和洗漱用品、一双登船和下船时穿的鞋子,还有旅行中穿的家用拖鞋,此外别无其他:这是她一生的梦想”[2]。从侯爵府到拉曼加的新房子再到“新忠诚号”,空间的转换为费尔明娜权力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从侯爵府的无权到拉曼加的有权再到“新忠诚号”的真正做自己,马尔克斯将权力空间具体展开在人与建筑的空间配置之中。
与费尔明娜一样,弗洛伦蒂诺也受到权力的制约,也有从被权力束缚到获得权力的转变过程。在他成为航运公司董事长之前,一直受到自己叔父权力的制约,直到叔父将管理决定权交给他时,弗洛伦蒂诺才真正掌握了权力。他有权签署命令让“新忠诚号”升起霍乱的黄旗。他成了“新忠诚号”命运的主宰者,将船又重新驶回黄金港甚至一直走下去。相比费尔明娜和弗洛伦蒂诺来说,乌尔比诺医生权力的转换不是特别明显。他既是无权的又是有权的。在侯爵府,他顺从于贵族礼仪以及母亲的独裁,没有权力为自己和妻子辩护甚至无力反抗母亲的霸权,只能让自己变得顺从。然而,在社会大环境中,他又是有权的,他有着上流社会的高贵身份,使他有权让洛伦索·达萨进入高档的餐厅。他倚仗权势帮助其掩盖丑闻,逃避追责,远离是非之地。同时,乌尔比诺医生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他继承了父親的诊所,为人们看病,他成为人们身体的主宰者。他还有相当的权力来拯救破败肮脏的环境和无知愚昧的人们,改变社会落后的风貌。
总之,《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空间是权力实施的支撑点,权力通过空间得以显示自身,同时它又作用于每个人身上,并塑造个体本身。权力关系在不同空间中的表现也不同,对个人的塑造也不尽相同。
四、结语
《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经典的爱情小说中,空间对小说的叙事、人物的塑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运用福柯空间理论对小说进行了解读:运用异质空间理论分析了弗洛伦蒂诺在妓院、镜子前以及“新忠诚号”轮船上时不同的思想变动;运用空间规训理论对费尔明娜在不同空间下受到的潜移默化的规训进行了解读;运用权力空间的理论,分析了费尔明娜在不同空间下权力有无的转变过程,以及弗洛伦蒂诺和乌尔比诺医生在同一空间和不同空间中的权力转变。本文运用福柯的三种空间理论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以期为该小说的空间理论分析提供新的视角,帮助读者充分体会作者想要展示的真实复杂的爱情以及社会生活面貌。
参考文献
[1] 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M].杨玲,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0.
[3] 张一玮.异质空间与乌托邦——一种都市文化批评的视角[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6).
[4] 李赛乔,庞弘.空间规训——理解米歇尔·福柯空间理论的关键概念[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1).
[5] 潘乐.福柯空间思想演进过程探微[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姚晓宇,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