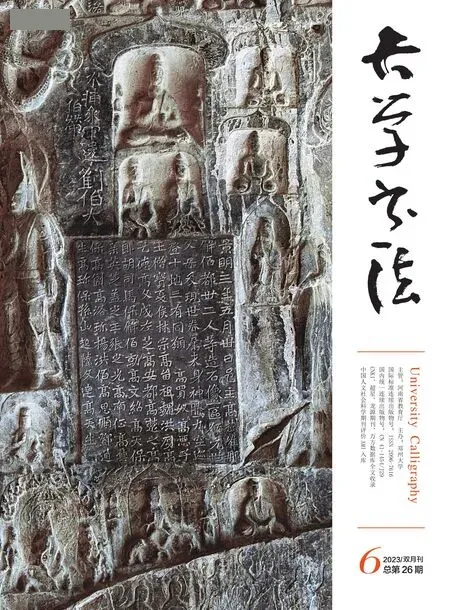书迹、文献与文物相互释证——从沙孟海古文字考释观谈起
⊙ 袁文甲
引言
在古文字考释及相关学术研究中,罗、王最早以传世及出土文献释证甲骨文与金文等[1],沙孟海在此基础上又依托考古、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书法文物资料相互释证,即以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以古器物刊刻资料与拓本及书法书迹资料互证。这种借助多种新学问及新资料的相互释证方法,也进一步推进了王国维先生“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相互释证”的二重证据法。[2]沙孟海多重证据的释证方法不仅仅为古文字考释提供了理据,也为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及线索。自古以来,古文字考释是汉字研究的基础,汉字是书法的基本构成元素,在错误的释读及错误的考释基础上,逐层推衍导致文字发展的以讹传讹,不利于汉字的正确传播与进步,更无从谈及在此基础之上对相关书法文物资料的书法学及书法史的研究。多学科及新材料的相互释证,也增加了学术研究中求真与求实的研究态度,这种研究的学术态度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对于书法而言,书法的书写还讲究美感,求美也是建立在求真与求实的基础之上的,沙孟海的古文字考释及多重释证的谨严学风也是后人要学习的。
沙孟海曾对传世书迹及出土文献中疑难字进行释证,笔者一一辑录如下:《古录》释文订[3]、《字说》[4]、《 字说》[5]、《也字说》[6]、《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牍“共侍”两字释义》[7]、《娄各盂考释》、《娄各盂考释·附记》[8]、《配儿钩考释》[9],《石鼓为鄜畤刻石考》中关于“鄜、畤”字的考释[10],《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钺——石钺与钺族》中关于“钺”字的考释[11],《洹子孟姜壶跋》中关于“ ”字的考释(此字单纯以通用习惯推释,不涉及音义用法推定,属于不完全考释)[12],《杞伯诸器跋》中关于“匄”字的考释[13],《越王勾践剑拓本跋》[14]《仓颉庙碑跋》《晋朱曼妻薛氏买地券跋》[15],《铜器篇·远古铜器之探究》中对“鼎、鬲、簋、敦、卢、匕、尊”等字的释解,《彝器之字体·上》中关于“殳、言、马”等字的考释,《彝器之字体·下》中关于“薇、逢、归”等字的考释,《彝铭考释之进步》中从释文、集字、字形、字义、字音、书体等方面简述考释之法,《彝器之时代》[16]《彝器之复出与初期考释》[17]《石鼓史话·石鼓文之校释》[18]《许慎以前文字学流派考》[19]《论简字》[20]等。沙孟海综合运用书迹资料、文献及文物资料进行古文字释证,体现了沙孟海综合的学术高度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其对于语言文字之考究,以多重证据的释证方法,也打破了前人多以文献释文献或文献传文献之单纯的释证体例,辅以沙孟海书法及篆刻并进,古典辞章、金石碑版、文物考古等无不精通,这也为他的学术研究道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新材料及新方法日益出现的情况下,沙孟海注重对传统研究理论的审视,也注意新的研究范式的转型,这种对书迹、文献与文物的综合释证研究法,在书法学及书法史学研究中都是值得借鉴的。
一、沙孟海古文字考释观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方式[21],在出土文献及书迹中出现疑难字或新见字,需要文字的阐释及进一步考释,考释的核心是记录语言的音义[22],阐释的目的是理据与构形,终究是厘清文字的音义与构形的相互关系,只有明辨其音义与构形,才能“完全释字”[23],而非仅仅是模糊推测或通时定义。这一方面是文字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正确书写汉字的必要前提,在大量的古文字文物资料的流传中,由于外在客观因素及久远文化的差异,一定存在部分疑难字及错误字,也难免存在错简、书误、混乱及伪作,继而需要对文字进行明辨释读,不得不考证及解决相关疑难字及错误字,继而考证作品的真实性,这也符合书法研究及书写中严谨、求真、求实及求美的基本思路。沙孟海考释古文字以精进扎实的文字训诂之学和文史兼备的辞章功底,加之旁涉考古及文献,又关注新问题、新学问及新发现,终究形成了一套古文字考释体系。对于古文字的考释方法,学者说法不一。如罗振玉以《说文解字》为中心参照[24],又以金文、甲骨等探窥书契,《说文解字》作为基本的分析汉字字源及考其形义的工具书,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许慎并未见到当下如此大宗的新文献资料,难免训释有误,因此过于依托《说文解字》并不合适;王国维则善于运用当下新材料,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交叉论证[25];于省吾在罗、王的基础上,多用考据得其每一个字所处的时代横向关系及字之本身在不同时期所处的纵向关系,善于综合辩证分析[26];唐兰则多用文字偏旁对照分析法。[27]通过梳理沙孟海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沙孟海的古文字考释方法已经非常成熟,它可以分为宏观及微观两个维度,宏观层面是指基于书迹、文献及文物诸多材料和多重证据的相互释证,通过借助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书法学及文献学等做多学科推定;而微观层面具体到某字与汉字形、音、义横向与纵向相互关系的分析及以自我学识为积淀的综合论证。
对于沙孟海古文字考释观的研究,笔者以沙氏《石鼓为鄜畤刻石考》(《 字说》)《大小盂鼎名称的商榷》《也字说》《 字说》《木牍“共侍”两字释义》等相关文章进行分析。
1.《石鼓为鄜畤刻石考》[28],沙孟海先借助历史学推定鄜畤所在及其重要性,根据传世文献《汉书》《史记》得出秦人多用畤字,其文献所载共有八处,初作西畤,后为雍四畤,汉代时称为雍八畤,后文献也佐证秦文公作鄜畤。沙孟海通过此字音、形、义综合分析,将《石鼓文》“ ”定为“鄜”字,“ ”字在《石鼓文》中两处可见,对于此字王国维及郭沫若均有不同考释,分别释为“雍”与“蒲”。《说文解字》“鄜”作“ ”,从邑,麃声。沙孟海借助音韵学分析汉字在古代并无轻唇音,凡轻唇音皆读作重唇音,所以“非、敷、奉、微”四纽的字古音与“并、明”四纽的字没有区别,“鄜”字古音应读作“铺”。 从㢚声,㢚又从虏声,㢚与虏两个字都是郎古切,音鲁。他又近一步通过文献《尚书》《礼记》《诗经》推定“鄜”作“ ”。沙孟海综合运用音韵、训诂及文献考订鄜字有四种写法,分别是《石鼓文》中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麃”,《说文解字》中的“ ”及今体“鄜”。沙孟海以汉字基本的形、音、义进行释证,以察其形、明辨音义及通读其境,而且注意分析汉字本身形、音、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形、音、义三要素考释推定[29],这种结合形、音、义的观点相互论证,实质上就是综合论证的基础。
2.《大小盂鼎名称的商榷》[30],在《盂鼎甲器跋》中,沙孟海借助考古文物及历史学的相关知识对《盂鼎》的流传与著录做了翔实的分析,通过对器物挖掘、收藏情况进行详细总结,具有典型的依照考古文物进行学术推定的范例。沙孟海所论颇具合理性,他以书法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进行判断,一方面增加了释证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以文献考文献及旧说以讹传讹之误。单一的文献论证往往缺少理论材料支撑,通过新学科、新学问、新科技、新思维的交叉能更加准确地做出定位。
3.《也字说》[31],“也”字是“匜”之本字,“匜”在商周时多见,沙孟海说“也”字作“阴”,多与女性有关。《说文解字注》有:“(匜)似羹魁,斗部曰魁。魁,羹枓也。枓,勺也。匜之状似羹勺,亦所以挹取也。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道者,路也,其器有勺。可以盛水盛酒。其柄空中,可使勺中水酒自柄中流出,注於盥槃及饮器也。”“匜”字金文作,象形惟肖,金文从皿作,从金作,从尸作,从金从皿作,沙孟海认为这些写法均为后起字,并认为篆文匜本作,又作,最后从 作。《说文解字》有云:“也,女阴也,象形。”后又以《礼记》《左氏传》《后汉书》等传世文献论之。《 字说》[32],这篇文章中“ ”字的考释依然是先以《说文解字》正之,后推其形、音、义之发展变化,结合相关传世文献进行考释。通过以上两篇文章的文字考释,可见沙孟海先生以《说文解字》为本的字学观,他常以《说文》为中心结合金文的不同形体,以窥其义。通过学者对《说文解字》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说文解字》所释字意并非全为本意,但结合《说文解字》,通过传统文字学中的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等方法,往往能相对准确地对文字进行考释。另外,沙孟海作为现代书法教育的先驱,一直强调《说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及古文字考释中的重要性,曾以宋代学生以篆、隶、草三体习书,并常课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为例[33],强调书家懂篆并通以《说文》为基。
4.《木牍“共侍”两字释义》[34],本文是典型的以汉字形、音、义综合互释的典型,对于“共侍”两字的释义,沙孟海先以简牍基本释录的办法,将此简所有文字进行排序校释,这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功底,并精通汉代辞章及用法。在考释时,他通用传世文献《诗经》《尚书》《国语》《尔雅》,就其书中所见“峙”字逐一释义,分析“峙”字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性质,将“峙”字在同时期不同用法的横向关系及在不同书目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关系进行对比研究,结合音韵学,得出“峙、庤”音义并同,属于同一字的异体的结论,并以假借读破法来阐释,即在古代,某些字词有音无字,固可以用同音字来阐释,就是已有本字的,也常常假借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达。最后,沙孟海考其“峙、歭”为同一例字,“共与供”“歭、庤、 ”非同形但同义。通过此文可知,书迹中出现的疑难字可以通过音、形、义的相互关系推定,以传世文献考其字用,即在文献中考察字与字间的相互联系及语境。汉字的发展是动态的,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中音、形、义是相互依存的,不会孤立地存在,所以依托汉字形、音、义的转换及释证往往是准确的。
通过研读沙孟海相关考释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较为成熟的文字考释体系,这种体系离不开先生深厚的语言文字学修养;通过资料可知,语言学、书法学、文字学及历史学是沙孟海学术研究的支撑。早年,先生从冯君木、陈屺怀学习古文[35],这为他对古文字词性及古汉语语言环境的了解夯实基础,这点从《助词论》《名字别号源流考》《许慎以前文字学流派考》《转注说》《汉字分笔排检法》等相关作品分别能看到。他在相关文字考释的文章中大量引用传世文献,足可见其对于传世文献的精通,对汉字当时的语境、用法及性质进行辨释,这些离不开语言文学的滋养;沙孟海从章太炎及顾颉刚通历史学,历史学的文脉是研究汉字及考证的基础,他延续了清代中后期的史学治学体系,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其中相关文章有《记沙村出土陈氏两墓志》《曲水流觞杂考》《北魏曹望憘造像跋》《石鼓史话》等;沙孟海接触考古学是从安特生、马衡二位学者开始的[36],尤其是马衡对沙孟海影响较大。考古学为沙孟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文物资料,地下出土文物资料结合传世的历史文献,更加夯实了文字研究的理据性,相关文章如《石钺与越族》《考古研究法》《五代吴越的雕版印刷》《宋元时代杭州的文物古迹》《再谈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中国古器物学讲稿——青铜器篇》;沙孟海又从康有为、吴昌硕、章太炎浸染书法,其书法宗锺、王、颜、苏,涉篆、隶、楷、行、草诸体,开北碑雄强一路新风,尤其将篆隶笔意融入行草书写,韵味沉厚,书法学及书法创作为沙孟海在古文字研究及创作上提供了实践基础。
附:沙孟海多重释证的研究成果较多,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类辑录:出土文物资料、传世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相互释证,刊刻资料与书法墨迹资料相互释证,写本资料与拓本资料相互释证,考古学、书法学、文字学及文献学多学科交叉释证(以下研究成果在多重资料互释或学科交叉释证中略有重合)。

沙孟海多重释证的研究成果分类辑录表
二、多重释证与书法研究
考古文物资料的新发现,不仅仅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也使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书法研究的固有范式,所谓传统书法研究,或过多地关注传世文献及怀有固有的文献情结,或过于专注书迹作品本身。20 世纪以来,随着大宗出土文献资料的面世,新材料及新学问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对于甲骨、碑刻、青铜器铭文及档案典籍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这些文献研究方法的逐渐成熟,也促进了书法研究转入求真、求实及求美的方向。多重释证研究本身对书法书写汉字的准确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古文献资料中,要辨明文字的书写正误及具体应用,要认清假借,也可以使书家明辨文物书法资料的真伪,提高审美认知的高度。笔者从文献释证、书迹及文物释证两个角度分别谈对书法研究的功用。
(一)文献释证
文献释证,主要是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释证。
通过双重文献,以此订正书法学及书法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对于文献的研究,文字的释读是第一性的,如果释读不准确,便无从谈及研究。例如,在先秦古文字中,往往有一种偏旁或点画在文字构成中是可有可无的,也或者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学者们常将此种饰笔或饰点统称为饰符号。
这个“保”字,我们可以借助出土的简牍资料《信阳楚简》《包山简·244》《包山简·212》看到其从西周以来的写法有明显区别性特征,战国后部分文字中保留了较为古老传统的写法,但是在简牍作品中全部增添了一笔,两撇分别置于竖画两侧,从记录语言的角度看,这一笔是多余的,从文字演变的符号系统上看也未有明显实质意义,但是为何添置一笔?大概是使之文字整体更加平衡与对称,具有修饰性的作用。书法的书写讲究美感,对称与平衡也是一种美,为了修饰性美增添的多余的符号称为饰符。[37]所以,在古文字中饰符是比较常见的,不能因为饰符而误读或否定了字意本身。在文字的演变中,对于这种现象的考察需要借助大量的出土文献资料,而不是仅仅通过传世文献所能解决的。对于这种用笔现象的研究要以出土文献的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继而量化分析,这样也能推定文字演变及文字书写发展的基本情况,这是文字发展史及书法发展史上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笔者继而得出求真求实的结论,这些源自饰笔的笔画在现在的汉字书写中也已越来越规范化。类似这种现象的字还有“言”“商”“帝”“童”等。
另外,出土文献除了可以研究汉字演变及构形的原理,还可以释证许多关于书法史类的问题,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有一段精到的叙述: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38]

“保”字自西周以来的写法演变
从许慎上文可以看出许多信息,如小篆的生成是“皆取史籀大篆”而成,或颇省改,书法史上也往往多以许慎之论而定,但是根据当下出土的文献资料可知,小篆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且发展得相对成熟了。秦始皇时类似刻石小篆的风格及结构造型特征更接近于战国晚期小篆的发展,如《秦公大墓刻石》《新郪虎符》《阳陵虎符》等小篆的写法,秦帝国时这些写法是直接顺承战国晚期小篆固有的写法,而非省改籀文。另外,“省改”籀文中的“省改”也并不准确,通过材料可知,有些秦小篆的书写比籀文还繁杂,我们从《说文解字》辑录的二百余籀文(《史籀篇》的文字统称为籀文)可以看到,籀文的风格特征逼近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风格,部分文字的结构比较繁复,但是也有部分文字比较简略,甚至比小篆还简,如“薇”(《说文解字》籀文作,《说文解字》小篆作)、“爨”(《说文解字》籀文作,《说文解字》小篆作)、“磬”(《说文解字》籀文作,《说文解字》小篆作)等字,所以许慎所言“省改”一词亦非妥当。另外,许慎上文“初有隶书”,意思是开始出现隶书,文中的时间是秦始皇初兼天下之后,通过现在出土的简牍资料看,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隶书,而且此时是隶书发展的大爆发时期,隶变的时间上限远早于秦始皇兼并天下时,从部分战国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中可以看到隶变的情况。由此可见,传世文献中的诸多观点因为是在当时资料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得出的,是需要重新审视的,需要借助新的出土文献资料进行考证,这样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化与真实化。
出土文献除了能重申传世文献中的诸多观点之外,也可以进一步佐证相关传世文献中观点的正确性,夯实古人的某些观点。如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秦书八体的记载情况,在另一个传世文献《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二者分别辑录为:
《说文·叙》记载: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39]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40](按此“六体”为“八体”之误,王莽时有六体,萧何于汉兴只有袭秦八体,无六体也。)[41]
这两个传世文献分别辑录了秦书八体的使用情况及分类情况,秦书八体是通行于秦的八种文字,实际是篆、隶二体,这关系到秦文字的文字发展及文字总结情况。秦书八体的提出与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它在文字演变史及书法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秦书八体的性质及真实性,若单纯以《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中相关记载还不能完全定论。而近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史律》篇则详细记载了秦书八体在汉初的性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记载:(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42]
张家山汉简《史律》篇的出现无疑肯定了秦书八体的准确性,也确定了秦书八体的功用性质,《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与之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以六体试之”,笔者以为此六体应为八体。通过资料梳理可知,一方面汉初的文字使用情况多沿袭秦制,还有,汉初也不会存在新莽六书,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常理,新莽六书出现起码是在汉人发现孔子壁中书等诗书百家资料之后。汉武帝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发现壁中书,距离萧何草律有近六十年,未见孔子壁中书及六国古文之前,何来古文一体呢?从目前的资料看,古文一体的确立起码在汉武帝之后,所以汉兴时应为八体试之,不会像班固所言为六体,王应麟、李赓芸、王先谦、李学勤等也有相关论断。近世所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篇证实于此,并确定了汉初“讽”书籀文为课试史学童的门径,秦书八体是试史的必备。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传世文献,对于出土文献应该足够地重视,这对于书法研究及文字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二)书迹及文物释证
书迹即为书法书写资料。文物则是通过考古出土的实物,主要是古器物等,在考古学的文物中,与书法研究相关的有甲骨文、青铜文、陶砖文、碑版文、摹拓文及笔墨工具等,这些材料的出现极大地扩充了书法研究的丰富性及可能性。
沙孟海在《两汉刻石讲稿》中综合运用书迹与文物释证,考其刻石之年代,依据刻石书写风格、书体的特征,以纯隶者尚未有波磔,与后汉隶书进行风格对比,得出东西汉刻石之风格差异。沙孟海分别对《杨量买山地记》《鲁孝王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等资料,运用书法学及文字学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沙孟海有《大小盂鼎名称的商榷》[43],在《盂鼎甲器跋》中,沙孟海通过陈介祺《簠斋传古别录》手稿中附录给吴云的信考其廿五祀《盂鼎》比潘祖荫《盂鼎》体积反而大,字数相比,潘氏所藏的《大盂鼎》字多百余,沙氏借助考古学辨出其器之真伪,并测定以大盂鼎称谓之器容八石,而以小盂鼎称谓之器容十二石,较大盂鼎反而大,于此,沙氏借助考古学之法纠正了旧误。他还认为《两周金文辞大系》中称孟姜壶甲器、乙器更妥,甚至认为王国维标题盂鼎一、盂鼎二也是合适的,此文是典型的依照考古文物推定旧有学术称谓之例。通过文中分析可知,《克鼎》《盂鼎》均属于潘祖荫旧藏的器物,后者共两器,其一是博物馆入藏的左宗棠供奉潘祖荫之器,是当下通称的《大盂鼎》,另一件出土于陕西,后亡佚。前者著录较多且文字拓本亦多,后者不见且著录较少,只有《捃古录金文》有记,并无从考其容积,今人习惯称大小盂鼎,此得名缺少理论依据。
另外,在综合运用文物、文献资料进行书法研究时,一定要详细考察文物、文献资料,证实文物及文献,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综合书迹及文物资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书法资料的真实性及价值。历史上,存伪的书法文物资料很多,作伪的手段相对也高明,包括书法墨迹、青铜器及碑拓本等。《韩非子·说林》云:“齐伐鲁,索谗鼎,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由此可见,在周代的时候便出现了赝品。在金石学大繁荣的宋代,收藏家为了喜好及牟利,大量的碑刻及青铜器出现仿制,这不利于书法文化的传播。金石学发展到清代时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清人注重金石考据学,从民间到官方,私刻及伪造金石文物的现象比较严重,也包含刻帖等书法相关文物的伪造,这就给书法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另外,书法文物的断代与书法风格的界定有必然的联系,而书法墨迹及版本的资料也更需要考古学参与。对于辨伪能力的提升,非仅仅书法学所能提供,必须诸多学科及诸多证据之间相互释证。文物的价值在于真实有效地还原历史,书法文物资料使我们可以近距离观摩古人真迹,一方面提升了书写体验,另一方面有助于对文物的出土、流传、形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到书法研究中,研究者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文献、书法风格等因素进行辨析,还需要结合考古学等手段进行界定。
结语
本文分析了沙孟海古文字考释的成果,确定了沙孟海以《说文解字》研究为中心的正字观,以形、音、义为基础的多学科、多重证据的考释观。基于沙孟海文史哲综合的文化修养,确定了沙孟海以书法学、考古学、历史学及文字学诸多学科交叉释证的研究理念,在学术研究上,他善于运用新材料、新方向及新学问,在文字考释上他侧重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综合分析及辩证比较,在罗、王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多重证据释证的古文字释证观及求真、求实的研究理念。对于沙孟海古文字考释观的研究,厘清了他在书法创作中正确的释读观及文字书写观,最主要的是他在书法研究中形成了多重释证的研究方法及求真、求实、求美的研究态度,养成了善于运用多学科及新材料的研究理念,这些都是在当下书法研究及书法创作中可以汲取的。
——纪念沙孟海诞辰120周年书法篆刻艺术展暨文献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