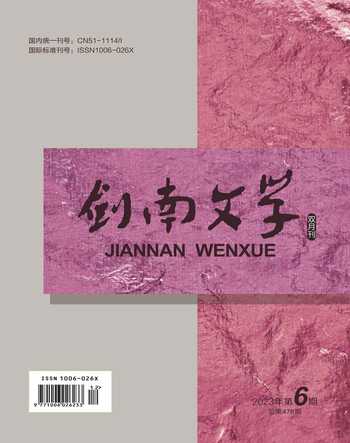桃花江挽歌
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而在桃花江,基本可以归类为能进屋和不能进屋。父亲和爷爷最终进了屋,而舅舅不能。但不管进屋与否,他们坟头的草木都同样茂盛。
1
蝉叫个不停的下午,我再次置身铺满灰尘的事件之中。另一个我被丢弃,无数只蝉飞进我的卧室,无数的情绪爬满房间。窗外的人通宵跺脚,一脚一脚地把我往回忆里踢。
得知爷爷重病时我正在南充实习,正穿着两股筋背心躺在师大一期的公寓里,许是同父亲一直交流极少的缘故,电话由母亲打来:“你爷爷快不行了。”我的声音像是在极短时间内进行了激烈的化学反应,越来越大却越来越不稳定——对,就是不稳定——身体的重量急剧流失,仿佛有两只手提着我的肩膀。
当我被那两只无形的手提着回到家时,爷爷就如同半山老家火塘上吊着的被柴烟熏了多年的腊肉一样干瘪地躺在幺爸家的堂屋里。两只高脚板凳已经支好,板凳上面是一块木制门板,门板上躺着的正是爷爷。旁边有一组液体、一个制氧机、吸痰器、心电监护仪,还有一些我至今不太熟悉的医疗品,医疗管像农村的电线一样凌乱地从铺盖里伸出来。当天晚上的我也正是在颤抖中从这个管道下手的。
“你爷爷在从镇医院转往县医院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但他一直问你在哪里读书。”
爷爷对我们的小家庭并不好甚至算得上苛刻。2002年,31岁的父亲患精神分裂症。糟糕的境遇不但没得到同情,反倒是他的父亲我的爷爷隔三岔五便要找个理由指桑骂槐。老爷子骂人的功夫甚是了得,前半夜骂的内容几乎不重复,后半夜复习前半夜的内容,一直到公鸡打鸣。
一气之下母亲在当年便决心另修房子。父亲不能做重活,九岁的我也是有心无力,我们便在夜里睡在邻居家吊脚楼的过道里守木头——那几年连长在林子里的柴木都时有人偷,更不说躺在路边的木材了。晚饭过后,在邻居家听一会儿收音机,我便和父亲打着电筒裹起铺盖。那个冬天的多数夜晚,我便是在父亲的鼾声和不时刮过的风声中度过的。
立房子的前一晚,爷爷洪亮的声音从半山上一直传到河坝里,骂了一个通宵。我不知道缘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针对的就是他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我的父亲,或者说是我们一家?否则他不会在骂了一整个通宵之后,第二天一早还能躺到屋基上闹事。
爷爷对我的家庭虽然刻薄,但在面对我和弟弟时,却是一个合格的爷爷。还在半山老家那几年,屋前有几株木瓜树,到了季节可将其摘下晒干背到镇上当作药材出售换些碎钱。一次他从乡上回来时从背篼里取出一袋名叫七个小矮人的冰糕——准确地说已经化成了水。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喜欢吃这个的,因为他已经十几年没有下过山了,更不用说上街。“他们说小娃儿都喜欢吃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们是向他推销冰糕的老板还是老爷子有意寻到的他们,但很感谢他们给了我此刻回忆不算幸运的童年时还能感受到一些温暖的力量。
“你爷爷不能死在明天!”幺爸说到这里时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
为啥?我的脑袋里满是问号。随后幺爸给我“迷普”——迷信的迷——了一个名词叫重丧。“重”为反复和又的意思,丧自然是丧事。若人在这样的日子死去或者下葬便是极不吉利的,重丧分为内重丧和外重丧,犯内则表示死的会是家里的人,犯外则是附近的外家人。顺便还举了河对岸村子的例子,那一家人和奶奶还是较为亲近的亲戚,老人去世后一个当官的儿子不信迷信在重丧日下葬以后,接下来的几年里家里人陆陆续续地患病离世或者莫名其妙地失踪。这一切让我在后来不得不将父亲的死和一个静躺在黄历上的日期(奶奶死的日子刚好犯内重丧)联系在一起。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所以你等会在他们都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幺爸是在经历怎样的挣扎以后才跟我摊了牌。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在这个夜晚的十二点以前有所行动。
晚上九点的样子,来看热闹来帮忙的人都已经吃完饭喝完酒离开了,只剩几个自家人和一些留在院坝里打牌的人。爷爷的喉咙处开了一个五毛钱硬币大小的孔,我需要不定时地拿起一根塑料管解开盖在洞口的纱布伸进去吸痰。
在我又一次将他体内的痰吸出后不久,爷爷突然将两只手抬起,做写字的动作。我们找来纸和笔后他先是写下了我和弟弟的名字,我和弟弟在旁边答“爷爷,我们都回来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表示点头。紧接着又写下了一个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的名字,看名字是父亲一辈的,最后还是在奶奶的提示下才猜出那是我父亲曾用过的名字,但是太早了,以至于连我父亲本人都想不起来了。我无法想象他是出于何种心情在以一种极恶的态度对待了父亲这么多年,又在临终时回想起他这个窝囊一生的儿子还在襁褓中的样子的。在写下父亲的名字时,有泪水从他的眼角落下。最后一个字几乎被分解成了现在已经拆掉的那所老房子一样,众人辨认无果便散了去,而我守在床前按着笔画顺序演示了无数遍以后,终于认出了那是一个“死”字。我凑到爷爷的耳边问了一句“爷爷,是不是想走了”,他点了头。
夜里十点,我在又一次为他吸痰以后理了理他的衣领和被子。爷爷帽子下的黑发越来越少,白发也越来越少,几十年的烟熏使得他的皮肤显出原油般的质感,叶子烟的烟油在他皮肤的褶皱里堆积。这一刻固守或被遗忘在老屋火塘边的他显得无比轻巧,他体内的水分一点一点重新回到桃花江,内心沉积多年的好与坏都泥沙俱下,顺着桃花江远去。轻巧的他使我内心的不安缓解不少,我伸向医疗器械开关的手也止住了颤抖,但手指拨动的前一刻我还是闭上了眼睛。
但爷爷的命似不该绝于此,他又怀着愧疚在轮椅上折腾了半年,直到半年后的除夕下午我在外公家团年回到家他才真正闭上眼睛。
2
外公一向喜欢养鸽子。儿时随外公去骡马头榨菜籽油时,主人家平房的阳台上有一只灰色的鸽子,脖子上挂着些和锦鸡一样的彩色羽毛,煞是好看,它也不怎么怕人,不同于我在老家看到的其他鸟类,很轻易便能靠近。抑或是它也放下了所有,耐心地在等待死亡或者被拯救。
主人家有一只鴿子,但是那人不会养,鸽子蔫耷耷的,都快养死了。在外公的示意下,为了拯救它,我偷偷从三楼摸到二楼的阳台上把那只鸽子裹在雨伞里带回了家。鸽子被外公照料得很好,好到外婆时常站在菜园里咒骂“总要被鹞子打了嘛”,最终也遂了外婆的愿,每隔一段时间总能听到外公说又有鸽子被鹞子打或者被猫抱走了。不过那时外公的鸽子队伍已经发展壮大了,从最初我抱回的那一只发展到几十只。
外公为那只母鸽子配了一只公鸽子后不久便孵了几只小鸽子,不时还能拐来一些放路落单的鸽子,捏住鸽身捋开翅膀能看到有三门峡的有湖北的一些比赛印章。
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几十只鸽子扑腾着翅膀在屋顶盘旋。就是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却在几年前突然全军覆没了,大多数是被农药毒死了,还有小部分是被外婆咒死的。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从深圳传来了大舅的死讯。母亲兄弟姊妹四个,母亲是老大,最小的是一个舅舅。大舅排行老三,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为了节省学费便选了当时学费极低的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航天公司做飞机零部件设计。
幺舅专科毕业后便到了深圳打工,大舅见自己一个本科生还没自己弟弟工资多,便不顾外公的反对毅然辞职去了深圳打拼,后来在那边安了家,与朋友经营着一家小公司,自己又在另一个公司担任设计师,也算在那边站稳了脚。只是离家太远,回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了,尤其是在生下老二以后,愈发忙碌。终于在2015年夏末的一个下午,他开车下班回家停在红绿灯前,等到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的车却一动未动,直到有人上前准备理论时才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父亲第一个接到电话,那时我正和父亲忙于照顾瘫在轮椅上的爷爷,父亲接起电话说“是,我是曾跃东的姐夫。”紧接着父亲有好长时间没说话只听着电话,但是神色越来越凝重,像极了每次要抄起棍子打我的时候。
那时我已不太惧怕父亲,便询问了一声。“你大舅出事了”,父亲的话语里带着些慌张,随后打了电话给母亲和二嬢。当天晚上母亲、二嬢和姑父便带着外公连夜到了绵阳,和幺舅约在深圳会面。
几天后他们从深圳回来时我看到外公本就消瘦的身体又瘦了一大圈,和他前些日子刚收留的病鸽差不多了。外公是盐亭人,本是地主家庭,但他还没来得及享受殷实的家境,父亲就被发配死在了青海,母亲则在被批斗时冷死(准确地说是寒冷加饥饿)在了某年冬天的一口水缸里。为了生计,外公十来岁便到了桃花江,学木匠、厨师、裁缝、泥瓦匠,同被人领养的外婆组成了家庭。
外地人自然是受欺负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母亲明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好还会选择他的缘由。那时外公一家时常受欺负,至今幺舅左耳的听觉都不太好,是被一个亲戚在村委会门口的核桃树下重重地扇了一巴掌导致的。
自那时起,母亲便一心要找一个有脾气能保护家人不再受欺负的对象。而父亲正好是当地的混混头目,只是自劳改回来以后销声匿迹了,可见改造颇为成功。我随作家阿贝尔登上北山时,看到了几堵过去由劳改犯砌的石墙便在猜测其中是否有我父亲的一份功劳。父亲为母亲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便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送了几只鸡,但是外公看到鸡的时候发现正是自家前几日被偷走的那几只。
经过几轮官司,大舅的死最终被认定为工伤,但也正因为打官司的缘故,时隔近两年后大舅的遗体才得以火化。骨灰由外婆背回。下葬时我正好准备前往北京学习,也是借此缘由我逃掉了新演绎悲伤,因为该悲伤的已经悲伤过了。并非我没有感情,而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去学习则给了我一个逃避的借口。
大舅去世以后,外公念叨的最多的就是大舅留下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懂事了,但父亲的去世让他变得十分叛逆,不喜欢读书更不喜欢他母亲的管教。小儿子喜欢与我的母亲交流,虽然大舅下葬以后他没再回来过一次,那时也还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家伙,但是他总喜欢借着跟他大娘開微信视频的理由玩手机。
从“你有空就多跟两个弟弟视频一下”到“你多跟弟弟视频一下,说一下”。外公的话语我总是连声应答,但却很少真正去做。一是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口吻去劝说一个因为早早失去父亲,而母亲又不怎么合格造成性格孤僻的孩子,况且又是自己的亲人,我怕一说多了反而引起伤感;二是隔得太远,与其永远重复着一些毫无用处的讲说,倒不如少说。
每每看到外公外婆站在路边围着手机叫远在深圳的两个孙子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头上的白发又多了一些,而视频完以后,他们则免不了偷偷抹上一把眼泪,有时候甚至视频到一半的时候,他们便红了眼眶草草挂断。
为了调节外公的精神状态,先是幺舅从雅安买了三对鸽子让他养,而后我又从诗人雨田那里要来了两对鸽子。他为这些鸽子从十里外的工地上拖回了两张没用的铁丝网,又拿出他的木匠工具在柴垛旁边给鸽子做了一个大大的笼子。笼子几乎不打开,他每日都要检查一番,然后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望着那些鸽子出神。
我想,外公的笼子里关着的不只是他早早死去的儿子,还有他失去丈夫的大女儿、成日忙碌在工地上的二女儿、患有抑郁症远在雅安的小儿子,还有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两个孙子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多么庞大的队伍。
3
我始终没有料想到,我还没有成为父亲,就已经失去了父亲。父亲已经很多年对这个家庭没有实际上的帮助了,甚至可以说因为他十八年的精神分裂症加上比我年纪还大的痛风和类风湿时间早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累赘。但如今,他的缺失让这个家庭变得空荡起来,母亲一旦出门打工,那栋在他患上精神分裂症那年建起的木架房就永远空着了。也许父亲仍旧在那个空荡荡的房子里住着,也许不是。
我工作以前,母亲常年在外地打工供我和弟弟上学,父亲独自守着那栋房子;后来我工作了,母亲仍旧在打工,弟弟仍旧在上学,父亲仍旧独自守着那栋房子,守着他一身的病症;现在,我和弟弟都工作了,母亲过两天仍旧要去拉萨打工,而父亲仿佛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在桃花江,只是他不再疼痛,不再为那些病症所折磨。
后来在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在去世前说了很多这种半截话,譬如去年母亲打工回家时他对母亲说“晓得你今年回来看得到我,明年回来还看不看得到哦”。母亲还讲述了一个关于父亲的痛风的故事,父亲三十岁左右时已经被痛风折磨得无法忍受了,某日遇一算命先生,他开玩笑似的问那个算命先生他的脚什么时候能不再痛,对方回答“你过了五十岁就不再痛了”。是呀,父亲去世时刚好才四十九岁,等他五十岁时哪里还有什么疼痛可言。
当我再次翻开这段文字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427天,这427天的时间里,我没少因为醉酒以后的情绪失控,在房中人睡得深沉时失声,上一次想起他还是在从蓉城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晚上。当日在蓉城同朋友喝酒,母亲打来电话问我符祇该如何写,我才猛然觉察到父亲已经走了一整年了。由于病症——有实际的疾病也有一种名为懒的病——的原因,自我读初中开始,每年清明、七月半和除夕家里所有需要撰写的符祇都是由我代笔。但倘若我没在或者忘记了呢?坟上新土都还未干的父亲是不是连一架符祇都收不到。
事实也是如此,他几乎已经被遗忘得差不多了,生前的床、被套、沙发和衣物被尽数焚毁,就连我的梦里他也几乎不再出现。家中唯一和他有关的就剩我从火堆里抢救出的一张皈依证以及我和弟弟身体里的血液。
我本想回忆一些有关于他的事情来,但当我像一盏孤独的台灯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却想不起关于他的任何细节或者故事。兴许是从小他便是我的反面教材的缘由,又或许是因为时间、地点或者我没有能够像他年轻时那般冲动和热血?
如果说最后十年的父亲像一只病猫,那他的前三十年就是一头狮子,暴躁、冲动,血液里埋藏着炸药,那些炸药足以将现已荒芜的矿山重新炸开。
十九年前,我正读小学,父亲刚刚从精神病医院回来——关于他第一次犯病,我只记得那天早晨我在只有一间厨房和一格卧室的半山老家的用砖块支撑的地铺上被吵醒,当我走出门外,婆婆从厕所拎来一桶尿朝正跳着我从未见过的舞蹈的父亲身上泼。爷爷手里拿着一炷香和一对牛角卦蹲在神龛前,母亲见我出来就把我抱在怀里。家里没有收入来源,母亲就带着弟弟同外公在矿山上打铁矿为生,我已经读书了,只能在放假时同他们一起前往那个满山碎石和牛粪的矿山。父亲则是被麻将和纸牌勾去了魂魄,有钱就亲自操刀,没钱上桌就在牌桌旁抱上一整天的膀子。
父亲从一头狮子变成了一只病猫,固守在那座木架房子里。不到十天时间我先后两次梦见父亲。一次是在家中,梦境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在醒后看了看日历,确认中元节还早便没再管;第二次是在北京学习时,那几天总是睡不安稳,梦见父亲神色冷峻地要我做桌子上那套物理试卷。父亲虽然纨绔,但对我的学习的监督是一点都不马虎,稍有不对便会让我屁股开花。父亲打我是极为舍得下手的,能抄家伙就抄家伙,最多的是扫把和柴棒,摸不到家伙什的时候就用最原始最好用的武器——拳头和腿脚。我如今的谨慎和怯懦便是父亲留在在我身体里的证据。
我从北京回到家的时候与母亲通电话说及梦见父亲这事的时候,母亲告知我父亲的生日快到了,七月半(中元节)也快到了,提示我到时候写几架符祇找个地方烧给他。亡者能否收到焚烧而去的符祇姑且不论,但总归是继承了他们的苦难的活人寄出了一缕缕炊烟般的思念。
4
2019年的冬天,我在老丈人家帮忙杀年猪,与其说是帮忙,倒不如说是为了杀完以后能拖走半只猪肉。这一年猪肉价格高得离谱,随便一小块便要花去半张红票子。自父亲患病以后,为了供我和弟弟读书,母亲一直在外打工,自家的猪圈也变成了蛛圈,养满了蜘蛛。恰逢我与妻子刚领好结婚证搬进现在的房子,老丈人便让我跟着回去帮忙,母亲也一大早坐客车过来帮忙收拾。
三条大肥猪被赶上三轮车后直接拉到杀房。
当天日子好,杀年猪的人户异常多,饶是刀儿匠连午饭都还没吃一直工作到下午一点左右,都还有十几条哼哼待宰的肥猪。我們从上午八点左右一直等到十一点才轮上,期间老丈人一直守在杀房看热闹,不时和熟人搭上几句话,我和老挑看了一阵便躲到了别家火塘去烤火取暖了。第一头猪杀完才发现装肉的蛇皮袋忘了带,我回去拿袋子时只见母亲直直地站在路边,见我回来便说“那我们回去哇”,我还没来得及询问,母亲又补充到“你老汉儿摔着了”。
老挑开车送我和母亲回家,在路上母亲一直抱怨父亲骑车的事情。女人面对事情的时候通常首先得好好抱怨一番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和手足无措。确实父亲这些年因为骑车的事情出了好几次事故,由于常年的痛风和类风湿,他只能借助狗驴子摩托出行。
把父亲送到县医院一番检查以后被诊断为脑出血,同时伴随着心衰、肾衰,“最严重的是肺,肺部积液已经把左边肺叶淹了一半了”,主治医生指着片子给我们说明病情。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高血压、痛风、类风湿、精神分裂症都需要他长期服药控制,他不间断服药的时间远比我认识他的时间长,长期的药物刺激早已经严重破坏了他的身体机能。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陪着母亲在县城一家小宾馆住着,由于担心影响弟弟期末考试,直到他考完试我们才将父亲的情况告知于他。“本来也就是这么个情况了,等爸实在不行了的时候再跟他说吧,等他先考试。”我赞同母亲的想法。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只在每天下午四点检查的时候才得以探视,父亲整个人像一株长得茂盛过头的多肉植物,时间一长,也愈发水肿,不看还好,看了反而心里更加难受,到后来,我本能地抗拒进入那间病房。
弟弟到的那个下午,父亲似是心有所感,母亲为他擦拭身体的时候,他反抗得异常厉害,直到母亲跟他说“你不要动,二娃等下就回来看你了”,父亲便乖乖听话了,侧头看向母亲的眼睛里有泪水流出。
半个月以后,2020年1月8日,已经是腊月了,我们兄弟俩和母亲商议后决定将父亲接回家,因为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家门的。
父亲被安置在堂屋(客厅)的沙发上,到家时他灰色的眼神不停地左右张望,兴许他是知道回家了,兴许这半个月对他来说太过漫长,漫长到他已经对家里的环境感到陌生。
“这样吊着命干啥,他受折磨,好人也受折磨。”我叫来母亲和弟弟轮番与父亲辞别,我不清楚那时的父亲是否还能正常思考,但他也似是听懂了我们的话,两行泪水顺着他水肿的眼皮缝隙流出。他努力把自己的眼睛撑开一条缝隙,眼球如同蒙着一层白色的浑浊的膜,黑眼球比平时小了不少,像某种擅于狩猎的动物的眼睛。他看看母亲,看看弟弟,看看屋中的陈设和我以后便闭上了眼睛。母亲接过弟弟手里的卫生纸将父亲的泪水和嘴角的白沫擦干净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看着臃肿的父亲——几乎没干过活,加之多年激素药物的作用,一向肥胖的他,此刻更显水肿。我着手取出他嘴里的气管导管,谁又能想到一个人的命居然全靠一截塑料管吊着。我捏着导管外露的部分一点点拉扯,父亲的胸口便跟着向上抬起,伴着急促的吸气声。我拿来剪刀将导管的气囊剪掉以后,才轻松地取出导管。
取出导管以后,父亲的面色好上了不少。不时便会有一些白色唾沫从他的口腔溢出,那种黏稠程度似乎是将他这一生没有讲出的话语压缩在了一起。
下午四点五十四分,我再次准备为父亲擦拭时,父亲已经没了气息。他原本水肿的身体恢复了不少,那双凶猛的眼睛也变得无比平静,不会动的平静,没有怒气的平静,我从没有见过父亲这般温和的模样,像是一个安睡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在接父亲回家以前,家里早就备好了棺材、寿衣、鞭炮等。鞭炮尤为重要,鞭炮一响大家便知道人落氣了。不时,整个院坝便站满了人。搭篷的搭蓬,支案的支案,接桌子的接桌子,扛板凳的扛板凳,整个流程像是排练了无数次的一台演出。
一直到父亲下葬,他的两位亲姐姐都没到我家堂屋看上他一眼。反倒是父亲生前的一位好友,带着重感冒陪同我和弟弟一起守夜。那位叔叔在我们不在场时还独自去医院看望过几次平躺在生与死的边界上的老友,至于父亲的姐姐们则自父亲入院那天后便人间蒸发了。
为父亲净身的时候也是这位叔叔陪着我和弟弟,先是由匠人为父亲剃去头发,古老的剃刀已然失去当初的锋利,打磨过后不规整的刀口不时在父亲的头皮咬出一道道浅浅的伤。我不知道这把剃刀曾剃过多少人,以后又还有多少人享受这把剃刀的撕咬。我也曾在心底暗暗地想要像这把剃刀一般让父亲感到疼痛,但纵使我绞尽脑汁也未能让父亲感到疼痛。倒是越来越像这把迟钝的剃刀一般泰然地一次次面对死亡。
父亲的身体冰得吓人,不只是凉透了,那一丝冰意顺着我触摸他的手指侵进了我的灵魂,但不足以引起我的悲伤,因为该悲伤的早已悲伤过了。我像是整理行囊一般将父亲摆弄着换上寿衣。
“早知道我花钱请几个人抬算了”,出殡的那天早晨母亲气到差点晕厥。我和弟弟要端灵牌和引路灯走在最前面不能回头,没能欣赏到端公喊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抬的场面。见多数人都抱着膀子立在一边,最后还是母亲体质虚弱的弟弟和身材虽魁梧但胆小的妹夫率先上手。姑父的胆小我是见识过的,那日他到病房中看了一眼父亲出来便面色发青好久没能缓过来。
父亲埋在了半山老家我们曾经的菜园中,当初的几户人家都已经搬到了河坝里,只剩下几堆长满杂草的废墟和一口手推石磨。屋基下像样的不像样的石头都已被堆到了父亲和爷爷的棺材上方。中间是曾祖母的坟茔,右边是爷爷,左边是父亲。
将父亲送上山后,腊月二十五我便回了绵阳陪妻子,恰逢疫情妻子作为医护人员春节没能回去。只在电话里听母亲说“她们觉得我们把你爸接回来得太早了”,我知道这个“她们”指的是父亲的姐姐们。我安慰母亲的时候又回忆了一遍从父亲入院到父亲回家、下葬,父亲的亲姊妹所有的行为,我不怪她们,但是面对她们我也是无语的。
“对他来说也是解脱”,邻居站在门口的李子树下跟我说道。确实,对于一个手脚都已变形溃烂,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的人来说死是一种解脱。那么换言之,我并没有杀死我的父亲,我从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的疼痛中拯救了他。
5
或许真有宿命存在?爷爷因脑溢血离世的第四年冬天,父亲也因脑出血而躺进了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是在同一张床上,但一定是在同一个房间;同样回到了半山菜园里,从同一地方取材,覆之以土,垒之以石。
我几乎是以相同的手法杀死了两个我最亲近的人,但我并未因此感到愧疚。相反,他们将在我之内活得更深刻。
如今,母亲已再婚,照顾她的那个人很是周到。为母亲庆幸的同时,继父的周到又让我即使是回自己家也不免生出些客居的感觉。桃花江名为小河水的村庄,村子岔路口沿小河沟上行三百米的那所房子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一个符号或者仅仅是几个碎片化的汉字和按期寄给亡者的福纸。
死去的人已得到救赎,活着的人仍将活着,徘徊于苦难和幸福之间。
【作者简介】
马青虹,1993年生于四川平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见《诗刊》《民族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著有诗集《身体里的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