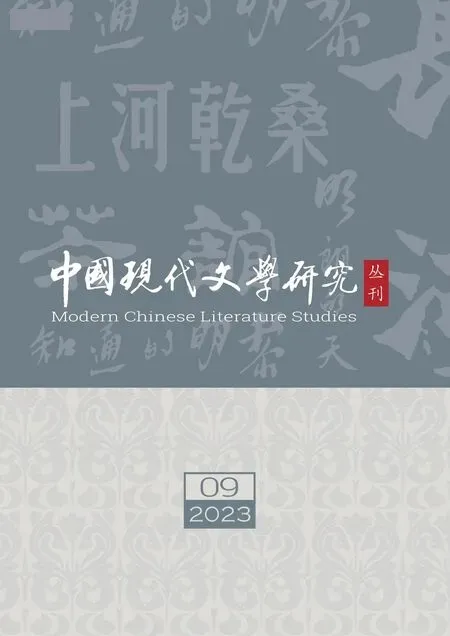沙汀研究史上几种观点的商榷※
王卫平 李 墨
内容提要:在沙汀研究史上,有几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是“农民诗人”与沙汀作品的“诗意”问题。本文认为,沙汀不是“农民诗人”,其作品也没有什么“诗意”可言。二是关于“客观性”与“客观主义”的讨论和争议,“客观性”既是沙汀创作的特点,也是缺点。三是沙汀是否属于“社会剖析派”,在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几个共性特征中,仅“客观化的描述”这一点才符合沙汀的创作实际,因此,“证据”不足。这样看来,“《子夜》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似乎与沙汀无关。
沙汀是中国现代左翼小说家,从1931年开始创作,对沙汀作品的评论、研究,比他的创作稍晚,至今有近90年的历程。在沙汀的研究史上,有几种很流行甚至很权威的观点,但细究起来未必能够坐实,确有商榷之必要。在这里提出来,以请教方家。
一 “农民诗人”与“诗意”辨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沙汀是“农民诗人”,其作品具有诗意。最早提出沙汀是“农民诗人”的是杨晦。他的《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是较早地评论沙汀创作的文章之一。作者在开头就说:“我们的作者沙汀,可以说,是一个农民诗人。你看,他使用多么优美的、散文诗一般的文字来写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所谓川西北的农村生活呀。”“沙汀不但是醉心于农民的题材,他也正是农民的性格。”1杨晦:《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1945年2月15日。在这里,杨晦说沙汀是“农民诗人”,主要依据两点理由:一是他用优美的、散文诗一般的文字来描写农民;二是他醉心于农民的题材,且具有农民的性格。其实,关于第一点,我们在沙汀的作品里是找不着答案的。杨晦在该文的结尾说:“你看,我们的作者沙汀,用多么哀婉而深切动人的散文诗篇,在他的短篇集《土饼》和《苦难》里歌咏出我们农村的生活,我们农民的悲剧,和我们时代的苦难呀!”2杨晦:《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1945年2月15日。这段话值得商榷:首先,在沙汀的《土饼》和《苦难》等作品里是没有“散文诗篇”式的语言的,作品所呈现的是农民的悲剧和“我们这时代的大的苦难”3沙汀:《苦难》,《沙汀文集》第四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页。。《土饼》《苦难》等小说呈现给我们的都是极度的贫穷、饥饿、苦难、死亡等画面。《土饼》中人们穷得“连蚤子都没有一匹”,丈夫失踪,留下“三个毫无工作能力的孩子,饥饿和折磨”“屋外,吹啸着凄厉的寒风”“巷道中间,流荡着无家可归的人们、儿童和兜售孩子的父母”,不断传来“饿死人啰!”的哀鸣。这样的农民生活有什么诗意可言?《苦难》中呈现的生活场景同样如此,“流离失所的灾民,拖着他们疲惫而冻僵的身体”,“无家可归的孩子,年龄在七八岁之间,褴褛,腿子瘦来跟鸡脚一样。他们成天在街上游荡着,啼叫着,好像一群被遗弃的生癞疮的小狗”。这样的惨剧有什么诗意可言?语言也不优美。其次,在沙汀的作品里,农民总是受着种种的欺压和剥削:饥饿、灾荒、凶杀、惨死、兽道、活人被钉入棺材,等等,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农民生活怎么能“歌咏”呢?在这样的苦难、惨剧面前,月亮也是“清冷而且苍白,比阴暗还可怕”(《土饼》)。哪有什么诗意?说沙汀醉心于农民的题材,而且具有农民的性格,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不等于就是“农民诗人”。
在杨晦之后,继续说沙汀是“农民诗人”的是石怀池,他在《评沙汀底〈淘金记〉》一文中说:“正如同某一批评者所指出的,沙汀是一位农民诗人。他自己出生农村,大半的生活也都在农村的环境中度过,他底全部创作也没有跃出农村一步,像一位忠于职守的某种特殊病理的卓越的医生一样,他一直在研究和剖解农村的烂疮和毒瘤,虽然到今天,他还没有从这一大堆的病况材料中得出迅急治疗的真确的方案;可是大声疾呼地把病患的严重性挑示出来,这个伟大的功绩却是不可抹杀的。”1石怀池:《评沙汀底〈淘金记〉》,《群众》第10卷第10期,1945年6月1日。这里所说的“某一批评者”自然是指杨晦。沙汀的确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创作也离不开农村,他的作品也的确揭出了农村的烂疮与毒瘤。但这样的作家并不就是“农民诗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到了1949年以后,在沙汀研究的论著和文学史中,似乎再没有人重提沙汀是“农民诗人”的问题。然而,关于他小说中的“诗意”,先被王瑶在文学史中提及,后被吴福辉论证。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在论及沙汀抗战前的三个短篇集《航线》《土饼》《苦难》时说:“他用优美的诗意的文字写出了地方色彩很浓的乡村故事”;在谈到短篇《野火》时,王瑶说“作者的文笔经济而优美”。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282页。今天,我们重读《野火》,完全看不出“文笔优美”,它只是客观叙述所见,仿佛生活速写,没有故事,人物都没有名字。至于“优美的诗意”体现在何处?从哪些篇章中看出?王瑶也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到了1982年,王瑶先生的弟子吴福辉继承了王瑶先生的观点并加以衍生和具体论证。在吴福辉看来,沙汀暴露黑暗的小说是具有“诗意和喜剧性”的:
……锤子敲在棺材盖上的声音,恰如敲在木桶上的一样。而在远处,突地响了一阵巫师的清脆的“司刀”声,接着便是一阵悠长而凄厉的呼唤。……
“……三魂七魄回来没有呵!……”
狗嗥叫着。……3沙汀:《在祠堂里》,《沙汀文集》第4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
首先,吴福辉说“这是一种诗的境地,然而,它含蓄、深刻地表现了如磐的黑暗”4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在祠堂里》写的是活人被钉入棺材的故事,不管钉入的是什么人,都是惨绝人寰、令人战栗的惨剧,也不管作者怎样侧面描写,都传达出可怕、凄惨的气息。其次,吴福辉在文中辨析“诗意”及其种类,“真正的诗可能是平静而朴素无华的。抒情,当然大有诗趣,但总不能简单地认为诗意便是抒情性、象征性,一定非要有表现为外部的丰盈的联想和朦胧的幻觉不可”。他还援引李健吾谈戏剧诗意时所言,认为还有一种诗意是真实,是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果实。在吴福辉看来,“沙汀的现实主义,就是这种真实的诗意的结晶体,冷静、客观的描写,笔锋直插生活的底蕴……假如说,诗意有奔放、凝重两类不同的品格的话,沙汀正属于后者”1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最后,吴福辉在文中还谈到了意境、诗情、语言等,认为这都是诗意的构成。他说“诗意不能单凭小技巧、小手法,而要由意境造成。沙汀的小说,简明而内涵深远。前面所举的《在祠堂里》,全文传达出一种黑暗无边的氛围,情景融合无间,诗情浓烈”。谈到语言,吴福辉认为沙汀“有特殊的叙述的节奏和调子,一种慢节拍的、凝重的短句,本色的语言,显出蕴藉、隽永的诗味”2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为了说清沙汀的作品里到底有没有诗意,这里的确应该辨析一下什么是诗意以及诗意的具体体现。顾名思义,“诗意”就是“诗的意味”。“诗的意味”就是作家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这种表达,是作家、诗人用浸透感情的、有内在节律的、形象而富有美感的语言来表达的,是精练而又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诗意”体现在何处?或者说“诗意”有哪些构成要素?第一是情感,这是诗的生命,也是诗意的根本。第二是想象,这是诗和诗意的翅膀,没有想象,诗或诗意就不能飞翔,诗意也就无从体现。第三是意境、意象,这是诗化的生活。第四是和谐,它由节奏和韵律构成。第五是天真、浪漫和美好。诗意常常是仰望星空,是欣赏皎洁的月色的艺术。法国十七世纪最具天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曾说过“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的美好的愿望的表达,也是追求理想的体现。
吴福辉认为,“真正的诗可能是平静而朴素无华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平静而朴素无华”必须是用精练的、精粹的、具有诗的韵味的语言来承载的,也必然是具有抒情性的。诗意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抒情性,除了抒情性,还有形象性、想象性、理想性、浪漫性、哲理性、音乐性等诸多要素。但真实、高度的现实主义以及凝重,绝不是“诗意”的体现。司空图在辨别诗味的基础上谈论诗歌的风格,在《诗品》中,他列出二十四种风格,却没有“真实”“现实主义”“凝重”这类风格。如果真实、现实主义都是“诗意”的体现,几乎所有的小说就都有“诗意”了,这无疑将“诗意”泛化到漫无边际。小说中的诗意,常常和充沛的情感、强烈的抒情性、优美的意境、象征的意象、深刻的哲理、精粹动听的语言相联系。这种小说,我们常常叫它“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自我小说”等。沙汀的小说和这些几无瓜葛。
二 “客观性”与“客观主义”辨析
关于“客观性”与“客观主义”的讨论和争议,主要是由沙汀的小说《淘金记》引起的。追溯对《淘金记》的原初接受和评价,第一篇评论文章是鹒溪的《〈淘金记〉读后》,该文简要地指出了《淘金记》的成就和特点,也指出了不足:“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人没有充分的感情,因之也就不可能把他所认识的来感染读者。”1鹒溪:《〈淘金记〉读后》,《抗战文艺》第9卷第1、2期合刊,1944年2月1日。有研究者认为,这“多少暗示了小说的客观主义倾向”2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之后,石怀池在《评沙汀底〈淘金记〉》中也提到了小说“某种程度地带有几丝自然主义的阴暗的气息”3石怀池:《评沙汀底〈淘金记〉》,《群众》第10卷第10期,1945年6月1日。。
明确提出《淘金记》是“客观主义的作品”的是路翎,他在1945年以“冰菱”的笔名发表的《淘金记》中说:“虽然,作者的观察的才能,使他写出了某一限度的农村生活的现象。这种作品,是典型的客观主义的作品。”在路翎看来,由《淘金记》我们能看到“对于人生的勇敢和热爱么”,“能得到任何一种热情的洗礼么?”4冰菱(路翎):《淘金记》,《希望》第1集第4期,1945年12月。胡风作为“七月”派的理论家,长期反对创作上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在《现实主义在今天》《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沙汀小说的“客观主义”,认为“作家们由于受恶劣环境的围困,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力和拥抱力,看不到历史的潜在动向和蕴藏着的光明、新生的力量,所写的只是缺少热情的灰色的东西”。胡风把这称作“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胡风还认为,作家在表现对象的过程中,应该自然地将感情渗透溶化进去,防止冷淡的客观主义态度。”1转引自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7页。这显然是指沙汀的《淘金记》等作品。稍后,季红木也指出“小说家沙汀的客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规定了他对生活认识的和深入的有限性和程度性”2季红木:《从〈替身〉感到的——对沙汀小说的一、二感想》,《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4期,1946年3月30日。。此外,发表于1946年《萌芽》的吕荧与何其芳的通信中也讨论了“客观主义”问题。次年,上海《大公报》也先后发表了洁民的《“客观主义”私观》(7月27日)、吕荧的《突破“自然主义”》(8月17日)、洁民的《正确的扬弃》(9月21日)、吕荧的《再谈突破“自然主义”》(11月2日),又一次展开了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继续涉及沙汀的创作。洁民认为“自然主义,应该是旧现实主义的一个分野”。“从事中国新文学的作家”,多“师承自然主义”,沙汀的“这种师承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能否认沙汀的小说有时陷入琐屑的描写,令人烦闷的困境中,然而这只是其缺点的一方面;在他的作品中,不可否定的一点是:存在着战斗的中心潜伏,令人欲憎之爱之的感情,而断乎不是自然主义。”从洁民的评价可以看出,对沙汀的客观主义的评价,肯定多于否定了。
对于以上这些批评,沙汀自己当然是不愿接受的,他在写于1984年的《漫谈有关〈淘金记〉的一些问题》中作了如下辩护:“说我是典型的客观主义作家,据我理解,无非语言平淡,语调冷静,没有丝毫主观战斗精神。这里我要坦率地表示,对作品的风格不能、也不应强求一律。我自己呢,却正是力求作品中不露声色,不是对人物大唱赞歌,或者摩拳擦掌,而是让读者根据人物本身的言行作出评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没有褒贬。从根本上说,作者在选择人物、确定主题时就有评断。否则,何寡母的顽固、白酱丹的狡猾,又从何而来呢?!”3沙汀:《漫谈有关〈淘金记〉的一些问题》,《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1985年第1期。
严家炎在谈到“社会剖析派”的“客观化的描述”这一特点时,也列举了当年对《淘金记》“客观主义”的指责,“这些批评指责其实并不符合于作品的客观实际:作品本身尽管有缺点,但政治倾向性却都很鲜明。批评家们所谓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无非是现实主义客观描写而已。把‘客观性’等同于‘客观主义’、‘旁观主义’、‘自然主义’,这是极大的误解”。“在三四十年代这些并不正确的批评里,既有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也有属于不同流派之间(如胡风、路翎等本来就属于强调主观精神的流派,而社会剖析派则历来强调客观描写)一些未必合理的要求。到今天,我们决不能再把这些流派的特点,当作缺点来看待了。”1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98页。
这一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在三四十年代对沙汀“客观主义”的这些批评到底对不对?符合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这主要应该由作品的客观效果去检验。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陈君冶《关于沙汀作品的考察》到黄曼君指出沙汀现实主义的局限和不足,再到王晓明论《淘金记》,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指出沙汀作品存在明显的缺点,早在1934年陈君冶就指出“沙汀的艺术是冷静的,不动人的,缺少感情的表现的能力,这是他最大的缺点”2陈君冶:《关于沙汀作品的考察》,《新语林》创刊号,1934年7月5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曼君指出沙汀现实主义创作的局限与不足是“不够舒展泼辣,严谨精当但显得有些拘谨简约,含蓄深沉也略显沉闷晦涩”3黄曼君:《论沙汀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1982年第1期。。王晓明指出:“作者过于严格地约束感情就可以说是《淘金记》的一个主要不足。至于刻意求含蓄以至过分,使有些描写显得单薄,那更是明显的缺点了。”4王晓明:《论〈淘金记〉》,《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3期。过于“客观”在沙汀的《淘金记》等作品中是客观存在的。其次,这种“客观性”是否等同于“客观主义”?这要澄清一个基本问题:“客观性”往往是褒义,而说“客观主义”则就是贬义了。所以,严家炎强调不能将“客观性”等同于“客观主义”,他承认沙汀的创作具有“客观性”,却否认是“客观主义”。其实,当沙汀的“客观性”走向极端并显出明显的缺点、局限和不足的时候,说他是“客观主义”也未尝不可。严家炎强调“决不能再把特点当成缺点”,他更多地看到“客观性”是沙汀创作的特点。但还是要从作品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效果出发。至今没有人说《淘金记》好看、吸引人,具有艺术的魅力,而更多人的阅读感受是沉闷、压抑,太客观、太冷静,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和应有的艺术生气,让人难以卒读。沙汀创作的特点和缺点是分不开的,他的长处和短处是并存的,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
鲁迅1932年在与沙汀、艾芜的通信中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用鲁迅这话来解说《淘金记》的缺点同样适用,那就是:选材不严,开掘不深,由于选材不严,也就难以深度开掘。作品中的内容是琐屑的、见闻式的、速写式的,没有生动的故事,自然也是没有意思的。这不仅在他的长篇中存在,在他的中短篇中同样也存在。就短篇小说来说,有人将沙汀与艾芜的短篇加以对比,认为艾芜“更留意于人物和情节的生动性,因此,他的作品,不深沉,也不够含蓄,不像沙汀的短篇那样深沉、滞重,耐人咀嚼和回味,但他比沙汀的作品明快、好懂,易为一般读者理解和喜爱。艾芜的作品,往往一下就能吸引住人,使你不能不读下去,并激起你感情的波涛。作家好像在向阔别已久的朋友谈心。他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向你倾吐,必然引起你的共鸣。而沙汀的作品,读一遍往往是不行的,你得咬着牙读下去,可是你越读就觉得越有味道,你必将从头再读一遍、两遍,才能体味到它内在的力量”1谭兴国:《论艾芜的独特性》,《文艺报》(半月刊)1981年第6期。。不够吸引人的作品是容易失去读者的,至于再读、三读能否觉得越有味道,能否体味到它的内在力量?那就因读者而异了。
三 沙汀是“社会剖析派”作家吗?
严家炎认为,《子夜》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子夜》的成功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对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以茅盾、吴组缃、沙汀和稍后的艾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78页。。这里明确界定了社会剖析派的成员。但我们认为把沙汀作为其中的成员似乎有些牵强。
首先,沙汀是否阅读过《子夜》并受到影响。严先生在书中认为,《子夜》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这就是说,社会剖析派作家都受到过《子夜》的影响。可是,沙汀是个例外。关于沙汀和茅盾的关系,他一共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于1945年的《感谢》,是为茅盾先生五十寿辰而作,只记述他和茅盾之间的一两件小事:“先生对我影响最大,他最显著的一件小事,却发生在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这件事,在当时先生也许并未如何注意,甚至已经记不得了,但我却难以忘记掉。因为他曾经帮助我克服创作上的危机。”这是指1931年夏天,沙汀把写好的三篇小说寄给了《文学月报》,半个月后,编者答应把《在码头上》一篇先发表出来,并且将茅盾的几句评语给了沙汀。茅盾说,东西写得还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沙汀说“当时编者很替我高兴,我自己更高兴得了不得,因而我们都只重视先生的奖掖,忽略了他的微词”1沙汀:《感谢》,《文哨》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沙汀高兴的不是茅盾对他的褒奖而是批评,这种批评帮助他“克服创作上的危机”。在这篇文章中,沙汀还提到了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上卷,但并没有谈到《子夜》,更没有说到他读过《子夜》并受到它的影响。另一篇文章是写于1981年的《沉痛的悼念》,是为茅盾逝世而作,回忆他和茅盾近年的交往,述说茅盾对他的创作的帮助、影响和鼓励,同样没有谈到《子夜》对他创作影响的问题。由此可以推断,《子夜》对沙汀的创作并没有产生影响,我们从沙汀的全部创作中也找不到哪一篇、哪一部受到《子夜》影响的例证,甚至沙汀读没读过《子夜》也未可知。所以,“《子夜》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似乎与沙汀无关。
其次,严先生在书中说“把小说艺术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各个角度再现中国社会,剖示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正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这个流派在小说史上的一大贡献”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84页。。可是,我们从沙汀的小说艺术中看不出“和社会科学结合”,也看不出“剖示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等特征。严先生接着说“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再现。社会剖析派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它们力图对社会生活作出总体的再现,全貌式的再现”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84页。。严先生特意在“总体的再现,全貌式的再现”下加了黑点,以示强调。这种独特性,在沙汀的小说中同样是找不到的。沙汀的小说,作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只是对生活的再现,而没有凸显“总体”,更没有展现“全貌”,他自己说“我的全部小说几乎都取材于川西北偏远城镇的社会生活”4沙汀:《沉痛的悼念》,《光明日报》1981年4月3日。。不少评论家也都认为他的题材领域过于狭小。因此,他的作品不符合社会剖析派小说的独特性,仅符合一般现实主义作品对生活的再现的特点。
最后,严先生在书中还论述社会剖析派小说所表现的“复杂化的性格,悲剧性的命运”这一共同性的特征。其实,“复杂化的性格,悲剧性的命运”并非社会剖析派小说所独有,我们在很多优秀的中外作品中都能看到。就社会剖析派的内部成员来说,只有茅盾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才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沙汀的小说哪一个人物是属于“复杂化的性格”呢?似乎没有。而“悲剧性的命运”在沙汀的小说中倒是有的,主要是川西北偏远城镇人们的悲惨境遇,像如前所述的贫穷、饥饿、苦难、死亡等,但那只是“略图”,是生活现象,沙汀并没有刻意塑造这种悲剧性的人物。沙汀是以塑造反面形象著称,他多数小说所写的成功的人物往往都是地主、豪绅、贪官、地痞、流氓等形象,而且以此形成他人物塑造上的成就和特色。这些形象都是反面的典型,自然谈不到“悲剧性的命运”。即使沙汀写到了一些贫苦农民的悲惨的遭遇,像《土饼》中的女人,《兽道》中的魏老婆子,《凶手》中的两个兄弟等。但他们和严先生所论述的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林老板、老通宝、赵惠明等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人物性格是复杂的和悲剧性的,而前者的人物性格则是不复杂的,仅具有悲惨、悲苦的命运。
应该说,在严先生所归纳总结的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几个共性特征中,仅“客观化的描述”这一点才符合沙汀的创作实际,这既是沙汀作品的特点,也是沙汀作品的缺点,既是长处,也是短处。但仅凭这一点是否显得单薄、显得“证据”不足呢?从严先生对社会剖析派小说的整章论述中,所举沙汀的例证是最少的,这也足以说明问题。从以上简要的分析来看,说沙汀是社会剖析派作家有些牵强,似乎证据不够充分。这样看来,“《子夜》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似乎与沙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