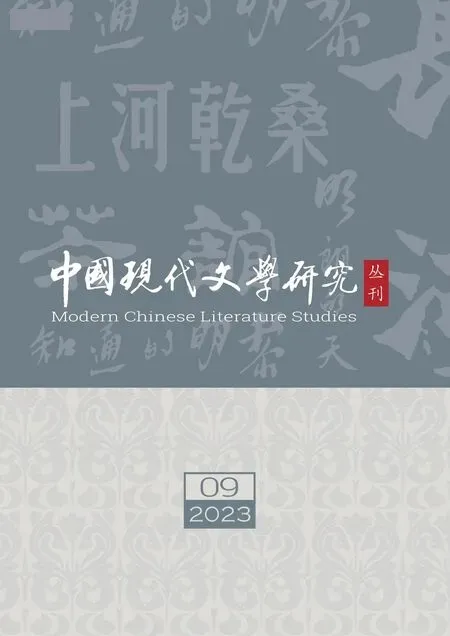异曲同工:论鲁迅与劳森的女性民族观※
——以《祝福》和《给天竺葵浇浇水》为例
张加生
内容提要:鲁迅和劳森分别是中、澳文坛的两位巨匠。他们的不少作品都借助对凄惨女性、受难女性形象的刻画共同表达了对(半)殖民地语境下女性与民族前途的忧思。文章以鲁迅和劳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着眼点,剖析他们笔下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与民族的关系。鲁迅在《祝福》中对祥林嫂和劳森在《给天竺葵浇浇水》中对斯佩瑟太太凄惨命运刻画背后有着共同的关于女性未来民族地位问题的思考,有着共同的女性民族观,即都将女性命运融入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共同考量,表达女性在新的民族中应当占据主体地位的民族观。
鲁迅(1881-1936)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赘言。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则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他与鲁迅一样,一生动荡漂泊,四处游历,也只活到了55岁,但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毕生围绕澳大利亚丛林与城市进行创作,在诗歌与短篇故事方面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享受“州葬”待遇的文艺家。鲁迅与劳森的女性民族观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平行研究,关于平行研究很多学者都有过专门论述。1国内外学者围绕平行研究做过很多论述,或曰其不可行,或论及其重要性、可行性与必要性。实际上,这个论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早在1857年,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讲座中就曾指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是相互阐释的。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种文学,如果不与别的事件、别的文学相联系,就不可能准确地被理解”(参见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钱锺书在《谈艺录》序言中也曾明确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强调东西方文学的共通性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近年来,曹顺庆对此也曾做过专论。在《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他批判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的“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认为“这是西方学界的偏见和谬论”,并指出“实际上,在全球化语境下,全世界的学者都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对话与比较,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早已成绩卓著;而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最主要领域就是东西方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学比较,多年来,尽管中西比较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却是没有可比性与合法性的,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理论缺憾;也是不正常、不应该的,令人非常遗憾的”。详见曹顺庆《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这些也即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如果再联系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所说的“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以及他在《集外拾遗集·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中所说的“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岛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鲁迅全集》第7卷,第411页),劳森作为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后期毕生关注底层丛林人生活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家,即“与我们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使得鲁迅与劳森比较研究的意义又更加丰满。本文立足鲁迅的半殖民地创作语境与劳森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创作语境,以鲁迅的《祝福》(1924)和劳森的《给天竺葵浇浇水》(WaterThemGeraniums,1900)中的女主人公形象为研究对象,剖析鲁迅对祥林嫂和劳森对斯佩瑟太太凄惨命运刻画背后将社会底层女性命运融入各自民族前途思考的创作思想,探究他们在反殖民,建立新民族基础上给予女性主体地位的女性民族观。
“人物形象是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支撑着文学世界,使文学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功能和恒久的艺术价值。”2段崇轩:《变革人物观念 创造新的形象——关于人物和典型问题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祝福》是鲁迅众多女性主题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小说中,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旧中国底层女性的生存卑微与无足轻重。稍早于鲁迅,劳森在母亲路易莎·劳森(Louisa Lawson,1948—1920)——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运动先驱——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后,毕生表达对澳大利亚丛林女性命运的关注。在《给天竺葵浇浇水》中,女主人公斯佩瑟太太的凄惨命运再现了澳大利亚丛林女性的生存卑微与凄惨。孤独、荒野、骇人的生活环境将丛林女性一步步逼入疯癫,死亡成为她们丛林抗争的唯一归宿。
本文拟从女性形象,母性形象,女性、母性与民族三方面剖析鲁迅与劳森民族建构中共同的女性应当占据主体地位的女性民族观。
一 “死亡是唯一归宿”的女性形象
鲁迅小说集《呐喊》与《彷徨》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病态人格:表情呆滞、见识短浅、教育匮乏、愚昧迷信、性格懦弱,但“种种病态人格既不是她们的天然禀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遗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心灵中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习俗渗透积淀蔓延的结果”1李明军:《文化蒙蔽: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鲁迅研究月刊》 2004年第7期。。一方面,祥林嫂是旧中国勤劳朴实、积极肯干的女性形象,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汇聚了中华民族女性所有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任劳任怨、善良淳朴的乡村女性,最后却在鲁镇一片欢庆、祝福的新年鞭炮声中凄惨死去。面对封建礼教的残酷迫害与摧残,她的抗争微不足道。
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是鲁迅对封建伦理制度残酷迫害女性的控诉,表达了他对旧中国封建礼教“吞噬”女性的强烈批判态度。如果说,“五四一代学人更多地将性别问题与社会政治改革及两性生活的实际情景联系起来”2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无疑,鲁迅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揭示有着“社会政治改良”的深层民族之思,表明鲁迅将女性命运纳入民族前途共同考量的女性民族观。
劳森在《给天竺葵浇浇水》中塑造了一个与祥林嫂凄惨命运相似的澳大利亚丛林女性斯佩瑟太太(Mrs.Spicer)形象。她独立顽强、隐忍坚韧、乐于助人。丈夫常年不在家,斯佩瑟太太独自在荒野孤寂、杳无人烟的丛林中照顾着数不清的孩子们,“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少个孩子”3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in Leonard Cronin (ed.), A Camp-Fire Yarn: Henry Lawson Complete Works 1885-1900, Lansdowne, 1984, pp.727, 729.。即便如此,她依旧热爱生活,热心助人,总是给新来到丛林的邻居提供帮助。在困顿的丛林生活中,她总是想方设法保障孩子衣食,常常为“孩子受不到学校教育”4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in Leonard Cronin (ed.), A Camp-Fire Yarn: Henry Lawson Complete Works 1885-1900, Lansdowne, 1984, pp.727, 729.而发愁,当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后,最终在“对一切都无所谓”(past caring)的彻底绝望中,安然离去。表面上,斯佩瑟太太的悲惨命运是由于丛林生活的心力交瘁导致的;实际上,“斯佩瑟太太的丛林悲剧早就注定了,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她们积极抗争命运的出路,也看不到她们恢复正常和回归社会的可能”1Rowley, Susan Elizabeth, Gender and Nation Form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sis)Wollongong University, 1993, p.236.,因而她的“死亡是唯一归宿”的命运,与祥林嫂一样,是无可逃脱的。
鲁迅与劳森女性民族观的共通之处还体现在他们对女性性格弱点的揭露和批判,目的都在于促使女性克服自身不足,成为更好的国民,以此实现女性在新兴民族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揭露深植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期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劳森对斯佩瑟太太性格弱点的揭示同样旨在对其进行克服和改造,就如他在积极宣扬丛林男性独立、勇敢、自由精神的同时,还“谴责”他们游手好闲、抽烟酗酒、放荡不羁生活态度一样,目的在于“纠正”。2Pons, Xavier, Out of Eden: Henry Lawson’s Life and Works—A Psychoanalytic View, North Ryde: Sirius Books, 1984, p.131.
《祝福》中,祥林嫂对自己像牲口一样被买卖并未格外反抗,但却誓死捍卫节操,想尽办法去“捐一条门槛”。面对灵魂的有无,她甚是困惑,寄希望于死后可以与儿子阿毛重逢,又害怕死后会被锯成两半被两个丈夫争抢。鲁迅揭示其愚昧迷信,旨在促成女性在自我觉醒基础上的自我改造,希冀她们成为更好的国民,实现新的民族的希望。
同样,斯佩瑟太太既有热情勇敢、善良淳朴、乐于助人的一面,也有着爱唠叨、爱抱怨、爱面子等不足的一面:
她总是爱抱怨,对孩子们唠叨不停。这已成为习惯,但孩子们对此倒是不以为意,大部分丛林女性都有爱唠叨的毛病……总体看,我觉得一个女人唠叨的毛病对孩子的影响要超过有着抽烟恶习的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尤其对敏感的孩子而言。3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pp.730, 726, 730.
斯佩瑟太太强烈而虚荣的自尊心成为导致其悲惨命运的性格弱点。威尔逊的妻子玛丽问斯佩瑟太太女儿安妮饿不饿,饥肠辘辘的安妮却回答说不饿,因为“妈妈告诉我,如果你问我饿不饿,要说不饿,但是如果你给我们东西吃,妈妈让我们接受,并要说谢谢”1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pp.730, 726, 730.;威尔逊与玛丽去斯佩瑟太太家看望她,斯佩瑟太太在桌上铺了一块打了补丁、破旧不堪的桌布,并致歉说,“真是不好意思,其他的桌布都洗了”,而孩子们的表情则表明“桌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2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pp.730, 726, 730.劳森揭示和谴责丛林女性的性格弱点,目的同鲁迅一样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以更好的形态参与到澳大利亚民族建构中去。
鲁迅与劳森在各自民族(半)殖民地历史语境下,共同将笔触深入“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底层女性生存空间,揭示她们凄惨命运背后的文化禁锢,表达了共同的“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能够、都应该、都将会拥有自己的身份,不管性别如何”3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s,London: Verso,1991, p.5.的民族理想。
二 苦难深重的母性形象
鲁迅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其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白话文论文是《我之节烈观》(1918),逝世前一个月的作品是《女吊》(1936),在《补天》(1922)中更是重塑了女娲这一人类伟大母亲的形象,“很认真地根据佛洛伊特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篇中的女娲的形象,是性的伟大和母性的伟大的统一”4参见舒芜:《母亲的颂歌——鲁迅妇女观略说》,《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期。,来阐明他对苦难深重母性形象的敬仰和赞扬。
旧中国的封建礼教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自女娲以来的伟大母性传统,正如莫言在“献给他的母亲,也是献给天下所有母亲的”5莫言:《丰乳肥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1页、封底。《丰乳肥臀》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世间的称谓没有比‘母亲’更神圣的了。人世间的感情没有比母爱更无私的了。人世间的文学作品没有比为母亲歌唱更动人的了”6莫言:《丰乳肥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1页、封底。。劳森母亲是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创办了澳大利亚第一份女性杂志《晨曦》(Dawn,1888),并积极撰文争取澳大利亚女性权利,为澳大利亚女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劳森。母亲在丛林生活中的种种艰辛让劳森对丛林女性命运格外关注,从而为改善丛林女性生活状况积极呐喊发声。母亲在艰辛丛林生活中照顾他们的同时,从未放弃诗人梦想的坚毅让劳森看到了丛林母亲身上的独特光芒。因而,劳森塑造出《赶羊人的妻子》(TheDrover’sWife,1892)中的“赶羊人的妻子”、《丛林中的孩子》(BabiesintheBush,1900)中的海德太太、《给天竺葵浇浇水》中的斯佩瑟太太等备受苦难的母性形象:她们在恶劣凶险的丛林环境中,积极抗争不退缩、乐观坚守不妥协、隐忍坚韧不言痛。
祥林嫂的生命无足轻重,孩子阿毛是她生前的唯一慰藉,然而儿子又“遭了狼”,祥林嫂总是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就说:“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然而,没人在意她深沉厚重的母爱,只是拿她当消遣,使得“母性的伟大,在历史的实现过程中,被异化力量所侮辱所损害”1舒芜:《母亲的颂歌——鲁迅妇女观略说》,《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 9期。,幸而“鲁迅对此有着炯照一切的视察”2舒芜:《母亲的颂歌——鲁迅妇女观略说》,《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 9期。,随后,他在《铸剑》(1927)中也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心目中理想的母亲形象”3竹内良雄:《鲁迅与母亲》,王惠敏译,《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
《给天竺葵浇浇水》中斯佩瑟太太历经苦难的母亲形象同样表达了劳森对澳大利亚丛林母亲伟大母性的敬畏和尊重,展现了“最忠诚、最有爱心、最专注、最具自我牺牲精神,很少考虑个人需求”4Diana L.Gustafson, Unbecoming Mothers: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Maternal Absence, New York: The Haworth Clinical Practice P, 2005, pp.xviii, 26.的母爱形象。尽管“母性的无处不在以及她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她们的个人职业生涯、社会生活、个人需求等方面都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母亲身份的认可和接受让她们乐于烦琐的家务和无私的奉献”5Diana L.Gustafson, Unbecoming Mothers: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Maternal Absence, New York: The Haworth Clinical Practice P, 2005, pp.xviii, 26.,因而,在叙事者乔眼里,他“每次看到的斯佩瑟太太,几乎都是一张因操心而憔悴的脸”6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p.727.,且鲜有怨言。丛林母亲是丛林孩子成长最温暖的摇篮,斯佩瑟太太历经苦难为孩子操心的“母亲形象”是澳大利亚丛林母亲形象的缩影,小说对丛林母性的赞美体现了丛林是澳大利亚民族孕育之地的深厚民族情感和鲜明的女性民族观。
在(半)殖民地社会语境下,鲁迅和劳森共同看到了备受苦难的伟大母性对于各自民族的独特意义。《祝福》中,鲁迅一再给人以警醒,如果不打破固有的封建礼教和变革“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就不能改变女性被侮辱、被迫害的命运;不弘扬和彰显母性光辉就不能消除中国“夫为妻纲”的糟粕思想,未来的中华民族就依然是看不到希望的旧中国模样。同样,在广袤的澳大利亚丛林,女性处于社会边缘的边缘,母亲们无论历经怎样的苦难,都在默默坚守和奉献着,就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着丛林大地,缔造着澳大利亚民族。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的历史档案,无论土著前历史,还是欧洲殖民史,都主要是关于西方白人男性活动的”1Kay Schaffer, Women and the Bush: Forces of Desire in the Australian Cultural Traditions,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p.2, 14.,那么有着深厚民族情感的劳森,他对苦难母性形象刻画背后的民族建构理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 女性、母性与民族
“民族是任何新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根基,新女性的公共空间和政治作用与民族发展程度密切相关。”2Joan Judge, “ Talent, Virtue, and th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2001, p.769.《给天竺葵浇浇水》中的斯佩瑟太太以及“那些终日在赤热炎炎下求生存的、可怜的丛林女性”3Henry Lawson, “ Water Them Geraniums ,” p.728.,振聋发聩地告诉读者历经生活苦难的丛林女性也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承载者”4Elleke Boehmer, Stories of Women: Gender and Narrative in the Postcolonial N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丛林女性在与丛林恶劣环境抗争时展现出的力量、果敢、坚毅等与男性无异,是澳大利亚的拓荒英雄”5Kay Schaffer, Women and the Bush: Forces of Desire in the Australian Cultural Traditions,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p.2, 14.。然而,“在民族主义组织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运动中,女性只是象征性的参与者而不是实际参与者”6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akland,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42.,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凄惨和母性的苦难往往都发生在狭隘的家庭生活空间,不为人所知;另一方面,在众声喧哗的男性话语中,女性发声的机会和渠道很少,以致她们的社会贡献与存在价值都尽付阙如。
对于祥林嫂的愚昧迷信、封闭落后,鲁迅有着“以恨为爱”7张鲁高:《先驱者的痛苦:鲁迅精神论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的民族大义,他深刻意识到国民性改造不仅是对男性的改造,而是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共同改造,因而对祥林嫂性格弱点的揭示验证了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目的。
在“丛林生活的父权话语结构”1Christopher Lee, “Looking for Mr.Backbone: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the Work of Henry Lawson.” in Christopher Lee (ed.), The 1890s: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ulture,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6, p.105.中,叙事者乔常年以抽烟酗酒对抗丛林孤独与烦闷的生活,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丛林女性面对丛林困境无比坚强、坚定和坚韧。十九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建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民族的呼声响彻云霄,劳森在此背景下创作了无数顽强抗争却命运凄惨的丛林女性形象,表达了他建构一个女性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拥有广阔表现空间”2Elleke Boehmer, Stories of Women: Gender and Narrative in the Postcolonial Nation, pp.90, 91.的崭新澳大利亚民族的理想。
祥林嫂与斯佩瑟太太淳朴、善良的性格和母性的温柔与勤劳可谓世界各民族女性道德品质的缩影。但是命运的多舛,使得尽管“到处都在颂扬她们的母性对于民族的意义,但她们在官方话语中大多都是缺位的、被边缘化或者被忽视的”3Elleke Boehmer, Stories of Women: Gender and Narrative in the Postcolonial Nation, pp.90, 91.,其抗争命运的唯一归宿也是疯癫与死亡。
如果说“阿Q是鲁迅‘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4吴正锋、舒小红:《鲁迅与沈从文民族观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祥林嫂身上的愚昧迷信则是鲁迅反省“女性作为国民弱点”的镜子,因为鲁迅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有摆脱历史桎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能进一步发展为“公民国家”和“人之国”5李永东:《鲁迅与“西崽”:半殖民文化的焦虑与民族主义的批判》,《求索》2017年第2期。。为了实现“公民国家”亦即“人之国”,鲁迅认为立人是“人之国”的基础,个体精神的觉醒是“群之大觉”,是“中国亦以立”的途径。6吴正锋、舒小红:《鲁迅与沈从文民族观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为此,鲁迅强调女性觉醒和对其疗救对于“人之国”建设的紧迫性、必要性,唯其如此,她们才能成为更好的国家公民,才能实现“通过新民与立人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7谭桂林:《现代佛教中的“语体文”观念与五四白话运动》,《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的终极夙愿。劳森深入孤独、枯燥丛林生活对斯佩瑟太太死亡悲剧的描写,对斯佩瑟太太女性和母性形象的双重刻画塑造了丛林女性以疯癫和死亡为代价与丛林男性一起缔造了澳大利亚民族的丛林精神,在新的民族中,理应树立一座祭奠她们默默奉献与牺牲精神的丰碑。
基于中澳文化语境和民族发展轨迹的差异,鲁迅与劳森的女性民族观又各有千秋。鲁迅以批判与否定的笔触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并深入国民劣根性层面希冀对女性进行改造,有着早日实现新的民族的急迫渴望,和女性与民族共进共退的女性民族观;劳森则从丛林女性狭小的生存空间探讨了澳大利亚民族理想的丛林性,证明了劳森对于澳大利亚女性与民族共患难、同荣辱的无限可能,体现了劳森的女性与民族荣辱与共的女性民族观。这种区别体现,“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基础上,平行研究才能在一种‘对话’的视野下展开,才能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互证、互释、互补,才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汇通”1曹顺庆:《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鲁迅与劳森共同聚焦于(半)殖民地历史语境底层女性的凄惨命运与母性苦难,“凸显她们在各自民族中的历史存在,宣扬她们对各自民族的道德和政治贡献”2Elleke Boehmer, Stories of Women: Gender and Narrative in the Postcolonial Nation,p.35.。
结 语
“女性是一个联结自然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性别共同体”3惠雁冰:《断裂的性别共同体——〈暴风骤雨〉中妇女的出路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鲁迅通过揭露女性悲惨命运的社会病根和女性自身不足来探求中国女性的出路,借此探寻中国女性和中华民族的出路;劳森则借助丛林女性的生存艰辛发出“女性在澳大利亚民族中如何才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民族未来之问。探究他们共同的女性民族观,旨在为这一学界尚无关注的比较研究论题抛砖引玉,文中不乏浅陋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