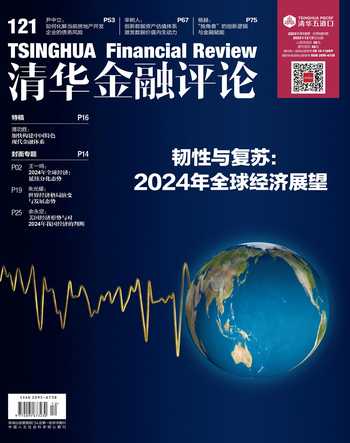我国上市公司中背信行为的基本监管思路:现状与展望
现有的司法解释并未对“违背受托义务”有任何规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于背信行为也无从进行行政认定,监管衔接缺失导致监管有效性不足。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思路,做好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衔接工作,形成监管合力,强化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关键少数”背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方能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规模与体量持续提升,证券市场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随之扩大,现代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也暴露得更为明显。基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设计的考虑及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践情况,“一股独大”而导致董监高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任或指派的情形较为普遍,极易导致此类人员在面临利益冲突时做出违背其对上市公司的忠实义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背信行为表面上是公司治理三大问题中“经理人对于股东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实质亦是“终极股东对于中小股东的‘隧道挖掘问题”。
现行规制方式
行政法领域以信息披露违规进行间接处罚
在法理层面,证券法虽归属于商法范畴,但亦具有明显的公法属性,其对上市公司规制的重点在于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相较而言,背信行为涉及对商业利益的实质判断,具有相当的私法属性。如将背信行为视作行为人对其与公司契约的违背,将其认定为民事领域的违约或侵权行为似并无不妥。
在现行法律规范层面,背信行为本身属于公司法及刑法的规制范畴。证券法赋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职权主要是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缺乏对背信行为的明确规定。在实践中,证监会一般仅认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不对背信行为予以认定和行政处罚。但考虑到背信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通常会将背信行为作为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的量罚因素。同时,2019年证券法已将信息披露罚款的上限大幅调高,一定程度上能够覆盖对背信行为的惩处需要。但是,仅将背信行为作为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的量罚因素,违规主体难以直观地感受监管对背信行为的打击,不利于向市场传递打击背信行为的监管信号。
刑事规制以背信罪追责案件数量少
在我国刑法条文层面,根据背信行为的具体表现(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不公允关联交易等),与之相关的罪名有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简称“背信罪”)、挪用资金罪和挪用公款罪等。在罪名要件上,背信罪和挪用资金罪在犯罪主体、客观表现形式上有所重合。若大股东做出占用资金的行为,可能同时涉嫌构成背信罪和挪用资金罪,此时属于“法条交叉竞合”。在司法实践层面,以背信罪定罪的案件数量少。截至2023年8月底,公开可查以背信罪定罪判决的刑事案例仅有11件。其中,刑期最长的是*ST中捷(002021.SZ)原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其他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决有期徒刑多在三年以下,实际最低为六个月;被处罚金多在数十万元左右,实际最低为人民币两千元。
刑事背信罪追责案件数量少可能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罪名要件问题。背信罪作为结果犯,其构成要件之一是“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认定难度较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标准的规定(二)》中明确,背信罪立案追诉标准是“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实践中,执法机关对于“重大损失”存在不同理解,经常以实际损失无法证明等原因不予立案。部分法院更为谨慎,倾向于仅认定已发生的实际损失。如果占用资金已予归还或可能归还,可能难以认定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是现实刑事立案的谨慎性问题。刑事立案亦有维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考虑,且追究上市公司相关方的刑事责任可能对地方经济及中小股东造成广泛的影响。
自律处分以声誉罚为主,效果有限
背信行为的一项主要表现为资金占用,以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行为的纪律处分情况为例:
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深交所共处分285件资金占用违规,其中有80件以自然人为监管对象,自律处分包括公开批评54人次、公开谴责29人次。同期,上交所共处分277件资金占用违规,其中有101件以自然人为监管对象,自律处分包括公开批评52人次、监管关注31人次、公开谴责14人次。通过沪深交易所的自律处分统计情况,可以发现两市的监管以声誉罚为主,资格罚较少。
交易所的自律处分惩戒效果有限,具体表现可为违规行为反复和整改不到位两方面的问题。如时代万恒(600241.SH)的相关人员在2018年11月因违规资金占用被上交所予以公开批评的纪律处分,又在2022年11月因同样的问题被予以公开批评的处分;再有安泰集团(600408.SH)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在2017年2月28日前偿还占用公司的资金及违约金共计约17.9亿元,但实际其并未按期履行承诺,并且公司因日常关联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及违约金还增加至18.8亿元。
以目前监管实践的反馈情况来看,部分上市公司对背信行为重视程度严重不足,违规反复发生,整改不及时,甚至在收到自律处分后仍维持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反映了以声誉罚为主的纪律处分的震慑效果较为有限。
监管方式的展望与考虑
现有制度下的监管优化路径
现行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做了相应规定,但缺乏对背信行为行政处罚的明确规定。因此在证券行政执法实践中,一般仅能认定上市公司表层的信息披露行为违法,不能对底层的背信行为本身予以单独认定和行政处罚。但是,交易所自律规则的规范运作要求和刑法的背信罪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了相应规制。由此,可以建立健全“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公安侦查-检察院公诉-法院审判”的流程体系用以监管背信行为。
在监管前端,交易所可以关注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事实,从规范运作角度对背后涉及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背信行为予以自律监管措施。在监管后端,行政执法虽不直接认定背信违法事实,但在调查信息披露违法事实的过程中,往往可以发现背后涉及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问题线索。因此可以通过移送材料的方式,将背信行为相关违法事实作为线索移送公安,对于重大案件可以开展联合公安调查,由公安部门发挥刑侦手段优势以调取和固定证据。
优化规则的推动方向
目前对背信行为的监管方式以交易所自律监管为主,但交易所的自律管理主要表现为对行为主体进行公开批评、公开谴责等声誉罚纪律处分,监管惩戒效果极为有限。虽然交易所近年来已逐步加大对资金占用的处分力度,增加公开认定资格罚的适用频率,但公开认定措施仅能剥夺大股东担任董监高的资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其继续利用大股东身份“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由其重新选任的管理层,可能也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制约效用。因而,仍需要推动立法规制背信行为。
在立法层面,通过修法将背信行为明确纳入证券法,以构建背信行为的独立行政法律责任,可以为证监会行政监管提供直接、充分的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衔接背信违法和背信犯罪的配套制度,形成层次清晰、优势互补的多层次追责体系,推动更多案件进入刑事领域。但将涉及证券法本身规制范围和证监会法定职能的重大调整,势必仍需进一步充分的研究论证。
在刑事司法解释层面,从历史上看背信罪的刑事判决数量较少,主要问题是刑法对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较为原则和主观,造成认定标准不明确、主观判断空间大等障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促进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落地。
在行政监管层面,应重点考虑督促归还问题。背信行为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可以通过规定相应量罚考虑因素等方式,督促违法行为人通过主动偿还、解除违规担保等多种方式消除背信行为的危害后果。
结语
2023年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当前资本市场中对背信行为的监管,在民行刑全链条上存在一定脱节,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思路,做好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和刑事追责有效衔接,强化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关键少数”背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进一步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
(朱力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助理经理,傅福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编辑/王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