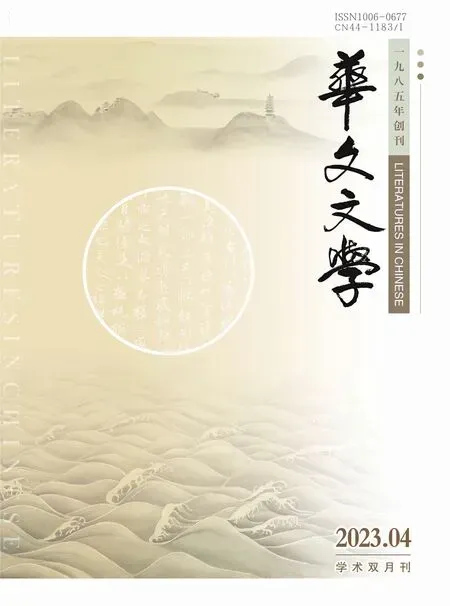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五四文刊》与1950 年代的香港校园文艺
朱云霞
在讨论1950 年代香港文学的发展面貌时,香港青年作者的成长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以此为核心,研究者通过青年报刊围绕青年创作、青年文化教养、文学主体性等展开了相关讨论,《中国学生周报》《海澜》《大学生活》《文艺世纪》《青年乐园》《文艺新潮》等都是聚焦较多的报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影响较大、发行量较广的青年报刊之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自发创办的校园刊物,如香港官立文商专科学校文学系学生创办的《五四文刊》、崇基学院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华国》等,也以校园文艺的方式折射了香港文学发展的阶段特性,是我们从“微观”视域进入历史语境的一种方式。
《五四文刊》很容易和新文化运动之“五四”作关联设想,实际上是香港官立文商专科学校文学系1954 级学生创办的校园文艺期刊——“刊名五四,乃我级名”①,所刊作品为该系师生撰写的学术评论、散文、诗词、小说和剧本等。与一般校园文艺刊物不同的是,其编创者多是再进修的香港中文教师,文艺热忱既源于职业需要与个人兴趣,也和重返校园后被激发出的文学热情有关:“我们是念文学的一群,我们认为只有不断写作才有进步,只有不断的学习才有创造。我们凭着这一点勇气和热忱,决朝着中国文学的大道迈进,为保存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而努力。”②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受香港自身的文化观念与审美习性影响,也与文学系的教授们通过授课、文学活动等进行的引导有关。但是,以“五四”为名,显然不仅是时间上的契合,通过刊物中的师生交往记述、文化思考、古体诗词创作及新文学实践,我们看到的是在时空交错的“五四”延长线上,20 世纪50 年代初期,香港一群师生“‘借文学革命’之义,想象、建构的正是延绵2000 多年不断更新的中华‘诗国’”③。不过,因是小范围发行的校园刊物,且仅有两期,1953 年的创刊号为第1 期,1954 年的毕业号为第2 期,是特定群体在短时期内的文艺活动,仅为当时香港校园文艺的一个侧影,故研究者较少关注。但回到历史语境,《五四文刊》作为微型校园刊物,可以说反映的是介于《中国学生周报》和《青年乐园》之间的另一种文化空间,教授们的文化指导和文艺实践关乎文化传统在地承续与重建的问题,而青年学生的文艺观念和文学创作则体现出立足香港回应“引导”的现实感,此种校园文艺已然超越青春色调或校园文化的范畴,为我们观察1950 年代香港文学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向度。
一、“时逢五四”与非典型校园刊物
在20 世纪50 年代的香港文化场域中,左、右翼阵营都非常重视青年读者,“出于推行意识形态、抢夺文学市场和青年读者等目的创办了一批青年文学刊物,但双方在具体的杂志定位、文章选取等方面大多均以‘培植青年文学力量’‘推动中国文学发展’为中心”④,如友联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面向学生群体的刊物《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其中1952 年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影响最为深广,而左派文艺刊物中当时颇受中学生欢迎的是创刊于1956 年的《青年乐园》,被认为是可与《中国学生周报》分庭抗礼且市场份额占有较大的报纸⑤。尽管政治倾向与文化立场不同,但青年报刊对20 世纪50 年代香港文学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香港青年的文化素养培育、文学品味形塑以及创作引导等层面。不过,与发行甚广、影响较大的青年刊物相比,还有一些校园刊物也值得关注,其作为“微型”文化场,并不只是青年与校园的叠加,在记录特定时期青年文化心理的同时,也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香港青年及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而在校园刊物中,微小如《五四文刊》又是“另外”之中的“例外”。
《五四文刊》由香港官立文商专科学校文学系1954 级学生创办,在第二期的编后记中编者透露其资金来源:“最伤脑筋的经费问题,终于决定由同学们自想办法筹足后,这样才算解决了”⑥,但它又非典型的校园刊物。原因之一是学校的性质——官立文商专科学校由香港教育司创办于1951 年,英文名原为Evening School of Higher Chinese Student,故有“官立汉文夜学院”之称,设有新闻系、文学系和商学系等,学生毕业后不授学位,没有校址,主要借用香港大学的校舍上课,“创办的目的是解决中学毕业的升学问题,希望以中国语言为媒介讲授高级学术使中英两大文化得以交流,使学生可在短期的专业训练之后成为香港优秀的新闻商界和教师方面的人才”⑦。尤其当时香港中文中学师资缺乏,以此种方式创办学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压力,时任署理教育司的毛勤先生就曾指出“中文中学缺乏师资的情形,更为严重,这些学校低级的部分学科所需的师资,可以由官立文商专科学校加以初步培植”⑧,“规定凡是念文学系的现任教员,若学年考试全部合格,可领回已交的全部学费”⑨。可以看出该校极为重视中文和文学教育,且教授阵容强大,“有的是过去国内的大学教授,而现在在港大任教,有的是在香港大专学校任教者”⑩,如谢扶雅、柳存仁、谭维汉等。故官立文商专科学校在当时也被认为“在本港几间大专学校中最为特殊”[11]。
文学系“第一期的同学,录取有四十人,实际到读的二十八人”[12],后又有同学陆续转入,毕业时有三十五人。《五四文刊》的创办者们,正是最早一期(1951 年秋)入学的文学系学生。作为该校首届进修学生,文学系同学的文艺活动较为丰富,不仅成立系会,还组织各类文艺活动,“成立话剧组,顾问是巢校长和谢教授等,导演是誉满中国剧坛的胡春冰教授,助理导演是郑立基同学。胡教授选定了曹禺名著《正在想》为剧本,全体演员出动,定期排练,准备成熟后在‘丽的呼声’播音。”[13]巢校长即该校首任校长巢坤霖,胡适在《南游杂忆》中曾提及与其谈论香港教育问题:“香港的教育问题,不仅是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罗仁伯先生细谈,才知道中小学的中文教学问题更是一个亟待救济的问题”[14]。巢坤霖出身望族,是清末圣保罗、黄仁、圣士提反的学生,后留学英国,在Durham University 和University of London 就读,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拉丁文和英国文学,于1921 年返回香港出任教职[15];此后曾担任国际宣传处驻澳大利亚悉尼办事处主任,1949 年任务完满返回香港[16],1951 年任香港官立文商专科学校校长。从早年经历可以看出巢坤霖对香港教育有切身经验,也极为重视文学教育,在《五四文刊》创办时曾题字鼓励学生发展文艺活动,报道中也有记载其参与学生演剧活动,1953 年11 月巢坤霖因病去世,《五四文刊》发表过学生的诗歌《灵魂在那里》,将失去校长之悲形容为“如孩子丧母,如妇人丧夫”,以“灵魂在那里”表示爱与精神之不灭。
以上可知,《五四文刊》的编创者身份较为多元。他们既是在读学生,又是社会上的职业人士,以香港中小学教师为主——“同砚凡三十有五,而任教职者三十”[17]。故他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化思考,不再是典型的青春风格或局限于校园文化,行文与表达都相对成熟,如黄国栋的《文艺与个性》、乐季雨的《青年人的使命》、曹美屏的《哲学与民族文化》等。他们对于为何继续进修,以及对文学和写作的理解,也都有相对独立的表述和判断:“今乃拓其余时,以所习经史之业,百家之言,诗赋词曲之选,伦理社会诸科,以至文字文法之探求,小说与戏曲之赏悟,穷逻辑哲学之秘奥,窥西洋文学之涯涘,发为文章,各尽其长汇辑文存……志不逮乎眩世,仅在光其所学……而毋负吾师殷殷之望”[18]。故从“青春”色调和学生编创者角度来说,在香港当时的校园文艺刊物中,《五四文刊》具有独特性。
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非典型”元素,即《五四文刊》的作者中教授占据重要比例。第一期中为刊物撰稿的教授有谢扶雅、曾希颖、罗香林、阮雁鸣、赵尊岳、柳存仁等;第二期为刊物撰稿的教授有谢扶雅、阮雁鸣、赵尊岳、曾希颖、柳存仁等。透过《五四文刊》所呈现的师生交往与互动形态,可以看出教授们其实是一种介入性参与,既指导学生们的文艺活动,也积极表述自己的文艺观念或文化思索,从形式和内容等多个角度影响了学生们的办刊理念。首先,来看一下《发刊词》和排在首期第一篇的文章《“五四”和新作家》。在《发刊词》中,确实有对“五四”的遥想与回应,可以看出是借“五四”之象征意涵,表达彼时香港青年学生当以历史精神自我激励、直面现实并勇于承担责任的时代意识:
时逢五四,亦饶深义,岂独声气相求,学业砥砺而已乎!吾人在卷册劳形之余,进修继昝感晚近国学凌夷,沉冥不返,无复彰时,邪说横流,真伪不辨,寻求坠绪,启发幽光,此固责不容辞,不敢不勉也。夫无所得于心而妄以告人者,谓之私己。爰于领畧所得,编成是卷,求正先达,借助他山,此刊之所由也。[19]
而与《发刊词》中青年人的主体自觉相呼应的,是为师者的期待——谢扶雅的《“五四”和新作家》,由本校“五四”级学生,联想到新文化运动之“五四”,进而展开讨论,以激励学生:
“五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也更是中国文学革命运动。在这一次运动中,曾经出版了许多云蒸霞蔚的刊物,产生了无数龙腾虎啸的作家,而达成了文学革命的伟大任务。然溯中国文学史上的革命运动,“五四”不是第一次……至今日,海角的香江也尚有流风遗韵。……正如这诗人节的主人公永给中外人士无限太息,激动,兴奋;现代世界,黑云笼结,陆沉之凶兆已具,全人类玉石俱焚之期日迫一日。热情敏感的新诗和新作家必然地会蓬兴崛起,椎轮大辂,挽既倒之狂澜!“五四”——五四级诸子乎;企予望之矣![20]
谢扶雅[21]也即上文提到的学生话剧社的“谢教授”,在该校讲授《中国文学史》《修辞学》《经学》。通过《五四文刊》相关文章的记述,可以看出谢扶雅不仅为刊物撰稿,也积极参与学生的文艺活动,在系会第二届主席改选时,谢教授即席题赠新诗予以鼓励:“在山明水媚的南天,产生了文艺的王国”[22],可以说参与、指导学生活动的实质,是对香港青年承续“五四”精神有企望,对香港文艺有新期待。同年一月,谢扶雅发表在《中国学生周报》的《香港的中国学生》也谈及对青年学生和香港的双重期待:“这里正是中西两方文化都落了空的三不管地带,没有见到如我们所理想所希望的,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文化中心……然而,学生们不需自哀所处的绝境和残酷的命运,我们应有自信和自信力,中国学生运动素具伟大光荣的历史”[23]。
虽然《五四文刊》仅有两期,但非常重视教授们的意见或建议。柳存仁在第一期发表的《做自己和为别人》中提及当时学校各系办刊风尚,肯定“五四”级办文艺刊物是“著丁先鞭”,但也觉得“就出版刊物来说,在一所大学或专科规模的学校里,大家只是分头摸象式的,各就所长,以及自己所特殊喜欢的事物来撰述,发抒一部分纯真的观感和研究的心得,固然未为不美,但好处似乎也就是止于此了,若然说到学术空气的培养,和寄托研究的热诚,那么这样的书刊,当然我们谁都会觉得不足。”[24]显然柳存仁和谢扶雅是从不同层面提出新期待,谢扶雅是站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延长线上,期待香港青年成为“新作家”;柳存仁更在意“研究”和“学术”,甚至建议五四级学生向学校申请编纂学术性杂志。在第二期中,《五四文刊》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学生们的学术探讨型文章增多了,有郑立基的《论文学的〈内在倾向〉》、黄振权的《中国文学教学漫谈》、吴月华的《中国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的演变》、吴鸿顺的《中国小说观念之演进》、唐和贞的《唐宋两代文学的价值》、马秀文的《短篇小说的取材与布局》等,总体数量较多。而以文学研究的态度,论及“五四”文学革命的文章《中国散文发展述评》,可以看出是从青年学生角度出发,但受到教授们影响的文学思考:
甲午迄今,外受列强之瓜分,内有军阀之专横因而产生五四文学革命,此后由于西洋科学之输入,文人因鉴于国家之危亡,为救国救民,文学乃由黑暗时代再复趋于新生,其始由于孙文学说之影响,而蔡元培、胡适、鲁迅等继之在文学上针对时病,发挥时事评论,用浅白之语体以报道民众觉悟,使知国家为民所有、政治为民所管,由颓废之旧有生活,转入民主之潮流,而中国文学至此时为数千年来,划时代之改造也。[25]
然而吾国吾民,久受儒家伦理观念之熏陶,于新文学之现阶段,总以抨击旧思想旧道德,一切均西欧文化为依归,以致国族失其重心,政治陷于混乱,新旧生活方式,尚未达到明朗时期,故近代中国尤处于剧变时代,五十年来内忧外患之交迫,予民族莫大之创伤,遗留万劫不复之祸患,神州陆沉,杀机四起,文化之出路尚在徬徨昏黑之暗夜,文学之发展在风雨飘摇之歧路,救国救民之最后觉醒,是亦吾人之责任。[26]
作者在梳理中国散文发展脉络之后,肯定新文学之散文风格,认为新文学的写法平浅通俗,融合欧美散文技法,有时代感,言之有物,并以《胡适四十自述》《鲁迅传》为例证,但其文学观念及文化理念显然又是站在“五四”的延长线上进行的总体性思考,文章结尾的历史感与忧患意识和上文所引谢扶雅的慨叹:“现代世界,黑云笼结,陆沉之凶兆已具”的情绪基调是相通的,而“救国救民之最后觉醒,是亦吾人之责任”则有回应师者召唤的意味。
二、“五四”之外:香港青年的文艺观
《五四文刊》并无政治背景,其编创者虽心怀“五四”情结,但“五四”更多的是作为象征性文化符号而存在,在“青年人”身份和社会意识层面自觉地将“五四”视为精神资源,因此他们的文章多在结尾处表达改变社会的担当意识。而具体到文艺观和文化理念,这一群学生的认知则显示出立足香港的、在“五四”之外的承传与探索。说其立足香港,未必是明确的香港主体意识,而是身在香港,或从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整体性角度谈文学应有的样态,或针对香港现实谈对文艺的理解和期待,在以“中国文学”和“民族传统”为基点的文化共同体想象中,具有独特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实感”也可视为青年群体更加关注香港自身文化建设的表征。
其一,从对新文学的传承与在地发展来看,《五四文刊》同仁强调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应有不受环境约束的独立性、自由性。不同于祖国大陆在1950 年代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选择性继承,尤其是对“五四”传统中人文主义与自由理念进行清理,香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文化影响,但香港文坛并未像祖国大陆或台湾那样受制于文学制度,而是有相对自由的文学空间,“文学创作一直拓展着其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对峙的脉络”[27],黄万华就认为文学真正能够超越政治束缚,又在于其对文学常识的坚持[28],他以20 世纪50 年代的香港青年刊物《海澜》为例,论述了此时文坛对文学的“常识性立场”的坚持,认为正是以文学常识的力量保存、发展了文学自身。在《五四文刊》中也有相关论述,尽管文章总量不多,但也可梳理出刊物同仁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倾向。当然《五四文刊》的作者们并非以“常识”立论,他们所秉持的文艺独立于政治,文艺应当是有个性的、自由的观念,实则是从更为素朴的角度或回应师者引导而进行的文艺思考。
较具代表的有黄国梁的《文艺和个性》,郑立基的《论文学的“内在倾向”》。《文艺和个性》认为文艺作品是作者个性的再现,“必然是非教条主义的”,因此对文学受制于“文艺政策”和“整风”进行强烈批判,认为在压抑和束缚的环境中作者是不愿提笔的,“真正的梦,真正的悲哀,真正的希望和真正的爱情”是无法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要文艺服从于政治,牵着作者的鼻子走”是泯灭作者个性,摧毁艺术的生命,强调文艺作者应该是独立的,自由地抉择所写的内容,“只有撇脱了政治束缚,粉碎思想的锁链”,作者才能真正表现个性,文艺作品才有丰富和美丽的生命。”[29]从中可以看到此时香港青年对文学的热诚,而这样的文学观念在当时也是较为普遍的。即便是带有政治倾向的青年刊物,在面对青年群体时,也非常注意文艺观念更加符合香港当时的文化语境,比如《青年乐园》虽然强调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经典的教化作用,但并不排斥或反对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个性,因此刊发的文学作品不乏写爱情、都市之作,也不乏风格感伤或唯美之作。
郑立基的《论文学的“内在倾向”》认为文学作品的实质主要由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决定的,主要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三种倾向谈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并且认为三种倾向,并无高下,各有优点和缺陷,以欧洲自然主义和《红楼梦》为例说明三种倾向配合得当就可能产生价值高的作品。显然这与唯现实主义为上的文艺观不同,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性及其不受环境支配的独立品格:“艺术与生活,一样的是我们个人的内部要求的一种表现,一样的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如果生活全然要凭借环境的支配,岂不是艺术家的创造,完全否定?”[30]不仅如此,还对文艺研究者提出期待——“改造境遇,刷新时代,是研究文艺者应有的精神与认识”。这种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对文艺研究者主动精神与独立判断意识的肯定,体现的同样是一种独立、自由的文艺观,也可以说是《五四文刊》的内在追求。
其二,从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来看,《五四文刊》有保存国粹、赓续传统文化的自觉。赵稀方在谈论早期香港新旧文学关系时,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是香港历史上中文文化承传的主要形式,担当着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角色。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在大陆象征着封建保守势力,那么它在香港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31]。因而,在香港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学如旧体诗词一直有其自身的脉络。至20 世纪50 年代初期,香港社会文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但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却未发生重大转变,旧体文学因南来文人的带动呈蓬勃之势,特别是学者诗人如饶宗颐、曾希颖、赵尊岳等,到香港后比较活跃,诗文述作并重,香港学者程中山就认为,“这些南来文人后来大多扎根香港,或办学育才,或结社唱和,提倡国故文学,促进香港五六十年代旧体文学蓬勃发展”[32]。被视为“本港汉文最高学府”的香港官立文商专科学校,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也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如曾希颖讲授《诗学》《诸子学》、赵尊岳讲授《词曲》、黄孟驹讲授《散文名著》、谢扶雅讲授《经学》。曾希颖和赵尊岳的诗词“早已鹊名中外”[33],为不少青年学生仰慕,但他们也在《五四文刊》发表诗词作品和研究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学生的文学观念。不过,这些学生作为有职业的青年,已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理念,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学的态度,并不完全承袭自老师,还和香港自身的古典文学传统有关,比如《发刊词》是极为雅致的文白兼容,其对文化的延续和发扬更多指向“国学”:“同人既获苟安,得修国学,宜有坚宏之力量,延续文化,应具命脉之机能;庚续发扬,是以非积学不为功,舍积理无由致,然积学积理,惟在研求,依仁游艺、井蓄兼收,同情与珍惜,究不如敦品励行之自珍,灌输与提挈,孰若勤学好问之为愈。”[34]
从两期内容来看,学生谈论古典文学的文章也较多,如张汉的《屈原与庄周》、黄容之的《略论温韦之异同》、陈载联的《庄子思想及其文学》、唐和贞的《唐宋两代文学的价值》、卓丽英的《漫谈诗词》、吴鸿顺的《中国小说观念之演进》等,即便论及新旧文学分野,也是较为客观地评述,较有代表性的如卢干之的《诗和词的认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谈论诗的发展,论及文学革命以后诗歌的发展也是新旧并重,认为“无论作新(近体)诗也好,做旧(古体)诗也好,第一个步骤是取材,而其所包含的资料时无所不具”,不过,最终目的则是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受到毁坏,而“本校为本港汉文最高学府,我们这一群学子,孜孜屹屹者,亦为钻研中国国粹,以期保存固有文化,因为香港,大多数人都注意研究ABCD,剩下一块田园,我们不耕耘,又有谁去耕耘呢,吾侪其勉之!”[35]与此对应的是,青年学子的创作也不乏旧体诗词,如《浣溪沙》《忆江南》《望江南》《相见欢》《渔家傲》《清明》《江城子》等旧体诗词都与新诗作品同在“诗词”篇。
其三,注重文艺的教育功能。《五四文刊》的这些青年们并非1950 年代香港文坛的重要作者,他们只是极为普通的一群,有不少都只在本校刊物中活跃,但正是这些知识青年素朴的文学认知,从侧面反映了此时香港青年对文学的某种理解与期待。并且,他们的文学认知并非停留在个人见解层面,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也多从实际出发探讨文学的教育功能。除却一些谈论文学教学法的文章,如《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贡献》《中国文学教学漫谈》《漫谈儿童教学法》等,还有像吴冰的《学校戏剧与教育》,认为有提倡学校剧运的必要,更进一步期待戏剧成为教育社会大众的方式,不负戏剧教育的真意:“中国的话剧运动,由清末到现在都是由学校剧运去支持的,虽然在抗战时期有点不同,但是今天也是一样由学校去支持,其中当然有不可以分离的因素和渊源,……戏剧是一种集体的艺术,要有合作精神,由演剧而训练出群体的道德,这就是公民训练的一种新方法了”[36]。此外,如刘世珍的《闲话粤曲》,批判当时粤曲内容低俗,范围狭窄,多用赤裸裸的市井口语,不乏隐秘颓败之风,“不忍卒听”,认为香港的粤曲家们,“可不必斤斤思索曲辞的绮丽,也不要渴望在世界乐坛上出风头,只要把着崇正的观念,本着好音乐的精神,把粤曲改造成为一种健全的音乐便很够了”[37],“崇正”与“健全”的诉求,正是基于粤曲在香港流行,对一般民众有着重要影响,但内涵不足,亟需更新。当然,他们对文学社会价值的关注,并不全然出于过往文学史论述中知识分子对香港商业化环境的抵抗,而是作为香港青年改善社会风气以“立人”的教育理想。
三、群体与时代:两种文学风格
《五四文刊》所刊文学作品,因作者的群体差异形成两种风格——以学生为主的唯美、浪漫与感伤的青年文风;以教授为主的沉郁、凝重与沉着的学者气度。这两种风格共存于特定时期的校园刊物,为我们观察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转型提供了独特角度——校园文化生态如何呈现/ 影响香港文学的发展?在过往论述中,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学院和香港大学的学者作家,尤其是1949 年前后的南来作家所建构的校园文化成为观察香港文学的重要视角,“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激情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故国之思’,提升了香港这一殖民性、商业性城市的文化品味。这种文化生态有助于香港文学的生存发展”[38],但是经由《五四文刊》,我们或可通过具体个案延伸考察向度——学生创作如何呈现时代,教授创作在影响文坛的同时,如何引导学生?
尽管《五四文刊》的学生创作具有总体相似的风格,但从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个体经验和精神世界来看,这一群香港青年,又可分为香港本地人和大陆南来香港者。郑立基的小说《邂逅》与署名珍的《缘》,讲述的都是香港都市的故事,属于浪漫主义的现代风格,注重细节和心理描写。《邂逅》写的是电车奇遇,青年男子家彦夜乘电车,邂逅年轻漂亮的马小姐,后又在同学家的舞会上相遇相熟,陷入爱恋之后,家彦说出自己的家庭情况,不料马小姐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因为她正是被他舅舅在台湾抛弃的女人。而《缘》写的是“我”在每夜的渡海轮船上都会遇到漂亮的“你”,“你”的一颦一笑都引起“我”的遐想,一切都朝着浪漫和美好的方向展开,但是“我”跳出叙事,告诉大家“你”突然不见了,又俏皮的说:“朋友,你想象中充满罗曼缔克的故事,是这样的结尾,可有替我难过吗?谢谢你的关心我,但我对这故事感着缺憾的满意。因为,我知道,它终不会如你所想像的结果,因为,因为——我也是一个女孩子。”[39]《缘》中刻意为之的浪漫叙事、轻松自如的心境,正与《邂逅》营造的唯美浪漫氛围,追求日常中的传奇一样,是都市青年最普遍的情感表征,而故事发生的场所又是极具香港都市特质的流动性空间,这是香港青年的香港故事,虽浪漫虚无,但又是“现实”的。莫志珍的小说《归来》,在叙述方式上和同学作品大抵相同,注重心理描写,聚焦细节,但写的却是一个与香港无关的大陆青年抗战的故事。当然写在香港,与此时祖国大陆的革命历史叙事是完全不同的,小说只是将抗战作为表现个体心理、家庭伦理的背景。小说中的情感表达是理性、客观的,大陆经验也是隐藏的。但在诗词和散文这类抒情作品中,南来青年的怀乡思归之情则倾泻而出。比如《浣溪沙(乡思)》:“无语高楼倚晚风,环山树色绿重重,思乡千里白云封。故国已教人事改,那回欢笑几重逢,回肠荡气永难穷。”[40]吴鸿顺的长文《杜鹃声声啼暮春》,也表达天涯落拓、去国离乡之悲。南来青年的失落和乡思,正与此时香港文坛南来作家强烈的“故国之思”相同,是此地时代情绪的一种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文刊》中,还有一种叙事有效弥合了香港—大陆经验的差异,郑立基的小说《情书和方帽子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大陆青年融入香港的故事。小说中,金兆光和梁青华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原本都有适合专业的职业,但时局不好,先后到港,因青华老家向来都在香港,凭借父执提携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兆光只在香港的一间私立学校做了小学老师,薪水微薄,因为有青华鼓励和安慰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日子灰暗。私立学校校长的女儿施小姐年近三十,尚未结婚,她要求的对象是无论贫富,但要戴过方帽子即有学位,还要会写情书。兆光写给青华的情书不小心被施小姐看到,因未署名被她误解是写给自己的,于是产生结婚之意,但兆光不为财富和稳定诱惑,化解误会,辞职离去。虽然在小说题记中,作者想要说明的是“物质”不能压倒一切,健康的爱情不是“物质”所能换得,“精神”更为重要,可以说是青年人追求理想爱情的表征。但在叙事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香港的爱意——香港在小说中被说成“天堂的领域”,即便描述兆光处境不好,生存苦闷,也因对校长女儿形象的漫画式勾勒带来的轻松氛围而消解。当这些作品共处一体,我们可以窥测校园文化与整个时代、与香港文学转型之间的关联:青年学生不仅呼应或反映时代潮流,也以自己独立的文学思考,延续现代青春叙事和香港都市书写,而他们在其间所表露的香港经验、香港情感,也是此后更多青年书写香港、建构香港主体意识的前奏。
从《五四文刊》中的教授创作来看,赵尊岳、曾希颖的诗词雅致厚重,对学生有引导和示范作用,亦是此时香港南下文人借由诗词唱和复兴传统的潮流表征,但从校园文化与香港文坛的深度关联、对新文学传统的承传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教授们的剧本创作以及对学生演剧活动的引导。《五四文刊》尚未出版时,文学系就成立了话剧组,在胡春冰教授的指导下曾演出曹禺的剧作,而中文系大部分同学也是该校云汉剧社的主要成员,剧社演出的历史剧《虎符》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该剧主要有巢坤霖校长、胡春冰、谢扶雅等人的积极参与和指导。据报道,此剧曾一连四晚在铜锣湾黄仁书院礼堂演出,第一晚招待文化界,嘉宾云集[41]。胡春冰抗战时期就曾到香港,是“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发起人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1949 年又到香港,致力于推动香港话剧运动:“倡议小剧场、全港戏剧人才团结,使戏剧运动扩大公开”[42]。《五四文刊》第一期就有“戏剧”小辑,第二期则发表了柳存仁的历史剧《月落乌啼霜满天》。胡春冰和柳存仁都是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的主要成员,该协会是1950 年代“香港最具影响力的话剧创作和演出团体”[43],并且努力推动校际戏剧比赛。《月落乌啼霜满天》曾是1953 年在皇仁书院参加校际比赛演出获得冠军的剧目。剧作主要讲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某小国一农村家庭因饥饿穷困,无力为老母治病预理后事,因而兄弟、母子之间发生冲突,进而产生误解,最后家人和解的故事。剧作一方面肯定以仁义、孝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将民不聊生的根源指向“苛政猛于虎”。《月落乌啼霜满天》是柳存仁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剧作,也是以古装创作躲避香港左右政治对峙的表现。借由教授们写剧、指导演剧的文艺实践,以及当时他们举办的一些列戏剧讲座,如胡春冰、柳存仁等讲“中国戏剧源流”(1952 年)、胡春冰等讲“戏剧与中国文化”(1953 年)[44]等等,可以寻出校园文艺与香港文坛之间互动的线索。而柳存仁的剧作在校园刊物发表、又由学生演出,也让我们看到南来文人不仅以指导学生演出现代剧作的形式让香港青年学习、接受中国现代剧作,也通过创作剧本、传播剧作的形态将推动香港话剧运动与引导香港青年文艺实践关联起来。
四、结语
与1950 年代影响较大的青年刊物相比,《五四文刊》并未培育出群体性或代表性的作家,但其以非典型校园刊物的样态,形构了独特的校园文艺景象,为我们思考香港当代文学的发展向度提供了微观切入口。一方面,《五四文刊》立足香港,从青年身份与时代意识层面自觉承续“五四精神”,在五四延长线上探索文艺的本质属性问题、热诚思考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续与转化,具有鲜明的现实感,但又超越了校园文艺的局限性,其文化视野往往是历史与现实融汇,言香港触及的却是“吾国吾民”与中华文化共同体;而青年学生的文学创作则从一般性角度表征了香港经验、香港情感的复杂性。其次,教授作者的论述或文艺创作,向内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学教育,起到引导、示范作用,其现代旨趣或古典素养皆有培育学生审美品味的意义,并且这些学生也会以“师者”身份培育新一代香港青年,潜移默化的文学影响也超越了单纯的校园文艺;向外,教授作者又是将校园文艺和香港文坛建立关联的重要文化中介。可以说,《五四文刊》及其呈现的校园文艺形态,为我们观察当代香港文学发展提供了微妙的线索,可探寻出名报大刊之外的时代记忆与文化实践。
①[19][34]黄振权:《发刊词》,《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②卢干之:《编后余话》,《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③黄万华:《“前存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背景下的香港澳门文学》中论及《五四文刊》,并有此论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 年第5 期。
④王艳丽:《试论战后香港文学转型——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年文学刊物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 期。
⑤当时为《青年乐园》做过派报员的石中英曾说“在1956 年创刊号的印刷数为5000 份,在六十年代高峰期超20000 份……在周报行销的11 年半时间内,与同类的‘竞争对手’《中国学生周报》相比是四六开,即《青乐》占市场40%,而《中周》占市场60%”。见石中英:《我们认识的〈青年乐园〉十之六》,《大公报》,2014 年6 月6 日。
⑥[33]编者:《写在刊后》,《五四文刊》1954 年第2 期。
⑦⑨⑩[11]黎键:《香港官立文商》,《中国学生周报》,1956 年5 月26 日,第6 版。
⑧《展望与检讨》,《五四文刊》1954 年第2 期。
[12][13][22]郑翰屏:《本会沿革与展望》,《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14]胡适:《南游杂记》,收入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1 卷上),东方出版中心2002 年版,第179 页。
[15]黄振威:《胡适在香港: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文学研究》2006 年第3 卷,第178 页。
[16]郭存孝在《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有一节《中国教育界前辈和驻澳洲外交官——巢坤霖》专门介绍巢坤霖。
[17][18]黄振权:《卷首语》,《五四文刊》1954 年第2 期。
[20]谢扶雅:《“五四”和新作家》,《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21]谢扶雅是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文学奖、翻译家,致力于比较中西宗教哲学文化的异与同,力主两者融会贯通,早年曾赴日本、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教于岭南大学,1947 年7 月离开广州至香港,曾在岭英书院任教,1952 年任教于香港官立文商专科学校。
[23]谢扶雅:《香港的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周报》,1953 年1 月2 日,第2 版。
[24]柳存仁:《做自己和为别人》,《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25][26]江仰和:《中国散文发展述评》,《五四文刊》1953 年第2 期。
[27][38]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第25 页。
[28]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 年版,第58 页。
[29]黄国梁:《文艺和个性》,《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30]郑立基:《论文学的“内在倾向”》,《五四文刊》1954 年第2 期。
[31]赵稀方:《小说香港·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7 页。
[32]程中山:《居夷风雅参时变:论百年香港旧体文学之发展——〈旧体文学卷〉导言》,收入陈国球、陈智德:《香港文学大系·导言集》,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6 年版,第309 页。
[35]卢干之:《诗和词》,《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36]吴冰:《学校戏剧与教育》,《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37]刘世珍:《闲话粤曲》,《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39]珍:《缘》,《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40]《浣溪沙·乡思》,《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41]《云汉剧社公演〈虎符〉》,《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42]何倩霞:《从组织到演出》,《五四文刊》1953 年第1 期。
[43][44]胡文谦、胡星亮:《1949-1966 年香港话剧创作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