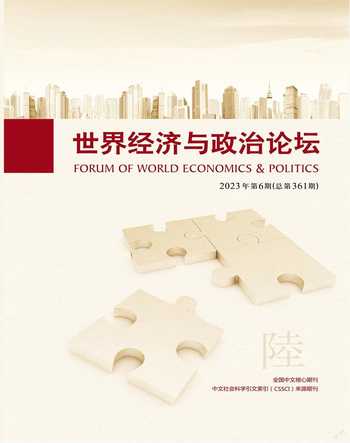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文化动因与影响
陈丽颖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其中,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文化因素在信任的形成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首先,基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所形成的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不同文化间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不仅需要文化上的认同,也需要彼此尊重文化差异。文化上的相似性有利于促进信任的形成;同时,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通过构建信任关系来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国家和人民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受两国文化中关于信任的理解方式以及国家内部信任程度高低的影响,各国的国际信任水平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不同文化间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加深文化间的了解,减少误判,从而增进互信,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价值观 国际信任 文化交流
一、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这一理念具有政治、经济、安全、文明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内涵,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中,信任关系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石,而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更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价值观上的共识有利于建立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从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信任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各国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信任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互利合作”十二字方针,把国家间的互信问题提升到外交战略高度。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已经成为国家间信任机制化的代表。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信任危机此起彼伏。各国应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消除文化上的误解,寻找彼此间的最大公约数。近年来,特朗普和拜登两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峻挑战,中美战略互信严重受损。2023年以来,美国击落其上空的中国民用飞艇等事件又给中美两国的信任关系蒙上阴影。因此,国际社会在文化上而非仅从战略利益上建立信任迫在眉睫。
首先,信任的定义和信任中的文化因素对于理解基于文化上的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说,信任指的是一方对于对方行为的良性阐述或者善意的理解,并且愿意对对方的未来行为有良性的预期。反之,一方对于对方行为的负面理解以及对对方未来行为的不良预期就是怀疑。信任和怀疑是信任问题的两面。从信任的文化维度来说,其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双方对于信任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具体而言,以一种文化内部的信任程度来划分不同文化类型,一般可以分为高信任文化和低信任文化。美国和日本等国通常被称为高信任文化社会,而意大利等国被称为低信任文化社会。
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4.第二,不同文化内部信任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影响某种文化中的人民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方式。从社会学视角看,信任文化是“关于信任和可信性的规则”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5:132.。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通过构建文化上的信任关系来实现。信任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是建立在广义的文化定义基础上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一般来说,两种文化间的共同价值观越多,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彼此信任的可能性就较小。也就是说,不同文化间的认同程度对信任关系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亚伦·霍夫曼(Aaron Hoffman)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提出“当领导人认为和可能要去信任的另一国的领导人是属于同一社会集团时,国家间信任关系会得到发展”
Aaron M Hoffman.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41. 。因为“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可以在成员之间创造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会因为群体和群体价值观的认同得以增长”
Aaron M Hoffman.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42.。事实上,决定群体间信任程度的因素,通常就是他们的文化。尹继武指出,文化与国际信任的有关因素是同质性、关系基础和关系交往。
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4):2139.上述群体价值观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来说,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中的人民需要寻找一種共同价值观,也就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共同价值观。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通过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多样性来增加互信,从而实现不同文化间个性和共性的辩证统一。《论语》中曾经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国一向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与融合,主张“和而不同”。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对不同观点的尊重,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反之,片面追求一致性未必能和平共处。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瑰宝,在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显得尤为珍贵。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由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两个方面来构建的。信任关系可以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但是共同利益常常是不够稳定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信任只能是一种情境下的特殊信任,而非全人类的普遍信任。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通过建立全人类不同文化间具有文化共识的信任关系,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基础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文化上互相信任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必要保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信任关系的文化基础:求同存异的共同价值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信任关系的文化基础是文化间的共同价值观。同时,不同文化中的人民对彼此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形成信任关系的重要保证。尊重文化多样性不仅不会损害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反而会扩大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促进信任关系形成,消除偏见和怀疑,有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首先,不同文化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和价值观等层面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立在全球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这一价值观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认可。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习近平.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EB/OL].(20150929)[20230321]. 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29/content_2940088.。这里的共同价值,指的就是全人类共同认可和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只有建立基于文化价值观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不断发展,共同体内部各国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这里的共同价值区别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尽管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包含“民主”“自由”等观念,但那些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中的。共同价值观不意味着否定各种文化自身的价值,而是通过追求共同的精神目标,建立文化上的互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适用于全世界各种文化和各个行为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只有人类社会实现了和平与发展,才能真正建立互相信任,并且向着这一共同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历史上,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近些年来的局部战争,都给人类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暴露了人性中的丑恶,也破坏了文明间的友好和信任关系。同时,发展是和平的保证,追求和平也是追求发展。全球经济目前遭遇挫折,环境危机、粮食危机等威胁着人类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能够全方位开展合作,共担责任,共同发展。公平与正义的共同价值观是一种崇高的目标,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相互信任,从而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另外,民主和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解决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提供了重要手段,也是解决各种争端的重要准则。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积极践行着这些共同价值观。
其次,文化上的共同价值观更有可能形成一种集体身份,也就是命运共同体的身份。共同价值观会使得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降低,彼此沟通和理解的潜在可能性增大,文化间互动频率和往来更多,彼此意图的透明度增加。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ra Wendt)认为,同质性会带来一种集体身份。组织行为形成一种同质性基础上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是指行为体在“基本组织形态、功能、因果权力等方面的相同性”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41442.。国家就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集体身份。虽然非国家机构的地位日益增加,但非国家机构往往缺乏强制力且比较脆弱,因此“国家中心论”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集体身份是组织之间一种比较紧密的关系形式,尽管互信未必需要集体身份,但是集体身份中组织之间的互信程度是很高的。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在国家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同质性较高,所以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发展仍然比较稳固。东南亚国家联盟虽然属于亚洲地区比较成熟的国际组织,但是相比欧盟和北约,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同质性程度偏低(具有宗教和政体的多元性),导致互信程度仍然不高,一体化的步伐比较慢,共同行动力也相对比较缺乏。
Christopher Hemmer, Peter J 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2,56(3):575607.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后的欧洲内部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并发展出较为稳定的机制作为保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共同体,欧盟已经有27个成员国,并通过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等组织保障日常运行。尽管英国“脱欧”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欧盟的发展历程植根于欧洲内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尤其是各个成员国对基督教、罗马法、古典主義和理性主义等文化传统的认同上,因而欧盟仍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信任基础。
在文化互信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寻找文化间的共同点,而且需要尊重和理解文化间的差异。当双方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坦诚地承认差异,并努力寻求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时,就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实现初步的互信。当双方能够从求同存异走向求同化异时,就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互信。文化上的互信是比较稳固的,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和平友好关系,使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
当然,不同文化之间由宗教传统、政治体制以及历史记忆等因素造成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强调了世界上不同的主要文明之间会因为差异而产生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其实,民族之间的冲突的确有文明差异的原因,但差异并不必然带来冲突。在新的时代里,我们更应该在寻求共同价值观和尊重文化差异之间保持平衡。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如何寻求文化上的信任提供了一些启示。在文化立法、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和文化认同作为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实践方面,欧盟注重尊重各国的个性和发展欧洲的共同文化身份的平衡。
陈兵.文化认同建构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对东盟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10(9):2528.欧盟作为区域共同体,是以共同价值观(宗教、政治制度等)为基础建立的,其强调欧洲内部的文化认同,但它一直尊重各种民族自身的文化特性,这是各成员能够长期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重要保证。
总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为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价值观基础,同时也对各种文化较为尊重和包容,为从文化上建立全人类各种文明间的信任关系指明了方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任重而道远的,全世界人民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向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化维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信任
基于文化上的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信任水平。本文认为,国际信任(international trust)是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形成的一种长期的文化倾向。国际信任不局限于国家间的信任关系,只是这一概念以国家为单位来衡量一个群体的外部信任能力。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布莱恩·拉思本(Brain Rathbun)提出的总体信任(generalized trust) 是和理性主义相反的,这种信任表明人天生具有的可信任的特质。
Brain C Rathbun. Before Hegemony:Generalized Trust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11.65(2):243273.在国家层面,一个国家的总体信任水平可以理解为国际信任水平。较高的国际信任水平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只有世界各国的国际信任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各国人民对他国人民普遍信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信任文化的基础。
国际信任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尚未成为研究热点。国际信任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解读。尹继武等学者把国际信任理解为国家间或是国家与区域等行为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而没有把国际信任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或者指标来加以定义。
尹繼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4):2139.国内学者一般把国际信任解释为国际社会中的信任,主要表现为国家间信任或者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信任。美国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布鲁尔(Paul Brewer)等对国际信任的定义是“公民就国际行为而言,对大多数国家是否能够按照国际规范行事的总体看法”
Paul R Brewer, Kimberly Gross, Sean Aday, Lars Willnat.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48(1):93109.。国际信任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总体信任水平。国际信任水平高的公民认为国际环境友好、信任和合作是一种规范,国际信任水平低的公民认为国际环境是充满敌意的。国际信任是长期的决策。
Paul R Brewer, Kimberly Gross, Sean Aday, Lars Willnat.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48(1):93109.陈定定也借鉴了这一定义,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前已成年的居民、收入较高的居民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的国际信任水平更高。
陈定定,张莉,王正绪.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一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5):8698.本文之所以把国际信任定义为一国对外部信任的文化倾向而非国际社会内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因为这一解释可以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一国内部的信任文化和信任水平,能更准确地评估国内各种因素如何影响一国基于文化对外信任的决策状况,从而探讨如何通过提高各国信任水平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际信任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存在一定争议。布鲁尔认为国际信任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国际环境本身的特质、年龄、对政府的态度以及教育程度。
Paul R Brewer. Public Trust in (or Cynicism about) other Nations across Time[J]. Political Behavior, 2004,26(4):317341.李晓隽等认为,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五个主要因素是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冲突、总体信任、认同差异和历史记忆。
Xiaojun Li, Jianwei Wang,Dingding Chen. Chinese Citizens Trust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Findings from a FourCity Surve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6, 60(4):778789.本文認为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一国的民族主义文化和总体信任文化。
首先,一国的民族主义文化是否在政治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非常关键。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情绪,更是一种文化,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的政治文化。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立民族共同体,提升民族国家的统一、独立、尊严和幸福程度。民族主义者往往对来自其他民族国家的威胁更为敏感。民族主义者,特别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更执着于提高国家影响力,而且比非民族主义者更有可能在兼顾大局的情况下扩大国家影响力。此外,民族主义者对国家统一问题具有更高的支持度。
马莎·科塔姆.政治心理学[M].胡勇,陈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43344.由于对外部威胁更为敏感,因此民族主义者更容易对其他国家的行为进行负面解读。
民族主义者的定义和特征说明,以民族主义文化为主流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信任水平较低;反之,民族主义程度较弱的国家更倾向于信任他国和国际组织。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造成侵略和战争。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民族主义文化特征是否盛行依然会影响一国对外部世界的总体信任水平。民族主义思潮一旦高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民族中心主义或是民粹主义,排外情绪蔓延,种族歧视盛行。这种局面轻则影响国际合作,重则导致侵略战争。历史经验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日本的民族单一性很高,19世纪至二战结束期间,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之外,日本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动因。
其次,社会的总体信任文化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和国际信任水平息息相关。根据信任程度的不同,社会信任文化可以分为高信任文化和低信任文化。另外,社会内部的信任程度会决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也会影响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信任文化中,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国家对自己政府的信任程度。通常来说,国民对本国的政府信任程度高,不一定会更信任其他国家的政府。如果国民对本国政府的信任程度低,通常他们也不容易信任其他国家的政府。比如,某国的人民看到本国政府的腐败,会联想到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会发生腐败。当然,一个社会里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高,也并不等于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高。社会的总体信任文化和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之间并没有正相关性,但它们同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外部世界的信任,也就是国际信任。
最后,一国的国际信任水平对其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国际信任程度高的国家更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主义合作。
Paul R Brewer. Public Trust in (or Cynicism about) other Nations across Time[J]. Political Behavior, 2004,26(4):317341.一个国家形成了一种信任程度较高的国际信任文化,就更可能倾向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当然也可能陷入干涉主义的泥潭。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三个特点是“美国清白无罪”“美国乐善好施”和“美国例外论”。在国际信任文化中,美国的理想主义常常表现为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文化传播。美国是对外援助和人道主义干涉大国,除受到其经济军事实力的支持,也和美国的文化自信及其国际信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从更大范围来看,国际社会中如果有崇尚信任的文化,那么国家间的合作会更为普遍,冲突和矛盾的发生率会降低,或者说国家间的问题更容易解决。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于建立国际信任相对比较乐观。他认为,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浪潮占据主流,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这种趋势消除了很多文化上的障碍,使得国家间的交流更加充分。另一方面,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确实造成了一些冲突和分歧甚至战争,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不同的文化是可以共同繁荣的。
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4.各国的友好共存不仅要基于文化上的共识,也需要尊重彼此文化的特殊性。国家之间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自身和他者的文化。这样,全世界才可能形成信任文化,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的来说,国际信任指一个国家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信任文化。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国际信任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间互信关系的指标。国际信任与本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有关,尤其和政治制度以及民族主义有关。当国际信任水平较高的时候,各国间建立起文化上的相互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化上信任的实现路径:文化交流
除了促进国际信任水平的提高之外,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交往所带来的互信关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在文化维度中的实现路径是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建立一种深层次的信任。这种交流不仅可以由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政府主导,也可以在人民之间自发地形成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交往。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文化互信逐渐形成。文化上的交往可以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同信念,培育共同价值观,消弭误会,减少分歧,在信任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给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信任关系带来挑战。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沖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中提到了西方与非西方在西方的“普世主义”“人权”“民主”以及移民问题等方面的冲突。从古至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不信任也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相比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交往,文化交流作为一种低政治形态的对外交往,常常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在交往双方的互信程度不高或存在重大利益分歧的时候,文化交流活动常常可以起到“破冰”的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文化交流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无数沟通的“桥梁”,在各国人民心里编织起一张“看不见的网”,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作为纽带,凝结友谊,建立信任,生发繁荣,“通过文化互动联接彼此的文化情感,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谌力,吴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J].思想理论战线,2022,1(3):76.。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和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唐朝的外交使团和留学生、鉴真东渡等历史经验证明,中国一直重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学互鉴。近代以来,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学习了中华文化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现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大批归国留学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历任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文化交流在加深信任和促进友谊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期间,中美两国在关系缓和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文化差异的挑战,互信的演进过程充满波折。中美双方领导人在两国接触过程中努力了解对方的文化,力图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发现对方文化的优点,并对对方的文化表示尊重。这些努力对中美关系缓和初期的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基辛格在访华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和尼克松总统对此进行了细致的交流。尼克松在访华的欢迎晚宴中使用了筷子。尽管他不擅长,但是在出访的宴会上使用了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工具——筷子,并通过媒体向世界转播,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接纳。而中方欢迎时演奏了美国著名歌曲《牧场上的家》,也显示了对美国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
Dong Wa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M].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230.晚宴上的这些友好行动是尊重双方差异和寻求共识的努力,中美双方通过自身行动表达了求同化异的愿望。习近平主席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性。2023年6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他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希望大家把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习近平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0629(01).从古至今,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离不开文化交流这一重要载体。
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文化上的碰撞,也给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带来了挑战。当今国际社会中,由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文化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正视和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审时度势,换位思考,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15世纪后期,传教士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教,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部分文化交流的功能。尽管他们常常会遇到抵触甚至敌对情绪,但其通过学习本地语言、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包括文化交流机构,例如哈佛燕京学社等)帮助本地发展等方式,融入当地生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信任关系的发展。而留学生作为人数众多的群体,在留学所在国也常常遇到文化差异带来的人际关系的信任困境。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其均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尊重差异,坦诚沟通,并学习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在求同存异中追求共同繁荣,实现文化上的信任。
总体来说,文化间交流对信任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文化交流对信任关系形成的影响路径在政府和民间层面都有所体现。首先,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以一种更便利、敏感度更低的形式实现了双方的人员往来,为更高层次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提供了载体和示范。当双方交往的“大门”通过文化交流的“小门”打开之后,不同文化间的人民可以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共同情感经历和共同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多维信任关系,从而形成命运共同体。其次,通过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不同文化可能发现彼此之间更多的共同价值观,消融之前由于某些历史记忆和新闻报道带来的误解,部分弥合意识形态的差异,找到双方对人性的共同理解,发展出共情和信任,从而构建命运共同体。清朝留美幼童赴美之初,其卓越表现打破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展示了中国学生的优良风貌。卡塔尔世界杯圆满落幕之时,世界各地的球迷不仅享受了一场足球盛宴,也对伊斯兰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文化交流中建构出的共有的经历会作为共有的历史,塑造出新的共同价值观,长久和深入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信任。这种文化上的互信是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五、结论
当今的国际社会面临各种挑战,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局部战争尚未结束,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环境和粮食安全问题也是全世界人民关切的重大议题。中国在2012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但其构建之路任重而道远。各国人民之间若要减少误解和冲突,就要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减少怀疑和猜忌。文化间信任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影响,也深受国家文化特性和国家间文化认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加深彼此的了解,在正视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扩大共识,消除误会与偏见,创造新的共同价值观。
在信任问题上,不同的文化体现了某一国家或民族自身信任程度的高低。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自身的信任文化对相互信任的形成十分重要。当某一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时,文化间的信任关系更容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会水到渠成。另外,国家间文化的认同程度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从文化认同角度产生的信任关系,不容易受到短期利益波动的影响,对两国之间的长期关系产生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不同的文明间建立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彼此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做到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建立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文明多样性的美好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5月14日在“一帶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20170514) [20230322].http://news.cctv.com/2017/05/14/ARTIlKFOqbrYI3dYDoks74sO170514.shtml.国家间的文化活动有利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两国之间只有经过充分沟通和交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意图和行为,为两国之间的互信关系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即使两国的文化认同不一定在交流中得到显著提高,但是通过文化交流减少对彼此的误判,增加对对方行为的预测能力也是尤为重要的。同时,文化交流作为一种低政治活动,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高政治行为,其兼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可以为其他领域的交往投石问路,能够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中培养共同的体验,在文化间互信的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对外政策的实施中,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扩大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提高软实力,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提高中国的国际信任水平。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美好的现实。
参考文献:
[1]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2]陈兵.文化认同建构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对东盟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10(9).
[3]陈定定,张莉,王正绪.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一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5).
[4]谌力,吴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J].思想理论战线,2022,1(3).
[5]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6]马莎·科塔姆.政治心理学[M].胡勇,陈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8]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28(4).
[10]Brewer P R, Gross K, Aday S,Willnat L.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48(1).
[11]Brewer P R. Public Trust in (or Cynicism about) other Nations across Time[J]. Political Behavior, 2004,26(4).
[12]Hemmer C, Katzenstein P J.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2,56(3).
[13]Hoffman A M.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14]Li X J, Wang J W, Chen D D.Chinese Citizens Trust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Findings from a FourCity Surve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6, 60(4).
[15]Rathbun B C. Before Hegemony: Generalized Trust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1,65(2).
[16]Wang D.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M].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責任编辑:陈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