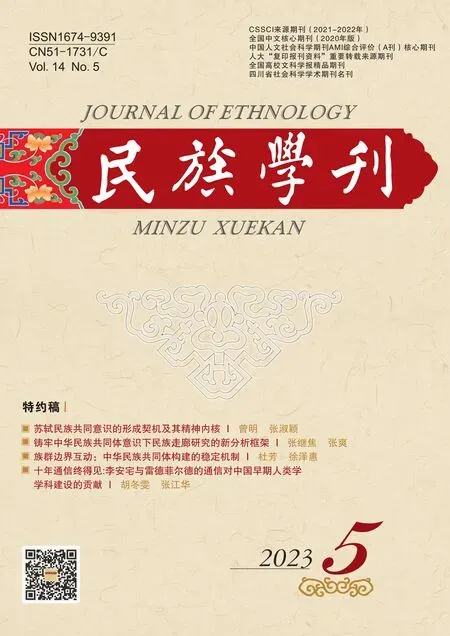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杜 芳 徐泽惠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成为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
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以中国为主要区域,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现有研究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族群边界的跨越与流动是正确处理族群之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主要路径,族群边界的消融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一、族群边界学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理论分析
(一)族群边界理论的相关研究
族群边界最早始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在多民族社会中,“边界”是连接和维系不同民族、族群的分界线,边界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含地理边界、行政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等。族群边界主要由族群的定义生发而来,族群是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藏族、彝族、华裔华侨),[1]族群边界则主要指群体通过强调某些族群特征限定“我们”以排除“他们”,并在特定环境下与被归类为“我们”和“他们”的群体产生关系网络。
国外关于族群边界的研究普遍始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涌现出原生论、工具论、文化说等理论范式。围绕上述理论,国外学者对族群边界的内涵外延、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以葛慈(1967)为代表的原生论者从现象心理学出发,认为“同根性”的原生感情可以跨越时空塑造不同族群间的共同认同。[2]以利奥·A·德普雷(1975)为代表的工具论者从行为主义路径出发,将族群视为经济现象,族群认同可以随着政治、经济资源的竞争等变化而定。[3]文化说学者将文化作为族群边界的关键因素,如韦伯(1922)将族群边界定义为一种基于对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的信仰主观感受上的归属感,是在个人之间划定界线,从而创造社会群体的模式;[4]巴斯(1969)从人类学视角提出族群的性质像一个容器,容器的边缘就是族群的边界。[5]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商品、人员的快速流通,国家领土边界的屏蔽效应消减、中介效应加强,族群边界研究也逐步从宏观的国家、民族视角转向中观的城市、社区乃至微观的部分族群,更加强调族群现象中的理性选择,如郝瑞(2000)深入中国西南地区,重点研究西南族群,进一步思考“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异同,得出“族群”倾向于指代不同文化差异,“民族”则是基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划分出的政治性人群;[6]柯恩(1969)基于非洲城市内族群的研究,在探究各民族如何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发现族群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利益群体;[7]安德烈亚斯·威默(2008)将族群边界视为社会领域中的行动者之间的分类斗争与谈判的产物。[8]
国内族群边界的研究主要受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白寿彝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汪晖的“跨体系社会”理论等的影响,从不同视角进行论述。如马俊林(2008)从政治学视角出发,认为族群边界是国家行使其主权的边界线;[9]谢劲松(2007)从文化角度出发,提出族群边界是一个拥有边界性的文化概念;[10]刘正爱(2010)、谭必友(2011)进一步强调国家在民族边界界定中起到的重要引导作用;[11][12]何元凯等(2021)从广西的饮食文化叙事中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13]朱碧波(2021)从哲学出发,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真意和伦理指涉;[14]魏霞等(2021)从跨学科视角切入,认为边界跨越是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的路径;[15]巫达(2022)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了族群边界的消融与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16]于洋航等(2022)创新性地从管理学角度切入,着眼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为我国民族工作状况的政策评价做出努力。[17]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族群边界的研究更多聚焦民族国家中心视角下的历时性分析,强调国家在族群边界建构中的功能作用。国内开始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并尝试对其进行分层次剖析,目前较少有关于族群边界的剖析研究。本文聚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通过引入多级过程的族群边界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和“内边界”,“外边界”是面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最大“边界”,“内边界”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多民族间内部可跨越、有弹性的“边界”;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分析内外边界的互动策略,通过内外边界的互动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最终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二)基于多级过程理论分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
1.多级过程理论
多级过程理论是由瑞士民族研究学者安德烈亚斯·威默于2008年提出,认为族群边界是处于社会领域中的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的结果。首先,该理论分析了族群边界具有“政治显著性(政治上是否显著)、社会封闭性(社会是否封闭)、文化差异性(文化上是否差异)和历史稳定性(历史上是否稳定)”四个特点:政治显著性是指族群边界在共同的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程度,即族群边界在多大程度上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影响越大则越显著;社会封闭性是指边界跨越的难易程度,越不容易跨越,则越封闭;文化差异性是指不同地区的大众由于教育背景、社会工作与生活经验的独特性,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历史稳定性是边界的历时性变化,即边界变化的快慢,变化越慢越稳定。①其次,该理论建构了制约族群边界互动与博弈的影响因素模型(体制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联盟网络),分析族群个体如何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界策略:一是通过扩大或收缩族群类别来移动边界;二是通过挑战族群的等级顺序来改变现有边界;三是通过改变自己的对象类别来跨越边界;四是通过强调其他社会界限来克服族群边界。最后,该理论提出“政治越显著、社会越封闭、文化差异越小、历史越稳定”的族群会在成员之间产生高度的族群认同,从而达到稳定族群边界。
本文拟引入分析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国情,通过对该理论进行可适化与本土化修订,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的理论框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进行划分,将其分为“外边界”和“内边界”两个层次,分析内外边界的形成及特征、内外边界的互动策略,研究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稳定的因素,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的稳定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图1)。
2.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
边界的流动是绝对的,边界的稳定则是相对的,两种特性此消彼长。根据多级过程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族群边界被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外边界”是面向其他国家及其他国家民族的最大“边界”,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其他国家”的排他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是指国内不同民族之间可跨越、有弹性的边界,各民族通过有序的边界流动、跨越、消融等形式,最终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的族群边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构建
(一)外边界的形成及特征
根据多级过程理论,若要达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相对稳定,则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影响因素,维护外边界的一系列“在场”特征,从而保证外边界的相对稳定。
1.制度在场
外边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边框,最重要的功能是将本国国民与他国国民区分开,即“我者”和“他者”的区分,这离不开国家自上而下的相关制度。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与周边国家的谈判与交涉确定了领土边界,通过开设使领馆强化了国家的实体存在,初步划定“我者”的空间范围;其次,我国采用血统主义②和出生地主义③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国籍这一“法律身份”将公民初步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畴中,进一步划定“我者”的身份范围;最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各地区、各民族提供充分发声的政治空间,保证民主的充分发挥,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终确定“我者”的权利范围。综合来看,国土空间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共同地域,是身份识别和权利实践的基础;法律身份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整合治理的重要范围;民主权利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权利诉求的重要保障。空间、身份、权利的三维“制度在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
2.组织在场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核心主体。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后盾和组织基础。
3.文化在场
中华民族文化具体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饮食、衣着、住宅等,精神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传统节日等。从物质文化来看,饮食可谓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文化也被称为“以饮食为中心的文化”。[18]经过历史沉淀,中国饮食以四季有别、讲究美感、烹饪多样而闻名于世界,绽放出独特魅力,特有的中华饮食被符号化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并通过味觉记忆、烹饪方法建构起民族认同。从精神文化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沉默的语言民族主义”[19]国家,是世界上使用汉语人数最集中的地域,主要通过普通话及汉字来体现与“他国”区分的“文化在场”。早在清末,受西学东渐思想文化的影响,部分曾旅居外国的国人提出中国应改革汉字来开启民智,由此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国语运动,④通过培养国语师资、编译国语书籍、开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式,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知,强化了各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基本消除了语言交际障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稳定建设奠定了语言基础。
4.历史在场
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文明,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如“龙的传人”“仓颉造字”等神话传说在流传中受到了部落间融合影响,原属不同部落或部落集团的天帝与祖神可以被归纳放到同一神坛上祭祀。[20]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炎帝神农氏教人们耕种,解决了粮食问题;黄帝轩辕氏带领民众驯养牛、羊、猪等家畜,成为了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部落;司马迁的《史记》以鲜明的血亲意识注明了五帝之后朝代的世系传承关系,明确了自夏至秦汉之间王朝传递的正统性,这期间每一个王朝都与五帝有着清晰的血缘传承。[21]这种瑰丽的民族共同体历史传说和血缘传统将56个民族的记忆起源和血统连接在一起,书写了国民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在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提下科学识别出各少数民族,使得外边界通过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得到加强和巩固。这种厚重的历史“依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相对稳定奠定了情感基调。
(二)外边界的互动策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博弈策略主要通过“本国、个体及他国”三个主体间的互动博弈来实现稳定中的流动。
1.“本国-他国”间的互动博弈
“本国-他国”的互动在外边界更多体现的是边境政策以及相关福利政策,如我国在边境地区实行的边民扶贫政策。处于中越边境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边境线长438公里,共有麻栗坡、马关、富宁3个边境县,2015年以来,文山州两轮“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与兴边富民工程“十三五”规划接轨;2019年以来,文山州38个抵边村实施了集体经济强村工程,主要通过基础建设、村企合作等模式,直至今日已实现了65.25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县(市)全部摘帽,81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此同时,仅一河之隔的越南河江省也十分重视北方边境民族扶贫问题,自1998年以来陆续实施《2000年消除贫困规划》《2001—2005年阶段国家消除贫困和就业问题的目标规划》《2021-2025年阶段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目标计划》等政策规划,但由于其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基础发展较差,河江省直到2021年底仍有高达18.36%的贫困率。两国政府在边界扶贫政策上的效果落差,使得边界人民在进一步的博弈与互动中形成更加稳定的外边界意识。
2.“国家-个体”间的互动博弈
“国家-个体”的互动更多体现在“个体民族”往往同时面对着“本国”和“他国”两方所提供的策略选择。个体在抉择中面临着“感性”和“理性”的拉扯,表现出或“离散”或“回归”[22]的行为,如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严格执行生育政策,导致中缅边境上的边民因生育缘故“离散”至缅甸,但随着我国近年来生育政策的放开、边境生育政策的执行,对边民通过情感召唤:“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政策好,少数民族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23],从而让离散同胞怀带着莼鲈之思回归中国,最终族群个体通过策略选择进一步稳定了国家的外边界。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构建
(一)内边界的形成及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是多民族间可跨越、有弹性的内部“边界”。正如费孝通描述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融合、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0]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处于相对稳定下的流动状态,具有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历史稳定性等特征。
1.政治显著性
政治显著性是指族群个体在共同的政治生活中,族群边界在多大程度上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影响越大则越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和途径,避免少数民族因为“少数”的族群特点而无法充分参与政治生活,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参与制度,明确了 “全国少数民族代表的产生一是基于人口数量,二是基于聚居分布状况,三是确定了最低保障名额”[24]的规定。⑤国家通过保障所有民族平等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在国家各部门降低了各族群在政治上的差异性,有助于建立起跨域族群的政治联盟,削弱内部族群之间的政治不平等,为内边界的流动创造了平等的政治空间。
2.社会开放性
社会开放性是指族群边界跨越的自由程度,越自由则社会越开放,反之则越封闭。社会开放性具体可表现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个体对本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充分包容,“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使得各族人民共同庆祝节日、共享彼此的特色饮食,在经济、文化的社会交往中形成友好协作的关系;对内,个体可以相对轻松的交流,可以灵活参与到多民族共同生活中,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字的使用和普通话的普及使得中国地图上遥远的各个族群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流成本,普通话和汉字有助于在不同民族语言的广泛族群中建立和维持社会开放性,便于形成包容多语言的政治统一体。汉字结构及超时空性的表意功能,为不同个体结成共同的政治联盟、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极大地降低了各个族群社会的封闭性,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发展,为内边界的流动创造了开放的社会空间。
3.文化多元性
文化多元性是指族群边界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多元性,中国每个民族都拥有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璀璨丰富的本民族特色文化,但也在彼此文化的交流互融中呈现出文化多元性,文化多元性是中华“天下为公”与“和合共生”文明基因的再现,指各族群表现出来的丰富多样而互嵌互融的文化符号,这种多元性很好中和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各族群拥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如汉族的汉服与龙凤呈祥的图腾、壮族的铜鼓与青蛙图腾、满族的海东青、回族的清真寺等。更重要的是,各族群在历史长河的交融中形成了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一是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遗产类,如故宫、苏州园林、吊脚楼等建筑符号;二是具有各种象征性的精神类,如红军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三是各类节日,如共享的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
4.历史稳定性
历史稳定性是指民族边界变化的快慢,变化越慢越稳定。在中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下,个体可以借助族际婚姻从一个族群边界跨越进入另一个族群边界的“领域”内,五十六个民族间的族际通婚已相当普遍和频繁,族群边界呈现出稳定性的流动。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统计,我国已经形成以汉族为中心,包括各民族的大通婚圈,同时还有东北、西北、南方3个次一级的地方民族通婚圈,族际通婚让各族群实现了血缘交汇和代际流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各民族间团结友好的关系,这为内边界的稳定流动创造了宽松的现实空间。
(二)内边界的互动策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互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方式,二是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方式。通过分析不同民族个体的行为选择,总结出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策略。
1.通过扩张或收缩族群类别来移动边界
多级过程理论认为扩张或收缩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通过聚变来减少类别的数量并扩大现有的边界或者通过裂变来增加一个新的边界,从而收缩以前的边界。[8]如以民族识别过程为例,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为了尽快确定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各民族人民代表)名额,将各民族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民族识别的工作便成为党在建设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民族识别工作组通过邀请不同部落或社群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来开“协调会议”,以语言相通为由,“劝说”云南文山县的“土佬”归并于“僮”;同样,使用相同语言的族群也有可能“裂变”出去,分别归类为不同“民族”,如被识别为“回族”的汉语穆斯林以及满、畲、僮、土家等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大致通用汉语。第二,在不改变现有类别数目的情况下,强调更具包容性或排他性的分类区分,具体表现在“国家建设”中,强调更高层次的民族分化,并在其中涵盖现有的民族、地区或种族分歧。如秦汉以来形成、巩固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初步完成了属地国家化、属民国民化整合,出现了更高层次的“中国人民”概念,随着后朝匈奴、鲜卑、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前朝的“中国人民”识别为“汉人”。在每一次的新王朝扩张之中,原先王朝的内部差异被统一涵盖进“汉人”,融入到新王朝之中,共享“华夏”“中国”之名。
2.通过挑战族群的等级顺序来改变现有边界
此种策略是指通过建立地位和实现政治平等,重新解释民族制度的规范原则,挑战族群类别的等级秩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民族间名义平等。在法律上,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方位详细规定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基础上,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在称呼上,由于过去很多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存在侮辱性,如在20世纪50年代贵州仲家(布依)族更正民族名称代表会议中,来自贵州35个仲家(布依)族的代表以及地方的水族代表和干部提出,本民族在旧社会里长期被统治阶级压迫,“仲家”“水户”等名称都有侮辱性,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对族称作了相应更改,改仲家族为布依族。二是追求民族间事实平等,如起初为弥补少数民族教育起点不公平,黄现璠先生(壮族)曾在20世纪50年代向全国人大提交过“对少数民族高考生录取采取一定照顾政策”的提案,建议政府在高考招生中对少数民族实行降分录取。应少数民族同胞的意愿,自1980年正式推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但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整体上升,该政策逐渐显露出一定的不适应性,仅以民族区分会使得同教育水平的汉族学生的努力被消解,最终将难免固化民族意识,使得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或隐或现的“歧视”。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促进民族友好,我国各地区在近几年严格规范招生范围和录取行为,合理划定片区,不过于强调民族成分,不以民族划线,而是以地区划线,做到事实上各民族教育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的一律平等。
3.通过改变自己的分类成员来跨越边界
此种策略是指不寻求边界扩大或收缩,而是将整个族群类别重新定位到一个多层次的等级体系中,在现有的等级边界体系内改变自己的分类成员来实现边界跨越,具体分为个人和集体策略。第一,个人策略指个体借助通婚对子女民族成份重新分类,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⑥变更子女民族成分;第二,集体策略指通过达到所谓“上层”的要求来实现跨域,如解放前的凉山彝族保留着所谓“民族内婚”“等级内婚”等制度,但由于凉山自治州解放、社会经济发展、婚姻法普及、劳动力市场流通、教育水平提高,凉山社会中的彝族青年们通过男女双方家庭对彩礼风俗的运用,如一些彝族女孩愿意通过婚姻来获得高额彩礼,[25]使得族际通婚和“等级外婚”越发增多,进一步加速了彝族等级身份系统的解体,从而实现族群内部边界的跨越。
4.通过强调其他社会界限来克服边界
此种策略强调不同族群之间通过相互协作的方式来克服边界,具体通过形成“跨体系社会”,意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例如,中国新疆的塔城地区是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地区,各民族因生计需要,形成了合作互补的社会经济族际交往,如没有牧场的汉族农民将自家的羊承包给有牧场的哈萨克族“代牧”,不会种地的哈萨克族牧民把土地出租给汉族农户。各民族被产业过程勾连起来,此过程中 “我者”与“他者”的识别和区分不再是族群身份上的不同,而是建立在雇佣、商业等契约关系上,从而达到内边界的稳定流动。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系统剖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应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的相对稳定与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稳定流动两方面重点发力。
首先,国家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以期维护外边界的系列“在场”特征,从而保证外边界的“制度、组织、文化、历史”的四重在场,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本国”与“他国”互动中依然产生极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进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一是制度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参与制度优势,维持制度在场,坚定制度自信;二是组织上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是文化上亟须凝练、弘扬更多各民族共通共享的文化符号,坚定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四是重视对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其次,继续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历史稳定性”等特征,鼓励各族群众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稳定跨越与流动。第一,政治上通过干部交流、挂职锻炼、党校学习等方式进行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同时加强政策宣传讲解,让少数民族群众更深入了解各项政治活动,提高少数民族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第二,社会上避免将少数族群认同简单地看作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挑战,积极将汉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对象,在日常活动中应注重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合作和交流,通过真实的接触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需要强化少数民族的认同,还应重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认同。第三,文化上积极宣传各民族文化,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节日的积极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通的文化想象,进一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字和普通话),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第四,通过频繁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鼓励开放、协作的经济生产关系、社会人际交往、族际婚姻的形成,将各民族通过不同的社会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民族之间不乏“边界”符号,但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部边界与内部边界,分析内外边界的特征与互动策略,运用族群边界理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这样的研究在理论上是重要的尝试。随着一体化建设的成熟与发展,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机会增强,交往空间发生交叉重叠,边界形态与特性也随之变化,族群边界的流动随之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各民族的适应能力不同,其中有遗传因素、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因素等,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不可一蹴而就,需审时度势,循序渐进。
注释:
①安德烈亚斯·威默(2008)将其论述为“一些边界顽强而缓慢地在许多代人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族群边界的重大变化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
②血统主义:即以父母的国籍来确定一个人的国籍。
③出生地主义:即出生在某国,即具有某国的国籍,而不管其父母的国籍。
④国语是指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共同语,在“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口号的推动下,众多知识分子为改革汉字、推行白话文和统一方言所发动的语文改革运动,被称为“国语运动”。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在同一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当地人口15%时,少数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也应有一名代表。
⑥《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变更民族成分,应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本人可以在年满十八周岁后的两年内自愿选择其父或其母的民族成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