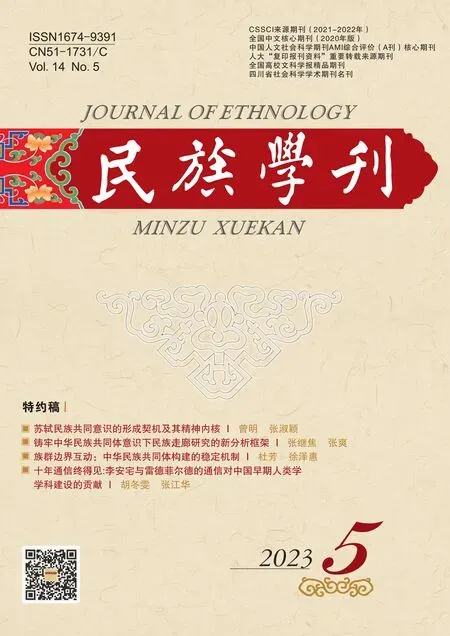民居博物馆场所营造中的原真性、表演和身体
李 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北京 100083)
当下社会言论密集出现对历史城镇“商业化”的批评。单纯的批评商业化,没有碰触到问题的实质。各类历史古城、古镇多数都是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市、商贸、物流为人口汇聚创造了条件。例如丽江最初是几个村落,随着商业贸易往来,人群在此汇合,才逐渐形成古城的格局。商业化并不构成问题,甚至商业化本来就是历史城镇的题中之义,有问题的是病态的、成问题的商业化。
除却各地旅游产品、旅游项目的千篇一律之外,人们所拒斥的是商业化给人造成的空洞、虚假感,这种虚假感涉及到遗产和旅游等多学科研究中的核心命题:原真性(或译真实性)(authenticity)。1964年,Authenticity一词首次出现在国际遗产界影响深远的著名文献《威尼斯宪章》之中,从此,它逐渐成为国际遗产界的重要术语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必须经受“原真性”检验。与此同时,原真性也被引入旅游研究之中。原真性的概念比较驳杂,最基本的含义指的是某样东西整体或其某方面具有真实、无可否定的起源,且具有备受肯定的性质,而非是仿照或复制的结果。
伴随城镇传统功能衰退与旅游的影响,古城镇原真性退却,只留其壳,遗失其神。然而不管是大众游客、本地居民,还是学术界、知识界,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群对原真性的要求却日益增加。对原真性讨论的著作已汗牛充栋,然而解决这个矛盾还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破除一些观念的迷障。借助“存在主义原真性”和“表演性原真性”的概念,本文认为,在资本横行、管理失控等制约之下,古城镇要从原真性破碎化的险峻情形中突围,就需要打破一种对“原真性”的执念。这种执念认为,日常生活必须得到“复原”才能获得真实感。同时还应突破视觉中心主义的束缚,重视对身体感知的观照。本研究以LJ古城一家改造为私立公助博物馆的庭院为例,引申出实现上述突破的现实策略、理论反思和未来可能性。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梳理:对原真性、身体以及表演的再认识
国内遗产以及旅游学界对原真性定义的讨论成果不胜枚举。如业内普遍认识到的那样,遗产保护从体系上来说是外来事物,需要脱离对西方标准的僵化片面认知,采纳变化发展的目光,建立适应本土的标准体系。具体在旧城遗产保护领域,研究者应重视动态的、变迁的属性。张杰以雷峰塔的重建争议为例,指出国内对原真性的理解偏重于追求原状,忽视体现历史延续和变迁的真实原状,和《奈良真实性文件》中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相对灵活也更复杂的认识有所偏离。张杰阐述道:在奈良文件中,已经明确了“原真性本身不是遗产的价值,而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取决于有关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有效。由于世界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将文化遗产价值和原真性的评价,置于固定的标准之中是不可能的。”[1]80“在不同文化,甚至同一文化里,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及其相关信息源可信性的评判标准可能会不一致”。[1]80本文案例中的当地居民尤其地方文人自己对本地文化遗产如何“存真”、哪种历史信息是可信的,都有一套鲜明的与主流不同的观点,他们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何为真实,也呼应了上述理论反思。
根据卢永毅的爬梳,在建筑遗产修复理论领域里,一直有“干预”与“维系原状”的两派分歧。[2]前者以勒-丢克为代表,认为物质干预落脚于将遗产复原到一种完整的状态,哪怕这种状态从未存在过。后者则以拉斯金和莫里斯为代表,主张以最小干预原则去最大程度地维护而非修复历史建筑。这种分歧一直延续至今,中间经历波依托、里格尔等人的综合性批判。背后的争论其实是“艺术风格之真”(干预派所倡导),与“历史之真”(维护派所倡导)的纷争。[2]各地常见的文化保护工作措施是兴建博物馆,而“博物馆化”是以封装生活维护为主,还是有机革新不吝干预,也可谓是上述修复理论分歧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的反映。
旅游研究领域的王宁在一篇影响广泛的英文文章中归纳出存在主义的原真性:原真性的判定不仅是标准判定以及主观建构的结果,也不仅是景观和旅游纪念品等旅游对象本身具有的属性。[3]王宁认为原真性的来源还包括旅游主体指向主体内部的体验。随着旅游者脱离日常生活,经历旅游期间的阈限时期(liminal period),旅游者或许感到一种更真实更自由的状态,精神和审美得到极大的满足。这种体验和旅游对象没有必然联系,更大程度上缘于游览活动是超越日常性的活动。王宁提出这种角度所理解的原真性是存在主义原真性,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该视角重新确立了主体在世界中的直接体验占有的重要地位。随着当下尤其国内旅游者文化自觉性和自我感知敏感度的提高,其解释力显得越发重要。
旅游活动涉及到多个方面,不仅仅关涉旅游者,也涉及旅游地的当地人。旅游者的主体体验,离不开当地人的活动。于是另有一些学者侧重于强调旅游现象中那些当地人为保持文化的延续性而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4]詹姆士·克里夫德(James Clifford)指出,不能将原真性的定义聚焦于一个被抢救的过去。相反,原真性已被重新构建,被视为一种立足当地、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混合的创造性活动。[5]类似, 本文案例里的保护行为不但是文化自救,也是一种积极的、有准备的经营策略。
本文试图去对话的第二个核心概念症结是“视觉统治”。人们对保持风格的要求、对原生态的要求,很多是满足视觉的认知。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诸多保护工程从“风貌控制”入手,依靠粉刷整治民居房屋的外壳来试图维系“文化”。其实,包括文化遗产工程和精细管理在内的现代文化都被“视觉范式”所统治,从认知层次上来说,知识、真理与现实阐述都由视觉生发,以视觉为中心。[6]这套统治和工具理性、技术特性相互印证支撑。当代主要思想家包括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福柯和德里达等都认为现代思想文化延续了视觉统治的消极趋势,一些左翼思想家如德赛托也明确指出衡量每件事情的标准变成了能否被“展现”,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则更明确地揭示出视觉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的统治地位。与这种趋势对立,现象学哲学以及神经认知科学都在不断解释被现代主义掩盖淡忘的基本事实——首先,身体是思考、感知与意念的场所;其次,视觉并非唯一,多种感官互相嵌套,不可割裂,总之身体与世界互相融贯、彼此界定。
传统中国文化里有丰富的替代视觉中心主义的认知传统。如文化遗产专家李菲所言:“‘身体转向’在西方世界是对身/心、物/我二元论反思的成果,而在中国,则应该是对传统身体观本有的潜隐维度的再度激发和彰显。”[7]中文语境里的词汇“体认”“身体力行”“身家”等,都反映出对身体的天然敏感;不论是传统民居和景观,还是传统视觉艺术如园林和中国画,强调的都是人在环境中的“栖身”与“寄情”。
对视觉统治的警惕,和重视“体验”以及内部认知的存在主义原真性一脉相通。身体是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来源,感官、情绪、身体反应,都在旅游中有极大的释放。而这种内部体验(intra-personal),无疑也会作用于社会性的、人际的维度(inter-personal),继而更加精细地营造阈限感、社区感。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观看”之道,从批判视觉中心主义的角度理解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需要和遗产有关的,包括原真性在内的裁量标准以及实践参与者,不仅仅从视觉出发,还应正视身体的在场,引导人们带动身体参与建构逻辑、接触物质实感,拉抻出被商品化压到扁平的情感体验。
笔者于2016年冬季对LJ市的文化公益免费开放场所“LJ私立民居博物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以及游客。与工作人员的口述史访谈揭示出,在具体的涉身化参与原真性构建的背后,是本地人对LJ多种经营性活动的范式转变的积极参与,以及为了挽救LJ的文化命运而付出的努力。这里面必然有利益纠缠,也浮现出社会道义,更凸显出来个体命运对于民族文化大命运的观照与认同。
二、LJ私立民居博物馆院落的功能演变及其保护历程
在LJ古城东北角有一个庭院清洁幽静,与其他客栈式院落氛围迥然有别。它保持了传统民居的基本格局,院落内无起居生活杂物,只摆放了几株盆栽、兰花,以及观赏石。门口悬挂的是“民居博物馆”的招牌,房间里却陈列着专业画家的画作。民居或民俗博物馆惯常展示的那些“日常生活”:生产工具、生活器皿,旧照片等等,在这里找不到踪迹。
院子里经常走动的除了进进出出的游客,还有院子的主人 “老六”。老六所在的李氏家族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创立了“恒裕公”商号,1875年建造了属于家族的宅院。目前保存下来的院落只是当年的一个角落。
老六四十多岁,从LJ开发旅游起,从事过导游、酒吧老板等旅游产业链里的多种工作。现在老六作为博物馆的导览员,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游客讲述院子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保住这院子的历程。《新京报》的记者曾经把上述内容经历写成深度报道,该期报纸被老六保留了很多份,给客人分发。根据这篇报道的记述,老六和自己的庭院在外地资本肆虐的LJ古城里,一度面临十分凶险的情境:
“恒裕公”的百年老宅在汹涌的商潮中又一次经历波澜。周边的邻居一家家搬迁到新城住上了楼房。房子都出租成了客栈、商铺。祠堂拆了,庙宇也拆了,周边近百年的纳西老宅院一座接着一座拆毁改造。传统的门楼和木雕木刻的木质结构变成了仿古、假古董的一座座建筑……
树欲静风不止。一波又一波的人来到老宅,融资的、投资的、忽悠的,最多的时候一天来几波,带着支票、拿着现金的……一天一个朋友带着一个暴发户进到院子,喊着老六来谈谈,要买院子,甚至提出要老六把房间里的两张八仙桌抬出来,要把现金堆在桌子上,要老六自己踩着凳子,可以踮起脚够钞票的高度,到多高就给多高的钞票,赤裸裸的侮辱。[8]
老六抵抗住外来者的资本诱惑的同时,认识到这座院落作为保持住原风貌的院落在LJ的资源价值,他自己充分依托院落的场所价值从事经营活动。在转型为私立民居博物馆之前,老六做了十年私房菜。从起初的50元一位做到了1000元一位的档次。而在这个获利的过程中,他依旧需要不停地婉拒其他竞争者对宅院的出价。
2009年,老六和恒裕公终于遇到了最大的危机。LJ本地的一家很有实力的商家看好了恒裕公的老宅,他们安排专人轮流拜访,董事长亲自出马,拐弯抹角找熟人托朋友,找到老六的几个兄长,动用相当高位的和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来做工作,甚至还有侧面的威胁,对恒裕公的祖宅志在必得。开出的条件也是诱人的,租金是以前的几倍,条件非常丰厚,甚至同意老六一家继续住在老宅里面,还给予公司的股份。几位兄长被情势所迫已经同意,仅有老六一个人还在坚持。怎么办?老六形容自己“就像走在悬崖边上”。“也许是祖先的庇佑”,在危急关头出现了一群千里之外的贵人。[8]
此时,同在LJ古城做生意兼休养的台湾商人林小喜发动一些台湾友人集体投资,出资100多万元对老宅院进行了保护性的维修和整理,并给老六几个共享宅院产权的亲戚支付了相应的租金。台湾友人的赞助性投资,以及在院落经营私房菜的收入维持了院落的维护。
2012年老六给院落挂牌“私立民居博物馆”。2015年在一位当地文化官员的穿针引线之下,“私立”得到“公助”,老六和古城管委会签订合同,得到了古城管委会每年20万元的五年经费支持。如今老六成为每日挂着工作证上班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每天下午和晚上免费开放院落给游客,并提供免费解说。
三、民居博物馆的展览特征:讲解员的身心在场
这个从私宅私营变成公益公助的院子存在几个鲜明特征:其一,它的功能经历了从私房菜经营场所,到艺术展示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演变,它的性质也从商业性的私人会所转换为公益性的、公开性的文化场所;其二,虽然身为公益文化场所它没有像民居博物馆所暗示的那样,用起居道具还原到某个节点场景,提供亲民性的信息展示,而是维系了原有私人会所的场所氛围,按照院子主理人的意愿,保持了一种高度提纯化的没有时间性的文人院落气质;其三,私立民居博物馆在追求功能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功能定位摇摆不定,但至少摆脱了功能单一性和平面化,表面上架空了时间节点,实际上成为一个多功能、有纵深感的场所。因为主人可以引领客人进入历史,并铺陈开细节,场所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了不可复制性、可拓展性。下文将详细说明上述特征,并阐明拓展场所纵深的关键在于本地参与者的身心在场,以及主客之间的互动合作。
既是受雇佣的讲解员,又是民居博物馆的院落主人,老六提供的讲解与常见的标准化讲解不同。首先,老六并没有程式化的讲解词,他每天都和大量游客攀谈,在语言互动中讲解原委,解答游客的问题。老六有时主动上去介绍,有时游客主动来询问在庭院里打扫整理的老六。一些游客发现老六不仅是工作人员,也是院落主人后,认为这是深入认识当地人和当地民风的好机会,会饶有兴趣地询问很多问题。有些游客和老六可以聊上近一个小时。主客在庭院里落座,伴着茶水,话题不限地谈天说地。这种形式,更像是主客之间的日常闲聊。其次,该院落的私人空间已经与公共空间联通起来,老六自己家的住宅紧邻庭院,跨过一道门即是。每日老六打扫庭院,在门户间进进出出,他在公私之间不断的穿梭,洒扫晨除。所以这个庭院除了“被展示”之外,也在“被护养”着。除了供人视觉观瞻,还在进行着有机的私人性的维护与更新。老六有时甚至会邀请游客一起在自家吃晚饭,客人随着主人进入了私空间,从公共展示领域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这个庭院看似没有日常,实际最为日常。讲解员看似在表演,却又在生活。所以身心在场让私生活与庭院的公共生活达成有限度的混融,“前台”与“后台”参差交错,起居也成为庭院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LJ民居博物馆作为文化展示场所,其所展示的内容,已经超越了从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的展品所能承载的有限信息,通过主客互动,让游客进入流动着的当地日常生活,展陈变得综合而立体起来。
除了老六之外,院子还有一个常驻的中年男性工作人员墨笛,宅院布置的具体操盘手。他常年穿一身麻布衣服,顶着一个发髻,经常在院子里旁若无人盘坐着吹箫,或者在楼上写毛笔字,有时也解答客人的询问,给人们介绍自己给院落布局装饰的理念。墨笛“遗世独立”的形象气质也和院子静谧的场所精神十分契合。墨笛与老六,塑造了院落的景观。又由于他俩常年的在场,对场景的深入调度,以及与客人的深度互动,自身也成为院落景观的一部分,其人其身已经是院子的一部分,让人分不清他们是处于表演性场域的前台还是栖居于此地的住家,同时这种身体在场是有意而为之的。主理人对身体在场的敏感,反映在他们对标牌的舍弃上。老六表示标牌已经过时,认为“现在都是自拍自媒体时代了,游客在一个地方拍照并上传社交平台才是最好的宣传。” 游客利用场所来呈现自我,他们的经营则利用了游客在自我呈现中为场所带来的宣传效果。
笔者随机访问了一些散客,询问他们对院子的印象,多数为赞赏性的答复,表示这个院子“清净”“安静”,与他们在LJ看到的其他院子都不同。一些游客听了老六讲保护院子的故事,也表示钦佩和感动。所以这个场所又在老六的故事传播中,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活化样本,其场所精神被渲染成为“风雨无阻保护祖宅、守护文化遗产”的道义故事。庭院一旦有了氛围或场所感,就如同一个磁场,自会招人前来。在我访谈的几日,一位山西籍的退休记者,单纯为了院落的氛围,每天中午都会前来院子里一个人闲坐喝茶,或和老六聊天,度过一两个钟头的时光。对于他来说,这个院子是远离喧嚣的“难得宝地”,当所有地方都在争先恐后把景点、旅游项目和商品推向游客眼前,一个显得空荡的院落却成全了“心灵度假”型游客对存在主义原真性的主体需求。恰恰是其空寂的场所精神,让旅游者的精神愉悦成为可能。
与这种赞誉态度形成对比,尽管有少数人在院落做了长久的停留,多数游客却匆匆转了一圈就离去。从游客的反馈意见中可以得知原因:一些人抱怨在“民居博物馆”看不到LJ普通人家的生活情形,缺少标牌和展板,不知道看什么。不管是游客出于惯性去找展出、找标牌、找展品(实际上是在找日常生活的“标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本地人和游客的对立二元关系,都反映出人们对空间和身体在场的麻木与浑然不觉。如果抱持敏感的态度,就会从全然不同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人与地景之间的关系。游客的反应说明我们的旅游产业还停留在对景点的视觉接纳上,而体验型、纵深化的旅游习惯需要得到培育。下面的章节将重点阐述庭院主理人的场所构想,从一个庭院的突围努力反映出本地实践者对原真性教条化的质疑,也试图说明古城申遗20年后所累积下来的一些顽疾沉疴与自愈的可能性。
在认知科学以及现象学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身体化的实践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已经成为常识。和旅游中的身体展演有密切相关性的是“表演性”(performativity)。表演性的原真性和前述存在主义原真性都着重于主体对个人记忆、意义与物理环境的整合。“与从内心或人际感觉两个方面关注真实状态的存在主义方法相比,表演性方法强调经由身体化实践而“成为”真实的动态过程。“成为”的显著意义更倾向于对自我的一种深刻的重新安排。”[9]朱煜杰通过表演性原真性的视角,发现一个为游客进行象征性表演的纳西族东巴,通过自身身体化实践,认为自己能判断两个生命力是否结合为一个家庭。朱煜杰指出:“通过身体化实践,个体能动性与外界互动,使得行为转变为意义的制造,实践具有了表演性,有意识地行动、非自反的和身体化的实践交织其中。因此,真实性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表演的。”[10]该见解很适合说明仪式性行为以及表演行为对原真性的影响。然而案例源于旅游节目的表演,容易让人们的理解停留在“表演”的字面意思。在一些更“日常”性的场景中,或者进入非旅游场景,表演性的原真性如何通过身体实践来实现?此外,朱煜杰论文中的表演主义原真性涉及文化内部人士对本地传统、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再认识,还未明确整合外来者的原真性认知。本文认为,一个和场景配合的身体在场,是让包括东道主和游客在内的各类人群,达到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必要条件。此外,意识到身体的介入,才能解答原真性中的主客合作何以可能。
四、一场本地文人试图用“原型”代替“标本”的努力
老六总结自己是儒家,他的搭档墨笛是墨家,前者外圆,后者内方,前者敦和,后者行动力强。墨笛喜欢墨子的哲学,于是给自己起的艺名也带了墨字,这位LJ本地的木雕艺术家自述身世坎坷,从小跟随一些落魄文人学习琴棋书画技艺,成年后墨笛混过江湖,做过各种工作,但一直没有丢下最喜欢的雕刻。后来墨笛还成为一个民间工匠艺术家组织“LJ市雕刻绘画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的理事,并积极为研究会奔走,在私立民居博物馆的场地策划了研究会成员作品的展览。民居博物馆庭院的布置,包括兰花、奇石、建筑修缮等,都由研究会这样一个本地文化精英组成的智囊团提供支持。
墨笛和他的朋友们把院子打造成了一个看不到日常复原的,没有历史定位的,又有地点感的一个庭院。对于游客抱怨在一个民居博物馆看不到起居摆设和日常生活,墨笛这样回应:
看你是什么节点了。你要恢复到什么时候?历史没有固定的模式,每个时间点有一个模式,这个并不冲突。事物它是变化的,要我按光绪元年来设计,设置布局就不是这样,但那是假的呀,有距离,还不如看故宫。它必须一定是活的,未来二十年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基本的框架不变。
墨笛的这段话触及到了活化文化遗产的一些核心问题。原真性的“原”字影响了概念界定,人们倾向于去复原一种历史状态,似乎恢复、回卷就是对原真性最好的保持。这种理念一方面忽视了原真性本身的变动不居,而宁可追求虚假的原初状态,对人为的补足性的完整感流露出不信任。墨笛所谓“基本框架不变”,人为填充及时更新内容,则呼应了文章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干预派建筑遗产修复理论对人为完整性的承认。墨笛的艺术家身份让他更重视在保有原型的前提下维系艺术风格的保真,而非对历史真实性的刻意还原,这种进路在将生活标本化的各地实践包围下,显得格外值得给予施展空间。
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需要同时保持地域性以及开放性。在地域性上,本地文人经营打理一所宅院如囊中取物。墨笛谈到,“你进来这个院子就是园林,花怎么搬,这就是园林,不就是一个空间布局么。我们不是专家,就是玩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玩的是最喜欢最擅长的,极具价值,都是二三十年的经验。”玩家胜过专家,反映出本地文化资源拥有者长期浸润在文化环境后的自信心。墨笛在谈及本地人才的地缘优势时这样说道:
需要由地方上自己的文化人,自己来做。靠外面不可能的。多少专家来过LJ,他们都起不了很大作用,其实只能是扼腕叹息和呼吁,实质的这个杠杆,点在哪里他们找不到。我们刚好处在这个杠杆,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盆花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几句话也可以解决。我也是觉得你要是本地人,自己意识到这个意义了,就会动力十足,很多时候会主动地去解决问题的,前瞻性地解决问题。
真正的定位是摸索,摸索社会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我们不仅要改变这个屋子,真正的目的是做文化引领,改变社会。LJ几个载体,园林、花卉、盆景、字画等等,我们这些玩家都是草根,都是很熟的朋友。(每个人)老天生下来就走(自己要走的)一条路,到了节点,自然就契合了。具体做计划的话,就框死了。这个院子也不是一个计划,而是大众的向心力。这个院子就是老师嘛,我们创新的体系就改变了,整个脉络就联系起来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场地气质的培育,离不开当地文人的点石成金。而本地文人网络合作的正面特征,包括无计划性的契合,懂得关节在哪的功力,以场地为师的自觉,这些都需要身体在一个文化环境里长期的浸润,日日夜夜地熏陶才能达到本能式的“体认”。墨笛和他的朋友们从年少就爱好并且沉浸其间的LJ民间艺术,雕刻、园艺、绘画、营造等等,从契合LJ本身的风土这个方面有天然的驾驭能力与合理性。墨笛以大肆种植新引入的花卉植物为例,说明外来者的核心问题,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缺乏对本地原生态文化的了解和尊重,这种不尊重当地原生系统的商业化让古城陷入重重危机:
对栽花养草,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我们引导示范,教他栽培。很多客栈不懂自然,物种入侵,这些物种将原生态的很好的植物毁掉。植物也是一样的,带有特殊的病毒和昆虫,对原生态东西要有毁灭影响。你来这里要尊重这里的,用原生态的花卉就可以。我们连物种都考虑进来的。环境没有了,人文也就废了。一定要有商业化,但现在这是掠夺式的商业模式。
从文化开放性上来说,LJ历来就是交通和文化中心,信息流通,人才汇聚。在商业化问题爆发之前,因为在文艺爱好者中间的名气和旅游带动,LJ保持了文化中心的活力,本地艺术家在那个时段还能利用到古城文艺交汇的优势,能够在各地买家的购买行为的鼓励之下,进行文化交流和创造,从而在特定时期形成了古城的商业和文化的协同繁荣。墨笛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总结道:
五年前古城里开着多家卖CD的店,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音乐,是国内最好淘碟的地方,大量音乐爱好者们可以自由交换各自的珍藏。五年前朋友们还都开着各自的店,做着自由创作的木雕听着热爱的摇滚乐,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现在最后一个卖CD的店,因为过高的房租改行卖起了姜糖,原来大多数开木雕店的朋友放下了刻刀,拿起了佛珠。古城再也没有了个性,酒吧发出的只有一种声音,店铺卖的几乎都是机器生产的商品,而这些全部可以冠以文化之名,人们在旗帜下飘离了方向,盲目地自我奴役。[11]
掠夺开发式的商业化的恶果之一即是多样性的消失,文化原生创造动力的覆灭。随着大众旅游接待人次的猛增,曾经的个性销售被千篇一律的旅游产品销售所替代,而这种情况的持续说明该模式仍能盈利。在这种走量不走质的商业潮流下,如何持续性地保持经济产出和社会影响,构成了私立民居博物馆试图超出公益模式的探索背景。墨笛的想法却超越了本地传统商业模式,构拟了一种口碑导向和体验、订制式服务的设想:
这个就是一个点,我们还有很多点,他们在其他地方有其他工作室,比如盆景栽培的就有其他工作室。这个以恒裕公为接口,就是一个文化生态圈。你来这不仅是旅游,你带着孩子学习传统LJ的文化,栽花这些,既然是文化场所,和教育也有关系,彩绘雕刻手工艺,也是一种职业嘛。文化传播和文化教育这才是未来LJ的方向。
努力造就一个典范,现在还没有淋漓尽致。如果院子能得到公认,粉丝多的时候,点赞率高的时候,取经还得收费呢。我们创造的是有价值的。
现在我们就是在想经济的东西,如果让这些东西产生价值,以后也不收门票,就是体验。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逻辑。我们相信创造了价值,再交换,先开放共享,未来自然会看到经济模式。
其实从私房菜开始,老六和墨笛就已经开始重视针对特殊人群的订制式服务。他们没有雇佣服务员,而是选择自己亲自端盘服务,立意就是做一个与众不同的餐馆。在没有足够商业运营经验的前提下,墨笛所构想的集群效应、文教产业拓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处理市场营销、团队管理等一系列综合性和专业性兼具的问题。这个时候墨笛和他的朋友,或许需要多次同外界合作。相应行动的达成,或许仰赖于LJ古城管理者的策略和思路。必须看到地方实践者已经十分敏锐地察觉到自身所保有的场所价值、提高附加值的路径和以及自身人力优势。从实践意义上讲,需要给本地文人足够大的施展空间,让他们在商业经营与文化救赎之间的中间地带,调动起“体认”积累的文化资源,探索出既保证生计收益,又能让LJ文化精髓得以传习的遗产活化道路。
五、结论
老六和墨笛带领游客游览院子,其实就是一种在院子里开展的地志学。地志学(topography)原意是对地点(place)以及各类生活实践痕迹的书写,引申义为人们在各种地理环境中借助地标、物体生活并认识世界。这个过程往往也就是确认社会关系、历史条件和身份认同等意义的过程。地志学关注主体在测绘体察空间之过程中的轨迹,刻画出来的路径,以及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与人,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不断闭合又打开。老六向游客讲述院子的细节和典故,和游客协作进行场所书写,把“恒裕公号”历史与“保护祖宅”的情感自然注入到游客体验中,让平面化的旅游经历变得立体,让游客与院落产生深度的连接。而这与导游标准化的知识灌输式解说又有所不同,游客与院子主理人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谈话内容可以引申到其他主题。通过主理人的在场,包括劳作、娱乐与言辞,游客不但视觉上有所收获,也在听觉和综合感官意境上,在和东道主共同书写中,体验到场所精神。
文章伊始回顾了原真性的几轮理论演进,以及反视觉中心主义的现象学观点,LJ民居博物馆也从事实层面印证了上述理念的更新。可以说地方实践者比学院里的批评者反而更加占据理论前沿。墨笛对还原节点的不以为意,其实批评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原真性视点以及维系原状的原真性标准。退休记者游客的每日到访,诸多游客对院子特殊气氛的体会,说明庭院给他们的内部精神体验提供了最重要的场所条件,呼应了存在主义原真性的表述。老六和墨笛半生活半职业地表演,通过身体化实践,主客双方的个体能动性与外界产生互动,使得日常行为自然转变为意义的制造。同时二人“文化保护者”的角色认同在职业性表演行动中得以增强。个人色彩强烈有其局限性,但也与官方、专家的强势声音彼此牵制,形成一定的多声部交织的社会共建效果。
从行动视角来说,本案例中的行为始终介乎文化自救与经营策略之间,原真性的话语背后是应对旅游、资本以及权力角力之下的一种文化适应性综合行为倾向。老六的院子经历了多场资本围剿,也经历过私人会所的辉煌,现今在政府公助下又成为一个纯粹的公益文化设施。在这几轮转变中,历史变迁、个人恩怨、经济趋势、资本博弈和LJ本身的景观与特殊的古城肌理等诸多场域混融,则构成一个LJ庭院的“地势”。在这多轮的“地势”突围中,始终不变的是和场景配合的身体在场,这是东道主和游客在内的各类人群达到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必要条件。此外在民居博物馆打造“非日常”的提纯化的空间说明在场所文化保育的过程中需要正视文化重建的逻辑,在积极干预之下,让场所精神驻留,并认可情感伴随的意义及相应的经济文化附加值。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身体的在场,私人化的服务,情感陪伴式的体验,都需要相当的条件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