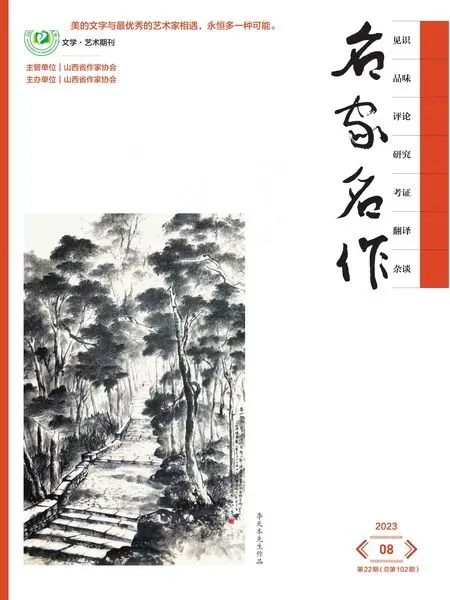民俗文化的叙事翻译研究
——以《阿 Q正传》为例
纪蓉琴
“民俗叙事”是民俗文化的文学叙事化,是小说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小说叙事中富于浓厚民族民俗文化色彩的部分。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是在目的语的语境中再现原文语言文化的叙事原貌,使原文的叙事目的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获得重生的过程。民俗文化是文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重构原文的民俗叙事策略、不断地再现原文的叙事目的的动态生成过程,是民俗文化翻译的叙事重构过程。
一、民俗叙事与叙事翻译
民俗叙事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所讲述的种种生命的历程,这些历程以文学作品的不同形态向世人展示某个人物生存的样态、风采和价值。民俗叙事翻译就是译者试图用叙事策略重塑原文中的意境和叙事目的,以动态的故事描摹民俗意象,为目的语读者传递原文本中的民俗事象和风貌,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人物和场景的原貌,重现故事和情节,用叙事的框架来设定叙述的一种互动模式。
Mona Baker提出翻译也是一个叙事建构过程,认为翻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对原文的叙事表述。原文在转换的过程中,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隐含的意义,都是一种框架设定,而翻译就是以多种方式起到阐释框架作用的过程。译语文本在重构原文本的叙事过程中可以通过叙事视角转换、叙事框架设定、标签框架设定等策略来实现。
(一)叙事视角转换
译者在叙事转换的过程中,根据原文本中参与互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与读者或听众的关系,通过语言的手段以及各种自我认同或他人认同的手段,对时空、指示、方言、语域、别称等进行操控,重新定位叙事文本中的参与者。
(二)叙事框架设定
将原文本的叙述时空在翻译时植入译文本中,使译文读者与原文本作者产生时空重合或置换。突出原文本的叙事意图,期待译文文本能与读者的现有生活体验产生叙事联想,且一般不对源语文本本身进行改变。
(三)标签框架设定
标签是指对人物、物体、事件等的指称词表现为术语和称呼等,原文本作者用这些标签描述话语过程,叙述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要素。译文本中通过对这些标签的阐释进行框架设定,引导读者对叙事文本做出正确的反应。
在重新设定叙事框架和视角转换的动态构建过程中,译者可获得一个重新审视原文的视角和一个能够使其进入历史、成就其“动态”和“历时”品质的研究路线。
中西叙事视角和方式不尽相同,中外民俗文化内涵差异显著,民俗文化的翻译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原文本在叙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社会现实。翻译是一个重构原文的过程,在转述原文的叙事目的和策略时,也在新的语境中重构译语的叙事目的和策略。
二、民俗文化叙事翻译分析
(一)叙述视角的翻译转换
“叙述视角”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叙事策略,第三人称视角是小说经常使用的重要叙事手段。小说往往利用叙事视角的切换来表现不同人物话语的鲜活性。相应地,在小说的翻译中,译者也要采取相应的叙事翻译策略进行人物话语的转换表达和传译,使译文最大限度地符合原文的叙事技巧与特色。
《阿 Q 正传》是鲁迅先生描述浙东社会生活状态的叙事型民俗文化小说。书中描绘了浙东乡民的生活百态,揭示了乡土社会的冷漠和乡民愚昧麻木的心态。鲁迅先生采取了一种传统的全知叙述、无固定视角的叙事方法,将自己作为叙述者置于所叙述的故事之外,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将阿Q 这一俗民人物完整无遗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如:当小尼姑被阿Q欺负时,小尼姑带着哭腔骂道“这断子绝孙的阿Q”。原文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经历型有限视角”,鲜活地呈现出阿Q的陋民本性以及他在社会底层生活中耳濡目染民间陋俗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充满“国民劣根性”的俗民。原文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从小尼姑的视角把阿Q设定为一个“民俗文化的负载者”,一个对泛社会陋俗的认同者。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如果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小尼姑对阿Q的厌恶、憎恨之情就难以充分体现。译者(蓝诗玲)把原文的叙述视角进行了一定的转换,运用第二人称的视角,将该句的愤懑之情以感叹句的形式转换出来,把该句译为“May you die without descendants, Ah-Q”,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同时强化了人物——小尼姑的情绪渲染。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将整个事件直观地展现出来,烘托出小尼姑的厌恶情绪与阿Q泼皮顽劣本性的对峙,使人物形象刻画得更为生动,使译文通过主观直接的叙事方式更鲜活地展示出小尼姑和阿Q的人物形象,使西方读者能更好地领略中国浙东地区的乡俗文化原貌。
(二)叙事框架设定的翻译转换
莫娜·贝克认为翻译是在译文语境中的再叙事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一个叙事再建构的操纵者,通过重设叙事的标签框架,译者可以使叙事建构偏离最初的目的,以使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或行为更好地达到原文作者最初的意图和期待。
1.标签框架设定的翻译转换
小说《阿Q正传》描述的是浙东绍兴地区俗民的生活样态,从人物场景到时空框架的叙事尽显乡间民俗多彩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堪称一部厚重的关于地方民俗的作品。鲁迅在小说中叙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阿Q的俗民形象,把浓郁的浙东乡镇习俗融入小说的叙事中,使浙东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了小说生动的故事背景,勾画出了阿Q等一众乡民的生活画卷,乡民的生活样态成为意蕴深刻的情节主干,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小说细节,使小说独具意蕴和风采。《阿 Q正传》把大量的浙东民俗文化信息,如具有文化价值的民俗、独具魅力的语言民俗,融入小说丰富的人物素描中,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民俗特色文化叙事。从叙事的视角看,对该书的翻译策略选择应该以向西方读者呈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白话文夹杂文言文的叙事特色为视角,尽可能展现出原著的民俗风貌,传递出原著的民俗文化叙事目的。由于在原著与译文中存在时空错位——原著是20世纪早期的中国浙东乡镇的民俗叙事,但是读者却是当代的西方人,要使作品有时代感,就要进行“时空框架”的转换。原文作者采用充满乡土气息的浙东方言进行小说叙事,而译文则采用准确、流畅、优美的当代英语来转换,所以在语言上就要采用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阿Q正传》中包含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如“黄酒”“黄伞格”等,若将这些充满浓厚民间乡俗文化的词语进行直译,原文承载的民俗文化意蕴则无法实现。
(1)物质文化负载词。鲁迅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叙事标签词汇——物质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汇承载了特别的物质文化信息,在译文中没有可匹配的叙事标签词。如:“黄酒”是浙江地区民间常见的一种用稻米酿成的酒,而西方没有用稻米酿制的酒,一般用葡萄酿酒,有“white wine””red wine”。中国传统的米酒与西方的葡萄酒颜色不同,稻米酒是米黄的,而葡萄酒呈褐色。若把“黄酒”这一民俗事象直接译为“yellow wine”或“rice wine”,西方读者对大米酿制的酒缺乏直观的对应感,容易直接与褐色的葡萄酒联想,会造成西方读者的迷惑。译者可以转换叙事框架,将西方读者直接拉入异域文化的民俗事象中,直接采用音译的方式,用汉语拼音译成“Huangjiu”或“Shaoxing wine”, 通过标签框架设定来达到原文的叙事目的。
再如另一个叙事标签词“黄伞格”。“黄伞格”为旧时的一种极其正规的书信格式,以八行为一组,是一种骈体文式,多用来表示敬意和赞美。这种书信格式的写法是隔行顶格跳写,每行都不写到底,留出中间一行写受信人的名号,因此使得每一行都比其他行高出一格,导致隔行的文字很多,要一直排列到底,与左右两旁的短行居中相间,看起来像旧时官吏仪仗中矗立着的一把散开的黄伞,故而得名。若将这种象形似的书写格式的名称进行直译,西方人会不知所云。翻译时运用阐释性的叙事框架设定,将原文本中的术语运用描述叙事的方法,解释性地译为“an extremely formal letter”,以达到叙事转换的目的。
(2)社会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典故、艺术风格等,社会文化负载词指承载一定社会习俗、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词汇。在《阿Q正传》里,鲁迅用了许多乡土粗语来刻画人物的生动性,如:“忘八蛋”一词。这是小说中秀才在人群后面骂人的口头禅。“王八蛋”是中国人常用的粗俗的语言之一。“王八蛋”的字面意义就是指“乌龟”下的蛋,并无任何不雅、粗鲁的含义,但是在旧时的中国,这个词最早是由“忘八端”这个词的谐音转化而来。“忘八端”是指放弃了八种道德准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后来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地被谐音成了“王八蛋”,其原有的词汇“忘八端”也早已被人们忘记,而是直接用“王八蛋”来形容一个人的不耻行为。虽然这个词已被简单地替换成为“王八蛋”,但其原意尚基本保留,在翻译成英语时,通过阐释性的框架设定,采用英文中的“Shame on you”加以注释和描述它的叙事内涵,使其文化内涵意义得到转换,使异域的民俗事象在译语中尽可能得到体现,达到原文的叙事转换目的。原文本作者用这些叙事标签描述话语过程,叙述故事中的人物情结要素,进行框架设定,引导读者对叙事文本做出正确的反应。
2.时空框架设定的翻译转换
《阿 Q正传》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白话文夹杂文言文的小说,它的“时空框架”设定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浙东乡镇,但是译文读者却是当代西方人,要使作品能被现代西方读者读懂和接受,进行现代语言表述的“时空框架”转换就成为必要。如:小说中表现俗民阿Q的享受状态时描写道:“这是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的如同六月里喝了雪水。”“六月里喝了雪水”用来比喻阿Q喜悦的心情。浙东地处北半球的亚热带,夏季气候异常炎热,若能在炎热的夏季喝上冰雪一样凉的水,被视为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但是,西方的读者群并非都是居住于北半球的,一些位于南半球的国家六、七、八月是冬天,即使有一些说英语的国家位于北半球,因纬度不同,夏季也不一定如浙东般炎热,因此处理这类时空交错的表达时,要结合读者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时空框架重置的叙事转换,才能使目标语的读者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以提高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三、结语
民俗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叙事的转换和传递,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在传递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恰当、适宜地传递出原文本的叙事特征和风格,使具有独特的区域性和文化性的民俗叙事,通过叙事视角和框架的转换在目的语文化中获得新生,在叙事的“体验性”“可叙性”“意旨”等方面与原文契合,达到新的叙事目的,从而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重塑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