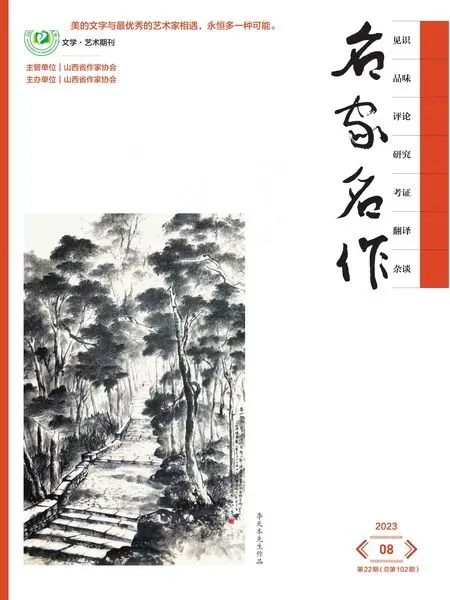解构主义视角下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以林纾的译文为例
初春璐 董海琳
一、研究背景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比较显赫的后现代思想,它起源于对结构主义“不满意、失望甚至否定、反抗”的态度。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这种观点引入翻译理论中,并对传统进行了彻底颠覆,对传统的翻译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解构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逻各斯中心论、作者的绝对权威和传统结构论提出了异议,主张先有明确的内部含义,然后才能用文字来表达,而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这就是对语义真实性和结构真实性的直接否定。解构主义主张打破原有的体系,开放闭合的结构,排除中心与原点,消除二元对立。德里达认为,二元结构是死板的,它的严格界限只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并不存在。具体而言,德里达解构了结构主义的原始体系与结构,摒弃了“中心”与“本源”,让“本源”与“本源”自由地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无穷可能性的“意义”网络。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译者的主体性问题都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人们关注的重点一直都是语言层次,认为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因此译者一定要严格遵循原文。字里行间的翻译,精确地传达了原作者创作的意图。“媒婆”“仆人”“锁链舞女”“翻译机器”“文化搬运工”等,都为翻译赋予的不同的称号。然而,解构主义的译学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译学理论,并为译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理论。本文试图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性做一简单的评述,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寻找到其与翻译理论的切入点,从而促进翻译理论向多视角、多层次发展。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 特(Roland Barthes)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他们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中,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逐渐形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流派。
解构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从解构主义角度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从解构论的角度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在这一背景下,解构主义对翻译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是否可以在理论上进行反向思考,假设原文对译文的依赖性?如果没有翻译,原文就不会存在;如果原文中的意和义并不取决于原文而取决于翻译呢?这种大胆的假说反驳了原作的本体论,而更关注于原作的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认为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一种语篇都存在着互文性,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着对等和互补的关系;翻译应该努力体现不同语言间的差别,而译文的价值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不同语言间的差别。就像翻译家布朗绍指出的那样:“翻译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游戏,它必须包含不同的东西,而且必须隐藏不同的东西,但有时会使不同的东西显现出来,有时会使不同的东西更加明显。”因此,翻译就是这种区别的具体表现。
四、 解构主义的重新解读
解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引入中国后,关于解构主义和它的译学观点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予以彻底否认,认为解构主义过分强调含义的不确定而造成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破坏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造成了译界的胡译、乱译和译者的不负责,是“学术上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断绝作家的生命,否认所有的文学创造,“使译文和原作之间的差异消失,同时也使译文自身消失”;“没有对具体的翻译过程进行细致的讨论”;对翻译的实际指导意义不大等。另一种观点则承认解构理论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但又认为其存在较大的缺陷,使翻译界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为胡译和乱译提供了正当理由。
本文认为,解构主义对语义的强调并不是一种偏激,更不是一种虚无主义。德里达曾说过,“除了文字,什么都没有”,随后,他将其发展为“除了上下文,什么都没有”。语义是一个语境事件,语义与特定的语境密不可分,此处的“语境”既包含“语境”,也包含所有与该语境相关的语篇,还包含较大范围的社会、历史语境。德里达相信,我们之所以能读懂莎士比亚的话,是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重复的编码,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它就会积累起来,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含义。
解构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了理性的思考,解构主义也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构建和阐释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更加注重非理性的成分,而不是一种虚无主义。有人说,这样做只会造成胡译、误译,无人负责。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般认为,翻译应该是能够同时使用原语与译语语言进行翻译,思维正常,具有较高的文学欣赏水平。出于对语言与文学欣赏的需要,我们不能随意地将它胡乱翻译出来。
五、解构主义视角下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一)原文因其可译性而与译文紧密相连
Benjamin认为,再好的译文也无法表达原文的意思。但是因为它的可译性,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密切了。然后他补充道,这种联系是自然的。关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不能从自然过程中理解,考虑如何翻译才能与原文相似,而是从译文中理解原文。
(二) 原文与译文是平等且互补的
根据德里达的观点,任何一种文本在翻译过程中都存在着“互文性”,这是由于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化造成的。原作中“文化语境”的重建与翻译,开启新的历史、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从这一角度来说,译作并非原作的具体体现。翻译并不完全依靠原作,而是要依靠原作为自己带来新的读者、新的生活。译本就是原文的“来世”,而译者的使命就是使原文继续存在下去,使原文的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得到延伸。所以,任何一本书,只要有更多的机会,它就有更大的生命力。因此,原作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补充的,而不是主从关系。对原文来说,翻译文本在意义或内容上不发生变化,而只是在语言上发生变化。翻译是显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根据德里达的说法,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篇文章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差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种“互文”,它否认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差异,也否认了原作的权威,即源语和目的语是对等和互补的。
(三)原文的权威被推翻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原文的作者和原文的权威这两个概念。解构主义提供了另一种理论来重新评估这些概念,甚至打破这些传统概念。解构学家认为,原文在当下不断被改写,每次阅读/翻译都会重建原文。德里达应用沃尔特·本杰明语言的“生存”来解释翻译是如何修改或补充原文的。原文在变异和转换中幸存下来,原文也被修改——在不断的修改中得以升华。Benjamin在论及翻译主体地位时,他提出了“纯语言”如同一只花瓶,而其他语言则如同一只破碎的瓶子。每个片段都有不同的形状和尺寸,这就意味着这些语言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翻译的工作就是找出那些可以互相搭配的片段,将其拼凑在一起。他把译文比作原文的“来世”(afterlife),他说,“就像生活的表象虽然对生活的现象并不重要,但它与生活的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翻译也是从原作品中产生的,但它更多地来源于原作品的来世,而不是原作品现存的生活。原著的生活之花在翻译作品中以最新鲜和最灿烂的姿态绽放,这一持续的更新让原著焕发出青春,万古长存”(Benjamin,1923)。翻译者要做到的,不是简单地照搬原文的意思或内容,而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发现原文的意思,并借助译语语言不断地对原文作出新的解释,从而给原文以新的生命。一种译本是另一种较早出现的译本的译本,像这样往前不断地循环,就变成了一条“无限”的意义链。“互文性”作为一种语篇现象,其实质就是对作家权力的一种挑衅。因此,解构主义对文本的结构进行了瓦解,将其视为一种无中心的系统,作家并非文学行为的中心,译者和作家一样,都是翻译的主体,唯有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二次解读,原作才能生存下来。
六、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比较分析林纾的译作与原文
(一)标题的解构
林纾译的书名,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黑奴吁天录》,都与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书名相似,充满了江湖恩怨、儿女私情,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且书名上还带着很强的主观性,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特色。但原本的书名却很普通,甚至有些模糊,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和感情。《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原文标题为La Dame aux camélias,很明显,原本的书名并没有透露出故事的结局,也没有透露出作者的喜怒哀乐,读者只能猜到故事的主人公是茶花女,但在林纾的书名中,“遗事”两个字却告诉读者主人公是最后一个死的,这就说明了这个故事的悲惨,也说明了作者的悲哀。《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的原文标题为 Montezuma’s Daughter,简明扼要,没有暗示出作者的情感和剧情。从林纾的书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豪迈之情,也可以看出小说情节的曲折和精彩。《黑奴吁天录》的原文标题为 Uncle Tom’s Cabin,从书名上看不出作者的用意,也看不出作品的内容,但光是这个书名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这与时代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对小说的翻译是以教导百姓为主,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小说并不是一种高雅的文学,而且它的受众也主要是普通百姓。对于平民而言,他们并不喜欢依附于贵族。林纾在此基础上,将译文的书名加以本土化,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在那个时代,中国小说充满了英雄气概,甚至还带着几分市侩和粗俗,但在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修改后的书名要比深奥而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书名要好得多。林纾先生很清楚这一点,他调整了自己翻译的标题,不是死板的翻译,而是把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打碎,加入翻译的标题中,重新组合原著的标题,使翻译的标题更适合当时的社会大众。
(二)内容思想的解构
林纾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殊的历史特征,那就是“国难当头”。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林纾的译本对原著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作品在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力。林纾在其《黑奴吁天录》的跋文中写道:“黄人将灭,故更感忧伤。”其时中国社会正在遭受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人遭受的剥削、压迫比黑人还要严重,林纾曾经在序言中写道:“因为中国人遭受的欺负比黑人还要多,因为使节不敢反抗,加上没有文字记录,故无从知晓。只有那本《黑奴吁天录》,才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林纾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广大民众,让民众自觉地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以求自救,以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七、结语
时至今日,中国翻译界对“信”“达”“雅”这三个字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但“信”仍然是我国译者应遵循的最根本的原则。解构主义在理论界引起很大的争议,被指责为“虚无主义”“不可知性”,但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也有其优点,即把译文看作是对原作的一种再创造和继承,肯定了译文的地位以及译者在译文中的作用,给了译者很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长期以来,“信”原则一直制约着译文的发展,制约着译者的思维,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则强调了译文与译者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译文在目的文化中更具有生命力,也使整个翻译过程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解构主义,我们要取其精华,从而用于指导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