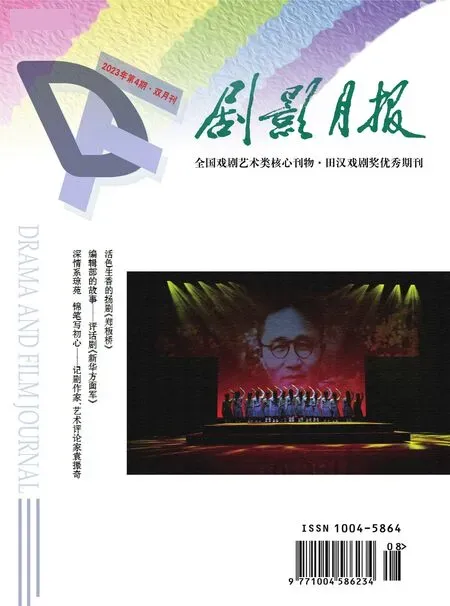以空间视角看《妈妈!》中生命问题的诗意表达
■董逸娟
《妈妈!》于2022年5月上映,是继《春梦》《春潮》之后杨荔钠执导的第三部关于女性的影片,由吴彦姝和奚美娟主演,讲述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女儿与母亲之间的故事,暗含了家庭与伦理、爱与生命的主题。杨荔钠导演及其团队都是女性,以温情却不缺乏深意的眼光关注女性生活和社会现实问题。在电影处理时,又将镜头聚焦于普通家庭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诗意的画面将故事如流水般缓缓诉说,不高大、不空洞。在电影中,女性的日常生活通过一系列主人公的工作、家庭生活、周边环境等空间场域的转换得以展现,关于生命的思考也以一种空间诗意的方式得以探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着重渲染了“空间”这一命题,他的空间思考是基于空间感知、空间想象、空间经验三层维度为一体的空间观念,由此构成了关于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表征性的空间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本文试图以镜头中私人空间、社会空间、自然空间的建构为纬,以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理论为经,对影片中交织的伦理与生命问题进行解读与回应。
一、私人空间的塑造
(一)离群索居的独栋小院
在电影中,冯济真与母亲所居住的独栋小院是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空间。从物质空间的性质来看,这所远离闹市的小房子是母女两人简单的家庭生活环境的真实再现:黑色的铁门、红砖砌的围墙、透明的玻璃门窗、种满花草的庭院,一切都显得生机盎然、充满诗意,营造了一种静谧美好的视觉效果。从拍摄手法的使用上看,当冯济真与母亲同处于一个场景时,画面往往以景深镜头呈现,或是镜头与被拍摄的人物隔着一层门窗,进行远距离拍摄,不仅丰富了家庭画面的空间感,也使得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加朦胧且富有诗意。此外,母女两人远离人群的居住环境本身就已经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信号:她们的身份与经历是与普通人不一样的。随着影片播放,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家庭与常规家庭相比,是“不完整”的,家中没有父亲,也不存在下一代,母女俩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退休大学教授,她们的生活自足,社会关系简单,即使冯济真每天都在做义工,也常常以沉默的方式出镜。列斐伏尔认为独栋住宅的居住者往往具有一个想要保护的私人的人格,这种住房常常对应着一个理想,即它包含了保护与孤立的愿望,暗含着认同与自我确认的需要以及独处的需要。由此,外部的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矛盾对立赋予了独栋住宅以意义。
从空间的表征这一层次来看,对于失去父亲之后的冯济真而言,这栋住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在电影开头,冯济真与母亲蒋玉芝的关系是“颠倒”的,母亲是被照顾的一方,而冯济真则沉稳可靠。但冯济真没有结婚生子,生活也很节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做义工一事上,没有额外的社交,可以说是独来独往,这些使得她身上包裹了一种孤独感和压抑感。直到电影后半部分,观众才得以窥见某些原因,冯济真始终认为自己导致了父亲的去世,是有罪的,为此她一生背负着沉重枷锁,而她的节俭的生活以及做义工都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小院的大门与围墙既是划分私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界线,更是冯济真为自身筑成的坚硬外壳。这座孤独诗意的房子是冯济真精心打造的充满美好回忆的乌托邦。不管是庭院中被精心照顾的花卉,还是房屋内陈列的父亲珍爱的古物,乃至出版父亲考古日记的执念,冯济真对物的投入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对安全感和自我救赎等意义与符号的投入。
(二)被门窗框住的房间
门与窗作为内置于家中的物像在电影画面中经常出现,但导演不仅仅是简单将其作为一种背景处置,而是充分利用了玻璃门与玻璃窗的透明性质及其边框在画面中的空间感,当电影中的人物处于私人空间时,镜头常常会透过窗户拍摄屋内的人物活动。在画面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占有很大比例的方方正正的窗沿以及有点模糊的玻璃窗,人物活动所占的比例反而变小,且具有一种朦胧感,由此形成了一个包含着语言符号意义的精神构造与想象的空间,这也正是作为空间主体的导演及其拍摄团队所特意构建的。采用这样的手法拍摄时,窗户内的场景一般都比较温馨美好,如母亲向女儿撒娇、母女两人读书时的岁月静好、母亲安静的睡颜、周夏耐心地哄孩子睡觉等。这种时候,镜头聚焦于窗内人物,周围的窗楣以及物品会虚化处理,外部画面色调暗,而内部人物画面则色调偏暖,画面整体如同一幅老旧的回忆,而人物被限制在大面积的窗框内部,使得人物距离银幕更远,营造了一种极具空间感的诗意画面。
然而,玻璃窗的功能不止于此。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尽管窗外的人能透过窗户看清屋子内部人物的活动,但却始终没办法穿透这层隔膜真正触摸美好,窗户如同一个保护罩,具有一种看见却不可得的功能。而窗户内部无疑是冯济真渴望的美好,这点从她的幻觉场景得以明显表现:冯济真多次透过窗户看到父亲教学时的身影以及父亲在玻璃门外抽烟赏景的身影。在黑暗的画框中,小小的屋子透着昏黄的灯光,屋内是曾经拥有的美好,冯济真作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最害怕就是遗忘,然而玻璃窗就如同相机的镜头,将一切不愿意忘记的回忆都定格在房间里。同时,透过玻璃窗拍摄的小房间也可以看作冯济真柔软的内心世界。冯济真自16 岁就没有笑过,一生都沉默寡言,背负着沉重的镣铐艰难生活,这间屋子也是她整理父亲考古日记时工作的小屋,可以说汇聚了她所有的执念与思念,是她内心唯一没有荒芜的土地,因此色调以暖色来烘托,而外围模糊、暗调的一切可以看作冯济真内心一层层裹起来的壳。导演以玻璃窗为媒介,刻意制造了一种明明不在场却又有极强在场感的第三者视角,借此既拉远了观众与冯济真内心人格的距离,又创造了一双虚无的眼睛,这双眼睛代表着另一个冯济真的自我观察与审视。其实不只是窗户,电影中一切具有映射功能的物质都有类似的作用,如海洋馆的玻璃、进入客厅时的玻璃大门以及房间的门框等,以上这些都以规矩的边框凝固了某些温馨的画面,让这些美好的温度得以借此绵延。
二、自然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立
(一)社会空间的不安与窒息
社会空间作为一个动态、生产性、充满想象的场域,既不同于直接感知的物质实践空间以及被语言符号化的精神性空间,但同时又包含前两者,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它要生产的关系使用者与环境之间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社会空间存在不是物性对象物或空场,而是由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建构起来的场景存在,它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表征性的空间作为三元辩证法中第三个维度,是一个被各种权力与规则支配的空间,列斐伏尔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形式与权力的运作进行探讨,揭示社会空间的生活层面。
在电影中,导演有意让冯济真面对人群,借助观众与镜头的他者视角来观察社会关系下的冯济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对她更为真实的存在状态的还原。然而在这种社会空间的场域中,冯济真总是处于某种不自在的状态,因此与身边人群相比具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异样感。尤其是在构建公交车这个人群混杂的社会空间时,特意用镜头的转换表现了冯济真眼中的公交车世界,当男人指明手机在她的包里时,观众借助冯济真的视角能清楚地看到公交车上他人的猜忌及男人眼神中的厌恶。在表现这段情节时,镜头一度在他者与冯济真之间反复切换晃动,以此表现出冯济真内心的慌张无措。在这个过程中,每当镜头转向冯济真本身时没有发生虚化且人物所占比例较小,但转向其他人时,画面明显变虚、四周出现了许多光斑且有意放大了人物比例和人物的表情动作,这既可以看作是冯济真得病的前兆,但更重要的是它以这种方式塑造了一个在社会关系中极度不自信、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角色。
(二)自然空间的自由与释放
自然空间的构造是这部电影中除家庭以外的一个重要的故事发生场域,也是冯济真日常活动的又一重要空间——一片小湖。“在被认识之前,空间就已经存在,在可以被解读之前,空间就已经生产出来。因此,对空间文本的解读和解码,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表象的空间如何向空间的表象的转变。”当冯济真出现在湖边这个自然空间时,往往是独自一人,如果说家庭是冯济真的牵挂,那么这处与天地共生的宁静湖水对她而言则是一个人独自疗愈、寻找救赎的空间。然而自然在整部影片中的表征性意义并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以冯济真意识清醒与否为分界而发生转变,导演以冯济真心理及情绪变化的张力为要素构成了整个表征性自然空间。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是自我的构成性话语,相反它仅是我的身体、是我身体的对应物,是身体的镜像”。镜像态的身体揭示了身体和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镜像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也披露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通过镜像,身体和自我毫无保留地展露在对方面前,并且自我把自己从身体中抽离出来,以一种他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身体,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杨荔钠将原本就具有镜像作用的湖水作为冯济真表露内心的自然空间,借助湖面使得观众和冯济真本身都从身体中抽离出来,从他者的视角将冯济真的内心状态变化更加直观地展现了出来,由此自然空间的表征体系更加完善。
湖水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冯济真患病后的幻觉,与她的内心状态互为呼应。湖水作为冯济真的重要空间第二次出现是在父亲的考古日记出版后,镜头从长满杂草与淤泥的湖底缓缓过渡到波光粼粼的湖面,冯济真穿着裙子坐在船中缓缓入镜,小船周围散落着树叶,由近景到远景,从仰拍到俯拍,整段画面只有自然的水声、风声,却将冯济真内在的释放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考古日记的出版让她心中的夙愿得以实现,盘亘在心中的执念与愧疚也逐渐消散,宁静广阔、泛着波光的湖面正如冯济真此刻的状态:平静自由,重获新生,仿佛她真的回到了与父亲相处的愉快时光。湖水第三次出现时,她又穿上了碎花裙,捡起落在水面上的落叶,与第一次对湖边的描写相呼应,但此时她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了妈妈的陪伴,然而这段关于人物的场景全都通过湖水的倒影来拍摄,冯济真蹲在水边轻声呼喊“爸爸”,紧接着父亲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水中,一家三口就这样通过湖水连接在了一起,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思念反映在了这个自然的空间,在这种现实与虚构之间呈现出了诗意性。在最初,湖水对于冯济真而言是一片自视为只有自己可以抵达的安全领地,并独自沉浸其中,成为她逃避外界、寻求救赎的场所,然而逃避总是暂时的,这里仍然有着动荡与不安侵蚀着她内心的乌托邦。随着冯济真心结的解开,对湖水这一空间的描绘由狭窄逐渐变得宽阔,这里真正成了冯济真纯洁的内心世界的代表,在这里她可以不顾复杂的社会关系,不拘束于一方小屋,尽情释放自己,享受和幻想中的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三次对湖水这一自然空间的描写借着对人物自身内在情感的冲突与张力构建起了冯济真的心理空间体系,也让观众得以意识到精神失常下冯济真心中真正的所思、所念、所感。通过湖水这一自然空间的表征性走进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内心,让原本对此一无所知的也无法感同身受的“正常人”借此理解他们,这也正体现了导演关注个体生存境遇、关心社会问题的拍摄初衷。
三、空间与生命的诗意交织
(一)从未远离的父亲
杨荔钠以诗意的镜头构建起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空间,但她所聚焦的不仅仅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群体,更是试图通过镜头探讨关于生命的终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可以在冯济真与父亲、母亲和周夏这三对关系中得以窥见,可见可感的空间与无形却充满力量的生命也得以交融,构成了一个弥散着爱与希望的场。导演将“不在场”的父亲解释为:“影片里的魂魄,没有他就没有这对母女,所以他把三个人的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影片对冯济真的塑造是着墨最多的,但在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加重之前,观众很难从镜头中感受到冯济真身上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她仿佛是一个“被建构”的存在,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尤其在电影前半段,镜头所展现出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客观性的,而很少带有她个人的真实气质:我们只知道她每天的最主要工作是整理父亲的考古日记,却不知道她本人喜欢、厌恶什么。父亲的自杀让年幼的冯济真背负了一生的罪念与愧疚,可谓她个人气质的直接塑造者。也正因此,冯济真的每日辗转的生活空间始终充斥着父亲的影子,“日常空间是日常生活所代表的那一类空间,它是表征性的空间,正是身体的独特实践产生了这种既不同于自然空间,也不同于心灵空间的日常空间。”以冯济真无数次的幻视幻听为媒介,观众清晰地知道不管是处于具有乌托邦意义的独栋小院,还是连接着生死虚妄的湖水,又或是让人拘谨不安的社会环境,父亲所营造的影响与秩序都是无处不在的。对冯济真而言,尽管父亲早已离去,她也从不正面提到自己的父亲,但他却仿佛始终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父亲的爱与遗憾、幼时的美好与过错始终萦绕在冯济真所生活的日常空间中。
父亲对冯济真而言是特殊的,虽然她对父亲充满了爱意与敬意,但每当父亲的幻影出现时,冯济真表现出来的行为除了惊喜以外更多的是弥补。电影中有一个父亲出现在房间外的庭院中的镜头,这时屋内的冯济真发疯似的试图打开房门,这无疑召唤了她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又如在冯济真去医院看病时,镜头对着冯济真,但却传来了医生对另一个病人说的话“天鹅绒、面孔、教堂、红色、菊花”,而这里提到的每一个词语都对应着一段与父亲有关的记忆:天鹅绒是冯济真想要送给父亲的礼物、面孔指父亲的脸、红色是和父亲一起跳舞时的红裙子和小皮鞋、菊花是父亲生前喜欢的花束。尽管父亲是“不在场”的,但他串联起了家庭三人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他的不在场,冯济真所有的沉默与孤独都变得合理化,也间接地使得冯济真所有的日常生活空间都含有不同于物质实践的表征意义,而那个关于“我爱你”的暗号则成了失语情境下穿越时空、跨越生死的浪漫表达。
(二)母爱与自然的表达
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以子女对母亲的称谓为名,不如说是子女对母亲发自内心的呼喊,正如导演杨荔钠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的,“如果‘妈妈’不放任何标点符号,它就是一个名词;如果放上感叹号,它就是一个情感词,为母亲这个词汇注入更丰富的情感和力量感,它的意义就不像名词那么单薄。”虽然电影主要以冯济真为视角,但毫无疑问全片饱含着浓浓的母女之情,尤其是在冯济真病症加重后,母亲蒋玉芝对她“母狼护崽”般天然的保护让整部电影都溢着暖暖的爱意。虽然冯济真的性格孤僻,在表达爱意时也常常采用隐晦甚至有点强硬的方式,母亲反而成了弱小的一方,但正是前期这种颠倒的母女关系的设定,让蒋玉芝更显出身为母亲为保护孩子而焕发的强大能量。在描述母女关系时,自然作为冯济真整个人的疗愈与救赎空间,同时也成了彰显两者之间关系的镜子,尤其是自然中与水有关的空间成为电影中表达母爱的表征性空间,电影中主要包括三个空间:被雨水洗刷后的庭院、湖水以及大海。在冯济真与母亲坦白了自己的病情后,有一段长达20 秒的关于雨水浇打庭院中花草的空镜,在这之后,母女两人的关系再次“反转”:蒋玉芝再次恢复了照顾者的角色,披上盔甲重新回到保护幼崽的战场,用自己的光与热为冯济真树立榜样。这之后的故事发展正与雨水淋过花草后阳光再次照到庭院中的空镜相呼应,既是她们内心从恐惧沮丧到积极向上的反映,也是遭受疾病摧残的生命仍然顽强生长的反映。后期随着冯济真疾病的不断恶化,她非理智的一面不断展现出来,与母亲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两人之间的激烈拉扯与母亲的崩溃也是发生在下着暴雨的庭院中,冯济真肆意地躺在椅子上接受着这场来自自然馈赠的雨水的洗礼,而母亲面对无法沟通的女儿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在这处半开放式的庭院中,在雨水与院中花草的互动中,母亲对女儿的照护、包容展露无遗,生命的意义也在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下得到了新的诠释。
在故事前半段,湖水一直被冯济真视为安全、自由的空间,她常常独自一人出现在这一场所,而母亲作为“外来者”与冯济真一起出现也意味着冯济真封闭的内心逐渐愿意向母亲打开,对父亲的愧疚感也逐渐消散。然而湖水对于母亲而言似乎是一种沉重的存在,湖面所倒映的目前的面孔充满了一种沉淀过后的忧思与悲伤——她的丈夫投湖自杀、女儿日渐加重的疾病都成为她无法言说的隐痛。在湖水这个镜面中,她凝视着自己衰老的面孔,在自然这个静谧无人的空间中反复咀嚼生命的流逝与岁月留下的无法抹去的刻痕。在电影结尾,母女两人穿戴整齐,以优雅的姿态走向包容万物的大海,而这又与冯济真所言的“妈妈是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重叠。海这个孕育着巨大生命的自然空间正如同母亲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与对子女的爱意,温和地抚慰着疾病折磨下的冯济真。“大海更像是蒋玉芝和冯济真这对母女的精神家园,海浪汹涌,人生浪潮,还有母爱的力量都包括其中”,同时,在这个自然形成的广阔空间下,大海似乎也以一种更广大的胸怀拥抱着每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在这里关于生命的终极意义的答案也以开放的方式交付给了每一个愿意倾听的观众。
(三)生命的延续
在电影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就是周夏,她的出现打破了冯济真原本循规蹈矩的生活,成为电影中一抹鲜活的色彩。周夏以“犯错的年轻人”这一形象出场,冯济真在公交车上与她的对视意味深长,在这之后,冯济真一次次选择宽恕,用自己的爱意感化了叛逆的周夏。而对于冯济真而言,周夏不仅仅是他者的存在,更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犯错的自己,正如影片中周夏所言“看上去像是你拯救了我,但其实是我成全了你也说不定”。周夏的鲜活、充满生命力是过去的冯济真拥有过的能量,也是现在的她最缺失的部分,冯济真不愿意看到年轻的生命走上歧路,这既是对周夏的救赎,也是对曾经的自己的救赎。在临近结尾的部分,焕然一新的周夏再次出场,这时她依然充满活力并且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当她出现在冯济真的家中并为冯济真和蒋玉芝帮忙时,电影响起了轻快的音乐,整个家庭的色彩明显提亮,画面中充满了阳光。
冯济真的前半生一直将自己封闭在这处象征着美好也包含着罪恶的空间中,父亲曾经居住的小屋更是她不愿意轻易打开的私人空间,而镜头透过那扇小窗,最终缓缓定格在屋内周夏育儿的画面上,也意味着原来的执念与愧疚终究逐渐淡去,新的生命将会不断承载着爱与希望,一直延续下去。在这处原本充斥着昏暗与衰老气息的封闭空间中,杨荔钠以最后窗户内的暖调画面作为漆黑房间的点缀,以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生命作为整个空间生产的辅助,以此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完善了影像空间生产最为重要的层面。
整部电影以一个又一个空间连接起冯济真的日常生活,也借此将她的内心世界外化,构建起冯济真的过往与未来。在空间的转换下,冯济真与父亲、母亲和周夏三人的关系不断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关于生命问题的终极回答。杨荔钠导演以细腻真实的镜头对准隐藏在社会皮囊之下的问题,画面中对家庭中日常生活的表现,始终都以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为底色,讲述个体的生存境遇,成就了一部包裹着浓厚温暖之情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