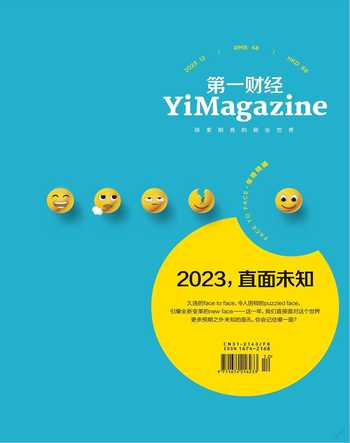气候变化下的农业
崔硕
2023年10月被国家气候中心认定为有气象记录以来连续第五个同期最暖月份,这意味着2023年6月至10月为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同期最暖,2023年夏天也是中国自1961年以来第二热的夏天。即使是冬天,气候变暖的迹象也日渐明显,在过去的11月里,北京有17天的日最高温在10℃以上(截至11月25日)。我们正在加速走向一个更热的气候时代。
联合国下属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今年3月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11年至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相比1850年至1900年升高了1.1℃。气候变暖正从此前气候专家呼吁要警惕的趋势,变成人们生活中的感知。
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研究,2019年太阳辐射的强度比工业革命元年——即1750年——增加了2.72瓦/每平方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气候韧性农业技术研究部首席科学家许吟隆认为,如果作类比,相当于地球每天要多承受200万颗原子弹级别的能量。而在这些能量中,“万幸海洋吸收了91%,陆地吸收了5%,冰川融化吸收了3%,真正留给大气层的只有1%。”许吟隆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即使这样,地球温度也升高了1.1℃。
但大众对气温升高存在理解误区。通常人们认为气温升高是一个逐渐叠加的过程。但事实上,气候变暖会导致极端天气的增加。在许吟隆看来,“暖冬”与“气温屡创新低”恰是气候变暖的一体两面。
人类活动加剧,致温室气体能吸收的太阳辐射增强。在中国北方,作为暖气团的北大西洋暖流也随之加强,北极涡旋气流的涛动,使这个暖气团作用于由西伯利亚高压、蒙古高压组成的欧亚大陆冬季冷气团,导致更强的冷气团破碎南下,形成极端寒潮天气。
“温室效应导致平时冷空气没来时比原来暖,但冷空气来了后比原来还冷。”许吟隆说。天气的波动将越来越频繁,波动的具体表现除了特别热、特别冷,还有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多。
今年的“7·31京津冀特大暴雨”就是最典型的极端天气例子。许吟隆认为,有3个条件共同造成了这场大雨。首先是伴随海平面温度升高,蒸发的水汽增多,杜苏芮由此积累了大量水汽;其次,是杜苏芮自福建泉州登陆后,当地的复杂地形造成极端降水,而其北上过程中又大多是平原没有阻挡,再加上过程中大面积高温,甚至杜苏芮周边的空气比它热量还高,中间没有消耗多少能量。最后,台风到达北京周边时,正好副热带高压北边界在北京附近,北部的冷气团阻滞了台风北移,而燕山山脉、太行山脉的地形抬升,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的84小时极端降水。
对于中国南北方的夏季来说,变暖的成因截然不同。南方的高温是由副热带高气压本身的热度带来的,北方的高温,则是因为“原本的北方冷气团会一路南下,但它停滞了下来”。许吟隆说,当冷气团通过太阳辐射不断吸收能量,地面不断加热后,造成其变性,变为了热气团,给北方带来了热量。
所有的天气变化都是缓慢持续的,以十年、百年甚至几百年为单位来计量,人们有时会忽视这种长期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相比同样生存在土地上的人,植物对气候更敏感,其中,农作物的生长又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北方,极端的干旱与暴雨正在影响华北地区蜂农的收成;在甘肃、宁夏和东北,原本并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地区开始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种植品种,全国的酿酒葡萄和水稻适宜种植区在不断北扩;在南方,云南山区的干旱与雨季的推迟使得野生菌产季推迟了一个月。
我们选择了以上4个区域的代表性农产品,希望能呈现出从餐桌到气候之间更复杂的关联。
農业生产还涉及农田管理,因此不能将产量、质量,与气温的升高、降水的变化直接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暖正带给农业生产越来越动态的不确定性。当光照、气温、降水等一系列影响农产品产量的因素都随着气候变化发生改变,种植方式也必须快速调整。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带来的是整个农业系统都亟待应对的问题。

高温不仅影响了蜜蜂春夏之交的繁殖,也让荆条在这个夏天延迟开花和停止吐蜜。
荆花蜂蜜
北京市房山区
北京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这里的蜂蜜以荆条产的荆花蜜为主,这种野生灌木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沟、谷底、河流两岸和荒地。位于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就是其主产区之一,荆花蜜是房山区一年中唯一的主产蜜源植物,荆花蜜也是中国大宗蜜源中每年最稳收的蜜品之 一。
郭涛的蜂场就位于房山区的佛子庄乡黑龙关村,但整个6月,郭涛一直忙着往自家蜂场拙朴坊的红砖上一遍遍地泼水,希望能降低地面温度。
7月当地的地面温度能达到47℃至48℃,而蜂巢内的哺育区应保持在恒温35℃,过高的温度不利于蜜蜂的繁殖。为了降温,工蜂只能不停往返采水。“蜜蜂一生的飞行时间只有21小时”,郭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而由于高温的原因,蜜蜂的寿命在缩短。
“高温、干旱叠加,对养蜂业影响也挺大的。”许吟隆说。蜜蜂“过劳死”的原因是在高温条件下,蜜蜂要用翅膀不断地扇风,蜜蜂的寿命可能从30天减少到15天。
受高温、干旱影响,6月10日到7月2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里,“满山的花,但是花上没有蜜”,郭涛说。作为家族里的第四代养蜂人,郭涛2013年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这门生意。他还记得在他小时候,雨季是6月,但自他接手后,雨季慢慢推迟到了7月下旬,今年更是一滴雨都没有下。郭涛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停止产蜜是荆条花的自我保护机制。
蜜源植物的共性是在花期内既有温度又有湿度。雨下得透,荆条才能从土壤里吸收更多的养分,也只有在高温的晴天作用下才会有很强的光合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按照正常的花期,郭涛将面临绝收—刨去养蜂的成本,单算蜜价,他将损失至少20万元。但今年他反而收获了每箱50斤的蜂蜜。
一切得益于7月31日的强降水。杜苏芮让门头沟区、房山区沦为洪水重灾区,但郭涛的拙朴坊养蜂场躲过一劫。长在山上的荆条借此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二次开花,有了花蜜,虽然花期只有10天不到,荆花的花期也只有正常的一半,但能有收成,他就觉得还不错了。
“每箱50斤的蜜算是中上的水平,这十年来基本都是亏,实际上能有平年(卖蜂蜜所得的利润足够维持各项成本开支)就不错了。”郭涛说。在此之前,他已经遭受了气候波动大带来的影响。2015年因为大旱近乎绝收、2021年产蜜季节雨水多,空气湿度大,蜂蜜质量受到影响,近年的一次平年是2022年。
搬到高海拔地区是蜂农比较主流的应对方式——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会降低0.6℃——但郭涛还不想搬到更高的海拔,“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条件。”作为应对措施,他计划在院里种树降低地表温度。
大米
黑龙江省五常市
7月到8月的大雨使得五常水稻大量减产,昼夜温差加大,影响了原本大量种植的水稻品种的质量。
8月2日,黑龙江五常市最大降水量达222.4毫米,为自1957年有气象观测数据以来的最大值。持续多日的降水导致五常市水稻近乎绝收。据当地24个核查小组统计,五常市250萬亩水稻的过水面积为100万亩左右,共约减产40%至50%。
许吟隆说,这是由于台风杜苏芮继续北上,停在了东三省,以大米闻名的五常市也位于降雨带内。如果还按照原来的天气准备排涝措施,“跟不上了,必须出现根本性的调整”。
五常市地处黑龙江省最南端、松嫩平原和黑龙江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整体东南高、西北低,拉林河与其支流牤牛河交汇于五常市区西北方向的延河朝鲜族乡附近。这条曾经给予五常水稻灌溉便利的河流今年却让五常面临绝收的困境。

但对五常大米来说,要操心的不止是“百年难遇”的降水。一方面,随着气候变暖,东北的气温也在升高。“水稻的必备种植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从水稻发芽起,每天环境的平均温度减去作物生长的下限温度值(生物学零度)的累加和(有效积温)达到2100度;另一个是要在扬花期有持续三天超过26℃的最高温,”许吟隆说。原本的积温带近几十年也在北扩,这导致五常所处的第一积温带的气温一直在升高,这对温带农作物来说本是好事,但温度升高也会导致其营养生长期普遍缩短。而且,身为寒稻,昼夜温差对稻花香2号的品质养成极为关键,这种大米品种让五常大米声名远扬。白天的高温有助于加剧光合作用,也有利于其吸收土壤中的矿物质;夜晚温度低,植株减少呼吸,降低了有机物和淀粉的消耗。而天气变暖正导致昼夜温差缩小,进而影响其品质。
另一方面,当家水稻品种之一稻花香2号在当地大面积种植已有19年,时间长了,品种质量会随着种植年份的增加而退化。“(适宜种植的)品种会随着气候条件也不断改变,现在的品种更新换代很快,原来可能一个品种还能顶10年,现在连10年都顶不了了。”许吟隆说。
野生菌
云南省昆明市
原本6月中下旬就该到来的雨季整整推迟了一个月,使得山林没能形成适宜野生菌生长的小环境,直到7月中下旬野生菌才陆续冒出 头。
低纬湿热的气候环境、独特的立体气候带和高原山地地形让云南孕育出了最适合野生菌生长,同时也拥有全中国最复杂气候带的土壤。野生菌对气候的变化极为敏感,不同品种有各自适宜生长的条件,想要长得好,需要满足气温、湿度、降水、植被等多方的因素。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品种依然无法人工种植,这种今夏最火的食材之一,其生长也跟气候的变化相关。
和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一样,云南省在这个夏天经历了漫长的酷暑。原本6月中下旬就该到来的雨季整整推迟了一个月,菌子生长的松林被晒得焦枯,干燥的土壤下也很少能看到菌子的身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副研究员郭相等人就观察到了野生菌的总体减产。今年7月初,郭相到大理和楚雄州的南华这两个云南野生菌主产区采集野生菌标本,但产量都非常少。“前期林地里边特别干燥,山上几乎没有什么草,都是一些枯枝落叶,希望今年后期能够有所收获。”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这导致今年野生菌价格高涨,迟迟没能回落。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则被外省菌“占领”了。
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总经理成爱丽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今年云南野生菌的上市时间相比往年推迟近20天,而外省的上市时间比云南提前了半个月,“前期能占到(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五六十左右,比往年增加了10%到15%。”
直到7月中下旬,雨季到来后,野生菌才慢慢露出了头。昆明的雨季本应是绵绵细雨,但今年的雨急且大。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赵永昌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这极易导致肥沃的土壤被冲刷,造成水土流失。他建立了一套依据光照、空气温度、土壤温度、土壤湿度预测野生菌生长态势的模型——通常需要依靠天气预报来评估生长条件。过去常有菌农找他预测山里不同种类野生菌的出菌情况,但这两年赵永昌发现,预测越来越不准了。
原因在于,作为衡量温度、湿度的重要依据,天气预报“频繁失灵”。即使降雨预测准确,但“昆明城里(今年)淹了好几回,有些地方却连雨都没下透”。有些地方指的就是山里。
“我现在已经不能用天气预报了,(而是)用天气后报趋势做预测。”后报指的是对当天天气情况的记录。“我把每5天、10天的这4个数据积累起来,然后预报未来哪几天菇会出,这(种)产量情况是什么样。”赵永昌改用天气后报后,预测的准确率提高到了80%。
许吟隆认为,下垫面(与大气下层直接接触的地球表面,包括地形、地质、土壤、河流和植被等)的改变、气溶胶的增加和气候的不稳定是导致云南降雨不规律和降雨量产生波动的主因。“工农业的生产活动让植被改变太大了,(前者)改变了水循环。”而人类活动的增多导致气溶胶增加,“水汽凝结核太多了,因为水汽会形成小气溶胶,它的水汽都粘在上面不断聚集,太多了以后它形成的雨滴就很难汇聚成雨点——绵绵细雨少了,一下就是大暴雨。”可见,降水过程跟原来相比更复杂,波动性更大。
成爱丽发现立秋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上云南野生菌的产量反而在增加,以往通常是到立秋后野生菌的产量就开始减少。这种变化同样是气温升高、昼夜温差小导致的。


攝影Graeme Kennedy
葡萄酒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
初春的霜冻、盛夏的高温、初秋的多雨,让种植酿酒用葡萄的农民从萌芽到采收,一刻也不得放松。
气候变暖带来的西北暖湿化使得降水增加、气温升高,让原本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西北地区开始拥有更多的农产品,宁夏葡萄酒就是最好的例子。
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变暖,生长期变长,全国的酿酒葡萄适宜种植区不断北扩。根据中国天气网2018年的分析,近100年来,酿酒葡萄的适宜种植区向北推进了100到160公里。
但坏消息是,气候变暖让葡萄的萌芽期提前了。宁夏农学院前院长李玉鼎2021年在关于贺兰山东麓葡萄冻害的研究中指出,发生于冬末春初的晚霜冻害已成为大部分北方地区仅次于干旱的重大气象灾害。近年来,宁夏因为晚霜导致酿酒葡萄减产的年份高达40%以上。
在宁夏、四川、河北怀来等多地与当地葡萄酒庄合作酿酒的戴鸿靖今年在宁夏青铜峡遇到了晚霜。“4月29日零下5度,葡萄嫩芽的部分会被冻,细胞会被破坏。”那一晚他合作的酒农损失了将近一半的葡萄苗。如果这种情况更加频繁,或许酒农就得将葡萄出土时间继续延后。
7月至8月是酿酒葡萄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也被业内称为果实着色期,在此期间,均温小于25℃,才能促进色素、芳香物质良好发育。
宁夏气象信息中心银川站1961年至201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显示,7月到8月的平均气温每10年增加0.28℃。而在葡萄生长发育的夏季,温度变高会让葡萄成熟得更早、糖分变多,在教科书上,这意味着葡萄酒口味的变化:酒精度变高,葡萄酒的口感更加浓郁强劲,香气和酸度降 低。
到了9月、10月的采收期,葡萄需要阳光的照射以加速果实内水分的蒸发,所以最怕降水。银川1961年至2015年间的气温观测数据显示,酿酒葡萄采收前一个月降水量及降水日数呈现增加趋势,极易造成果实开裂,稀释果实中的糖分,还使葡萄易遭霜霉病的侵蚀。
青铜峡在今年的采收季就遭遇了长时间的小雨。“宁夏到了9月底基本都降水,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不是下了一次,是下了好几次。”戴鸿靖说,“降雨后,温度下降,温度还没回升的时候,又下雨。”
发表于《大气科学》的研究文章《1961—2018年西北地区降水的变化特征》指出,1961年至2018年间,西北地区的降水量大约以13.5 mm/10a(a:年)的速率在增加。
气候升温、降水增加的尺度常以“10年”为单位,即使在戴鸿靖这样关心气候变化、会选择用更环保的材质装酒的人看来,这些宏观的气象变化与他在宁夏从事的葡萄酿酒“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当地酒庄也对此习以为常,”毕竟,“每过几年就会有这样的一年,或降水变多,或霜冻增加。”
科学研究呈现的全球变暖、极端天气,更多是长期、整体的过程,而农业生产更多是从农业种植户个体视角出发,后者对极端天气的感知往往有着延迟性和独特性。这也是气候学家们在参与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之后看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