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启蒙
张大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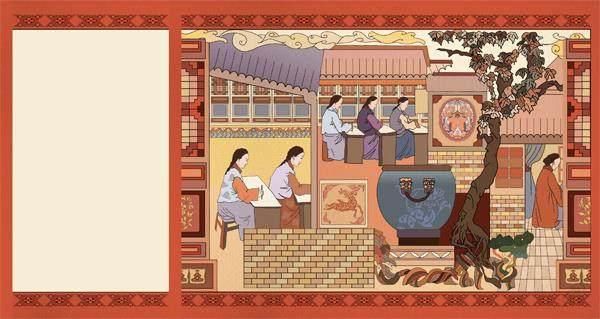
先父在日,说教总趁机会,不轻易出击,想是怕坏了我学习的胃口。尤其是关于某些难教难学的知识或手艺,若我不攀问入里,他仿若全无能为,往往只是应付几句。除非我问到了关隘上,他知道我有了主动求知向学的兴趣,才肯仔细指点。
那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无意间翻看了书橱里的几本风渍书,纸霉味腐,蛀迹斑斓,字体粗黑肥大,个个都认得,可是通句连行,既不会断读,又不能解意,仍把看了很久,觉得太奇怪了,只好请父亲给说一说。
那是一套名为《史记菁华录》的书。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捧在手里的,是给父亲翻烂了之后,重新用书面纸装帧过的小册子,父亲接过书去,卷在掌中,念了几句,说:“不懂也是应当。这是《项羽本纪》。”
这一天晚上他给我说了楚霸王自刎在乌江的故事,却始终没解释书上的文句为什么那么写。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看得懂,我看不懂?”(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每个字我都认得,却看不出意思?)
父亲回答的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个个的人,你都认识;站成一个队伍,你就不认识了。是罢?”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扔,说:“这个太难,我说个简单一点的。”
接着,他念了几句文言文,先从头到尾念了两遍,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在将近五十年后,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字句:
“公少颖悟,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遂学医。公病,公自医,公卒。”
公,对某人的尊称。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颖悟,聪明。学书,读经典。学剑,练武功。学医,学习医术,给人治病。卒,死了。
他说到“死了”,我就笑了,他立刻说:“懂了?”
那是一个笑话,描述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令人悲伤的人。没有谁知道那人在死前是不是还医死过别的病家,但是能把自己活成个被称为“公”的年纪,应该还是有些本领的。只不过这中间有太多未曾填补的细节。
父亲说:“文言文的难处,是你得自己把那些空隙填上。你背得愈多,那空隙就愈少。不信你背背这个‘公。”
“公少颖悟,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遂学医。公病,公自医,公卒。”
这是我会背的第一篇文言文,我把原文背给张容听,他也大笑起来。我说:“懂了?”他说:“太扯了!”
大部分的孩子在课堂上学文言文时觉得痛苦,是因为乍看起来,文言语感并不经常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日常生活里也不乏被人们大量使用的成语,这些话俯拾即是,人人可以信手拈来——仅此“俯拾即是”(出自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信手拈来”(出自宋代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诗:“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来俱天成。”)二语,都是文言,只不过谁也不需要在读过、背过司空图和苏轼的全集后才能使用这两个词语,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已经将文言文自然化约在几千年以来的语体之中了。
然而,一旦要通过文言叙事、抒情,就得理解那些空隙。我们单就“公少颖悟”这一篇来说,一共九句、二十五字,行文者当然不是要颂扬这个“公”,而是借由一般行状、墓志惯用的体例、语气和腔调来发展嘲讽。那些刻意被省略掉的生活百态、成长细节、学习历程、挫败经验……通通像掉进沙漏的底层一般,只能任由笑罢了的读者追想、补充,你愈是钻进那些不及展现于文本之中的人生,缝缀出也许和自己的经历相仿佛的想象经验,就愈能感受到那笑声之中可能还潜伏着怜悯,埋藏着同情。
从用字的细微处体会:初、乃、又、遂领句,让重复的学习有了行文上的变化,可是末三句显然是故意重复的“公”字,却点染出了一个一事无成者此生的荒谬喜感——即使它有个悲剧的结局。九句不超过四个字的叙事,的确到处是事理和实象上的“漏洞”,却有着精严巧妙的章法,读来声调铿锵利落,非常适合朗诵。
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此外,我们可别忘了:《史记·项羽本纪》一开篇介绍了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之后,就是这么说的:“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樂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章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