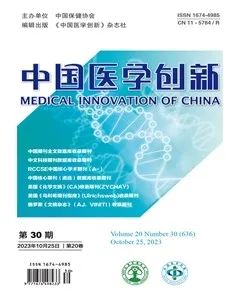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细胞免疫治疗现状*
王燚 孙涛
弥 漫 性 中 线 胶 质 瘤(diffuse midline glioma,DMG)是一种位于中线结构(如脑干和间脑)的高度侵袭性脑肿瘤,常见于儿童和年轻成人。高达80%的DMG 出现在脑桥中,它们也被称为弥漫 性 内 生 性 脑 桥 胶 质 瘤 (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DIPG)[1]。在病理学上,2021 年世界卫生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中 枢 神经系统肿瘤的分类中将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和 组 蛋 白3(histone 3,H3)野生型小儿高级别胶质瘤(pediatric high-grade gliomas,pHGG)与 组 蛋 白3 赖 氨 酸27 (histone 3-lysine 27,H3K27)突变型DMG 区分开。无论位置和分子改变如何,H3K27 突变型DMG 都被归类为WHO 4 级肿瘤且预后不佳[2]。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400 例新诊断DIPG,其中位年龄为6.8 岁,中位生存期为11 个月(7.5~16 个月)[3]。组织学分析通常显示高级别星形细胞瘤,但有趣的是,肿瘤级别与肿瘤进展速度或临床预后均无关。DIPG 通常具有快速的局部浸润,大约20%的DIPG 患者会发生神经轴转移[4]。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手术切除、放射治疗(放疗)和化学药物治疗(化疗),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一定的临时缓解,但对DIPG 的治疗效果仍然有限。迄今为止,数十年的研究未能产生具有生存获益的治疗手段。因此,寻求新的治疗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细胞免疫疗法作为一种新的治疗策略在肿瘤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5-6]。细胞免疫疗法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通过激活、增强或改造免疫细胞的功能,以攻击和消灭肿瘤细胞。在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治疗中,细胞免疫疗法被认为是一种有希望的治疗策略。尽管细胞免疫疗法在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治疗中显示出了潜力,但其应用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克服免疫逃逸机制、增强疗效和减轻副作用等。然而,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技术进步,细胞免疫疗法在治疗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方面的应用前景仍然令人鼓舞。
本综述将对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细胞免疫疗法现状进行概述,包括CAR-T 细胞疗法、NK 细胞疗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应用前景及其在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深入了解细胞免疫疗法的现状和挑战,对于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以提高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患者的生存率具有重要意义。
1 免疫治疗挑战
免疫疗法已成为实体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新型治疗方式,并已纳入许多成人和儿童癌症的护理标准[7]。然而,免疫治疗对DMG 患者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新一代测序技术的进步,体内外更稳健疾病模型拓宽了研究者对DMG 肿瘤的分子和遗传异质性的认识,并能够识别突变肿瘤细胞特异的抗原区域,这些区域最终可能成为治疗靶点。免疫疗法固有的一个显著风险是广泛的免疫激活和促炎状态的诱发会导致后遗症,这可能会导致脑干等中线结构内出现明显的水肿和液体外渗,从而加重肿瘤相关症状。激活有效的免疫反应,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炎症的潜在破坏性副作用是设计和实施DIPG/DMG 安全免疫疗法的核心考虑因素[8]。
DMG 治疗的另一个物理障碍是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它限制了全身给药治疗剂的分布。虽然全身递送的一些小分子和亲脂性分子可以通过BBB 进入大脑,但通常需要高剂量才能在目标组织中达到治疗水平,这可能导致较大毒性[9]。
除了解剖学方面的考虑,DIPG 已被证明具有显著的免疫衰老,即使与成人GBM 等其他“免疫冷”肿瘤相比也是如此。例如,与成人GBM 组织相比,DIPG 样本中胶质瘤相关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glioma-associated microglia,GAM/macrophages)的绝对数量较少[10]。反过来,DIPG-GAM 分泌的趋化因子/细胞因子明显减少,并且表达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显著降低,例如IL-6、IL-1α 和CCL4[11]。批量和单细胞测序分析还表明,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1,TGF-β1)(一 种已知的免疫抑制生长因子)在DIPG 中上调,表明TGF-β1可能会阻止针对DIPG 的T 淋巴细胞激活[11]。然而,与半球pHGG 相比,DIPG 被发现具有更大的炎症环境;尽管DIPG 相对“冷”的免疫特征在开发有效的免疫治疗方面存在独特的困难,但操纵这种肿瘤的免疫抑制微环境的能力可能代表一种替代和补充的治疗途径。
2 过继细胞转移
过继细胞转移(adoptive cell transfer,ACT)是一种将免疫细胞从患者身上分离出来,在体外进行修饰、扩增,再转移回患者体内的免疫疗法[12]。经过基因改造以表达嵌合抗原受体的T 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在各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显示出明显的临床响应率和缓解率,并已成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弥漫性大B 细胞淋巴瘤[13]。CAR-T 细胞被设计为特异性靶向肿瘤相关抗原,由细胞外Fc 结构域、跨膜结构域和细胞内结构域组成,可产生完全独立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激活的有效细胞毒性[14]。
迄今为止,已经在成人GBM 中使用CAR-T疗法进行了四项临床试验,初步结果显示在少数患者中没有剂量限制性毒性和抗肿瘤反应的证据。靶向抗原,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变体Ⅲ、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和白细胞介素13 受体亚基α2,也在pHGG 中表达[15]。鉴于抗原谱的重叠,这种靶向方法有可能扩展到DIPG。目前已有正在进行的BrainChild-01(HER2;NCT03500991)和BrainChild-02 (EGFR;NCT03638167)儿科临床试验。值得注意的是,CAR-T 细胞输注已经在其他疾病中进行了颅内和静脉(IV)内试验,影像学和病理学数据表明通过两种给药途径,CAR-T 细胞及其他炎性细胞可浸润进肿瘤组织[16-18]。
CAR-T 治疗DIPG 的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开发和评估抗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2(disialoganglioside 2,GD2)CAR-T 细胞治疗[19]。与周围的健康组织相比,GD2 在神经胶质瘤、神经母细胞瘤和骨肉瘤等许多实体瘤类型中的过度表达[20]。抗GD2 抗体dinutuximab 于2015 年获得FDA 批准用于治疗高危儿科神经母细胞瘤,推动了抗GD2 疗法的进一步转化和临床研究[21]。在携带H3K27M 突变的四个独立的源自患者的DIPG 培养物中鉴定出GD2 的高表达,为在这些高级别肿瘤中靶向GD2 提供了证据。
在迄今为止最大的DIPG CAR-T 临床系列中,Majzner 等[8]描述了使用GD2-CAR T 细胞治疗4 例患有H3K27M 突变DIPG 或DMG 的儿童或年轻成人患者,3 例在初始静脉输注GD2-CAR T 细胞后经历了临床和影像学改善。对唯一对GD2-CAR T 细胞疗法没有反应的患者进行尸检脑组织的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分析,显示GD2-CAR T 细胞仍可特异性浸润到肿瘤中。因此,这些有希望的Ⅰ期研究不仅预示着CAR-T 细胞在未来DIPG/DMG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了在治疗期间对这些患者进行仔细的临床规划和监测的必要性。
尽管临床获益,但CAR-T 疗法的副作用构成了临床挑战。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细胞因子释放脑病综合征和肿瘤炎症相关神经毒性是CAR-T 相关并发症,范围从轻度炎症变化和意识模糊到体液超负荷、呼吸衰竭、癫痫发作/迟钝和死亡[22]。作为CAR-T 治疗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发病的重要原因,这些毒性可能在解剖学受限的实体神经系统肿瘤中变得更加明显。上述CAR-T 相关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均源于IL-1 和IL-6 介导的炎症诱导,以及与肿瘤抗原接触后T 细胞活性的急剧上调。Tocilizumab 和Siltuximab 均为抗IL-6 单克隆抗体,已与皮质类固醇联合用于治疗CAR-T 相关并发症,可在必要时消除毒性。Anakinra 是一种IL-1 拮抗剂,可类似地用于调节肿瘤CAR-T 疗法的神经毒性炎症作用[8]。对回输CAR-T 细胞的成年GBM 患者进行的研究显示出可耐受的副作用,没有患者需要输注Tocilizumab[23]。然而,在DMG 中GD2-CAR T 的Ⅰ期研究中,所有4 例患者都需要在初始静脉输注后使用Tocilizumab 和Anakinra 或皮质类固醇对CAR-T 相关并发症进行积极管理。3 例患者中有2 例在随后的颅内输注后需要类似的治疗[8]。一般来说,与随后的颅内回输相比,患者在静脉回输GD2-CAR T 细胞后经历更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最近报道的3+3 试验(NCT04196413)中,所有患者都出现了CAR-T 相关并发症 症状,这些症状使用Anakinra 并根据需要额外使用皮质类固醇或脑脊液引流进行治疗。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共同证明了基于免疫的治疗方法对DMG的威力,并强调了未来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临床前和临床数据可用及对DIPG/DMG 基因组成的理解不断加深,使用CAR-T细胞靶向新抗原可能被证明是可行的、精确的免疫治疗选择。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儿童神经炎症相关副作用的耐受性,进一步描述新抗原,以及成熟的给药技术将是至关重要的。
3 CAR-自然杀伤(CAR-NK)细胞疗法
虽然CAR-T 疗法仍然是DMG 和其他肿瘤的主要ACT 方法,但最近的研究也在研究新型CAR-NK细胞疗法。一般来说,CAR-NK 方法比基于CAR-T细胞的疗法有几个优势。例如,当前的临床方案通常仅限于自体CAR-T 细胞以防止移植物抗宿主病,而患者可以安全地接受同种异体NK/CAR-NK 细胞疗法[24]。此外,CAR-NK 细胞可来自多种来源,包括自体或非HLA 匹配的外周血单核细胞、脐带血、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等,而大多数CAR-T 细胞是从患者白细胞分离术中产生的。最后,初步证据表明,与CAR-T 细胞相比,CAR-NK 疗法可能具有更高的抗肿瘤功效,同时具有更低的神经毒性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相关后遗症;与CAR-T 细胞相比,CAR-NK 细胞的先天免疫功能增强了这些细胞的CAR 介导的细胞毒性[24]。
NK 细胞已证明在体外对DIPG 细胞具有细胞毒性潜力,其通过NK 细胞上的活化性受体与DIPG细胞表面上调的应激反应配体结合介导免疫反应。对DIPG 中免疫细胞浸润和存活的研究表明,增加的NK 细胞浸润与更好的预后相关,支持CARNK 在这种疾病中的转化研究。将基于NK 的疗法与现有的癌症疗法相结合也可能会增强由此产生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赖氨酸特异性脱甲基酶1(lysinespecific demethylase-1,LSD1)抑制剂在体外增加了DIPG 细胞上NK 细胞激活配体的表达[25-26]。
NK 细胞疗法的开发和临床实施存在一些障碍。与CAR-T 细胞相比,CAR-NK 细胞在体内的持续时间更短,这可能需要更大和/或更频繁的回输才能达到相似的肿瘤浸润水平[24]。此外,与T 细胞相比,NK 细胞的病毒转导更具挑战性且不太成功,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寻求载体整合的替代方法。最后,NK 细胞的增殖速度远低于T 细胞,这使得生成用于临床应用的扩大的CAR-NK 细胞库变得更加困难。
4 结论和未来方向
细胞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策略,为DIPG 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CAR-T 细胞疗法和NK 细胞疗法等细胞治疗策略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了一些潜力。正在进行的针对DMG 和其他恶性小儿脑肿瘤的大量临床试验不仅将阐明细胞免疫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将阐明将指导未来精准医学工作设计的风险因素和生物标志物。然而,DIPG 治疗仍面临许多挑战。DIPG 的特殊位置和弥漫性生长使得细胞治疗的回输和渗透成为障碍,而免疫逃逸机制和治疗后复发仍然是限制治疗效果的主要因素。综上所述,尽管面临挑战,细胞免疫治疗为DIPG 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创新,有望改善细胞治疗在DIPG 中的效果,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最终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书写要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