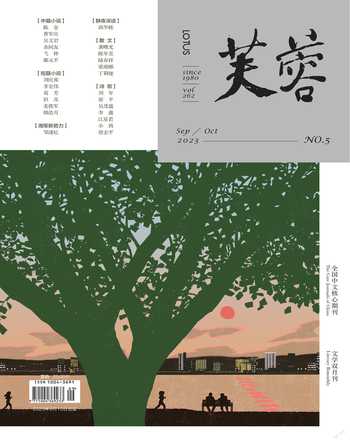缝衣记
陈年喜,1970年生,陕西省丹凤县人。有诗歌、散文、评论见于《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天涯》《散文》等刊。出版诗集《炸裂志》,散文集《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昨晚,把柜子里的衣服翻出来,裤子、衬衣、棉衣、袜子、手套,一一再检视一遍。过了重阳,就要过正式的冬天。这些年,家里别的没有增长,衣服倒真的积累如山了。开缝的,冒线的,破损的,扯荒的,缺扣的,飞针走线,无微不至,一直忙到凌晨两点。窗外寒气如织,被褥冷得冰窖一样,一觉睡得却无比踏实。我心安处,是补旧如新。
我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养成的这女人似的习惯,用爱人的话说,这是对女权的严重蔑视和抢夺。想起在矿山那些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缝补衣服。最气人的是工作服的裤裆,在操作爆破面的底眼时,一俯下身子它刺啦一声就开了,机器巨大的后坐力,不骑跨着按不住。机器的气腿提把儿的螺丝总是松动,我们就用铁丝捆扎着它,冒出的铁丝头像一只淘气的手,每次都那样准确无误一击得手。
那时裤裆的缝法有两种:一种是粗线,就是米面袋子的缝口线,这种白色的尼龙线结实无比,结果常常是缝过的地方再不会开了,衣服就在紧挨着的地方再开一道新口子,如此循环往复,最后,裤裆缝成了一张网。另一种方法是细铁丝缝补,就是用起爆引线的电线,这是一种半铜半钢的线,又软又韧。这种缝法没什么技术含量,是个人都能操作,在矿山广泛应用,缺点很多,比如伤内衣,比如洗衣服时很麻烦,但也有好处,起爆时电线若短一截,把它抽出来就派上了用场。被抽了线的裤子像一面舞动的旗,在下班的巷道中迎风招展。
不光是工作服容易破,所有的衣服都容易破,矿山地老天荒,来去困难,所有人都好像没有新衣服换,总是在缝补衣服,哪怕口袋里揣着一万元工资。在秦岭矿山那些年,见得最多的是小百货商贩,挑着针头线脑的担子满山走。
我记得2010年前,爆破工人还没有戴防护手套的习惯,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如果谁有一双手套,那就是奢侈品,上班下班都别在腰间,如果破了,就要绣花似的缝补,有人用一双旧的套补在新手套上面,耐用度大大增加。大部分抓杆的,都用空手抓杆,六棱的钻杆,在手心拧不出火花,会拧出一手水疱,下了班,用热水浸透,挑破放了水,下一班再接着拧。抓杆三年抓成了师傅,再来一个抓杆的。
爆破作业,单机时两人一班,双机时三人一班,也有三机和多机作业的,但那样的情況很少,只有大型隧道作业才有。掌握机器的是师傅,扶杆帮闲的是徒弟,叫抓杆儿的,这词儿非常准确形象。开孔时,扶杆人抓起钻杆的钻头往岩石上认,叫认孔,认孔是个眼头活,非常严格,认远了近了都不行,远了爆不下来,近了要多打孔,浪费材料。抓杆不仅费手,更费衣服,抓不稳时要用身子去扛。抓杆人的衣服特别费,下了班,不仅补裤子,也补上衣。
张小平跟着我抓了一年杆,也补了一年衣服。张小平的缝衣水平要比他的抓杆水平高得多,他抓杆也能抓准位置,就是稳不住钻头,如果是一字钻头,钻头会在岩石上走八字。我只能把风挡开到一挡,机头不停摆动位置,修正他的错误,可他还是抓不稳。幸运的是,他工作在可以随便戴工作手套的后爆破时代,每班消耗一双手套。工作面的岩石凹凸不平,但爆破是科学,孔位只认死理,没办法,张小平就用肩去扛,用身子去顶。这样做其实极其危险,六棱的钻杆有极强的附着力。他的衣服常常被卷在杆上,或撕下一片来。
张小平有一个针线袋子,就是人说的荷包,荷包有些年头了,五彩丝线绣着一对少年,像是在折荷花,花塘万顷,池水涟漪。我猜这个针线袋一定有一个故事,当然不大可能与张小平有关,它应该是一个老物件。张小平的衣服破得快,缝得也快,下了班,大家打牌喝酒,他就缝衣服,他有两套工作服,换着穿,也换着缝。他在袖口上缝一圈民国大帅服似的玩意,特别厚,也特别结实。那里是最容易磨损的地方。他也常给我缝衣服,有一回在屁股上绣了一幅太极图,两条鱼都是黑色的,像在游动,被我骂了一顿。不是嫌不好,是针线活太好了,但那是时间。
并不是人生下来就会针线活的,特别是男人。张小平说,这双手艺,是在河南矿山练出来的。有一天晚上,大家喝了酒,酒是老村长,那时候矿山流行喝老村长,便宜,劲足。他借着酒力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种相似的故事我听说过,但从没有见过这种活。他说的是掏矿。
山高的地方,天晴得稳了也没有风,月光就显得特别亮、特别清,像被纱布滤过了。我们出来撒尿,三个人站成一排,尿液呈三条射线,一直放射到山体下面,月亮的清辉打在上面,又把它穿透了,那些分解出来的一颗颗珠子,在岩石上摔得粉碎,更小的珠子溅到岩下的另一个工队的工棚上,发出沙沙声响。
我们躺在床上,酒劲上了头,大家都有些兴奋。张小平娓娓道来。
那一年,我二叔在灵宝金矿包了一个洞口。可能是开采时间太长了,洞里早已千疮百孔,连主巷道的地板也被挖得无处下脚,人进进出出像走夜路。我二叔包的活之一是掏矿,就是在垮塌的采场乱石堆下寻找矿石,这个活有点像乱河滩里捉鱼,有没有鱼,鱼大鱼小,要靠运气,那时候开空了的洞子都在掏矿,也有挣了大钱的。我二叔从老家找来了一帮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因为女人和孩子工价便宜。我们从山下集市上买了五百个编织袋,锅碗瓢盆,被褥粮油,在洞里选了个宽敞的住处,就开始掏。
大家掏了一个月,掏了三个采场都没有掏到一疙瘩矿,谁也不知道哪个采场有矿,哪个采场的矿有价值,就是盲掏。第四个采场掏到一半,终于见了矿石。二叔拿了一块出来,用锤子敲碎了,放到一只碗里,用酒瓶子反复碾压,当用水淘去石末,碗底清水里一溜金米显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金子,玉米色的浅黄,不发光,稳重,并不随水波动荡。我一下记住了它的颜色,后来到过很多矿洞,见到不少颗粒金属,分不清它们真伪时,我就用心里记住的颜色去对比,没有一次错的。
我们住的地方在一个水坑边,是一个采废了的下采坑,不知道有多深。用手电照射,上面是绿的,下面是黑洞洞的,像黑夜。不见阳光的水和见阳光的水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只有你见过了才有那种奇怪的感觉。在一条废巷道的尽头,石壁上有一个孔,是爆破失败后的残孔,水从那里一年四季不断往这边流,所以水坑总是满泱泱的。我们喝坑里的水,也用它洗衣服,洗澡。二叔说,水坑下面还有好矿,我们要在这里干三年,三年结束,我们都发财了,回家盖楼。
干活的采场离得也不远,有一百来米,饭菜熟了,我们在石堆下的缝隙里能闻到香味。我们叫它四号采场,其实也叫得没什么道理,只是它正好是我们掏到的第四个采场。另一方面,也方便定位,比如有人问,谁谁哪儿去了,回答的人说,在四号采场,就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免得担心。四号采场是一个大采场,面积有三四亩,人站在这一头,看那一头的人,特别小,特别不真实。后来好多年,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大的采场。一般来说,只有大采场才有好矿石,没有好矿石,也不会开采到那么大。
天板都垮下来了,就没有了天板,半间房子大的石头堆在采场上,堆成了一座乱石山,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石头支撑着这些大石头。用矿灯往上照,什么也看不清,挺吓人,不知道有多高。我二叔告诉大家,没事,天板不会再垮了。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怕,慢慢地,都不怕了,因为再也没见有石头掉下来,确实是垮到顶了。
大石头动不了,就把小石头掏掉,沿着一个方向,一个个石头掏掉了,就形成了一个洞,就是一条小隧道,小隧道曲里拐弯,只能一个人爬着进出,人像老鼠似的。我们在乱石堆下掏出了好多条小隧道。大石头也不稳当,有时候也会动,一动,挺吓人的,像地震似的,有时牵动一大片,就有石头把洞道堵住了,只得再掏出一条路来。也有正干活时,道上的石头动了,把人卡在前面,这时候要大家齐心协力把他掏出来。矿石的来源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天板上当时没采干净的矿石,采场天板塌下来,带了下来;一个是当时正干活,天板突然塌了,埋了一采场的矿石。第二种情况少,但碰到了能挣大钱。掏矿人赌的就是这个。
这个活特别伤衣服,上衣裤子都费,鞋子也费,一身迷彩服十天就破了,下班了就得缝衣服。我们一般两个月出洞一趟,买身衣服也难。有好些人不会缝,就交给菜花缝,菜花是给我们做饭的,她不上采场。菜花是云南人,她是唯一的外省人,好在云南挨着我们那儿,语言都听得懂。
有一天吃饭时,二叔说,菜花,你干脆就帮大伙缝衣服算了,大家一天下来都挺累的,工资给你再添二百。又对我们说,大家好好干,我把工作服多上一些。
除了掏矿,另一条线也在同时展开——采矿。那个地方离我们驻地有些远,也是二叔包的活,且是主战场,所以采矿工人也和我们在一块儿吃饭、住宿。他们破了的衣服也由菜花缝补。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哪儿人,人是讲地片的,哪怕吃住一块儿,也很难相融一片。他们喜欢面食和馒头,一笼馒头能吃三天不改样,一手拿着一只馒头,一手拿着一个洋葱,左一口,右一口,香得不得了。虽然这样简单,但菜花每天也是很忙的。
我们最害怕的是他们爆破的那一刻,地动山摇的一阵炮声,传导到我们掏矿的地方,乱石山就会一阵震颤,而且他们的爆破极没规律。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岩石不但能传导声音,也能传导震动。为了防止小洞道被震塌,我们每进一步都要做好扎实的支护,这样一来,进度更缓慢了。
他们机器用的也是下采坑的水,一台高压泵,一天到晚嗒嗒嗒地抽水,而水坑的水没见少下去一点,可想那水坑有多么深。绿汪汪的水坑,每次见了更加让我心惊胆战。
他们里面的一个人喜欢上了菜花,下了班,爱往菜花身边凑,帮着洗菜,或者捅煤火炉子。菜花有时搭理一下,有时不搭理。我们都看出来了,菜花不会看不出来。二叔看在眼里,裝着没看见一样,毕竟,他要掌握一种平衡,何况别人的事,往好往坏,也没到干涉的时候。有一回,我下班得早,看见菜花往煤灶里塞一张纸条子,纸条子瞬间成了纸灰,在炉头上飘起来,飞走了。
掏矿,也不是掏到的所有矿石都能要的,要看品位,金多少,银多少,铜多少,铅多少,综合起来计算价值,所以二叔不能总在矿上,他要三天两头拿矿石样品下山化验。我去化验过一次,很复杂的工序,化验工先把矿样称了重,用粉碎机打碎,除湿,添加各种化学药品,硫酸烧煮,显微镜下观察,分析,最后得出含量结果。山下小镇上到处是矿样化验室,竞争也很激烈,听说生意好的化验室,一年能收好几吨矿石,仅此一项收入就发财了。二叔有一次下山前,悄悄对我们几个说,晚上别睡太死,护着点菜花。
那一晚我睡得正香时,听到外面响了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是从菜花房间那边传过来的,接着好像有脚步声从帐篷外面跑了过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又归于平静。第二天早饭,大家看见一条刀印砍在厨房的门柱上。
菜花还像平时一样做饭、补衣,在房间一声不发地待着,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也许,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是人们产生了错觉。不过,她的蒸馒头手艺精进了不少,蒸出的馒头,在笼屉里像一笼白云。
时间到了八月,其实也不知道是几月。在矿洞里,没有天黑天亮,更没有人关心时间,早和晚一个样,这月和那月一个样。每次出洞下山去,要戴一天墨镜,不然眼睛受不了,阳光一刺,眼水哗哗地流。有一天二叔问,大家喜欢吃啥月饼?我们便都知道到八月了。
五百条袋子装得差不多了,矿袋围着我们的住处码了一圈,直垒到天花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踏实感。这些矿石准备到了十月拉到山下碾坊里提炼金子。二叔说,十月的水不冷不热、不快不慢,出金最好,到时把工资给你们结干净。我一直以为水就是水,一年四季没有啥区别,听二叔一说,才知道水有这么大的学问。二叔真是个厉害的人。我们的运气特别好,其实是我二叔运气特别好,我们掏到了一窝好矿,就是在大石堆的中间部位,我们打通了四条小隧道通向那里,四面出矿,效率很高。至于那堆矿石的来历,那是另外一个谜,谜底得问早先的主人,那又是另一个谜的另一个。有时想想,人活一生,就是个猜谜的过程,谁也猜不完、猜不准。
我特别不喜欢菜花,她让我常常想到老家山上的菜花蛇,又冰冷又神秘,对谁都好,对谁都防着。看不出来她多大,像二十多岁又像三十多岁。有一次晚上睡不着,我听见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说悄悄话,说菜花是逃婚出来的,欠了男方家好多钱,不敢回去。我猜这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女人的想象力比男人强,没有的事也能想象得有头有尾。不过菜花每天心事重重倒是真的,像谁欠了她十条命似的。
菜花做出的菜很不好吃,不是不熟就是太熟,总之难以下咽,不过,她的缝补手艺是真的好,不仅好看,而且结实,衣服从别的地方破,而不会从缝补过的地方出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厨艺的不足。她用的是一种特制的丝线,五彩缤纷,这种丝线不是山下集市上买的,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她用的针脚也很特别,复式的,往前走一针,再后退半针,像一行整齐的蚂蚁,它们头和脚衔接得天衣无缝。我仔细研究过,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针法。我姑姑开过裁缝店,给人手缝西服领口,但它们有区别。我说不清楚它的奇妙,但很快也学会了,学会了,我就自己缝,不知道为啥,我不想让她缝。
我们有洗澡的习惯,几天不洗就难受,掏矿的活特别脏人,得一天一洗。二叔给男人女人各弄了个洗澡房,就是彩条布围起来的那种,上面吊一个插电的热水袋子。女人们洗澡也不避人,她们开着灯,彩条布上映出她们好看难看的身形。水太热太冷时,她们会大声骂人,夸张地大叫。晚上睡不着,男人就讨论她们,分析她们老公的感受,并把那些老公的感受转移到自己身上來。
大家都说菜花从不洗澡,是个脏人,有人说肯定是洗澡的,不过是把洗澡水给大家煮了饭吃。菜花住一个单间,她是炊事员,有这个特权,谁也没有进过她的房间,连二叔也不能。里面都有什么,没有人知道。菜花除了做饭,剩下的时间都在自己房间里,她的房间和厨房紧挨着。大家把要补的衣服挂到厨房门口的钉子上,喊一声,菜花,把衣服补下哟,里面应一声,知道啦!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事不大也不小,在别的矿洞,掏矿这种活,这是常有的事,但在我们洞,这是第一次——有人被卡住了。说起来有些怪,前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老鼠在厨房打架,是打群架,它们掀翻了米袋子,碰倒了油壶,把菜刀打落到地上。第二天上班时间不大一阵子,老李就被卡在了矿道里。矿道很窄,只能爬着进出,有人向前爬着进出,有人退着进出,手里拖着或推着矿袋子,效果都是一样的。老李推着一袋矿石往外出,推得有些猛,矿袋子碰到了墙壁上,石壁上一块石头落了下来,没有了支撑的大块石头下来了,卡住了老李的腰,他进不得,退不得。
里面的人迂回到老李身后,拽住脚往里拖,老李只有一声声惨叫,外面的人抓住老李的胳膊往外拖,也只有惨叫声。老李精瘦,腰很细,腰细的好处是没有被卡死,坏处是禁不住拖拽。大家急出一头汗,怕上面的石头再往下压。大家都在想办法,都想不出办法。二叔喊:菜花,快出去给老子拿千斤顶!二叔的千斤顶在洞口的车上。
千斤顶拿回来了,石头咯咯吱吱被顶起来,老李被咯咯吱吱一寸一下拽出来,拽得一丝不挂,屁股蛋上划出一个大口子。口子汩汩冒血,往上面浇了半瓶酒,止不住,又浇了一泡热尿,终于止住了。
半月后, 我和老李从山下镇上医院回来,菜花不见了。大伙说,菜花被公安带走了,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二叔,要他去讲清楚。谁也不知道菜花出的是什么事,只听人说她那天出去拿千斤顶,被人看到了,认到了。大家第一次进到菜花的房间,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像随时准备走掉。有一个洗澡盆在床下边,床头有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一只荷包,塞满了针头线脑。
三天后,二叔回来了,带回了一个新炊事员。二叔说,没事,大家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我去金店问了,金价三百了,再干半月就碾矿。我们又天天照旧,只是再没有人帮缝补衣服。
碾完矿的那天,我们大喝了一场,大家都喝醉了。最后,我们去歌厅唱歌,大家唱得驴欢马叫,好听就好听得很,难听能难听死人。这个小镇很大,号称神州第一镇,热闹异常,歌厅和金店是主打,一条街就有好几家。躺在沙发上,二叔大着舌头告诉大家,菜花是个杀人犯,她被人卖到一个山里,有一天夜里,她用剪刀捅了男人一刀。二叔再喝一口酒,说,他妈的,欠菜花的半年工资可咋办?
张小平离开的时候是6月,我提着他的行李给他送行。他把被子和布满油渍的工作服都扔掉了,只带了一只行李箱、一个随身小包。6月是南疆真正意义上夏天的开始,此前的季节称为冬天也行,春天也行,两个季节的气温和景色没有什么区别。这时叶尔羌河刚刚涨水,雪山初化,大地像老事业焕发青春,又像新事业开张。当然,人间所有的气象都是在开业和歇业的轮转里变幻、接续,流水又岂能例外。我听见杨树林里有一只羊羔在喊妈妈,奶声奶气,吐字清晰。它的妈妈刚刚被冰冷的叶尔羌河水卷走了。
张小平的左手不能再提重物,我把行李交到他的右手,他的右手立即承受了双倍的重力,身子歪斜了一下。他的左手不太可能再抓杆了,也不能再缝衣服了,它少了两根关键的指头。我们把一条巷道送到了三千米远,没见到一颗矿石。张小平走后,剩下的人还要接着送,其实我知道,送也白送,不过是把老板的千万资产和我们的一点儿也不宝贵的时光送掉。
张小平是贵州人,那个地方离六盘水不远,四季清凉,到了夏天四面八方的人纷至沓来,但穷,干矿山的人,家乡都穷,不穷就不会干矿山了。对于另一些人,穷是个好东西,替人们完成了生活和命运的分配,维持了有些残酷的平衡。张小平有一个姐姐叫朵。若干年后,她给我打过几回电话,是关于张小平糟透了的生活。张小平糟透了的生活,是与他的残手匹配的生活。当时我记住了一些细节,比如他在牌桌上,凭借一只镀铬打火机的表面反光,判断出对手手里纸牌的花色,但那些不久就忘了。无论别人的生活,还是自己的生活,忘掉比记住好。
有一回朵在电话里说,如果有机会来看我弟弟,我给你杀鸡吃。电话里,有一只鸡正好叫了一声,引起了一片鸡的跟随,但都没有它高亢、明亮,声线饱满又光滑,边沿没有一点毛刺。我猜想它一定是站在一根篱笆的竹尖上,难得的阳光,为它和院子里慢于人间的生活镀上了一层淡淡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