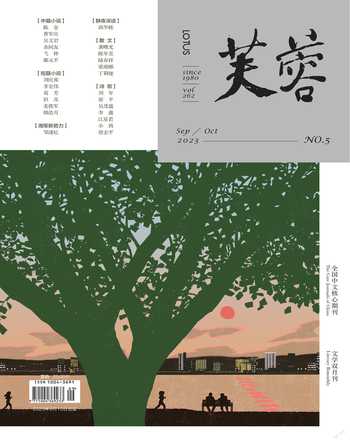弱者的伟业(创作谈)
邹谨忆
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开发商大概是个形容词吧,约等于无良。
也难怪,从来没有哪一个行业,拥有如此大的体量、如此庞杂的上下游产业链,又与所有人的日常,真正切肤相关。
就宏观经济而言,房地产当然至关重要,对每一个购房者来说,买房更是人生中最重大的决策,甚至可以不用加之一。
假设,你买的房子不幸烂尾,能否想象,你的人生将会变成怎样?
网上不乏这方面的跟踪采访,无他法可想的人们,凑合着住在水电不通的钢筋水泥森林里,他们将床靠墙铺设在毛坯房内,日日都得下楼拎好几桶水,搭个灶台,买来煤气罐,做最简单的饭食,夜里用手电筒照明,不敢多饮,最怕上厕所,来回爬十几层楼甚至更高才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家鄉亲朋打来电话,恭喜他们乔迁,他们一味苦笑着,不愿吐露实情,只是默默地,在冬天来临前,用透明胶糊住窗户漏风的每一处。
看到这些时,我早已潸然泪下,哪里还能继续共情,当他们生了病需要急救,当他们遭了贼无法自保,当他们的孩子因办不到房产证上学都成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当真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静坐常思己过,闲来莫论人非,怎奈命运,时常要将他们捉弄!
但,还有更狠的。
广州最著名的烂尾楼——澳洲山庄,据公开消息显示,开发商系加拿大归国华侨,20世纪90年代开盘爆火,领一时风气之先,孰料财务挪走一个多亿(当年的一个多亿是什么概念),包括购房款与集资款,项目一下子陷入停工状态。
多年后,楼栋长满藤蔓,芜杂荒凉,恰似科幻电影场景,很多购房者老去了甚至辞别了人世,开发商却还在那个烂尾楼里苦守着。没想到,当年的财务竟又返回,也不知他们怎么谈的条件,总之结果就是,财务从澳洲山庄划走一大块地,转手卖给别的开发商,开发为高端别墅楼盘,高价出售,目前已售罄入住。而澳洲山庄的几十名业主,忍耐着停水断电、发霉开裂等诸多不便,一直住在这烂尾楼里,同时,他们抱团自救,几十年如一日,不断上诉和申办房产证。
在被当成皮球踢了多年后,他们竟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事实,他们当中,有些人的房子,连土地产权都早已经划给隔壁的别墅项目,哪还可能给他们办证?明明他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地上而不是飘在半空中,这叫什么匪夷所思的事儿?
狂飙突进的历史进程中,因规则尚未完善造成的权力寻租空间,遗留下无数理不清的烂账,迄今对于澳洲山庄,网上能查到的资料都相当有限。我只能借助自己对房地产行业的粗浅认识,强行梳理来龙去脉,尝试赋予生活的逻辑以艺术的真实——这便是整篇小说最大的难点所在,却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佛曰,一粒沙中,有三千大千世界;一滴水里,有十万八千虫。宇宙本无大小之分、宏观微观之别,是以众生平等,五蕴皆空。而写作者的追求,也当在见微知著间,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谈到文学,我实则是一名迷途知返的逃犯。
记得2000年前后,一度痴迷到,所有同学挑灯夜读备战高考时,我却偷摸着编织情节与对白。那会子电脑并不常见,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写,写完甩给几位相熟的同学、朋友,她们趁自习课读完,便挥笔在文后留言,剖肝沥胆,细致妥帖,无异于今日豆瓣阅读大段大段的野生评论文章。
进入大学,我仍将写作视为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件,逃课看书是家常便饭,寒暑假更足不出户,从早到晚蹲在键盘前面,打字声彻夜不息。然而那个时代,市场经济已全面降临,很少有机会能找回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对文学的热忱,哪怕办校刊、办比赛都基本无人问津,而我又生性守旧,很晚才接触网络,因此,竟时常陷入无人对话的苦闷。
大学出版人生中第一本小说遇挫,研一为出第二本书触到人性的暗面,加之当时我父病重,不舍花钱入院,差点丢掉性命……种种外力叠加,促使我放下心心念念的写作,从事了房地产。在见证了行业的起落后,我甚至开过公司,干过工厂,做过其他杂七杂八很多与文学无关的事。
回想不读、不想、不表达的那些年,一度失魂落魄到,唯湘西赶尸当中的那具尸,可堪比拟。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我转过头,闭上眼,不再认识自己。
直到2019年末,人生晦暗,一事无成,回上海见到导师,导师问我可还写作,我一脸赧然,答说读了些心折的大作,方知自己从前是无知者无畏,我之于写作,终究是过分浅薄了。导师温厚,反倒安慰说,这个世上,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总不能光让大狗叫了,小狗不能发声,所以,写吧,哪怕最后证明并没有天赋,只管写下去。
是啊,除了写作,还能做些什么呢?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啊!我需要写作,从来大过写作需要我,如果没有写作,又将如何应对这千疮百孔的生活?
只管写下去。
我重新打开电脑,斟酌着敲下第一行字,那个逃亡多年的、真正的我,又回来了。这一次,是不打算再逃了,要昂起头啊,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暴击!
这样雄心勃勃地想着,下一秒,却发现那些字、词、句子,我认识它们,它们统统不认识我了。好比做过腿部手术的人,需要重新学习走路,而我,在停摆整整十五年后,竟需要重新学习写作!
重学写作是怎样的难呢,如果将所有汉字看成是一整座巨大的石山,我将手放在键盘上,不眠不休地开凿打磨,尽力去除掉多余的、占绝大部分的那些字,祈祷着心中的塑像慢慢吞吞从中浮现。
想想三年前写的那些东西,是多么做作,多么无病呻吟,多么拿不出手……毫不夸张地说,是到了需要向我的导师和几位同学、朋友诚恳道歉的程度,感谢他们没有轻慢地下定论,说这根本行不通,还是去找份正经工作吧——或许他们说过,而被我选择性遗忘了吧。至于我父母,是从不赞成我做这样的无用功的,他们朴素的脑子里,永远朴素地只想着并不朴素的钱。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一位同学突发奇想做了个公众号,几乎把我所有不成熟的作品都拿了去,表示喜欢得很,更关键的是,她还慷慨地、强行地付给我一大笔钱,前前后后算下来,省吃俭用的话,可能大半年不用上班都不至于饿死。
我能说什么呢,唯有加倍努力地写着,不断恳求导师介绍杂志编辑,忍耐着投过去的稿件一路石沉大海的苦闷,直至终于获得某位主编赏识,一连发表两篇,他更亲自下场指导,将重要奖项授予我,并与我谈论文学和人生的真意。
啊,真乃个人的高光时刻,值得永生铭记。
不错,最无助时,我也曾愤然抱怨,说不定成为中国版苏珊大妈,五六十岁才爆得大名,岂非更具戏剧性。咳,冷静下来又不免脸红,我个人的成与不成,有什么重要,不都是寄蜉蝣于天地间,渺沧海之一粟,仅此而已啊。
事实上,写作的回报早已在写作中显现,那些不为人知的时刻,完全进入迷狂状态,遗忘了时空,背离了庸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福至心灵……不写作的人,哪里领会得到它的妙处。
如今,我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做一份兼职,养活一个孩子并两只猫,将物欲压缩到活下去便好,最喜悦是兼职时摸鱼,得以静下心来,观摩许许多多文艺电影,不明就里的部分,再去B站查找解读,反复思索回味。
一流的影视和文学,根本就是相通,其他不同的艺术门类,也都相通,通在命运的波谲云诡,通在人性的复杂幽微,通在追问到最后,都只剩悲悯。
末了,必须郑重感谢《芙蓉》杂志,感谢湖南这片热土——我生长在这里,离开过这里,又回到了这里,你们非但没有将我厌弃,反而一如既往地接纳我,温暖我,鼓舞我,令我深深体认到:吾道不孤。
人生如此,更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