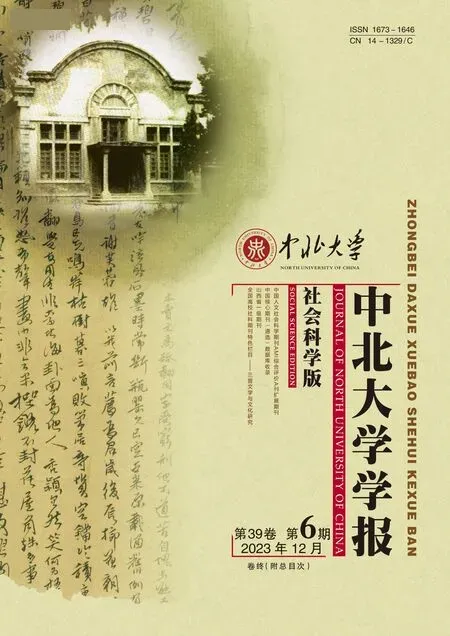严复所作双语工具书序言的文化意蕴
甘 霞
(1.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与外界进行思想沟通和文化交流,都不得不从了解对方的语言入手。清末民初,中国的双语工具书编纂事业飞速发展,内容涉及音韵、语法、文字、百科、地矿、天文、动植物、法律等多个领域,语种涵盖英华、德华、法华、俄华、日汉等。据粗略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将近80年时间里,我国出版的各类双语词典近70部[1]。
双语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发行和推介,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部受读者欢迎、广泛占有市场的词典,除去本身的吸引力外,前期的推广和宣传必不可少,而词典的序言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广告。为了扩大词典的影响力,出版机构或词典作者一般都会请当时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知名人士赐序。严复被称为“西学第一人”,是清末极具影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理所当然成为那个时代中英工具书的最佳评价者和推介者。严复为双语工具书作序,不仅以自己的社会威望直接或间接影响读者对相关工具书的判断与选择,大大拓展工具书的销路,而且他关于工具书的普遍价值的阐释和说明,也折射出工具书之外的深层文化意蕴。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开启民智必先引进西学,而通西学必先通西文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始知旧学不足恃”,必须“开启民智”才能救亡图存。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汇频繁,言辞瞬息千里,无一日不推移,无一日不增积。朝廷虽广立学堂,但教育的内容仍是旧有的经义辞赋,德行道义有余而“功利机巧兵商工虞之事”不足。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必须从文字语言入手。编纂双语工具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帮助国人学习外国文字,更是为了输入西学、启迪民智,从而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
双语工具书的用途是用一种语言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且保证释义对等。早期双语工具书多由西方在华传教士编纂,由于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再加上编译者的水平所限,当时市面上的双语工具书鱼龙混杂,存在“解释欠详确,讹误甚多”“世俗通用之语多未采入”“体例不善,不便检查”[2]等诸多不足。面对这些问题,1897年创办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多次组织人员重新编印,先后出版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罗存德原著,企英译书馆增订和校阅,1903年)、《袖珍英华字典》(吴治俭、胡诒毂编纂; 马国骥、徐铣增订,1903年)、《华英字典》(邝其照,1904年)、《英华大辞典》(颜惠云总编,1908年-1910年)等,在双语工具书出版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严复与商务印书馆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目前可见的资料中,严复共为7部工具书撰写过序言,其中,双语词典序言有5篇,集中创作于1901年-1908年期间,这5部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表1)。

表1 严复所作双语词典序言概览
双语工具书的编纂是民族重要的文化工程,是发生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的,承载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学习外语会“驱吾国之少年为异族之奴隶” “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3]154。对此,严复反驳道:“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 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3]156中学兴废的根源不在于是否引进西学,而在于其是否顺应了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西人之所以立国以致强盛,其盛大之源就在于西方的语言文字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通西学,必须先通西文,彼时西方的科学、美术等皆已精进,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不通其文,便无法互换智,更无从谈“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中国在教育过程中要把外语作为专门学科加以学习,培养明习西语、深通西学的新式人才而非不通西语不治西学的庸众。国人在学习本国母语的同时,最好再兼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尤必通英文。
《英华习语辞典》(原名《习语辞典集录》),由卓定谋、曾牖编,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1日发行初版,之后多次再版。《英华习语辞典》完成后,编者卓定谋的父亲卓芝南邀请好友严复为其子编的书作序,严复欣然应允。
《英华习语辞典》共有两篇序言,另一篇是林长民所作。由林长民的序文可知,自《尔雅》《方言》《说文解字》,以至《康熙字典》,中国在训话音韵方面的字典“不可谓不备”,但是属于小学的,则只有朱谋玮《骈雅》称得上辞书。类书之中以《北堂书抄》为最,诸如《古蒙求集》《注事类赋》《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等虽为辞书,却并不普及,辞书之不完备,“为吾国文化病矣”。在林长民看来,释字书易,释辞书难。字书之字简,辞书之辞繁。“言辞者,国民之习说也,子孙世代各状其所见,而其所用之字,则恒沿袭其宗祖之遗,而强以比之。”[4]卓定谋、曾牖为编写《英华习语辞典》,“搜得此类辞典凡十余种,更取英释日语译本,以相印证,凡万五千余言(条),其间有不能解者,则就正于英美学者,积一年而编译始成”[5],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双语辞典编纂的最高水平。
2 语言的发展遵循天演进化之律,传统字典应与韵府相结合,普及语法
清末民初,西方词典出版事业已经相当成熟。“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6]253当时中国的词典虽然也取得较大进步,但仍局限于说文解字,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拼音和语法。《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即《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分音节”的英汉双解字典,由企英译书馆在罗布存德《英华字典》的基础上增订。企英译书馆的主人谢洪赉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他曾译注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包含上万条词汇和短语,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出版的最完美和最精致的一部字典”,无论对中国人学英语还是外国人学汉语都有很大的帮助。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一共有5位名人推介:内封由盛宣怀题签,之后的卷端文字包括李提摩太写的《概述》、严复作的《序》、辜鸿铭写的《绪论》和薛思培(Silsby,John Alfred)写的《论英语之重要性》,这种推介规模在辞书出版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由此足见商务印书馆对该字典的重视。在这些卷首语中,除严复的序言为中文以外,其余都是英文。李提摩太在该字典的《概述》中说这是一部跟上时代步伐的英华字典,为当时中国急需,它会让大多数努力学习英文常识的人们受益匪浅。辜鸿铭在《绪论》中指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可以与已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邝其照先生的《华英字典》相媲美,甚至比后者还要全面[7]。1901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二),严复致信商务印书馆主人张元济,信中称:“商务《英华字典序》,近已草成,取书名《音韵字典》,‘音韵’二字似不可通,当改‘审音’二字,或有当也。”[8]545这里提到的《英华字典》,即是指《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于1902年出版以后,非常畅销,“为学旁行者所宝贵”。为了进一步扩大销量,同时方便读者,张元济决定“酌删繁重,主捷速简”,又出面请吴治俭、胡诒毂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排为袖珍本,“以便适应者之所挟持”[9]144。于是,《商务书馆袖珍华英字典》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问世。严复为《袖珍英华字典》写的序大约是在1903年12月19日至1904年1月16日之间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字与音韵一直是分开的,而西方文字“虽以埃及之鱼鸟画形,状若金石款识,而究其实,亦字母也。惟用字母切音,是以厥名易成。而所谓辞典者,于吾字典、韵府二者之制得以合”[6]254。严复曾说,字典之用在于供“考古者于一字之立,讨本寻条,而常人日用诵读之时,则取了大义,期捷速、简当而已”[10]。《康熙字典》和阮元的《经籍纂诂》都是集中国数千年字书天演之大成,这些辞书按“平上去入”四声部将一韵分为一卷,并没有注音,只是解释字的意思。由于中国的名物习语往往不可以独字之名穷尽其意,于是有了清代官修大型词藻典故辞典《佩文韵府》。该字典以部画相次,韵府则以韵为分,读者可以根据这些字典自学。大约在1910年-1911年间,严复写成《英文汉解》,对中西文字的演变与区别作了详细论述。严复讲道:“天下文字皆切音,独中国以四象为文字。四象者,象形、象意、象事、象声也。四象为经,而以假借、转注为纬,是谓六书。”“泰西诸国文与竺乾梵字为一源,……英之语言为条顿之一种,而他种文字杂行其中。”[11]286严复考据了中国字的创造者仓颉、沮诵、佉卢,指出仓颉所造字为下行,而沮诵、佉卢所造为旁行书,中国汉字于是有了左右之分。严复把英语中的形容词(adjective)称为“区别字”,把副词(adverb)称为“疏状字”,试图借用英文的语言学知识梳理中国语言。严复倡导国人学习西方,把中国传统的字典与韵府结合起来,形成现代意义的辞典。
1903年10月,熊季廉(熊元锷)邀请严复用文言讲英文“文谱”(即语法),以方便初学外语者。严复于是杂采英人马孙、摩栗思之思,释以汉文,积数月之功,终于编成《英文汉诂》(EnglishGrammarExplainedinChinese),并交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5月出版。在《英文汉诂》中,严复以英汉双语经典文献为例,试图借用英语语法规范汉语秩序,形成一种跨文化的语法重构。《英文汉诂》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英文语法的书,也是中国第一本采用左起横排格式,首次使用西方标点符号的著作。严复坚信文字有穷,语言无尽,语言文字必有语法,语法是天下言语所共同遵守的原则公例。他提到,“进化之民,其言有经”[11]286,语言文字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优者自存,劣者自败。所谓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12]151。
言为心声,发于自然,其律令也应出于自然。一切语言文字都有共同遵循的规律,而不同民族的语言又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则,将此二者汇通归纳便是语法。“语言文字者,所以达人意thought者也。其所达者谓之辞,Speechor Language。究辞之理,著其律令,使文从字顺者,谓之文谱Grammar。”[13]学习英语并不能只是寄希望于语法,更要博学多通,多加训练,否则“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12]152。这就是说,语法源于语言,而非语言来自语法。所谓语法,只不过是把大家约定俗成的话语习惯记录下来而遵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依据制定的语法去说话。1907年,严复应邀在南京主持出洋考试时,《代提学使陈拟出洋考试布告》中罗列的考试内容就包括英文法、修辞学等,参考书目分别为NestFieldGarmmar;AleranderBainandothers;Bain’sEnglishComposition等[14]247-248。严复认为,白话文的普及不是因为有更多诸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样的人,而是因为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会“自鸣自止”。1919年,严复给熊季廉(熊纯如)的信便表达了他的主张,严复提到:“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须知此事,全属天演。”[15]415
3 植人才铸国民应以汉语为本,兼通数旁国语言文字
工具书的发达程度体现了一国文明的进化程度和文化的深度。一部出色的双语工具书必基于本国当下的文化需求作出反应,并旨在提高国民的普遍文化水平。清末民初,世界上大多数报纸都是用英文印成的,各国对外贸易的通用语言也是英语,当时英汉词典的出版规模远大于其它语种的词典。由于西学的不断输入,旧有英文词典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需要与时俱进,益展闳规,广延名硕,在原有英汉词典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最新版本。
《英华大辞典》(上、下)由译学进士颜惠庆等编著,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之前,颜惠庆曾应张元济之邀,与王佐廷一起出版过修订版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该字典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仲冬)已出版第7版。用颜惠庆自己的话说,当时学界钦崇,几与人置一函。在1907年写成的《英华大辞典》自序中,颜惠庆提到:“英华之辑有字典也,假训诂之例,通中外之邮,俾泰西今昔政教艺术诸书,凡有裨于我中土者,译行则藉作梯航,肄习则奉为圭臬。疏明音义,考证异同……既足为文明输入之助,而于当轴维新之化,或亦不无小补矣乎。补苴雠校,俾溃于成。”[16]该辞典全帙共计三千余页,除诠释文字外,多及中外新旧名词,内容比《音韵字典》更繁富,图画精详,迻译审慎,译文力求更准确,同时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英华大辞典》的另一篇序文写于1908年正月,同为严复所作,出版时采用了其手书原件,墨文朱印,十分美观。在序中,严复写道:“吾国之民,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又以英文为独多。模略人数,今之习西文者,当数十百倍于前时,而英文者又数十百倍于余国。”[6]254严复认为颜惠庆所编新词典相较前者,“犹海视河”,对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严复对西方国家多语教育十分赞赏,他认为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有时候仅仅通晓此国的文字语言是不够的,甚至需要通晓数国言语文字才能深入其文化义理。他以欧洲人的启蒙教育为例,提到他们一开始学习就先习罗马文,再习希腊文,而不是孤习本国文字。他多次援引英国著名学者约翰•穆勒的话说:“欲通本国之文辞而达其奥窔,非兼通数异国之文字言语不能办也。”[17]164
清末双语工具书的编纂者或作序者大多具有留学背景,博学多闻且通晓中西,他们倡导学习外语,是以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为前提的。他们认为任何国家要想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往中占据优势,都必须先精通其他国家的语言,而后方能精其文化义理。“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3]155一国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只有国家先强大起来,该国的文字语言才会相应地受到重视,而不是反过来一个国家的语言受到重视了,这个国家才随之强大。
一国的语言文字承载了一国的文化精髓,仅仅依靠字典、语法,还远远不能达其要旨,必须全面了解文字传达和承载的内涵与旨趣。“盖一种之克存,一国之久立,则其中必有聪明睿智之民,思虑识知所大异于凡民者,有所欲云而理不概见,则托譬成章,比文见义,闻者或默以识之,或笔之于书,物之精理以明,心之深情以达。”[5]学习者对其它语言文化的学习更有利于加深其对本国文化的理解,所谓:“道生于对待,得所比较,错综参互,而后原则公例见焉。”[17]历史上英、荷、法、德的学术大师,其著书大抵不用本国文字,而用拉体诺语。要真正学习西方文明,掌握其语言是最佳捷径,“假道于迻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3]156。那些通过日本转译到中国的“二手西学”,已经远远不是其本来的面貌了。严复借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论述文字语言的价值,指出:“民无论古今也,但使其国有独擅之学术,有可喜之文辞,而他种之民,有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文字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3]153孔子的《春秋》、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都是旷世佳作,然而西方人却难以译而求之,得其真意。同样的,中国人在译介西文时,也常常难得其全部精华,或名词标目未有其观念; 或简号公式未有其演习,因此,纵使有至敏强识之夫,也难以融会贯通,了然心目。况且在中外文转译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名不一译,字不一音”的情形,因此对西学的掌握之粗可想而知,所以说:“求西学而不由其文字语言,则终费时而无效。”[12]152
言语文字乃古人殚毕生精力所得,大义微言,每个字词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源流,有其所以承载、传承之典故。字典有大有小,意在满足不同群体在不同环境中的需要。“故字典大者其籍专车横列数十百卷; 而小者如拳如拇,怀挟褚袖之中,以便舟车翻检,夫亦各适其用而已。”[10]今人之所以读古书难,是因为不精通文字含义。后人未学古人之学,若仅读古人之书,有时很难对古人之心思有切肤精怃之体会。再加上历时久远,风俗殊沿,简牍沿讹,声音代变,通假难明,更是所知者甚少。中国人只有建立在对汉语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学习外语才能事半功倍。
4 结 语
清末民初双语工具书的编纂为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双语工具书的广泛普及,工具书中的“序言”所传达的文化思想也日益深入人心。在当时,谁能读懂外文,谁就能了解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并介绍给他的同胞,为民族和国家“植人才铸国民”。严复用一种现代性、世界性的眼光分析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应秉持的态度,从思想、文化、制度层面阐述救国建国理念。严复所作工具书序言表面上是广告,实则是通过倡导外语学习,论述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语言的重要,进而号召国民通过兼通旁国语言文字去领悟西方思想文化真谛,开阔视野,互换智识。这种超前的文化策略和对民族文化改造问题的深沉思考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国民的觉醒和民族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