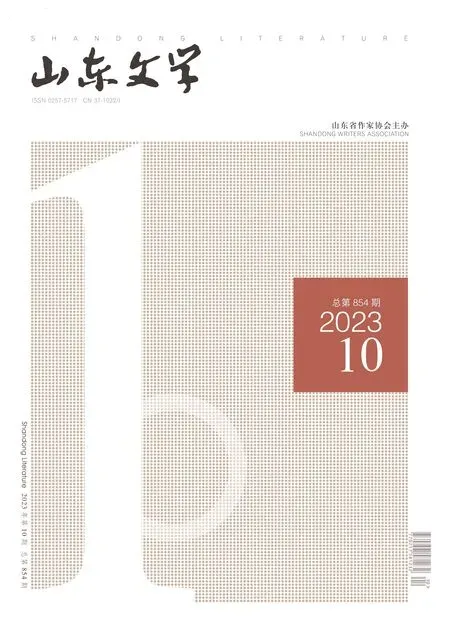旧物微凉
璎 宁
一
三十岁,在我进城,搬到楼房里之前,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衣柜。母亲的瓦房里,除了八仙桌,缸与瓮,也从来没有过衣柜,只一个碗橱,还是舅舅搬家替换下来送给她的。也就是说衣柜,从来没有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直到母亲去世。
衣柜,也只是存在我的期盼与渴望里。其具体的存在是伟收媳妇喜房靠东墙的角落。一米八的个头,一米六宽,四开门,核桃木色,高大稳健,似乎喜房里衣柜一落地就开始发光。菱形的门把手上紫红色的“宝石”耀眼夺目。衣柜左边整块的大玻璃,洁净明亮,像一片秋后的湖水。那是我见到的最大的镜子,竟然能把整个人装进去。伟收媳妇的娘家在我们村向北二十里地外的一个渔村。她父母常年漂在海上以打鱼为生,家境比我们村的人家都好,买了衣柜作为陪嫁。那个时候,乡间都叫衣柜为“大立柜”。新媳妇结婚都坐牛车,而“大立柜”也是坐了牛车到的我们村。大立柜上的玻璃反射着太阳的光。把黄河的流水、天上的鸟雀、娶亲队伍的锣鼓声欢笑声都装了进去,算“入世”。以后它会以宽阔的空间,坚实的臂膀,陪伴女主人在另一个村庄的生活。
母亲赶集买了红头绳,自己揪一个小辫,到伟收媳妇的大立柜前照照,父亲赶脚回来买的铁盒也拿到玻璃前照照,似乎照一下,铁盒就会变出很多美妙的东西。比如糖,比如红蓝铅笔,比如女孩子用的卫生带。
十四岁来潮以后,忽然的一次照镜子,发现了自己隆起的胸部,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甚至潮红汹涌之时也偷偷跑到镜子前看看经血有没有染了裤子。伟收媳妇生孩子坐月子后,大门紧闭,把我挡在了镜子之外。我们没有大立柜。裤头、罩胸的小褂子都装进一个塑料袋,塞到被窝的脚头,或者压在麦草的枕头下,某个隐蔽部位。似乎这些是应该隐藏不能见天日的。外穿的褂子、裤子都悬挂在墙上的木撅子上。借着昏黄的煤油灯,有时感觉有人爬在墙上一动不动。
我上初中那年,父亲赶脚带回来一块右上面缺角的玻璃。很显然那是一块衣柜的玻璃。上面还有别人生活的气味和痕迹。右下角的一点红色似乎是指甲油,左上角露出的黑色划痕好像是打架留下的佐证。我很欣慰地判定这是一块来自城市的玻璃。它一定见识了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不同。譬如城市的街道是硬的,有汽车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要么坐汽车,要么骑自行车,反正不像我们村的人坐牛车上坡下地。那牛车慢得就像一个镜头。但是没有人着急,也不去打牛让它快点走。
父亲找来了零碎的木板,在我居住的房间开始给我打造大立柜。地上挖出四十公分的凹槽,把两块木板插进去固定,作为柜壁,把那块玻璃镶嵌进一个旧木门上,作为柜门,木板上方不用封顶,横一块木棍作为挂衣杆,一个大立柜就算完成了。有了一个密闭的属于我的空间,有了一块能照出整个人的镜子,有了一个大立柜,让人欣喜得难以入睡。我把隐藏很多年的内裤、罩胸的小褂子拿出来挂在木棍上。原先它们隐藏在被窝的角落时,从来没感觉它们的丑陋,而现在它们带着我身体的形状悬挂着,裤头是由大人不穿的秋裤改的,裤腿肥大,直接像一条裤子被剪去了裤腿。都不敢想象,它是如何被我的粗布裤子无情挤压,紧贴着我的皮肤的。那罩胸的小褂子也像把一个大褂子剪去了下部,没有乳房的形状,更谈不上性感。所幸我有了一面镜子、一块玻璃。我时常与镜子里的我对视交谈,妄想找到一条逃出农村的道路。有时,我也钻进大立柜里一待就是一天。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黑暗、逼仄、静寂。我陷入各种冥想:考上大学、嫁一个白马王子、拥有一个胸罩、一个像裤头的裤头……有时,闭上眼睛倾听老鼠走动的细微响声,听老鼠咯吱咯吱磨牙,听壁虎从一个墙洞里钻出来,在暗影里爬行一会,又消失在一个看不见的墙洞里。有一次我在大立柜里睡着了,我感觉自己拥有了一个真正的衣柜,像伟收媳妇那样的大立柜,衣柜里挂着我的裙子和他的西装领带,我们站在衣柜前拥抱接吻,亲密无间。当我们沉睡或者外出时,衣柜还照出了细微的部分:一块蓝色碎花的布头、一只闯入屋内蹁跹的蝴蝶、一只在墙角结网的蜘蛛……
而事实上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衣柜。它只在我的记忆深处闪烁着光芒。高考落榜那年,我把自己关在西屋的衣柜里自我摧残,两天两夜不吃不喝,当压制不住的悲伤打碎了那块玻璃,摧毁了衣柜,我拿起一块玻璃的碎片割伤了自己的左手腕。那块玻璃,从彼岸到此岸,从城市到乡村,依然锋利无情,我与它接触时,听到了皮肉的撕裂声,“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城市的新家做衣柜,拒绝做带玻璃的,自己也越来越不喜欢照镜子。似乎照镜子只属于懵懂而反叛的青春岁月。至于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视对话的勇气,早已丧失殆尽。衣柜完全成了储物的一个空间。它像床铺一样普通不再有吸引力。我甚至讨厌它被格式化的空间,讨厌由木料碎片压制而成的柜壁,还有虚伪的贴纸。柜门上不再有带“宝石”的把手,而是推拉门。那塑料门闪电般的滑动,让我特别怀念“大立柜”的持重和淳朴。
二
在某个人造古村落,名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上见到它们时,我颇为惊讶。街道上形状不一的青石,泛着陈旧的气息,街道四周飞檐灰砖的高大房屋,将整个村落向远古推去。
那些缸,体型庞大,缸壁呈坡形,底部到缸口逐渐张开,颜色古铜,外壁粗糙,口沿灰白,像训练有素的仪仗队,站立在街道的中心,成为抢眼的风景。我更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跑过去抚摸,凝视,轻轻敲击缸壁,它们发出了浑厚的陶的回音。很显然,这些大缸没有现代制作的印痕。它们来自岁月深处,某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村落里它们是财富的象征。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几口大缸“压阵”,就说明了这家的贫穷。女子找婆家,先差遣媒人到男方家里看有几口大缸,大缸里是否粮食满缸,才决定是否将女儿嫁到男方。如果男方家里没有缸,这门亲事多半告吹。难以置信,一个陶器,一口缸,竟然能赢得一个女子的芳心。这缸的重要性,也相当于现在的汽车与楼房了。
一个家庭里一般都有好几口大缸,有的用来存水、存粮。用缸存粮食,不但老鼠无法偷吃,粮食还不长毛腐坏。在我的故乡鲁北平原,大缸用来腌制咸菜时方见其肚量,其胸怀宽大。一地排车的白菜或者萝卜,一个一个跳进去不见了影,再放入晶体的白色粗盐粒,一整个冬天的菜就都在缸里了。晚上用大铁锅煮上一锅豆子黏粥,再捞上一片咸滋滋的白菜帮子,也算是一顿丰盛的晚宴。
有的人家则放一口大缸在门口,缸里不放粮食不腌制咸菜,只清凌凌的一缸水,俗称为“门海”,取意门前有海,海水可以扑灭火灾。故宫的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等随处可见青铜、铁质大缸,工艺精美,光彩夺目。相对于故宫这些地位显赫的大缸,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则显得朴实,憨厚,可爱。
那些口径狭小、肚子鼓出、底部较小的瓮,则被众多不规则的青石举在了半空。口中吐出的一叶莲花“可远观不可亵玩”。它们外部灰白,粗砺,四处的磕痕明显,口径的一块三角形陶片不知所踪。往事却被它的腹部储存,时间久远,一直在发酵,并在我经过它们时散发出旧时光的醇厚味道。那是一种酱香的味道,那是一种猪油的味道,或者炸货的味道。甚至,那是一种岁月的静寂之味,缓慢澄澈。我尝试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冬天,用一场雪的白,打开一个村落的内部。那个冬天离我很远又似乎刚刚过去。一向贩卖粉皮粉条的父亲,忽然拉来了一地排车的缸与瓮,而且还是在大雪飘飘中。下堤坝时为了不让缸与瓮成为一车碎片。父亲往后倾斜身子,死命拉着缰绳,让毛驴放慢脚步。毛驴的嚎叫响鼻,车载吱吱扭扭的响声与父亲吆喝毛驴的声音撞开了故乡的黎明,激荡起黄河的浪花。与其说他们是走下堤坝的,不如说是滑下去的。村人围着雪人似的父亲,围着体型巨大的缸与瓮,惊奇父亲是怎么把二十多个缸与瓮,在博山装车,刹车,经过一路颠簸,安全到达村落的。父亲用高高扬起的皮鞭,用几丝微笑,隐去了那令人提心吊胆的过程,开始按用途帮人挑选缸或者瓮。当当当、当当当,人们围着这些陶器转圈。用他们的手指敲击缸壁或者瓮沿。有人把自己的身子探到缸底,只留两条腿当啷在外边,有人直接跳了进去,试试缸的牢固度。响声清脆浑厚,说明缸烧制的火候恰到好处。如果一口瓮发出薄弱的声音,这瓮八成无法使用太久。父亲一个一个敲着它们,似乎已经懂了陶器,懂了泥土加入火焰被烧制时的疼痛与蜕变。
那些缸体型庞大,一个人难以搬动。把缸放倒滚动回家,显示了村里人劳动的智慧。缸上的釉早已成型,即使巷子的地上坑洼不平,即使有石头瓦块也奈何不了一口大缸,从它们身上滚过去,滚进一个木板子门,滚进一个家庭的琐碎日子。村里没通自来水的年月,水缸都在正屋的一角,靠墙而放。缸里的水长年不断,是生命之源的承载者。通了自来水以后,很多人家依然在自来水龙头下放置一口大缸,缸里依然储满了清水。这是对陶器的一种情缘与不舍。岁月悠长,日子里的甜蜜与苦痛,欢乐与悲伤,缸——都替他们保存着。而瓮只能充当配角,但是也是重头戏。煮熟的豆子晾晒后,一把一把放到瓮里,封口,搬到炕头上任其发酵。隔着厚厚的纱布,我们能闻见豆子的香气。甚至能感觉到缸里匀称的气泡。很想一把撕了纱布,挖一勺子豆酱抹在地瓜饼子上狼吞虎咽。无奈,豆酱酿好之后,母亲在吃饭时总是挖一勺,分来给大家吃,地瓜饼子上只有蜻蜓点水似的那么一点。因为一瓮的酱需要吃一个冬天呢,哪能像喝糊糊一样,想吃多少吃多少。有一年麦收季节,我们吃完了最后的一勺酱,母亲把瓮刷得铮亮,北屋东面的窗户下,靠墙根而放,不知什么时候一条蛇潜入了瓮中,把瓮当成了它的避暑胜地。我们趴在瓮口偷看,它把自己带斑点的长身体盘在瓮壁上,悠然自得地朝着我们吐着红色的蛇信。父亲怕它伤了我们,敲击瓮壁驱赶它未果,把瓮抬到了胡同,用木棍将蛇缠绕,放到了南边的树林里。父亲一边用棍子击打沙土驱赶它,一边念着我们听不懂的咒语。这口瓮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从此闲置,像是一条蛇,在瓮内布设了阴森恐怖的东西。
三
赤手空拳拧开封在巷口的铁丝网,手指流血了也要拧开;从两米高的土堆上翻越过去,即使一再摔下来也要翻越过去,回家(老宅)。
我是今年春天趁着祭祖的空当,把这个梦变为现实的,竟然像一个远游而归的孩子心情激越。村民早已弃村而去不再返回,只有我这个早年脱离故乡的人偷潜回来,想寻觅什么:一个脚印、一声咳嗽或者一件器物。昨天那场大雨对于老宅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正屋屋顶已经塌陷出一个大窟窿,上面露着不规则形状的一片晴空。芦苇狂野地钻进了正屋成为新的主人,它们披着一身绿衣,举着刀子似的叶片,把自己的枝干从屋顶塌陷处伸出去,想要上天似的。
那张八仙桌在正屋对着门口靠东的方位,幸免于难。一米二九见方,九十九公分高,桌面下拉枨处镶嵌雕花流云的图案,几经岁月,云花依然清晰,“骨架”尚且健壮,四条桌腿下还垫着枣木的小方块。很显然它已经成为旧物,属于过去我曾经参与过的慢生活。
桌面上尘埃很厚,一把白色带粉花图案的茶壶,几个豁口的茶碗,一个哈德门烟盒,几个一次性简易打火机,一个圆桶状、三十公分、口径很小的盐罐,保持着我们离开时的样子。那个母亲使用过的打火机,微弱的光亮穿透了岁月,将八仙桌从厚厚的尘埃中剥离出来,熠熠生辉。恍惚间我看见母亲坐在桌边,她正喝着一壶从麻湾集市上买来的廉价茉莉花茶,一根烟在她嘴唇上发出时明时暗的烟火。她的目光慈祥、深邃,像是在思考关乎生活的大事,又像是一直朝前看。我在她的目光里近了又远了,像一个虚幻的影子。
我们站立良久,开始搜寻可以带走的东西。抽屉已经松懈,一些细小的物品呈现过去日子的模样。我从缠绕成一团的细铁丝中扒拉出一枚蓝色小铁架,以前是我夹作业本用的,又从抽屉的边角捏出了几枚生锈的铁钉。其中一枚铁钉我很熟悉,它在柴火堆里被我发现,并扎伤了我的脚心,它们已然生锈,但是锋利依旧。小妹看着我,拿起一件物品又放下,最后什么都没拿,似乎这个养育她的老宅与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拖动了一下八仙桌,有把它带走的意图,又想揭下几张墙画。这次偷潜,虽然以我拿走一枚铁夹和几枚铁钉而结束,总是感觉有些东西已经长在了这方泥土上,我挪移不动,譬如黄河。有些东西我早已装满心胸,譬如乡间的朴实、温暖,过去日子的慢与苦。
那个春天,一根水曲柳木在木匠张老三的眼里晃动成一件艺术品。他用手丈量木材尺寸,放倒,闭上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目测木材曲直。最后把布满树皮皱纹的脸颊凑到柳木年轮上自言自语:凳不离三,门不离五,床不离七,桌不离九。
一块木材去皮、分割,散发出青涩好闻的味道。刨子刨出的白色花儿满院子飞舞。凿子下落处,榫卯成型,这一场精彩的演出,吸引了我好奇的目光。斧头、锯子、凿子相互碰撞,如“坎坎伐檀兮”。春天在老宅里跳起迷人的花式舞蹈,一条墨线紧贴木材,时而伸出,时而缩进黑色的小匣。我很想把那条线偷着揪出来,画在明晃晃的大地上。
腿、边、牙板三个部位的榫卯相接固定,刷桐油,上漆,辽金时代就已出现,盛行于明清的一面八仙桌像一个人,大气平和,顶天立地。在堂屋正对门靠右六寸成为岁月里重要的存在,雕花木椅、铮亮的茶壶茶碗、白瓷的盐罐,整洁沉默,叙述生活另一个鲜活的层面。尤其北墙上几张父亲赶脚带回的内丘神码,给八仙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墙画上的神仙有树枝一样头发的女神,有留着八字胡的井神,有头戴瓜皮帽,手持如意的上房仙。尤其“家堂”族谱上的人物画像,身材高大结实,竖眉圆目八字胡,身着绿衣锦缎,胯下一匹枣红马做奔跑状,好似我的祖先曾经是威风凛凛、叱咤战场的将军。
母亲每天把八仙桌都擦得纤尘不染,并把桌子上的器具清洗干净,规整整齐。如果做了像扁食、炸鱼、花式馍馍等特别的吃食,母亲也会先端到八仙桌上供奉一番,求得祖先护佑赐福,并说我们要仁慈要虔诚,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当八仙桌的桌角写上,狗剩、根州、梅、鞠等被办喜事的人家借去“坐席”用,我们家的屋子好像一下被掏空了,墙上的杨柳青年画好似翘首以盼做等待状。当我的乳名“秀梅”,出现在八仙桌的一角,在锣鼓喧闹里,在深深的巷子里,被抬来抬去,我感觉特别神气与自豪。八仙桌被抬回来时,桌面上多了办喜事人家送的一碗肥肉片,而我的名字早已消失不见。
来串门的人,比父母辈分大的,被让到右边的椅子上时,总是朝墙上的家族族谱望一眼,似乎是请示。辈分小的主动坐左边的椅子,也是坐有坐相,母亲说祖先面前谁都不敢造次。有了八仙桌,串门的人多了起来,你来我往,有时谈人情冷暖,谈庄稼收获。有时在八仙桌左右一边各坐一个,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就那么坐在黑夜里像两尊雕像,与墙上家族族谱的人融为一体,似乎沉默静坐也是应对岁月的一种生活方式。
古人对于方是很执着的,认为天圆地方,为人要方正,做人宁方不圆,要棱角分明。古代铜钱是外圆内方,你可以表面上很圆滑,但内在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则。如此说来,八仙桌代表了一种心境,一种态度。重要的节日祭奠时,母亲在八仙桌上摆贡果三盘,上三炷香,三炷香,代表天、地、人,敬天、敬地、敬人,三炷香为满香,是万物之极致。三在祭祀里,包含最大的敬意,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倘若母亲懂“三”这个数字的含义,知道对于天地和人类心存敬畏,心要如八仙桌方正。她何尝不是八仙桌边的一位女神,用自己的骨血生养了我们,并替我们阻挡所有的苦难。
四
对于乡村童年的那些夜晚,光明是奢侈的。除了星光和月光之外,煤油罩子灯和马灯曾是一个村子、一个家庭的使者,举着光明的尚方宝剑,斩去黑暗的头颅,让我们得以在光明的照耀下,演绎悲欢离合的人生大戏。
煤油罩子灯底座大约8 公分,灯罩大约16 公分,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灯口的位置有五六个铁片围成的爪子,用来固定玻璃罩。一根棉线做的灯芯,一大部分伸到煤油里,只露出小小的灯芯。
等夜幕降临,只听嚓的一声,一根火柴把罩子灯点亮,把乡村的安静点亮;只听又嚓的一声,一根火柴又把一个罩子灯点燃,又把乡村安静的夜晚点亮。整个村子的罩子灯,不约而同都被点亮了。屋子里不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从窗口看去,灯火隐隐约约,微微弱弱地颤栗着,罩子灯照的范围很小,只有一米或者几米,人们要想做什么活计就得凑到罩子灯下才能看清楚。家里有上学的学生,得把罩子灯先让给学生写完作业,不写作业的人摸着黑拉家长里短。乡亲们彼此熟悉,只听声音就能知道谁的脸上长了几道深沟似的皱纹。那个说话吞吞吐吐不利索的准是患了半身不遂的二大爷,那个看不清脸庞,身体上只沾取少许光晕的是会计股长,迷糊爷爷。他每一次来我们家串门,进门的时候,罩子灯芯虽然被罩子封着,但是还是摇动了几下。
我们家的罩子灯是比较大个的那种,肚子里装的煤油也多,一晚上也燃不完。吃过了晚饭,围在罩子灯下看母亲穿针走线,给我们缝补衣服,纳鞋底做鞋子。母亲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们讲黄鼠狼偷鸡吃的故事。我们支着耳朵细心听着外边的动静,也绷紧了弦听着鸡叫的声音。生怕我们家的鸡被黄鼠狼叼了去。其实黄鼠狼啥样,母亲都没有见过,但是在村子里却传得神乎其神,有的说像狗,有的说长的像狼。那年月,人都吃不饱,黄鼠狼能吃饱吗?其实村里的鸡也并不都是黄鼠狼叼走的,有的是耐不住饥饿的人偷吃了,又伪造了黄鼠狼偷鸡的假现场。
我想,如果给鸡窝上也安置上一盏罩子灯,黄鼠狼还会不会再来偷鸡?而偷鸡吃的人会不会连罩子灯一起偷走?同时丢失这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户人家会觉得天都塌了!
罩子灯是会游走的,它在村民的手中游走,在村民的眼里和心里游走。甚至我想,我们村子的罩子灯会走到天上去,和天上的星星相互交换光明。
罩子灯缺油的时候,灯芯蔫吧蔫吧地打不起精神,过不了一会灯光像一个人的命一样,忽地灭了。围在灯周围的人使劲地叹息了一声就陷入了黑暗,供销社缸里的煤油也见底了,买煤油的人趴在缸沿上伸长脖子朝缸里瞅,似乎要用眼球搜索一些煤油出来。
学校夜晚的那种黑,浓稠而又安详。那两个木格子窗户上全是黑洞,像被机关枪一阵狂扫过,黑洞到了夜晚似乎更黑,比墨迹比煤炭还黑。学校里没有一盏煤油罩子灯,供上晚自习的学生使用,学生们不能把家里唯一的罩子灯拿来,只能自己制作煤油灯:空了的墨汁瓶,瓶盖上钻一个小洞,把棉花碾成的灯芯一头伸到瓶子里,一头露在外边,一盏简单的煤油灯就诞生了。为了不让风把这微小的火苗扑灭,用五颜六色的纸卷成长圆形,再用浆糊粘牢,一个灯罩就成了。
随着一阵惊呼,随着彩色的隐隐约约的小如豆丁的火苗,在漆黑的深巷里闪现,孩子们便三三两两沿着坑洼不平的街道去学校,没有灯的孩子也跟着这小小的火苗,不敢大声说话,小心翼翼走过又黑又深的巷子,在学校黑色的院子里集合。总有一两个胆子大的孩子把教室黑色的门推开,把教室里的黑色逼出来,大家才把煤油灯举过头顶,蜂拥而入。一两个孩子或者好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围着灯火读书或是习题,小小的火焰在孩子们脸上跳来荡去,火苗也把孩子们的鼻孔熏得发黑。
读着读着,我们的巷子里灯火通明,读着读着,自己就爬上了缥缈的夜空,长出了翅膀,有了飞起来的心和飞出来的梦。
去年春节回家,偶然看到父亲的那盏马灯,骨架不全地挂在墙上,写下浅薄的一首诗:
那盏有四十年历史的马灯/退出夜的舞台/父亲漏雨的偏房里/独自寂寞/轻轻一碰,就会成为时光的碎片;父亲年轻的时候/提着那盏马灯/去很远的地方/为生产队置办农具/半夜起来为马儿/增添草料,那盏马灯/引领父亲跳过岁月的沟壑;那盏马灯也曾/照亮我上夜校的路/微弱的光亮是我理想火苗的起始/现在,灯的玻璃/灯的铁,灯的光/均已没有了灵魂/我在心里,尝试/把暗藏的灯芯,拨亮。
马灯比罩子灯的地位高些,同样是一个家庭重要的财产和使者,马灯明显比罩子灯“装备精良”。马灯不但有圆形稳固的铁质底座,有像鱼缸矮胖的玻璃灯罩,灯罩上有交错的铁丝,最重要的是马灯有提手。马灯能随便游走,提着马灯,可以去马槽,可以去羊圈,可以神气十足地走街串巷,可以堂而皇之地穿过一片坟地。
提在风里,风吹不熄它,提在雨里,雨浇不灭它。如果一个人提着马灯深入田野,他的脚步就不会步履蹒跚,也不会因为恐惧而惊慌失措。马灯的光亮虽然微弱,被一个人提着行走在大地上,足以压倒一切鬼火,也足以让一个深入庄稼地的小偷,望而却步。
生产队解散的时候,有的人抢牛,有的人抢耧、杈,有的人抢独轮车,只有我爹,不顾一切地抱着一盏马灯不放。他知道,冬天的夜里,一个人多么需要一盏灯的热度;远行的路上,一个人多么需要一盏灯的陪伴;疾病缠身的时候,一个人多么需要一盏灯给与希望。
我们家有幸有一盏马灯,让我觉得日子是温暖的,也必将充满光明。我们家的马灯,不被点亮的时候,就被挂上墙,一个固定的木钉子上,而且这个位置一定是冲着屋门口。似乎马灯不但能扫走屋里的黑暗,还能照亮屋子以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在告诉村人,家里有了马灯,日子会一步一步走向红火。
有一年七月的某天,大雨像受了谁的指控,从早上到晚上一个劲地倾泻,我家的院子里早已变成一片汪洋。吃完了晚饭,我爹忽然从马扎上坐起来,说了一声:坏了 !从墙上取下马灯,匆匆点亮,提着从院子的水里,走向巷子的水里。
我们站在门道里,看着提着马灯走在水里的爹。觉得水里全是马灯,一闪一闪的,水里全是爹湿漉漉的影子,也一闪一闪的。
爹去了自留地,自留地里生长着三百棵玉米,正长势喜人,正在抽穗马上结果了,这大雨无疑是当头一棒。我等着背着玉米干粮去读高中,家人等着这些玉米果腹,玉米,可不能有事。
爹到了玉米地,爹的眼泪开始像雨似的下个不停,三百棵玉米东倒西歪,刚抽出的缨子,被雨一把一把揪得纷乱。爹顾不上马灯了,他把马灯蹲在连营的坟头上,就蹚进玉米地的水中。先在地头掘开一个口子,让水流到沟里,再把一棵玉米从水里捞起来扶直,用脚在四周踩一圈,把另一棵也这样,把三百棵玉米都扶直了身子。
到了大半夜,也不见爹回来,也不见雨停,娘带着我们摸索着去自留地。到了自留地的时候,我们只见那盏马灯,立在连营的坟头上,火苗忽闪忽闪的,似乎在给我爹加油,也似乎是连营蹦出来给我爹加油。夜晚,全是黑暗,全是雨帘,一豆丁似的火焰,是对黑暗绝对的反击。怕雨削弱我的声音,我蹲下,身子几乎挨着水面呼喊我爹,我爹在地的最东头有了应答,他的声音传过来的时候,马灯又忽闪了几下。三百棵倒地的玉米直直地立在雨雾里,我爹从地的东头走到地的西头,从泥水里拖出自己疲惫的身子。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爹脸上的沟壑里藏着,还没有来得及流下来的雨以及泥巴。
爹看到我们抱着马灯在等他回家,他的脸上有了马灯的光亮和温暖。回去的路上,马灯走在爹的前面,我们跟在爹的后面,我们一同在水里雨里闪闪烁烁,一点也不觉得冷和苦,就觉得迷蒙的雨雾里,还有一盏马灯,在家里的墙上,发出耀眼的光束。它温暖的呼唤,穿过深深浅浅的巷子,穿过坎坎坷坷的岁月之河,直照到我的心里和灵魂深处,直到现在也是它一次一次地引领着我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