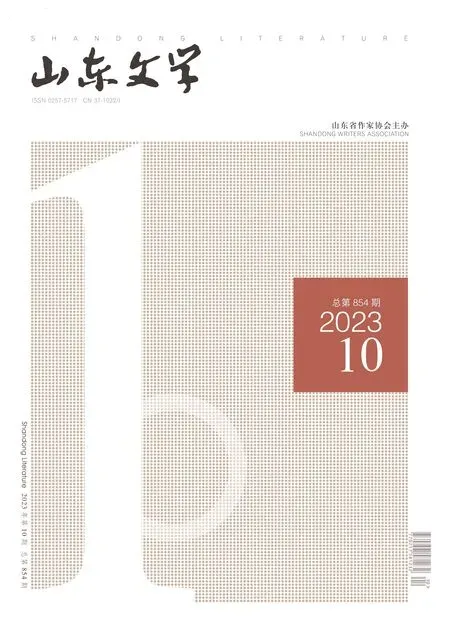野性与天真(组诗)
晓 岸
九三年
锯木房里培养了绿色的汁液
来自黑暗的气息,始终像一种不可接近的美
我被它牵引、蛊惑
让我相信了另一个时空的存在
我凹陷进去
在一个无边的圆弧上站住——摇晃的灯光
像六月里的土豆花
我看见了父亲,从一个新鲜的地方来——
他要告诉我什么——
死亡对他不再是一种负担
我从破桥上跑过,躲进山的阴影里
黑夜跟随我
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我听见它
慌张的心跳,仿佛渴望扑进母亲的怀抱
房子里的汁液流淌出来——
桦木,松木,坚硬的柞木都沾染上了,重
新长出叶子
就像我的耳朵,听见了呼唤——
它们飘起来,朝黑暗最深的地方
我在后面跟着奔跑
我的后面,一个巨大的月亮正在落下
松湖的另一种
雪是多余的,干草也是多余的
矮鹿从桦树林里走过,像一个好奇的婴儿
它纯净、漂亮,代表
造物之神对这个躁动世界的安抚。我需要它
至少在离开松湖后的日子
至少在你醒来,又重新躺在春天的湖畔——
那是浅绿色的世界,不像冬天。人们留下的空白
覆盖我的祈祷——你知道
每一个山峰都沾满了我的气味
每一条不安的小路
它们被荒草遮蔽,不再通向未知的远方
你要知道,松湖的另一种读法——
撕开它冬天的表皮
我和另一个自己的相逢——这神圣的仪式
仿佛是火——冰的火、雪的火、干草之火的交融
这是烈焰的宽容
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负担——
深深的责备。我将它藏起来
但它并没消失,跟着我在身边低语,确保
我不会忘记
在针叶植被稀疏的岩石地带
我又一次眺望了它——那巨大的镜子
哦,就像记忆的渊薮——时间沉陷,星空
沉陷
死亡将在那里得到最高的尊崇
大寒,落叶林里的雪
怎么绕过这一年——
我们曾过度相信命运,用力去遮盖自然蓬
勃的本性
为一座假山、曲折的景观公园
分享了有限的时间
现在,应该结束了——虚假的、敷衍的
聒噪的一切。当雪落下来
死亡之白沉默而耀眼
松鸡也停止了张望,为送行的人群
标记好每一棵树木的高度
林场乌黑的车轮,映出了铁锈的真实面目
松湖三年——黑与白交替
山峦的莫须有之名,被落叶层层覆盖
它从不针对新生
就像野葵花的理想生活,独自完成自我的
进化论
活着,仿佛很少具有代表性——
针叶落光,人们安放好棺木,有一大段空白
填充了我们生活的新一页
或许你还能效仿星鸦,横渡两座山林
给亲爱的家人带回温暖的晚餐
——这不是我们的追求吗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你看呵
神迹不会显现,只有人群起伏着消失
雪落满针叶林之后
还将覆盖掉我们的所有的痕迹
野 鸭
野鸭最早回到湖面,无风的中午
在冰面完全化开的区域游荡
它们是一个小家庭,它们也是一个小宇宙
而我则不同,我有私心
我有无法更改的人类的狭隘
不论是啄木鸟,还是潜伏在灌木丛里的野狐
对野鸭的生理反应
都不会超过我的十分之一
我爱黄绒毛的小野鸭,也对它们飞翔的本领
心生艳羡。有一阶段,我甚至垂涎它们的
肉体——
看,我是一个多么阴险多变的家伙
——可是,野鸭不同
它们划开水面
它们没有定义、规范、行为指南
因为生命的本身,那些超自然的感知
使它们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
在命运的悖论之内
我们收束野性的本能,也丧失了自由的天真
等一个月亮
在城市里,我会关了灯,等着它安静地出现
有时候在前半夜
有时候,是在更安静的后半夜
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看看它,听一下那里的声音——
一种类似于松湖的声音
春天鹅黄色的柳叶在水面上打旋
有人从雾霭里走来
在黄昏巨大的月亮底下点起篝火
今天想起来,我已经不记得那个人——
留在松湖的人
没有和我真正见过面的人——
像一个虚构的敌人
还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为此我还要浪费多少青春与之对抗
现在,在那沉默的星群中
等待一个更需要沉默的反光的石头
仿佛是为了救赎,又更像一种忏悔
它断裂的沟壑藏不住了——
曾经的河流、鱼群、秋天的针叶层层落下
一个年轻的肉体,伴着熟悉又陌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