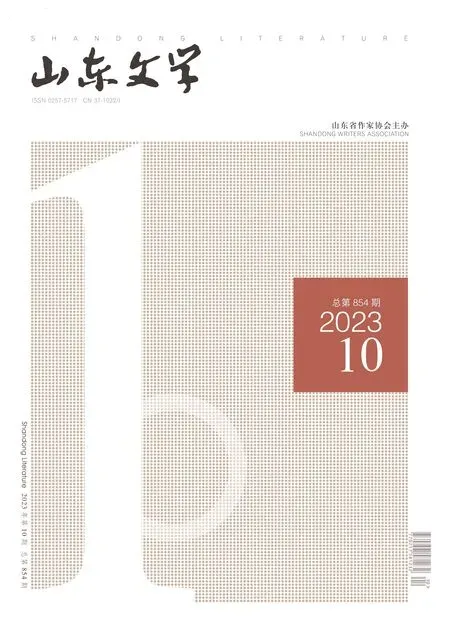灵魂手札
杨彩云
一
2015 年,我六十五岁,想写一部抛却所有虚伪和浅薄,真正属于自己的书。这并不是说之前写的书不诚实,只是出于各种客观制约,许多时候敞不开心扉,而不得不将一些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扣下来,造成部分的缺失和无奈的遗憾。而人到暮年,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什么也不怕了,不要糟蹋了最后的岁月和手中的这支笔。于是很快有了一个选题:我们这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虽然晚年大都安乐幸福,但我们经历的太多了,饥饿、迷惘、挣扎、沉沦、奋进……可以说,人间的苦难,除了战争其他都经历了。
总结阅历,世间的事啊,有着惊人的重复性,以为突围了,却还在里面,不知什么时候还会突然被撞一下,撞得头破血流。就像遭受了邪恶的诅咒,怎么也不能彻底摆脱,于是还没有动笔,书名便有了:《魔咒》。
说写就写,当年年底,《魔咒》便完成了一稿,电脑显示五十七万字。我打字飞快,但不是写出来的,是“喊”出来的,那是一种纯粹的发泄,有什么泄什么,黄河决口,滔滔不绝,怎么痛快怎么来。后来常有人奇怪地问:“你怎么写得那么真实?”能不真实么?那是在地壳的高压下挤出来的原油,是西瓜熟得自个儿落了地,又裂开淌出的红瓤,能不真么?严格地说,最初的那一稿不是小说,而是个超大的日记,在肆无忌惮的叫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泄之后,我的情绪有所缓解,不再是个发疯的婆子,渐渐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作家不能自说自话,应该为社会发声,为大多数人起码为一部分人发声,个人情绪必须与大众情绪保持一致,才有社会性和代表性,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引起共思和共议,才可以成为送给别人观瞧的文学作品。
于是开始了第二稿,这一稿就比之前内容丰富了,切入了时代背景,将故事进展、人物成长与时代拧在一起,我想起了许多熟悉的人和事,许多故去的和活着的朋友,许多印在脑子里永远也洗不去的事件和场景,开始重新组合重要人物,重新确立主人公形象,重新洗牌,尽量将内容立体化具象化。我要尽其所能地为那代人呻吟、呼喊、流泪和欢笑。
当然,这并不太难,因为我对那些东西太熟了,无论人或事,都活了似的纷纷跑到我的笔下,挤着让我安排,我就是起了个召集的作用,把他们尽量有序地放在合适的地方。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这由不得我,而要由着历史的推进和人物性格的发展。我就是个调度员和化妆师,负责每个人不要乱跑,负责他们的服装头饰,自然也负责道具和美工。
而我也必然是其中的一员,属于自编自导自演,所以很投入。我回到了六十多年前朦胧记事的时期。还记得当时的民歌:老年赛黄忠,青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后来就记得提着小瓦罐去食堂领饭了,先是大个的红薯,有一斤多重,稀溜溜的,小孩都拿不起来,大人们感叹:得烧多少柴禾才能煮成这样啊。后来红薯没有了,只提回来半罐清汤。有次路上被人伸腿绊了一跤,汤洒了,我哭了,一辈子不爱理那个人,至今想起心里还有点儿耿耿——那是饥肠辘辘中唯一可下肚的东西啊。
但那时,人们是多么地振奋啊,似乎共产主义真的明天就要到来了。我六岁上学,老师嫌小不要,但我已经认得一些字,数数也不差。那时收学生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数够十个数。我学会的第一支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而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的第一支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每当听到她们的时候,两行热泪滚滚而下,那种激动和当初的激动一样,心弦随着旋律一齐颤动。我爱我们的国家,我爱我们的人民,我也爱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从小印在心里的思想。所以,《生命深处》多次提到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由此可见,幼年的教育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我今年七十三岁了,身体不好,已是风烛残年。但往事历历,依然如初。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可恨的好记忆,许多的事情放不下。爱的依然在爱,恨的依然在恨。不仅没有削减,反而某些感觉还在加强。好坏的作用是长效的,就像往人体里打激素,打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越来越严重。但对搞写作的也许是好事,它可以帮助人不太费劲地就找到感觉。于是,我从刚记事那时开始,一节一节地回忆起来,并一节一节地开始叙述。当然,《生命深处》的延伸期在一百多年前,那肯定是虚构,小说就是虚构嘛。只有思想内核是真实的,这种思想内核是作者的原动力,也是作品的内在支撑,是作品和作者的共同灵魂。我想干什么呢?我想让尚有良知的人们知道,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希望许多的悲剧不要发生起码少发生,让善良的人得到安宁,让邪恶的人感到羞耻,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而要达成这样一个目的,必须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思考,对历史进行认真的回顾,对人性进行CT 机式的切片扫描。
二
写这部书真的需要一定的勇气,这是自揭自家的疮疤,而且没有麻药和消毒水,时时都是撕皮割肉火辣辣的痛感。
亲戚中正式送书看的只有大姐。因为大姐问“又出书没有?出了就寄给我。”我趁机赶紧寄了过去。我俩都是被上海抛出来的孩子,感情上比较接近。过了一阵子,做贼心虚似的打电话问看多少了?电话那头大姐的声音平静中略带激动:“看完了,惹得哭了好几回。”我一下子放了心,谢天谢地,我的大姐没恼。大姐问:“你怎么还记得三阳路?我都忘记三阳路了。”是的,我记得三阳路,尽管在我出生那年上海的三阳路就改成了中山北路,但我还是记得。并根据三岁之前少得可怜的几个画面还原了三阳路,也还原了上海解放初期的棚户区。前几年有部电视剧叫《国家的孩子》,讲困难时期上海将一群孤儿送往草原,后来在那儿生活成长的故事,由傅程鹏主演。我看了好几遍,是替我大姐看的,大姐十七岁离开上海去往戈壁滩,虽然不是孤儿,但也和孤儿差不多。至于我,曲里拐弯同样存在着那种感觉。
大姐没有恼,我很欣慰,这样也算替大姐写了一番文字。还有我那个可恶的记忆,抹上了就再抠不去,上海中山北路126 号就是我家的门牌号码,直接就写上去了,改一个数字都不痛快。是的,《生命深处》的不少地名和人名都是经过反复思量的,都和原型有着某种关连,甚至一字不改,直接实名制。只有这样我的情感才通畅,笔下才有感觉。比如里面的冯氏,那是个量身打造的人物,活生生的就是那样,几乎一点儿都没有走形。我也曾把她改为柳氏,但不行,感觉立刻不对,看着就别扭,就像钥匙没对准孔眼,咔啪咔啪乱响,只好又改回来。当然,主人公端木槿绝对是综合了那代人基本特征写出来的,她是那代人行为和思想的代表,是平民英雄。但她也不是完人,有马失前蹄的时候,甚至关键时刻会有重大失误。比如与马向东的婚姻,自己给自己设下了个巨大的陷阱,深陷其中走了许多弯路,吃了许多苦。有读者十分惋惜,问为什么要让她嫁给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马向东?但设身处地想想,她那个时候还有出路吗?她也是个知冷知热有血有肉的人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她崩溃了,她完了,这就是人生悲剧。但端木槿之所以是端木槿,是她依然站起来了,并冲出来了,尽管伤痕累累,她还是凤凰涅槃地踏入了社会,成就了自己。这就是那代人的情操和追求,那代人死而复生的钢铁意志。
端木槿的人设当然是很慎重的,因为她是主人公,整部书几乎都是围绕她来写的。百万字的长篇,第一章她出生,最后一章她去世,一生涵盖了中国七十年的历史。她如一只小船,在九曲十八弯的历史河道里迂回前行,也有顺风的时候,但顺风远没有逆风多。所以,端木槿必然要用巨大的努力来换取最后的成功。但这种为了追求理想九死而不悔的精神不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吗?不正是许多人所缺失的吗?所以,只能让她受苦,不受苦没有办法,我救不了她。她出生的家庭、所处的年代加之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必然要发生那样的事情。她一生没有过真正的轻松和幸福,最后的结局,在定稿之前比这还要惨。于是有人说,你不能这样残忍,惨得看不下去了。中国戏剧往往以大团圆结局,所谓“不杀奸臣不煞戏”,那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梁祝死后也得让他们化为蝴蝶,然后一起翩翩起舞,那是浪浪主义。而我是现实主义。但在别人的提议下,也来了一点儿中和,于是最后一稿让结尾有了一丝温情,端木槿在没有遗憾中比较安慰地死去。但书问世后立刻又有人尖锐地指出:她不应该这样温和地死去,这是一种人为的安排。建议如果将来改电视剧,一定要按原稿改过来,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真佩服这位先生的洞察力,一眼就看出了“作弊”。也就是说,我还没有真正地正视现实,没有将悲剧进行到底。没有进行到底的原因是我的心软了一下,但现实会软吗?现实是无情的,如果端木槿真有其人,她的最后肯定也是悲剧,她就是个悲剧性格。
但我让她有了一段真正的爱情,甚至让她与真爱发生了性。这在我四五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是破天荒的唯一一次。我所有的作品与风月无关,从不写情爱。有人当面开玩笑:你的作品不好看,连个接吻的场景都没有。世间除了情爱就没有其他了吗?非得戏不够爱情凑吗?太可笑了。我对情爱没有兴趣,所以不写情爱。但必须给端木槿一段情爱,还必须让她与所爱的人发生性,哪怕只有一次,也能让她的人生完整,不然那才叫残忍。
《生命深处》中的秦月,是个比较受喜爱的人物,因为个性特别。这个人是有出处的,我说过几乎所有人物的名字都与原型有关,此人名叫孙月霞,是我的一位初中同学,著名剧作家,曾凭历史剧本《画龙点睛》名噪一时,可惜去世了。秦月便是为了纪念她而设的,而秦月从形象到特征则完全是小说版的孙月霞。我们俩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竟同年一个开始写小说,一个开始写剧本,并都获得了成功。当时有人撰文写了篇“宋江河畔三女杰”的文章,挺有影响,那就是她和我,另一位是歌唱家。她的去世,让我难过和沉默了许多时日,人生无常啊。作为怀念,我让秦月成为三剑客中人生最完美的一个。她还好好地活着,活在我的心间。至于王凤华,则集中了农村基层妇女干部的所有正面形象,可以说她是张英,也可以说她是李华,她是优秀妇女干部的代表。在长期的工作中,我和许多这样的女同志成为朋友,她们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会在有意无意间观察她们,当然那时不是为了写《生命深处》,而是一种职业的本能。
三
为什么要写悲剧?因为我写的是端木槿。端木槿是行走在悬崖上的人,悬崖很高,路很窄,雨天路滑,不掉下来都困难。而当她坠落的时候,眼看着也没有办法。够不着,够着了仅凭人的双臂也托不住,她带有高空冲击力。在我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时候,最初动笔写的就是一部长篇悲剧。也许因为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有些感人,被推荐参加山东省作协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著名作家刘知侠、林雨和王希坚亲自审阅,并在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了修改意见,可见其重视程度。可是伤痕文学瞬间过去,有人提出了质疑:新社会有悲剧吗?我那时只有二十几岁,是个初学者,连标点符号都点不太准。但我很不理解这种提问,你没活在天底下吗?有些悲剧的发生是不讲时代的,辟如车祸,辟如天灾,太平间里哪天没有冷冻着的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悲剧,就像有空气的地方就会有生物。只是要看这个悲剧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说明问题的可能性。悲剧是最彰显人性的事件,人在它面前无所遁形。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生命深处》想动手了就可以即刻动手,连腹稿都不打,那是因为我已经为它做了一辈子的准备,决非一时兴起。我绝非多愁善感之人,喜欢交友,喜欢大笑,还能豪饮。以往文章中也常带有一种豪气,谁又知我能写这种以泪洗面苦不堪言的悲剧,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这是真觉得苦了,不吐出来不行了。也许水火交融,才能产生更状观的景象。更重要的,我的职业是作家,老牛自知黄昏晚,还能再写多少东西呢?一生都没有怎么追求荣华富贵,到了这个时候,更应该放下一切的虚伪和怯懦,去表达心中最想表达的东西,写出一部有分量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来,相当于阿Q 画他的圆圈。最初的时候,我想大概能写五十万字,但第一稿就是五十七万,接下来这里补上一个情节,那里再添加一个人物,添去补来,最后达到了一百万。我要的不是数字,数字说明不了根本问题,我要的是质量。一小块黄金顶过一大车石头,但如果真有一大车黄金那不更好吗?质量的问题在于深度和厚度,在于驾驭文字的能力,在于所要表达的东西有多少价值。我真的是个很不聪明的人,空有一身胆,却很难看透事物的本质。所以只好拼命地想,想破脑壳地想,分析社会,回顾历史,拆解所有可能触及到的现象,当然更要分析人。世界上最复杂的是人心,人说人心有六个棱,而我说不知道有多少个棱,连每个人自身都不会真正清楚自己。因为会变,万花筒般动一动就变。而活人又是在不停的运动之中,那么就要去捕捉瞬间的变化和形态,来完成自己的作品。我读过两年中文,记得最结实的两句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生命深处》的最难点,就是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虽然作品中没有几个直接关于这种问题的字眼,但它无处不在,是情节推进最根本的掌控点。情节不会自个儿产生,人物也不会自儿长成,都需要时代和社会做他们的根基和铺垫,或者说是一切人物运行的底色和轨道。
我有一个长处,就是会看人,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想什么做什么,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笑脸或哭相,也就是说,文字语言还算过关。我时常坐那儿冥思苦想,怎么样才能让作品更厚重一些?让人物更丰满一些?让语言更精彩一些?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苦思苦索,诚实地去反复回忆和思索所写时代的外在和内涵,寻找人物命运和它们的重要关连,掘宝一般去努力地深掘一点,再深掘一点。哪怕掘出一丝丝新的光亮,也欣喜若狂。因为我知道这是作品厚度和深度的根本所在,更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部作品了,必须把它写好,必须把圆圈画圆,不让此生留下遗憾。
人物也不是那么容易写的,端木槿这个医生身份就让我费了老鼻子劲儿。我对医学一窍不通,又必须写得像个医生,还是个中西医结合,会针灸,会开方,会急救治疗。我去郓城县中医院学习,实习生一样跟在医生屁股后面从病房走到药房,从办公室走到ICU,装模作样地摸摸病人的头,询问病人的情况,看人家的病历,要人家的处方。郓城中医院十分配合,第一天为了等我,晚了半小时才开始查房。之后,只要需要,就打电话询问,再加上我自己生病和看病的经历,好歹凑成了端木槿。这个人物不是医生的时候,我几乎游刃有余,而当是医生的时候,不敢多写一个字,不敢有半点儿发挥,一个词也要在百度上查找,唯恐露出马脚。以至后来有人问:你当过医生?我笑着摇头。甚至有位先生打电话咨询精神病患者怎么治疗,因为端木槿用针灸治好了病人。当然,也有真正的医生提出了一些问题,说有些儿不太像。这是肯定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在真人面前糊得再好的纸人也糊弄不过去。如果我把端木槿的身份改为民办教师,那就无论如何也不会露蹄爪了,因为我有着十三年的教龄啊。但不能把她弄成教师,弄成教师就更成了我了。为了避这个嫌,可累死我了。
许多人属纯虚构,比如李玉全,比如曲峰,比如端木友和董先生,还有马任远等等。端木槿需要有这些人,这些人能帮着完成端木槿形象的塑造。但假人得当成真人写,他们真的活动在我的眼前,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生动鲜活,我也就用语言把他们生动鲜活地搬了下来。曲峰死了,我哭得很伤心,心痛曲峰心疼端木槿,那么悲壮,那么凄惨,我自始至终陪着端木槿在追悼会上痛哭。写到曲峰给端木槿的几封信的时候,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写一遍哭一遍,似乎真的看到了曲峰在雪山之上寒夜之中披着毛毡给爱人写信,一封一封又一封,充满爱之激情地写,却不知这是绝笔。许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边写一边哭,一边写一边笑,只是笑的时候没有哭的时候多,也就造成读者哭比笑多。有读者在网上说,看这部书要先准备好擦泪的纸。可他们不知道,最早哭的是我,哭得最多的也是我,许多时候,我伏案大哭,而且是写一遍哭一遍。就像那些地方有泪泉,一到地儿泪就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是个多么硬气的人啊,几次生病开膛破肚都没皱过眉头,可是我为我的人物哭,我深爱他们,就像母亲爱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可是我没有办法拯救他们,我只能把他们的事情写下来,以叙衷肠。于是,我的笔下便出现了一幕幕悲催,希望这些悲催能引起人们的思索,能化解些人世间的戾气和邪风,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四
我的重点在于写人,社会历史只是背景,人物投在这些背景上,折射出时代和历史的色标。我只是在充当一个端木槿式的医生,大声说出自己对病情的分折。而人,都会生病,社会也会有病,没有病就不需要前进了。可怕的不是病,而是讳病忌医。虽然我不会鬼门十三针,去扎回一个人的记忆,但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去唤醒一些稀里糊涂生活和在错误的路上不肯回头的人,我希望我能像蜡烛一样点燃起青年的希望,给他们一点向上的勇气和力量,我在拿端木槿为他们做榜样。所以,尽管我写的是悲剧,但风格却绝对悲而不哀,苦而雄壮,满满都是正能量!我极不喜欢负能量太多的人,让人丧气,让人提不起精神,让人活着也像死了。为什么不精神地活着呢?生命只有一次啊,所以我们要振奋,要努力,要像保尔那样把自己炼成钢铁。当然,我们离钢铁都还很远,这就需要继续努力。《生命深处》要实现的是一种价值,追求的也是一种价值,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步步走向的是生命的高峰。当然,价值最终水平会因人而异,但一个人只要尽到他最大的努力,他就达到了自我价值的顶峰。
《生命深处》第八稿完成了,是该送给某些朋友看看了,提些修改意见。这也是写作生涯中从没有的事情。我是个独行者,从不请人看稿提意见,也从不请人写序,似乎那是狗尾续貂,有蹭别人热度之嫌。2018 年4 月,我乘车去菏泽,参加市文学创作突出贡献奖颁奖仪式,路上接到一位朋友电话,和我谈修改意见。他是一位资深编辑,对于小说创作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提了四条诚恳且中肯的意见,我一一记在心间。颁奖完毕,顺道回了郓城,与朋友相聚,同时也去医院做了一下体检。影像报告单上显示“肾积水”。何为肾积水?不懂,其实上一年就说肾积水,但忙于写作,没当回事,连找人看报告都没有。这回找人看看吧。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学生皱着眉严肃地望着我:“杨老师,你回济南以后要马上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不然,你的肾可能要保不住了。”我有些吃惊,没太大感觉啊,有这么严重吗?但也不敢再大意,回来后就去了医院,医生让住院,这才觉得可能是有些问题。但向来独立独站,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虽然和女儿同住一个城市,但没有住在一起,住院也没有告诉她。一个人捏着单子,楼前楼后楼上楼下,每天反反复复做各种检查。怎么这么烦人呢,比我写文章还复杂。第七天午睡醒来,一睁眼女儿在床前站着,我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女儿一脸委屈:“你住院了也不告诉我。”我笑了笑,告诉她干什么,她又不是医生,我又不需要照顾。半月后我被从内科转到了外科,医生问:“你有孩子吗?”我回答:“有。”“明天让你孩子过来。”我感到有些不妙,但医生的样子根本不想对我说什么,只好给孩子打了电话。第二天,女儿女婿都来了,首先去了医生办公室,出来后脸色不太好,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说:“需要手术。”我说,“手术就手术呗,要做赶快做。”赶快做赶快好,我还急着去改稿呢。那会儿还想起赵丽蓉侯耀文演的相声《英雄母亲的一天》,记者反反复复教给她如何说话如何走路,她却“司马光砸光”一个劲儿地说不对,急得最后装病,然后端着盆急急买豆腐去了。我也很急啊,却在医院里没完没了地耗着。我所知道的就是个瘤子,需要切掉一个肾,切掉就切掉,反正还有一个。于是若无其事地进了手术室,出手术室以后,人是不能动了,还高烧不退,好容易退下去就该出院了。可病理报告却迟迟不拿给我看,催了几遍,女儿哭了,我一下明白了怎么回事,但训斥她“你哭什么?我还没哭呢。”是恶性,而且属高密度。唉,看样子一时半会好不了,既来之则安之吧,接下来化疗,计划六期,每期比同病房的室友多用一倍的药,重药治大病,看样子是不轻。各种难以忍受的不适很快到来,头发很快脱落。但我极不喜欢住院,病房太吵,夜里无法睡觉。只要有一点儿可能,我走几步歇一歇,一个人走到公交站牌,傍晚再一个人走回来。女儿太忙太累,我知道人在岗位上的不易,不能长期请假,尽量少影响她工作。第四期刚开始,血钙突然成百倍地升高,立刻转往内分泌科,是甲状腺旁瘤,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病。但这个病十分可恶,会迅速地把骨中的钙吸出来,然后积存到肾里。我只有一个肾了,可不敢让钙占地了。于是立刻手术。这个手术在脖子上,医生给我拍了照,看上去血乎乎一片惨不忍睹。原以为是小手术,结果失音了,一年多不能发声,指手划脚冒充哑巴。喉咙里那个负责开关的物件失了灵,吃饭喝水都往气嗓里跑,整天弄得狼狈不堪。化疗还得接着进行,这下好,一刀没过瘾,再来一刀,化疗也值得了。
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平躺,好在有个躺椅,日夜在躺椅上躺着,直到现在五年了都没有上床。人不能动,可脑子能动,我在思索我的稿子,思索怎么才能让它更厚重一些,更艺术一些,哪些地方需要怎么改,哪些地方需要再添些东西。毕竟八遍了啊,所有的文字几乎全都打印在了心上,哪儿有什么问题全知道。还有题目,原来不是叫《魔咒》吗,三稿的时候有天看电视,突然在屏幕上出现“风雨晚来秋”,呀,这个名字好啊,那时正在写端木槿凄凉的晚年,与我的心境十分吻合,且十分文学。于是改为《风雨晚来秋》。但八稿之后躺在那里再次认真考量的时候,感到风雨晚来秋调子太低沉,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那么叫什么呢?要找一个通透全文纲举目张的名字,但想啊想啊想不出来。急得无数遍抓着自己的头发喊着自己的名字在心中高叫:“杨彩云,你到底在写什么?你到底要表现什么?” 突然,一个名字出现了:生命深处。虽然这不像文学名字,而更像个哲学名字,但写的就是这个!
于是最终定名:《生命深处》。
我在叩问生命的意义:在生命的深处,我们能留下什么?能找到什么?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叹息。
大半年后坐得起来了,我立刻走到了电脑前,打开电脑的那一刻十分激动,我终于回来了!但手指僵硬,敲打不起来。我打字多快啊,还是四通打字机的时候,所有报刊和出版社都不再接受手写体,需要先送到打字部去打印。可是打字员们从来没打过文学作品,许多地方根本不懂,弄得错别字满篇一塌糊涂,气得我大光其火。随后说:“你们别气我了,我也不骂你们了,我自己去学。”社会上刚有电脑,极贵,还需托关系才买得到,但也有了电脑培训班。我去了,问什么输入法最快,人家说“五笔输入法”。那我就学五笔。整整两个月,天天坐在电脑前,只练习指法,听着啪啪啪啪清脆而有节奏的键盘声,像听歌似的享受。之后便会用了,盲打。二十多年练习下来,如果失了业完全可以去干替人打字的活儿。可是,我的十指不听话了,一天下来,不过改了百十个字,所有的指关节疼得像断了一样,全扎煞着弯曲不得。我暗惊,坏了,不能打字了。第二天,还是试着打,慢慢的,能动了,啪啪啪啪有节奏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我放心了,没事了。
如此又过了一年,改到了十一稿,为什么改那么多遍,因为像打发心爱的女儿出嫁一样,总想再好一点,再完美一点,哪怕一根头发丝也不要乱。2020 年初,与作家出版社达成了出书意向,让把稿子快点发过去。但我还是没发,还要再检查一遍,就是这一遍,把结尾改了。那是即将年关的时候,累得站都站不住,因为我的病始终没有好,而这种病又极怕累,但病痛和劳累对于那时的我已不是事儿,我只要完美的作品,起码保证自己满意。还要尽快把稿发给人家,作者对出版社都是怀揣敬畏的。身体不好以后可以慢慢地养,文字变成印刷体就一个也改不了了。我依然坐在那里,啪啪地敲打着键盘,感觉就是个上了战场的战士,在端着刺刀浑身是血地拼杀。终于把稿子发出去后,我虚弱地对编辑说“从此我再不看一个字,最后校对定稿也不看,拜托了。”
是的,我可以说自己是个战士,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各种艰难困苦只能自己解决,无依无傍。从而养成了独立独站不依赖任何人的性格。但我也是幸运的,我人生的最大幸运就是从事了写作这项事业。前几天身体特别差劲,因为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说话都快没声了。女儿担忧地问还有什么事能让我快乐一点?我想了想说:“还是写作。”只要一坐到电脑跟前,一进入写作状态,就会精神大变,迅速振作起来。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忘记所有,思维敏捷手指飞快,大概我就是个为写作而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