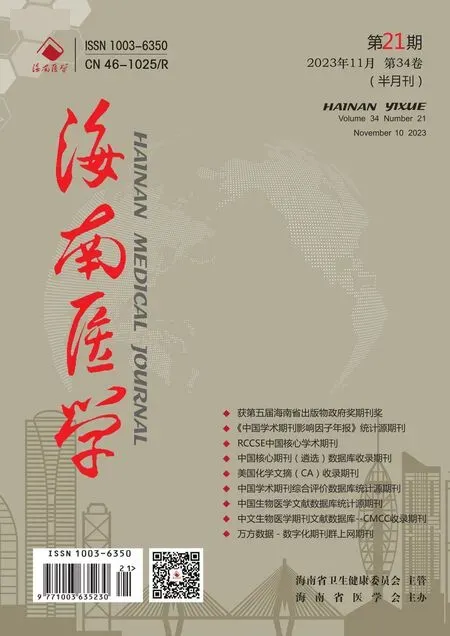铜介导肿瘤细胞死亡的机制及其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
梁浩源 综述 黄许森 审校
1.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2.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广西 百色 533000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早期诊断及治疗极其困难、预后极差的消化道恶性肿瘤。CRC 渐渐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疾病之一,是癌症死亡的第三大常见原因,尽管CRC的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发病率、死亡率仍然不断提升,2021 年的发病率为10.2%,死亡率为9.2%[1]。由于CRC患者早期的症状并不典型,容易被漏诊或误诊为其他肠道疾病,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都处于中晚期状态,癌细胞已经发生了侵袭和远处转移,致使其治疗效果极差,早期CRC患者根治性手术后的5年生存率约80%,中晚期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不足50%[2]。
铜是人体中最常见且不可或缺的微量金属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氧化还原活性和蛋白结合能力,是机体中多种生物过程所必需的催化因子和结构辅助因子,参与能量转换、线粒体呼吸、铁收集等多个生理过程[3]。机体中的铜代谢在自身铜稳态机制的调节下维持动态平衡,从而维持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当机体内环境遭到破坏时可引起细胞内铜代谢失调,包括铜积累过多或运输不当,都会产生有害影响。人体铜含量不足可影响金属结合酶的功能,从而导致严重的发育缺陷;过量的铜堆积会触发铁硫辅助因子的破坏,并刺激由铜驱动的芬顿反应产生具有破坏性的活性氧,进而诱发细胞死亡[4]。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一些铜代谢疾病与铜失稳相关,包括威尔逊病、阿尔兹海默病、Menkes病[5]等,此外铜失稳还可导致肿瘤的发生,相比正常组织细胞,肿瘤细胞对铜的需求更高[6]。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相比过去也有了很大改变,CRC 发病率也正逐渐增加,人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为此,本文简要综述铜介导肿瘤细胞死亡的机制及其在CRC 中的研究进展,为CRC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有价值的线索。
1 铜代谢、转运及功能
铜是一种必需的微量金属元素,在细胞的增殖和死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铜主要以铜离子(Cu2+)和亚铜离子(Cu+)两种形式存在,Cu2+具有氧化性,主要存在于细胞外;Cu+具有还原性,是胞质环境中的主要形式,在体内两种离子动态调节,共同维持体内铜稳态。人体所需的铜主要来自牛奶、坚果、内脏等食物,然而膳食中的铜以Cu2+的形式存在,不能直接被机体利用,Cu2+的吸收发生在小肠中,在小肠上皮细胞表面存在的金属还原酶(如STEAP家族)的作用下Cu2+被还原为Cu+,然后与铜转运蛋白1(CTR1)结合后进入小肠上皮细胞[7],随后在铜转运ATP酶α(ATP7A)的帮助下,Cu+穿越基底外侧膜进入门静脉循环中,然后由白蛋白等血清蛋白转运至肝脏中[8]。肝脏是铜离子的集散中心,大部分Cu+在肝脏中与一种分泌性多铜氧化酶(铜蓝蛋白)结合,在铜转运蛋白ATP酶β(ATP7B)介导下转运至机体所需部位[9]。当肝脏细胞中铜离子浓度高于正常时,Cu+与铜伴侣蛋白抗氧化物1(Atox1)结合,在ATP7B 的辅助下以囊泡形式分泌至胆汁中,大部分经过粪便排出体外,只有小部分经过消化道进行重吸收[10]。肝脏是调节机体内部铜稳态的关键器官,负责对铜的收集、调配、排泄,确保细胞内的铜浓度维持在较低水平。铜蓝蛋白、CTR1、Atox1、ATP7A、ATP7B以及细胞质-线粒体金属伴侣等蛋白质相互作用,共同维持机体细胞内铜的生物利用度,同时确保铜依赖性金属酶的金属化。
2 铜在肿瘤中的表达
有研究通过检测多种癌症患者及肿瘤动物模型体内的铜含量,结果显示在血清和肿瘤组织中的铜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受试者,包括乳腺癌、结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瘤、胰腺癌[11]。机体内的铜稳态水平被打破后,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即可发生,例如:赖氨酰氧化酶(LOX)是铜依赖性金属酶,结直肠癌的侵袭和迁移取决于LOX 的活性,LOX 的活性增加可引起基质在体内和体外的刚度增加,进而导致FAK(黏着斑激酶)和SRC(非受体酪氨酸激酶)的磷酸化增加,这些蛋白质对于黏附复合物的转换有着重要作用[12]。通过沉默ATP7A,可以抑制乳腺癌和肺癌细胞系中LOX 的活性,从而抑制肿瘤的增殖和迁移[13]。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于血管形成至关重要,通过铜转运蛋白CTR1 的氧化还原依赖性修饰,可以驱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2(VEGFR2)内化和信号传导,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和肿瘤毛细血管生成[14]。
3 铜介导肿瘤细胞死亡的机制
根据研究发现,铜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介导肿瘤细胞死亡,首先是氧化应激反应:铜介导的芬顿效应(Fenton)或抗氧化分子消耗,造成活性氧(ROS)水平升高,从而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并加速细胞凋亡;其次是抑制泛素-蛋白酶体系统:铜与蛋白酶体亚基结合,导致泛素化蛋白质积累;再者是抑制血管生成:铜耗竭会抑制新血管的形成,从而切断对肿瘤组织的营养供应;接着是目前最新提出的铜死亡:铜直接与三羧酸循环(TCA)中的脂酰化成分相结合,引起脂酰化蛋白质聚集和铁-硫簇蛋白的损失,从而发生蛋白质毒性应激,最终诱发细胞死亡[15]。
3.1 氧化应激反应 氧化应激反应是一种有效的肿瘤杀伤方式,其最基本的原理为氧化剂-抗氧化剂失平衡,主要表现为ROS 浓度短期甚至长期升高,ROS是正常氧化反应的代谢产物,是一种含有氧自由基的高活性化学物质,中低浓度的ROS可以维持许多基本的细胞功能,然而高浓度的ROS对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都是有杀伤作用的[16]。因此,通过提高肿瘤细胞中的ROS 浓度从而杀伤肿瘤细胞可能是癌症治疗的一种有效方法。Cu2+通过Haber-Weiss 反应还原为Cu+,Cu+介导芬顿效应产生最活跃的羟基自由基,从而升高肿瘤细胞中的ROS浓度,促进肿瘤细胞死亡[17]。谷胱甘肽(GSH)是体内的一种特异性抗氧化剂,GSH相关的抗氧化防御系统(ADS)可清除细胞内的高活性羟基,从而抵御有害物质对细胞的破坏[18]。然而,铜可以将肿瘤细胞中的GSH氧化为谷胱甘肽二硫化物,还原性GSH被大量消耗的同时,肿瘤细胞ADS防御有害物质的能力下降,为抗肿瘤治疗提供了有利的有条件[19]。线粒体是维持细胞呼吸作用和能量产生的关键部位,高浓度的ROS可以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间接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20]。研究结果表明,铜离子载体可以通过细胞的质膜或线粒体膜结构转运铜离子,伊利司莫(elesclomol,ES)是一种铜离子载体,可将铜选择性转运至线粒体中,引起局部ROS 浓度上升,从而导致线粒体功能丧失,最终诱导肿瘤细胞死亡[21]。其具体机制为线粒体中的铁氧还蛋白1(FDX1)可将elesclomol结合的Cu2+还原为Cu+,线粒体释放的Cu+与分子氧反应可产生超氧化物,该超氧化物会歧化产生过氧化氢,过氧化氢可进一步与Cu+反应产生更有破坏性的羟基自由基[22]。铜离子与载体结合,从而产生羟基自由基,进一步引起活性氧浓度升高,最终诱导细胞死亡,因此,将铜离子载体应用于抗肿瘤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铜离子载体在不同的癌症中诱导的细胞死亡途径往往是不同的,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铜离子载体针对不同癌症诱导的具体细胞死亡途径的相关研究能有进一步的突破,从而将铜离子载体更好地应用于癌症治疗。
3.2 抑制泛素-蛋白酶体系统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the 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UPS)是真核生物蛋白降解的主要途径之一,参与调节细胞周期、增殖、凋亡等,对于维持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有着关键作用[23]。泛素化是指通过泛素对目标蛋白进行标记,蛋白酶体特异性识别目标蛋白并将其降解,蛋白酶体是蛋白质的小复合体,大小与核糖体相似,26S蛋白酶体仅存在哺乳动物中,由一个20S 核心颗粒和两个19S 调节颗粒构成,20S 核心颗粒中包括β1、β2、β5三个亚基,分别控制半胱天冬酶样、胰蛋白酶样、糜蛋白酶(CT 样)活性,其中β5 亚基是调控细胞凋亡的关键亚基[24]。研究表明,相比正常细胞,癌细胞的增殖更需要蛋白酶体的参与,一些过渡金属的络合物对蛋白酶体的抑制具有较强的作用,双硫仑(DSF)是一种获得FDA批准的治疗酒精中毒药物,DSF在胃酸等酸性条件下可转化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酯(DDC),DSF和DDC都是二价过渡金属离子的强螯合剂,DSF或代谢物DDC 与铜形成的结合物对于许多癌症中的功能性蛋白酶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5]。DSF体内代谢产生二乙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铜复合物(CuET)靶向蛋白酶体上游的p97-NPL4-UFDI 信号通路,CuET通过结合NPL4发生聚集并抑制p97依赖性蛋白酶体的活性,导致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在细胞中积累,最终促进细胞死亡;此外,细胞实验结果提示:分别用CuET复合物和蛋白酶体抑制剂处理的细胞表型特征相似[26]。NF-κB 是重要的转录调节因子,蛋白酶体参与抑制分子(IkB)的降解,从抑制复合物中释放NF-κB p50/p65异二聚体,最终转移到细胞核中发挥其转录调节因子的功能,因此蛋白酶体的活性对于NF-κB通路的激活非常重要[27]。除了硼替佐米等蛋白酶体抑制剂外,还有很多药物通过与铜结合形成铜络合物,通过抑制泛素-蛋白酶体系统而用于抗肿瘤治疗,例如:席夫碱、氯碘羟喹(CQ)、8-羟基喹啉等[28]。
3.3 抑制血管生成 新血管以多步协调顺序形成,主要包括血管基底膜的破坏、细胞外基质内皮细胞的迁移和增殖,以及血管的形成。铜在血管生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生血管形成有利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铜的促血管生成活性的主要机制是多种细胞因子和蛋白质通过多方面作用而触发的血管生成反应的激活和放大,这些蛋白质包括血管内皮生成因子(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血管生成素(ANG)[29]。在血管生成的早期阶段,细胞内铜已被证明可以稳定缺氧诱导因子(HIF-1)的生物结构,从而确保其对血管生成基因(VEGF 和铜蓝蛋白基因)的转录活性,血浆铜蓝蛋白是一种血清球蛋白,通过与铜离子结合,刺激新血管生成[30]。血管生成素是一种分泌蛋白,通过多种途径调节不同的血管生成步骤,细胞实验证明铜可增加人脐静脉内皮(HUVEC)细胞系中ANG 的表达水平[31]。经典的促进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和ANG可促进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在肿瘤的进展和转移过程中有着关键作用,然而这种现象的发生离不开铜的参与。鉴于此,通过降低细胞内的铜离子浓度或抑制铜转运过程中的相关蛋白,从而抑制血管的形成,进而抑制肿瘤的增殖和转移渐渐成为了肿瘤治疗的一种新思路。铜螯合剂抑制癌症的机制通常归因于它们对肿瘤血管生成的抑制作用,四硫代钼酸盐(TTM)是一种高度特异性的铜螯合剂,以前作为一种铜消耗剂而应用于威尔逊病的治疗,其抗肿瘤功效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被人们所发现,因其可抑制肿瘤的血管生成而被作为转移性肿瘤的一种新型疗法[32]。TTM诱导的铜缺乏可能通过抑制缺氧诱导因子发挥作用,从而阻断缺氧反应和相关的VEGF上调,进而抑制血管的生成[33]。免疫疗法是癌症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通过将免疫治疗药物与铜螯合剂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治疗药物,从而提高药物疗效,让更多的患者获益。RPTDH是一种铜螯合螺旋梳状嵌段共聚物,R848是一种免疫反应调节剂,RPTDH/R848 多功能纳米颗粒通过结合抗血管生成和免疫激活而被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34]。
3.4 铜死亡 在过去的研究中,大部分人认为铜诱导的细胞死亡主要是由铜对线粒体作用产生ROS引起,直至2022年3月,Tevetkov等[15]首次提出人体细胞中存在着一种新型的细胞死亡方式,该种细胞死亡方式不同于既往已知的形式(凋亡、坏死、焦亡、铁死亡等),其依赖于细胞中的铜离子,并受铜离子诱导,可调节性细胞死亡——铜依赖性死亡(cuprotosis),简称“铜死亡”,它表明即使已知的细胞死亡方法被阻断,铜也会诱导细胞死亡,铜诱导细胞死亡机制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铜死亡主要受FDX1介导的蛋白质脂化作用调节,FDX1 是一种参与多种氧化还原反应的铁硫蛋白,其作为细胞色素p450 的单加氧酶,参与类固醇的生成[35]。铜离子载体ES 和DSF 引起细胞中铜离子过载,铜可以直接与线粒体呼吸中DLAT 等在三羧酸循环(TCA循环)中被FDX1修饰的脂酰化蛋白结合,诱导脂酰化的DLAT 发生寡聚反应,寡聚化的DLAT 可引起细胞毒性反应;此外,FDX1 可将Cu2+还原为毒性更强的Cu+,从而降低铁硫簇(Fe-S簇)蛋白的稳定性,两者共同作用引起蛋白质毒性应激,最终导致细胞死亡[4]。根据研究结果显示,FDX1 是与ES 敏感性最相关的基因,其可通过直接与ES-Cu结合从而抑制Fe-S簇的形成,进而诱导细胞死亡;然而,通过降低ES 的铜结合能力时,ES 触发的细胞死亡效应显著下降,在完全去除铜结合能力后,不携带铜离子的ES不能独立导致细胞死亡[36]。此外,更多依赖线粒体呼吸作用的细胞对铜死亡敏感,研究者通过使用线粒体呼吸链抑制剂,如寡霉素(ATP酶抑制剂)、FCCP(线粒体解偶联剂)、抗霉素A和鱼藤酮(电子传递链抑制剂)来测量耗氧率(OCR),从而明确线粒体呼吸中与铜相互作用的具体成分,OCR结果显示呼吸备用能力显著降低,然而基础呼吸和ATP产生的相关呼吸过程未受影响,由此可见铜直接与三羧酸循环的成分相互作用并引起DLAT 发生寡聚,而与电子传递链和ATP 合成组件无关[15]。此外,FDX1 是蛋白质脂化的上游调节因子,通过敲除FDX1 可完全抑制蛋白质脂化从而阻断铜死亡。硫辛酸(LA)是线粒体代谢中氧化脱羧的关键物质,铜死亡相关基因LIAS、LIPT1在LA通路中有着重要作用,两者表达的蛋白可介导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PDC)转录后的硫辛酸修饰,这对于维持正常细胞活性和铜死亡都是十分关键的[37]。LIAS 的表达水平往往与癌症患者的预后有着密切联系;通过敲低LIPT1 基因的表达,可以有效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阻断侵袭作用[38]。DLAT、DLD、PDHA1 和PDHB2 是PDC的三个亚基,PDC通过三个亚基的相互作用产生乙酰辅酶A 和NADPH,从而控制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这三个亚基在铜死亡过程中非常重要,其表达水平也被认为与癌症预后相关[15]。
4 铜介导的细胞死亡在结直肠癌治疗中的应用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铜与肿瘤有着密切联系,异常的铜水平成为癌症治疗的新目标,因此,深入了解铜与CRC之间的关系,为CRC的治疗开辟新的路径,这对于改善CRC 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影响机体铜稳态来治疗癌症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思路:第一:通过含铜化合物或铜离子载体增加癌细胞细胞的铜含量,从而诱导细胞死亡;第二:通过铜螯合剂降低癌细胞的铜水平,从而抑制铜依赖性细胞增殖。
铜离子载体或含铜化合物可增加癌细胞的铜含量,从而驱动氧化应激反应,最终引起细胞死亡。常见的铜离子载体包括DSF、ES、CQ 等,DSF 可上调细胞内的活性氧浓度、抑制泛素-蛋白酶体系统活性、抑制肿瘤干细胞等而被应用于抗肿瘤治疗[39]。DSF可以与铜发生反应,形成双硫仑/铜(DSF/Cu)复合物,DSF/Cu 复合物可通过抑制NF-κB 的活性,从而逆转结肠癌细胞系和乳腺癌细胞系对化疗药物吉西他滨的化学抗性[40]。此外,DSF/Cu复合物还可以通过抑制NFκB的活性,从而抑制肿瘤细胞从上皮细胞到间充质细胞转化(EMT)[41]。实验研究结果表明,DSF/Cu复合物还可通过上调Unc-51样自噬激活酶1(ULK1)从而诱导CRC 细胞发生自噬反应,进而抑制其增殖[42]。此外,CuET通过miR-16-5p和15b-5p/ALDH1A3/PKM2轴介导的有氧糖酵解途径降低葡萄糖代谢,从而抑制CRC的进展[43]。ES通过将铜选择性转运至线粒体中,引起局部ROS 浓度上升,从而导致线粒体功能丧失,导致CRC 细胞死亡;此外还可通过促进胱氨酸/谷氨酸反向转运蛋白(SLC7A11)降解和增强氧化应激而诱导CRC细胞发生铁死亡[44]。
铜螯合剂通过降低细胞的铜水平而抑制细胞增殖,铜螯合剂既往被应用于铜积累综合征的治疗,近年来,铜螯合剂在癌症治疗中的功效得到证实,其主要通过抑制血管生成,从而抑制肿瘤的增殖和转移,目前TTM、D-青霉胺(D-pen)、曲恩汀等铜螯合剂已用于结直肠癌治疗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TTM 通过影响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和2(ERK1/2)的不同磷酸化水平,进而影响存在v-raf 小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系物B1(BRAF V600E)突变的人CRC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并有效降低癌细胞的克隆形成潜力[45]。临床试验发现,CRC患者将TTM与化疗药合用,可以有效降低铜离子含量并维持血清铜蓝蛋白水平,从而延缓肿瘤进展[46]。D-pen 是一种还原性铜螯合剂,可减低铜对蛋白质的亲和力并使其螯合,从而使铜耗竭,进而抑制癌细胞增殖;此外,还可通过抑制LOX 的活性而抑制VEGF 的表达,抑制肿瘤血管形成[47]。近期有研究者通过将N-(吡啶-2-基)乙酰胺基团结合到噻吩并[3,2-c]吡啶核中,合成了一种新的铜螯合剂,命名为JYFY-001,通过细胞实验发现JYFY-001可以特异性结合细胞内的铜离子,从而抑制糖酵解和线粒体呼吸,促进CRC 细胞的死亡;此外,JYFY-001可以促进结直肠癌移植肿瘤模型的组织及外周淋巴细胞浸润,发挥免疫调节功能从而抑制肿瘤生长[48]。JYFY-001提供了一种使用铜离子螯合剂治疗CRC的新方法;此外,JYFY-001也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等免疫抑制剂治疗CRC 的重要辅助药物。铜螯合剂是一种较为经济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延缓疾病进展和控制肿瘤扩散,在未来有望广泛用于CRC的抗肿瘤治疗。
众所周知,癌组织主要通过有氧条件下的糖酵解获取能量,大约一半的三磷酸腺苷(ATP)由癌细胞的warburg 效应(有氧糖酵解)产生,warburg 效应可促进癌症转移和重塑肿瘤微环境[49],通过抑制有氧糖酵解可有效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这可能与糖酵解被抑制后癌细胞通过氧化磷酸化获取能量从而增加TCA循环活性,最终引起铜死亡有关。衣康酸4-辛酯(4-OI)是TCA循环的代谢产物衣康酸盐的酯衍生物,4-OI 通过靶向糖酵解关键酶甘油三磷酸脱氢酶(GAPDH)从而抑制有氧糖酵解[50]。Yang 等[51]通过体外实验用4-OI抑制乳酸生成和GAPDH活性,用2DG(一种糖酵解抑制剂)靶向己糖激酶,两个实验分别抑制CRC细胞有氧糖酵解,均能促使癌细胞通过氧化磷酸化产生能量,从而增加线粒体TCA循环活性和对铜诱导细胞死亡的敏感性,最终引发CRC 细胞的死亡,结果表明抑制癌细胞有氧糖酵解可提高铜死亡的疗效,这将会是一种潜在的治疗方法。此外,该实验组用ES-Cu 分别脉冲处理CRC 细胞和奥沙利铂耐药细胞系,结果表明ES-Cu可有效抑制CRC细胞和奥沙利铂耐药细胞系的活力,因此,将ES-Cu应用于化疗药耐药的CRC患者可能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
对于已发生转移的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现有的治疗方案极为有限,通过使用抗VEGF-A 和抗EGFR抗体进行靶向治疗,可以提高总生存期,然而,研究表明许多CRC 患者带有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这是抗EGFR 治疗的阴性预测标志物[52]。KRAS 突变的CRC 细胞通过巨胞饮作用获取铜从而促进癌细胞的增殖,并通过上调细胞表面的ATP7A的表达以保护CRC 细胞免受铜毒性侵害,由此可见通过铜代谢可以治疗伴有KRAS 突变的CRC[53]。研究者通过运用CRISPR/Cas9 技术验证ATP7A 对调节KRAS 突变的细胞内铜水平及细胞增殖的作用,结果表明KRAS 突变细胞依赖于高铜水平,铜的生物利用度是一种KRAS选择性弱点,ATP7A抑制剂可能通过加剧铜毒性特异性靶向KRAS 成瘾的CRC 细胞[54]。尽管ATP7A 相关抑制剂尚未在临床中应用于CRC靶向治疗,但这为未来针对KRAS突变的CRC患者的治疗指明了方向。
5 展望
铜在许多生物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铜稳态是机体生命活动正常进行基础,作为一种常见的癌症类型,CRC的发生发展与细胞中的铜离子水平失衡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通过靶向改变铜离子水平成为治疗CRC 的潜在选择。然而,目前的研究几乎都仅限于CRC与铜状态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明确CRC与铜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推动铜相关治疗在CRC中的应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深入探索纳米颗粒在细胞器中特异性铜耗竭或特异性铜转运的相关机制,运用纳米制剂特异性降低细胞中的铜离子水平从而抑制癌细胞增殖,或升高细胞细胞中铜离子浓度从而诱发氧化应激杀伤癌细胞,对癌细胞进行精准杀伤,可避免正常细胞的破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产生。此外,使用测序深入研究药物输送和药物再利用中的铜状态,将化学治疗、免疫抑制治疗等药物与铜离子载体、铜离子螯合剂联合应用,从而有效改善CRC 患者的预后,延长生命周期,降低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