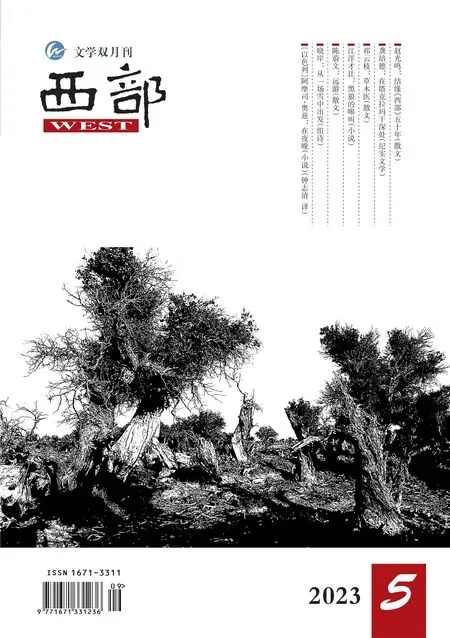锡婚宴
丁奇高
一
宴会设在一个免门票的景区里。景区很大,挂着“AAA”级的牌子。周边广袤的荒滩地里种满了常青树,郁郁葱葱的。
我进去以后,跟着指示牌,绕了一大圈才找到地儿。
一座农家饭店掩映在茂密的小树林里,像是扩大版的“四合院”。一身喜庆的迎宾小姐领我到达宴会厅。她精致的高跟鞋在我前面发出“嗒嗒嗒”的响声。我突然有点儿后悔来这里了。
宴会厅的背景屏幕上是一家三口的巨幅合影,照片像是在某个公园的草地上拍的,上面的一行大字写着:爱在你的左右。我虽近视,却一眼就看懂了这行字的寓意。三个男人从我身边经过,他们边走边谈,中间那个就是今天的男主人向左。他居然假装没有看见我。
白色衣裙搭配平底编织凉鞋。我从来没有这么穿过。也难怪。
真是不该来这里见证别人的锡婚。
前面的几排椅子上人已经坐满了。过道上几个小孩子拿着气球,举着扎了羽毛的魔法棒四处乱跑。一个小姑娘嘴里喊着:“别过来,黑暗女巫。”只见她东跑西跑,最后躲在了一张椅子后面。我悄悄走过去坐下,对她眨了眨眼睛。她蹲到地上,一只手抓住我裙子的一角,另一只手捂着嘴笑。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小时候偷吃甜果子,而妈妈却毫无察觉,仍旧拎着果子盒带我去串亲戚的画面。
“陈旭,你早来了呀。”是吕丽,是个上身异常丰满的大美女。
“我也是刚到,不过你小声点儿,我正在掩护在逃公主呢。”
小姑娘见有人来了,嘴里叫着“奶奶,奶奶”跑开了。她是向左哥哥的小女儿。
吕丽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时我们住一个宿舍,像是影子一样整天黏在一起。近一年不见,她消瘦了许多,下巴上冒出一堆奇怪的小痘痘。
“瘦了啊,只是你这脸?莫非是迎来了第二春吗?”
“哎,一言难尽,怎么说,算是辣椒吃多了吧。”
“你们都来了呀。”向左朝我们走了过来。他那张脸白净、帅气。看得出来他今天精心收拾过。“吕丽可是出过国的女人,见多识广,不好伺候。”
“我哪儿不好伺候了?”吕丽撇撇嘴,“你这是推卸责任,想轻易就把我打发了?今天你这锡婚宴的酒必须给我备足了,姐姐我不醉不归。”
“管够,晚上你们睡我家里。”向左笑嘻嘻的。他看了我一眼,马上扭过头去。前面有人叫他,我和吕丽示意他快去。
舞台上主持人开始讲话,宾客们渐渐安静下来。
吕丽凑到我的耳边说:“向左的媳妇看起来不像有那种病的人呀!”
“那是一种慢性病,照顾得好,十年八年死不了人。”
“她挺可怜的。”
我拍了一下吕丽的屁股,发现她的皮肤异常松弛。
主持人请今天的女主人谈谈感受,女主人声音很小显得有气无力,说了没几句,眼泪便“滴滴答答”落了起来。
二
向左的媳妇家有姐妹三个,她在家排行老三,小名三儿。我跟前夫没离婚时,她跟着向左来过我家,那时她还没有得病,看起来楚楚动人,我揶揄向左捡了个大便宜。
她婚后患上了红斑狼疮,致使五个月大的婴儿胎死腹中。
我的第一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七年,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前夫看不惯我的生活方式。他训斥我都结婚生孩子了怎么还整天做着文学梦。我们离婚的导火索是一套《博尔赫斯全集》,当时花了三百多块钱,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前夫为此气恼不已,伸手打了我。
“陈旭,你看,”她嘴里不知什么时候含着一颗糖,我闻到了是薄荷味的,“向左怎么还跟棵杨树似的戳在那儿,三十七岁了也不发福。”
的确,台上站了十几个人,都是他们一大家子的。向左的媳妇三儿个子不高,穿了高跟鞋勉强一米六,向左妈更低,向左的哥哥矮胖。三儿身边的小男孩大约五六岁,是向左的儿子向右。还有刚才那个小姑娘,一直被她奶奶扯着小手。
“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向左还是个小不点。”我感叹。
“可不是吗,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吕丽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我和向左高二坐过一年同桌。那个时候他身高不足一米五,长着一头细软发黄的头发,小脸蛋,深眼窝,说话奶声奶气的,跟个洋娃娃似的。
我在家挨揍,向左在家挨过的揍不比我少。扇脸、罚跪、拧大腿,即便挨了揍,他哭也是错不哭也是错。我们的友谊就是在互相倾诉自己受过的疼痛中建立起来的。
但仅仅过了一个并不漫长的暑假,高三开学时再见到向左,他竟然长成了一根旗杆,身高足有一米九,那张拉长的丝瓜脸扭曲得让人不忍心看。
三
吕丽给我看她发的朋友圈,配的文字是:别人的锡婚,有白金钻戒,我的呢?
我笑她真是个爱慕虚荣的家伙。
“这点虚的都不敢,还活个什么劲儿,可活到今天什么都变了。”
这女人今天怎么多愁善感起来了。
向左的儿子向右两岁大的时候,三儿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引发股骨头病变住了院,向左的母亲不愿意照看孙子,向右在医院里哭闹个不停,情急之下向左给我打电话求救。我撂了电话,拿了个毛绒玩具塞进包里就往医院赶。
我到了医院大吃一惊。三儿很年轻,却因为长期服用激素,面部严重浮肿,眼睛几乎睁不开了。她躺在病床上,见到我只说了一句“陈旭来了”,就不再开口。我知道她很痛苦。
我蹲下来跟向右打招呼,掏出毛绒玩具。他一下子扑到了我怀里。
那天我深深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男人负担其实挺沉重的。
那时我的第一段婚姻刚刚结束。我以净身出户的形式换得前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尽管办离婚证的几块钱也是我出的,但三十一岁的自己终于重获自由。我对着蓝天深吸了一口气。
我从小恨我的父亲。他为了让母亲生儿子不惜毁了她的身体。
当初我和前夫结婚只是想从家里逃出来而已。前夫比我大十四岁,我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他。
婚后我有三年没有回过娘家。
四
“仪式结束了,咱们去趟洗手间,回来就该吃饭了。”吕丽撩了撩头发,枯黄的脸上展露出一丝笑容。
“看不出来向左挺浪漫的,给媳妇办锡婚宴,还送白金钻戒,真让人羡慕。”我说。
“的确,这样的老公,全国也找不出来几个。就是这家伙一见面就夸人家胸大,我总以为他是想揩我油呢。”吕丽挺了挺她的F 杯。
“现在又想被人家揩油了?”
“去,你个女流氓。”
我在洗手间门口等吕丽。洗手台很干燥,镜子上看不到水珠。我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今天化的淡妆,耳边垂下来一缕头发。
我和向左一起考上了本地的大专——言午学院。当年言午市的文化宫影院名字听起来很官方,却是南方来的一个私人老板运营的,过了十二点后,影院就会播放一些外国影片来吸引观众。向左带我去看过。我不敢睁眼,只听声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向左坐在旁边,不停地开导我,说我早晚要长大的。然后,我就看了一点,再然后周末没事他就约我去看夜场电影。
事实证明性启蒙是有必要的,这让我对男朋友这一物种有了更多的认识。很快,我就和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生好上了,向左则如同消失了一般。
“一个人在这儿干啥呢。”
我扭头一看,是向左。
他一边洗手,一边盯着镜子,他说:“在镜子里,你也能看见我的脸。”
“镜子里的有什么用?”我笑着问。
“你还是不戴首饰?都快奔四了,也该戴了。”他没有搭我的话茬,而是谈起了世俗的东西。
有几滴水从他手里甩出来溅到了镜子上。
“我不稀罕那些东西。”我回答。
“三儿喜欢那些东西,今儿又送给她一枚白金钻戒,”他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今天你很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我问。
“是太迷人了吧!”吕丽出来了。我往后退了退,腾地儿让她洗手。“不但迷人,俺们陈旭还有才,从高中起就是个才女,还嫁了个作家。”
“就你话多。”我有些生气,空气一时变得有些凝滞。
吕丽低头摆弄手上的甲片,向左趁机摸了我的脖颈。
“走吧,吃酒去,猪场的左经理。”吕丽说。
“不敢当不敢当,我胆子小,两位美女先走。”
吕丽当然知道我和向左的一些关系,但她的理解存在偏颇。第一段婚姻破裂以后,我过了三年多的单身生活,向左曾不止一次发出暗示,只要我“需要”,他可以随叫随到,但我拒绝了。
有一次我梦见了一个死人,我趴在那人身边痛哭,死人的床板太低,后来我想挪一下身子,一瞬间来了一个男人,他说着话,但他说的是什么,我却完全听不见。他是向左。
前夫的母亲找人带话,让我和她儿子复婚,她说离婚的女人就是一张破报纸卖不上好价钱,她儿子有房有车随时可以再找一个,到时候我后悔都来不及了。我没有理睬她。前夫是个妈宝男。
起床后我浑身酸痛,精神不振,就去了出租屋门口的美容店推背。
“波颜国际”美容店的女老板很会聊天,一顿东拉西扯后,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女人得学会花钱。
离过婚的女人应该让自己更美,这是她的原话。我接受了她虚伪里掩盖着的真诚。我让她把我的杂眉修掉,她说我这野生眉太粗犷,一点儿不精致,这次她要免费带给我美。我一咬牙一狠心在她那里充了一万块钱的卡。
五
向左大学宿舍的舍友只有老七来了,他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我离异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没想到见面时居然是老七,我们不由得感慨言午市真是小啊。
大家聊的大都是和向左有关的事,他的牌技,他如日中天的养猪生意。
“向左你快过来,我非要问问你高二那一年暑假,你到底吃了什么好东西,怎么突然就长那么高了?你今天必须给大家解释一下。”吕丽发问。
“肯定是吃了‘壮壮精’(一种速成猪饲料的名称)。”有个满面红光的中年男人接话。
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做怪梦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向左见了一面。他把我拉到他厢式货车的驾驶室,问我:“快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哪有,是人家非要娶我。”
他摇下车窗玻璃,掏出一支香烟塞到嘴里,手里握着火机,却没有点燃。
“可以啊,陈旭。”他语气里有些不屑。
“志趣相投,不分年龄,再说我只比他大六岁,我爱读书,他喜欢写小说!说真的,我本来以为我这一生再也不会结婚了。”
“快给我讲讲。”
“我倒是希望收到像沈从文写给三三那样的情书,但他至今没给我写过呢,也许以后会写的,不急。”听到三三,他愣了一下。我说:“那个三三可不是你的宝贝三儿。”
他没有听懂,但把两条腿朝我靠了靠,想拉我的手,我用力甩开了他,然后我指了指自己凸出来的肚子。
“你又怀孕了?”他吃惊地问。
“是啊,四个月了,胎儿很稳定了,前几天在医院做了四维彩超,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他又想摸一下我的头,我下意识地躲开了。我从车上下来了,我的身子尚不到笨重的时候。
我们简单地聊了以前、现在和将来,情绪都有些伤感,交流变得索然无味了。我和他仿佛一直都没有长大。我该走了。
我对向左说:“今天见到你,很想告诉你,要好好照顾你媳妇,不可以再对不起她。”
“就告诉我这个?”他反问。
“是啊,你以为是来闻猪肉味的?”
“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三儿离婚的,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六
“不好意思啊大家,如有招待不周,请多多包涵。来,三儿,给哥哥姐姐们倒酒。”向左领着媳妇过来了,三儿刚刚哭红了眼,妆都花了。
“你们能来是我们的荣幸,我不敢喝酒,以茶代酒敬大家了。再次感谢大家照顾俺家向左的生意。”
向左的一只胳膊始终贴在她的后背上,显得十分亲昵。
老七掏出一个大红包塞到三儿手里。他说这是宿舍七位兄弟们的心意。向左在三儿耳朵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三儿收下红包,走过去和老七抱了抱,老七的脸顿时臊得跟红盖头一样。老七三十八了,离我们上次“相亲”过去三年多了,仍旧没有找到对象。
轮到我和吕丽时,向左接电话去了,三儿过来敬酒,我表示酒量不行,吕丽也说不会喝,我们俩本想和三儿以茶代酒,不料坐在吕丽旁边的啤酒肚男起身慷慨相助,他舔舔嘴唇替我们喝了,说好东西不能浪费,喝完还不忘加了吕丽的微信。
几个大男人拿起话筒:“我对你爱爱爱不完,昨日像那东流水……”一听就是暴露年纪的老歌。一直热闹到下午四点多,宴会才陆续散场。
我问吕丽能不能多玩一会儿,我和她虽然都住在言午市,可一个住大南边,一个住大北边,见一面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们去划船吧?”我提议。
“就咱俩?”吕丽问。
“你还想要谁去?那个啤酒肚男?”
“NO,他不行,吨位太大,不安全。可以喊上你的大作家,让我深度了解一下。”吕丽一脸狡黠。也许是她闻酒气多有点上头了。
“他在家看书,不爱凑这些热闹,我喊不出来的。”我说。
“是喜欢和你单独相处吧!不见了,不见了,真是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你可真不够意思了。”
“怕你有非分之想呗。再说一见你,万一他忍不住诱惑呢?”我笑嘻嘻地回答。
我拉着她向码头走去。她一看见船,像个小姑娘似的,欢呼雀跃起来。
坐船的人还挺多。我们排了一会儿队,才等上了一条绿色的四人座脚蹬船。
双洎河的一截河水被一座水泥大坝拦起来,汇聚成了一个猪耳朵形状的水库。有本地人依托水库修了个景区,发展起了旅游业。景区里建设了水上高尔夫、跑马场、游泳池、游船、钓场等设施,又引进了民俗园、红色教育展馆、儿童乐园、网红秋千、乡村食堂等特色项目,吸引了周边很多人前来游玩。
我们脱了鞋把脚伸进河水里。小船随着水流任意东西。
“我想我还是告诉你吧。”吕丽一脸郑重,令人不太适应。我沉默不语,等她说下去。
“我决定去做手术了。”
“手术?什么手术?”我好奇地问。
“左胸全切,乳腺癌中晚期。我本来下不了决心,我怕就算切了也活不了多久。可现在不切的话,怕癌细胞扩散,我会很快死掉。我舍不得女儿,她那么可爱。活着多美好呀,陈旭。”
吕丽看着水面上的夕阳,面容生动。
我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小船短暂失去平衡产生一阵晃动。
“切,明天就切。你那大圆球,太气人了。等一下,我能再摸摸吧,以后就摸不到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占便宜。”
“割一个,我就不嫉妒你了,吕丽,我想要你活。”
我们一定是笑得太大声了,惊动得水面起了风,浪头多了起来。
吕丽高中落榜后,身为包工头的父亲花大价钱让她上了四年的外语学院学习商务英语,她毕业后去了上海,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认识了马来西亚商人拉吉。拉吉十四岁就出来闯荡世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英文和泰文,吕丽经不住他的爱情攻势,很快就和他同居了。他们办理了旅游签证,四五年间,她跟着拉吉辗转去过澳大利亚、泰国和美国。他们在塔斯马尼亚州摘过苹果,在曼谷当过导游,在纽约的一家孔子学院代过汉语课,后来他们又在吉隆坡生活了三年多。两人一度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拉吉曾在一个夏天跟着吕丽回农村老家商量婚事,拉吉害怕蹲坑里蠕动的白虫子,吕丽的父亲特意在自家的楼上为拉吉修了个厕所,崭新的抽水马桶专门供他使用。两人最终没有结婚。
分手后,吕丽从马来西亚回来了。已经三十一岁的吕丽成了村子里的大龄剩女,她不得不面对迫在眉睫的婚姻问题。家里人比她还要着急,由于十里八乡都知道她过去的事情,没有一个媒人愿意上门提亲。一年后,她仓促地嫁给了初中同学宋伦,当时她的父母没有要一分钱的彩礼。
宋伦曾经追求过吕丽,那时候的吕丽家庭条件好,穿着又时尚,吸引了一众男生的目光,甚至有不少校外的青年等在学校门口看她,那会儿她根本看不上宋伦,没想到宋伦竟然在她寝室楼下用削笔刀割腕了。
尽管口子不深,只流了一点儿血,却在学校里产生了不少议论,宋伦后来患了抑郁症。他初中没上完就去读了技校,毕业后在外地的一家水力发电站维修发电机。
同学聚会上,吕丽见到了仍旧单身的宋伦,两人闪婚。
婚后,吕丽跟着宋伦在发电站的职工宿舍里住过一段时间,她怀孕后回到了家里。随着女儿的出生,她没有再出去工作,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宋伦在外上班,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两人聚少离多,他经常连句话都不和吕丽说。
五六年下来,吕丽过得并不快乐。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她偷偷想念过拉吉。我自然明白,女人类似“丧偶式婚姻”的日子当然是不好受的。所以,我才劝她多带着女儿出来走走,只当是散散心,但她已经习惯宅在家里了。这次她能来向左的锡婚宴倒是个意外。
我们刚上岸,就看见向左朝我们走来。吕丽说她得赶紧走了,回去通知家人今天晚上就去省城住院。她走得太急,差点儿撞到河边的一棵柳树上。
“她怎么了?”向左问我。
我不说话,一个劲儿地流眼泪。
吕丽的背影很快消失了,我怕她再也不会出现了。
西边的太阳正在一点点坠落,阵阵的晚风裹着浓稠的鱼腥味。
“吕丽得了乳腺癌,必须尽早切掉一个,只有切了才有可能活。”我的大脑不自觉地在回放着……
那不是梦境,而是真实存在着的。
“要相信奇迹,乳腺癌中晚期存活率挺高的,切了就好了。”向左惋惜地说。
“吕丽,求你不要离开我。”我哽咽着,试图把声音吞没在自己的喉咙里。向左不知何时浅浅地抱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