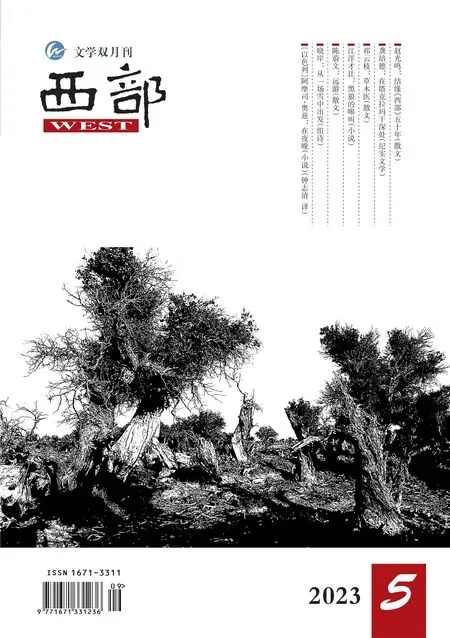草木医
祁云枝
尽管天天和草木打交道,我依然不能完全了解它们。我或许能说出它们的尊姓大名、产地和生态习性,却无缘知晓流动于草木里的诸多神迹,诸如,藏匿在根、茎、叶、花、果里莫测的气力,是如何通过一碗水的煎熬,击败横行于人体里的病、毒、伤与痛的?
有段时间,我常站立窗前,呆望楼宇间的天空,偶尔看到如小时候的蓝天白云时,思绪便活泛起来,那些童年里被郎中或母亲拣选,用来治病救人的本草,纷纷从记忆里伸枝展叶,与头顶的蓝天白云对接起来。
荞麦
这个秋天,在一处名为“荞麦花海”的山头,我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同乡。看到它们,我笑了,它们也在笑,笑容,是以花朵的方式绽开的。
一座山伏下身躯,驮起一条螺旋状多彩的河流,翻卷出粉红、碧绿、紫红的浪花,每一寸山冈都柔情蜜意。扑面而来的浪花里,我闻到了曾经生活过的村庄的味道。
迫不及待地向荞麦花靠近,我在年少时就熟悉它们。
当我在荞麦花前站定,我感觉身上的每个细胞“唰”地一下都醒了,齐齐地竖起一片树林,林子里的每片叶子都伸开双臂,想要拥抱荞麦。指甲盖大小的粉色小花,绽放得无所顾忌,开成一嘟噜,连成一大片,天地间便妩媚起来。
这该是乡村旅游推出“荞麦花海”的缘由吧。
和童年一样,站立花前,总想把荞麦花叶织成衣裙穿在身上。眼前这座山,正穿着令我着迷的碎花衣衫——紫红的茎干、三角形的绿叶、粉白的小花,全都嫩生生的。阳光在素雅的衣衫上腾挪,闪耀出巴比松画派的神韵。
一些人和事儿,水流般沿荞麦花蜿蜒而来。
荞麦,在乡下并不多见。它属于粗粮,当年,有限的自留地里,乡人多种植细粮小麦,只在倒茬地或是灾年错过最佳播种期的庄稼地里,才能看到荞麦的身影。荞麦生长期短,从种子落地到收上场,大约七十天,是步履匆匆的庄稼。
荞麦开花的时候,乡村单调的土地上呈现出少有的诗意。由红秆绿叶托举的小白花,瓣顶有从花心炊烟一样洇上来的粉红。至纯至简的五枚花瓣,俨然田地长出的“五言绝句”,蜜蜂在歌咏,蝴蝶在翻阅。风行花朵,摇晃着美妙的诗篇,一句诗“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鱼儿似的从浪花里跳跃出来。
父亲在荞麦地里,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当兵的回乡探亲,看见他大(陕西方言,爸爸)在荞麦地里忙碌,对着满地花朵拿腔拿调,操着普通话问:“爸爸,这红秆秆、绿叶叶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呢?”他大二话不说抡起锄头就打,被打得趔趔趄趄的兵娃子赶紧求饶:
“大,大,甭打咧,甭打咧,你快把我打死在这荞麦地里咧。”
哈哈哈!哈哈哈!荞麦花也乐了,一些花开怀大笑,前仰后合,一些花半掩芳唇,笑不露齿。笑声混合着蜜蜂的嘤嗡在空气中荡漾。
那时年少,荞麦花随心存留,成为令人开心的花朵。之后,看见荞麦花,必想起笑话,也必说给身边的人听,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荞麦花有资格教导一个浮夸之人,让他谦逊,不要忘记家乡的一草一木。
我们渐渐长大,只有荞麦花替我们收藏童年的笑声。
“荞麦最降气宽肠,故能炼肠胃滓滞,而治浊滞、泻痢、腹痛、上气之疾。”这是药圣李时珍说的。
李时珍在壮年时有次患病,肚腹疼痛,如厕便泻,泻也不多,但白天晚上总有多次。淅淅沥沥两个月后,他自感逐渐虚弱消瘦,擅自服用了消食化气的药物,并不见效。凑巧一位高僧听说了,便传授给李时珍一偏方:单用荞麦面一味做面条或做面糊糊吃。李时珍连吃五天,果然痊愈。
李时珍认为,这正是荞麦所谓的“炼肠胃之滓滞”。
我目睹过荞麦治病的能人。那时候,荞麦医病的本领,需得通过五爷才彰显出来。五爷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郎中,擅长推拿。张三脚崴了,李四腰闪了,王麻子胳膊脱臼了,等等,都去找五爷,五爷都能手到病除。
当年,村子里的人似乎都是半个郎中,伤风感冒类的小病没人去医院,大都寻一两味草药解决。在人人皆医的乡村里,五爷无法靠行医养家糊口。五爷家也有麦田菜地,和大伙儿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农闲时,五爷喜欢坐在村子里的大槐树下,一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一边分享些简单实用的祛病良方,他身上有种令人踏实的草木气息。
通常,大槐树下是村子里的聚会厅、饭堂,也兼信息交流站,男女老幼有事没事都喜欢凑过去。饭时,一准儿端着饭碗,手擀面居多,一边吃一边谝。时事新闻,家长里短,还有诸如五爷分享的医病妙招,鸟雀一样从大槐树下飞出,飞入家家户户,钻进更多人的耳朵里。
无论春夏秋冬,大黑的头顶上都戴个厚厚的棉帽子,一刻也不敢卸下——大黑患了头风病。头风,像一柄猎人手中的枪,时时刻刻在暗中窥伺着大黑,大黑用一顶棉帽子躲避,仍不时被头风击中。大黑说他总觉得头顶上有嗖嗖冷风刮过;疼痛,也像无数找不到出口的蚂蚁,在他的头里撞击、噬咬。大黑去过乡医院,诊不出个子丑寅卯。家里没钱,去不了省城医院,大黑只能将就着用棉帽子抵挡。新荞麦上场入仓后,五爷告诉大黑,让他准备二升荞麦面粉,用水调制成两张饼,烘热贴额上,冷了即换,要捂到微微出汗。一周后,大黑终于摘掉了帽子,困扰大黑一年的头风,被荞面赶跑了。
一天,拴全在大槐树下刚吃完一碗面,还没送回饭碗就“哎哟哎哟”地喊叫起来,迅猛之势像一场突发的雪崩,饭前毫无征兆,饭后地动山摇。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一下子扼住了他的命脉。拴全蜷缩在地上,喘着粗气,一会儿说胸闷,一会儿又说恶心想吐,冷汗小溪一样自他的额上流下。五爷从大槐树旁经过,闻讯赶了过来,给拴全切脉后,五爷说:“这是绞肠痧,赶紧回家,取一把荞麦面,炒黄,用水煎服。”拴全媳妇照做,果然奏效。
荞麦面经过水与火的煎熬,似乎一下子有了灵魂,拥有了令人讶异的能量。从入口开始,以秋风落叶的速度走经入脉,融入血液,调整失衡的身体,救人于水火。虽然,我始终都无法参透荞麦治病的秘密,好在,荞麦一直以慈悲为怀。
“三块瓦砌个庙,里面坐个白老道”,草木有灵,居住在黑褐色三棱体荞麦壳里的“白老道”,果然精通自然之力。
这是荞麦之功,也似上天的神谕。
艾蒿
艾蒿,是迄今为止我仍然离不开的一种本草。
艾蒿生长在家乡的沟渠边、河滩上。惊蛰后,艾蒿和白蒿、米蒿一同醒来,一同苏醒的,还有很多被我们称之为野菜的小草。它们伸胳膊展腿,像书法家怀素信笔挥毫,横竖撇拉弯钩,“纵横千万字”的草书,熙熙攘攘,给田野披了层绿衣裳。
新鲜的草木,像新鲜的日子。
父亲在节前启刀磨镰,他要去河滩上割艾。艾蒿的味道一旦在院子里飘散,端午节就来了。
天光擦亮万物时,一大捆带着露珠的艾蒿回家,我和妹妹手脚麻利地选出几枝艾蒿,用马蔺叶子绑好,安插在门楣和柜子上,剩下的,听从我俩的调遣,单排站在院墙边,士兵般齐整。墨绿色的叶面微微卷曲,露出叶背的银白。
浓烈的药香从枝叶间散发出来,在院子里冲撞、回旋。那味道,有香有苦也有辛,说不清到底是香多一些,还是辛与苦多一些,恰如我们的苦乐年华。
艾蒿晾晒到半干时,父亲收拢它们,端坐艾蒿中间,取出两撮在大手间搓揉起来,就那么一捻一搓,一条长长的艾绳逶迤而出。最后,所有的艾蒿都变身绿绳子,在父亲脚前盘踞成一个巨型蚊香。这盘艾草绳晾干后,也的确是我们家整个夏天的蚊香,父亲称之为“火药”。
傍晚,打开门窗,把截取的一段“火药”点燃,放进屋子中央那个盛了草木灰的瓷盆里。
黄昏被黑夜慢慢涂抹,艾绳在瓷盆里明明灭灭,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在腾起的缕缕青烟里,蚊蝇落荒而逃。一屋子艾烟,仿佛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圆圈,什么虎豹狼虫,俱莫敢近,我们安睡期间,夜夜无虞。
端午节当天,母亲还会将早年的艾蒿和柴胡研磨成粉,加入雄黄粉一起缝进用绸缎做成的心形香包里,再用花花绿绿的丝线,履行仪式般郑重系在我们的脖子、手腕和脚腕上;伤风感冒和磕磕碰碰的小伤,在母亲眼里,一锅艾蒿水就能摆平……这世间美妙之事,莫过于人与艾的相爱,艾蒿向荣,人面欢欣。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父母已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是艾,让我这做女儿的,把父母的爱从童年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这是一条“爱”之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让我在某些时刻,很想成为一株传递爱的艾。
如今,艾蒿以艾柱的形式,经常游走在我的皮肤上。
整日里面对电脑,一些疾病不请自来。某天,我的右手腕痛得连点击鼠标这样的动作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我的目光不得不从电脑屏幕上撤离,当我把胳膊肘撑在桌面上,手掌缓缓降下,我发现手腕处凸起了一个疙瘩,花生米大小,圆溜溜,瓷实。待手掌伸直和胳膊成一条线,那疙瘩又不见了,但能摸到,酸、胀、涩、痛,仿佛锈了的滑轮,活动手腕,听得到骨头的摩擦音。
天,这疙瘩是何时移民手腕的?它看我不曾理会,径直以刺痛的方式告知。
时光的利刃,就悬在我们头顶,一直削切着我们的肌体,虽然这利刃看不见摸不着,但削切的结果,隔三岔五就显现了出来。
去寻医问药。医生看了一眼,说:“这是腱鞘囊肿,需手术切除。”
“手术”二字,让我的惊惧陡然升级,我低估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小疙瘩。
我刚想询问,医生的目光把我尚未说出口的话语剪成了碎片。
“可以保守治疗,但有可能会更严重。”见我迟疑了几秒依然点头,医生大笔一挥,写出一串活血、止痛和消炎的药名,吩咐我手腕处要休息少动,多用热水浸泡。
老中医的药方更吓人,他说:“先用火针刺破囊肿,用手按压排出里面的积液,辅助针灸治疗,再贴膏药巩固。”火针刺破疙瘩的画面,想想就叫人战栗,还要加上后续漫长的针灸。临走,我只买了两盒膏药,与其如此遭罪,不如与疙瘩和平相处,先尽量减少右手腕的使用频率吧。
不久,便静默在家。一日上网,见一专家说艾灸可强身健体,散布于空气里的艾草小分子还可杀毒杀菌。突然间想起家里还有一盒艾灸贴,我家先生不喜艾味就搁置起来。我翻找出来征询他的意见,先生说试试吧,比起消毒水,艾草的气味要好闻一些,也环保。
缕缕白烟从抽水马桶状的孔眼里流了出来,在手腕的皮肤处游走片刻,化作细线袅袅散去,患处即所谓的阿是穴感到了温热,空气里也有了少时常闻的艾香。
铅笔粗细的小艾柱上方,清灰一寸寸变长。变短的艾柱、变长的灰柱,与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与年龄的关系何其相似,皆此消彼长。待艾柱燃尽,揭下悬空的底座后,患处颜色泛黄,皮肤上冒出几粒亮晶晶的水珠,这是被艾从身体里拔出来的寒毒吗?
索性天天艾灸。直到有一天,我屈手腕时突然发现那个凸起的疙瘩不见了。是的,它真不见了!那疙瘩仿佛链接上了艾蒿深处隐秘的信号,被艾烟一天天拽走了。手腕,又恢复了从前的灵活。
我晃动着手腕奔向我家先生,喊:“看!好啦,好啦!”厨房里飘来青韭鸡蛋的味道,真香。一定得喝上一盅,小小艾柱把腱鞘囊肿给干掉了,免去了手术与火针之痛,治疗过程优哉游哉,太值得庆贺了。
这一天,距离我第一次艾灸,过去了四十一天。
先生也很吃惊,笑着说他收回从前对这种气味的微词,并吩咐我多买几盒艾柱,他要灸因多次崴脚如今已怕寒怕累的脚腕。
从此,童年结识的悠悠艾香,一次次涨满家里的角角落落。和当年我的母亲一样,一些小毛病,我都用上了艾灸,腰膝酸痛时灸一灸,伤风感冒,也灸一灸。几十年过去了,失散多年的气味,重又停泊在斗室里。
若是萃取艾蒿精神,最恰当的词,莫过于“爱”。或者说,在所有的草木里,只有艾蒿,才配担起这个“爱”字。艾与爱,同音,也同义。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里的这几句情诗,是进入中年后的我,只想说给艾蒿听的。
扫帚菜
有那么几年。我家的菜圃边,种着一排扫帚菜。
春来,扫帚菜的芽尖破土,噌噌噌,一天一个样儿。叶子纤细,细叶儿你拥我挤,争抢阳光和空气,乒乒乓乓,争宠的叶子最终迸溅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球体,毛茸茸,葱郁,远观像一个鹅黄暄软的大丸子。一夜春雨后,它长得更圆、更鲜嫩了,细密的露珠在嫩叶上闪烁,宛然童话里拥有魔法的水晶球。
等这些绿丸子长到篮球大小,就可以采来蒸菜吃。
揪下水灵灵的嫩叶,洗净,撒盐,挤出水分后拌匀面粉,放进大铁锅里蒸熟,用油盐酱醋、葱姜蒜水简单调和一下,吃起来清香绵软,这是田地用阳光和雨水酿造的美味。
在初春的寂静与微寒中,一盘扫帚菜,有着嫩绿的奢华。
岁月里总有一双无形无情的手,把每个生命的青春带走。
还没有吃够扫帚菜呢,那叶子已老得跟柴火一样,叶子间爬满米粒大小的花苞,结出淡黄色疙疙瘩瘩的花朵。主茎增高增粗,侧枝则细细密密地向四面八方伸去,全然一个立体的孔雀开屏。茎干先是被秋风染红,末了,叶子也泛出幽幽的红色,像一位老来俏的妇人,着红衣红裙在风里招摇。一两米的个头,也使它拥有了作为一把扫帚的良好资质。
成年后的扫帚菜茎如铁骨,枝稍柔韧,是天生的扫帚。
初冬,母亲砍下扫帚菜苗,削掉主干底端的枝杈,打磨光滑,再将仅余枝条的树冠压扁晒干,一件趁手的扫地家什问世,看起来像一帧无叶树的剪影,有着嶙峋的美感。母亲也会把一些低矮的扫帚菜枝条绑扎起来,理个平头,用来洗锅,沥水沥油。
大多数时间,扫帚们都乖乖站在我家大门的背后。我和妹妹会在下午放学后,轮换着挑出一把扫帚打扫院落里的落叶,嗤嗤嗤,新扫帚触地的感觉真好。那时,我尚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落叶外的其他垃圾,也不知道,扫帚菜还能扫净被病痛杂染的身体,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麦萍和我同岁,我俩结伴上学,结伴挖猪草。是一个暑假,一种小虫子亲吻了她,麦萍细嫩的脸颊上快速鼓起一个红包。那时候,被蚊叮虫咬的事儿多了,我们都没在意,以为挨过两天就好。可两天后,那红包不但没消下去反而化脓感染,患处被麦萍抠出了黄水和血迹。
麦萍以手捂脸来到我家,眼睛里漫着雾一样的哀怨,她低低啜泣:“你说我以后就要变成疤瘌脸了吗?我咋这么倒霉呢!”我用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指间全是湿答答的泪水。除了诅咒那该死的虫子,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晚风吹响簌簌的菜叶,扫帚菜旁,一只雪花鸡单腿站立,把头埋入翅膀里。
时间似乎停滞,黄昏从没有那样漫长过。
麦萍细细高高,眉清目秀,然而此刻,她的颧骨外侧多出来一块紫红肿胀的疮疤,牵拉得眼睛变成了三角眼,嘴唇翘起了干皮,灰暗的脸颊上,不时有泪珠滚落,一滴,又一滴。
锅台前忙碌的母亲,端来一碗扫帚菜水给麦萍清洗了患处,又摸黑出门采了把扫帚菜叶子捣烂,用勺子舀了糊在麦萍的伤疤上。一碗汤的功夫,麦萍说她感觉疙瘩处舒服多了,好久都没有这样舒服过了。母亲让她多摘些扫帚菜叶子带回家,天天如此这般熬水并捣烂敷脸。
一周后,麦萍蹦跳着来到我家,她的声音先于她的身体出现在我家的院子里,透着止不住的欢喜:“二婶儿,快看,我脸上的疤,掉啦!”菜圃里惊飞一只麻雀,扑棱棱绕了个弯,落在院墙上。我和母亲凑到麦萍跟前看,那难堪的疮疤果然已结痂脱落,露出新生皮肤的粉红。
“放心,不会留疤。”母亲安慰麦萍。
“真想不到这扫帚菜还能把我的脸打扫干净。”说这话时,麦萍的眼睛和皮肤都亮亮的。她站在一株扫帚菜旁,一些叶子从扫帚菜上下来进到麦萍的衣兜里,一些感激之言涌入母亲和我的耳朵。来自扫帚菜里旺盛的生命力,氤氲环绕着麦萍,她的脸,恢复了往日的美丽。
有那么一瞬,我感觉院子里的扫帚菜,就是童话里女巫乘坐的那把飞天扫帚,拥有神奇的魔法,在赶走疾病的同时,也扫除了麦萍身上的晦气和忧伤。
从此,我看扫帚菜的眼神里又多了一层意味,它至柔至刚,是可口的菜,是刚健的扫帚,是惩罚我们顽劣的工具,也是一味良药。
多年后,读到《医学正传》里的一则偏方时,一下子想起了麦萍,想起了她脸上曾经的疮疤,眼前浮起绿丸子一样的扫帚菜,我是好久好久都没有见过麦萍和扫帚菜了。这则偏方其实也是治疗皮肤病的:“抟兄年七十,秋间患淋,二十余日,百方不效。后得一方,取地肤草捣自然汁,服之遂通。至贱之物,有回生之功如此。”
地肤草,即扫帚菜,有些医书也称之为地肤子,地肤子是扫帚菜成熟后所结的种子。
“地肤子对于荨麻疹、疥癣、湿疮、皮肤瘙痒等症状有疗效。”这些刻板地印在医书上表明地肤子功效的文字,早就被我的乡亲们在生活里验证过了。
但从中不难看出,作为药物的扫帚菜,也拥有扫帚的功能——涤荡皮肤之病痛。
地肤草、地肤子、扫帚菜,这些名字,都好。读来,就像冬日暖阳从皮肤上拂过,有轻谧的疗愈和修复感。
一个“女”字加一个“帚”字,便是繁体“婦”字——“从女持帚,洒扫也”,这是《说文解字》对于“婦”之理解,小小的扫帚,是“婦”管理家务的装备。一个家,离不开“婦”,自然也离不开扫帚。
一直觉得,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内外装备齐全的“婦”人,家里邻里大大小小的麻烦,都能被她轻松“扫”走。
苦裙
苦荬菜,家乡人叫它苦裙,更亲切的称呼是:苦裙裙。
在野菜里,苦裙以“苦”立身,是苦的宿主,苦得根深蒂固。苦,被镶进了苦裙的名字,苦,是苦裙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开春,苦裙和其他野草一样,打着哈欠醒来,在依然料峭的风里睁开眼睛,甩甩胳膊,抖抖肩,做伸展运动。和其他野草不一样的是,当它被我用双手拔起,又不小心弄断茎叶时,断差处,会渗出白白的汁液,闻起来苦味鲜明。这白汁不小心沾到皮肤上,黏糊糊的,会变黑,会让皮肤发痒,很不舒服,也很难清洗。
苦裙虽不开口说话,这白色的汁液,就是它的语言。
记忆里,苦裙的这种自卫策略在对付昆虫方面蛮有成效,拔草多年,我很少见到苦裙茎叶上有虫眼。但这毒素的剂量,在对付庞然大物人与猪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苦裙大概也没有想到,它费尽心机鼓捣出来的对付昆虫与食草动物的苦汁,竟然落得人与家猪都喜欢食用。所以,它虽是野草,也被叫作野菜,草与菜,其实只凭人的嘴巴来界定。
我和麦萍人手一个竹笼一把铁铲,在返青的麦田里找寻苦裙。抖抖手,甩甩土,苦裙们就换了空间。回家后,母亲摘出水灵灵的苦裙做菜,剩下的,一股脑儿倒进猪槽。咔嚓咔嚓,猪吃得心满意足。青草,对于家猪来说,大概类似于人类正餐后的水果,是用来补充维生素的。
作为一种野草,苦裙是寄居在麦苗中的小小过客,不被我们拔掉,也会被乡亲们铲除。而我们的到来,更早地终结了它在阳光下的日子,这让我对苦裙始终怀有些许歉意。但哪怕只有一株苦裙被漏掉,夏秋,它绽开小小的黄花后,就会生出成百上千粒种子,它有着令人讶异的扩张力,有着坚韧顽强的个性,也有阳光和雨露的无差别眷顾。苦裙的种子堪比蒲公英,一个个驾驶着小小降落伞满世界飞。只要有泥土,就能扎下根来续命。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苦裙其实很古典,它就是《诗经》里走出来的“荼”。“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苦苦的荼,烛照了一位女子的心境。当她经历爱情以及被丈夫抛弃后,我从中读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况味:“日子苦点儿算什么?只要和他在一起,日子再苦也甜。”“谁说荼菜味苦?比起我心中的苦,它鲜香如荠菜。”苦与甜,该是一个事物的两种特质,犹如人生,是苦还是甜,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更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
苦裙入菜最简单的做法是凉拌,去根后的苦裙叶子,淘洗干净,在沸水里打个滚,挤净水分,切碎,加入葱花蒜泥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入口有轻微的苦涩,回甘,去热下火。
对人来说,甜,是安慰,苦,是唤醒。甜是温柔的,安抚肠胃乃至心灵;苦,则是凌厉的,令人瞬间清醒,“良药苦口”般给人力量。
到城市后的许多个夏天,苦裙的味道会自动回到鼻息里,挥之不去,这是苦裙在我身体里留下的印记。燥热之际常忆起浆水鱼鱼的好,可惜这吃食终究没能逃脱命运的寂灭,浆水鱼鱼现已全然退居至我的记忆里。
当年,母亲把苦裙在滚水里焯一下,放进缸里加入沸腾的面汤,盖好缸口发酵,三四天后,乳白的浆水就做好了。热浪滚滚的夏日,最喜食浆水鱼鱼。鱼鱼是一种两头尖,中间圆的面食,把面鱼捞进碗里,浇上事先加入蒜泥、辣椒和葱丝的浆水,就成了动感十足的浆水鱼鱼。鱼鱼们游进口里,呼啦一下,又游进胃里,酸辣,清香,解暑,那叫一个爽。
那时六七岁吧,猪嫌狗不爱的年龄,好动,身体里的能量多到可移走太行王屋二山。一天,不知为啥,我就撞翻了母亲盛好的一碗玉米臻臻,刚出锅的热臻臻一下子糊在我的手背上,一团火苗和尖锐的哭声同时腾起。母亲快速从缸里捞起一把酸菜,抹掉我手背上的玉米臻臻又翻转过来捂在烫伤处,如此反复了两次,我的哭喊声和手背上那团火苗才慢慢熄灭。那烫伤好了后,手背上也没留下难看的疤痕。
有那么几年,每一个黄昏,我都是闻着草香度过的,打猪草,是那个年代放学后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家庭作业。那天,我和麦萍像往常一样进到村东头的坡地,我俩相隔不远,各自蹲下,舞动小铲子,将荠荠菜、蒲公英、车前草和打碗花一一收入笼里。
雨后的田野充满了泥土和草木生长的气息,春天,也在生长,由嫩绿正走向墨绿,那是一地的音乐家、声乐家在演奏、在歌唱,幕布是满地的草木,掌声也来自这些草木,这些声息伴随着两只紫蝴蝶的嬉闹在空气里回荡。突然,麦萍发出“啊”地一声尖叫,只见她歪着脑袋,用手使劲拍打头部。
我跑了过去。麦萍一手拍打头部,一手揉捏太阳穴,她语无伦次:“耳朵进虫子了!嗡嗡嗡、嗡嗡嗡,这里、这里,震得疼死人咧。用手指掏,它就往里爬,快帮我看看。”
又是一只虫子!麦萍到底是招虫子喜欢呢还是招虫子嫉恨?她龇牙咧嘴,双手又拍又抓,编成麦穗状的头发,已乱成风中的鸟窝。
望着麦萍幽深如隧道的耳朵眼,我束手无策。茫然四顾,我看到了救星——五爷在远处割草。
五爷听罢,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镇定,他弯腰在地里拔了一把嫩苦裙,在手心里搓揉出汁液,他让麦萍侧头,往麦萍的耳朵眼里挤进数滴苦裙汁,又吩咐麦萍反向侧头,不久,一只芝麻粒般的小黑虫,随绿色的汁液缓缓流了出来,小虫子腿脚横斜,它已中毒身亡。
我惊讶:“这么大点虫子,不细看都看不到。”五爷道:“娃呀,能有多大?大了,弄不好她的耳朵就聋咧。”
风儿和缓地拂过我们的脸庞,我看见麦萍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后来,五爷在大槐树下还分享过苦裙的其他祛病良方,譬如,把苦裙根叶捣汁敷在痔疮上,日敷三次,屡用有效;用苦裙断茬处流出的白汁,直接涂抹脖子上的小肉球“猴子”,坚持涂抹,来无影的“猴子”,去亦无踪。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我周围的人一一验证过。
时光,贴着苦裙的种子在风中飞驰。苦裙医病的往事,已封入时间的壳,成为一粒粒琥珀。
很多年过后,当我看到李时珍对苦裙的描述时,不禁莞尔。生长在《本草纲目》里的植物,无不闪现出医药的光芒。苦裙可医病,五爷是实践者,而李时珍是形成理论者。医圣说它:属于菜部,名荼、苦苣、苦荬、游冬、褊巨、老鹳菜、天香菜,气味(菜)苦、寒、无毒;主治血淋、尿血,喉痹,对口恶疮,赤白痢。
可见,这苦裙名字里有“苦”,却不会带给人“苦”,相反,它用苦口婆心,疗愈了那么多人的伤与痛。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周围的好多草木都是医生,都可医病:柴胡根煎汤退热医治感冒,马齿苋熬汁止痢疾,茵陈泡茶退黄疸,刺蓟叶子捣汁止血,破开了的苍耳子加麻油涂鼻腔治鼻炎……这些环绕我们老屋也环绕我们童年的草木,一直在默默地守护我们,慰藉我们,并用生、繁、实、落的生死轮回,知会我们做人与处世的道理。
草木里,既有医家的大能,也有道家的修为。
草木,医病,也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