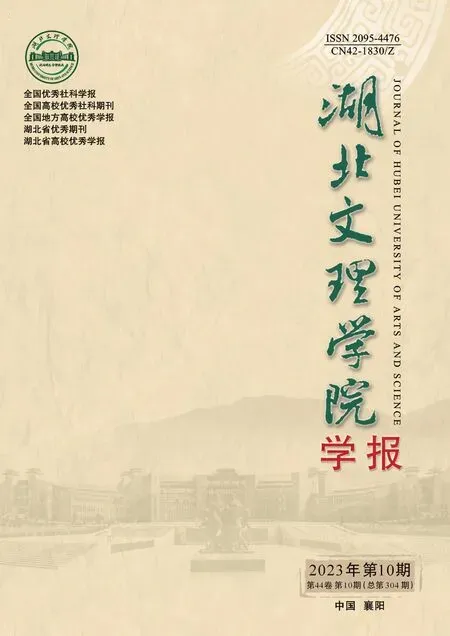“《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
——章学诚与钱锺书的对话
张 金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提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认为《易》之象包纳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1]23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乾》中,钱锺书与章氏隔空对话,指出“《易》之有象”与“《诗》之有比”虽理有相通,但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2]20。章氏与钱氏同为学术大家,就“《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产生的观点碰撞值得我们加以注意探讨。本文立足《文史通义》与《管锥编》,试图从对话视角来考察两位学术大家围绕这一焦点问题进行论述的学术语境及其隐含的思想理路,从而揭示二者对此问题辨析的学术史贡献及其研究理路之于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的启示意义。
一、对话的语境:“《易》之象”与“《诗》之比兴”概念溯源
章学诚与钱锺书所探讨的“《易》之象”与“《诗》之比兴”,涉及两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两个重要的文论概念,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易》即《易经》,为儒家六经之一。按《周礼》记载,《易》原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3]802,后来仅有《周易》得以流传,故今之《易经》多指《周易》而言。《易》的外在形式是以六十四卦为内容的卦画。所谓“《易》之象”,即《易》的封画用符号所表现出的形象,它摹拟客观事物的现象,具有象征意义。《易》本用于占卜,占卜者因数定象、观象系辞、据象辞判定凶吉。因此“《易》之象”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系辞》有言:“《易》者,象也。”王夫之解释为:“汇象以成《易》,举《易》而皆象,象即《易》也。”[4]1039可见“《易》象”实为《易》之中枢,甚至于成为《易经》的别名。
“《易》之象”体现了上古时代人们“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3]83盖原始初民抽象概念思维尚不发达,因此多用形象类比思维来认识世界。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指出“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3]14可见《易》象不仅用实象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关系,更用虚构的假象来展示世间万物所蕴含的哲理意蕴。
《诗》即《诗经》,亦为儒家六经之一。汉代《毛诗序》记载,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孔颖达注疏:“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3]271乃就《诗经》的表现手法、文本内容将六义划分为两方面。所谓“《诗》之比兴”属于六义中的表现手法。“比”“兴”析言之有显隐之别。“比”即比喻,比喻的本体与喻体有相似之处,中间用“如”“若”等喻词来表明。“兴”即托物起兴,起兴的事物一般放在诗句开端,其与被兴的事物的联系较隐微,往往需借助《毛传》的解释才能“探微索隐”。“比”与“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附于外物,取诸物象,故“比兴”浑言之都是一种借助于物象来言情明理的艺术手法。
从创作角度来说,“比兴”体现了诗人形象类比的思维方式与含蓄寄托的情感表达方式。郑众所说的“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孔颖达所谓“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3]271便都可以说是一种形象的类比。刘勰指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5]601同样从比拟类比的角度谈“比兴”,且关注到了这种类比思维在表达创作者“情”“理”方面的有效性。后代的文论家多从情与物的关系角度阐释比兴,显示出物象的直观联想与情感的寄托表达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宋代李仲蒙语:“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6]明代李东阳有言:“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7]
由此可见,章学诚与钱锺书关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关系的探讨有其学术传统与知识背景。要而言之,“《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确有相通之处,历代文人学者对它们内在联系的论述体现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这一理论命题的普遍性与经典性。一方面,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相通,“《易》之象”所体现的“观物取象”与“《诗》之比兴”所体现的“联想类比”都是一种直观感物,都需借助于形象。另一方面,它们在表现效果上也有一致之处,“《易》之象”的“立象尽意”“观象系辞”的符号表达与“《诗》之比兴”的“含蓄寄托”“言情达志”的艺术表现都是一种象征和隐喻,都通过具体个别的形象展现广泛普遍的情理。章学诚正是在继承了前代文人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而将这一理论命题推向了新的高度。钱锺书则在此基础上辨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二者“貌同而心异”,立足于现代学术视野对这一理论命题做出新的开拓。
二、对话的焦点:“《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辨析
作为两部儒家经典中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尽管前代有不少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但大多比较零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易教下》与钱锺书的《管锥编·周易正义·乾》则集中论述了二者的异同,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做了详细探讨。
在《易教下》中,章学诚首先指出“《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象欤,兴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即认为二者都富于变化,表面上来看毫不相关。不过“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易》之象”与“《诗》之兴”“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1]22,即认为它们都是一种类比的形象思维。一方面,“《易》之象”是一种类比的形象思维。《易·说卦》:“《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便是将《乾》卦类比为“天地自然之象”。《易·睽卦》:“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则吉。”便是将《睽》卦类比为“人心营构之象”。另一方面,“《诗》之比兴”也是一种类比的形象思维。《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将雎鸠雌雄之挚而有别,类比为淑女与君子好配之象。《诗·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便是将熊罴、虺蛇类比为男女之象。[1]22-23因此,章学诚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即揭示了它们在思维方面的共通之处。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引用了《易教下》的论述,同样认为《易》之象“与诗歌之托物寓旨,理有相通”,并且补充了意大利美学家维柯的说法,指出它们都是“以想象体示概念”。然而,钱锺书在同意章学诚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也。”[2]19-20具体来看,钱锺书从《易》《诗》这两部著作的目的及象喻在其中的作用这一角度做出了区分。钱锺书认为《易》作为哲学著作,其目的在于阐明事理。《易》之象的作用就在于它是阐明事理的工具与中介,为了道理能够被阐明,则不必拘泥于某一形象,可以变换不同的形象来说明同一个道理;倘若道理已经被阐明,也不必执着于某一形象,可以将用来说理的形象舍弃掉。相比而言,《诗》作为文学著作,其价值在于构造形象来感发人心,《诗》的语言是“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倘若舍弃形象,则《诗》之所以为《诗》的特性便不复存在;倘若变换另一种语言形象来表达,则这首诗就变成另一首诗,甚至称不上是一首诗了。举例而言,《易·说卦》说《乾》为马,亦为木果,无论是取象于马还是木果,都是对《乾》之道的阐释,取象的不同并不影响意旨的把握。然而,《诗经·车攻》中的“马鸣萧萧”,倘若换成“鸡鸣喔喔”,便牵一发而动全身——取象的不同会直接影响整篇诗歌的情景与意境。
由此,钱锺书借用西方符号学术语,对“《易》之象”与“《诗》之比兴”下了定义:“《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2]20-21根据上下文语意及注释,钱锺书大致借鉴了索绪尔与皮尔斯的观点。索绪尔即将符号(sign)定义为概念(concept)和音响形象(sound-image)的结合,或曰“所指”(signified)与“能指”(signifier)的结合,并指出符号(sign)中的“所指”与“能指”关系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11]皮尔斯将符号划分为三类:图像(icon)、标志(index)和象征(symbol),并认为图像(icon)“仅仅借助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12],其“所指”与“能指”关系是等同的。以sign定义“《易》之拟象”,即突出符号与意义关系的任意性,表明“《易》之拟象”只是阐明事理的工具,可以变象尽意、得意忘象;以icon定义“《诗》之比喻”,即突出符号与意义关系的固定性,表明“《诗》之比喻”的意义本身便蕴含于形象之中,形象与意义密不可分。
基于以上认识,钱锺书进一步阐明接受者与创作者面对“《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应该具有的态度与意识,对二者异同问题的分析做了全面的开拓。其一,钱锺书从接受角度告诫读者读《易》不可拘泥于象而死在句下,不可过度关注象喻而忽视对义理的理解。如其引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即主张读者需“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2]21。引述佛典《大智度论·释七比品》:“诸佛贤圣怜愍众生故,以种种语言名字、譬喻为说。利根者解圣人意,钝根者处处生著,著于语言名字。”[13]即指出接受者若执着于表象,便不能解圣人之意。其二,钱锺书从创作角度揭示哲人“以言破言”“以象破象”来消除害意之词的现象。如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14],用心即在于“以象破象”,防止读者囿于一喻而生执着。柏格森说理喜欢取象设譬,认为“各种各样的形象”可使直观本身不至于为某一譬喻形象所篡夺僭越。[15]弗洛伊德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一文中也说:“在心理学中,我们只能借助于类比来描述事物……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这些类比,因为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供我们长久利用。”[16]其三,钱锺书从接受角度告诫鉴赏者读《诗》不可执着于探究作者的隐含意旨而忽视对形象辞章的鉴赏,不可“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通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2]24。对于比兴寄托、诗史互证的做法钱锺书向来颇有微词,其在《管锥编》中论《毛诗正义·狡童》便赞同朱熹《诗集传》的解释,反对将《狡童》“附会为‘隐意君臣’”[2]185,钱锺书认为“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2]187。其四,钱锺书从创作角度阐明诗人可以“视《易》之象如《诗》之喻”,借鉴采纳“《易》之象”的表现手法。尽管“《易》之象”用于阐明事理,但它含有文学性成分,故“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2]24。这一点中国古代文论家即有所认识,如刘勰指出“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领”[6]22,韩愈指出“沈浸醲郁,含英咀华……《易》奇而法,《诗》正而葩”[17]。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则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其考察《易经》中《归妹》与《履》发现“二卦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便从文学辞章的角度指出这是一种“比喻之两柄”的修辞现象[2]64-65。通过考察归纳“《易》之象”所蕴含的文学性,钱锺书发掘了新的文艺创作规律,总结了新的艺术经验。
综上所述,围绕“《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这一焦点问题,钱锺书与章学诚展开了对话。章学诚提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认为“《易》之象”与“《诗》之比兴”都是一种类比的形象思维。钱锺书在同意章学诚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二者貌同而心异”,并从《易》《诗》两部著作的目的及象喻在其中的作用这一角度对“《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做出了区分,指明了接受者与创作者面对“《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应该具有的态度与意识。“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对比章氏与钱氏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则章氏的观点更具传统性与继承性,“《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提出可谓是对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关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关系探讨的历史总结,其关于“天地自然之象”“人心营构之象”的划分亦可谓是对孔颖达“实象”“假象”说法的继承,这对于我们总结传统文论的历史经验和固有观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钱氏的辨析则更具现代性和创新性,其对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的区分实乃现代学科视野下哲学与诗学的区分,从文本、创作与接受多方面切入此一论题,对于西学理论著作的大量借鉴既开拓了中国传统文论的阐释空间,也使“《易》象通于《诗》之比兴”这一传统命题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因此可堪称为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典型案例,对于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三、对话的理路:“史意之贯通”与“文心之打通”范式争衡
对于上文分析的章学诚与钱锺书的对话,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章学诚在《易教下》明确提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但若以钱锺书的分析思路作为考察视角,则章学诚未必没有认识到“《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的差异所在。王怀义教授曾指出:“实际上,章学诚虽言易象与诗喻‘尤为表里’,但并未将二者等同,他对二者性质的区分与钱锺书‘殊途而同归’:两人都主张将易象和诗喻从根本属性上区分开来。”[18]具体而言,从《易》《诗》这两部著作的目的来看,章学诚指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辞通于《春秋》之例”,“《易》以天道而切人事”[1]22-24,即表明《易》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客观的天道为标准来指导人事,其言辞的体例是十分严谨的。章学诚在谈到《诗》的时候则指出“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1]23即认为《诗》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推衍《诗》的“比兴之旨、讽喻之意”来出使专对,其言辞的表达是善于修饰的。由此,虽然《易》《诗》中都含有“象”,“《易》之象”多受到客观自然天理即易理的制约,“《诗》之比兴”作为一种讽喻修辞,主要服务于主观的目的。章学诚对于“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的区分便在侧面提示了二者的差异之处。
数学本质是对复杂世界的简单抽象,人类生而就潜移默化地利用数学而不自知,从有无是非等判断,到数字、比例、精确计算、测量、决策,数学实际上应用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起来微积分这样的高等数学和人类的生活没有联系,但是如果要作高级决策、精确计算和尖端技术,必然离不开这些高等数学。数学在本质是对人类文化的抽象,在人类的所有学科里都要应用到不同层次的数学原理。
由此可以说在认识层面章学诚与钱锺书识见相当。只不过,在实际论述及价值判断层面两位学术大家各有所侧重。西方学者托马斯·库恩曾用“范式”(paradigm)来指将一个“学术共同体”结合在一起,使其区别于其他类型知识集团成员的因素,即“每一个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19]80,“范式为除了反常之外的所有现象提供一个在科学家视野内的确定的理论位置”[19]83。以今揆古,章学诚与钱锺书实则都是自觉开辟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范式”的学术大家(1)胡晓明教授曾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将陈寅恪与钱锺书的诗学研究进行比较,认为陈寅恪与钱锺书代表着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陈寅恪开创了“诗史释证”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学术传统,钱锺书开创了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相贯通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修辞、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现代新学的融合(参见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7-73页)。,他们关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辨析的背后实则还隐含着古今文史两种学术范式的对立与争衡。
章学诚所代表的古典学术研究范式可概括为“史意之贯通”,此源自其经世致用的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六经皆史”的论断之中。结合章学诚所处时代风气来看,当时乾嘉训诂考据学兴盛,以戴震为代表的学者们充分发挥“经学即理学”的思想纲领,认为“道”或者圣贤的“义理”全部存在于六经之中,而要阐明六经的含义则必须借助于训诂考证。[20]章学诚则认为“道”并不仅存在于六经之中,而主要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现实与变化发展中,六经只不过是具体的历史现实的一部分。在《文史通义》中,他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原道下》又指出:“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怪也。”[1]161相比于专攻一经,纠结于训诂考据,章学诚主张“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1]162,即把握六经的共通的意旨,探究文史之“通”义,从而顺应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
章学诚“《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提出,便源于其贯通的学术精神及其以“易教”统摄六经的理论思考。章学诚指出“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1]22是以“《易》象”不仅通于“《诗》象”,还通于《书》《礼》《乐》《春秋》之象,因为这些经典中所阐释的道理都通过形象展现出来。《易教上》指出:“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1]2表明《易》与《礼》《乐》《诗》《书》在指导人事、切于民用方面也是相通的,《易》悬象设教为“天道”[1]22,《诗》作为六艺之一,自然也贯通于“易象”“易道”,从而服务于政治教化与人伦日用。
与章学诚相对,钱锺书所代表的古典学术研究范式可称为“文心之打通”,即旨在挖掘一切人文著作“心理攸同”“诗眼文心”之所在。在致郑朝宗的信中,钱锺书指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27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辞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2)信中标注参见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1、270-271、406、875-878、116页,即《左传正义·一三·僖公四年》论“重言”一节、《史记会注考证·四·秦始皇本纪》论“野语无稽而颇有理”一节、《老子王弼注·二·一章》论“道”与“名”一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全上古三代文卷九》论“伤高怀远”一节、《毛诗正义·三八·伐檀》论“诗之象声”一节。,etc,etc,皆‘打通’而拈出新意。”[21]《管锥编》对于中国古代十部经典的具体阐释,便是这种“打通”方法的体现。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钱锺书的“打通”始终以“能文为本”,以谈艺为当务之事,对于文学与哲学、史学的区别洞若观火。如钱锺书论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指出:“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22]76又如《宋诗选注·序》中对于文学与历史的划界:“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23]因此,钱锺书的“文心之打通”相比于章学诚的“史意之贯通”,有着更为明确的现代学科划分的意识,尤其强调文学学科本身的特殊性与自律性,在此基础上再探求其他学科与文学特性的相通之处。
对于“《易》之象”与“《诗》之喻”的分析便是钱锺书运用“打通”方法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钱锺书通过辨析“《易》之象”与“《诗》之喻”的差异揭示出《诗》作为文学作品与《易》作为哲学作品的区别,强调了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形象和语言。另一方面,钱锺书指出“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2]24,即认为“《易》之象”含有文学性的成分,由此可以转化为“《诗》之喻”。可见,钱锺书打通“《易》之象”与“《诗》之喻”的关键在于它们共通的文学性,而非章学诚所推举的“易理”“政典”,“《易》之象”在这里并不具有统摄“《诗》之喻”的地位。
由于“史意之贯通”与“文心之打通”两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差异,钱锺书与章学诚对于“《诗》之比兴”的批评态度大相径庭。如前文所述,钱锺书重视诗歌艺术形象本身,反对持“诗无通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章学诚则轻视诗歌艺术之工巧,肯定“文须依附名义,而诗无达指,多托比兴。”[24]其在《言公上》中指出:“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1]200在鉴赏具体诗歌的时候,章学诚亦注重发掘诗歌背后的隐含寄托,认为“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1]199,“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讽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1]643。
章学诚治学着力于“史意之贯通”,故主张“六经皆史”;钱锺书治学着力于“文心之打通”,故主张“史蕴诗心”。《谈艺录》中,钱锺书不满意“古诗即史”的提法,不满意学者们只偏信诗是征献之实录,提出过“史蕴诗心”的观点。[22]100-106对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钱锺书亦有评述,他指出“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政典,龚定菴《古史钩沈论》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22]659-660这里将“六经皆史”更往前推进一步,认为“若经若子若集”都是史,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是“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立足于此,钱锺书考察历史史料也指出:“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2]443可见,对于人情、人心的关照,对于精神、心理的揭示,构成了钱锺书打通文史的契合点。
由于两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差异,章学诚与钱锺书在考察《焦氏易林》这部易学著作时也产生了观点的分歧。章学诚认为“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1]93尽管章学诚也认识到《易林》运用了韵言的文学形式,但是由于他注重探求作者意旨,强调论文不拘于形貌,故认为《易林》乃是阐发义理的占卜之书,与《诗》无涉。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专门批评了章学诚的这一观点,指出“顾乃白雉之筮出以黄绢之词,则主旨虽示吉凶,而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si carica l’operazione utilitaria/d’un intenzionalità formativa)。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家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2]816-817可以说,钱锺书对于《易林》诗性的发掘,对于韵文形式美的推崇,与其“文心之打通”的研究范式是密切相关的。
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同一个理论问题做出不同角度的阐释,与人文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学者本人的性情有关。一方面,人文学术研究贵在博观而约取,所谓“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1]189另一方面,大学者的学问必定是有性情、有个性的学问,所谓“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1]190。考察章学诚与钱锺书关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问题的论述,则章学诚以史家之意贯通六经,“《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归究于史意;钱锺书以文人之心打通四部,“《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区别于文心。古今两位学术大家都以各自学术性情之精专通于学问境界之广博,其内在的学术思想理路具有典范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体会,取法学习;而中国文论中不同概念范畴在不同学者研究范式关照下所呈现的种种微妙关系,亦或不仅限于本文所探讨的论题一隅,值得我们抉发辨析,作更广阔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