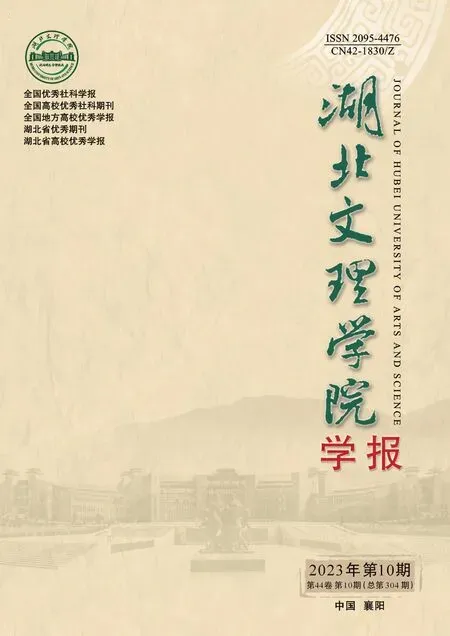中晚唐乐舞诗中“霓裳羽衣”意象的生成与审美
何鑫妍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霓裳羽衣》作为唐代歌舞大曲的集大成之作,自玄宗朝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盛世大唐的代表,中晚唐时期这一大曲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类似于《玉树后庭花》,成为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有五十余首诗歌涉及。然而目前对《霓裳羽衣》的研究,多聚焦乐舞本身的创制、流传演变以及乐舞样貌的考证复原,将涉及“霓裳羽衣”意象的诗歌用作史料,较少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即使是专论诗歌,也多探讨该大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士人对雅乐俗乐的接受。但是从大曲《霓裳羽衣》到“霓裳羽衣”意象,生成原因是复杂的,意象内涵也并非以盛世追忆或者讽刺明皇就可概括。在“霓裳羽衣”意象内涵与盛行原因的分析中,又可发现中唐、晚唐有关霓裳审美的转变,在丰富人们对唐人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认识的同时,探析中晚唐诗风流变之一端。
一、中晚唐乐舞诗中的“霓裳羽衣”意象内涵
“霓裳羽衣”究竟是盛世象征还是亡国之音历来备受争论,事实上,二者共存于该意象中。它既是盛世气象、生命力的彰显,同时又与战争相联,在声色犬马中导致社会动荡。在对《全唐诗》中的“霓裳羽衣”进行提取分析后,又发现它不仅是李杨爱情的证明,还可视为仙境的象征。
(一)“霓裳羽衣”的盛世之象
大曲《霓裳羽衣》创制流行于盛唐,集高超的乐舞艺术与时代的浪漫瑰丽于一身,是盛世的见证者,自然拥有了盛世的含义。“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1]4702,白居易就将歌舞霓裳看作政治清明、安居乐业的象征。《长恨歌》的“惊破”之句,也只有在认同霓裳可代盛世的前提下,才能以曲子的骤然停止写战争打破太平。在《卧听法曲霓裳》中,白居易则言“乐可理心应不谬”[1]5092,认为此曲可助修养身心,可见诗人对《霓裳羽衣》的认可与欣赏,这是视其为亡国之音者不会产生的心态。
开成元年,《霓裳羽衣》甚至被用为科举考题,李肱以《省试霓裳羽衣曲》夺得状元。“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竞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1]6314。李肱将该曲与开元盛世联系,视奏演时乐器轮番上场、舞裙飞扬为太平昌盛时代的象征,肯定其治世功效,并强调只有文宗才能恢复该曲,即恢复大唐盛世。而文宗定李肱为榜首,也就表明了对盛世内涵的认同。而后更有李商隐在《留赠畏之》[1]6218中以李肱“咏霓裳”之事夸赞友人才华并祝其得取功名。
温庭筠的《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遗址仅有存者偶成四十韵》则十分明确地将盛世霓裳与政治动乱区别开,“紫绦鸣羯鼓,玉管吹霓裳。禄山未封侯,林甫才为郎。照融廓日月,妥帖安纪纲。群生到寿域,百辟趋明堂。四海正夷宴,一尘不飞扬”[1]6812。《霓裳羽衣曲》本为太平年间的艺术享受,歌舞霓裳时安禄山、李林甫尚未作乱,大唐正是四方来朝的强盛时期,因此不可将王朝动乱归结于此。
对盛世强盛与繁华的钦慕,使得诗人借“霓裳”流露追忆缅怀之情。“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1]2751。在一系列缅怀对象中,歌舞霓裳占据一席。可惜动乱之后物是人非,“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虽然张继悲叹动乱后的落没,但《霓裳羽衣》却不是导致落没的原因,而是太平年间美好生活的象征,在今昔对比中感慨盛况不再,吐露遗憾。相似的还有顾况《听刘安唱歌》,以“已逐霓裳飞上天”[1]2956写当今法曲无人再唱,诉说盛唐王朝的覆灭,由此产生悲忆太平年的感伤。
(二)“霓裳羽衣”的亡国内涵
当诗人将盛唐的覆灭归结于歌舞误国时,歌舞霓裳便成了亡国之音。这在李约《过华清宫》、李商隐《华清宫》、薛能《华清宫和杜舍人》中十分典型。“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1]3496,“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1]6224,“细音摇羽佩,轻步宛霓裳。祸乱根且结,升平意遽忘”[1]6543,三人直接将战争的爆发归结为《霓裳羽衣曲》,皆将此大曲视为游乐与女色的结合体。《霓裳羽衣》是盛唐宫廷乐舞的集大成之作,又公认属杨玉环最为擅长,歌舞霓裳也就有了女色误国之意,君王经常排演的行为,就包含了沉溺女色与贪图享乐的双重含义,亡国之音由此而生。李商隐“朝元阁回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1]6224,就明确以贵妃舞霓裳为首的宫中享乐生活牵绊了玄宗,使安禄山有机可乘。
在这类诗中,诗人常借歌舞霓裳来讽刺唐明皇,也时有规劝后世之意。如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1]5997,诗人讽刺明皇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太平假象,与此同时安禄山却密谋反叛并贿赂使者隐瞒真相,于是胡旋舞代替了《霓裳羽衣》,大唐江山岌岌可危。李益《过马嵬二首》“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1]3214,同样以太真血染马嵬只留朱阁断垣残壁,劝诫世人莫要沉迷于歌舞享乐以致山河国破。徐铉则有“此是开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别离声”[1]8692之语。《霓裳羽衣曲》始创于开元,本应是盛世代表,然而歌舞霓裳后,大唐盛世不再,李、杨生离死别。徐铉在送友人时取离别之意,一来表达不愿与友人分别,二来也是规劝君王励精图治,莫再重蹈覆辙以致亡国。
(三)“霓裳羽衣”的仙境象征
诗人也常以“霓裳羽衣”象征仙界,或者是以此塑造清冷氛围。白居易便直接将表演者写成仙子,“上元点鬟招绿萼,王母挥袂别飞琼”[1]4991,点出该舞是神仙之舞,同时以不着人间俗衣写外貌之仙,以“飘然回雪”“云欲生”写舞态之仙。鲍溶《霓裳羽衣歌》[1]5540则将整首诗都置入仙界,织女指引玄宗入仙境,玄宗得谱羽衣曲,织女又赠霓裳衣。不过此诗意在表现求仙的虚幻性。玄宗仙境得乐,又见三清,本以为能同黄帝一般飞龙升天,但却“鸾凤有声不见身”,只留怅然若失,得乐、游历皆是虚幻。
仙界得乐在诗中被多次书写,郑嵎在《津阳门诗》中便描绘了玄宗入月宫得曲的经历,“蓬莱池上望秋月”“上皇夜半月中去”[1]6620,杜牧也有“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之句[1]5993。刘禹锡则稍有不同,“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1]4010,是玄宗得观仙境后顿悟而作。
诗人笔下的《霓裳羽衣》不仅来源于仙界,也是神仙宴饮时的奏演曲目之一。李九龄在《上清辞》中就描绘了道教神仙紫皇设宴奏演此曲的情景。翁承赞言“旋听霓裳适九天”[1]8166更是将得听此曲视为羽化登仙的表现。
在这类诗歌中,清冷氛围取代了恢弘热闹的欢娱场面,歌舞多与寒月相衬,时有伤感之意。张祜将本应是欢娱的歌舞享受放置于“天阙沉沉”的夜晚,万籁俱寂中只有一声玉笛又瞬间消失,留下的只有清冷的月光和不断的宫漏声,萧瑟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刘禹锡《秋夜安国观闻笙》也是类似场景,“月露满庭人寂寂,一曲霓裳在高楼”[1]4138,以冷月无声与霓裳曲相对,寒夜、冷月、孤独一人,透露的是凄清之感。
(四)“霓裳羽衣”的爱情内涵
由于《霓裳羽衣》的形成与李杨二人息息相关,玄宗谱曲贵妃造舞,可以说《霓裳羽衣》是二人琴瑟和谐的爱情结晶,于是诗人将二人的情爱融入诗歌。
王建《霓裳辞》中的《霓裳羽衣》便是李杨爱情的载体。“伴教霓裳有贵妃,从初直到霓裳成”,玄宗挑选出色的梨园弟子教授《霓裳羽衣曲》,贵妃陪伴君王左右编舞相和,歌舞后又许下永不分离的誓言,排演霓裳成为李杨二人形影不离、互为知音的见证。可现实却是“去时留下霓裳曲,总是离宫别馆声”[1]289,《霓裳羽衣曲》成为玄宗追念爱人的情感寄托,虽然有亡国之音的隐喻在,却不得不承认也有暗示二人诺言破灭的爱情遗憾的成分。
这种相伴相知、分离思念的情感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有充分描述。君王看不尽以贵妃舞霓裳为代表的“缓歌慢舞”,在骊宫中二人形影不离耽溺情爱。霓裳梦破,贵妃死后玄宗穷尽碧落黄泉,终于在仙山再次重逢,玄宗见衣裙摇曳的贵妃又“犹似霓裳羽衣舞”[1]4826。可以说,《霓裳羽衣》是李杨爱情浮沉的载体。同样的,徐夤《再幸华清宫》以“霓裳旧曲”“梦破魂惊”[1]8222写李杨二人阴阳相隔,并用“肠断”“锦囊香”追忆当年,以“相思树”“连理枝”春至不生,诉说无法长相厮守的愤恨,整首诗皆从玄宗视角来描绘无尽的相思与遗憾。
刘言史《乐府杂词三首》则借《霓裳羽衣》写二人甜美的情感生活,“蝉鬓红冠粉黛轻,云和新教羽衣成”,贵妃梳妆打扮后歌舞霓裳,她的欣赏观众自然是玄宗,极富浪漫气息。在这首组诗中,刘言史又以宠姬郑樱桃舞与贵妃舞霓裳相对,增添爱情成分。这种“薄妆春寝觉仍迟”的闲适与“梦中无限风流事,夫婿多情亦未知”[1]5356的心态,是在爱情内涵中为数不多只有欢娱之情的作品。
中晚唐的“霓裳羽衣”意象主要是这四种内涵,多种意义可并存于一首诗中。比如王建的《霓裳辞》就同时包含了仙境、爱情、亡国之音的含义,霓裳羽衣由西王母处求得,又是李杨二人心意相通的爱情结晶,也是离宫别馆的亡国之声。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则具有盛世歌舞、宫闱爱情、山河破碎的多重内涵。郑嵎《津阳门诗》中的霓裳也同时具有了求仙、追忆盛世、亡国之音三种象征义。正是“霓裳羽衣”意象的多种意义,共同铸就了诗歌的朦胧多义之美。
二、中晚唐乐舞诗以“霓裳羽衣”入诗盛行的原因
大曲《霓裳羽衣》诞生于盛唐,但中晚唐“霓裳”入诗才盛行,这是在此曲特殊的历史经历、创制来源的传说、民间传播、宴饮娱乐之风以及经典化生成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一)《霓裳羽衣》盛行时间的特殊性
《霓裳羽衣》是宫中的大型乐舞,歌舞时呈现一派华美之象。舞者穿“虹裳霞帔”,戴“步摇”“钿璎累累”,伴随“磬箫筝笛”的“击压弹吹”,珠玉佩环抨击发出铿铮声,歌舞后“珠翠可扫”,这在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郑嵎的《津阳门诗》中多有描绘。玄宗在宴饮之时多演《霓裳羽衣》,更是将此作为千秋节的必备曲目。《资治通鉴》载:“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2]歌舞升平、极尽享乐的生活,满足了后世对盛世的想象,成为盛世的代名词。可惜盛极而衰,一味地纵欲享乐使得朝政荒废,安史之乱爆发,盛极一时的唐帝国轰然倒塌。从励精图治海晏河清的开元,到荒诞无度的天宝,再到动荡的战争,《霓裳羽衣》一直伴随着大唐,伴随着玄宗,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安史之乱后,此曲散佚,即使在后世不断搜集复刻的情况下,依旧无法恢复玄宗时代的样貌。
《霓裳羽衣》的命运与唐王朝的命运极为相似,文人将目光聚集于此,以歌舞霓裳象征大唐的兴衰,或歌咏过往之兴盛,或悲叹当今之衰败,这段沉浮的历史为诗歌创作输送了养料。
(二)《霓裳羽衣》创制来源的丰富阐释性
《霓裳羽衣》的来源传说为文学创作意义的丰富性提供可能。这一歌舞大曲究竟从何而来,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外乎三种说法,节度使进献、玄宗改制、玄宗独创。
进献说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依照地方献曲朝廷的惯例,搜寻地方乐谱得《霓裳羽衣曲》进献玄宗。[3]改制说则为杨敬述献《婆罗门曲》,玄宗润色修改,并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改名为《霓裳羽衣》。《唐会要》载“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4]615-617,《婆罗门曲》改名为《霓裳羽衣》亦在此列。进献说与改制说虽稍有不同,但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霓裳羽衣》并非传统清商雅乐,可能含有胡风。这在诗歌中也有所体现,鲍溶将《霓裳羽衣》与《云》《韶》相对,元稹《法曲》中称“宛转侵淫”,诗歌中对旋转舞姿的描写也可印证。
玄宗独创说则与月宫游历的传说有关。《太平广记》载罗公远携玄宗入月宫得曲之事,“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耍至月中看否’……见仙女数百,素练霓裳,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5]入月宫得曲的说法在《异人录》中也有记载:“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游都客,中秋夜同游月中……素娥十馀人,笑舞于广庭大桂树下,乐音嘈杂清丽。上皇归,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6]玄宗崇奉道教,而“羽衣”一词又使人想到道教羽化登仙的说法,舞者姿态又飘逸如回雪。因此,霓裳羽衣与仙境产生了联系,诗人在涉及霓裳时也多烘托脱俗的仙意。
以上三种说法是曲的来源,而舞则与杨贵妃有关。贵妃善舞,不论此舞是否为其首创,后世一般认为贵妃与此舞有关。“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7]李杨二人在切磋中完成了这一大曲,贵妃死去,霓裳舞也随之消失。不论是描绘二人情深义重,还是抨击红颜祸水、帝王沉溺美色误国,明皇与贵妃的形影不离使诗作中“霓裳羽衣”的爱情因素得以发挥。
(三)《霓裳羽衣》的民间传播与后世复刻
从宫廷到民间的传播以及后世的努力复刻,使诗人得以观之,这是中晚唐时期霓裳入诗盛行的另一大原因。《霓裳羽衣》本是“除却梨园未教人”[1]289的宫中乐舞,玄宗时期只在宫中演出。安史之乱后,梨园中的乐人被迫散落民间各地,李龟年尚且只能在寻常人家中表演谋生而非岐王、崔九的座上客,其他普通梨园子弟可想而知了。肃宗平定战乱后,寻找散落民间的宫伎,复归者十得二三,剩下大量的梨园宫伎则为民间带来了宫廷乐曲,“霓裳禁曲无人解,暗问梨园弟子家”[1]3504描绘的便是此曲在民间的传播情景。《霓裳羽衣》的民间传播大大增加了诗人们的接触机会:刘禹锡在安国观闻笙曲《霓裳羽衣》、元稹听乐师管儿的琵琶曲《霓裳羽衣》、白居易在赴任时以《霓裳羽衣》饯行、徐铉在送友时亦是奏演此曲。
诗人不仅是《霓裳羽衣曲》的欣赏者,也是传播者。诗人的传播不只是在诗中记载歌舞霓裳的场景,更是参与到此曲的复刻与演奏中,其中以白居易最为突出。白居易极为喜爱歌舞霓裳,元和初年曾在宫中观赏此曲,后对该曲进行整理复原,在其《霓裳羽衣歌》中就记叙了自己向元稹寻求乐谱的事情。白居易在各地任职时,多教歌女舞伎此乐舞,在钱塘任职时,传授玲珑、谢好、陈宠、沈平演奏该曲,又于苏州教名妓李娟、张态《霓裳羽衣舞》,此曲只经白居易一人便传到了苏州、杭州、洛阳等地。[8]
在民间复刻《霓裳羽衣》的同时,宫庭也致力于该大曲的复原创编。梨园子弟走向民间,一方面促使《霓裳羽衣》的民间传播,另一方面也导致宫中《霓裳羽衣》的短暂落没,直到宪宗元和年间,宫中再次上演。而后文宗朝重新编制《霓裳羽衣》并改为雅乐,“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9]4391。宣宗朝亦有歌舞霓裳的记载。甚至五代时,李煜与周后依旧在收集此曲,“自兵乱以来,《霓裳羽衣曲》其音遂绝。江南伪主李煜乐工曹者,素善琵琶,因按谱得其声。煜后周氏亦善音律,又自变易”[10]。正是宫廷与民间对《霓裳羽衣》的努力复原,才使诗人有可能观之。
(四)宴饮蓄伎之风的盛行
宴饮之风与蓄妓之风也增添了表演观赏的几率。神龙二年(706年),“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得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4]628到了天宝十年(751年),“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事,覃及中外”[4]630。至宪宗朝,公私宴乐的限制被取消,“元和五年二月,宰臣奏请不禁公私乐,从之”[4]630。朝廷对宴饮的限制逐渐宽松乃至取消,这使民间宴饮之风得到发展,家伎的数量与技艺水平更成为文人士大夫身份的体现。娱乐性宴会上的歌舞表演,让《霓裳羽衣》等一众乐舞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唐德宗时张尚书有爱妓眄眄擅舞霓裳,当时却十一年不曾舞,到了白居易却可在家中教舞伎乐童排演此曲。而后《池上篇并序》《湖上招客送春泛舟》等篇中,白居易又描述了自己醉后命乐童演奏《霓裳羽衣》取乐,以该曲款待宾客的场景。私人化的宴饮娱乐让《霓裳羽衣》有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同时,晚唐君王多沉溺于宴乐,上行下效更助此风,即使是在动荡时期也毫无收敛。长庆四年(824年),唐敬宗刚即位一个月,便于中和殿击球游戏,又“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9]508,三月,“幸教坊,赐伶官绫绢三千五百匹”[9]509,宝历元年(825年)五月,“御宣和殿,对内人亲属一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彩”[9]519,九月又陈百戏大宴群臣三日[9]521。而此时的唐王朝正在备战蕃寇,加之天灾,国库空虚,宰相李德裕请求节俭。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每月赐仙韶院乐官两千贯,且“支用不尽”[4]631。乃至僖宗亦是如此,从其四海奇珍靡不必备的曲江宴可知一二。宴饮之时《霓裳羽衣》也频繁上演。“宪宗时,每大宴,间作此舞”[11],文宗召舞人三百复编此大曲[3]478,宣宗时“每赐宴前,必制新曲……有《霓裳曲》者,率皆执幡节、批羽服……如是者,数十曲”[12],五代花蕊夫人在《宫词》中也有元宵节“按罢霓裳归院里”[1]9069的场景。正是在宫廷与民间的大量宴饮中,文人才能观得歌舞霓裳。
(五)“霓裳羽衣”意象的经典生成
诗歌创作中“霓裳羽衣”的频繁使用与典范作品的生成,又反过来推动了以“霓裳”入诗的盛行。“霓裳羽衣”正是在不断地书写中才有了丰富的内涵并逐渐强化,加上典范之作的示范作用与广泛传播,形成了以此入诗的风气,最终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典型意象。于是,即使没有观赏过《霓裳羽衣》,诗人也以此入诗,借助该意象的意蕴表达自我情感。
“安史之乱对于诗歌来说,不只是在内容上,更主要是在心理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3]安史之乱后,诗人们就已经对盛唐流露出一种怀念感伤,代表升平的《霓裳羽衣》自然进入了诗人的创作中,张继《华清宫》、顾况《听刘安唱歌》皆是如此。有了对过往的怀念,便有对现实落没的感慨与追问,以歌舞霓裳为代表的奢侈享乐成了落没现实的根源,李益《过马嵬二首》、李约《过华清宫》中的“霓裳”意象由此而来。大历年间,“霓裳羽衣”已形成了盛世与亡国的两大内涵,并具备讽谕劝诫的作用,在咏史怀古之作中频繁使用。到了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时期,“霓裳羽衣”讽谕的功能在诗中扩大,元白二人的《法曲》《华原磬》,都将《霓裳羽衣》与胡乐相对,以胡乐侵扰正声法喻家国之衰,劝诫君王励精图治匡扶正音。白居易的《长恨歌》《霓裳羽衣歌》《江南遇天宝乐叟》更是在盛世、亡国内涵外,又增添了神仙与爱情的意义,“霓裳羽衣”意象实现了综合性描写,这为诗人们广泛借鉴。尤其是《霓裳羽衣歌》中详细的歌舞场景与舞姿、乐曲的描绘,更是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想象素材。王建的《霓裳辞》、刘禹锡的《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诗中的爱情、仙境因素,以及流露出的淡淡哀伤与清冷之感,同样树立起凄清风格的典范。
至此,“霓裳羽衣”意象基本已凝结,而后“霓裳羽衣”成为一种事典,一种共同的情感表达,诗人在使用典故抒发己怀的同时,又从不同的角度再次丰富强化“霓裳羽衣”蕴含的意义,使之经典化,促使“霓裳”入诗的盛行。
三、中晚唐乐舞诗中“霓裳羽衣”的审美特征
中晚唐诗人关注到了《霓裳羽衣曲》,并将其化为诗中意象借此表达心中之情,不同的生活年代,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个人选择,赋予了“霓裳羽衣”不同的审美体验。然而诗人笔下的“霓裳羽衣”又透露出一定的相似性,在歌舞宴饮的娱乐与追怀反思的深刻中,共同建筑了“霓裳羽衣”的审美。
(一)“乐”与“悲”的交融
整体上,娱乐宴饮中的“霓裳羽衣”意象被视为生活享受,释放的是一种积极昂扬的情感力量,而在咏史怀古的诗作中则盛世之音与亡国之音并重,盛世中暗含亡国之意,悲哀之情为主。加上清冷仙境的塑造与李杨的爱情悲剧,霓裳羽衣更多的是一种冷色调。
宴饮中的“霓裳羽衣”意象,多是诗人在艺术欣赏中有感而发,这些诗作多描绘表演者优美的姿态、华丽的服饰、流转的眼波以及乐曲的美妙,在觥筹交错的欢娱中,自然流露出闲适之感。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花蕊夫人与和凝的《宫词》以及李太玄的《玉女舞霓裳》皆是典型代表。这种“霓裳舞罢君王笑”[1]8483“排比管弦行翠袖”[1]4986的享受自是一种昂扬的生命力,让人联想到盛唐的富足生活。不过宴饮中的“霓裳羽衣”数量较少,且多集中于白居易一人。
诗人大多认同“霓裳羽衣”可代盛世,哪怕是在悲叹昔盛今衰的咏史怀古诗中,也可以此指代盛世。薛能《华清宫和杜舍人》、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皆将歌舞霓裳视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但在富足奢华的盛世场景塑造中,诗人又以此为例,这就暗暗肯定了歌舞霓裳的盛世内涵。
与之相似,在一些直接将《霓裳羽衣曲》看为盛世象征的诗作中,歌舞霓裳也带有了一份悲凉的情感。安史之乱的伤痛渗入了诗中,哪怕是酷爱此舞以赞赏态度为主的白居易,也有“开元遗曲自凄凉”[1]5108的句子。舒元舆读史书发“霓裳烟云尽,梨园风雨隔”[1]5585之叹,感叹世事变迁,“霓裳”的悲凉之意更是力透纸背。
而在“霓裳羽衣”的仙境象征中,除却登临仙境听霓裳仙曲的欢娱外,也包含了对求仙访道的批判。玄宗是道教的狂热推广者,道观道士在玄宗朝急剧增多,于是批判求仙访道的诗人便借写霓裳劝诫世人神仙不可求,鲍溶的《霓裳羽衣歌》便是如此,点明“神仙如月只可望”[1]5540,以此规劝世人不可沉溺于仙道。爱情的欢娱则在描述李杨二人纵情歌舞的宫廷生活,但最终落脚到战争与死亡,反思杨氏专权与女色误国。
正是在欢娱与反思的缠绵交织中,缅怀昨日与遗憾今夕的惋惜痛恨下,共同铸就了“霓裳”的朦胧多义之美。
(二)中晚唐乐舞诗中“霓裳羽衣”意象的审美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与晚唐诗人的霓裳审美有着明显转变,中唐时期更多为盛世感慨与宴饮之乐,晚唐则更注重亡国之意与悲凉之感。
中唐诗人多将《霓裳羽衣》视为唐代艺术的典范之作,只有大历年间的李益明确提出此曲是亡国之音。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中唐时期诗人笔下的歌舞霓裳是生活的逍遥。“皆言此处宜弦管,试奏霓裳一曲看。霓裳奏罢唱梁州”[1]5204,诗人流露的是对艺术的欣赏,是一种典雅闲适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感叹现实的衰落中,也充满了盛世怀念之感,“霓裳法曲浑抛却,独自花间扫玉阶”[1]3419,宫人独自一人扫去闲庭落花时,也会回忆起当年歌舞霓裳的盛世。
到了晚唐,霓裳羽衣则更为悲凉抑郁。除了温庭筠的两首诗明确将《霓裳羽衣曲》作为盛世繁华的象征,并将由盛转衰归结为天命而非歌舞霓裳外,其余诗歌大都以其为明皇贪图享乐不务政事的罪证。杜牧、张祜、李商隐、李约、吴融等人的怀古诗都将华清宫、杨玉环与霓裳联系起来,“昔闻欢娱事,今日成惨戚”[1]5585,正是梨园舞霓裳的欢娱酿成今日之悲惨。
此外,晚唐“霓裳羽衣”的仙境表达也更加神秘化、私人化。中唐诗人以“霓裳羽衣”象征仙境,多与明皇仙界得曲的传说相关,并时有批判沉溺求仙访道的意味。或者以霓裳在仙界而非人间表明盛世不再,又或者以霓裳仙乐夸赞他曲美妙、形容舞者舞姿动人。而晚唐诗人则直接将歌舞霓裳当做神仙世界的产物,神仙宴饮时歌舞霓裳,辛勤修道成仙后的一大表现就是可闻霓裳曲,“武皇含笑把金觥,更请霓裳一两声”[1]7402,曹唐更是把玄宗观霓裳放入游仙诗中。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传统乐论中“乐与政通”的审美。审乐知政,“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3]476-477道调法曲与胡乐融合,华夏正音被扰乱,而后招致胡患,天宝十三年(754年)《霓裳羽衣曲》改乐,正是吸收融合了胡乐。歌舞的华丽奢侈、女子的妖娆妩媚、胡乐的侵扰,都集中在了这一处,如果诗人将霓裳曲视为玄宗创作的法曲,则多盛世评价,若将天宝十三载改乐视为来源,则为亡国之音。
但仔细观察诗歌,大多诗人都将《霓裳羽衣》视为法曲,忽视了本身的胡乐成分。既然都认同《霓裳羽衣》的法曲地位,即一定程度上认同歌舞霓裳的盛世象征,为何晚唐诗人更注重悲的表达?晚唐诗人虽然忽视了胡乐成分,却将目光转向了奢侈与女色成分,于是诗中着重描述与杨玉环、华清池有关的宫廷生活。“侈乐”带来的政治动荡,同样让文人士大夫惋惜,并引以为戒。
第二,中晚唐社会环境的制约促使对“霓裳羽衣”审美的差异。虽然安史之乱后大唐再无力恢复往日光辉,但生活在“中兴”时期的诗人们,尤其是宪宗时期的诗人们自然对乐舞有着更为积极的态度,他们笔下的“霓裳”都带有恢复盛世的渴望与希望。晚唐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专权把持朝政,党争严重,浓烈的艺术情感在动荡的形式下越发冷淡,衰亡之势引发悲叹,于是“霓裳”也带上了凄冷抑郁的色彩。与此同时,求仙访道之风日益加重。虽然道教在唐代一直受到重视,但晚唐时局的动荡、藩镇之间的斗争一系列事情都指向一个终点,即皇帝渐渐失去对时局的控制,君权神授成为皇帝权利的印证,道教必然受到极度推崇。长生不老以及仙境的缥缈也就成为诗人的精神寄托,翁承赞的《寄示儿孙》最为典型。
第三,史学观念的加强促使晚唐咏史怀古诗大量创造。相较于中唐诗人宴饮的“霓裳”,咏史怀古的“霓裳”更多出现在晚唐诗人笔下。唐文宗时“唯三史则超一资授官”[4]1401,官方将史学提高到其他学科之上,加上前代积累的丰富史学典籍与印刷术进一步推广,诗人的史学素养无疑得到提升。在绝望的晚唐社会,可被视为导致大唐走向末路的《霓裳羽衣》,成为诗人愤慨抨击君王的靶子。在过往的富庶繁华与今日的荒凉萧条中,诗人借古讽今、以古鉴今,或是以此讽刺君王荒淫奢侈的生活,或是警醒求仙访道的虚无,规劝君主励精图治,即使是在穷途末路之时,依旧期待国家能再次振兴。
在中晚唐诗人的不断创作中,盛唐大曲《霓裳羽衣》逐渐成为独立的“霓裳羽衣”意象,月宫求仙、天宝改乐、历史转折、宫闱爱情,为诗人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素材,并形成盛世象征、亡国之音、仙境塑造、爱情象征四大内涵。由于战乱,《霓裳羽衣曲》从宫廷走向民间,在中晚唐宴饮之风与蓄伎之风的推动下,歌舞霓裳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出现以此表达闲适生活的诗作。但在“乐与政通”的审美传统以及无法回避的历史伤痛下,“霓裳羽衣”整体透露出一种悲凉之感。又因“文变染乎世情”[14],中唐与晚唐的社会差异,使得中唐诗人的霓裳羽衣更多追忆与闲适,而晚唐则更为抑郁且更富道教色彩。经中晚唐诗人的书写,“霓裳羽衣”成为固定意象并被后世接受,为宋元明清乃至当今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不竭的灵感来源,在不断地创作中,该意象更加丰富饱满,形成了极具魅力的霓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