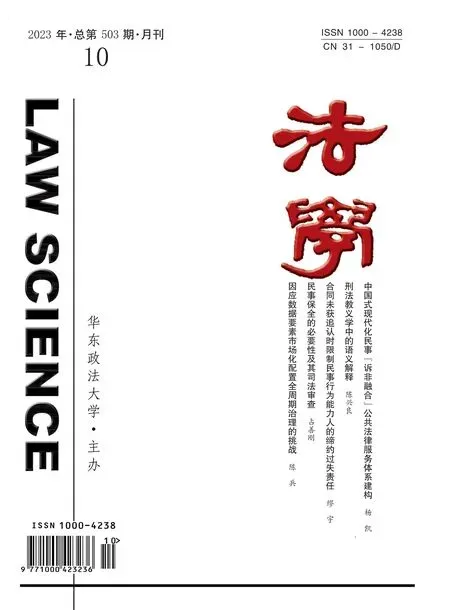正当裁判对依法裁判的超越与融贯
●张 途
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法官在一般案件中负有“依法裁判”的义务,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法官常常需要超越依法裁判的范畴,以“正当裁判”为目标作出裁判。对于正当裁判与依法裁判在司法中的关系,理论上的回答一般包括以下几类观点:第一类观点采取依法裁判不可动摇的强立场,对正当裁判秉持怀疑态度,主张依法裁判必须作为一种强裁判主张得到捍卫。〔1〕参见杨知文:《“同案同判”的性质及其证立理据》,载《学术月刊》2021 年第11 期,第116-117 页;孙海波:《疑难案件否定法治吗——依法裁判立场之重申》,载《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5 期,第57-71 页;蔡琳:《“依法裁判”:一种强主张的论证》,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2 期,第52-62 页。第二类观点采取以依法裁判为主、兼顾正当裁判的中间立场,认为司法裁判不仅要实现依法裁判的目标,同样要追求正当裁判的目的,依法裁判是法官的基本义务,正当裁判是更高要求,正确的司法裁判既要满足依法裁判,也要满足个案正义等。〔2〕参见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1 期,第278 页;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 年第1 期,第176 页;宋旭光:《依法裁判与民意诉求——基于弹性法律秩序的方法论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 年第2 期,第51 页。第三类观点认为严格依法裁判是不可能的,对依法裁判的过度普遍化反而会阻碍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因而需要超越依法裁判。〔3〕参见泮伟江:《超越“依法裁判”理论》,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2 期,第19-28 页。总的来说,大部分的讨论将正当裁判视作与依法裁判针锋相对的裁判理念,正因如此,目前学界对正当裁判在司法裁判中承担何种角色相对持怀疑态度。
本文对正当裁判的态度相对积极,将在说明正当裁判的内涵基础上论证正当裁判并非与依法裁判相冲突的裁判理念。正当裁判虽有时超越依法裁判,但两者本质上相互融贯。司法裁判的本质目标是正当裁判,依法裁判是实现正当裁判不可或缺的手段,其中包含两个面向:其一,在疑难案件中,依法裁判与正当裁判只存在或然性的交叉关系,因为在疑难案件中为了达到正当裁判的目的,法官有时需要超越依法裁判(此面向以下命名为“超越命题”);其二,在通常情况下,依法裁判蕴含了正当裁判的要求(此面向以下命名为“融贯命题”)。在这两个命题中,融贯命题更为根本,只有理解两种裁判的内在逻辑关联,才能理解为何在一些情形中正当裁判超越了依法裁判——这种超越正是两者内在融贯的要求。
一、正当裁判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内涵
(一)正当裁判的实践基础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三类疑难案件蕴含超越依法裁判进行正当裁判的可能。第一类是规范缺失或者因规范效力层级太低导致实质上规范缺失的案件,如2014 年的“无锡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我国现行法律对冷冻胚胎的权属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且此案涉及的代孕合法性问题,目前我国最高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也只是卫生部的部门规章。第二类是法律规范中的语言和规范的开放性结构〔4〕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 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284 页。给法官带来指引不确定的案件,如2005 年发生在我国广西的一起交通肇事案就考验了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中的“死亡”是否包括宣告死亡。〔5〕参见陈景辉:《“开放结构”的诸层次:反省哈特的法律推理理论》,载《中外法学》2011 年第4 期,第671 页。第三类是法律规范虽然给出了清晰的指引,但是严格依法裁判会引发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巨大争议的案件,2016 年发生在天津的“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同样如此,一方面,《刑法》对非法持枪罪的定罪在规范上是清晰的(尽管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有争议),另一方面,一审对赵春华以非法持枪罪作出三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判决极大挑战了人们的道德直觉,至少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判决。〔6〕一审判决参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5 刑初442 号刑事判决。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改判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 刑终41 号刑事判决。第三类疑难案件最明显地体现了正当裁判的实践基础,因为前两类疑难案件的判决有可能被解释为依法裁判,但在“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这类具备清楚制定法的疑难案件中,法官显然并未依照制定法作出裁判。
以上疑难案件带来的理论问题是,法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越依法裁判进行正当裁判?正当裁判会动摇依法裁判的基本司法立场吗,两者是何关系?前者主要涉及法律适用问题,这在实务界和理论界一直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也引发了众多理论解决方案。后者的问题更为根本,事关裁判的基本目标及法官的伦理责任,因此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依法裁判即法官依据法律进行司法推理和论证。〔7〕参见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 年第1 期,第174 页。一般而言,依法裁判中的“法”不仅包括狭义的制定法规则,还包括判例在内的构成整个教义学知识体系的规范。〔8〕参见雷磊:《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载《法学家》2019 年第4 期,第23 页。依法裁判是依据构成教义学体系的实在法规范进行裁判,正当裁判的内涵相对不太清晰,但厘清两者关系必须澄清正当裁判的概念内涵。
(二)正当裁判的理论内涵
在“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如果说法官最终采取的是正当裁判而非依法裁判,那么看起来正当裁判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涉及法官对法律规范背后实质价值的衡量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正当裁判经常被等同于道德裁判。学界之所以对道德裁判疑虑重重,是因为道德价值本身争议极大,同时道德哲学缺乏法教义学方法支持,且道德论证极有可能演变成意识形态或利益之争,无法像法教义学以科学的方式解决法律规范冲突一样来解决道德争议等。〔9〕参见孙海波:《论道德对法官裁判的影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5 期,第88-89 页。以上疑虑都有道理,因为在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中,一般性道德观念确实受制于广泛的价值分歧,即不同的人对道德观念分享不同看法,且这些分歧往往不可调和。同时,人们对一般日常道德观产生分歧这件事本身亦是合理的。〔10〕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6-57.现代多元社会意味着我们无须追求以某种单一价值共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价值分歧的合理存在有可能使以任一特殊道德观念作为裁判基础,引发更大的社会分歧,不利于一个现代多元社会的正义和稳定。因而,一旦正当裁判等同于道德裁判,纷繁的道德争议和道德观念将被带入法律适用中,构成对法治的挑战。
但是,正当裁判并非道德裁判或个案正义,只需要裁判结论具备足够的可证立性即可。本文同意阿列克西的观点:可证立性即规范及其结论的可接受性,而可证立性总是与其证立程序相关,建立在一定的理性程序基础之上。〔11〕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9 页。但与阿列克西不同的是,本文认为作为可证立性基础的理性证立程序并非追求结论的正确性,而只追求结论的合理性,因为正当裁判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政治道德共识基础上的裁判,不是建立在一般日常道德共识基础上的道德裁判。
与一般日常道德观念不同的是,政治道德的范畴更狭窄,突出关注的是公民参与到政治制度中涉及的权利和义务。〔12〕See 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27-328.政治道德因此较日常道德特殊,政治道德中的原则,如自由、平等、公平等并不一定适用于日常道德的评价标准或与其有必然关联。作为一个范畴相对狭窄、特殊的概念,政治道德本身具有独立的正当性,即便其不依赖某种特定一般日常道德观念,也是独立成立的(freestanding)。它的独立性在于政治道德是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和实现的,而一个道德观念只有在承载它的社会形态是政治属性的情况下才是政治性的道德。〔13〕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140;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4(1997): 776-777.政治道德之所以能独立于日常道德成立,是因为它一般基于公共生活的基础性价值,因而非常重大且不可被轻易逾越。〔14〕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9.此外,在证立程序上,如果政治道德足以得到社会中每个人的日常道德观念的支持,或至少不与个体的道德观冲突,那么政治道德就可被视作社会基本法律结构的基础。〔15〕同上注,第137、393 页。因此,建立在政治道德共识基础上的正当裁判就意味着,法官对裁判提供的理由能被绝大部分人接受,或至少与自己的道德观念没有根本冲突。〔16〕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xlvi.
正当裁判的实践基础在于疑难案件背后的“疑难”在根本上是相竞价值的冲突,法官有可能要对案件涉及的价值问题作出判断或进行价值排序。同时,正当裁判的理论内涵决定了案件涉及的价值判断或排序无须深入一般日常道德。当然,不乏一些理论家依然将疑难案件中的正当裁判解读为依法裁判,而这将面临诸多理论困难。
二、超越命题:正当裁判对依法裁判的超越
与其说理论家怀疑的是正当裁判,不如说是他们夸大了依法裁判的范畴,试图通过改造法概念或解释论将正当裁判统摄于依法裁判(正当裁判→依法裁判)。这种思路的大致逻辑是:裁判中出现的众多根据并非都是法律,法官应当采纳的根据就是法律,不应采纳的根据就不是法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裁判根据是不是法律。如果裁判根据是法律,那么这些根据对法官产生义务,如果这些根据不属于法律,那么法官无须受其约束。“法官应当如何进行裁判”的道德问题化约为“什么规范是法律”的概念问题。可能正是在“法官应当如何裁判”问题实践重要性的驱使下,何种规范具备“法律”资格的法概念论辩(即法律实证主义和非法律实证主义分野的核心论辩)才主导了理论法学界半个多世纪。本文要澄清的是,法概念讨论无法等同于“法官应当如何裁判”的问题,因为无论根据何种法概念理论还是法律解释论,在典型的疑难案件中,法官们事实上的行动都已经是正当裁判。
(一)非实证主义消解法概念
在非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沃金看来,“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本质上受到法律在道德上善恶的影响,“法律在本质上就是政治道德的一部分。”〔17〕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05.一个规范是不是法律正是法官在裁判中如何辩护他的结论的问题。〔18〕参见陈景辉:《法理论的性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德沃金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载《清华法学》2015 年第6 期,第10 页。法官需要为自己的裁判结论提供正当依据,这一依据有可能成为法律,至于能否最终获得成为法律的资格,则依赖该依据是否具有足够坚实的政治道德基础。
德沃金认为,法概念问题包含了事实和价值两个面向的考虑。其一,是事实上的“符合”(fit),即这一规范或者法官在裁判中的某个方向上的决定是否有过往判例资料或制定法。“符合”是裁判依据是否具备法概念的门槛条件;其二,更重要的是价值上的面向,如果律师、不同法官给出的不同裁判依据都达到了“符合”的门槛,那么评判的标准就落到了“最佳辩护”(best justification)上,即哪一个依据能最好体现法律实践在政治道德上的价值。〔19〕See 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11.既符合来源又具备最佳道德辩护的裁判依据就是真正的法。法官在决定应当以何种根据进行裁判的同时,就对该根据的法律属性作出判断。例如,对于“泸州遗赠案”,德沃金也许会如此来解决法官面临的裁判困境:不是因《继承法》的规则太不道德而不能被适用,而是在该案中《继承法》规则不能被视作有效的法。如果这一法律因太不道德而不能被视作法,那么法官依照该法律作出裁判的义务自然也因此消失。换句话说,不是法官要依法裁判,而是司法裁判的结果决定了什么是法律。
这种对疑难案件的处理看似符合人们的直觉,因为似乎消解了疑难案件给法官带来的是否要依法裁判的实践困境。在疑难案件中,法官不是通过查明事实决定哪些规范或根据具有拘束力;相反,需要全面考虑裁判中可能的规范或根据,决定哪个根据满足符合和最佳辩护的条件才是真正的法律。“应当以什么规范或根据来裁判”和“什么是法律”两个问题合并后,就从根源上消解了疑难案件带给法官的实践困境,因为正当裁判一定就是依法裁判(正当裁判→依法裁判)。将正当裁判等同于依法裁判就使法官的政治道德责任决定了法律的概念,法官在裁判活动中只需考虑自己的政治道德责任。然而,将法概念问题与政治道德问题完全融为一体将带来三点主要困难:第一,无法解释很多常见的法律实践,因为有相当多道德上并不完备甚至有缺陷的法律被适用和执行。〔20〕See 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8.第二,使法概念问题在逻辑上依赖法实践的结论,但实践结论具备较强的偶然性色彩,无法回应一般性的法概念问题。第三,使“什么是法律”问题的重要性被抵消,导向概念上的法律消除主义(eliminationism)。〔21〕消除主义认为,不存在一种独立的法的概念,或者说法律谈不上具备本身相对于道德的特殊规范性。类似观点参见Mark Greenberg, The Moral Impact Theory of Law, Yale Law Journal 123 (2013): 1288.Scott Hershovitz, The End of Jurisprudence, Yale Law Journal 124 (2014): 1160.Lewis A.Kornhauser, Doing Without the Concept of Law, NYU School of Law,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15-33 (2015).Hilary Nye, The One-System View and Dworkin’s Anti-Archimedean Eliminativism, Law and Philosophy 40 (2021):247-276.其中消除主义的困难包括两方面:其一,除非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是法律”的概念问题在裁判之外不重要的观点,否则无论从概念上还是教义学上我们都很难认为法官在具体个案中未采纳的法律规范不是法律;其二,虽然法律的义务性要求主要指向法官,但法律对广大普通人的指引同样重要,因为广大的普通人需要依赖相对确定的法律来计划、指引和安排自己在法院之外的生活。在法院之外,法概念问题对普通人依然重要。〔22〕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 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9 页。
(二)实证主义无法解释自由裁量的义务性
法律实证主义认为,什么是法律不是由法官应当如何裁判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事实决定。〔23〕在法概念的问题上,现代自然法理论的主流,以约翰·菲尼斯和罗伯特·乔治为代表的新阿奎那主义者们广泛地接纳和承认了社会事实标准。See Robert George, Natur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52(2007): 55-75.不论是早期奥斯丁版本的法律实证主义,还是后来精细化的哈特版本和拉兹版本的法律实证主义,对法概念的标准都建立在社会事实基础上,法律本身的善恶、正义、合理与否并不在其是否是法律这一问题之内。
社会事实虽然能清楚地确定法律的界限,但是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常常需要超越法律的界限,无法忽略实在法范畴外的规范。例如,“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社会事实命题意味着《刑法》本身对非法持有枪支的规定就是法律,但一审法院对赵春华的五年有期徒刑判决又在公平和自由的政治性道德上深受挑战。因此,如果根据社会事实命题对法律进行界定,那么就会得出法院对赵春华的终审判决是正当裁判而不是依法裁判的结论。
不过,支持社会事实命题的实证主义理论对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行动有自己的解释,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拉兹看来,法官的能力既包括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也包括道德能力。在疑难案件中,有能力的法官有时需要依赖道德或其他非法律的论证进行自由裁量,即造法(developing the law)。〔24〕See Joseph Raz, Legal Positivism and The Sources of Law, in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8-50.但法官并非在不用受到任何标准约束的意义上拥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25〕See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1-39.如果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据依然在一定范畴内(法官若引用自己的个人信念或偏好作为自由裁量的根据将无法成立),那么无论该范畴由原则还是政治道德限定,法概念命题本身都无法解释法官裁量的自由为何不是无边界的,以及为何要被原则或政治道德限定的问题。因此,以社会事实作为法概念依据无法说明正当裁判为何属于依法裁判(正当裁判→依法裁判):如果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仍必须考虑法外因素和要求,那么法官仍然是超越法外要求作出正当裁判。
应当说,通过法概念论的改造能更加清楚说明,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遵循的是正当裁判。若要将正当裁判统摄于依法裁判框架,将面临以下两大都不具有吸引力的选项:要么需要接受“什么是法律”的法概念问题已被“法官应当如何裁判”的道德问题消解;要么面临法外的自由裁量为何仍然受到限制的拷问。因此,与其说法官在疑难案件中依然在依法裁判,不如说法官真正在做的是正当裁判,一方面,应当如何裁判的道德义务问题与“什么是法律”的概念问题可以清晰分离,另一方面,在正当裁判下的自由裁量并非完全自由或任意的,因为它依然处于政治道德的指引下。
(三)法解释论陷入循环论证
法律解释论的思路是将正当裁判统摄于依法裁判。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规范采取不同法律解释可能导致完全相反但同样正当的判决,但无论怎样的裁判结果都完全可能通过解释论与依法裁判相容,这就会导致依法裁判陷入空洞。同时,如果将任何一种法律解释下的裁判都解读为依法裁判,那么就会忽视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为是否合理而非是否合法。
从法律解释角度看,法律文本和演绎推理本身的局限性导致法官在面临疑难案件时的解释依然属于依法裁判,因为法官解释可以救济法律文本的不足,使本来含义模糊的文本变清晰,压缩自由裁量的余地。而且,法官解释不是任意解释,而是根据法律的解释,因此一个开放性的依法裁判主张依然能够成立,甚至更有说服力,即法律解释补充或者强化了法官依法裁判的义务。〔26〕参见蔡琳:《“依法裁判”:一种强主张的论证》,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2 期,第57-58 页;王云清、陈林林:《依法裁判的法理意义及其方法论展开》,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2 期,第35、37 页。但这一逻辑是倒果为因的,即不是法律解释补强了依法裁判,而是为了维持依法裁判,法官通过解释弹性扩大了法的内涵。一旦对依法裁判中的法以制定法、文义及体系解释为轴心作出限定就会看到,超出这些解释的法律解释是在为正当裁判服务。例如,在“烈犬攻击人案”中,吴某带领宠物狗参加上海宠物领养日活动,在活动当日被未佩戴嘴套的罗威纳犬咬伤。当时的《侵权责任法》第80 条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吴某要求罗威纳犬的救助人陆某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陆某辩称自己并非这条罗威纳犬的饲养人,救助完成后这条烈犬一直被放在流浪狗基地饲养。法院认为,该案中救助人陆某系致人损害的罗威纳犬的饲养人,应对吴某承担侵权责任。〔27〕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 民终13012 号。可见,该案的争议之处在于法律文本规定的损害责任人是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救助人在不在这一范畴内至少在文本上不明确,因此需要法官在审判中对救助人是否属于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范畴作出判断。一审法院认为,该案致人损害事实并非发生在流浪狗基地,陆某从流浪狗基地接犬参加上海宠物领养日活动的行为意味着其有义务控制该犬以避免危险的发生。二审法院进一步补充认定,陆某系致人损害的罗威纳犬的饲养人,应对该烈犬咬伤吴某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28〕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 民终13012 号。该案正属于哈特所说的文本本身包括法律规则中的“开放性结构”存在的典型情境。在这个案件中,法官对“饲养人”或“管理人”作出扩大解释,将救助人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第80 条规定的“管理人”范畴。这似乎是一个依法裁判。
假设法院不将陆某认定为饲养人或管理人,而认定为救助人,救助完成后并未如同宠物饲主一样持续承担饲养或管理工作,那似乎也很难认为这一判决不是依法裁判。也就是说,无论法院将陆某认定为饲养人还是非饲养人,都很难说法院不是在依法裁判,因为法律中饲养人或管理人的内涵可以在具体案件中被作扩大或者缩小解释,这种弹性空间使依法裁判极难被违反,从而陷入空洞。因而不是法律解释补强了依法裁判,而是法律在特定情况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依法裁判极难被法律解释突破。通过法律解释说明正当裁判就是依法裁判可能陷入循环论证:论证的目的本是证明法官在疑难案件中对不特定规范作的法律解释依然是依法裁判,但论证的起点是绝大部分解释都与依法裁判中的“法”相容。相反,一旦跳出该循环论证,一审和二审法院在该案中所作的法律解释都是试图在法律规范不明确的前提下为何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提供一个最具有正当性或可证立性的说明,这将受到的评价也不是其是否合法,而是其是否合理或正当。因此,在存在“开放性结构”的疑难案件中,法官的法律解释面临的评价不是这一解释是否属于依法裁判,而是这一解释是否是好的或合理的解释,以及在这一解释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是否为正当判决。
在疑难案件给法官造成的困境中,法官事实上常常超越法教义学标准中的法律寻求正当裁判。除非将法官的裁判结论等同于“什么是法律”,否则在疑难案件中无论法官是“越法裁判”进行自由裁量,还是依靠法律解释,判决的依据都并非来自实在法本身。法官在以上疑难案件中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依法裁判,而是正当裁判。
三、融贯命题:依法裁判应蕴含正当裁判
超越命题展现了正当裁判对依法裁判的超越,但这并不说明两者是对立的,相反,对超越命题的完整理解建立在融贯命题基础上:正当裁判之所以能超越依法裁判,是因为依法裁判是正当裁判的手段,服务于正当裁判的目标。要论证依法裁判服务于正当裁判,就需要论证依法裁判不是一个独立的裁判目标,这需要从法的安定性这一价值入手。依法裁判、正当裁判和法的安定性三者的关系将凸显依法裁判与正当裁判的融贯:依法裁判之所以构成正当裁判的手段,是因为在大量的简单案件中两者的要求是重合的,法官以依法裁判实现正当裁判。
(一)依法裁判与法的安定性:不完全义务
相对于正当裁判对实质正义的贡献,依法裁判被认为在促进形式正义上具有构成性的功能,尤其有助于法的安定性或裁判的可预测性,这也是包括依法裁判强理论(正当裁判怀疑论)和中间立场在内都认可的依法裁判的独特优势。
具备安定性的法律能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可预测性,使他们足以在法律框架内控制、引导和计划自己的生活。〔29〕参见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载《法学家》2015 年第4 期,第2-3 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公式”赋予法的安定性相较于其他价值的优先性。依法裁判对法的安定性的保障体现在它取代了法官对个案实质正义的判断,法官不能随意再以个案正义为由抵抗依法裁判,如此才能保障判决的可预测性和法的安定性。法的安定性对“依法裁判作为手段”的挑战在于,法的安定性被视为与实质正义同等重要的形式正义原则,而法律的形式主义特征恰恰是“法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核心特征。”〔30〕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 年第1 期,第175 页。即便在一个实质不正义的法体系中,法的安定性本身亦有价值,从而依法裁判在独立于正当裁判之外亦有其独立重要性,不仅仅只是正当裁判的手段。因此,在疑难案件中,法官若要超越依法裁判进行正当裁判,需要提供更强的理由,承担更重的论证责任。〔31〕参见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5 期,第130 页;雷磊:《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载《法学家》2019 年第4 期,第23-24 页。
但是,并非只有依法裁判才能满足法的安定性,依法裁判是法的安定性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这一分析可以借助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的概念来解释。康德将道德上的要求或者道德义务分为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和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是严格的、指向具体行动的,一般来说涉及的都是消极的禁止性行动。违反完全义务(比如杀人、对他人作出虚假承诺等)在道德上是可归责的。不完全义务通常涉及积极行动,对它的实现在道德上是可赞许的,如发展自身的才能或帮助他人获得幸福等就是不完全义务。〔32〕See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of Metaphysics of Morals, Mary Gregor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4: 422-424.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这一区分被进一步地清晰化为正义义务(duties of justice/right)和德性义务(duties of virtues)。前者可以被强制,后者受制于道德评价,无法被强制。不完全义务仅指向目标,并不要求具体行动对于何种具体行动有助于实现好的目标给行动主体留下了一定自主选择的空间。这意味着,无论行动者的具体行动看起来是否与目标一致,都有可能满足不完全义务,同时,行动者亦无须在所有情形中都以某种特定具体行动去促进目标的实现。〔33〕不完全义务的这一性质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之间并不存在冲突。See Lawrence Masek, How Kant’s View of Perfect and Imperfect Duties Resolves an Alleged Moral Dilemma for Judges, Ratio Juris 18(2005): 415-428.
法的安定性作为一种法体系的目标,给法官施加的正是一种不完全义务,因而对以何种行动来实现该目标不存在特定的具体要求。法的安定性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人们对于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形成稳定预期的社会秩序,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亦常常来自社会惯习和常识的累积。当一个人在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往往依靠社会惯习和常识也能预期该如何遵守交通规则、进行日常商业交往、不能随意暴力对待他人等。既然在实在法不在场的情况下,人们也能做到有预期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依法裁判就不是法的安定性或可预测性这些形式目标的必要条件。对法官而言,在实在法缺失或实在法不合理时,依据社会惯习进行裁判反而能更好地维护法的安定性或可预测性。在20 世纪50 年代以前,中国尚无婚姻登记制度,相当多未登记过的老年夫妇在法律上不存在婚姻关系,当其中一方去世发生遗产纠纷时,法的安定性会要求法官超越依法裁判,判决给予另一方继承权。
(二)正当裁判不挑战法的安定性
既然并非只有依法裁判才能维系法的安定性,那么正当裁判亦未必挑战法的安定性,或许还可以维持法的安定性。这需要回到正当裁判与道德裁判的区分问题上,同时这一区分还将展现正当裁判的限度,即正当裁判在何种程度上能得到制约。一般来说,司法裁判常常需要满足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这两个目的,但这两个目的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34〕参见雷磊:《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载《法学家》2019 年第4 期,第23 页。即对法的安定性的保障需要依赖依法裁判来完成,判决的正当性有时又需要超越依法裁判才能实现,但超越依法裁判难免动摇法的安定性,其中的关键是,动摇法的安定性的不是正当裁判,而是道德裁判。因为在道德裁判中面临的是无法化解的根本性分歧(foundational disagreements),无法凭借赫拉克勒斯般法官的“上帝视角”以道德真理将其化解。相反,正当裁判中面临的政治道德之间的分歧仅是一种建立在基本共识基础上对具体结论的辩护性分歧(justificatory disagreements)。〔35〕这两种彻底与不彻底的分歧的区分参见Jonathan Quong, Liberalism without Perf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93.辩护性分歧意味着,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唯一正确答案是什么,甚至是否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但由于处于分歧中的几个候选答案均建立在政治道德基础上,因此均合乎情理。可以说,正当裁判与依法裁判都反对道德裁判,因为要求普通人接受基于某种自己无法理解或接受的道德观念的裁判是不合理的。
正当裁判与道德裁判的关键区分在于,基于政治道德的裁判未必满足道德真理,根据合理但是可能错误的理由(正当裁判)进行裁判是一回事,根据不合理的理由(道德裁判)进行裁判是另一回事。〔36〕See Lawrence Solum, Public Legal Reason, Virginia Law Review 92(2006): 1477.例如,在关于代孕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如果A 组结论都支持代孕,但理由不一,理由出自“代孕促进女性身体自由解放”是一回事,出自“传统伦理道德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另一回事。反之,如果B 组结论都反对代孕,但理由出自“代孕是对女性人格权的侵害”是一回事,出自“孕育与否都是天意,人力不可干预”是另一回事。在A 组(B 组)同样的结论中,前者理由来自政治道德,其理由未必一定正确,但内容是基于所有人都可能支持的政治道德,因而是合理的。后者理由来自一般性的日常伦理道德,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人对此存在根深蒂固的价值分歧,而这些分歧的根本性决定了,若基于一般日常道德进行道德裁判将进一步加剧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分歧,削弱法的安定性。
在一些疑难案件中,真正的困难发生在政治道德之间的辩护性分歧中。“泸州遗赠案”的争议就是对公序良俗与私法自治两大政治道德的分歧。政治道德中的辩护性分歧既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调和的。合理性在于,正当裁判关注的是结论的前提,不是为了指引法官在裁判中获得正确的结果,而是为了通过给法官裁判的理由施加程序性限制保障裁判结论的正当性,限制的并非裁判结果本身。〔37〕See 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4(1997): 770, 795, 798.可调和之处在于,正当裁判追求的目的不是裁判结论在道德上的唯一正确答案,而是为个案正义的结果提供可证立的条件。因为政治道德并非标准型概念,关于何为正义、何为自由、何为平等等问题的回答无法依赖一个确定的标准。对政治道德的理解必须围绕对它的诠释进行。〔38〕See Ronald Dworkin, Justice in Rob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6.对同一个政治概念的诠释可能包含了几种同样重要但会驱使法官们作出相反判断的价值。这些价值的重要性旗鼓相当,如何排序都是正当的,尽管排序结论未必一定完全正确。〔39〕See 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4(1997): 798.政治道德如同一个滤芯,在裁判中过滤掉非政治属性的、一般性的日常伦理道德,只要法官的裁判是建立在政治道德基础之上的,它就不致引发激烈的社会分歧,人们就有理由接受其正当性。
此外,正当裁判中的辩护性分歧既可以建设性地为未来的司法裁判提供方向,又可以为人们提供进一步理解政治道德的指南。因为政治道德的分量是一个随实践向前的动态过程,对于相竞政治道德的诠释或者更佳政治道德的追寻亦始终在不断向前的司法实践中变动,只要这一变动始终处在政治道德的范畴内。因此,超越依法裁判的道德裁判因其易陷入不可调和的价值分歧而伤害法的安定性,而超越依法裁判的正当裁判并不会如此,它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由道德的政治性质制约,并不挑战整个安定的法体系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
(三)法的安定性预设正当裁判
根据正当裁判的内涵,正当裁判与法的安定性至少相容。对正当裁判和法的安定性的关系更进一步的论证是,当法体系失灵时,如果总是以依法裁判维系法的安定性,那么这种安定性或许不值得维持。
法的安定性之所以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重要价值,是因为稳定的预期对人们安排自己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但法的安定性本身有内在(intrinsic)价值吗?两个同样不正义的法体系,一个稳定不正当的法体系会比一个任意不正当的法体系更好吗?通常而言,前者的优势主要包括三点:第一点,人们至少可以预期自己的损失,从而提前规避可能的不正义和压迫。〔40〕参见王琳:《论法律原则的性质及其适用——权衡说之批判与诠释说之辩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 年第2 期,第97-98 页。第二点,政府至少在不偏不倚地、稳定地执行那些不正义的法律。前后一致的不正义依然比反复无常的不正义要好。第三点,在拥有法的安定性的社会,一般也能发现或培育实质正义或正当的法体系,即法的安定性作为形式性价值也能培育实质价值。〔41〕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9-60.
本文反对前两点对纯粹形式性的法的安定性的论证。固然两种不正义对于个人而言存在程度区分,个人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对于一个法体系而言,法的形式正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实质价值要求上。〔42〕参见王琳:《论法律原则的性质及其适用——权衡说之批判与诠释说之辩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 年第2 期,第98 页。法律在本质上是一项道德事业。从一个极为一般化也极为单薄的意义上说,法律与政府的建立既是为了防止人们不公地对待彼此,又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社会合作,法律的存在能更有效地实现人类的共同善。〔43〕See Robert George, Natur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52(2007): 70.换句话说,法律的存在在根本上服务道德目标,具备道德意义,尽管我们未必能就这一目标是什么达成共识,〔44〕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 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375-383 页;Scott Shapiro, Leg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13.至少一些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不可或缺,否则我们就无法分享一个共同的政治生活。一旦法体系本身是道德上恶劣的,法的安定性将失去意义。因为依法裁判被认为能够维护的那些价值,如法的安定性、可预期性等将最大程度上惠及那些从不正义中获利的人。〔45〕See David Lyons, Derivability, Defensibility, and Judicial Decisions, in Moral Aspect of Legal Theory: Essays on Law, Justice,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2.正如富勒所认为的:如果法律规则本身就错误甚至邪恶,那么为了法的安定性坚持依法裁判相当于助纣为虐。〔46〕See Lon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 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Harvard Law Review 71(1958): 654-657.
就上述第三点纯粹形式性的法的安定性的论证而言,并不能说明形式性价值培育实质价值,反而说明的是,形式性的法的安定性价值建立在法体系的实质价值基础上。正如上文对正当裁判与道德裁判之区分展示的,法的安定性既寄希望于其长期稳定、统一的裁判,亦依赖其裁判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一方面,当裁判结论建立在政治道德基础上时,其合理性将同样有助于人们建立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总是对裁判结果莫衷一是,那么该法体系即便达到了客观道德真理也难称可欲。因此,如果一个法体系通过长久而稳定的正当裁判凝聚了可靠的政治道德、社会规范及常识,那么法的安定性就会大体上被满足。真正伤害法的安定性的裁判方式不是超越法律的正当裁判,而是超越法律的不正当裁判。
一一反驳如上三点论证后可以发现,法的安定性或形式正义本身并无独立实质正义的内在价值,它的重要性附随法秩序的正当及合理性,这种对法的安定性的界定包含一个对法律和裁判关系重要直觉的挑战:当形式性的法的安定性失去实质价值基础时,依法裁判与法的安定性的充分关系将无法成立。
(四)依法裁判服务于正当裁判
根据前文所述可知,第一,虽然依法裁判能够有效维系法的安定性,但社会惯习、正当裁判等也能维系法的安定性。依法裁判不是法的安定性的必要条件,最多是充分条件(命题a:依法裁判→法的安定性)。第二,当依法裁判只服务于实质不正当法体系时,其法体系的安定性没有意义,法的安定性价值只有在一个具备基本正当性的法体系,即法的安定性预设了长久而稳定的正当裁判所塑造的基本正当法体系(命题b:法的安定性→正当裁判)中才有意义。
在命题b 中同时隐含了一个对命题a 的挑战,即当法的安定性失去实质价值时,依法裁判甚至都不是法的安定性的充分条件,这一挑战将直接撼动依法裁判的价值,与“依法裁判作为法官基本义务”这一根本直觉相悖。要化解命题b 中隐含的挑战以维系命题a,需要补充一个从命题b 推导至命题a 的关于依法裁判和正当裁判关系的命题c,使命题c 与命题b 的结合能够推出命题a(命题c+命题b →命题a)。要满足从命题b“法的安定性→正当裁判”加上该前提条件推出命题a“依法裁判→法的安定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命题c“依法裁判→正当裁判”,即依法裁判蕴含正当裁判。〔47〕命题c 不可能为正当裁判→依法裁判,否则加上命题b 就只能推出法的安定性→依法裁判,而正如文中说明的,安定性当然并非只有依法裁判才能做到,从而命题c 只可能是依法裁判→正当裁判。正因为依法裁判蕴含正当裁判,而非正当裁判蕴含依法裁判,所以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文中第二部分无论是法概念还是法律解释扩张依法裁判范畴的逻辑问题,都试图将扩大或目的解释后的裁判界定为依法裁判,而该逻辑正是正当裁判→依法裁判。依法裁判之所以能作为法的安定性的充分条件,是因为大部分时候法官正是通过依法裁判维系一个在政治道德上相对合理可靠而值得维系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的依法裁判就是正当裁判,体现了两者的融贯。
这两种裁判既超越又融贯的关系在逻辑上是否相矛盾?借助于拉兹“法律作为正当性权威宣称”的理论可以类比展现超越命题和融贯命题并无矛盾。所谓“法律作为正当性权威宣称”指权威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行动主体的目的。法律之所以能够作为正当性权威的宣称,是因为服从(conform)法律能提升人们对理性的服从,而之所以服从法律帮助人们服从理性,是因为法律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理性行动的目的(telos)。〔48〕See Joseph Raz,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Revisiting the Service Conception, Minnesota Law Review 90 (2007): 1018.换言之,法律服务的对象是包括道德在内的实践理性,它之所以能作为服务型权威的基础,是因为它提供的道德慎思比个体包括法官个人的道德慎思更好,提供的行动理由能帮助行动主体更好实现理性的要求,即更好地实现理性目标。同时,法律作为权威(的宣称),其作用体现在要取代行动者包括法官个人的道德反思,行动者不能再以道德为由抵抗权威。因此,一方面,法律的理性和范围来自道德的赋予和限定,另一方面,道德一旦进入法律,将破坏法律的权威。〔49〕See Jules Coleman, The Architecture of Jurisprudence: Part I, 1st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and Law Neutrality and Theory of Law (2010): 23.法律作为断然性权威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法体系的道德目标,但这一服务需要通过法官在适用法律中暂时将道德切断才能完成。
法律和道德的复杂关系能够凸显依法裁判和正当裁判同样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立法者将整个社会的政治道德共识凝聚到实在法体系中,作为裁判渊源的实在法因凝聚社会政治道德共识而获得其正当性。因而,在一个基本正当的法体系中,法律在最大程度或最基本层次上已经凝聚了一系列正当或合乎情理的(reasonable)政治道德标准。正当裁判是在政治道德共识基础上的裁判,依法裁判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尊重和稳固化这种共识基础。依法裁判为法官提供的行动指引能帮助法官更好地实现正当裁判,或者说依法裁判在通常情况下代表的就是正当裁判的要求。
另一方面,法官通过依法裁判将道德与个案裁判分离,不得轻易以道德质疑法律。这既是法律作为正当权威的功能,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整个法体系的道德目标。法律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区分私人观念和公共标准,当私人观念成为公共标准即法律时,它对全体社会成员均有拘束力。要做到这一点,法律就必须提供公共的、可确认的标准作为社会生活的指引,法律的指引不体现在它的内容是否满足某些道德要求,而在于它作为标准本身。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公众的标准,社会成员不能轻易从挑战标准正当性的角度为自己偏离标准找借口。〔50〕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 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298 页;Joseph Raz, Legal Positivism and the Sources of Law, in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1-52.此外,法律相较其他政治道德的特殊性在于强制性,而法院常常是展现法律强制力最直接的场所。当法院处理一个争议时,要作的决定将涉及国家权力并且常常是国家强制力的分配和使用,这对个体的权益产生真正直接甚至巨大的影响。这种强制力的影响亦决定了依法裁判特殊的重要性和超越其进行正当裁判的审慎性。因此,依法裁判虽然是正当裁判的手段,但它依然极其重要且不可被轻易超越。若法官以日常道德或其他考量轻易超越依法裁判,既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实现正当裁判的目标。
为什么法律和道德既分离又联系的论证可以换算为依法裁判和正当裁判既超越又相互融贯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两个挑战:其一,在法体系追求道德目标的志向中,公职人员与普通公民对法体系的政治道德责任是有区别的。其二,即便在公职人员中,法官承担的政治道德责任和立法者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51〕参见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 年第1 期,第175 页。更直接地说,就是法官如何可以承担依法裁判之上的政治道德责任,以及司法为何及有何资格担当政治道德守护者的角色。
笔者认为,对第一个挑战而言,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和公职人员在施加政治道德方面的影响能力、可用方式上是相当的,公民与官员对法体系的政治道德责任在本质上无必要做出区分。对第二个挑战而言,虽然法官的身份具备一定的特殊性,法官的任务确实在于尊重立法者的意志,并将立法适用于具体个案中,〔52〕参见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5 期,第128 页。但是首先法官和立法者的区别在于权力分工而不是道德责任上,只要法官依然需要在疑难案件中超越法律的限制作政治道德上的判断,法官的特殊性就没有特殊到使其和其他官员尤其是立法者有什么决定性的不同。〔53〕See Jeremy Waldron, Religious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Deliberation, San Diego L.Rev.30 (1993): 817.其次,疑难案件的困境足以使我们看到,法官依据实在法作出的判决只能是这一案件结果在法律逻辑上的可推导性(derivability),而不必然等于这一判决具备可辩护性(defensibility)。〔54〕See David Lyons, Derivability, Defensibility, and Judicial Decisions, in Moral Aspect of Legal Theory: Essays on Law, Justice,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6.司法判决对于普通人如此重要的关键原因在于判决中蕴含了个体如何行动的标准,这一标准需要来自判决的可辩护性或可证立性,而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可推导性。因此法官和立法者都对社会制度负有政治道德上的承诺,无论该道德承诺的内容是什么。〔55〕法官负有对整个法体系在价值目标上的责任。参见沈宏彬:《裁判的双重结构:论一种“建构—回应”的裁判观》,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2 期,第63-75 页。最后,正当裁判虽然要求法官有时超越依法裁判以深入个案的实质道德之争中,但正当裁判不是道德裁判,法官无须也无法以道德哲学家的身份为一般道德争议定分止争,只需深入个案涉及的政治道德,作出在政治道德上具有可证立性的裁判。
四、结语
在说明正当裁判的内涵基础上,本文论证的核心命题是正当裁判是司法裁判的根本目标,依法裁判是正当裁判的重要手段。在通常情况下,依法裁判蕴含了正当裁判的要求,两者内在融贯。在疑难案件中,法官为了得到理想裁判结论往往需要超越依法裁判进行正当裁判,因而两者呈现出相互交叉的或然性关系。融贯是两者更为根本的关系,只有理解两种裁判的内在联系,才能理解为何在一些情形中正当裁判超越了依法裁判的要求,超越正是融贯的结果。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对“依法裁判作为正当裁判的重要手段”的论证绝非忽略依法裁判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依法裁判的实践。依法裁判在维系整个法治的基础上极为重要,不可被轻易取代,它在法官对法体系的道德承诺中具有重要的道德分量。本文主张的仅是:依法裁判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对法体系政治道德的承诺,即正当裁判的承诺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