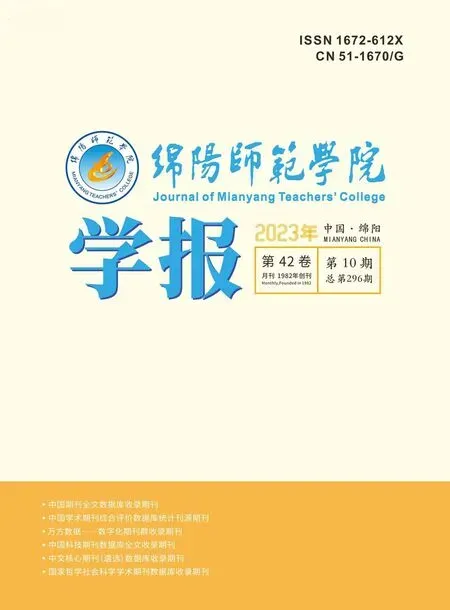《井》中海斯特边缘性解析
——论多维共同体建构的失败
肖 颖,于元元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1)
《井》是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1923—2007)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书创作于1986年,并于同年斩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井》秉承了伊丽莎白·乔利惯常的写作手法,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书中的女主角海斯特是一位身体残疾、离群索居的老处女,与父亲和祖母居住在小镇最大的农场内,幼时丧母的她领养了同样被社会抛弃的年轻孤女凯瑟琳。但随着祖母和父亲的故去,海斯特性格愈发扭曲怪诞,她无法忍受凯瑟琳离开自己嫁给他人,表面上她和凯瑟琳在农场中过着“桃花源”般的安宁生活,但平静之下暗潮涌动,海斯特对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实则暗含其病态的占有欲和无法控制的爱恋之情。随后一次意外肇事彻底撕裂了生活表面的平静:凯瑟琳在一次醉酒驾驶中不慎撞死一个男人,海斯特和凯瑟琳选择抛尸入井,但变卖农场的现金也疑似被男人偷走并一同埋于井下,阴差阳错之下她们亦被物质上的窘迫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反噬。凯瑟琳的精神状态处于崩溃边缘、沉溺于幻想之中难以脱身,海斯特也同样受到身心的双重折磨。乔利在《井》中使用了开放式结局,其背后的重重谜团埋葬在被封死的井口之下,而海斯特和凯瑟琳未来的生活也犹未可知。
澳大利亚学者对乔利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年代以前,偏重于乔利小说主题的阐释、人物和结构模式的分析,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以后,把文本放在后现代语境下,结合现代文学理论和叙事理论探讨乔利小说的意义[1]。国内对《井》的研究较少,且多聚焦于海斯特的边缘化书写、弗洛伊德人格解析以及女性主义解读等方面,但笔者认为,共同体建构的失败是造成海斯特精神世界危机的重要成因,与世界的割裂使得海斯特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难以找到正确的宣泄途径,最终只能逐渐被社会边缘化,沦为失去归属感与亲缘感的悲剧人物。
共同体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意为“共同的”[2],指向人类的情感联结与精神层面互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定义为“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公共生活”[3]68。滕尼斯通过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对比来阐释共同体的特性,指出共同体的有机性和生命性,“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与此对应,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机体,社会则应当被视作一个机械的集合体和人为的制品”[3]71。因此,共同体的构建对精神世界意义非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了自我身份,只有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连结足够紧密,才能避免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继而缺失归属感,游离于社会边缘。
纵观《井》全文,不难发现海斯特是一位社会关系薄弱的人物。一方面,身体残疾使她与小镇上身体健康的普通人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差异,天然无法共情;另一方面,家庭关系的不完整——母亲这一角色的缺失给她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赖以生存的农场和小镇仿佛都没有海斯特的容身之地。滕尼斯将共同体归类为三个基本类型: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以及精神共同体,其中血缘共同体是最基本的类型,它逐渐演化形成地缘共同体,随即形成最高形式的精神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构建的失败正是造成海斯特边缘化、精神异化的重要成因。伊丽莎白·乔利的创作,集成了怀特派的怪异性和心理叙事,同时也突破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界限,体现出多种创作理论与手法紧密联系[4]。《井》给予读者的现实意义早已远超怪诞离奇的故事情节所带来的艺术价值,乔利通过边缘人物的悲剧书写勾勒出传统父权社会的光怪陆离,以及共同体构建失败下边缘人物满是疮痍的内心世界。
一、血缘共同体:家庭亲缘联结的缺失
亲属关系是血缘共同体的具象化表达,是构成共同体最基础的部分。房屋是亲属关系的重要场所,亲属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房屋为他们遮蔽风雨,亲属之间分享喜悦、共担风雨,获取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共建和谐的家庭生活。《井》中的农场是见证海斯特亲属关系的重要场所,作为农场主哈珀先生唯一的孩子,海斯特本应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先天的身体残疾使海斯特与哈珀先生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沟壑。幼时丧母的海斯特对父亲与祖母存在难以割舍的依恋,但父亲和祖母却缺乏对海斯特内心世界的关怀与爱护。乔利对哈珀先生着墨不多,但不乏哈珀先生为海斯特读故事书等表面上温馨慈爱的画面。“海斯特父亲讲过的一个火狐狸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常常要大声叫唤的狐狸,它总是叫‘脑袋出来了,半拉脑袋出来了’,还有‘脑袋全出来了’”[5]171,从作者的描述可以看出,火狐狸的身份是个接生婆,乔利用隐晦的方式告知读者哈珀先生对一个男性继承者的渴望,他寄希冀于家庭教师希尔德·赫兹菲尔德为他孕育新生儿。“海斯特的父亲,本来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认为用自己所知的那种方式能得到一个儿子,现在又开始盼望生个儿子,一个健康健全的男孩,能给自己做伴、成为自己伙伴的儿子。”[5]182此时乔利用全知视角析出哈珀先生的内心世界,作为农场的主人和话语权的绝对拥有者,他意欲培养一名健康的继承人以延续农场的繁荣和家族的兴旺,而海斯特显然并非最佳选择。父亲对男性继承人的渴望投射在海斯特身上,间接导致了海斯特性格的异化。共同体的建构注重精神层面的联结,而海斯特与父亲之间却存在无法消解的隔阂,表面上他们处于同一屋檐之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实则亲属之间的情感连结早已分崩离析。
海斯特所处的农场构成了父权规训的绝佳场所,在此空间内她是无声的存在,是边缘化的“他者”[6]。而父亲则是权力的绝对拥有者,海斯特只能处于被凝视、被规训的位置。哈珀先生对海斯特的规训目光不仅裹挟着其对男性继承人的渴望,同时暗含父权威严和权力掌控。《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曾对“凝视”一词做出定义:“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7]349凝视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看”或“观察”,当我们“看”事物时,仅仅只是对事物光、颜色和形状留下综合的印象,而我们“观察”事物,也只是为了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但凝视却携带着权力的目光,最终目的是控制被观看的客体[8]131。幼时父亲哈珀先生以绝对的权威规训着海斯特的行为,在家庭空间内,海斯特是被边缘化的“局外人”,她没有权力挥霍金钱,饮食甚至比不上父亲的狗。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曾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9]23。父亲对海斯特的目光投射使得海斯特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存疑,这导致海斯特不得不压抑真实的自我,甚至抛弃自己的女性气质,主动加入男性气质的阵营,成为父权压迫的继承者。父亲在世的时候,海斯特就已能够熟练地扮演好家庭内的角色,知道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举手投足、回答问题,俨然沦为父权规训的牺牲品。成年后海斯特即使厌恶父亲的做法,却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父亲的诸多习惯,例如用金链子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把钱藏在帽子里,甚至与父亲一样独行专断,拒绝听取他人的建议。海斯特的女性意识在一次次规训中被扭曲和抹杀,最终沦为男权社会压迫的继承者,将自己受到的规训与凝视目光反投射于凯瑟琳身上,完成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变。
除却父亲,祖母同样是血缘共同体联结失败的帮凶。年幼的海斯特缺少母亲的陪伴,这无疑给她的成长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母亲这一角色的缺失让本就摇摇欲坠的亲缘关系愈发脆弱,但赫兹菲尔德的到来无疑为海斯特的幼年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温暖和爱意,以至于她在成年后的悲伤黯淡时刻也不可避免地回忆起赫兹菲尔德。“脆弱的时候,她越来越多地想起了希尔德,想到了希尔德是怎样贴心地呵护和爱惜着自己。她想起希尔德唱着寂静夜,神圣夜,虽然唱得有点走调,却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柔情,根本无妨于耳朵对这曲调的享受……”[5]146-147但在赫兹菲尔德怀孕生产失败之后,祖母却将她无情地驱逐出农场,同时忽略海斯特孤寂的内心,将其送往寄宿学校。“‘书里说女孩子们都要上学’祖母的话给了海斯特一记重击,就像是第一次头痛对脑袋的重击,第一次那么痛苦的头痛”[5]146,而祖母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离开家去上学,就像书里写的那些女孩子一样’,祖母说的好像是什么好事似的”[5]146。祖母对海斯特内心孤寂世界的忽视同样催化了血缘共同体建构的失败,虽然处于同一屋檐下,亲属之间却无法渗入对方的内心,感知彼此的喜怒哀乐。血缘共同体建构的失败使得海斯特逐渐沦为家里的“局外人”,家庭生活中缺失精神寄托,继而难以完成身份认同,联结强大的共同体以抵抗外部世界的变化。
二、地缘共同体:小镇边缘空间的游离
邻里关系是构成乡村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共建良好的毗邻关系。住宅之间的紧密距离以及共同的土地使人相遇相知,即使缺乏血缘关系的联结,也能构建地缘共同体。滕尼斯于《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的三个最主要规则:1)亲属之间、夫妻之间相亲相爱;2)相爱的人们之间存在“共同领会”;3)相爱着并互相理解的人们居留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3]98。其中着重强调亲属、朋友及邻里之间的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感知彼此的喜怒哀乐。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会相对立,他设想的社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圈子,与共同体相似的地方在于,人们在社会中同样以和平的方式在一起居住,但人与人之间却是彼此分离的状态[3]34。在社会中,没有人会因为情感的因素为别人做些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多是利益的交互。《井》中的小镇则构成了滕尼斯所构想的社会而非地缘共同体,农场所属权的变更是《井》中重要的矛盾冲突点,海斯特曾是小镇上举足轻重的人,作为小镇最大农场主的女儿,海斯特因富有财产而在社区一直备受尊重,“她一直都这样直截了当,她不需要婉转,她心地善良,对不太富裕的人慷慨大方,因而在社区非常受尊重”[5]9。海斯特对小镇同样拥有深厚的感情,“小镇不大,海斯特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虽然她说不出镇上的人口是多少,却能对每个农场养了多少头牲口如数家珍。她怜贫惜弱,帮助过不少人”[5]39。“每当离开小镇,开车上了路桥,海斯特的内心必定会涌起开启归返家园之旅的兴奋之情。”[5]40但随着农场所属权的变更交替,海斯特在小镇上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流转至博登先生一家。“这笔交易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但好像哈珀的良好声誉却在一夜之间突然落到了博登的头上。”[5]78在邻居博登先生和博登太太庆祝农场转让的舞会上,海斯特备受冷落,“她觉得人们不再像往常那样停下来向她致礼问候。甚至都没人愿意挪挪窝,让出一条路来让她通过”[5]86。而她也明白自己在小镇上所受的尊重是作为最大农场主的女儿这一身份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当这一身份被剥夺时,一切附加价值也将随之消散,此时的海斯特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小镇居民中普通的一员。滕尼斯于《共同体与社会》中探讨了社会的特性,他指出“在社会中,所有的物品被预设成分离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对一个东西占有的事实就排斥了另一个人对其的占有,社会中不存在“共有的东西”[3]130。农场所属权的变更是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土地的私有形态同样排斥共有土地这一概念。
作者伊丽莎白·乔利有着与海斯特相似的边缘化经历,作为收养国的澳大利亚彼时远离世界主流文学和文化,而她定居的澳洲西部城市柏斯城更是处于边缘位置,地理位置的边缘化构成了乔利作品中难以释怀的边缘意识[10]。这种边缘意识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人物的创作中,海斯特边缘化的地理位置间接导致了她与小镇成员地缘共同体建构的失败。空间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描绘人物的背景板,同时承载着塑造人物性格、体现人物情感联结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海斯特在《井》中一直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她幼时所居住的农场本就位于小镇边缘,哈珀先生去世之后,海斯特又搬到了农场最边缘的草屋,居住场所的逐渐边缘化暗含着海斯特在父亲亡故之后日益被小镇边缘化的事实,她难以在小镇上找到归属感,最终只能在一次次地理位置迁移下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幼时偏僻的农场使得海斯特缺乏年纪相仿的好友,故其只能在孤单的环境中长大,后被送去寄宿学校愈发形单影只,形成孤僻冷漠的性格。而她成年后的离群索居正是因为其性格孤僻,想要与凯瑟琳避世隐居,继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难以与邻里建立良好的地缘关系遂形成地缘共同体。即便最终博登先生一家的比邻而居打破了海斯特地理位置上的与世隔绝,但她仍然无法与博登先生建立友好和睦的邻里关系。对于海斯特而言,博登先生一家对农场所属权的争夺导致了她在小镇上话语权的流转,而他们更是地理空间上的侵略者,是海斯特欲与凯瑟琳构建理想家园的破坏者。
地理位置的隔绝在客观层面导致了海斯特地缘共同体建构的失败,而群体意识与社会集体观念则在精神层面抑制了其共同体意识的萌芽。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问题,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我”是谁,从何处来,又该往何处去?身份认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社会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11]。在这个传统的小镇上,海斯特显然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徘徊于群体意识之外。有悖于小镇居民眼中正常的夫妻制度,海斯特选择了不被世俗所包容的同性共居,她对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嗤之以鼻。博登先生一家是小镇上传统婚姻制度的代表,家庭内部是传统父权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标准模式,博登先生致力于经营农场,而博登太太的任务则是孕育更多的子女为农场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博登先生给人的印象就是总是频繁而坚决地履行着男人的天职,一心想着多生几个儿子以壮大自己的产业。博登家已经有六个孩子了,这些孩子长大了就能繁荣农场,正如繁殖旺盛的牲口也能繁殖农场一样。”[5]80在博登先生一家的农场转让舞会上,博登太太用符合父权社会的异性婚恋观对海斯特进行说教,“我们,我和博登先生,都认为你让凯瑟琳这样的年轻姑娘离群索居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她难道不会想男人吗,一个男人?偶尔总会的吧?”“你该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想单身哦。”[5]83作为小镇上传统家庭的代表,博登太太所表达的不仅是自己一家对于海斯特与凯瑟琳离群索居的看法,更是小镇居民集体观念的缩影,海斯特的同性之爱在小镇居民看来有悖伦常,而海斯特也将博登太太的劝说看作已婚妇女诱骗未婚女性进入婚姻牢笼的把戏,并对其置之不理,傲慢自私地欲将凯瑟琳困于身边。地理位置的边缘化与彼此观念的冲突使得双方在客观层面和精神层面无法达到有机的统一与联合,故海斯特只能游离于小镇边缘,目睹地缘共同体建构的失败。
三、精神共同体:理想家园构造的幻灭
精神共同体在滕尼斯提出的三种共同体形式中处于最高位置,血缘共同体逐步分化成地缘共同体,而地缘共同体又进一步演变成精神共同体,它是一种真正属于人类的最高级别的共同体形式[3]87。精神共同体超越了血缘共同体中亲属关系和地缘共同体中邻里关系的限制,以人与人之间的志趣相投、思维相近为基石,而友谊则是精神共同体的具象化表现。因此相对于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受到的限制较少,但维系精神共同体的难度也相对增大。无论是幼时给予其温暖和关爱的赫兹菲尔德还是成年后相依为命的凯瑟琳,亦或是在生意上为海斯特忧心操劳的伯登先生,海斯特自始至终都没能构建出持续稳定的精神共同体以抵挡外部世界剧变,最终只能独自面对精神世界的异化和崩溃,孤身一人游走于社会边缘。作为小镇最大农场主的独女,海斯特本应拥有小镇居民羡慕的生活,但物质富足的表象之下却是精神世界的无限落寞。她心中的理想家园是有所爱之人长久陪伴,家庭教师赫兹菲尔德曾为其短暂地搭建了心中理想的家园,但这一理想化的家园幻觉很快就被现实戳破。赫兹菲尔德怀孕生产失败之后,祖母无情的驱逐使得海斯特被迫与赫兹菲尔德分离,由此海斯特迎来了第一次理想家园的幻灭。与赫兹菲尔德的分离也成为海斯特未来生活的一道分水岭,至此海斯特被送至寄宿学校,性格也愈发孤僻冷漠。
与赫兹菲尔德的被迫分离导致了海斯特理想家园的幻灭,但朝夕相伴的凯瑟琳同样没能与海斯特成功地构建出精神共同体。表面上看,凯瑟琳是海斯特相依为命的朋友、家人,甚至是海斯特心中相伴一生的爱人,但在两人共同居住的小屋内,海斯特却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号令者,是凯瑟琳非名义上的“主人”。海斯特最初将凯瑟琳带回农场时,面对父亲的询问,她的回答是“我带来了凯瑟琳,不过她是我的”[5]11。一开始收养关系的成立就决定了海斯特与凯瑟琳之间的不平等性,而凯瑟琳在海斯特眼中更是被物化规训的对象,是理应被掌控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海斯特不顾逐渐长大向往爱情和婚姻的凯瑟琳,自私地欲将其永远禁锢于小屋之内,成为自己的玩偶和宠物。与此同时,经由赫兹菲尔德对幼时海斯特的影响,她难以摆脱对同性的爱恋之情,“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母亲或姨母之类的角色。她不想对自己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进行某种界定。很快她意识到自己对凯瑟琳强烈的占有欲”[5]16。海斯特自私自利地拘束着凯瑟琳的肉体,渴望与其建设理想中的家园,文中曾不止一次提到海斯特对和凯瑟琳永远生活在一起的美好幻想,“这才是海斯特真正向往的,两个遗世独立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相依为命,幸福相守。只有她们两个,永远在一起,幸福美满”[5]23-24。但凯瑟琳孤儿院密友乔安娜的即将到来和醉酒后的意外肇事却彻底撕开生活祥和的面纱,海斯特欲与凯瑟琳建造“伊甸园”般理想家园的憧憬也随之破灭。对于凯瑟琳而言,海斯特是收养自己的好心人,是自己理应报答的“恩主”。收养关系成立之后,凯瑟琳同样被囿于一种混沌的关系之中,她与海斯特之间的感情既非姐妹友情,又非母女亲情。但不可否定的是,凯瑟琳只能在生活上依赖海斯特,对海斯特言听计从以换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崇尚浪漫的凯瑟琳并未拥有与海斯特长久居住在小屋的想法,文中也不止一次提及凯瑟琳对婚姻的渴望。“我们也许会碰到某个不错的人。也许能碰到一个很不错的男人。说不定会碰上我的真命天子!很帅的哦?很有钱的哦?”[5]75因此,海斯特并未与凯瑟琳建立起精神共同体以给予自身足够的精神养料来与外部世界抗衡,当外部世界剧烈震荡之时,她们之间的关系愈发脆弱直至危如累卵。精神共同体构建的失败真正将海斯特置于极度孤寂与凄凉的处境,在凯瑟琳意外肇事之后,她不仅需要解决财产失窃的经济危机,还需时刻提防凯瑟琳疯魔的幻想和乔安娜犹如定时炸弹一般的即将来访,四面楚歌之下,海斯特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每况愈下,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
四、结语
伊丽莎白·乔利在《井》中刻画出游离于社会边缘的悲剧性人物海斯特,在家庭生活中与父亲和祖母难以构建血缘共同体,最终只能沦为家里的“局外人”,变卖农场后在小镇上日益边缘化的地理位置、与集体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同样象征着海斯特与小镇成员之间地缘共同体建构的失败。与此同时,曾给海斯特带来温暖的赫兹菲尔德被祖母无情地驱逐出农场,而自以为与她相依为命的凯瑟琳不过因物质生活对其奉命惟谨。海斯特与凯瑟琳收养关系成立伊始便暗含着不平等性,无论是凯瑟琳作为依附者不自觉的讨好亦或是海斯特作为话语权掌握者下意识的施令无不昭示着她们之间精神共同体构建的失败。海斯特欲与凯瑟琳构建心中的理想家园,但凯瑟琳却自始至终想要逃离海斯特的掌控。共同体建构的失败使得海斯特难以抵挡外部世界的剧变,精神世界缺乏情感的滋养,最终只能沦为社会边缘性人物。而海斯特的厌世、避世正是因为她与外部世界缺乏情感联结,继而导致共同体建构的失败,囿于痛苦的牢笼之中难以脱身。对乔利来说,爱是滋养作家的灵药,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自己怎可去认识他人?如果互不相识又怎能去爱?乔利摆脱了狭隘的民族和性别歧视界限,将爱和关怀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井》离奇的故事情节下投射出乔利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密切关注,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这样一位怪诞孤僻又充斥着悲剧色彩的人物,从而引发读者对边缘人物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