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 饨
达瓦次里
猪肉绞馅,加入生鸡蛋、姜末、生抽、黄酒、胡椒粉搅匀,馄饨皮包好入水煮熟。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西宁住青旅,刚进房间就被脚下的拉杆箱绊了一趔趄。
“这谁的东西?信不信我倒地上讹人啊?”
上铺探出个脑袋:“大哥对不起,箱子是我的,别讹我……”
他叫徐潭,假期来西宁看同学,刚住青旅第一天,就被一个背着旅行包的大胡子把拉杆箱给踢坏了。大胡子还说要讹他,吓得他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青旅联谊会,“罗汉局”。我百无聊赖,跟桌上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姑娘和远方。这俩话题还真适合一起聊。你远观,她们是姣好的,诗意的;你“亵玩”,她们便都长出了尖牙和利爪。
徐潭坐我对面,隔几分钟偷瞄我一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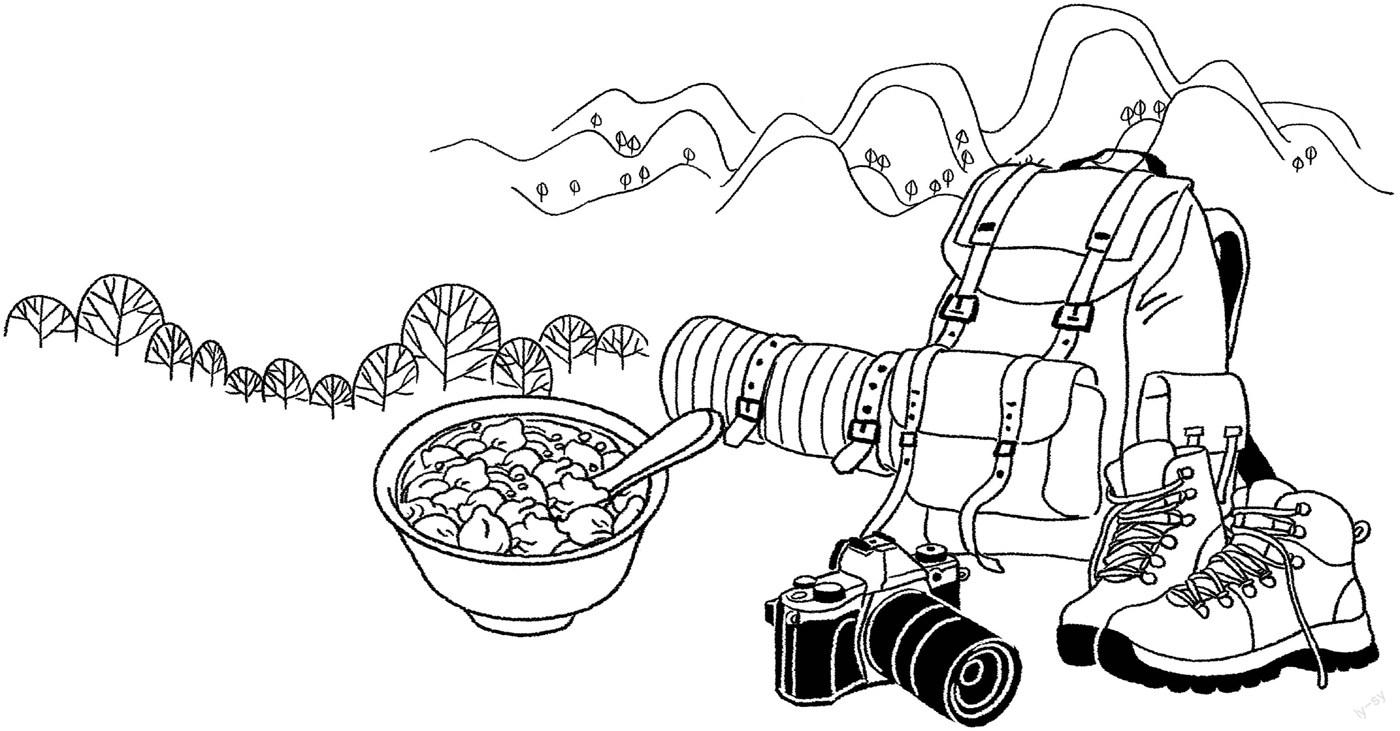
“嘿,徐潭,咱俩没戏,我有女朋友了。”
徐潭连连摆手:“大哥,你真牛,跟谁都能聊。我跟你混吧!”
我和徐潭一起玩了七天,去青海湖,去塔尔寺,去日月山,去丹噶尔古城。
徐潭很听话——我安排的他从不反对。
徐潭心思很细腻——我跟司机、餐厅服务员、小卖铺大姐聊天,他会把有用的信息记本子上。
徐潭内心很柔软——每去一个景点,他会在门票上写下见闻;路过邮局,他会给未来的自己寄张明信片。
徐潭很饥渴——当我说到姑娘的姣好和远方的诗意时,他眼中的什么东西仿佛在疯狂生长。
徐潭回家那天请我吃馄饨。我们蹲在路边,一口一个,哈出的水汽在阳光里升腾、消散。
“大哥,总有一天我也会过上你这样流浪的生活。”
“旅行!不是流浪!”
“啥区别?”
我思考片刻:“粪便味儿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味儿的粪便。”
“怎么说?”
“瞎说的。”
徐潭思考片刻:“大哥,我还有张明信片,能给我写两句话吗?”
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不知怎的,我忽然想到某个中学老师的故乡,便落笔: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饨。
他接过明信片,用力抱我:“大哥,谢谢你!”
我轻轻推开:“嘿,徐潭,咱俩没戏,我有女朋友了。”
徐潭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职。他打电话跟我说,辞职时离发年终奖只差一个月。我问他为啥,他说窝囊废才会为那点钱出卖自由。
辞职后,他买相机,学摄影,朋友圈不再分享乐高模型和常春藤名校报考指南,而是发他的摄影作品——每张姣好的照片上,都配着诗意的文字。
他离开了办公楼,走进大山,走进旷野,走进荒漠,走进那片姣好而诗意的天地。
三年后,某天清晨,拉萨,我在仓姑寺茶馆喝茶,徐潭打来电话:“大哥,看朋友圈你也在拉萨啊!见一面吧!”
我们约在一家早餐店见面,我看着他背着旅行包朝我走来,一脸大胡子。
“徐潭,你怎么秃了?秃得跟没下锅的馄饨一样!”
“我头发少,以前不方便剃光,现在无所谓了。”
坐进店里,徐潭一口馄饨一口羊肉一口蒜,哈出的水汽在阳光里升腾、消散。
“大哥,让我搭车到拉萨的大卡车司机人可好了,不要我车钱,还给我糌粑吃。
“大哥,我逃票进的纳木措,走了四十公里路。那里的餐馆一个炒青菜要四十,真贵。
“大哥,我在呼伦贝尔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胳膊上缝了四针。
“大哥,我在凤凰古城认识了个叫雪莲的姑娘,我想娶她。”
徐潭一口气吃了七个馄饨才停下,接着说要搭车去丁青县拍雪豹。
临行前他用力抱了一下我。
“嘿,徐潭,咱俩没戏,我有女朋友了。”我说。
我看着他的背影,纯净无瑕,光芒万丈。
徐潭真的跟雪莲结了婚。
结婚那天没有接亲,没有宣誓,没有闹洞房,这货就请了我们几个朋友到馆子里撮了顿羊蝎子。在那样一个冬天,那样一个跟往日没有区别的午后,徐潭牽起雪莲的手,站在圆桌前,感谢朋友,感谢缘分,感谢青春。
听朋友说,雪莲认识徐潭前就有身孕,但那姑娘也没骗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做个好丈夫,外加一个好爹。徐潭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实诚的姑娘,感激涕零,以婚相谢。可没两年,他俩的爱情长出了尖牙和利爪。
孩子的亲生父亲找来了,把徐潭揍了一顿——肋骨骨折,他妈在病床旁泣不成声。徐潭还没出院,雪莲就带着孩子跟那男的跑了。我问他为啥挨揍不报警,徐潭说:“男人打架,窝囊废才去报警。”于是,徐潭没去追也没去找,然而他眼中曾疯狂生长的东西不见了。
再见徐潭是在千户苗寨。他身形佝偻,头发像被狗舔了一样。他变得慢慢吞吞,变得小心翼翼。
“徐潭,你吃点啥?”
“馄饨。”
“还有吗?”
徐潭摆了摆手,从背包里掏出袋咸菜。
“大哥,雪莲后来带着孩子回来了,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她告诉我她又怀孕了,还是那个男人的,想跟我复婚,踏踏实实过日子。我答应了。”
我没法接话。
“养俩孩子压力大,我在外面打两份工,雪莲操持家务。一开始还挺好,后来我发现家里的钱越存越少,逼问之下才知道她那个老相好嗜赌,欠了好多钱,雪莲月月给他还债。我气疯了,抽了自己几十个巴掌。大女儿吓坏了,躲雪莲怀里哭着喊着要找她亲爸。”
“抽自己干吗?摔东西多好!”
“窝囊废才拿物件撒气。”
2020年夏,我最后一回见到徐潭。
那天清晨,他从酒吧出来,拎着酒瓶,一头脏辫长虫似的盘在脑袋顶上,眼窝深陷,面色苍白,隔老远我就闻到他身上那股粪便味儿。
他朝我走来,步履忽左忽右如鹅行鸭步,目光忽明忽暗如风中烛火,刚走到我跟前就摔倒在垃圾桶旁一片破砖残瓦上,嘴里念叨着:“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窝囊废,窝囊废,窝囊废……”
“徐潭,你醉了,醉着吧。”
我将一碗冰冷的馄饨摆到徐潭手边,正准备转身离开,却见他口袋里掉出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有时,生活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饨。
朝阳一寸寸升起。逆光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少年在吃早饭,一口馄饨一口羊肉一口蒜,哈出的水汽在阳光里升腾、消散。
“大哥,让我搭车到拉萨的大卡车司机人可好了,不要我车钱,还给我糌粑吃。
“大哥,我逃票进的纳木措,走了四十公里路。那里的餐馆一个炒青菜要四十,真贵。
“大哥,我在呼伦贝尔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胳膊上缝了四针。
“大哥,我在凤凰古城认识了个叫雪莲的姑娘,我想娶她。”
他说着这些,那么纯净无瑕,那么光芒万丈。
[责任编辑 冬 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