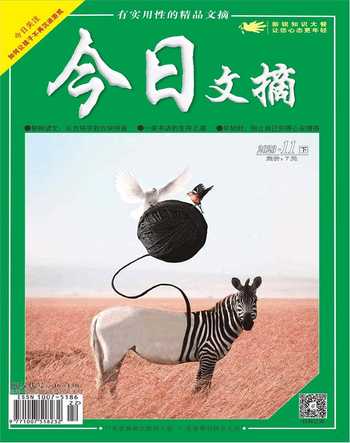炒饭
张佳玮
小时候,蛋炒饭装在搪瓷盆里端上桌。那时我坐着椅子,扒着桌子,鼻尖刚到搪瓷盆边,觉得一大盆蛋炒飯,比山都高。蛋炒饭是我妈的手笔,饭碎粒,蛋成块,金黄泛黑,略带焦香:这是她炒饭的风格,火候唯恐不猛,油炒唯恐不透。我扒拉着饭,稀里哗啦,时不常就一口旁边的汤——热水、酱油、撒点葱,我们那里叫“神仙汤”。我妈炒饭水平并不总是很稳定,但神仙汤总能完美地调整:为炒淡的饭补一点味道,让炒齁了的饭得以下咽。何况只要是新鲜热辣出锅的饭,怎么都不会难吃。如此一口饭一口汤,慢慢地饭吃完了,露出搪瓷盆底的字,标注说那是我妈参加工厂运动会赢的奖品。
于是很长时间,我都觉得蛋炒饭该用搪瓷盆装,搭配着筷子和搪瓷盆轻碰的声音,该是火候猛烈、蛋块焦香,还得配酱油汤。
这个成见,是我上大学时破了的。大一第一学期入冬,到黄昏全身透风,不仅想吃东西,还想吃口热乎的。学校食堂的东西不难吃,但有点像混迹职场多年擅长推诿的老油条,热度半温不火,吃着虚无缥缈,嚼着滑不溜秋,缺少吃东西的实在感。
我想吃点有实在感的东西。于是去了校门对面的一家小炒店。那家老板别的菜倒也罢了,一碗炒饭极好:鸡蛋下得不多,碎金散玉,但下别的玩意儿:火腿肠碎、青豆、洋葱、青椒——青椒?
我第一次吃有青椒的蛋炒饭,但事后想起来,青椒是点睛之笔。尤其是第一个离家的冬天,外头灯光下草木苍茫,油桌,旧凳,一碗青椒蛋炒饭,老板送的一碗汤——猪肉炖萝卜汤里舀出来的清汤,有点骨头香,有点萝卜味,淡淡盐味,但终究是热乎的。青椒炒得透,洋葱炒得透,米饭吃起来极有嚼劲。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蛋炒饭的妙处不单是蛋或者饭,而是各类口感的驳杂多样。炒透的青椒味极开胃,尤其是饿了的时候。吃着这么碗炒饭,眼看见店门口老板大锅炒得乒乒乓乓,觉得吃饭都带出了侠士气;吃完了推碗搁筷去结账,跟老板说声:“炒得好吃!”老板锅铲翻飞,说:“费力气啊!”
古龙笔下阴险的反派,律香川和唐玉,都爱吃蛋炒饭。唐玉是:前一晚杀了人,早起半斤猪油、十个鸡蛋,炒了一大锅蛋炒饭。我后来自己做炒饭时,明白了“一大锅蛋炒饭”的用意。蛋炒饭这玩意,一小盘吃不开心。得大锅大铲费力气炒,炒得透,炒得乒乓作响,才好。
我和若一起离开上海、去到巴黎的第一年秋天,恰逢周末,既人生地不熟,又哪哪都不开;偶尔开的小超市里打眼一看,只认识冷冻披萨和德国酸菜香肠。好在有米,有油,有盐,还买了一根大葱。吃了一顿米饭+酸菜香肠后,到得晚上,一看锅里只有剩饭了;天色已晚,出去又没处吃。
我说,这样吧。大葱绿叶切碎,烧水,切冷饭用铲子扒拉散了,热锅冷油滋滋儿响,葱叶下一半,嘶拉一声冷饭下去,不停炒,炒到分际,下盐,接着炒,颠倒反复,出锅装盘成两碗,顺手另一边葱叶搁热水锅里焖了会儿,加酱油。跟若说:委屈下,这我小时候吃的,先吃着吧。若吃了口饭,喝了口汤,“挺好,比中午吃得踏实。”
说,人也真奇怪;比如就一碗冷饭,一点大葱,一点酱油,吃了会觉得委屈,总觉得就点菜才像过日子;可是一碗冷饭,过了油,过了火,吃着就有几分踏实了。
让人踏实的也许不一定是炒饭。是旧习惯,是暖和,是烟火,是人为了心里踏实,做出的一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