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民间性的彰显与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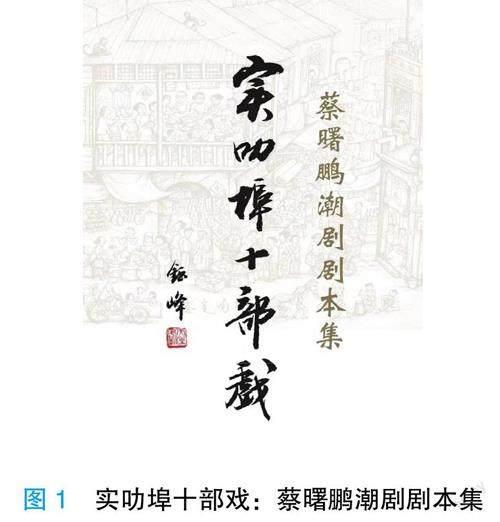


摘 要|蔡曙鹏的潮剧创作既有来自民间的精魂及其世俗品格,又有来自他作为戏剧学者的雅化改造和提升,最终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较好地推动了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接受。蔡曙鹏的潮剧创作较好地实现了传统民间传说及民间故事的现代传承与传播,其戏曲民間性的彰显和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对今后戏曲创作和演出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蔡曙鹏;潮剧;戏曲民间性;雅俗共赏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蔡曙鹏先生是新加坡著名戏剧家,创作了大量的戏剧、舞蹈与偶剧作品,曾受邀参加近百个国际戏剧节的演出,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华文戏剧圈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新近出版的《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年出版)是他有关潮剧剧本的选集,内含他精心挑选的十部潮剧作品,并按照背景说明、剧目全本和相关评论的顺序进行合理编排,图文并茂。该书虽是选本,非其全部作品集结,但从中不难看出蔡曙鹏先生戏剧创作的特色和成就。
在本书的序言和相关评论中,大家都充分肯定了蔡曙鹏先生潮剧创作的跨文化特色,中山大学吴国钦教授指出:“这十个本子有一个共同点:跨文化的特色非常鲜明,它们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底色,涵盖了潮剧文化、中国戏曲文化、新加坡的多种族文化、东南亚文化、甚至欧美与日韩文化。”这跟蔡曙鹏先生具有国际文化视野,以及他自己经历的多民族文化生长环境有关,跨文化创作使他的潮剧能够被其他国家、剧种所移植、传播和接受。围绕“跨文化”,也有学者指出蔡氏创作在全球化或世界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等方面做出的开拓和贡献,尤其是其作品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掘和利用,值得珍视。另外,蔡氏创作重视戏曲“场上”演出的特点亦为众多剧评所认可。具体表现在突出人物表演,行当齐全,戏里穿插大量歌舞,有独唱、合唱和伴唱等,舞蹈形式则不拘一格、丰富多彩,他还精心设计能够反映人物情感和心理的“重头戏”,做到“有戏则长,无戏则短”等。我认为蔡曙鹏先生对潮剧演出“场上”效果的重视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跟作者的戏曲观有关。在本书的后记中,他坦言自己非常认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编剧理念,赞成文本与表演同等重要的戏曲观,认为剧本要同时具有文学性和演剧性这两重性特征;二是他长期坚持为剧团度身写戏,其创作力求尊重和遵循潮剧的本体特色。他说:“为剧团写戏,需要根据演员的风格、特点和才华,设置角色,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创造发挥技艺的空间,以产生最好的演出效果。”蔡曙鹏先生从小受祖母的影响爱上潮州戏,除了去剧院欣赏外,在临时搭建的戏棚里更是看了不少“出街戏”。作为一位戏剧学者,他对潮剧创作、演出的特点有专研,他本人兼具丰富的编、导、演实践经验,懂得按照潮剧的创作原则和审美规律进行创作,有评论指出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展现了戏曲性”亦有不少专家从戏曲化、剧场性或舞台性、技艺性等范畴来对此分析和阐述。
笔者对以上见解和评论都非常认可,这里想在前人言说的基础上“接着说”。文化是一个较为宽泛庞杂的范畴,包括多种形态,我记得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在分析乡村社会时,曾提出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这一对概念。大传统主要指士大夫文化传统,是权力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民间信仰等,体现了非主流(非官方)的文化特征。就蔡曙鹏先生创作的跨文化、全球化、民族化、本土化等特色来说,笔者发现他似乎更注重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汲取和运用(这也许与他早年在北爱尔兰皇后大学攻读民族音乐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改造,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这是他的剧作能够获得跨国界、跨文化演出的重要原因。因为相较于国家(官方)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羁绊,民间文化因为人类的共通性似乎更容易被各国和各族人民所亲近,且便于相互交流和被接受。同时,以民间视角看待其戏曲创作的戏曲性、演剧性等特色,也会产生新的理解和认知。
具体来说,蔡曙鹏潮剧创作的民间性首先表现在他的选材和主题上。“实叻埠十部戏”有八部戏的选材来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例如《绣鞋奇缘》的题材情节取自西洋童话故事《灰姑娘》,《红山的故事》取材于新加坡家喻户晓的马来民间传说,“拉弓定亲”类似民间比武招亲的“桥段”,《哪吒闹东海》则改编自中国民间神话故事,《老鼠嫁女》也是在亚洲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有的取自经典作品,例如《宝弓奇缘》改编自印度尼西亚的民间史诗《罗摩衍那》,《邯郸梦》改编自汤显祖的《邯郸记》,两剧均带有民间传奇色彩。至于《画皮》《聂小倩》则改编自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该小说虽是文人创作,但其情节内容来源于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1],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即使《烈火真情》《新民的故事》这两部选自现实题材的戏,作者也采用民间视角,贴近老百姓生活,《烈火真情》聚焦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情感意识、价值观念,彰显他们在灾难面前乐观友爱、守望相助的精神。《新民的故事》是写民办的新民中学如何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名校的戏,除了关注几任校长外,整部戏也把目光聚焦在新民中学的几位普通教师和学生身上,写他们与“新民”共患难、同成长的故事。
在主题意蕴上,作者也着意民间信仰和民间伦理的表达。例如《宝弓奇缘》在写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和友情的同时,也揭示“正邪对立、邪不压正”的道理。《红山的故事》结尾写宫廷主管阿旺被雷击中,天上下红色的雨,山体出现土崩现象,作者用超现实手法揭示了“恶有恶报”的结局,彰显了嫉恶如仇的民间正义的力量,是民间立场、民间思想和情感诉求的真切表达。日本剧评家漥邦雄评价《红山的故事》说:“从这个小戏欣赏了新加坡民间传说,看到地方风物、礼仪习俗、马来舞蹈。故事寄寓着民众对红山村童被杀害的事件的评价,发人深思。”其他如《聂小倩》《哪吒闹东海》《画皮》等都写出善良、正义和邪恶、残暴的斗争,表达了人民不听从命运摆布、靠个人努力争取自身幸福的美好心愿,给观众以信心和力量。
其次,蔡曙鹏潮剧创作的民间性也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安排和人物刻画上。其潮剧创作多采用线性结构模式,故事有头有尾、一线到底,便于观众理解和欣赏。例如《哪吒闹东海》共有七场戏,分别是“序幕”;第一场“哪吒出世”;第二场“龙王祝寿”;第三场“太子横行”;第四场“龙王问罪”;第五场“哪吒自尽”;第六场“哪吒复活”;第七场“大战龙王”,情节曲折完整,简洁明快。《邯郸梦》则有九场:第一场,入梦见美女;第二场,赠试做大官;第三场,夺元露锋芒;第四场,凿陕立奇功;第五场,东巡遇战事;第六场,勒功遭陷害;第七场,召还转命运;第八场,极欲享荣华;第九场;梦醒悟人生,可谓一脉相承,前后呼应,中间通过梦境描写突显卢生在官场中的命运沉浮,结构清晰又富于变化。该书所选的十部戏多为民间小戏,以灵活生动见长,基本上不追求大场面、大制作。即使像《烈火真情》《新民的故事》这样以宏大题材作为背景写客观史实的戏,也是立足小中见大,正如吴平平在分析《烈火真情》中所指出的:“犹如交叉运用聚焦镜头和运动镜头般地,截取了灾难中的几个场景和几个小人物,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感时,抒写了社会的真情和生活的希望。”为了叙述简洁,人物出场多采用“自报家门”形式,如《聂小倩》中浪荡公子高庆松的出场:“(唱)公子我名叫高庆松,厝边(闽南方言:邻居)叫我疯叮咚(指疯子),爹爹为官在朝中,慈娘任我放轻松”,三言两语就交代人物背景、姓名和性格,并很快进入故事。这种概括叙述方式在他的潮剧创作中较为普遍。
在人物刻画上,作者常用民间文艺刻画人物的方法,有意突显人物身上的某一特征,塑造类型化角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哪吒闹东海》塑造了哪吒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形象,龙王则是兴风作浪、为非作歹的形象,二者形象特征鲜明。此外,《红山的故事》中纳丁的机智敏捷,阿旺的自私残暴,《老鼠嫁女》中的老鼠妈妈贪恋钱财、爱慕虚荣的形象等都昭然若揭。作者还喜欢采用善恶冲突和对比对照方式刻画人物,《宝弓奇缘》就是代表善良正义一方的仁昭、仁贤、猴将军哈努曼,和代表邪恶残暴一方的十头魔王、千面魔王等展开激烈冲突。《绣鞋奇缘》中韩慧娘的勤劳善良与二姐韩美娘、三姐韩丽娘,以及继母韩大妈的自私虚荣形成对比和对照,并构成矛盾冲突,从而展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差异性。俞唯洁在《逾越“跨文化戏剧”,迈向“交织文化表演”》一文中就指出:“蔡曙鹏在潮剧《绣鞋奇缘》中对女主人公与异母姐妹的人物设定,不但对应了童话传说中的人物原型,且还擅用华语言文字和华族文化的内涵来具化并赋予这三个人物的性格基调:女主人公慧娘,意即聪慧勤劳以对应故事原型中的灰姑娘,二姐三妹分别为美娘与丽娘,隐喻其徒有外貌却有失内秀的特定品格。因此,通过人物名字释义与隐喻,即为开场便立刻展开的不同人物间的戏剧冲突奠定了人名联想与文本脚注。”
再次,蔡曙鹏潮剧创作的民间性离不开民间语言和民间艺术元素的运用。综观《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不难发现其语言极为生活化、口语化,富有地域特色。人物对话中有很多方言土语的运用,例如《红山的故事》中阿旺对他妻子抱怨说:“Kulit babi yang tersangkut di kepala saya!(这耻辱简直就是往我头上丢猪皮!)就是录自马来人的口语,猪肉是马来人的禁忌,头部更不能轻易触碰,以此作比喻说明是奇耻大辱。还有,苏菲亚笑骂丈夫的臭脾气:“就是用了一桶油,也没有办法把你的狗尾巴搓直”,也是借用地方谚语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语言形象生动。《新民的故事》中则有“石看纹理刀看刃,树看木材人看决心”的唱词,这是民歌比兴手法的运用。许振义在《新加坡戏曲的创新和在地化——以〈红山的传说〉为例》中指出:“本剧虽是潮剧,但唱词大量运用马来班顿为基调。……班顿是马来人的一种诗歌,通常是由四行组成一首,故称为马来四行诗;歌词多属抒情,又称为马来四行抒情诗。在新马一带,华人对班顿并不陌生,《红山的故事》取材马来民间故事,潮剧大量唱词运用班顿形式,虽罕见却贴切,相得益彰,堪称跨文化创作的一个佳例。”[1]方言和地方民歌的运用使蔡曙鹏创作的潮剧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在表现手段上,蔡曙鹏先生也广泛吸纳民间艺术元素,包括民间说唱、歌舞、美术、武术、地方音乐等,例如《画皮》中王生第一次出场就有一段画轴舞,《聂小倩》中也设置了多个舞蹈场面,代表性的如燕赤霞的月下剑舞,同样《新民的故事》在学校举办的游艺会上也有民间剑舞的表演。《红山的故事》中则有多元民族舞蹈的场面。《宝弓奇缘》《哪吒闹东海》更有不少武打场面展示。在剧目演出时则注意地方戏曲音乐运用,例如南宁市歌舞团演出的《老鼠嫁女》运用了广东小曲《海南曲》以及地方小调《跳花鼓》《四不正》等音乐元素,还有长号、短笛和木琴的组合运用,这使得蔡曙鹏的戏曲极具视听效果,富含观赏性。
最后,蔡曙鹏潮剧的民间性也体现在他创作的喜剧特色及其谐虐效果上。《烈火真情》属于宣传正能量的戏,但也有插科打诨的地方,如开篇写林炳海去探望耳聋的刘老婶,写邻里乡情,两人有一段对话:
刘老婶:来坐来坐,吃杯茶。
林炳海:感谢感谢。感谢。今日好无闲。
刘老婶:(听错)甘蔗破成两边?你又带甘蔗来送我?
林炳海:(走向前,大声重复)我是说感谢感谢。感谢。今日可无闲。
刘老婶:(笑弯了腰)哈哈哈哈哈,我耳聋,常常听错。笑死人,笑死人!
林炳海:不不不,是我说不清楚。我来走。
刘老婶:免,免,免。你喂狗?狗,我早上喂好了。
林炳海:(走向前,大声重复)我是说我来走。
刘老婶:(笑得合不拢嘴巴)哈哈哈哈哈,我来走听成要喂狗。笑死人,笑死人。慢走慢走。
这一段戏就带有浓厚的生活氣息和民间情趣,令人忍俊不禁。
除了插科打诨外,作者还喜欢在多部潮剧中通过增设丑角来增加戏剧的娱乐性。例如《哪吒闹东海》中作者加入了蛤蟆精、蛤蟆婆两个丑行角色,除了行当整齐的考量外,也增加了该剧的喜剧色彩。《烈火真情》也增设了一个丑角,戏的中间写到地痞流氓阿狗看到美芳一人独自在家,就嬉皮笑脸地上前调戏她,后被李书松的妻子沈秀兰撞见,遭到严厉斥责。虽是一个插曲,但明显调节了戏剧气氛和节奏,带有即兴演出的色彩。儿童剧《老鼠嫁女》更具有强烈的喜剧性,老鼠妈妈的选婿标准在她唱词中有显示:“(白)傻闺女,你听阿妈说,(唱)玉梅有才又有貌,新郎条件要提高。一要英俊长得好,二要精明有头脑。三要社会地位高,财源滚滚是富豪。(白)要有航空公司金卡,还有Visa和Master,各种信用卡。(唱)别墅跑车样样有,四季出国去旅游,巴黎上海迪士尼,吃喝玩乐乐悠悠。”唱词类似“顺口溜”,让人想到当下一些女孩子父母不切实际的择偶标准,令人发笑。剧中,老鼠妈妈嫌贫爱富,不让鼠姑娘和心爱的鼠壮士结合,竟然选了大黑猫做女婿,也让观众瞠目结舌,搞笑不已。最后,大黑猫要吃鼠妈妈和鼠姑娘,鼠壮士前来营救,邻里众鼠上场,舞台上充满闹剧色彩和狂欢性质。《聂小倩》中,作者也别出心裁地增设了高庆松这一花花公子的角色,写出他的浪荡形骸,如出场时唱:“初一东楼尝海味,十五西阁找歌姬。山珍海味胃口开,寻花问柳乐开怀!”后被聂小倩戏弄,丑态百出。作者自称是为了行当整齐而增设高庆松这一丑行的表演,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剧趣味性和谐虐效果,并让他和正直善良的宁采臣形成鲜明对比。《绣鞋奇缘》中二姐韩美娘、三姐韩丽娘,以及继母韩大妈在进宫献艺时的忸怩作态、弄巧成拙,除了引起太子的反感外,也引发观众的阵阵哄笑,极具讽刺效果。
潮剧等地方戏曲属于俗文学范畴,长期根植于广大人民生活之中,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日常娱乐的重要载体,蔡曙鹏先生的潮剧创作注意从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和资源,赋予创作鲜明的民间特色,并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使他的戏曲很接地气,更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得到各国人民的青睐和喜爱。但这不是说,他的创作就是一味迎合大众,追求低俗、媚俗。众所周知,民间文化往往精华与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这就需要改编者有一个去芜存菁的改造过程。如同中国戏曲有一个雅俗流变的发展路径一样,蔡曙鹏先生对于民间资源和传统也是有自己的取舍、丰富和加工的,或者说有来自他作为现代文人的雅化和提升。
一是让民间传统与现代意识进行有机衔接。已有不少评论指出蔡曙鹏先生的改编注重对当下观众的教育意义,作品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反映普世价值观,这是他的作品能超越国界、文化、阶级、种族乃至年龄的原因。例如《聂小倩》中,作者舍去了原作中宁采臣搬运聂小倩尸骨,聂小倩与宁采臣结婚生子,以及最后战胜鬼怪等离奇怪诞事件,而使情节更加简洁合理,同时,聂小倩形象也改变了原小说中的哀怨受虐的气质,作者赋予她更多的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这就符合现代观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欣赏的需要。同样,《邯郸梦》较之《邯郸记》也有了更多现代意识,反映作者对当下官场生态的关注和思考,也给予了卢生一定的理解和同情。正如《邯郸梦》创作说明中所交代的:“《邯郸记》通过卢生梦中的经历,揭露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嘲讽卢生心态随着地位的升沉而剧变。缩编时作者尽力把握原著对父权社会中有志仕途的男子的生存状态,突出官场的权力结构与金钱政治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压抑和困惑。”《画皮》也一改原小说中对王生轻薄好色的批判,转而关注一个普通人的生理和心理世界,揭示他在“礼”与“欲”之间的挣扎,该剧杜绝“道德绑架”,有意开掘人性内涵和生命情绪,去除了原小说中“女色是祸水”的封建意识。尤其是改变王妻一味“忍让”的贤妻形象,删除王妻当众受乞丐之辱的情节,而写出她对丈夫的责难和反抗,女性的独立、平等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我个人认为,蔡曙鹏戏曲改编的出发点是当下观众的欣赏接受,体现出作者与时俱进的观众本位意识,是站在当代思想高度和审美趋向上对传统题材进行演绎和处理,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给观众以新时代的思索、启迪和趣味。”
就观众接受层次而言,蔡曙鹏十部潮剧创作的受众主体主要是青少年,意在推动潮剧在青少年中的传播和传承,同时起到教育青少年的作用。
二是在戏曲语言和审美形式上进行适度改造。蔡曙鹏的潮剧作品很少有一些地方戏曲常见的水词、套词,唱词内容也杜绝低俗粗鄙和“其文不雅驯”的地方,唱词形式除了借鉴古典词曲外,也注意向现代诗词学习,富有文采,例如《红山的故事》开头的合唱:“九重葛鸡蛋花,年头开到年尾。芭蕉树棕榈树,青青葱葱如画。小小海岛在赤道,常年如夏气温高。早出晚归为三餐,风雨同舟苦也甘。”虽是对本土风物的描绘,但清新如画,朗朗上口。
在作品尾声(或某一场次)的终曲中,作者喜欢采用卒章显志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理解和思考。如《绣鞋奇缘》剧终的后台合唱:“踏破铁鞋无处寻,多谢仙姬来指引。一只绣鞋巧姻缘,皆因慧娘好人品。”意指韩慧娘的勤劳善良得到仙女的认可并在她的帮助下获得美满姻缘,这是作者对全剧主旨的总结和揭示。再如《邯郸梦》第三场结尾的后台合唱:“书生白面好轻人,只道文章稳立身。直待朝中难站立,始知世上有权臣。”唱词句式工整,浅显易懂,含有作者对官场人生的思考和情感抒发,通过演唱加深观众对全剧的理解和接受。
对于一些原著情节较为复杂的改编,作者巧妙地采用缩编方式,使得故事简洁自然,绝不拖泥带水。例如汤显祖的《邯郸记》篇幅较长,共有三十出,放在现代剧场演出就会显得冗长拖沓,作者把它缩编成九场戏,戏剧节奏明显加快,更适合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除了情节内容上“做减法”外,作者在人物设置上也会适当“做加法”,例如越剧版《邯郸梦》第三场“夺元露锋芒”,就增加了一个《邯郸记》没有的角色——宇文融的宠妾“七夫人”,用她来反衬宇文融的恶行,同时在行当上更加齐全。何玉人在《让经典永远流传——谈潮剧〈邯郸梦〉的整理改编》一文中高度评价说:“蔡曙鹏先生潮剧《邯郸梦》的改编本,做到了增删合理,保留了故事的主要脉络,突出了精彩的情节、台词和唱段。阅读剧本可以感受到,凡涉及的故事、情节、唱念和表演手段都做了精心的选择,对每场戏的改编也都作了认真的艺术处理。”[1]
综上所述,蔡曙鹏先生的潮剧创作既有来自民间的精魂及其世俗品格,又有来自他作为戏剧学者的雅化改造和提升,最终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较好地推动了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接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科技和资讯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对民间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对传统民间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蔡曙鹏先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的潮剧创作较好地实现了传统民间传说及民间故事的现代传承与传播,其戏曲民间性的彰显和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对今后戏曲创作/演出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陈军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吴国钦:《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序一,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5页。
[2]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22页。
吴平平:《戏曲的生长性——从新加坡题材潮剧〈烈火真情〉谈起》,载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43页。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渔洋老人题辞曰:“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压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1]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78页。
[2]吴平平:《戏曲的生长性——从新加坡题材潮剧〈烈火真情〉谈起》,载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39頁。
俞唯洁:《逾越“跨文化戏剧”,迈向“交织文化表演”》,载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313页。
许振义:《新加坡戏曲的创新和在地化——以〈红山的传说〉为例》,载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107页。
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162页。
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350页。
将青少年作为潮剧创作的预设目标和主要交流对象源于潮剧在海外面临的生存危机。周宁曾在《东南亚华语戏剧研究:问题与领域》一文中提出东南亚华语戏剧面临双重危机,既有来自电影与电视的观众分流,也有戏剧未完成本土化的原因,同时,传统戏曲由于限于传统方言族群,戏剧危机更为严重。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新加坡,华语属于少数民族,潮剧发展的族群更小,面对危机,蔡曙鹏秉持不同的戏剧发展观,他在《全球化格局中的戏剧与本土文化》一文中虽也提及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并谈到了一个鲜明的现象,即许多华人青少年对传统戏曲的陌生和隔膜,但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流活力和青少年对传统戏剧接受和传承的重要性(参见蔡曙鹏:《全球化格局中的戏剧与本土文化》,载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苏省文化厅编《全球化与戏剧发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第70页)。因此,十部潮剧创作以经典童话、民间故事和各国神话为改编和创作源泉,讲述传统故事的同时也为作品注入现代意识,对青少年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做到寓教于乐。
何玉人:《让经典永远流传——谈潮剧〈邯郸梦〉的整理改编》,载蔡曙鹏《实叻埠十部戏:蔡曙鹏潮剧剧本集》,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2021,第193页。
——以潮剧《情断昆吾剑》为例
——以人才培养模式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