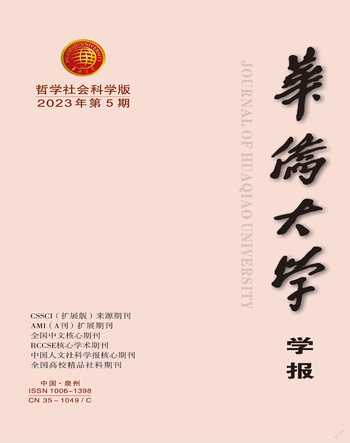元宇宙的似真非真属性与思维创生元理
汪栅 么加利 李冰
摘要:元宇宙具有似真非真的属性,似真性表现为观念或想象符码在感觉或者功能层面构筑出的“真实”效果;非真性表现在由思维生成的虚拟之物并非如现实客体一般具有物理意义,所以不存在事实层面的真实性。又因元宇宙的生产是肉身不在场,思维在场的实践,所以元宇宙实际是人类思维居住并进行“物质”生产的场所。没有人类思维的引领,数字技术无法自动承担元宇宙的建构工作,因而元宇宙的创生本质实际是思维数字化的实践,而非数字的直接创生。虚拟对人类创新思维解放的程度越高,思维对元宇宙世界的加工、改造、创构的实践能力愈强,反之元宇宙的发展也能反作用于人类思维灵性的提升,二者相辅相成。然而,人类思维在元宇宙中的过度解放可能会带来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一是造成人的主体性失落,沉溺于数字世界的符号狂欢,背离原则、人性与伦理;二是自我设限的消解,从固化的思维中脱离出来,寻求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与人文形式。人类文明的前进或是凋敝取决于思维解放的偏向,只有时刻保持对元宇宙產生的可能危机进行预测与警惕,才能防止人类陷入科技带来的感性迷狂。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思维;虚拟实践;思维创生
作者简介:汪栅,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哲学(E-mail:wshan0525@126.com;重庆 400799)。么加利,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李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知识体系与课程建构研究”(22JJD840016)
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5-0005-11
何谓元宇宙?“元宇宙”一词作为“Metaverse”的本土化翻译,目前尚未达成一个完整且权威的定义,但普遍认为元宇宙是一个“境身合一”、综合运用“包括区块链、5G、人工智能、3D、VR/AR/XR、脑机接口等目前人类最尖端科学技术”的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全息数字空间。从更为感性的角度来看,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是映射现实世界的在线虚拟世界,是越来越真实的数字虚拟世界。”可见这一概念几乎吸纳了“信息革命(5G/6G)、互联网革命(Web 3.0)、人工智能革命,以及VR、AR、MR等虚拟现实技术革命的成果”,这些跨界技术的深度融合能够组建模拟现实世界的人、事、物、环境、生态体系、政治体系、交往体系、生产体系等一切要素,等同于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人们对元宇宙生活的期望立意于现实,却远高于现实,既希望在其中体验到媲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还希望自身能像“造物主”那般任意创构世界万物,从而应证“我即是宇宙”的唯心之意。然而,无论是将元宇宙当作一种数字媒介作“形而下”的应用研究,还是从其“元”这一含有“超越”之意的符号追问其本质,我们对元宇宙的所有思考、猜测、预设,除了依据媒介技术更迭的反馈,更来自于人类构筑未来虚拟世界模型的先验想象。想象是我们应对未知事物进行形象建构的关键思维,尤其是从那些科幻图景的想象碎片,甚至可以间接反哺着元宇宙技术的生成,而元宇宙则成为实现人类想象之物的载体。所以我们虽不能定义元宇宙的最终样态,但却能确定思维的联想力是生成理想元宇宙的动力来源,更是人类设计自身未来的感性力量。一旦人类的意识进入虚拟世界被数字化后,突破日常逻辑、肉体束缚以及物质世界规则的思维又是如何呈现、运作与进化,如何进行创造性工作,便成为本文探讨的内容。同时,人类也只有把握住思维在虚拟世界中的发散样态,才能不被数字技术制造的视觉幻象所迷,致使主体意识走向消解的境地。
一元宇宙:人类思维的栖息之地
元宇宙作为人造的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存在逻辑相反,并非是存在决定思维,而是思维决定存在。甚至有观点认为元宇宙实践意味着“人们的意识创造了宇宙,而不是宇宙创造了人们的意识。”这源于现实世界的实践是肉体行为,而元宇宙的实践则是思维的行为。桑业明等人曾提出“虚拟使思维与行为真正地统一在一起,‘思维即行为”的观点。他指出人类一旦从现实进入虚拟世界,思维方式就从现实性思维(以“是什么”“不是什么”为对象的求真、求是思维)转向虚拟性思维(以“不存在”“不可能”为对象的如何是的思维),思维在虚拟空间中运行时,思维如何思的过程就被算法编辑呈象,即被数字编码后得以形象化、行为化,这时的思维是能看见并能被捕捉到的行为。元宇宙中的虚拟化身就是用于承载现实本体思维的阿凡达(Avanda)形象,我们如何思维,阿凡达就如何行为。人们能够在元宇宙中借由阿凡达让思维实体化,成为犹如行为一般可视的实践系统。
在元宇宙里,每一个阿凡达都是现实本体的思维承载物,换言之,它们是人类思维在元宇宙世界里的数字寄生体,当神经信息链接到元宇宙,实体思维就以阿凡达的形象成为元宇宙中的原住民,此时的阿凡达等同于人类思维的化身。据此而论,元宇宙成为人类思维的居所,也以人类的思维运思(阿凡达进行实践)反哺自身。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思维运思的内容既包含“现实的可能存在”也包含“现实的不可能存在”,通过代码以及数据建模可以将人类脑海中现实社会的商业模式、交往模式、物理生态等复刻于元宇宙,而那些存在于人类想象中却难以出现在现实中的生物、物品或工具等也可经由思维编码、算法创构,因而元宇宙是个超现实的社会。这个社会空间既铺垫了现实层也叠加了虚拟层,进而能横跨虚实边界,从人类的想象思维中发掘与补充虚拟层中的元素,并借助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将这一空间发展成人类可感知、可想象、可实践、可生活的另一种现实;二是进入元宇宙时代后,人类的生活空间被自然地划分成现实与虚拟两重维度,有限的个体生命借助脑电连接设备可以让自身意识以数字形态重生,只要人类的意识数据能够永久保存,数字生命即可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得以永恒存在,成为一种生命状态介于虚实之间的新人类。新人类在元宇宙中的实践是将思想观念映射为数据的数字创构,思维实践而来的创构文明,实质是一种数字智能文明,指向思维演化与实践的规则、代码运行与组合的方式以及自组织系统的运作。有论者认为这类“文明的起源不是实用,而是对实用的超越”,旨在唤醒人类思维的造世能力,用数字方式去演化、构成人类的想象之物。
在陈志良看来,“虚拟是人类的思维中介系统”,“人的思维运动借助于它来表达万物,从而在思维中构成万物的工具。”然而,在笔者看来虚拟也并非仅仅是作为人类思维运动的中介,而是将“思维”实体化的建模,人类思维在元宇宙中以虚拟呈象,这样的虚拟思维既具有以“0—1数字方式去表达和构成事物以及关系”的虚拟功能,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对象性思维所共有的间断性、抽象性、形式化等特征”,可以借由虚拟算法构筑自身。这样看来,虚拟思维应证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观念中那类“不被创造的无限的思维实体,即上帝”,是可以确证“我”能以纯粹精神形态存在的基础,更是能不断自我运算、自我进化的思维系统。那么元宇宙中的人类思维作为一种被虚拟化的思维,便具有了如下特性:
虚拟思维是有形的思维。元宇宙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人类的思维“以数字化的方式行为化、感性化”,“我思”成为再现“我”存在的思维实体,在虚拟空间中拥有外在化的数字皮囊(Avanda),是一个“有意识的思维克隆人——智能的、有情感的、活的虚拟人。”虚拟人的行为即为虚拟思维的行为化,是思维执行认知运演与视觉类推的衍义过程,这一过程借由数字技术与代码操作被转换成可见、可视、可感的虚拟“行为”。
虚拟思维是自主运思的思维。元宇宙中的虚拟思维如同能自主学习的AI一样,带有自我增殖、自我学习、自我进化的自组织特性,这样的虚拟思维在没有肉身的反馈下也能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长,所以更像是拥有了“主体性”的智慧“行动者”。与AI学习不同的是,人类思维能够不断认识未知、解读未知,甚至产生无中生有的创造性灵感,所以“虚拟思维”除了具备AI自主学习、自主反馈的功能,还具备与人类一样可以自我复杂化的创造力与反思力。这样的“思维”既不受现实认知限度的制约,也不受肉体的束缚,能极大解放思维“构建现实中的不存在和不可能”的创造活力,从而实现人对现实性以及自我的超越。
另外,结合信息论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思维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通过知觉系统的体验输入感官信息,从而对已知事物或未知事物进行建模。人类天生就是一种会建模的动物,大脑通过整合、排列各类感官信息以建模的方式认识世界,而虚拟本身就是建模,只是虚拟建模的过程透明且可见,人类思维的建模则是抽象与隐秘的。虚拟即是人类思维的建模活动,思维在元宇宙中就是以虚拟的数字化方式来进行映射。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虚拟同时也是元宇宙存在的实存方式,那么元宇宙与人类思维便构成相互成就的嵌合关系,思维建模的内容是完善元宇宙世界的符号元素,只有多元性、多样性、创造性的思维才能促进元宇宙世界的发展,但同时元宇宙也是拓展人类想象力,生成创造性思维的媒介,二者共融互通,相互反哺。
二元宇宙的似真非真属性:“真实”的数字幻象
(一)数字幻象何以“真实”?——来自“缸中之脑”的隐喻
现代科学表明,人类是通过神经元信号传递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感知、认知以及意识,这些内在的心理活动要素让我们拥有活着并存在于此的感觉。假设元宇宙能为人类的感知体验提供真实的模拟环境,并配备高精度的传感设备,为我们传递各类情景的感觉信息,那么身处于程序模拟世界的我们是否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虚假性以及所处世界的虚假性。针对这一问题,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提出了“缸中之脑”的假想实验,就是只在盛满营养溶液的玻璃缸中放入人类的大脑,并将之同电脑联通,只要在实验中保持计算机与神经末梢相连的稳定性,没有人体且只存在于玻璃容器中的大脑可以靠代码的输入得到与现实情景类似的感觉材料,从而获得类像现实世界的真实体验。
那么大脑是否能认识到自己经历的生活与所存在的世界只是自身的构想?
从科学实在论的角度来讲,置于缸中的大脑所认知的己在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而是电脑模拟所建构的形象反馈,而大脑神经所接收的感知觉信号刺激让这份模拟有了实在性的效果。确切来说,“缸中之脑”的认知边界是由程序设计者(观察者)的认知体系决定,对于玻璃容器内的大脑而言,幻象即为真实,思维着的自己即为存在本身;对于设计者而言,大脑所体会到的“真实”世界只是自身为其设定的虚妄假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电脑信号的刺激下,大脑能够制造出现实世界的幻境,让自己感知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性。对于此种现象,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提醒我们正是因为在缸中的大脑能够进行思考所以明确了“我”的存在,“‘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无法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的思想主体‘我的真实存在”,所以我怀疑,我存在。“我”必须确认“我”是存在的,才有大脑对信号的反馈,若我不能确定自身的存在,那么感知、意识、思维这些不可见的精神要素便陷入了虚无。由此可见,即使一个人类仅剩大脑存在,只要有持续的外部信号刺激,大脑就能进行思维运动对感知体验进行图像化的编码,从而幻想出一个真实存在世界。同理而论,当人类在虚拟现实中拥有在現实世界一般的感知觉体验,那么处于其中的当事人就如同被困在缸中的大脑一样,凭着对现象世界的反馈建构自身的认知,认定眼前的一切能被感知就是“真实”。这样的虚拟对于人类而言,恰恰是一种感性的真实存在。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认为的那样,虚拟世界的拟真是以符码拟像来替代真实,真实就此变得不再重要。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虚拟世界中生存的人类,体验到的并非是某种事实存在的真实性,而是相对于真事实存在的意象“真实”。也正是这份“真实”的幻象体验赋予了符码拟真的“真实”感,从而僭越了客观真实的本体地位,让“真实不再构成参照系,真实本身反倒是从符码编码中复制出来的存在。”元宇宙吸收了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又以符码拟真生成想象的真实,从而扩展了“真实”的范畴,使虚拟在效果上、观念上具有了“真实”的品质。由此可见,虚拟世界的“真实”并不完全停留在对真实的指涉物或某种实体的模拟上,而是通过思维或感觉的建模来生产“真实”,成为由“符码操控和演绎”的超真实世界——这个世界“泯灭了真实和非真实的界限”,混合了“真实的虚假和虚假的真实”,相对于现实而言,这个世界不存在事物本体的真实,只有思维之物——符号的真实。
(二)似真还是非真?——虚拟“真实”具有双重属性
面对符码时代的统治,鲍德里亚用“超真实”概念动摇了存在者意义上的真实根基,将“真实”转变成人为的想象或创造之物,使之抽象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真实”。元宇宙的“真实”便是一种基于现实与想象之上的“超真实”,这一空间的虚拟效果并非是还原事物的本真,而是再造一个“真实”世界的序列,塑造新的“真实”。这份“真实”的基础靠的是符码拟真与感官沉浸。符码拟真包含了现实存在与现实可能的拟真,也包含了现实不可能的拟真,拟真让“真实”成了一种能被复刻与再生产的东西;感官沉浸是元宇宙主要特征,全感官沉浸带来的真实刺激感越强,人类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解构越快,“对于沉浸在元宇宙中的个体来说,世俗的现实或者绝对现实的‘直接就失去了意义。”这意味着元宇宙无限接近于现实甚至超越现实局限后,虚拟世界不仅生产了属于自身“真实”秩序,甚至让这种秩序成为人类在进行虚拟生存时的一种感觉性惯习。所以,超真实的元宇宙是一个不分真假的世界,真实与意象相互纠缠、游离,“真实”秩序成就“真实”的意象,那么虚拟存在就显现出“似真非真”的属性。
虚拟是元宇宙的实存方式,而“似真非真”则是虚拟这一实存方式的状态属性。分野而论,虚拟的似真性体现在“虚拟不是外在于真实,而是使自己成为真实的一部分”,虽不是现实层面的“真”,但却能将思维之物从感觉或者功能层面构筑出“真实”的效果。这种感觉性的真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知觉真实与想象真实。知觉真实在于一旦进入元宇宙,现实本体的感知就不再是从与现实环境的互动中产生,而是由自己的虚拟人的行为所反馈,即肉身虽静止,但处于元宇宙中的虚拟人也会按照本体意志的选择进行活动,如同玩家操作自己的游戏角色完成任务一样,只是元宇宙中的虚拟人复刻了现实本体的感知觉系统,能够让现实本体体会到虚拟人在元宇宙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只要透过感官设备我们静止的肉身就能感受到虚拟人活动时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的实时反馈,这便是肉体知觉实时同步虚实世界信息所带来的体感真实。而想象的真实,则是通过对元宇宙的预期所产生的假定真实,只要想象的事物是为人所感知,即使是影像也能让人感觉到真实,甚至由此认定这种“假定真实”在未来必定成为会发生的事实。在张怡、郦全民、陈敬等人看来,人类的经验世界本不该只有一种事实维度上的实在世界,还有一种受创造性支配的实在世界,即虚拟是人类想象的现实,“必然服务于主体的特定需求,而它的最终结果还是要在现实物理时空中加以验证和实现。”虚拟本身不是真实的事实,但却能影响现实,因为虚拟代表着一种想象模式,在爱因斯坦看来只有想象才能创造知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想象与事实耦合状态中才能得以发展。所以虚拟的似真指向的是想象符码的生产——即数字技术对想象符码的拟真,通过模拟体验与想象的视觉化让符码具体在场并发挥自身的功能,从而为人类的创构性活动提供新的思路或新的可能,这时“我们便不应该把虚拟现实想象为现实消失的一种形式,而应当视为另一种现实的展开。”
虚拟的非真性则体现在构成虚拟空间的符码本身只是比特的演化,“真实本身往往只有依靠符码编码才能存在”,这种真实缺乏事实的根基却具有实际的效用。“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现实的存在,是有根据的存在,有理由的存在”,虽然虚拟也能打造物质真实的形态、触感与功能,但相对于现实世界那些由分子、离子、原子的物质构成相比,虚拟属于主体感性的数字模拟与虚构,并非存在如客体一般的物理意义,所以虚拟现实“在功效方面是真实的,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的事件或实体。”这样的元宇宙虽具有能模拟物理世界“真实”的功能,但那些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实践真实却只能由人类的肉身行动达成。正如海姆(Michael Heim)所言:“虚拟世界是一个功能性的整体。它是平行而不是描述了或同化了我们所习惯的本原世界。”虚拟存在的非真性也意味着虚拟真实无法替代物质世界的真实,物质与符号对应的价值关系也只能在物质世界得以实现,而虚拟世界实质是通过遮蔽这层关系来达成自身“真实”的生产。
总体而言,元宇宙是能让主体得到一种实际而非事实上的感觉性存在,受创造性而非现实性的支配,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观念来说虚拟的元宇宙其实是相对现实而言“按主体意志演绎的新‘在场”。虚拟在向着主体展开的过程中就蕴涵着创造性的行为,人类可以借助不可能的现实转化为虚拟的可能,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在现实与虚拟的循环生成中不断生成某种存在的真实性。元宇宙的火爆意味着人类充满了对超越现实、寻求心灵自由以及突破物理有限性的渴望,这也意味着虚拟浪潮已不可逆转,“人类和这个虚拟环境应是沉浸其中、超越其上、进出自如、交互作用”,在超越作为自然人麻痹于单一“复制”式生活的同时,得以生成数字生命获得高于现实、更为理想化的人生。元宇宙即是人类用另一种“生命”形式追求存在真理的空间。
三元宇宙的创生本质:思维的感性实践
(一)勾勒虚拟图景:思维符号的数字创生
在理智主义者看来,感觉、知觉、表象都是意识的内容,而思维则用抽象符号将意识的内容编码。我们在脑海中虚构出正感受着的或是想象的画面,甚至也包括对他人正在思考的东西进行想象就是思维的符号编码,所以思维是一种将感知觉体验转化为符号呈象的工作模式。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描述过自己进行思维时的思维状态,坦言道:“单词和语言在我的思考过程中似乎不起任何作用。我思索时的物理实体是符号和图象,它们按照我的意愿可以随时地重生和组合。”可以说“没有符号,人就不能思维,就只能是一个动物,因此符号是人的本质……符号创造了远离感觉的人的世界。”美国神经人类学家泰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也把“人类描绘为符号物种,思维之物即符号域是符号元素的集合,由人这个符号物种的行为组成。”对于人类的这一符号属性,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曾揭示人的思维中天然的是一种符号的运作,指出符号能传递意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任何符号最终都会在思维模式中得到解释。虚拟的数字化方式决定了个体也是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张明仓看来这种呈现方式“表现为思维形态的虚拟即虚拟思维,作用在于以虚拟思维的形式观念地超越世界,并进而通过虚拟思维引导现实实践。”虚拟思维不是虚假思维,而是打破规则,超越现实,从虚拟维度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作更多可能的探索与观念性的预测,在虚与实之间重新审视自身的认知與经验,进而反馈于实践。而虚拟思维的过程在元宇宙中则是以数字化、行为化的方式展现,这意味着构筑元宇宙世界的符号皆为人类的思维之物,智能算法对思维的符号进行挑选、组合、转换、再生后得到一个由符码组成的新现实。
虚拟思维除了具备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还具备一种能调动符码进行创造活动的“行为”特征,所以虚拟思维应是实践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双重思维方式的虚拟形式。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物质改造,元宇宙中的实践是“借助语言、符号、规则、数字等这些人化形式作为思维中介系统,达到对世界、对象、活动、意义等的人化形式的建构。”人作为一种会建模的动物,通过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可以让大脑进行形象建模后将文明、语言、环境等内容想象出来,借由数字技术将想象之物数字化后人类便能如“上帝”一般进行数字创生。又因为元宇宙是依赖虚拟技术与虚拟思维创造虚拟之物,延展数字世界维度的空间,所以我们可认为元宇宙的生产方式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符号生产。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判定,将大脑的思维图像符号化、表征化是人类在元宇宙中进行“物质”(这里的物质不具有实在性而是数字、信息或图像一类的事物)生产的方式,过程是通过符号化或数字化中介系统超越现实、观念地或实践地建构非现实的真实世界,目的是作用于上层建筑——元宇宙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灵性的提升。这样看来元宇宙的建构与发展几乎离不开人类思维的运思,而虚拟思维几乎解除了人类生理的限制,开放了主体的个性,得以让人的认知领域、思想空间得到空前的扩展。
人类通过交互技术、通信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建构虚拟思维中的想象之物,即是将感觉性的、空间性的或者经验性的东西以数字手段转化为虚拟之物,借此创造出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元宇宙是一堆代码组成的虚拟数字世界,只要虚拟思维的想象力不断绝,人类就能任意构造元宇宙,成就幻想视觉化的奇妙景观。元宇宙创生的基础是0与1组合而来的比特代码,虚拟思维是实践的中介,符号是展现之物。虚拟思维让符号生产摆置到更为广域的数字场域中,摆脱了自然规律与物理法则的约束,通过复制、模拟、想象将物质的基本属性抽象出来的,构成内涵更为丰富的虚拟创设。虚拟人会代替人类的肉身行为践行改造世界的任务,当任务完满之际,元宇宙也会像现实世界一样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并且是围绕着人类意志进行变换、蜕变的世界。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元宇宙是以意识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的世界,一切事物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对于生活在元宇宙中的虚拟人而言,虚拟思维就是用以模拟“上帝”造世的数字编码工具,能无限衍义元宇宙世界的数字图景。
(二)面向数字生存:思维行为化的虚拟实践
科技推动元宇宙布局的落地,让人类的生存空间由自然与社会的“二位一体”向着自然、社会、虚拟的“三位一体”世界转变,元宇宙也成为了新的劳动实践场域。虚拟思维作为建构元宇宙的重要思维工具,关键作用是将人类的视域从客观存在的实在性扩展到现实存在的不可能性,结合数字技术从无到有、从0到1地进行数字创生,也就是将人感性的时间、空间观念符号化、数字化。感性活动依赖于人类的思维表达,思维的光影“诸如法电,新新不停,一起一灭,不相待也”,今天的现实与昨日的虚拟、昨日的虚拟与今日的现实转化“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不同的是物质实践以“行为”为中介,虚拟实践的中介则是“思维”。虚拟实践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实践主体以数字化为中介手段,对对象进行的一种有目的、能动的构建、合成的感性活动。”在元宇宙中思维是行为的再现,而行为则是思维在现实中的落地方式,可以说“思维是行为”是虚拟实践的根本内核。虚拟实践转变了人类的传统生产关系,亦使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物,元宇宙成为了精神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
元宇宙作为未来人类可能生存的数字化平台,被认为是一个虚实高度交融的空间。这一空间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现实部分、虚构部分、虚实交融部分。现实部分既包含了对现实客观之物的全镜像,还包括现实社会“人文诸相”的投射;虚构部分即是人类运用创新性思维建构现实世界未有的新事物、新人类、新规则以及新智慧;虚实融合部分主要是指现实世界各类元素的属性、外形、功能等在元宇宙中被重构、改造,通过现实与想象的碰撞,得到全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新的环境决定新的思想,如果生存在元宇宙中的原住民形成了独属于虚拟世界的社会结构、虚拟文明、知识体系等,我们便不能以单一的精神或物质、虚拟或现实的二元对立目光看待虚拟实践的活动,而应该从虚拟存在的三个向度——虚拟存在的现实性;虚拟存在的虚实融合性;虚拟存在的虚构性,去观望虚拟思维在元宇宙实践中的作用深度、广度以及创造性范围。那么虚拟实践在虚拟思维的指引下何以从虚拟存在的三个向度进行对象性数字建构:
(1)虚拟存在的现实性。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经过思维的编码演化为虚拟的数字形态,无论是具有物质实在性的自然之物,还是诸如商业、娱乐、社交、文明等人文形态的创造之物皆以0与1的组合在元宇宙组合与编码,所以人类在元宇宙中的实践任务就包含复刻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与建构虚拟世界的人文系统两类。复刻现实世界的虚拟实践就是人类利用各类数字技术、模拟技术以及仿真技术打造三维现实世界,以期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建构元宇宙中的人文系统需要个体从具体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转移到抽象、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之中,利用自身在元宇宙中的某种身份进行生活经验的虚拟与人际的交互,从而人类社会的人文价值融入元宇宙的社会建构之中,进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种族等社会形态要素与虚拟世界的融合与重塑。可以说,人类在元宇宙中可以“从有到有(即从1到无限)”感受数字造物的过程,体验文明的创生与世界的涌现。
(2)虚拟存在的虚实融合性。在去中心化的机制作用下,元宇宙以人为本原,“聚焦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将所思所想以数字化的符号形式呈现出来。在现实世界,受认知思维的限制,以常规方式难以确证或认知的事物,例如未来的人类形态,宇宙宏观的发展脉络,甚至是已经封尘的历史事件、人物等都可以经由模拟、投射的方式在元宇宙中呈现,让人得以其中走进历史,畅想未来。可以说人类的思想能够运用虛拟技术在元宇宙中得到再现的同时,元宇宙也为人类的思想研究提供了实验条件、实验手段,这也意味着思想的思维运动已然成为可观察、可测量甚至可控制的变量,有望挖掘人类思维的密码以及认知水平的极限。
(3)虚拟存在的虚构性。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人类可以体验到现实不存在之物存在的真实感,如科幻生物、魔法异能、穿越时空等任何所能想到的模式都能透过感官设备反馈给知觉神经,在虚拟设备的加持下个体对不属于现实的虚拟物有了“感知即存在”的真实感。这种虚拟体验产生的所有知觉、经验、记忆等感觉材料不是由肉体行为传递,而是成为神经元的信息得以复制并创造。如此一来,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脑科学等高科技为基础的元宇宙建构,本质就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无中生有的创造”,这种人造的虚拟说明了“世界才是依赖主体的,或者说是主体建构了世界的性质”,即人类以“造物主”的身份引领科技的“造世”之举,操控、制造自己的想象,创造一个数字化的自由并具有无限可能的世界。
四创生转向:思维引领数字造物的两面性
(一)自我的失控,极端性的“数字进化”
元宇宙在虚拟实践与虚拟思维共同作用下,“将物质系统、观念系统、经济系统、活动空间、时间创造等本来不可能合为一处的社会各部分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实体。”人、符号、算法之间的碰撞、交涉、融合,加速了元宇宙世界数据造物的进程,其中突破现实认知限度的虚拟思维最大限度地为人类的虚拟实践发挥了创造性功能,借助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对事物进行各种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再组合。”人类现有的思维逻辑可以将自己从A点带到B点,但虚拟思维的无限想象力却能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这意味着“人类将从一个以描述活动为主的时代,进入到一个以创构活动为主的时代。”不过,由于虚拟思维是借助数字化实现的视觉化效果,所以诸如道德、伦理、情感等非理性的判断便难以运用数字计算规则进行理想化的处理,也无法用0与1一类冰冷的数字组合表示伦理情感的模糊项,因而在“非0即1”的虚拟世界里若过度放任虚拟思维的自由与滥用,可能导致道德、伦理、法规等一切约束人性的“因果链”在元宇宙这样的平行世界中失控、断裂,从而加剧了“人类知识与文化体系的裂变。”
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若人类进入到这种价值任意扩散,碎片化/片段化的秩序阶段,那么无论是价值的法则还是价值的判断都将消散于虚无,他将这种图像的发展称为“病毒的(viral)或放射(radiant)的社会/秩序。”在这个阶段,“事物、符号和行为都摆脱了各自的理念、观念、本性、价值、参照点和因果链,只是处在一种无止境的自我复制过程中”张天勇:《社会符号化—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研究》,第85页。,元宇宙社会可以让个体的意识数据、感知觉材料、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得到无穷的复制,如此一来虚拟思维反而会被元宇宙中的智能算法左右,导致本体意志沉迷于感性观念的符号狂欢中,如中了电脑病毒般失去自我的辩知。在元宇宙中,虚拟思维能够发挥不同于现实的创造性功能在于各类信息、数字的组合是由思维所驱动,表现形式为虚拟实践,驱动的工具则是用于搭建元宇宙底层架构的智能算法,智能算法虽能让“思维之物”以数据形态“体融相摄”,“融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融通在场和不在场的万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异化——主体的极端数字化甚至是虚拟化,这种极端性不仅表现为所有的喜好、偏向、个性等都为数字所裹挟,毫无知觉地认同算法的管理,而且也让人在高度数字化的虚拟世界里任由虚拟生存代替现实的劳动生产,将自身默化为虚拟存在并沉溺于算法制造的幻象泡沫之中虚实颠倒、人格混乱,失去自我。过度依赖算法的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反而会被智能算法蚕食殆尽,最终被消解了主体性,沉沦于算法制造的数字幻象之中。所以,即使元宇宙能突破人类生存的认知限度,我们也应警惕人类文明可能会随着智能算法对人类的全面支配逐渐凋敝,致使人类的主体性走向消亡的境地。
(二)消解自我设限,释放思维的创造力
“对人而言,事物就是非存在的有——其存在并不是客觀的,而是我们带着主观目的观察的结果。”英国哲学家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曾提出“存在即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命题,某个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能看到、观察到并触摸到,马克思以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一切存在都是观念的反映,“一个观念的存在,正在于其被感知。”而元宇宙的真实感便在于能为人带来沉浸式的实在感,“‘感知即真实就是元宇宙深度沉浸体验的本质表现。”观念是源自人的心灵的感知,并不需要依赖外在的物质存在便可以“按照我们所常见的秩序产生出来,而且也可以永远产生出来。”元宇宙作为人类思维的栖息之所,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笛卡尔、贝克莱、黑格尔等哲学人士对于“吾心即宇宙”的期待。元宇宙是以意识为第一性的世界,所有的知识、规则或者形态都可以被打乱、拆散、组合、异构,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不现实都在其中交织、碰撞、缠绕与勾连。
张明仓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是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在人脑中的内化,而内化的符号产物则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全部,勾连着过去到未来整体变化的人文形态。每一阶段的社会实践,人类对自然界以及自身都作出了最大努力的探索,现阶段物质文明的加速发展就是人类不断用智力超越体力局限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在怎样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人类对创世造物之迷的不懈追求,造就了虚拟现实的未来,也打开了探索人脑可延伸的思维向度的大门。元宇宙作为承载人类意识本体的数字空间,不仅是一个观察人类思维变化以及精神力量的实验基地,也是人类创新思想得以视觉化、虚拟化、实在化的绝佳场所,人类数字创生、思维造物的能力可以在元宇宙中得以孵化与生长。借由数字重组的生命在虚拟维度重新焕发犹如生孩童般超越现实尺度的想象力,这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也是数字创生最核心的动力。
人类必须进行虚拟革命不是为了享受数字世界带来的精神满足感,而是为思维创造一种无限衍义的进化条件,用于突破认知限度的屏障,使人真正获得解放自我、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元宇宙的落地与布局,也在晓示着科技的发展已隐隐有了突破现阶段人类文明之象,“人类或许已经不得逗留于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之中,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也许在与虚拟这一有别于现实的异己力量的对撞后,人类能从物质实在被消解的虚拟幻象中领悟到意识、思维、观念等元素里更为隐秘的力量,从而为进入下一阶段的人类文明作准备。
元宇宙的出现是科技推动社会步入智能时代所必经的节点。目前人类对元宇宙的所有设想都是基于弥补现实缺憾或者改善生产生活的角度进行的探讨,承载了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期望。我们与其将元宇宙看作是一个数字技术跃迁后所构建的虚拟世界,倒不如将之视为人类长久以来希望实现自我超越、突破自身有限性的一种象征体。一种集合了人类虚妄幻想、抽象认知、精神迷狂等意识内容的象征系统,也是释放人类内心最深处欲望的智能载体。网络空间暴露人性邪恶、虚伪一面的语言暴力与舆论戾气若成为居住在元宇宙中人类思维实践的惯习,那么元宇宙则会成为放大人类情绪思维的媒介,因而我们不得不担忧道德约束的消解是否会导致人类的思维运动背离人性,使人走向“非人”之路。元宇宙作为一个尚在实现中的假想世界,我们却已经从对它的想象中获得了反思,总结了问题、经验、方法等,甚至生成了各种预测、相关理论、应用场景的讨论与分析,并作用于现在的虚拟实践。所以元宇宙是会让人背离初心,堕入虚无网络的“鸦片”,还是让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得以提升的实验场所,关键在于人类是否能合理看待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形态。如果人类对于元宇宙的创构仅仅只是停留在造世的快感处,那么自由、泛滥的数字创构会将人类文明推向终结。只有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齐头并进,人类才能在安全的阈值内走向更高级别的文明样态。
The Quasi-Unreal Attribute of the Metaverse
and the “Primorism” of Thinking
WANG Shan, YAO Jia-li, LI Bing
Abstract: The metaverse has the quasi-unreal property, and the quasi-authenticity is manifested as the “real” effect constructed by the idea or imaginary symbol in the sense or function level. The non-authenticity is manifested in that the virtual object generated by thinking does not have physical meaning as the real object, so there is no truth in fact. And since the production of the metaverse is a practice where the physical body is absent and the mind is present, the metaverse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 human mind lives and produces “matter”.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human thinking, digital technology cannot automatically under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averse, so the essence of the creation of the metaverse is actually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hinking, rather than the direct creation of number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virtual liberation of humans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stronger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thinking to process, transform and construct the meta-universe world. Convers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a-universe can also react to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s thinking and spirituality, and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However, the excessive liberation of human thinking in the meta-universe may lead to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One is to cause the loss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dulge in the carnival of symbols in the digital world, and deviate from principles, humanity and ethics. The second is the elimination of self-handicraft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olidified thinking and seeking a new civilization and humanistic form. The progress or decline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pends on the tendency of thinking liberation. Only by always keeping the prediction and vigilance of the possible crisis generated by the meta-universe can we prevent human from falling into the emotional mania brought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metaverse; virtual thinking; virtual practice; thought creation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