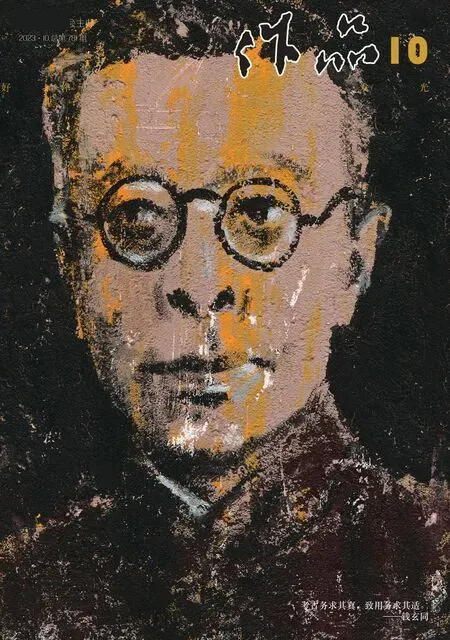胃的指向(散文)
耿立
一
在岭南有人问我哪里的
我说山东的
在山东有人问我哪里的
我说菏泽的
在菏泽有人问我哪里的
我说鄄城的
在鄄城有人问我哪里的
我说什集的
在什集没有人问我。
什集是我的故乡,我散文里常写作木镇,把什集拆开而成的一个精神的符号,这个暑假,我翻阅嘉靖年间的《濮州志》,什集被写作“石家集”,我们的村子,是明朝初年间从山西洪洞迁过来的,大人说,是有石姓周姓马姓等十家人家在这里成了一个集,方便人买卖,称为什家集。但对照400 多年前的《濮州志》,我觉得这个理由牵强。但从“石家集”到什家集,再到缩略版的什集,这期间的变故,早不可考。
这个暑假,我抵达了菏泽,故乡所在的市级的行政区划,抵达了鄄城,故乡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划,也抵达了什集,村一级的行政区划。
在什集没有人问我,我只是和姐姐穿过玉米的青纱帐,在农历七月十一日,给父母上坟。中午在外甥家里也吃到了老字号的什集烧羊肉。
我有时觉得,故乡就是一种馋,如一个热的老寒腿时时发作而已。
当我刚到岭南珠海时,开始是从曹濮平原到这亚热带气候,身体的转换和不适,身上起水疱瘙痒,接着是连续吃大米的胃的抗议。
我是吃面食长大的,父亲是做面饭生意的,在母亲和姐姐的手下,我吃过馒头,馍馍,卷子(黑卷子,白卷子,花里虎卷子),窝头(黑窝头,包皮窝头,米面窝头,杂面窝头),吃过烙饼,壮馍,炸过面泡、油条、肉盒、香油果子,馓子,也吃过韭菜鸡蛋菜托,饸烙,浇上醋蒜,粥,叫糊涂,玉米面的粥,高粱面的粥,地瓜面的粥,另外的汤,丸子汤,凉粉,甜汤,咸汤,疙瘩汤,面筋汤,鸡蛋汤,小鱼汤,胡辣汤,羊肉汤,最普遍的是面条,母亲擀面条,有白面条,绿豆面条,杂面条。
随着时令,不说白菜、黄瓜、甜瓜、西瓜、丝瓜、萝卜、蔓菁、苤蓝,就说那些柳丝、柳芽、榆钱、槐花、马蜂菜、灰灰菜、银银菜、苦苦菜、荠荠菜、扫帚菜,地瓜叶这些野菜,用点盐一腌,凉拌,配上醋蒜姜,再加上香油,真是无上的美味。
过去,故乡的人打招呼,都是一句:吃了吗?我记得,每次包饺子出锅,煮肉蒸馒头,母亲就会在灶前向虚空说:
爷爷吃,奶奶吃,灶爷吃,姑姑吃,财神吃,各路的,请到的请不到的,都来吃。
即使烙张饼,把饼烙煳了,母亲也忘不了祷告这一环节,母亲一辈子担惊受怕,生怕自己哪一丁点做得有了漏缝,就会被神灵怪罪,那她和孩子就会饿肚子遭灾殃,小民有的只是承受,只是大难来时的侥幸。
现在胃是可以喂饱了,但感觉灵魂的饥饿却一日甚于一日,也许,为了安妥自己,我才走出曹濮平原,但胃的诚实是,你的灵魂出走了,但它不舒服了,胃也会诚实地提出抗议。在岭南的第二个月,我的胃给友人诉苦,朋友就从故乡的银座商城买了几袋玉米面、小米面,快递到珠海。
还有就是五月的槐花从菏泽到珠海追了四千里,在快递员口中喊着:故乡,故乡!
当时,我正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晚间课堂上,突然手机响了,我挂掉,手机又响,挂掉三次,接着执拗响三次。我觉得一定是遇到急事,就对同学说声抱歉,接听了电话,听筒里只一句:槐花放你门口了,这是易坏的东西。
槐花是绪林寄来的,泡沫箱里放了冰袋。在槐花之前,绪林为我寄了榆钱。故乡的食物是驳杂的,稍一思索就可推测出,我们的祖先,是经历过饥荒和歉年景的,只要是药不死的,能果腹的,那就拿起来吃。食物中的那些咸鱼干、腊肉、臭豆腐、酱窝窝、酱豆子,这些能放一些时日,经冬历夏的东西,这些有着别致味道的食物,按鲁迅先生的推测,一定是先前的祖辈经历过饥荒才传下的,那些古怪的臭、干、咸的味道是饥荒和战乱的痕迹。
这次还乡,最大快朵颐的就是与朋友几个,一人一个羊头,也不管是报社主编、企业家、律师、诗人,大家像一下子回到了乡下的那个羊肉汤的汤锅前,一人抱着一个羊脑壳,满屋的咔哧咔哧的磨牙声,满口的留香。这里的人不说吃羊头,叫啃,更形象,更有质感。
吃羊头,主要是吃羊脸、羊眼、羊舌和羊脑。
现在人信奉吃啥补啥,在菏泽的羊肉汤馆里,有专门在碗里要一个羊脑再添汤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说,羊瘦不瘦眼,羊的眼窝是最肥美的地方。老北京的食客,嘴刁,在羊头铺子里,如果没有羊眼睛,那不算是卖羊头,会吃羊眼睛,才是老饕,才算资深的食客,会吃,味觉细腻。
想到宋朝人吃羊的仔细。
宋朝是我国生活的美学时代,《东京梦华录》里就记载了很多羊肉的吃法,看看那些留下的名目叫法,就令后人咂舌,比如乳炊羊、羊角腰子、罨生软羊面、入炉羊头签、羊闹厅等,但这些吃法,现在的人早就不明就里了。宋朝人对羊的看法有意思,觉得羊性格温顺平和,最是善良友好的代表,于是招待贵客的时候,就上羊肉做的菜品,以示尊重。
宋朝人吃羊,讲究吃活肉而不是死肉,而这传统菏泽也有遗存。吃活肉,就是吃羊脸肉。一只羊在其一生都要不断地吃草咀嚼,使羊脸的肉一直处于活动状态,因而味道鲜美。一个羊头上面,严格上说纯肉很少,那就是羊的脸子,羊头的双颊,这在宋代是所谓的“羊头签”,王安石最爱吃。有点像现在的寿司的吃法,把羊脸肉弄成卷,弄成圆筒样,状如抽签的签筒。
要我说活肉,那羊头上的羊舌最有资格。我是羊舌的拥趸,认为这是羊头之中最为味美的部位。剥去舌头上的一层白膜,那粉红的细肉,直冲眼睛鼻腔肠胃,所谓的色香味,一个舌头就全了。
但现在,人们吃羊头最重视的是羊脑。在儿子小时,那是他四岁之前,我父亲还在,几乎是每周的周六,父亲天一明,就到了我所在的师专的筒子楼。他骑着自行车,然后车子放在楼下,提着黑色的皮革提包,那里面放着两个热乎的羊头。父亲的理念里,小孩的脑子还没长全,吃啥补啥。
也许,有道理,儿子长大,性格偏于羊的温顺、善良。记得我母亲在的时候,我七八岁,母亲常说,要给我找个羊一样脾气的媳妇。那是母亲看出我温柔其表背后的烈与不管不顾的性格吗?虽然那种性格轻易不爆发,但母亲看出了这种潜藏,需要一个羊式的女性温柔以待,来包容感化。
二
好长时间,我是拒绝故乡的,日本俳句名家一茶的俳句最能诠释我对故乡的情感悖论。故乡对一茶而言,既让他怀念,又让他心痛,故乡对我亦复如是:
故乡呀,
挨着碰着,
都是带刺的花。
不错,故乡有父母的墓冢,有我情感的最后的牵挂,但父母生前在故乡的遭逢与磨难,还有我童年的记忆、青年的记忆,很多的是伤与痛。我曾尝试与故乡和解,但那些不快,就如我肉里扎下的刺,没有一根针可以从肉里挑出,那刺一直在,也一直提醒。
我喜欢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亲人》,这表达的对世间爱的逐渐缩小,最后入针尖的蜜,这多令人感动: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诗人的爱是狭小的,也是博大的,但随着岁月的沧桑,从年轻时的博爱逐渐回缩到眼前和鼻尖,云南省昭通市的土城乡,爱得逐渐缩小,爱得偏狭。自私没有大错,有时偏执的爱会更感动人。
我现在就反着想,我要像父母爱我一样爱他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翻转呢?如果真有轮回,让他们做一回我的儿女,颠倒一番,把这一世的爱补偿给他们。
因为,我的父母在人世间是缺爱的孤零的。父亲的父母是早早去世的,而母亲的父亲和母亲也是把她从小就寄养在姥姥家,而去闯了关东,母亲的父亲把命丢在了鞍山日本人开的煤矿里。我童年记得,姥姥去世下葬的时候,陪葬姥娘的应该是姥爷,但姥爷的尸骨无存,就用一只木匣子装了在十字路口抓的一抔黄土,算是姥爷的尸骨与灵魂在地下相会了。
父亲一辈子是被侮辱伤害的角色。在曹濮平原,曾被人无辜打昏死过,曾为生活屈辱下跪过,曾跳机井觅死被人扯着腿救上过,曾被投机倒把学习班当众侮辱泪流满面过,即使他有不平和怒火,也不敢哪怕对人间亮一下拳头,顶多只是私下号一句,骂一句,在酒里放平自己,躺倒自己,麻醉自己。而母亲是热血挣扎抗争,但由于丈夫的窝囊,而受到更多的歧视打击。但我们姊妹三个都继承了母亲的脑壳和性格的烈,基因的传承在暗处,但支配着你的行为。
母亲记忆力好,算账能力超群。在农村乡下,那些老头老太常有小赌,这是故乡的民性和民风。年轻的男人玩麻将,推牌九,输赢大,而母亲她们那些老太老头们赌注就一块八角。这种赌,叫码纸牌,就是明朝都有的水浒叶子,有120 张,对应的梁山寨诸好汉。老家离梁山不到200 华里,大家谈这些水浒人物就像说隔壁村的人物,透着一股亲切。
那纸牌分条饼万,还有老千。
记得一万——浪子燕青,二万——行者武松,九万——呼保义宋江;一饼——豹子头林冲,二饼——白日鼠白胜,九饼——花和尚鲁智深;一条——浪里白条张顺,二条——立地太岁阮小二,九条——玉麒麟卢俊义;老千是托塔天王晁盖。
我母亲和舅舅,就是母系家族的人,记性都特别出众。大舅也码牌,只要是他码了一圈牌,对手手里的牌他就能记住。母亲和大舅一样,除非自己走神了,在码牌的时候,十次就能赢九次。大舅就是靠在乡间的这种小赌,赢得一家的吃油点火的钱。
有次回老家,见一些老太太和母亲在我家门楼下码牌,夏天,都光着脊梁,那些哺育了儿女和日子的乳房都干瘪如空了的布袋,垂在腋下,见我,就随口说一句,别笑话。
那些人接着就说“三奶奶又赢了”(我们家族辈分高,这些老太太在母亲面前,大都是子孙辈,且我父亲行三,就叫我母亲三奶奶)。
“三奶奶,你儿子在外抓工资,还赢我们的?”
但我每次回家去看母亲,我的疲惫母亲是看出的,她总是问我,是否外面的水土不服?母亲会为我擀面条,或是,我躺在老家的床上,一气睡个一天一夜,母亲也不喊我。
曾有一年,我在城里,整夜整夜睡不着,临近年关的时候,临近天黑的时候,北风呼啸,我买了一张通向老家的车票,50 华里,3 块5 毛钱。到家,各家都已掌灯,各家的屋瓦上开始覆上一层白雪,天地苍茫。
我拍了拍门,母亲问一句:“成的(我的奶名),回来了?”
母亲有极强的感知,她知道雪天她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
母亲说,我给你烧汤去。
不想吃。
那你想吃啥?
想睡觉。
母亲为我铺了床,第二天我醒来,看母亲在床头正看着我,用手抚我的额头。外面的雪已经把整个村子覆盖了。
我到岭南十年,去父母的坟茔只有两次,一次是今年暑期,在疫情稍缓的七月十一日,在中元节的档期里。
早晨,姐姐和外甥女接我回老家的车未到,在杂乱的书桌前,我用毛笔于毛边纸上写下《壬寅七月十一日祭父母大人》:
父逝二十八载母别一十七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遭难后辈安康,唯愿父母在另一世界,无苦厄无灾殃,平淡平静。呜呼吾父哀哉吾母,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爱若纯金。赐我肉体生命,四野绿色,庄稼茂盛,沧海桑田。
祈父母在天之灵,福泽后辈,护佑子孙,使香火永续,家族兴旺。
言辞不及吾心,祷告父母万安。
耿立叩首。
壬寅七月十一日。
父母的坟茔在绿色的玉米林里,和姐姐外甥女穿过几米高的玉米林,找到了荒草覆盖的父母的坟茔,把祭文烧掉。
上一次上坟,是几年前雾霾正浓的二月,我去故乡讲学,天明,朋友驱车去宾馆看我,我说跟我去父母坟前一拜。
朋友颇知农村的礼仪,在路边,买了水果、纸钱,我说买瓶酒,父亲爱喝酒。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找到了那天的文字记录:
我看到了母亲的苍老,但我看不到地下,我知道她的肉早已朽腐,与土为一,而骨头会在;父亲的骨头也在。在地下十年的母亲的骨头,在追赶在地下二十年父亲骨头的成色;那骨头,是挑水、翻地、出工、灶下,赶集的骨头,是命运循环,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为活所羁的骨头;流泪,绝望,复制姥姥和爷爷基因的骨头,这两堆骨头回到大地的子宫,但我觉得大地乳房的干瘪,无法给这两堆骨头以营养,我带了一瓶酒、一挂香蕉和点心,在暗中,这些物质是否能给这两堆骨头以生活的补贴?我怀疑,这只是一种愧疚的方式,这两堆骨头不会再需要这些,他们委屈惯了,他们的苦,我怀疑我是否能安慰半分?
我蹲在麦田父母的坟茔前,浇地的水,使坟地有些塌陷,这些水应该能浸泡到那两堆骨头,这两堆骨头又多了一个春天,我把酒洒下了。母亲曾把最后的一滴乳汁给我,那是八岁,如今四十年过去,我怎么能补偿?我满眼的泪也许能抵达这两堆骨头,我想抱一抱这两堆骨头,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如果命真的有轮回,让我也抚养这两堆骨头一次,那样才少一些亏欠——
朋友和我来到父母的坟前,放上香蕉、点心,点上纸,朋友念叨着:老人家,你儿子看你来了,在那边,如果委屈了,就托梦。没钱花了就托梦。今天,你儿子,给你们带来了钱和酒,还有水果,你们慢慢享用。
父母的坟在快要返青的麦地里,寒碜,荒凉,衰草仓皇,天色晦暗,世间有谁知道这里的两堆枯骨呢?在我短暂讲学的几天时间里,灰暗的天幕下的县城,与满是委屈扭曲的脸庞眼神搭配,只有在与高中学生的短暂的对话中,我觉得涌动的热血还在。
家乡已经面目全非,我可能是故乡最后的容器了,那里还收纳着我求学一中后大门的红色木门,灰砖的院墙,我曾骑在上面,抄近路到新华书店买书。我在陌生的改造后的街道寻找亘古清泉古井,寻找旧戏台,和我曾与姐姐拉着地排车,上面装着4 个400 斤油桶的加油站。都没有了,我还是偏执地寻找着,仿佛那样的县城的故乡才是我的故乡,我的心理的地图的标示,还是一张旧的县城地图和乡镇地图。
我在故乡享受着荣耀,走出去的光环,也感觉到处处的不适与异样,访旧半为鬼,认识的人已经很少,老的那一辈,父母那一辈都不见了,同辈的堂兄,也有几个患癌症去世的,一个没出五服的老哥,快九十了,却硬朗,却一天一天说:我咋还不死呢?
母亲走后,只侄子结婚我回过老家,我看到什集一半是新的,镇子在扩张,镇子在破败,好像新与旧在比赛,看谁更能在天幕下荣耀。
我离开故乡时,故乡种棉花、小麦、红薯、大豆、高粱、谷子、芝麻,现在没人种棉花、红薯了,高粱已绝迹,麦子的种子与玉米的种子,也是转基因的,即使农村种的菜,也大多是转基因。
种棉花的时候,整日听说谁谁中午给棉花打药,中毒送医院了;谁谁两口子打架,媳妇抓起打棉花的药咕咚喝了半瓶,用地排车往医院送,半路就断气了。
什集村里,我认得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好像走掉的人,都在村外的地里埋葬了,这也是另一个村子。你觉得这土地最有情有义,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吃国粮抓工资,还是一辈子农民,光棍汉子,手脚不干净的,好吃懒做的,无论泼妇淫妇打爹骂娘,在村外土地里都集合收纳了。
这恰恰是另一什集的村民,在地下的村子里又做了邻居,但我还有担心,一辈子窝囊的父亲和抗争的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会受到良好的待遇吗?那些世间的魔鬼在另一个世界会有悲悯与良善?
我是满怀着激愤离开故乡的,故乡早已成了一个“他者”,故乡世界只是一个心灵的世界,没有父母,故乡就没有了归途,即使是缓慢的归途。
其实人类离开了母亲,就是告别了故乡,失去了故乡,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我们总是在回归和远离交错中,左右失据。故乡是地理坐标还是人情物理?它早已成为一种图腾,一种精神符号。
看到精神对故乡的依恋而看不到故乡对精神的钳制和枷锁,那是另一种故乡的囚徒,故乡你走不回去,故乡你也走不出来,这就是一个悖论和死循环。
但是否能超越这个死循环,把安心处、把巴黎伦敦布拉格,把塞万提斯、卡夫卡、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作为故乡?其实,故乡,就是一个安心之所,一个安顿人灵魂的处所,无他,哪里安顿灵魂,哪里免于恐惧,哪里就是故乡。
三
阿城有个独特的发现,这发现在我身上得到切实的印证。阿城说,所谓思乡,据他观察,基本是在异乡,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我到了珠海,大部分饮食习惯,还是山东靠近中原一代的面食习惯,对广东的早茶、煲汤,虽喜欢,但连续几天吃,胃就会提出抗议,于是就找山东餐馆,如果找不到,就找同属于中原的河南餐馆,每次到餐馆,必点一种凉菜:荆芥。
这是最解馋的菜品,那独特的有着薄荷药香的味道,外地人别说吃,闻到那气味,就会呕吐。
依照阿城先生的说法,小时候的食谱越单一,越有地域特性,那么长大后他的食物乡愁依赖就会越严重。
食谱越单一,则蛋白酶构成越顽固,非得那几样食物才能解扣,才能解馋不可。如果一个人年少时到过多个地方,他的蛋白酶就会丰富,就可以包容多种风格的东西吃,那成年后,对某种食物的执念,就不会那么重。
所谓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最好的例证。那些春运期间,大包小包,千里万里打包返乡,是匆忙,而不是迟缓,说白了,那是忘不掉家里灶前的酥肉、丸子、杂烩菜,那是少年的蛋白酶顽固执念的产物。
背叛故乡,背叛童年的蛋白酶哪能这么容易。在去年春节,若松给我寄了家乡的烧鸡、肘子、鸡爪、酱牛肉,季冬给我寄了赶在除夕绽放的牡丹,当时,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句文案,聊抒胸臆:
一棵离开故乡的牡丹
来珠海找我
我反抗过故乡
故乡却追上我
让我做故乡的证人
所谓故乡的证人,就是为故乡蛋白酶背书的人,是你的胃为故乡的味道守贞的人。我真真明白了,乡愁确实是一种馋,一种蛋白酶,这个馋,既指一个食物,也指一枝花朵,一个声音。
因为我讲话的土味,曾被某些人嗤笑,所以,这就如坐下的病症,以至于我时时确认我的位置,无论在何种地方,少发言或不发言,在人前掩饰自己缺失的自信,我的口音会暴露了我,我是移民,不是这里的土著。
但我却喜欢珠海,或者岭南的这些土著,最喜欢他们用粤语朗诵诗歌。虽然到这里十年,我还是听不懂一句粤语、一句客家话、一句潮汕话。
在课堂上,我让孩子们用家乡话来朗诵,一个孩子哭了,她说,她好久没说家乡话了,只有和奶奶通电话,才能听到家乡话。她是一个留守甘肃甘谷乡下的儿童,奶奶把她带大,后来高考,她考到了父母打工的珠海。我知道,那家乡话,一定是勾起了她有病的佝偻在乡下的奶奶。她说近八十岁的奶奶,还要养一头驴子,奶奶要攒些驴粪晒干,驴粪不用到地里,那是冬天填炕用的,填炕就是把那些驴粪做燃料,奶奶会让土炕成个把月地持续燃烧而不灭。
我忽然起了对家乡话,对方言的肃穆。我的父母去世了,我也很少能和谁用方言那么顺畅地交流了。
那是“创意写作”课,我让大家写出轻易不告诉别人的童年秘密,然后用方言讲述,那真是一幅奇异的世界。
潮州,汕头,河源,韶关,甘谷,黔东南,平顶山,口香糖、凉鞋、野黄狗、白乌鸦、娃娃鱼、海鸥、玩具汽车、飞机、篮球、洼地、影子、树木、灌木、燕群、阳光、树叶、餐具、鸟儿、青蛙、落叶、野兽、植物、动物、地震、梯地、矮树、平原、小屋、路、荒野、菜园、山谷、舞台、炕头,窑洞、途中、村子、超市、画面、土地、孩子、奶奶、竞赛、表演、风、荔枝、龙眼、死鱼、粪便、死者、记忆、河流、房子、纪念日、节庆日、河水、河岸、冰凌、响声、雪团、篮球网、铁框、暗影、猫、桌子、嘴唇、舌头、眼睛、睫毛、时间、生命、死亡、电线杆、图腾、轮胎、图案、木头、厕所、套话、警车、玻璃、相册、文身、墓地、白蘑菇、教堂、借书处、长椅、风琴、小鸟、鱼、河谷、河湾、源头、河口、沙子、流水、淤泥、网、细胞、地面、骨头、内心、草丛、树枝、树冠、石头、目光、棉袜。这些词语,都是生活的形态,都还原出了孩子们心灵里童年的故乡,孩子们在方言回忆中,缓慢地回乡,回到原初,大家都很严肃而兴奋。方言是另一个故乡,她是血液,在我们血管深处奔突,即使被普通话覆盖,有合适的机缘,她还是会被唤醒,那是我们的一次精神还乡。与普通话比起来,方言更具人情味,方言更像是母语,就像故乡在沦陷,方言在逐步消亡吗?下一代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为主,很多小孩已不会讲方言了,上海的小孩不会沪语,广东的小孩不会粤语,大家都讲普通话。有点像现在的城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标准的建筑,少了那种美丽的乡愁。方言就是一个人的故乡。
即使是课堂上,我大部分时间坚持用普通话授课,但一到需要抒发情感的时候,我在普通话里找不到对应的词和语调,我就会不自觉转化成方言。特别是我写文章、朗诵,用方言,我觉得才能走进文字。方言就是乡愁。
这次暑假我回到故乡,也很少听到方言的对话了,只是和姐姐交流,能听到最土的方言。姐姐虽不识字,但她每天坚持看《菏泽新闻》,她说那种说话腔调好听。在姐姐身上,我感到了深深的撕裂或者割裂:她喜欢种地割麦子,也喜欢盖房子,更喜欢城里,她现在就住在儿子在城里的17 层的楼房里。她闲不住,虽然中风语言有点影响,但她找了个一天就工作半天的环卫的活,最轻巧,只扫马路的树叶和尘土。她喜欢城里,见的人多。一辈子的庄稼地,她看够了。
城市和乡村是割裂的,一边渴望五谷丰登,一边在楼宇和车间的流水线做工。城市喜欢乡间的土地、空气、无污染的蔬菜,乡村追慕城里的超市和学校。我在思考有乡愁,也一定有城愁,故乡是一个地理的标尺,那可以是乡村,也可以是城市,但故乡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人是一个难伺候的物体,一边想念着故乡,一边却宁愿漂泊在他乡。我们离开故乡,然后再寻找故乡。故乡不会还在老地方等你,也许在你从来没有到达的方向,那里才指示着你的真实的心灵里的故乡,所以,我一直信奉王鼎钧先生说的: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因为我们人人都是一个异乡人。王鼎钧说:“‘还乡’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还不是由一个已被人接受的异乡到一个不熟悉不适应的异乡?我离乡已经44 年,世上有什么东西,在你放弃了他失落了他44 年之后还能真正再属于你?回去,还不是一个仓皇失措张口结舌的异乡人?”
我这次归乡,在家乡的一个多月里,因疫情,被静默在家几乎一半时间,陌生的楼房,街道几乎都不认识,原本的熟人,因为戴着口罩,都非常含糊,对面相逢不相识。我离开了十年,其实没离开前,我也不适应故乡,整日惶惑,就像是一个生活在故乡的异乡人。
与同学见面,同学说,每次聚会,你都不在;同学的孩子结婚你不在,同学的父母去世吊唁你不在。你就是一个活着的影子。齐格蒙·鲍曼有个术语,称这个变化的世界为“液态的变化世界”,液态的生活意味着流动的生活,我们人,何尝不是个液态的人?我们的流动,早把自己变成了自己家乡的异乡人。
但还乡的意义在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讲了一位叫乔治·保灵的保险推销员为了摆脱庸碌的家庭生活与乏味的工作,就做了一个抛弃现在安稳生活的决定,打算重回童年的小镇下宾菲尔德,重温母亲子宫一般往昔的美好时光。然而,当他驱车抵达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子宫时,一切都令他大失所望,子宫破败,故乡不再。“下宾菲尔德已被吞没,并像秘鲁那些消失的城市一样被埋葬了”,童年的美好,一切都成了夕阳下的废墟,一切都是枯败的明日黄花。
小说主人公乔治·保灵非但没有透上一口气,反而陷入了恐惧,艰难呼吸。他觉得:“现在是没有空气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垃圾桶高到了平流层”。让一个人的乡愁破灭,子宫破碎无疑是十分残忍的,但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谁的故乡不是液态的呢?谁的故乡是固态在那里纹丝不动地等你?
王鼎钧先生明白,乡愁是一种怀旧,但怀旧何尝不是一种负担,“回去,还不是一个仓皇失措张口结舌的异乡人”,你回不去,你也不必回。
纳博科夫很早就背井离乡离开了俄罗斯,流亡对他来说是液态,他并不觉得液态是痛苦的,他说,“流亡是他现在唯一可能的家园”;乡愁现在被看成了宣传,看成了一种引导,正愈来愈多地被看成一种伦理、一种道德,有时甚至是一种沉重的难以言说的政治。
美国的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01 年出版了一本书《怀旧的未来》,在这书中,她告诉人们,面对那充满残酷而又富于诗意的过去,一个知识分子应是如何面对?
英文词汇Nostalgia,来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因此英文Nostalgia 在汉语中就被译为“怀旧”或“乡愁”。在西方语境中,乡愁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它是一个医学用语,代表一种不易根治的病症,即那种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据说乡愁将耗尽精神的活力,引起恶心、失去胃口、肺部的病理变化、脑炎、心脏停跳、高烧、虚弱和自杀倾向。
古代人常患乡愁,但古代的乡愁偏重于空间,现代的乡愁偏向于时间。有的人想回到宋代,那其实是一种文化乡愁。布罗茨基曾试图与怀旧情结保持一种“疏离”,他尝试将乡愁转换成为“对世界文化的怀念”;就像诺瓦利斯所说:“哲学的确是一种乡愁;这是一种希望所到之处都是在家的要求。”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给“怀旧”一词下的定义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换句话说,在远方想家并不是怀旧,并不是乡愁,但是如果你返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却再也找不到回家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怀旧,真正的乡愁。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怀旧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冲动,精神的飘移,记忆的沉迷,幻象的觉醒。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的书给我的是棒喝:“当代的怀旧,与其说关系到过去,不如说关系到迅速消失的现在。”是的,乡愁是一种消失,它关乎的是现在,这无疑告诉你该如何清醒地对待乡愁,如何怀旧。
四
在我到有中原风味的餐馆寻找一种名叫荆芥的菜时,很多人都会疑惑地问:啥是荆芥?
我说是一种草,在夏天,暑气蒸腾,家里人拍了黄瓜,剁了蒜泥,配上麻汁,那黄瓜的清脆,蒜的辛辣,加上麻汁和荆芥的奇妙组合的香。那是夏天的防腐剂败火草。
没有吃过荆芥的人,你给他说荆芥的功能在醒窍效果,那味道直冲鼻腔、口腔,他不会明白,有时在饭店,我能一人独享一整盘凉拌荆芥,放点醋和盐。看到的人会惊讶咂舌。
春天的时候,在老家,人们在门口或是菜园的一角,那些犄角旮旯,随意一把种子,不知不觉间,一场雨后,荆芥就蓬蓬勃勃。什集及其中原一带,几乎家家都拥有席大的一片荆芥,有时吃面条,母亲就掐一把荆芥,放在面条上面,面条好像一下有了灵魂。
我吃荆芥的那种蛋白酶是母亲培养起来的,至今我还认为,荆芥才是天下至味。再就是,我童年的最高理想,就是能陪着察明山天天吃馒头。小时候家穷,只有到旧历的年下,才能在大年初一吃一天馒头,年初二,家家都换饭,白面馒头变成黑白面参半的食物。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离什集八里地的察明山插到我们班,他父亲在什集拖拉机站,开解放牌汽车。拖拉机站,是属于什集公社的财产,有几辆履带拖拉机和四轮拖拉机,察明山父亲开的一辆汽车,也属于拖拉机站。我问过察明山,汽车为何在拖拉机站里?
他说,我不知道,我爹知道。
一次下午放学,我在打扫教室的卫生,看见察明山坐在课桌上,在吃白面馒头,还有一块酱大头咸菜,我咽了一下唾沫。
察明山的腿来回晃荡,桌子的腿吱呀叫着。
他把手中的馒头掰了一半,递过来:吃吧,我爹开车去山西拉炭去了,七天回来,馍票都给我了。察明山像个富豪。
我们的友谊从半个馒头开始,馒头蛋白酶的加强也是从半个馒头开始。我在菏泽学院中文系做主任的时候,察明山到学校找过我,我安排了一大桌大菜,我说,伙计,吃吧,还你的馒头账。
但我不知道的是,我到了珠海,胃里还是欠着馒头账。岭南的馒头不是馒头,只能称作点心,它们没有酵母,没有杠子盘面,没有木柴火,没有铁锅,没有那些中原的泥土种下的麦子。那麦子经过霜,经过雪,经过干旱,那样的麦子蒸出的馒头,才是馒头,香甜,筋道。
每次我到北方讲学,都要背馒头回来,或者在网上网购;在珠海,凡是卖馒头的点,我都光顾过,但都没有北方馒头的那种味道。
我写过一首分行的诗句:
你的胃想说什么?/它的语言只有馒头听懂/上一次在家乡,你的胃召集/油条、豆沫、花卷、大饼、烧饼/还有水煎包、羊肉汤/就像是全委会/当时馒头只是点头通过//
到了珠海/你的胃总是点名家乡的馒头/你想和她谈谈家乡/她把面粉领回的家乡/她发酵粉膨胀的家乡/她揉面时专注的家乡//
胃开始拾掇出空隙/有一亩的地方,就给爱腾出一公顷/胃开始计数/吃一个,再一个/吃一个歇一会/吃馒头时,没咸菜/也好吃/胃里传导出小麦的清香。
这是一首本事诗,我从山东到广东,很多北方的朋友到岭南看我,来了,就大喝几次大酒,还是山东的做派,酒好对付,菜好对付,而馒头不好对付。
我不会用酵母蒸馒头,就到超市买面条,食单非常单一。一天,一个山东的朋友在黄昏时,提着一袋小麦面粉来了,还带着发酵粉,不用我打下手,发面、醒面、接面、揉面团、做馍、蒸馍六七道工序,如行云流水,最后连和面的盆、案板、手上,都不沾半点面粉,如庖丁解牛。
她一连给我蒸了她带来的20 斤面粉,把我的冰箱塞满。等她完工时,那都到了夜半时分。伶仃洋就在窗外,我看她瘫在沙发上的神情,那种倦怠,忽然就觉出,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只一个馒头、只一口辣椒面糊就能把我的胃拴牢一辈子,还有榆钱、槐花、玉米糁子、烧饼、烧鸡、酱猪蹄,还有小麦面的饼、壮馍、花糕,这些都是绳子,接力来珠海捆绑我。
故乡的蛋白酶。
就是好的那一口,温情的那一口,在四千里外的地方,像村口一样站立、像碗口一样敞开、像井口一样遥望,我把它命名为向故乡敞着的胃口。
我的胃向故乡敞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