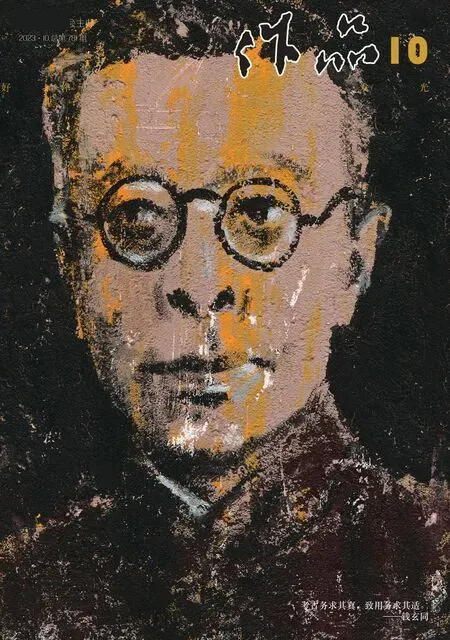结婚记(短篇小说)
杜峤
1
柳湘莲追上我时,已哭得不像个美人儿。眼泪像普罗米修斯的心脏般在上一颗坏死、崩解、飘散风中后以加特林抛壳的速率结出下一颗。脸被悲伤攥成一团,像颗没抿干净的果核,比他初生或临终时还要皱、还要苦、还要丑。一触到我,他就用树懒的姿势抱紧,将涕泪一泻千里地糊在我的道袍上,呜噜呜噜说,三妹啊!我并不知你是这等刚烈贤妻!可爱!可敬!老天障了我这双生疮的烂眼!你若定要出家,就是天要亡我啊!天要亡我!
我们这行,日日要看人堕泪、听人哭喊的。为了防止腻味,常在工作时把心翻个面儿,逼着自己想些解颐之事。例如此时,我的心念就游到某场跟警幻或她莺莺燕燕的小姐妹儿们调情的百仙之宴上,哪位姐姐手心最冷,哪位妹妹睫毛最软,心中渐渐浮出笑意。但这笑能露在脸上吗?人家在哭,你却在笑,未免被人嚼舌。永远不能被凡眼看透,这是我们的职业准则。心中大悲大喜时,面上却古井无波;面上大哭大笑时,心中却要无悲无喜。
见我无动于衷,他又换一副面目,显出日后作强梁的凶戾气,道,你若死了心要出家,我便屠光世上三千六百仙佛,拆遍天下四万八千寺,让你无佛可拜,无寺可依!这大不敬的妄语让我无名火起,但依然耐住性子,虽一时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至少先用一种蔑然的悲悯目光摄住他。
按照预想,这本该是趟闲差。这柳二本应在破庙失魂落魄地遇见我,稽首问道: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我只须露出一种空蒙的微笑,吐出一句云山雾罩的箴言: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他便醍醐灌顶,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乖乖随我回太虚境去了。一切本应如此。但在庙前我便发现事情已经脱离了掌控:他看见我时眼中一亮,迸溅出鎏金般的惊喜,像早已与我熟识似的,径直奔来。此前每一次度化任务都极为顺利,在我们的预先铺垫下,度化对象总会顺理成章地大彻大悟,成为我们业绩簿上的数字。这是第一次出现度化对象偏离预设行为轨道的状况。说实话,当时我感到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惊慌,好像从桥上走过时失足落入河中。我起身就跑,柳二拔腿便追。因为脚跛,我很久没跑过了,可能从出生起就没跑过。柳二虽风尘仆仆,却矫健激动得像只回光返照的荆棘鸟。我知道自己终将被追上,于是喘着气停脚,抚平道袍上的褶皱,面向他。在柳二的恸哭与威胁轮番上阵后,我渐渐冷静下来,逐渐明白眼前状况:因为悲伤过度,他错将我认作了自戕的未婚妻尤三姐。又见我身着道袍,坐在庙前,便误以为我这“三妹”要出家。
我很想呵斥他:尤三姐已经死了。自刎在你面前。用你的剑。或故作亲切地向他表明身份:你可以叫我渺渺真人。等以后我们成为同事,你可以学老癞头叫我渺渺。但《度化守则》第一百二十八条说,“度化对象陷入精神错乱或精神崩溃时,不得进行强烈刺激”;第二十四条说,“不得向世人及尚未完成度化的度化对象透露身份”。但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我也想不起哪一条写过“如果度化对象脱离预设行为轨道时怎么办”或“如果度化对象将你误认为另一个人怎么办?”。可能写过,但我的记忆里没有,那就等于没写。这时冷面柳二郎已经把我蹭成一只湿漉漉黏糊糊的蜗牛,伸手要掀我斗篷,说,三妹,我要看看你的脸。我强忍呕意,灵机一动,想到曾听老癞头提过一种“角色扮演疗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扮演度化对象心中最重要的人,取得其信任,进行循循善诱的、温和的度化。这种疗法较为保守,完整疗程耗时甚巨,但偶有奇效。此时我束手无策,只能一试。既然他误认我为尤三姐,我便化作尤三姐度化他。当下尽施法力,揭开斗篷,露出一张妙龄女子的脸。柳二立即歪着嘴像恶狗一样啃上来。我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你要完成任务。你要取得他的信任。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尤三姐。我渐渐挺胸站定,低声说,我不会出家。轻轻抚顺他因各种情绪向各个方向竖起的硬发,以一个泼辣女子内心潜藏的母性与柔美。只有那条腿仍跛着,如同狐妖化为人形后藏在裙下的尾巴。
2
治疗比想象中顺利。没有人对一个活生生的尤三姐感到诧异,好像在他们的时间线里我根本没死一样。最重要的是,在我的积极治疗下,柳二郎的脸日益冷了回来。他跟宝玉那种关系户不同,能成为万中挑一的度化对象,全靠他自个儿的天分。这天分全在一个“冷”字上。宝钗有宝钗的冷,黛玉有黛玉的冷,妙玉有妙玉的冷,元春有元春的冷,迎春有迎春的冷,惜春有惜春的冷。有的面冷,有的心冷,有的眼睛冷,有的嘴巴冷,有的头顶心冷,有的脚底板冷。但冷二郎的冷跟他们全然不同。他面冷心冷浑身冷,从灵魂到肉体到腰间两股白蛇般的鸳鸯剑都嘶嘶地冒冷气儿。这样的人,内心澄明,冰雪聪明,最易悟道。按照我们的预设,我(尤三姐)的死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的心冷到极点,就好办了。到眼下这田地,大概是我当日之死令他心神激荡,反而失了这与生俱来的“冷”。我如今想度化他,最先便要帮他找回这“冷”来。
第一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抚床道,三妹何出此言哪。我爱你的一切啊,你的魂灵,你的核心,你的记忆,你的思维,你的忧郁,你的激情,你的静默,你的醉狂,你的性冷淡,你的性高潮,你的活色生香,你的穷途末路,你孤峰独峙的心气,你受迫于幽暗而逃亡的影子。时间在你身上泛起的涟漪,风经过你时产生的悸动。我难得为尤三姐流了一回泪,说,这不像你的话。
第二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深情道,三妹,我爱你的绝色,你的眼睛,你的唇,你的脖子,你的腰肢,你的秀发,你的玉足。我说,我拔剑之前,不也是绝色?
第三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咬牙切齿道,三妹,我爱你忠贞节烈。我说,我早不是处子,同宝玉都耍过。他憋了半天,说,我也同宝玉耍过。
第四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面目狰狞道,爱你是根木桩,能拴住我这匹野马;爱你是堵院墙,能绝了那呆霸王的邪想。我说,木桩自有断时,墙也终会倒塌。
第五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羞然道,爱你是贾家的小姨子。我说,我大姐二姐都是贾家的夫人,你爱不爱?
第六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露出AI 般迷惘神色,道,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应该爱你。
第七日,我问他,二郎,你究竟爱我什么?柳二面无表情道,我不爱你了。
听到这句话时我大喜过望,像个刺客般翻身跃起,问,二郎,你可是勘破了?他没答话,愣愣地盯着我,像要把我脸盯出一口井来。有一瞬间他眼中射出两根近乎固态的冷光,我以为他真的悟了,以为下一刻他就会削发跟我走。但醒过神来后,他说,三妹,我们结婚吧。
3
事情就是从“结婚”这两个字如癞蛤蟆自泥沼中跃起般从他唇间迸出时全然迈入不可控之境的。博尔赫斯在其隐不传世的小说《卡夫卡的阿克琉斯之踵》中写道,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对其长怀一种影子对主人的隐秘仇恨,坚信世界上有一个独属于卡夫卡的词语,与卡夫卡的本质紧密相连,能置其于死地。他相信那个词就藏匿在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中,但搜遍每一行文字仍无功而返。最后,他违背卡夫卡的遗嘱将其所有小说整理出版,将那个词留给世人寻找。初闻这个故事时我觉得纯属虚构,但今天终于明白,“结婚”就是能置我于死地的那个词。听到这个词的瞬间,我感到自身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人事物都产生了一阵眩晕。虽然只维持了几秒,但世界已足以抹除它偷天换日的证据。我听说过“曼德拉效应”,一场世界篡改人类集体记忆的阴谋。但此时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被篡改的远远不只是记忆。一切已有的事物,一切固定的事物,一切二元对立的事物,都像一只被翻转的沙漏,外观似无区别,但每粒沙子的命运都天翻地覆了。最直观的症候是:我的法力消失了。我心中默诵神咒,屈指长捏剑诀,尝试变回渺渺真人,但只召来一阵清风和两只蚊子。
更像召令的是“结婚”这两个字。这座大墓般的府邸里的所有人如同嗅到新葬尸体的蛆虫从平日寂阒的各处角落拥来。大姐尤氏淌下红黄蓝交融的泪,三妹,何必嫁这浪荡子!凭你的姿色,等闲到北静王府做个姨娘。薛大傻子喷出不加掩饰的紫色刻毒妒火,尤三,你敢嫁我二郎,他有朝一日厌了你,我便向他讨了你来,卖去娼门,让你做回千人骑万人压的老本行!宝玉眼露七彩淫光,上前捏我的手,三姐姐,你和柳二哥这是英雄美人的金玉良缘,这一来我们亲上加亲了。傻姑升起纯白色笑容,拍手喊叫,结婚好结婚好,两个妖精打架,大家一块打架。我神魂如同一颗被翻炒的蚕豆,身子软得像一阵烟,似乎随时可能散去。这时我听见一声咳嗽,众人如在耳边炸了一个惊雷,并腿收腹立直了,像一把把唰啦啦收拢的伞。一个母蟹般的胖大老妪端坐于十二轮纯金宝椅内,以祥云的速度与气质挪上前。众伞向两侧排开,给她的声音让路。两瓣孔雀屁眼般的老唇缓缓翕动,嗓音如同电音。不是一般的电音,我想起一种非常规混音艺术,叫“脏南低切”,由美国南部传奇DJScrew 首创,将音轨调得极慢,人声切得极低,营造出一种刚学会说地球语的外星巨人一字一句训诫众生的威严感、延宕感与不真实感。眼前巨蟹老太婆的嗓音就自带这种混音效果,尤三丫头和柳小二的婚礼,就定在七天之后,因为七是最接近世界本质的数字。她说完后,先前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就像屠城后的天空,好像一切都未曾存在过。这时蟹夫人金光灿灿的甲壳后揉出一个穿豹纹紧身衣却有鹦鹉气质的女子。她用磁性且有亲和力的播音腔说,老祖宗已经定下了好日子,大家七天之后在这里集结,带好酒杯。众人这才像被按亮了音量键,爆发出“WOW”“呜呼”之类的欢呼。呼声中,我听到自己喃喃说,我不能结婚,我不想结婚。我本以为没人听见,但豹纹女转过身来,似乎第一次注意到我。我听到了什么?她夸张地在耳边比了一个扩音器,继而像话剧女主角询问所有观众一样:你们听到了吗?这片天空底下竟然有不想结婚的女人!我本来身如筛糠,此时一股原先蛰伏在这具身体深处的郁气蓦地冲上天灵盖,霍地从一滩烂泥中站起,说,我不结婚!听清了吗?我!不!结!婚!嘶喊完大口大口吸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触碰到这种分贝,感觉爽透了,好像一瞬间年轻了几百岁。我以为豹纹女会大为光火,但没有。她扭动臀部走过来,我们的新娘还以为自己是十三四岁的小糖果吗?看看你的眼角,看看你的胳膊,看看你的小肚子。顺着她黄鳝般的手指,我第一次开始抚摸自己的身体。下眼睑像一台鼓风机,吹起其领海内肌肤的波纹。嘴唇有点干,有种苹果片氧化后的蜡黄。颈子继承了眼睑下的波纹,同样是微风的吻痕,但从溪流变成河湾。乳房让你想到“海底捞月”这个词,说不清为什么会想到,但就是它,那种动作,那种触感,那种失落,那种空无。她把耳朵贴上我的左乳,听,咚咚咚,规律得像节拍器,要知道少女的心跳每一声都是不一样的。大臂的截面,展现出一种从正圆变为椭圆的趋势,某种看不见的劲泄了,赘肉正如洪水般涌来。腰上长出一圈圈环形灯管,亮着那种暗巷里成人按摩店磨砂玻璃透出来的微光。阴道与苹果肌一般松弛,黑洞不可遏制地日益膨胀,已经做好顺产的准备。到大腿时我暗暗紧绷,使其摸起来像十四岁少女的,但豹纹女轻轻一揪就识破了:一截生锈弹簧而已。最后的脚底板,她用小拇指指甲挠了三下,我未及询问用意,就听到她的叹息:你已经丧失痒的能力了。不是我们逼你结婚,而是你的身体逼你结婚。如果你再不结婚,它就会自己腐烂掉。豹纹姐满意地总结。
在豹纹女指引下抚摸自身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第一次触碰凡人女子肉身的惊栗中。它与我在太虚境爱抚过的任何一具飞仙玉体都完全不同,丑陋得像肉虫或小猪,却又有一种极为怪异的灼热感与诱惑力。当我将手指嵌进一寸寸肌肤,那种确凿的触感与重量让那些仙子姐姐在记忆中都虚化为全息投影。我不知道一具被准许保持未婚(或永远保鲜)的合格女体是何式何样的,但显然,我这具肉身不是。我想为这具肉身做点什么,但又无法抵御“结婚”这两个字带来的恐惧感。这种反差感让我感到无力与耻辱。但恐惧太过强大,强大到令任何情感的枝蔓臣服。天平一端塞着一团乱麻,另一端压了一座泰山。没有办法。我对自己说:你输了。这次任务虽然几经波折,甚至在兵行险招之下有望成功,但终于还是功亏一篑。我已经准备好回到太虚境接受惩罚,至少要禁足思过一个月,禁色静心三个月。警幻那骚娘们看我吃瘪心里一定要乐疯了,不过大概很快就会想念我。是的,为了脱身,我决定放弃任务,并违反《度化守则》第二十四条“不得向世人及尚未完成度化的度化对象透露身份”,对柳湘莲与这些凡人说出我的来历。我以上仙的蔑然目光环顾每一个人,包括贾母、凤姐、柳湘莲。
太僭越了。我不是你们的什么尤三姐,我乃逍遥二仙之太虚左使渺渺真人,特来度化尔等。
4
众人看我的眼神不像看一个仙,更像看一只陷足泥沼的鹤。好像我的观赏性在几十秒之内完成了质的飞跃。放在以前,我会把他们都飘起来,再自由落体砸成肉饼,但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将我系何人、所来何为向他们和盘托出。
你若真是神仙,我们自然是敬重的。但你如何证明所言不虚呢?贾母缓缓开口。
是啊!如何证明?凤姐附和道,若证明不了,只能请张老神仙来镇压邪祟了。
我沉默片刻,说,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愿提及。除了“渺渺真人”这个法号,我另有一个绰号,称作“跛道人”。虽然我如今形貌大变,已无一丝仙风道骨,但无论我变作什么,都永远甩不脱这条跛腿。它曾是我耻辱的烙印,在今天,却成为我证明自己身份的唯一证据。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众人先是一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有喷饭的,有滚到女人怀里的,有叫男人“心肝”的,有说不出话来的,有饭碗扣在人头上的,有叫下人揉肠子的,整个院子就像一朵迎风怒放的霸王花。凤姐忍住笑,对我说,三丫头,你前番确实受了苦,这样当众刺你老公,咱们也说不了你,但累着老祖宗担惊受怕就不好了。贾母慢慢散了笑容,以一种令人生惧的慈祥说,下不为例啊。宝玉在人群中喊话,散了散了,三姐姐耍我们玩呢。
我拽他们衣服,你们别走啊,你们笑什么?但他们就像练了泥鳅功,哧溜一下就从手里滑走了。最后只有两个人留下来。一个是柳湘莲,另一个是个女孩儿。刚才她一直静静立在人群边缘,像一枚青黑色的太湖石,或一盆栽废了但主家因其别有风韵没舍得扔的盆景。她走过来说,你还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吗?我皱皱眉。她说,那日柳湘莲正欲悔婚,你在帘后听得分明,将一股雌锋隐于肘下,将雄锋掷还与他,回手便掣出雌锋,往颈上抹去。那柳二习武出身,眼疾手快,雄锋后发先至,在锋刃触到你颈子的前一刻,自上而下将其斜斜挑开。锋刃躲过了你的喉咙,但在你的腿上划出一道长近三尺的血口。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请来的太医说虽无性命之危,但这条腿恐怕要一年半载才能痊愈。结果你第一日就醒来,第三日就能撑着桌椅走路,第七日大闹要削发出家,趁所有人不留神竟逃出府去。最后还是柳二将你追回。她一边说一边喘气,好像她一辈子都没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又好像记忆中两剑交击的寒光与铮铮声迫得她难以正常呼吸。说完向我点一下头,走了。
我脑中轰轰乱响,不顾有人,扯开裙裾露出那条跛腿来看。那道长疤像一枝落在皑皑白雪中的梅。我能想象它最初血肉外翻的惨状,但现在更像一副妖冶的文身,好像我失去的仙力全被使用到使伤腿痊愈这件事上。这时柳湘莲走过来拥住我肩膀,说,三妹你看,它很快就要痊愈如初了。我一时有点愣神,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好像一觉醒来人类已经登上了太阳。这条腿陪了我几百年,从我还是一个婴儿道人时。它素来是我最大的心病。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天残地缺,最初谁也笑不了谁。但后来警幻脸上跟脖子上的粉色大痣都用激光点了,癞头和尚也早就植了发,而我除非愿意将跛腿砍掉重新装一只机械腿,否则它就会永生永世陪着我。但现在,它即将痊愈,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向我道别。我没有无数次预想中的狂喜,好像一个老朋友即将病逝一样。
5
柳湘莲其实有点可怜。这时节没人顾得上他这个准新郎。可能是我这个疯新娘抢了他的风头,也可能是他即将成婚,所以在这个圈子里的性吸引力大幅下降,你知道男明星喜欢隐婚就是因为怕女友粉掉光光。前几天我也对他忽冷忽热,但他似乎铁了心要跟我结婚,为此愿意按捺住所有情绪,成为一匹任我驱驰的小马驹。
他立下誓约,去为我寻那面遗失已久的风月宝鉴。我不知道他要如何寻、去哪寻,但既然他相信那是我唯一的嫁妆并保证会在婚期之前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我也乐得清净,嘱咐一句“只可看正面,不可看反面”后,便打发他去了。
此时房中只有我一人。这六天里,我以睡美人式的谦和乖巧将房外五个监视我的婢女麻痹得毫无戒心,此刻她们全都倚靠窗棂睡得如同死掉的河豚。这座宅子里的所有人都以为我认命了,绝望了(以他们的视角,是我悔悟了),但他们忘了我还有一张底牌:
我的金牌搭档,茫茫大士,癞头僧。
其实我早已在这座宅院里感受到他的气机。平静冲淡,说明事情皆在掌控之中。他没先来找我,大概也是因为另有计划。这几天里,我每日在屋内闭目冥想,已经确定了他所在之处——尤二姐所居的宅子。我细忖之下,他大概是见我失手,便化身尤二姐,先潜入贾府,届时里应外合,救我脱身,运气好的话,还能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我想拿到一个证据,证明我之为我的证据。不仅为让他们相信,更是为我自己。再这样下去,十日,百日,千日,我怕我真的忘了我是谁,真的变成尤三姐。
我在窗前哒哒哒敲了一段莫尔斯电码,侧耳等了半天,没有回音。起了疑心:以我和癞头僧的默契,就算按计划他必须暂时蛰伏,也不应该完全不理我。
我又想到,癞头僧或许也与我一样处于被监视状态。便轻轻叩门,躲在门后,待两个婢女先后出来时,以手刀将她们斩晕。屋里亮起一盏微灯。
是谁?声音像一段秋风,已经与本音迥异,但我依然知道是他。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把鸡尾酒调得五光十色,但真正的老酒客抿一口就能辨认出底酒是什么。我心中激动,虽然与他别过不足一月,却因为这段平地波澜,好似他乡遇故知一般。老癞头,是我。我跨进门,看见一张陌生的、泥金宣纸一样的脸。
妹妹,是你来了。两个丫头没回来,我也使不动她们,正要撑起来看呢。
你怎么成这样了?
妹妹,不要为我担心。我与琏二爷爱了一场,此生再无憾恨了。
谁把你弄成这样?我纵是肉身不保,也要杀他。
妹妹,你总是这么刚烈。我总对你说,这样不好。另外,凤姐姐待我很好,我走之后,你莫要跟她置气。
你全忘了吗?放在以前,你怎会受这等鸟气?
以前?你说的是前世吧。前几日听她们说你要出家,想来是得到大师指点了。我以前不信这些。但这些天里,我躺在床上,每晕过去一次,就会看见莲花。我越来越相信命,相信因缘际会,相信前世。你能帮姐姐看看前世吗?
你不要瞎想。
说说吧,姐姐想听。
那我慢慢地说,如果你想起什么,就告诉我,好不好?只要你都想起来,病就好了。
好。我听着呢。
你前世是一位高僧,名叫茫茫大士。你头上曾经生过疮,后来治好了,甚至植了发,但我还是叫你老癞头。你知道当一个绰号或玩笑并不指向真实时,就不具备攻击性。你叫我渺渺,从来不叫我死瘸子,因为我的腿一直治不好。也正是倚仗这一点,我总对你表现出一种不对等的、近乎依赖性质的蛮横与懒散。别人如果盯着我的跛腿多看几秒,我就要上去抠出他的眼球来。但和你做任务计划分工时,我都会拍拍我的腿,向你狡黠地点一下头,意思是:你做大头,我做小头。有时任务太过复杂,我直接大声骂娘,甩手回太虚境找小仙女喝花酒。一个月后上面派人下来表彰,往我额头上贴大红花,回头看你,你笑着边鼓掌边推我。我一直觉得你是根红杉木,竖起来能撑住天,横下来能渡过海,滚起来能轧死所有魑魅魍魉。长久以来,我在对你的敬慕、友爱、依赖、默契之外,还生出一种暗流般绵绵不绝、纤弱极富韧性的感情:嫉妒。但现在轮到我手足无措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你会这样躺在我面前,这样羸弱,这样安静,这样视死如归。你还能想起来原先的风光吗?
姐姐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就是被琏二爷娶进门的那天。
你听我说。你记得那次任务吗?我们被要求去度化家庭美满、官运亨通的甄士隐。你曾经向上面提问,这样根骨普通的凡人,究竟有什么度化价值呢?上面说,这是一场职业能力测试,考验你们如何让一个最平庸、最完满、最不可能顿悟的人顿悟。当时我们产生了分歧,我花两个月写了一首《好了歌》,并谱上最萧然、最空寂、最令人心死的曲调,在他眼前高唱,却收效甚微,他只当撞见了疯子。在我以为任务即将失败的时候,你出手了。你擦燃了火柴,做了一个我们小时候飞扑克牌那样的潇洒动作,将它丢进甄府,然后轻吹一口气,那火柴便燃作扑天大火。我还怔怔地站在那时,你又将那个叫甄英莲的女婴丢进人贩的背袋中。那次回来后我上书控诉你的恶行,你知道的,当然石沉大海。从那以后,我很少跟你说话,做任务与你分工明确,分头行动,井水不犯河水。我知道你好几次在我能力不支时暗中帮我做完扫尾工作,回去交完任务歇脚时也想走过来给我递根烟。但你不知道的是,我这么做不是(或者说绝不仅是)出于对你的憎恶,而是因为长久以来积压的嫉妒终于达到一个令我无法控制的顶点。你还记得我们这次的任务吗?我毛遂自荐参与行动计划组。首先,要将柳湘莲“冷”的天赋激发到极限,就必须让他直面人生的虚无,我们没有时间让他悟透沧桑,也没有时间复制上次的计划,等他生下子女再褫夺。只能将虚无最直接的形式呈现在他眼前:死亡。他双亲早亡,生命中最难以斩断的羁绊只剩爱情。那我们就杀死他的爱情。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他们二人相识时间较短、感情基础较为薄弱,无法保证尤三姐之死对于柳湘莲的刺激能使其悟道。任务风险太大,且一旦失败,我们将永久失去尤三姐这个唯一的刺激物。以可卿为首的几位研究员倾向于放弃计划,保守治疗,等待柳、尤数年后感情愈笃,再作打算。但我等不起,我必须尽快解决自己道心不稳的危机。那几天我彻夜难眠,在脑中如导演系学生拉片般翻来覆去回想你当初丢火柴时那种视万物为刍狗的漠然神情。最终,我想出一条妙计。我们可以人为强化尤三姐之死对于柳湘莲的刺激。我们可以让她死在他面前。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让她死在他的剑下。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的误解与过失。我们要让他紧紧抱着她从活泛到安静的躯体,让他凝注她由炽热到冰凉的眼睛,让他吻她脸上那滴由莹润变干涸最后晨露般消散的泪。让他经历一个气球慢慢散气、一方废弃泳池慢慢晒干、一朵玫瑰慢慢枯萎的过程。我们相信,能全身心地沉浸、感受、憎恨、畏惧、喟叹、漠视生与死并在此过程中产生其他生物无法理解的精神升华,是人类独有的高贵能力。怀着这种一闪而逝的敬畏感,我给宝玉下了迷药,让他对柳湘莲色迷迷地提起尤三姐的绝色来,炫耀他们兄弟几个都曾与她们姐妹混过。为了确保尤三姐有足够的魄力与勇气,我给睡梦中的她打了一种消除恐惧感的新型兴奋剂,并在梦里对她说,死亡是你对爱郎的轻蔑最有力的复仇,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这一次,激烈反对的反而是你。你说自己火烧甄府毕竟烧的只是身外之物,并未伤及人命,而这个计划未免太过残酷。但当行动计划组发现这个计划(诸多细节由他们去打磨)将任务的可行性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便以高票当选为行动负责人,作为组员,你只能按计划行事。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赢了,彻彻底底地赢了,用你的方式赢你,但又是一种变相的失败,因为我的方式最终被你的方式打败了,我终于变成了与你一样的人,甚至比你更像你。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变成了这样。但不可否认,我们就是由我们的所有行为构成的。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其实我注意到,说完“姐姐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就是被琏二爷娶进门的那天”这句话后,尤二姐就咽气了。但我还是把话说完了。还是那个老博尔赫斯,他说,记忆只有贮藏于时间深处时才是确凿存在的,当它们化作语言宣之于口的那个瞬间,就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被抹除了。按照这个逻辑,我这段话也算替他完成了某种临终忏悔。我本是为求救赎而来,却最终救赎了茫茫。我本想借此脱身,却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我想这就是茫茫到死仍悟不透的因果。他可以一死了之,我还得去面对我的因果。
6
柳二郎是提着剑回来的。一看眼睛,我就知道他道悟了。我想起茫茫那次纵火时的眼神,没有杀气,没有情绪,你非要往深了看,只能看到一片冰湖。一模一样。
我顺着两把鸳鸯剑锋刃上滴滴啦啦的汁液向外望去。满地被切碎的水果。虽然它们都爆裂分崩、汁水四溢,但我还是能认清谁是谁。你们参加过每人用一种水果代表自己进行自我介绍并让大家猜身份的假面舞会吗?这烂苹果是贾母。这烂山竹是宝玉。这烂车厘子是凤姐。这烂荔枝是宝钗。这烂龙眼是袭人。这烂梨是李纨。这烂哈密瓜是薛蟠。数不胜数,一共有七百多个水果呢。注意,不是七百多种水果,很多人共用一种水果,只是大小、形状不一。这些水果都开膛破肚,露出它们的核心,展露出它们最真实的妍媸。你们可能会觉得那是很美的画面,彩虹、梦幻与迪士尼。但现实状况要更复杂些,一开始确实很美,但当所有果肉都化为汁液并汇流于沁芳渠时,你会发现所有颜色都被消弭、吞噬、融合了。小时候美术课玩过把所有颜料都挤进调色盘看看能调出什么颜色的游戏吗?好奇心往往被耐心打败。但我试过,当最后一种颜色滴入搅匀,那种最终的颜色出现了,就如同眼前一样。黑色,与人瞳孔一样的颜色,与柳二郎剑锋一样的颜色。
他没说话,从怀中掏出风月宝鉴递给我。我以为自己会露出惊诧的表情,但只是轻声问他,你看背面了?他静默点头。
我没有再说话。仔细想想,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让他去找,他就有可能找到。既然他找到了,就有可能会看。既然他看了,就很可能会看背面。既然他看了背面,就很可能会顿悟。既然他顿悟了,就很可能想切水果。至于他看到了什么,我没问。
他也没再说话。我们都知道,我还有最后一个程序没走,一个定义、一个审判、一个答案。我没有看正面。在它尚未遗失时,我就看过无数遍。每次镜中出现的脸都是我自己。他年轻,皮肤好,没眼袋,胡子剃得只剩一层青青的磨砂,眼神因为过于澄澈而显得空洞,其余都与我没什么区别。有时我想,这不就是一个美颜相机吗?有时我怀疑它已经失去魔力,变成与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镜子一般无二的凡物。有时我又想起,在那次失败的任务中,贾瑞说他在宝鉴正面看见了凤姐。如果每个人都会在宝鉴正面看见自己爱的人,那我大概有点自恋倾向。其实想测试风月宝鉴是否还具有魔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背面。但我从未试过,是不敢试吗?还是单纯觉得无聊?是怕看后像贾瑞一般暴毙吗?还是害怕得到那个终极答案?我不知道。唯一可喜的是,此时此刻,我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无喜无惧,无悲无乐。
我轻轻擦拭镜面,在某个瞬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其反转。以前和大家玩牌时,茫茫教过我一招老千,当你摸到的牌点数不佳时,就用大家来不及反应、它也来不及反应的速度将其翻转,它就会变成另一张牌。正是凭这一手,茫茫在太虚境屡战屡胜。我的技术远不如他熟练精湛,有时千术失效,有时开出更小的牌。每次张开手掌查验结果前,我手心就会冒出一个泉眼,耳垂会红成一块烙铁。我本以为在经历这么多事后,紧张这种情绪不会再降临在我身上了。但当我的目光移向手中那张硕大无朋、性命攸关的牌时,它再次掠过,比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浅析尤三姐形象及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