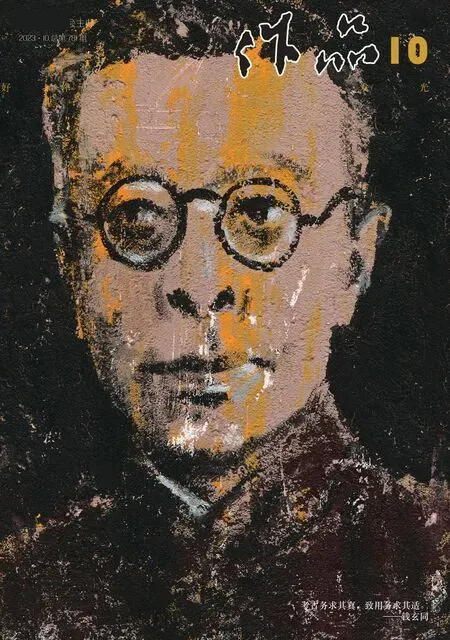照相记(短篇小说)
杜峤
1
在苏廷乾先生失踪一年后,我收到他的短信。陌生号码,打过去已停机,但我确定是他。内容仅短短八字:饯花之期,故地重游。“饯花之期”,即饯花节,农历四月二十六,《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生日,也是苏先生的生日。他曾有句诗以宝玉自拟,“我在百花死日生”,说的便是此日。“故地重游”,答案也昭然若揭。我们的足迹曾遍布金陵,但第一个从心中跃起的地名,无疑是小观园。
89 路公交车坐到豫和路下,拐进九曲八折的幽巷。尽头有片围墙,让出一个篱门,上书“小观园”。我推门进去。院中有池无水,置白灵璧数品,古拙圆匀。石径旁杂竹几竿,疏影在壁,似二毛之头。今天雾重,天像没完全亮起来似的,有点像教学楼后山的那段夜路。很多次我随他在竹前走过,他的背影一没入黑暗,好像就松懈下来,颓惫下来。每值这种时刻,我才会惊觉他老得如此赫然。但老毕竟只是老,我们都觉得他还能再老几十年。警方的电话打过来时,我们都觉得他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几天后就会回来。几天,一周,一个月,直至一年后的今天。
整个院子模仿大观园建成,书中一切亭台池阁,在此地都能寻到遥相呼应的风物。门口那几块灵璧石,便是蘅芜苑;那几竿竹子,便是潇湘馆;脚下这条蜿蜒小径,则是贯通大观园诸景的沁芳溪。而石径尽头的那幢小楼,正是怡红院。它也是此园的中心,苏先生失踪前的住所。我慢慢踅过去,有一种近乡情愈怯的忸怩。好像梦境与现实只有数步之隔,短短十余步,竟像要泅渡过长河般的半生。
转角出现的背影是熟悉的。在我僵住脚步之前,她转身仰首。那张脸像二十岁时一样光洁明丽,好像任何人事物在她身边就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时间也未能免俗。但待到看第二眼,又发现她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没以前那么瘦了,鼻尖与下巴的线条柔和下来,眉眼间的坚冰融成了春水,“笑”的天赋时隔多年重临她的唇角。
你也收到老苏的短信了?声音也暖软。我怔怔地点头。那陪我走走吧,短信里不是说了嘛,故地重游,她说。老苏还没来?我问。边走边等他嘛,她笑。我没理由拒绝,但控制步速落后她一个身距。那些说恋人分手后也能做回亲密无间好友的,在我看来都是扯淡。我在心底默想:如果春懿重提我们破碎的感情,我就立即离开,即使苏先生来也不管用。但她好像并无此意,反而说那些我不忍忘却的细琐小事。比如某次学校超市买的三明治变质了,但我们三个都顾着聊天,没一个吃出来,最后收拾垃圾时才在包装纸上发现过期一个月,回去后我们每隔一个小时打电话问彼此有没有拉肚子。还有次我们走到半路突然下雨,没人带伞,我们就把学院发的餐布张开撑在头顶,三人挤作一团,像棵刚学会走路的连体蘑菇。最后我们干脆扔掉餐布,在雨里疯跑起来。还有“掷团子”。这是我俩的暗号。《红楼梦》元妃省亲一节,宝玉连作三律,才思枯竭,黛玉帮宝玉想好一律,写在纸上,搓成个团子,偷偷掷到他眼前。我们把背着苏先生说小话戏称为“掷团子”。后来苏先生远远看到我们,就蹑足潜到身后,突然说,你们又掷团子呢?吓得我们像受惊的小鹿般跳起来。沿着小观园的围墙走了一圈后,我已经与春懿并肩而行了。某个时刻她停下来望着我的脸,柔声说,我们拍张合照吧。这么多年,我们连一张合照都没有呢。
我心中升起一丝歉疚。我确实欠她一张照片,但如果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摆造型未免太傻。一会拍吧,你先跟我讲讲老苏是怎么失踪的,等你讲完再拍。
2
我和春懿都是苏先生的学生,说得严谨一点,是弟子。
苏廷乾,红学学者,我大学时期的导师。母校是经济类院校,文学院门衰祚薄,师生比将近1:3,“导师制”是为了使老师免受“吃闲饭”之讥。我那时痴迷《红楼梦》,也拜读过苏先生的文章与旧诗,很具讽味,填导师志愿时毫不犹豫选了他。入门后才知道,苏先生是院里有名的“硬骨头”“甩手掌柜”,绰号“苏石头”。上下四届,我独苗一根。现在想来,苏先生时而肃容寡言,时而一副睥睨时俗的痴性情,我若是早些听到他的名声,大概也要迟疑。
我从系主任那要到了他的微信,战战兢兢在申请中附上简短自我介绍,发过去。第二天中午才通过。我赶忙发“老师您好!”。他没再回我。
真正有接触是在公选课“红楼梦与文学写作”上,他给我们一段苏轼的文字,六十个字,让我们发挥想象,将其扩写至五百字左右,课间上交。说完洒然出门。邻座几个女生纷纷拿出手机开始玩消消乐。我忘带充电宝,又正好有些兴致,便操笔涂鸦了一段半文半白的浮文,在女孩们的不屑目光中以“考试第一个交卷”的激动步伐走上去,刚回到座位,就见他抽完烟回来。他拈起来看毕,石皮般的脸竟然皲裂出微笑,叩击三下黑板,将睡觉的同学惊醒。这位同学写得不错,哪位同学来帮他读一下?第一排最中间的女生举手,随即开声吟诵,咿咿唔唔,清越流亮,如同云上的琴音。我面热之余,心下也生一点痒意,想赶紧等下课走到前面看她的脸。
自那之后,《红楼梦》常把我们三个聚在一起。身在工程学院,春懿没法选苏先生做导师,但学业之余,常与我们雅聚。小观园草坪上常常能看到带学院商标的绿色餐布,比青草还鲜明打眼。我们围坐谈谈最近读的书,吃一点三明治和鸭脖子,春懿从包里拿出三盒她做的水果沙拉。苏先生不许我们喝酒,最多乘兴喝点五颜六色的鸡尾酒。天光明媚,亭榭曲折,有点“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味。苏先生的不苟言笑带有唬人性质,按他的话来说,“我只是不想在庸人身上浪费时间罢了”。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心中一凛,但很快就会展颜。我们没人会说笑话,但那段时光蓝天是笑的,青草也是笑的,我们没法不笑,即使是聊学术相关的问题时。春懿基础远不如我,更别说苏先生。当时我有一种傲慢的潜意识,觉得每次野餐聚谈,春懿的受益总是最大的。但这种偏见短短数月内就被打破,春懿脱口便能大段背诵《红楼梦》原文,或提到某句时能谈出背后极隐晦或极冷僻的典故。我们不知道她是记忆力超群还是在背后下了惊人的苦功,或许兼而有之。但无论是苇草般的韧劲,还是晨露般的天才,都曾让我着迷不已。有一次聊到我当初课堂上写的那段小文,苏先生问,同样那个题目,现在让你扩写成一千字,能行吗?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问,迟疑地点点头。他接着问,五千字,能行吗?我说不确定,即便写了,恐怕也失其原貌。他再问,一万字呢?我说,何必拘泥原文呢,新写一篇就是了。这时身后传来春懿的声音,可以。他继续问,十万字呢?春懿咬牙点头。他最后问,七十万字,还行吗?春懿说,穷极一生,一定能行。我瞠目结舌。苏先生拍拍我俩的肩,说,小妮子适合传我衣钵。
那天之后,苏先生多配了把小观园的钥匙,交给春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给我,或许他觉得女孩子心细,给我怕遗失,或许他觉得我俩天天黏在一起,给一把就行。那段时间春懿常约我去小观园照相。小观园是苏先生亲自设计,集园林古典韵味之大成。最初我以为是女孩子爱美,想让我给她拍点古装照,还特意在网上搜了些教程。但很快就为自己的浅薄臆测而感到羞愧。相机几乎没有传到我手中的机会。她拍天拍地拍一草一木,比专业摄影师拍得还有感觉。她说她相信摄影是最接近时间本质的艺术。文学也能描述时间,但往往失之冗滥。而摄影能将飞瀑般流动坠落的时间定格为一瞬?最为简洁、最为准确、最为精当。有时候她在一滴露珠前都能蹲一早上,它因风滑落时才叹息一声将镜头移开。在她拍照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被遗忘了。那是一种玄妙的心境,好像从所有嗡嗡颤动着升起的尘埃中穿过,从天光及被一切事物反射的或明或暗的光线中逃逸。我喜欢拍照时的春懿,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喜欢默默站在一旁看春懿拍照的那个自己。直到有一天春懿说要拍我,我当时着实吃了一惊。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拍照。小时候去公园拍照,母亲总说“比个耶”“姿势再酷一点”“再笑一点……够了,再回去一点,这样不自然”,那种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能达到期待的煎熬感随着我长成少年逐渐变为厌憎甚至恐惧。高中时我逐渐发胖,额上开始冒痘,毕业照上那张脸让我介意至今。当时我婉拒春懿的借口很拙劣,好像是说有个藏族朋友跟我说,摄影会摄取人的灵魂。等我真正做好准备将灵魂完整地献给你的时候再拍,好吗?我那时显得非常郑重,像个想把贞洁保存到新婚之夜的古代少女。我以为她会嗤笑,但她竟然相信了,也很郑重地说好。等我们都准备好将灵魂交给彼此的时候,就拍一张合照。我半安慰半承诺地补了一句。
但后来我们都没时间拍照了。我们约好一起考F 大的古代文学硕士。苏先生也很鼓励,说只要过了初试,就能把我们推荐给他的同门师兄。预报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好,萌生退意,想换填一所省内的211 高校。春懿那天赶到我宿舍楼下跟我聊了两个小时。她握紧我的手说,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冲击顶峰,一起把老苏的学说发扬光大。我跨考都不怕,你一定要撑住。我默默苦笑,但还是下决心舍命陪君子,咬牙报了F 大。后来调剂的时候,苏先生说有把握让我留在上海。我舅也给我打了通电话,说他那边有个闲差,过时不候。春懿不理解我的选择,大吵一架,就此分手。毕业典礼时我们分别和苏先生合了影。我能感到春懿一直望着我,目光灼灼。但我一直背对着她。苏先生没责备我什么,只是显得很疲惫,像老龟般缓缓拍了拍我肩膀。
3
苏廷乾的研究方向是《红楼梦》作者之谜。
《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论断,是由胡适拍板。但弊窦也极其明显,诸如曹家宗谱并无曹雪芹此人,且曹寅号“雪樵”,其孙为避讳不可能叫“雪芹”云云,红学界已有系统而丰富的研究。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曹雪芹”三个字,只是作者的托名。甚至有一种显说,即《红楼梦》作者是明末清初人,而非康乾时人。现在曹氏的支持者已经将阵线退守至“《红楼梦》作者或许不是曹雪芹,但是曹氏后人”,而反对者则众口纷嚣,洪昇、冒辟疆、吴伟业、袁枚、顾景星等数十人皆有其拥趸。
苏廷乾无疑是反对者之一。但与所有人不一样的是,他并未选择皈依哪一尊神,而决意要做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造神。他二十八岁博士学成回到故乡苏镇,像个孩子一样呼喊着奔向列队欢迎他的镇民。前晚新下了雨,路面坑洼,他被一块凸石绊倒,将一坨泥吃进嘴里。镇长等人赶忙上前相扶,却看见他将泥巴一口咽下去。我们问过他泥巴是什么味道,他摇摇头说,太苦了,比世界上任何药都要苦。他看着骷髅一样枯瘪的乡亲,泪流不止,立志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他决定将《红楼梦》的作者定为生于明末的苏氏族人,北宋文豪苏轼的第十五代孙。因为难以稽考,暂且称为苏X。接下来便是虚构苏X 的生平。苏镇人,家业巨富(填充这部分细节时,他咬牙切齿地想到老镇长说的“我们这方水土养出来的都是穷命”),少时轻财结客,昌大门闾;中年始折节读书,举茂才而不就仕;晚年断发庐墓,出家为僧。与宝玉的命运轨迹基本吻合。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寻觅《红楼梦》与苏氏的联系。开篇讲神瑛侍者灌溉绛珠仙草于三生石畔,其本事正是出于苏轼的《僧园泽传》,且预示了宝玉出家为僧的最终命运。文中园泽投胎之母为王氏,正是王夫人。“白玉为堂金作马”暗含苏轼之号“玉堂”;“太虚幻境”取自其弟子秦观之字“太虚”,贾政书房名为“梦坡斋”,等等。再如苏氏昆仲于古苏镇界溪两岸建东、西二府,与宁、荣二府对应。以及苏X 于苏山之顶兴办苏山诗社,与海棠诗社对应;苏氏别墅二十八景,与大观园诸景布局相似云云,他搜罗、篡改甚至虚构史料,做着与近百年前胡适一脉相承的事。他做得如此滴水不漏,发表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苏镇地方志所隐藏的〈红楼梦〉创作信息》与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上的《“玉堂”与“梦坡”——〈红楼梦〉作者为苏氏后人的明显例证》等十余篇论文中有详细考述,此处不作赘论。
但即便如此,“苏X 说”也只能与“袁枚说”“顾景星说”沦为同侪,难以脱颖而出。就在他的研究因拿不出关键性证据而陷入僵局时,奇迹出现了,某天他步行去苏镇边缘的江郊散心,竟在江畔一间破庙中发现了一块奇石,上镌数十字,虽已被江风漫漶,但他清理过后,竟也能一一辨认:
坡顿首:昨日快哉亭与数客饮,至醉才归。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示客与共讽味。夜宿平山寺,月出诸壑,与众僧对坐冥然。
时元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也。
他对苏轼平生行迹了如指掌,石上所镌之字,应是苏轼元祐四年四月自黄州抵苏镇时所作。应是寺僧请赐墨宝,坡公兴至书于石上,寺僧便请工匠将笔墨锲刻入石。细察笔痕,当是真迹无疑。
他当即如米芾般向那奇石跪地三拜,心中澎湃:此为天意。天欲兴我苏镇。天欲降大任于我苏廷乾。
他于是继续铸造苏X 的形象:苏X 癖石如命,常以米颠自况,在众石中又最爱这一块。“质如奇璞,色如苍山,上有老坡题识觞咏之语。石之挺挺拔拔,如老坡独立于山林丘壑间,愈见其孤标雅致也”(苏X《苏山名胜集》)。他逐渐将这块石头视为神迹,视为先祖苏轼降下的庇佑,视为他借以撬通真实与虚构边界的支点。但最大的问题随即出现:石上所锲之文,如何与《红楼梦》产生深层关系呢?他已对自己先前那些捕风捉影的惯伎不屑一顾,认为它们配不上这段文字。他开始真正相信这六十个字是“一”,是本源,是宇宙学中的奇点,整本《红楼梦》都是在其基础上写成的。他找啊找啊,整个人仿佛经历了核裂变,散发出一种刺猬、迫击炮与风筝的奇美拉结合体的气质。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无疑已经失败了,颓废得像个隐士,在远离学术纷争的小学校教书,没有意外的话,会这样慢慢老成一块石头,就像他的绰号一样。是我们两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年轻人重新点燃了他的心火,他说。
4
毕业后,我到我舅当主管的八排楼艺术馆当售票员。其实票是免费的,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我就给打一张票,附赠展览手册与一张书签。艺术馆极小,二十分钟能逛个来回。展览作者基本都是本地的小艺术家,这个“小”不是指年龄,很少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基本都是须髯油腻、顶心寒凉的老家伙,但不出意外他们的画或书法一辈子进不去像样点的艺术馆。出于对平庸之人的天生亲近感,我本以为能跟他们成为朋友。但发现他们并不自认为庸人,并且只记得我是“那个卖票的小孩”,于是我继续过没有朋友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跟家里关系也很僵。我舅让我考个导游证,说能把我塞进四牛山景区,前途比这小破庙光明十倍。我觉得就这样挺好,我妈骂我就是个扶不上墙的刘禅,考不到证就不让我回去住。我干脆在艺术馆附近租了个北卧,一个月六百。主卧是对如胶似漆的小情侣,半夜起来冲洗下体的水声经常把我惊醒。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应该不会太差。他们基本不用厨房,外卖经常是牛排或炸鸡。次卧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儿,叫小真,长得有点像刘诗诗,高淳人,幼师一毕业就进了区幼儿园,下半年就能转正。有几次小朋友家长没来接,她拖到很迟才下班,就让我帮她收一下衣服。由此便有一搭没一搭聊起来。她看我每天端泡面去接水,叫我每月给她两百块,她每天晚上多煮一个人的饭。我说两百块够吃啥,她说你看着吧。次日起三菜一汤,有鱼有肉。我吃了一周,实在心中不安。说吃泡面是因为懒,其实我也有手艺,你一三五我二四六,周日包剪锤。其实我哪有什么手艺,只会蛋炒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好在她也不笑我,我借坡下驴说两百就当学费。她坚决不要,亲授之下,半年我也学到了五六成功力。我最初吃饭时爱刷手机,但她经常给我夹菜,我过意不去,也给她夹菜,后来就不看手机了。有时她笑着复述小朋友白天说的趣语,我摘出某句说这就是天然的诗啊。有时我给她讲某书法家高谈阔论时假发被风吹掉仍不自知的糗事,她笑得把脸闷在碗里,扬起来憋得粉扑扑,沾了满脸饭粒。有几次我不禁莞尔,伸手想用指甲帮她挑下来,又惊觉身份有碍,触电般缩手。她也明白过来,抱臂坐得笔直,饭粒还沾在脸上。我们对视一眼,终于憋不住会心大笑。那对情侣开门皱眉看了一眼,又砰一声将门关上。我们觉得解气,又笑了一阵。笑累后我们并排倚靠在窄小客厅里面朝阳台的沙发上,看对面高楼一格格的灯火和灯火里的小人儿。某些瞬间我恍然觉得我们就像是事事默契的贫贱夫妻,如果后半辈子这样过也实在不错。
春懿从上海回来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那天是周日,我包剪锤五局三胜,在床上赖到十点半还没起来。这时接到春懿电话,到你家门口了,开门。我脑中嗡嗡,但还是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去开门。她和本科时完全不一样了,鼻梁格外峭拔,嘴唇很红,挎包和高跟皮鞋都是一种我只在时装周视频里见过的亮银色。我当时有点被镇住了,就问,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问完就后悔了,这不是待客之道。她没答话,走进客厅,将另一只手提的一只硕大米色纸袋放到餐桌上。小真听到声响,从厨房出来,插不上话,看她一样样往外拿东西。联系到她的穿着和纸袋样式,某个瞬间我特别担心她一件件掏出金光灿烂或皮革油亮的奢侈品。但幸好没有。在餐桌上渐渐堆积成山的是一本本贴着图书馆条形码的专著和A4 纸论文。我瞟了几眼,都与《红楼梦》相关。我说回房间里找找茶叶,她跟了过来。小真都没进过我房间,那一刻我却没想过阻拦春懿。实在太乱了,她踮脚从没喝干净的可乐瓶、待洗的破洞袜子、睡黄的废弃枕头、缺胳膊少腿的老旧比基尼美少女手办与散发着喷嚏味或石楠花味的纸团中走过,看了我难忘的一眼,像在说:你已经堕落成这样了。茶叶没找到,我给她倒了杯水。她看都没看小真,也没说其他话,开始把那些论文简述给我听。很快我这些天在小真心里树立的一点文化人形象就全然崩塌了,在她渊博且严谨的叙述下,我常拽的那点小文全如泥丸坠地,连野狐禅都算不上。我想等她说完问问她近况如何,找到男朋友没有,反正就是找点话题寒暄,最后顺理成章问她此行的目的。但她一读完就开门见山,说她和老苏的研究已经到达最后关头,需要我的帮助。我苦笑指指太阳穴,说自己已经废了。她说不只需要我的大脑,还需要我的心。老苏最近总惦记着“那个臭小子”。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她担心他迟早要走火入魔。我有点担心,说,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还走火入魔。她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你想象不到的。我很想问个明白,但还是咬牙说,我早就跟你分手了,也早就从老苏手里毕业了。现在只是普通朋友,你们做什么事我不感兴趣,也与我无关。她有点急了,说,你不爱《红楼梦》了吗?我别过头说,不爱了。我不相信,她说。好像想要唤回我的记忆似的,她抓住我胳膊问,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讨论的问题吗,你爱宝钗还是爱黛玉?这时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冷酷者的角色,说,现在爱宝钗了。这时我看见春懿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层雾,她有种本领,可以让眼泪在眼眶一圈圈打转时慢慢蒸发,越积越少,无论如何都不让它掉下来。我拼命忍住想替她抹泪的冲动,冷声说,把这些装上,我送送你吧。春懿是普天下最绝俗的女子,但那天在楼下告别时她说了句最俗的话,我恨你。
5
你的放弃对他打击蛮大。你先不要内疚,听我说完你就知道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春懿将手轻轻搭在我的手上。
那段时间他对我表现出一种父亲对女儿般的依恋,提出想跟我去上海。我在F 大念书,他寄住在一个正在云游的物理学家朋友家里。我周末时会去那栋大房子跟他喝酒,互通研究进程。整座房子的中心是书柜,装满了那个因为在物理课堂上教授神秘学而被大学开除的物理学家的异端邪说。老苏读了那些书后,便如中了蛊般将他的学说升华到玄想的层级。他找到一个被称为“绝对时间”的概念。与牛顿的那个截然不同,他的“绝对时间”是根据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而设定的。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是某种客观独立存在的宇宙精神,而万物都是对其的模仿与演化。而在他的设想里,绝对时间概念也相仿:这是一种作为模板而呈现的时间,其后的无数时间都是对它的承袭。这种承袭是广义的,不一定是克隆体,也可能是后裔,或外貌毕肖,或行止相仿,或精神瓣香,总之存在某种或明晰或奥邃的神秘联系。他完全陷进去了。他觉得这门时间学说可以解释他毕生的研究。若仅此倒好,但那本书的后半部分不出意料地将触角伸入了神秘学的领域:只要通过某种方式将“绝对时间”记录或定格下来,就可以创造、衍生出无数以其为底本的时间。这种伟力极其强横,强横到足以篡改正在行进着的现实,能将一天变成数十年,将一瞬变成一生,但代价同样惊人,施术者的余生将被奉献给那段时间,成为那段时间的切身参与者。
后来怎么样了?老苏成功了吗?我忍不住问。
春懿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讲起了苏先生失踪的那个晚上:
那晚老苏在电话里像个孩子般央求我带一点酒去看他,说他要做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当时精神医生嘱咐他戒酒。我本想空手去,但被一种女欲养而亲不待的不安预感驱使,带了宿舍最贵的一瓶酒去找他。进门时我就发现苏先生与往日不同,显出一种回光返照般的精神矍铄。喝完最后一滴酒后,苏先生问我,你还记得咱们仨的起点吗?臭小子课上写的那篇小文章?你能背吗?我开始流泪。苏先生微笑着递给我纸巾。等流不出眼泪时,我开始背诵那篇你的涂鸦之作,就像当年我无数次向你们背《红楼梦》一样。
苏轼与张怀民等几位诗客来游快哉亭,时隔六载,风物依然。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溯回到元丰六年,人还是这几个,亭却是新造的,当日有记,“窗户湿青红”。现在已干透了,再一个六年,或许就被风削得黯然了。再一个六年,人还齐不齐都难以预想,遑论聚首于此,所做的只能是珍重一觞一咏。他们到亭时是巳时,便开始饮酒。饮的是泰州雪醅,系州治客次井的蟹黄雪水所酿。此酒味极清严,饮后酣醉而神思不倦。于是诸公乘兴讴咏,优游自得。及至未时,坡公将一直随身所携的三卷《易传》《尚书传》《论语说》示与诸客。苏洵晚年读《易》,欲作《易传》而终,驾鹤前将这桩伟事交给苏轼。坡公一生以辞章闻世,但真正呕心沥血的事业却是这三部专著,治经不仅是乃父遗志,更是其作为儒家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诸客翻阅讽诵,皆赞其发覆阐扬之功、醇厚雅正之志。畅论忘时,不知觉中已至晡时,诸公各自回返,坡公独行一程,发意去平山寺借宿,也好吃一吃寺里闻名的素斋。及到寺中,寺僧大半面生,坡公与住持法师对饮了一盏茶,便相对默坐。众山壁立,月出其中,松声廓然,陶陶入憩。
随着我的背诵,苏先生脸上的红光愈来愈盛。最后他几乎是和我一起背,当我结束,他的嘴唇依然在翕张。最开始像是喃喃自语,随即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像是呐喊。好像他不只是对自己说,对我说,对远在金陵的你说,还对所有人说,对世界说。
让我们回溯苏X 的一生,将其简化为最精练的事件,即:少年与客觞咏,中年在家治学,晚年出家为僧。最显而易见的是,苏X 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将自己的压缩、凝聚,揉成了贾宝玉的数十年时间。优游,治学,出家——这是命运轨迹的模仿。而更多细琐的模仿,我在论文中已然备述。这曾让我产生了某种既视感,但又模模糊糊,无法看清。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既视感来自何处。令人瞠目结舌的秘密是,苏X 的一生,其实是对苏轼元祐四年二月四日那一天时间的放大、伸长。这是最虔诚的模仿:坡公巳时与客优游觞咏;未时治学,讽味《易》《书》《论语》三传;晡时到寺用斋饭,与寺僧长坐到天明。这便是那段“绝对时间”。苏X 将其等比例放大为自己的一生,将六十个字化为六个时辰,再将六个时辰拉长为六十年。随后,他将自己的一生写入《红楼梦》。如此疯狂,如此庄重,如此宏伟。《红楼梦》这一宇宙般的旷世巨著,其剑坯是由苏X 纵身一跃投入炉中炼成的。我永远对这种悄无声息的伟大牺牲怀有至高尊敬。在种种事无巨细的篡构中,我好像已经与苏X 合为一体,天纵奇才,野心勃勃,呕心沥血,撰成奇书。这么多年我在文学院藏锋守拙,职称也停在副教授。但我一直知道,如果将这个成果抛出去,红学界将掀起轩然大波,恒星般的常识将被改写。今天是时候了。山呼海啸的时候。我用最颠覆、最戏谑、最令那些老学究不齿的方式完成了这项伟业。我终于解开了时间的秘谛。我与苏X 及贾宝玉的时间也将趋近直至重合。你知道他们命运的尽头是什么吧——消失在世人面前。
最后一句落下后,苏先生似乎带着某种宝玉的郁气,向整个世界与那些年高德劭的父辈们深深一拜,实则在大袖下嬉嬉然一笑。最后他向我挥了挥手,踏出一步,消失在空气中,就像宝玉与一僧一道隐没于白茫茫旷野。
听春懿说完,我心中实在难以沉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怆然还是欣慰。但苏先生确实是我心底最崇敬的那种人。另外,如果苏先生消失了,那短信是谁发的呢?这时春懿已经把相机在窗台摆好,然后少女般小跑过来与我站在一起,她亲昵地挽住我胳膊,将头柔顺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像在拍婚纱照一样。三二一,笑一个。我听到她温情脉脉的声音,像从许多年后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