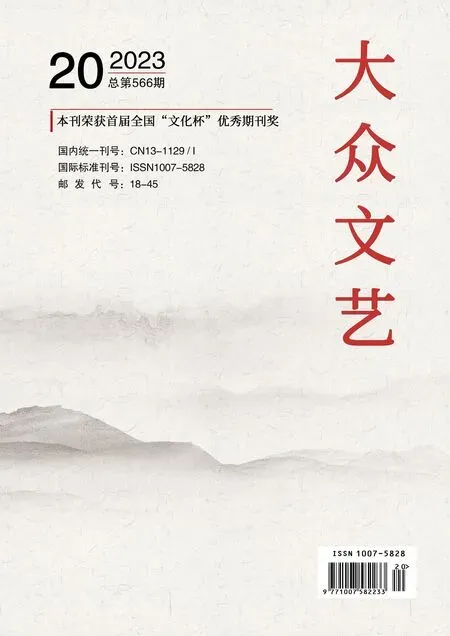概念史视角下的“民艺”涵义考察*
杜静文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1924年12月末,专注于研究民间工艺之美的柳宗悦和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一同将由不知名工匠所制作的日用工艺品命名为“民艺”。自第二年起,“民艺”正式作为工艺领域的术语出现在这些研究者们发表的文章里。1926年,他们三人与富本宪吉联名发表《日本民艺美术馆设立趣意书》,计划建立以研究、收集、保存和管理于一体的日本民艺博物馆设施,同时开展了影响广泛的民艺运动。时至今日,民艺已经成为日本设计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其相关理论中,以柳宗悦为主的研究者们传达出的语言概念与社会既存概念之间存在冲突又相辅相成,更牵涉出民众与学者、实用与审美、过去和现在的概念差异。因此对民艺的考察不能仅从表面掌握语言表现,更需要慎重考虑该词所表达出的内在涵义。
一、“民艺”的前世——下手物
在日本文献中,有些不同版本对“民艺”一词被创造时具体情形的描述。柳宗悦之子、日本著名工业设计师柳宗理在随笔中记载,“民艺”是柳宗悦和河井宽次郎、滨田庄司去高野山旅行时在旅宿里想出来的①。《日本民艺馆》一书中写道“三人一起乘车去三重县的津市寻访木喰佛像时,想到用‘民众性工艺’来称呼他们的收藏品,取其简称就成了‘民艺’这一新词。”②也有一说是三人去纪州旅行的时候在车中讨论出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民艺”一词的创造背景是一行人进行木喰佛的考察。这一考察过程使柳宗悦逐渐意识到造物中存在的民众特色,以及因贴近土地生活而产生的对工艺品的热爱。柳宗悦对木喰佛像的研究成为他思考并创造出“民艺”一词的契机。
另一个契机则是1924年柳宗悦一家受关东大地震影响迁居京都。他们在京都共生活了9年的时间,之后在1933年回到东京。纵观整个民艺运动的进程,住在京都的日子是柳宗悦发起并推进这项活动的重要时期,他在这里获得了许多与民艺运动相关的人脉。同时京都地区保留着大量传统工艺,为柳宗悦做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柳宗悦对民艺的兴趣可以说是从李朝陶瓷开始的。早在1914年,柳宗悦就对朝鲜的李朝陶瓷器密切关注,认为李朝陶瓷的美学价值是在此之前没有得到认可的。为此他特意前往朝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研究。在从朝鲜去往中国时,柳宗悦见到了当时在北京的英国陶艺家伯纳德•里奇③。里奇的制陶更加深了他对于工艺的认识。1920年里奇在日本结识了滨田庄司,并与他一同回到英国创建了“里奇陶瓷”。1924年滨田回到日本,住在同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在的东京工业大学)的学长河井宽次郎家中。这三人在之后民艺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迁居京都后,柳宗悦与滨田、河井二人结缘,并一同到各地对民间工艺进行考察。
柳宗悦居住在京都的时候正是他开始追求杂器之美的时期,同时因为被木喰佛④所吸引,前往日本各地进行了考察调研。河井宽次郎与柳宗悦接触后,也被他发现的木喰佛之美所感动。二人为了研究木喰佛在日本各地走动。在此期间,他们看到了集市上的“下手物”。“下手物”的叫法来自市场上的卖家,被柳宗悦所沿用,并在自己的很多文章论述中都表现出了对这一词语的喜爱和留恋。在《京都的朝市》一文中柳宗悦这样写道:“‘下手’指相当普通的廉价物品的性质,对应民器和杂器⑤这两个词。也许我们是第一个用文字写下这个俚语并描述它的人。”⑥
柳宗悦很喜欢“下手物”这一词,认为它有趣、自由、朴素。但作为俚语,“下手物”本身在传播时就十分容易产生歧义——事实上随着它在民间的广泛使用,确实被用来指代“被抛弃、被讨厌的东西”或是“粗货、低级趣味的东西”。因此当柳宗悦等人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表达吸引自己的这些物品的魅力时,势必要创造出新的术语。“民艺”一词的诞生使得在此之前各种已有但模糊、不全甚至错误的界定得到明确。虽然在此之后,如柳宗悦、河井宽次郎等人于1927年前后刊行的《杂器之美》中采用了不少“下手物”和“杂器”的表达,但可都被看作是“民艺”的同义词⑦。对民艺研究的限定和扩展都变得清晰起来。
二、领域分化和术语矛盾
以将原本的下手物命名为“民艺”为界线,此后柳宗悦对“美术”或“艺术”这些词语的使用也发生变化。例如在描述朝鲜陶瓷时,用词就从“朝鲜的美术(艺术)”置换成为“朝鲜的工艺(民艺)”⑧,甚至在以新的民艺概念为主体的工艺论体系中,出现了将“美术”作为工艺的对立概念的情况。
“民艺”作为目前日语中的专有名词,通常被认为是“民众的工艺”的缩略语。“‘民’是指‘民众’,‘艺’是指‘工艺’,因此作为‘民众的工艺’的简称,选择了‘民艺’两个字。也可以理解为‘民众艺术’,但说到艺术,就会让人联想到高级的个人美术等等,所以(选择‘民众的工艺’这样的表述)意为暗示这是无名的工人们制作的实用工艺品。”⑨可见柳宗悦等人在创造这一词语的时候,希望能以此与贵族的工艺美术区别开。这样的造词意图似乎也预示了在“民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工艺美术”以及各类工艺领域的术语产生冲突。
民艺理论提出后不久,也就是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10年间,日本工艺领域进入了“工艺分化的时期”⑩,被视为美术分野追求审美形式的“工艺美术”、以机械化和大批量生产为目标的“产业工艺”以及新生的“民艺”陆续登场。其中“工艺美术”作为上等工艺品的生产领域,其人员构成是以工艺生产第一线的东京美术学校的教师们为中心,所以在分化初期就成了工艺领域的关键性存在。
对此柳宗悦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将工艺分为“民艺(民众的工艺)”和“美艺(美术的工艺)”,并指出美术工艺容易陷入过于注重审美而轻视实用性的倾向中,这就打破了工艺所遵循的原则(在这一语境下,“美术的工艺”与美术工艺可看作同义)。因此柳宗悦认为“民艺”才应该是“工艺”的主流。他在对工艺的研究中尝试着将民艺定位为工艺的主导,将长期模糊的工艺领域以民艺为中心进行重新构建。当然,这一尝试与在东京美术大学担任工艺教师的工艺家们“将工艺定义为美术(工艺美术)”的看法截然相反。因此在民艺领域的确立时期,民艺在工艺的主流探讨中遭受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柳宗悦以“民艺”为基础的工艺观太过狭窄,同时指出“上手物”才符合当时日本的社会认知——那些精致的高级工艺品推动着国家的工艺生产,给国家提供了切实的振兴作用,因此工艺美术家们相比于民艺家也处于优越地位(11)。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另一个矛盾,就是“工艺”和“美术”。自明治以后,“美术”这一概念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被引入,如何划分其与“工艺”的界限就成为不断被讨论的话题。在明治时期,“工艺”指的是所有制造业的集合,等同于工业和手工业。而在日本逐渐接受西方艺术史观的过程中,“工业”领域逐渐独立,“工艺”慢慢被定义为介于“工业”和“美术”之间的领域,却又与另外两者间有隐约重叠。因此人们普遍会认为“工艺”一词本身就包含了“用”与“美”两个部分。但民艺理论或者说柳宗悦心目中的工艺观是将工艺与美术完全区别开来的,如果说“美术”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产物,那么“工艺”就是“以自然为中心”的产物——这里的“自然”指的是生产者在大地上切实进行着的生活。因此“工艺是指实用品的世界,这一点与美术完全不同。绘画是为了看而画的美术品,而和服、桌子则是工艺品,是为了使用而制作的。”(12)不可否认“工艺”也是存在“美”的,但这种美必须伴随着实用性才会出现,或者说“工艺之美”就是实用之美。柳宗悦在他的文章里也不止一次地指明了“为使用而制作的是工艺,为欣赏而制作的则是美术”这一界线。可以看出,不论是作为工艺领域的一部分还是对“民艺”本身,民艺家们始终在保持这种维护自身主体的意识。长期的民艺研究中,这种对概念界定的探讨并不在少数。柳宗悦等人提出新主张的同时必然要与一些原有概念和理论进行区分或对它们展开批判,这也有助于“民艺”确定自身的有用性和创新性。
三、“民艺”“民俗”之争
1940年柳宗悦与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进行了一次谈话,刊登在《月刊民艺》同年3月的杂志中。彼时民艺运动家们正努力通过协团的形式来倡导民艺这种“即将到来的艺术”。从民俗学的角度,“即将到来”这种的想法并不被柳田国男所接受,他认为“民俗学是一门正确解释过去历史的学问,因此将来的事情不在我们学问的范畴里。”(13)在这次谈话中柳宗悦主要表达了自己的工作与民俗学的区别,但之后二人并没有在那次谈话中达成学术共识。第二年柳宗悦发表了一篇名为《民艺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再次表达出自己与民俗学的立场是不同的,并批评民俗学“并不能为民族文化打下深厚的基础”(14)。
之所以“民艺”和“民俗”被频频混为一谈,是因为在“民艺”被提起的同时,日本民俗学家也在收集民间用品,这一点与民艺的研究方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在日本现今对民艺研究的分类中,有大量文献被归类为“民俗学”。关于“民艺”与“民俗”的区别,或者说为何抛开“民俗”一词而创建“民艺”,柳宗悦的解释是,民俗学毫无分别地收集民间用品,其目的在于保存和调查历史资料;而民艺研究中严格挑选收集的民艺品既是生活里的实用品,也是能作为工艺样板的美术品。他认为民俗是向后的学问,而民艺则是向前的运动(15)。
但在柳田国男的研究中民俗被分为三种形态:有形生活、语言艺术和精神现象,即研究生活的样貌、生活的解说和生活的意识,从这三个分类阐述了对生活文化从物到心、从外在到内在的把握,最终实现对乡土研究的价值。从柳田国男的分类来看,民艺可以归属为有形的物质文化。然而从民艺研究者的角度,尤其是柳宗悦的眼中,民艺与民俗在学术范畴和研究方法上的关系值得仔细辨析。
在针对日本的传统和民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词也会常常被和“民艺”“民俗”一同提起,就是“民具”。“民具”同样是一个新词,它的提出者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孙子涩泽敬三。“民具”被定义为普通百姓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制作和使用的传承性器具和造型物的总称。相比“民艺”,“民具”研究与民俗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会以“民俗——民具——民艺”的关联方式来进行说明。因此也可以看出,在一部分研究中,民艺也会被归类为民具的一部分。从民具研究的角度,民艺以欣赏为前提,“在民具中,对适合鉴赏的物品进行取舍选择,称之为民艺品。最近喜爱者都在赏玩,最后(民艺品)只不过成为玩物。民具则不然,不问其物的美丑与新旧,也不问其健康与否,凡生活必需之品,皆以此为民具。”(16)
有趣的是,在日本研究中,从以柳田国男、涩泽敬三、柳宗悦三者为代表的不同立场和视角出发,他们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分别被称之为“民俗学”“民具研究”和“民艺运动”(17)。民具研究在学者田边悟的笔下曾被作为“民具学”提及,柳宗悦也曾撰文《民艺学概论》将民艺作为一门学问介绍出来。当与思想语境结合时,“民俗”和“民具”虽然包含“民艺”的性质,却与“运动”一词并不相符,民艺运动不论从方式还是宗旨上都与其他日本传统文化研究活动有着明显区别。
从语言发展的具体轨迹来看,柳宗悦早年从事宗教哲学方面的学习,后转而研究陶瓷器,在他的知识体系下构建起的是“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相统一的美学目标。他希望能够在研究中获得认识真正的美的能力,并凭借这种美的直觉发现民艺的价值。这也证明了“民艺”本身存在与“民俗”及“民具”完全不同的研究意义。
四、从西化的思想到“mingei”
西方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思潮传入日本时,柳宗悦、富本宪吉、滨田庄司等人都学习了西方全新的工艺思想体系,这对之后的民艺运动以及日本各地的产业振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威廉•莫里斯和约翰•拉斯金发起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经常被和“民艺运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在时间上,“工艺美术运动”发生在“民艺运动”之前,前者通常被看作后者的示范和先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风潮开始进入日本,相关作品被翻译和介绍到各个领域。民艺理论创立之时正值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在日本流行,仅柳宗悦本人就在超过百篇文章中对二人有所提及,其他如富本宪吉、河井宽次郎、滨田庄司等在民艺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学者也对此颇有研究。但这就导致“民艺”所宣扬的独创性受到质疑——富本宪吉等人在一些表述中被称为“Morrisian”,或者直接指出民艺理论是莫里斯和拉斯金的派生物。
然而对于民艺家们来说,民艺有其独特的使命,即以发现日本文化的个性为出发点,加深对日本美学的探究。从《日本民艺美术馆设立趣意书》中可以看出,其实一开始柳宗悦等人就意识到民艺需要的不是模仿他国,而在于展示独特的日本和民族价值,甚至有意表明民艺运动绝不是威廉•莫里斯等人发起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效仿。在学习的基础上柳宗悦还对莫里斯和拉斯金提出批判,认为莫里斯的身份更像是“美术家”或是“个人工艺家”,缺乏和民众的交流;拉斯金的艺术构想则是乌托邦,只追求世界的美术化而忽略了工艺美,因此他们对美的想象是无法实现的。(18)同时,这些出身于日本上流社会家庭的学者们自幼就读于贵族学校,求学经历完全处在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动荡之中,因此从他们的思想中不难看出其自身社会背景、当时日本社会文化与知识分子们试图在被西化倾轧的环境中寻找民族文化认同的复杂斗争。不可否认莫里斯“在生活中发现美术工艺品并加以使用”的想法在民艺运动中有所体现,但最终民艺还是在一种“东方视角”下发起和推进的。
确立“民艺”概念独创性的意图在其英译方式上同样有所表现。民艺的创造者们在对词语进行翻译时刻意避开“Folk Art”,而选择用“Folk Craft(19)”来作为“民艺”的官方英文表达,这种英语表达其实也是他们造词的一部分(20)。在张道一先生于1988年写作的《中国民艺学发想》(21)一文中,开篇便谈到日本“民艺”:“现代日本的辞书中常把‘民艺’作为‘民众工艺’(Folk art)的略称,或称作‘民间工艺’(Folk craft)、‘民间手工艺’(Folk handicraft)。”这样的用法与柳宗悦对“民艺”的辨析并不相符,可见在当时日本对这一概念的表述是存在差池的。
1972年,伯纳德•里奇翻译了著作《The Unknown Craftsman》介绍柳宗悦和他的民艺思想,在英国受到好评。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这本书又相继被翻译成法语和德语。这段时间里,《牛津英语大词典》立项将“民艺”以“mingei(民艺在日语中的字母音标)”的拼写方法作为名词收录。这一用法的出现也为针对“民艺”的英文研究指出了更规范的表达方式,以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创新的主体。这种表达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概念内涵在意译的传输和理解过程中可能或必然发生的变化,在日本甚至东方长期追随西方的设计解释权下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主动性。
结语
在对“民艺”进行命名时,学者们还曾考虑过“地方工艺”,但最终选择“民众的工艺”这样的含义,又不同于“民众工艺”,旨在思考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朴素的造物美学。在实际进行的民艺运动和研究中,“民艺”一词的含义并没有像创造者们期待的那样始终保持起到最精准的表达作用。当这两个字风行之后,日本各地都陆续出现民艺料理、民艺茶会、民艺家具等各种被冠上“民艺”二字的东西,这种情况使民众对于民艺的认知逐渐产生偏差,加上当时很多民艺店铺中所出售的并不是来自生活里的物品,甚至把收藏品当作民艺品来销售,使民艺氛围变得似是而非。柳宗悦本人在民艺热潮高涨之时也表达过对此的担忧,认为民艺趣味如果变了味就会背离初衷。因此民艺必须永远保持其独立性,从变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展现其真正的价值。
注释:
①[日]柳宗理.柳宗理隨筆[M].蘇文淑,葉韋利,王筱玲譯.大鴻藝術,2015:231.
②[日]坂田和实,尾久彰三,山口信博.日本民艺馆[M].徐元科译.新星出版社,2017.1:83.
③伯纳德•里奇(Bernard Leach,1887~1979),英国艺术家、陶瓷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受到日本陶艺的影响。译有柳宗悦所著《The Unknown Craftsman》等书。
④木喰佛,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由木喰上人用巨木雕刻的木制佛像。木喰上人(1718—1810)出生于甲斐国(现日本山梨县),其在日本修行期间在各地留下了很多佛像。目前残存的约260尊木喰佛像大部分出于新潟县,成了当地人心灵的依靠。
⑤“民器”和“杂器”在民艺研究的概念里都是指大量制作的、到处可见的、能够便宜买到的、任何地方都有的物品。它们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日用品。有时也被称为“杂具”。
⑥[日]柳宗悦.蒐集物語[M].中公文庫,1989:111.
⑦郑巨欣.日本现代设计的近代学术渊源——以日文著作为例的书物学视角[J].艺术设计研究,2021(04):35-43.
⑧[日]白土慎太郎.越境する「工芸」——日本民藝館のコレクションと柳宗悦の工芸観[J].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11:20.
⑨[日]柳宗悦.全集第16巻[M]:182.
⑩[日]田境志保.工芸美術―現代性への試み[A].長田謙一,樋田豊郎,森仁史.近代日本デザイン史[C].美学出版,2006:208.
(11)[日]杉田禾堂.柳宗悦氏に[J].アトリエ,1930,7:95-97.
(12)[日]柳宗悦.全集第8巻[M]:209.
(13)[日]池田敏雄.民芸手帖[M].東京民芸協会,1980,0120:6.
(14)[日]柳宗悦.全集第9巻[M]:272.
(15)[日]坂田和实,尾久彰三,山口信博.日本民艺馆[M].徐元科译.新星出版社,2017.1:62.
(16)[日]染木煦.北満民具採訪手記[J].1986.
(17)[日]佐野賢治.“民”の発見: 民具·民芸から民俗まで[J].人類学研究所研究論集,2015,2:3-12.
(18)[日]柳宗悦.工藝の道[M].講談社学術文庫,2005:207.
(19)很多研究日本“民艺”的英文文献中也会使用“Japanese Folk Craft”的表述,以使其区别于英语里的“民间工艺”。
(20)同⑩.
(21)张道一.中国民艺学发想[J].中国民艺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