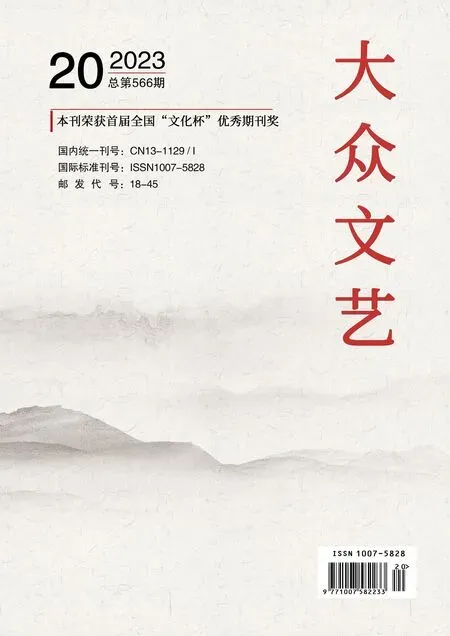解读莫兰迪绘画背后的中国文人画元素
江乐清
(天津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天津 300143)
一、时代更迭下的思想意识变革与个人选择
著名画家巴尔蒂斯曾经说过:“莫兰迪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艺术家了”。[1]莫兰迪的绘画与我国文人画是在两个不同地域文化演变下所诞生的,但在精神追求上以及在人生态度上颇有相通的地方。这一方面源自相似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上的变革,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文人画的发展与文人阶级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由于社会环境的动乱使得大批文人选择逃避现实、远离政治,其次随着儒道佛哲学思想的盛行促成了一个在精神思想趋于开放自由的氛围,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很早就显露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在个人思想意识上的自由开拓性。然而在西方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包容性直到文艺复兴的爆发才逐渐出现,力图突破宗教和王权的束缚回归到人本体的关注上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莫兰迪的绘画出现会晚于中国文人画这么久才出现。另一方面是艺术家个人的世界观所衍生的孤隐的人生态度和脱俗的生活方式上的接近,莫兰迪身上的那种先天谦逊、内敛的性格加上他对自然平凡事物的热爱以及长期以来善于自我内心的观照,或许还由于他的某种信仰以至于他选择远离社会和世俗文化的生活方式从而归隐自然。在我国文人士大夫们十分推崇且向往这种避世归隐的理想生活,在某些朝代更是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和一种高尚人格的象征,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驱使文人知识分子催生出消极遁世的念头,他们将思想寄托于老庄哲学,将老庄哲学思想所提倡的清静无为、崇尚自然作为自己心灵净化的有效途径。[2]那么避世归隐也就成为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的文人士大夫的不二之选。因此我们能发现一是在关于个人独立思想价值的觉悟,二是在选择孤身隐退这条窄路的选择上,这两方面莫兰迪和中国文人画家不谋而合。
展开来说,就引发思想意识变革的历史环境来看,莫兰迪是生于19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这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工业化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带来科技大发展、工业化生产的洪潮中,有的人渴望新时代带来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有人对这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感到迷茫和质疑,它打破了以往平静缓和的思绪,人们迫切在意识上产生突变。如此汹涌的变革所带来的意识转换率先在对社会动向极为敏感的艺术家们身上凸显出来,这催生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现代主义思想是对传统思想理念的反思与创新,不再对传统艺术中文学叙事性和情节性的关注,抒发艺术个性和表现时代的巨变是主流。因此莫兰迪也就是生活在这样格外热闹多样的艺术时代,但莫兰迪并没有盲从这个时代艺术的多样与活跃,他的艺术与现代主义时期西方的主流艺术有所联系又保持相对的距离,更多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自决,潜心地创造自己独特的个性价值。他的这种独特性首先是由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所带来的对主观精神以及艺术形式方面的关注,开启了对绘画形式上的探索和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超越了再现的自由开拓,这给予莫兰迪发掘自我独特艺术价值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艺术环境。其次源自他低调和内敛的性格以及不慕世俗名利的处世态度,这使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绘画的独立探索中去。这与中国文人绘画的出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文人画的诞生同样是与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以及文人士大夫们的脱俗隐逸的风尚有着直接的作用。文人画并非画匠画也不是职位画家所画,而是一群有思想、意在明心的文人士大夫所作,文人阶级自古一直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所相应的变化。早期文人士大夫大都世代为官且文化修养很高,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主要分布在贵族和仕宦阶级,往后随着隋朝科举制推出后逐渐从仕宦阶级中分化出来,科举出身的文人逐渐代替了世代为官模式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主体。在朝代的更迭中所出现一系列的政治动乱以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禅宗的一些超凡脱俗思想的盛行,自此由于社会的动乱以及对此的无能为力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在对家国政事上逐渐灰心丧志,从而转而将重心聚焦到自己内心心灵的净化与安止,到元代时期蒙古族的统治以及明代的政治黑暗时期这种文人隐逸的文化潮流逐渐达到顶峰。另一方面老庄哲学思想以及禅宗脱俗思想对于文学艺术上的介入,他们选择远离世俗喧嚣归隐山林并通过诗书绘画创作的形式将精神思想寄托于对自然物象,从而寻求内心世界的理想精神家园。[2]这种由于历史的剧变所带来的抨击从而在精神思想上率先进行主观变革在莫兰迪和中国文人士大夫身上都能凸显出来。
从艺术家的人生态度以及处世方式的角度来看,陈英德在《莫兰迪》中说道:“莫兰迪的一生未婚,长年居住在博洛尼亚,唯一的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看塞尚的画展,一生都过着近于修士般的孤隐生活,简单而有序。”[3]他的家极其简朴平凡,没有奢华的家具和琳琅满目的日用品,也没有色彩绚丽的饰品和衣物,画室只有不足十平方米大小,里面布满了陪伴他终身的瓶瓶罐罐,旁边就是平日里所用的画架,透过窗户能看到时常出现在他风景作品中的田园一角,如此的生活环境显得格外的朴实淡雅,透露出莫兰迪安逸淡然的生活状态。平日里他少有与别人社交往来,也少有参加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即使在他绘画逐渐走向成熟且在艺术上享有一定知名度之时也未陷入名与利的追求,甚至十分抵触名利带来的困扰,他不希望越来越大的声誉打破他原本简朴安静的生活状态,更不希望搅乱他对艺术的纯粹,就如莫兰迪自己所言:“我需要的是对我的创作所必需的平静与安宁。”[1]他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对艺术的那种真诚态度以及对归化自然的向往。莫兰迪的这种不慕世事功名利禄的处世态度和简单朴素的生活状态透露出一种中国文人般的归隐情结,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是一种自适的精神极致,他们的避世隐逸是一种孤寂状态的选择,远离外界的热闹喧嚣与世俗琐事,向往悠然自得的孤寂之境,通过投身于自然用简朴和淡泊之心去体味物象和宇宙,完善自我的人格达到与自然共通,天人合一的境界。莫兰迪虽生活在艺术氛围极其活跃的年代但他并未如同其他艺术家一样怀有立志于在艺术能够扬名立万的野心,他远离外界喧嚣与浮躁,与形式主义的浮夸保持距离,一直在通过绘画的方式去找寻内心的大千世界,无惧于外界的不理解与批评,潜心发掘透过平凡物象背后的精神价值从而达到忠于内心的真实,无声但有力地传达了“真”胜了“美”和“理想”。
二、“物与我”上的艺术观
莫兰迪的艺术观与现代主义时期盛行的艺术观念有所关联又有所差异,忠于内心才是他真正的艺术主题。莫兰迪曾在刊物《突击》上谈道:“我像那些有思想的年轻人,感到有完全改变意大利艺术环境的必要,但是我意识到那种新的美学观念比旧的更不能适应我精神上的追求。”[1]现代主义盛行之时西方涌现出众多风格各异的艺术流派,莫兰迪没有盲目跟从这些流派的创新主张和精神鼓动,而是对其主观的明辨。接纳并学习那些对他艺术追求上有真正指导意义的艺术观念比如塞尚在绘画空间所给予的启发以及形而上画派在超越现实图像的精神引导,同时也与那些轻浮、造作妄图用艺术改造生活的艺术思潮保持距离。由于莫兰迪对多变的艺术思潮所具有敏感的洞察力以及自身绘画观念的独特性,莫兰迪才能够在追求自己独特艺术价值的路上走得远、走得深。这种独特性在于他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主义画家陷于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巨变中的急于创新,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对平凡物象的静观之中,通过对于身边日常普通的静物和风景的静观描绘来寄托精神追求。随着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艺术表达从以往注重客观对象的表现向注重主观性、精神性的表达,开启了艺术上的两种趋势,一是以塞尚为代表对于理性精神地注重,二是以凡•高为代表对于精神性情感的表现。笔者认为这两种趋势在艺术家创作理念上,并非极端独立的存在,而是作为思维表达的一个坐标的两端,艺术家的表达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坐标点,可能理性部分大于感性部分也或许感性部分大于理性部分,这取决于艺术家的创作动机,这种动机也自然来源于艺术家个人的艺术观。莫兰迪创作中的感性是面对物象主观情感的抒发,而理性情感则是源于对自然物象的观察态度,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找到一个与内心表达相吻合的平衡点。用一种超凡脱俗价值判断的心灵和面对自然物象的主客体融合的态度去发掘体会社会与自然的精神感悟,这里有多个方面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有着相通之处。
首先,他们在追求个人艺术观念的方式上不谋而合,都将寄景于情、托物言志作为抒发某种形而上精神的方式,借自然物象来显现自我心灵。宋代郭若虚曾言:“画乃心印,文人画以作者人格精神为标榜,形只是一个表象,重要的是内心情感的抒发与表现,托物言志于绘画,抒发个人胸中逸气”。[4]文人画区别于匠人画和宫廷画体现在他们有深厚的情感和文化素养,将内心的情感寄托于绘画之中。莫兰迪的绘画虽与中国画的媒介不一样,但同样注重作品中情感的置入,强调主观感受和情绪的表达。莫兰迪不满传统绘画观念中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被动关系,那种将生命置身于冷漠且毫无生气的注视之下的绘画模式,也不满于部分现代主义时期西方流行的矫饰、浮华的绘画,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表现形式与自我精神性关联的重要性,莫兰迪绘画中的大面积的留白背景以及整体灰颜色的布局透露出一种含蓄、从容的感受。在笔者看来有一点不一样的是莫兰迪更多的是一种向内的力量,一种含蓄的情感抒发,他将很大一部分主观精力放在赋予物象的形而上精神上。而中国文人画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外放的情感表现,在个人主观情感的释放较莫兰迪来说更为强烈,尤其在元代以后更为明显,当然其中也不乏如莫兰迪那样情绪内向力的表现如北宋时期的文人画家范宽。但总的来说在借物象传达精神情感方面他们是一致的,正如清代文人画家郑板桥所提出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过程,体现了在借物抒情这方面莫兰迪的绘画与中国文人画有着殊途同归之处。
其次,莫兰迪的绘画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在对真实挖掘的路上发现大千世界的本质,这是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他如苦行僧一般在这条路上苦苦修炼,这显露出一种中国文化的品格。北宋思想家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天地立心是为人的基本,强调的是用精神力量即内心去认清客观世界即天地的本质和规律。上面谈到,中国文人的退隐山林以及莫兰迪的足不出户是一种脱俗避世回归自然本源的选择,在认清客观世界的本质前他们首先完成对自我的脱俗即一种出世态度的选择,消除任何现实中的束缚与界限并排除功利的思想从而达到内心的宁静、纯洁、无为和真诚。莫兰迪常年在狭小的画室对着排布缜密的瓶罐进行静观创作,以一种虔诚、尊重的态度与所看到的物象交流,摒弃一切世俗的惯性思维和社会文化意识介入的束缚,力图达到纯粹、无为的初心。《论语》中提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意为为士就要将精神生命即心放在首位,把世俗物质追求放其次,不然即为口头说说都是虚言,中国文人士大夫历来追求修心修身,修的就是不被世俗功名利禄所迷惑,一颗纯洁至简的心。心灵上的净化才能纯粹的介入对于大千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注视中。
莫兰迪的绘画和中国文人画都是在主客体之间达到一种相对适应的平衡,强调物我上的相通。在创作者的角度需达到心灵上的净化,同时对客体观察方面同样要达到与其相得益彰,莫兰迪并非如传统西方风景静物画一样将主客体对立的分开,而是对物象以一种平视的姿态并注重它作为物本身的存在价值,强调尊重自然物象并将其作为组成自然宇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来与其对话,才能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物象的真实和本质。在我国唐代时期画家张璪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在《历代名画记》中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即是大自然,心源就是艺术家的心中所悟,先要做到师法于自然才能达其所悟,那么物与我的关系并非毫无生气的主被动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联关系。莫兰迪对自然的态度上透露出老庄哲学思想,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于自然的态度上采取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要与自然合为一体,顺应自然胜于人工造作。”[5]在莫兰迪的静物画中能感受到每个瓶罐都有自己的性格,与其说是一幅静物画不如说是一组瓶罐的合影更为贴切,就如莫兰迪所言:“一个人可以环游世界但却无视一切,了解不在于要看很多东西,而是要认真地去看你所看到的一切。”清代文人画家石涛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美学观点,强调要通过对自然物象的多方面的细致观察,体验分析来把握物象的精神,才能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在对于自然本质探寻的路上莫兰迪和中国文人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真实以及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纯洁的坚定态度。
结语
莫兰迪的绘画与中国文人画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这并非某种意义上的巧合,都是有迹可循,笔者主要从对创作主体分析来挖掘这种相通之处背后的诸多迹象。社会的动乱引发的思想意识上的变革是首要因素,面对混沌的社会局面莫兰迪和中国文人都选择避世归隐从而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对世界的凝思。在艺术创作观念上,莫兰迪有着中国文人一样的反俗倾向,秉承着创作上的真诚与纯粹的精神,将绘画作为与心灵交流的媒介,表现出一种体现自然本质的平和之境。莫兰迪虽是在西方的体系中,但他与中国的接近是显而易见的。十几年如一日地与瓶瓶罐罐厮守,他终其一生力图通过极为普通的事物发掘隐藏其背后形而上的精神。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