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
陆春祥
癸卯夏至凌晨,突然被一阵激烈的鸟声吵醒,窗外还是灰灰的,不过,我没有怪鸟们,富春庄里的这些群鸟,就是好动喜鸣,似乎一刻也静不下来。
据鸟們在庄里的生活规律,我将这些鸟群大致分成几个行动小队。
麻雀队,规模最大,常常是十数只几十只,好几群,霍地一声,从红花继木,突然钻到围墙边的桂花树间,或者从高大的雪松枝条上直飞进池塘边的樟树里,那樟树也有些年纪,树高叶茂,枝虬乱伸,麻雀们喜欢开玩笑,钻进密密的树枝间,有个一两分钟,不发声,你想找它们的身影,无影无踪。有一天,我和瑞瑞仔细观察后,找到了原因,它们将自己变成了树叶,难怪看不见。
麻雀们还喜欢一两个单兵活动。伫立A楼二楼的阳台,盯着前面D楼文学课堂的后门看,有一只麻雀,个头极小,小到似乎有点似蜂鸟的形状,它从盆栽红梅树枝顶飞到草地上,两米高的空中,它是螺旋而下的,翅膀如直升机启动时那样快速地转动,好不容易停泊到草地上,刚跳了几步,另一个伙伴,霍地飞来,与它一起觅食,几分钟后,双双飞往另一边的一株红枫上,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一对,不过,实在辨不出来。
普通翠鸟队。个头与麻雀差不了多少,头背深蓝,胸及下体橙黄,数量也多,富春庄前的田野中,有两口半亩水塘,想必是它们常觅食的地方。它们成群从富春庄里进出,叫声嘀嘀嘀,连续发声,不过它们在庄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家燕队。上体深蓝色,胸有点偏红,腹白,尾分叉,它们喜欢黄昏时分,成群聚集在文学课堂前杜仲林边的枝干上。富春庄的建筑基本都是徽式,白墙,有屋檐,但不像农村泥房那样,容易筑窝。去年冬天,我在庄中前前后后观察,终于看到三个小鸟窝,但肯定不是家燕们的,家燕筑窝喜欢衔泥,那窝只是树枝间的普通草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家燕在富春庄的屋檐下筑窝。
乌鸫队。三四只,五六只,小规模,鸣声清脆响亮,无论颜色或者声音,辨别度都特别高,杭州小区里乌鸫特别多,我也写过不少,不多说。只是,富春庄大小只有五幢建筑,与城市中密集的小区还是有区别的,在这里,它们往往从高大的杜仲林上俯冲过来,在我的书房窗口鸣叫几声,就转身飞过文学课堂的屋顶,直接扑向更深更密的山中去了。
喜鹊队。一般人都喜欢听喜鹊的叫声,即便没什么喜事,心理上总是能得到安慰。我走运河的时候,常常听到喜鹊叫,我以为喜鹊喜欢水。富春庄里也常有喜鹊光顾,它们来的时候,成双成对,也是热闹的,切切切,切切切,高调得很,似乎要向我宣布什么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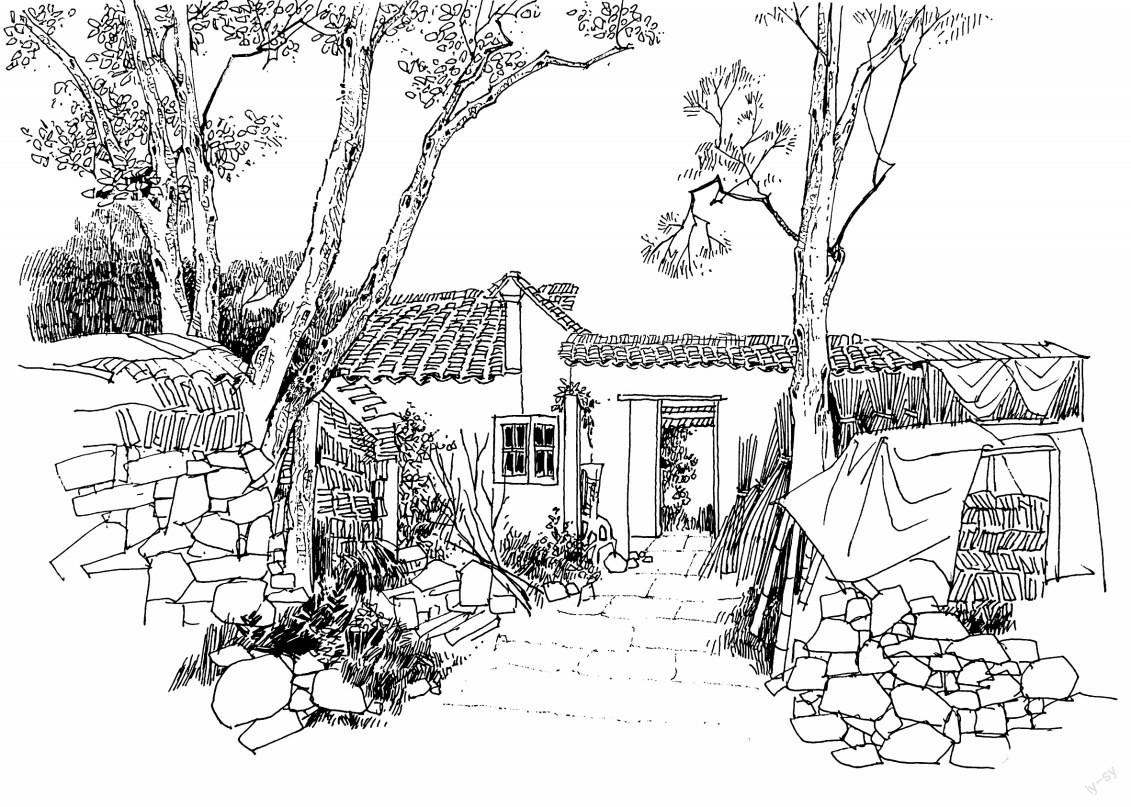
布谷鸟队。我在文学课堂前的樟树墩子旁,一边喝茶,一边看杜仲林里的布谷鸟,咕咕咕,咕咕咕,在这广深的山野间,布谷鸟的叫声不稀奇,奇的是,它们在林子里在我面前竟然如此慢悠悠地寻食。我不能大声,怕吓着它们,两只大的,几只小的,大的在林子两头踱步,小的在中间地带拱着碎叶,它们的脚步小心地踩在枯枝叶上,嘴中不时地发声咕咕。我早晨吃完苹果,曾将果核扔进林子里,不知道它们找着没有。
清明过后,富春庄的微信群里突然发出一张图:紧挨围墙边的一株月季中间,有一个鸟窝,织得精致,底部竟然用了一片塑料袋,这是什么鸟,具有防雨意识吗?过了两天,他们又发现窝里有三颗蛋,从蛋的形状上看,也辨不出什么鸟,我曾连续三年观察乌鸫下蛋孵鸟,好像也不是乌鸫。过了几天,他们终于拍到了鸟孵蛋的场景,原来是白头翁。我们于是满心欢喜,静静地等待即将从富春庄中诞生的新生命。才过几日,惨案发生,鸟窝被严重损坏,蛋也没了,大家连连叹息,但都猜是松鼠或者黄鼠狼干的。
富春庄的松鼠,不是成群,但至少有几个别动队,在我书房前面杨梅树上常窜上窜下,餐厅的屋顶上,也常见它们窜下来。有次一袋垃圾放在餐厅前门边,次日晨我去厨房,发现垃圾被翻得乱七八糟,狗进不来,只能是从空中或者夹缝中窜进来的松鼠。还有黄鼠狼,也是庄里的常客,但它们来无影,去无踪,移动迅速,力气又大,那鸟窝里的蛋,十有八九是它们偷走的。
A楼的后院有三棵樱桃树,今年是大年,樱桃至少几十斤吧,不过,有一大半是被鸟吃掉的。A楼的右前方,有两棵杨梅树,今年第一年挂果,也是大年,如果完整计算,不会少于百斤。六月初来时,我是坐等杨梅红;夏至前一周,我到富春庄,杨梅只剩三分之一,且每日急剧减少,就是说,昨天还是青的,次日上午就红了,如果不摘下,下午就掉果。撇除人为因素,有不少杨梅,就是鸟与松鼠吃掉的,各种鸟,它们似乎都要吃,专拣枝头红的吃,笃笃笃咬几口,杨梅就掉下来了。
飞鸟飞到了我的窗前,又飞走了。它们集于树,树顶、树间、树梢、树洞。它们来来回回地飞,小鸟飞成了大鸟,大鸟飞成了老鸟,直至某一天突然倒地。它们乐此不疲地叫,多声部,几重调,舒缓与急促,自由与散漫,完全任性。
天新雨,答答答不停,鸟们在树叶间缩着身子,它们将声音也藏起来,偶尔间鸣几声,鸣声依然清脆。
——选自2023年10月7日《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