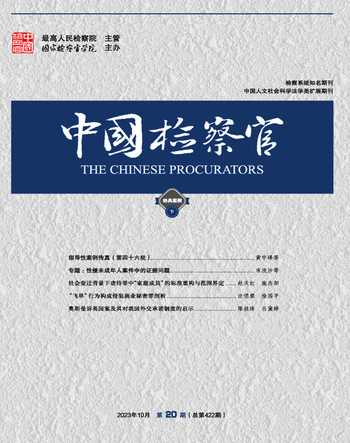使用经著作权登记的“美术作品”生产假冒产品行为的定性
郭大磊 李皓
一、基本案情
“LAKME”(中文译称莱肯)系联合利华旗下品牌。“ ”图样由著作权人Hindustan Unilever Limited(联合利华)于2016年2月26日在国家版权局登记为美术作品。“LAKME”标识在印度系正式商标,但本案案发时,“LAKME”标识在我国境内因商标抢注纠纷仍处于争议阶段而尚未注册成为我国商标。
2019年起,浙江省义乌市某公司总经理李某某与外籍人员接洽,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约定由该公司为客户生产一批印有“ ”图样的化妆品(口红、精华套装等)。李某某委托王某等进行商标仿制并安排工厂员工完成具体包装生产以牟取非法利益。2019年9月,公安机关查获涉案公司印有上述图样的化妆品共计12万余件。
二、分歧意见
关于李某某及涉案公司未经许可生产假冒“LAKME”品牌化妆品行为的定性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李某某及涉案公司的假冒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该化妆品上的图形标识虽然未进行商标注册,但该图形进行了著作权登记,且登记为美术作品,应当认为其具有独创性,系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属于刑法第217条所规定的“美术作品”,因而可以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李某某及涉案公司的假冒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主要理由是我国的作品登记仅做一般形式审查而不做实质性审查,《作品登记证书》中对于美术作品的登记仅有备案效力。涉案图样能否被认定为作品需要进行实质性判断。“ ”图样不具有相当程度的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难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就不属于侵犯著作权罪中的犯罪对象,因而无法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一)涉案“ ”图样缺乏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
相对于刑事法而言,民事法具有前置法的性质,因而刑事法的实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民事法的制约。[1] 基于此,侵犯著作权罪中“作品”的含义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含义保持一致。根据《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相关定义,“作品”认定的各种要件中,最重要、最关键且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是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正如有学者指出,认定“作品”关键在于独创性的认定,而独创性的“独”要求“獨立创作、源于本人”;“创”是要具备起码的艺术美感和智力创造成分。[2]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亦认为,“能否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关键在于涉案形象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作品的独创性强调独立完成和创作性”[3]。应当明确的是,我国的作品登记仅做一般形式审查而不做实质性审查,《作品登记证书》中的美术作品登记仅有备案效力,不具有证明涉案图样构成作品的证明力,《作品登记证书》中的图样无法等同于《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本案中,仅凭《作品登记证书》就认定涉案图样系美术作品缺乏充分证据,涉案“ ”图样是否属于美术作品的判断标准应对标《著作权法》中美术作品的判断标准。
第一,涉案“ ”图样不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独”的标准。“独”即“独立创作、源于本人”,要求作品应由创作者独立完成,而非抄袭的成果。实践中,“独立创作、源于本人”意味着作品创作的完成日期、首次发表日期需“先于他人”。而《作品登记证书》中记载的上述日期均为申请人自述,国家版权局对此不进行实质审查。因此,就本案而言,权利人仅凭《作品登记证书》的日期记载,在无创作过程的其他证据,例如作品首次公开发表的相关报道等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尚无法证明涉案图样系“独立创作、源于本人”,进而享有对作品的在先著作权。
第二,涉案“ ”图样不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创”的标准。“创造性”的判断标准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早期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只要劳动成果包含作者独立艰苦劳动并具有实际价值”即可,但因违反《伯尔尼公约》的实质精神而备受质疑。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创”的要求更高,《德国著作权法》认为作品应当具有一定的创作高度,缺少创作高度的作品不具有独创性。《法国著作权法》认为作品应当表现或显示作者的个性。[4]《德国著作权法》专家雷炳德指出:“那些运用普通人的能力就能做到的东西,那些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成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是新的,也不能作为作品受到保护。”[5]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对“创”的高度进行明文规定。但“作品中必须体现作者的智慧与个性”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从一些民事判决中可以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独创性审核标准较为严格。例如“红黄搭配的虎头电池包装图因构图过于简单,独创性较低,难以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上所指的作品”[6],又如“WMF标识仅系三个字母的简单叠加,缺乏作品独创性要求”[7],再如“游戏玩家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完成捏脸后的人物形象,其个性化程度很弱,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8]。此外,“原告所采用的元素均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素材,且仅系将上述元素简单组合,形成涉案主张权利美术作品,并不能体现出作者的创造性智力劳动”[9]。从上述判决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机关对于“创造性”的判断都要求需要达到富含作者个性、具有艺术美感的程度,而非一般人都轻而易举能够达成。具体到本案中,涉案“ ”图样包括两部分,一是“LAKME”字样,二是图形“圈L”,即简单的图形与字母的组合。“LAKME”字样系常规字体字母的直接排列且同时为商品标识,无法体现作品基本的创造性要求,“圈L”系实心圆中镶嵌商品标识首字母的组合图形,两者的简单叠加系商标的一般构成思路,符合一般人可以轻易达到的设计高度,无法体现作者无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也不能体现出作者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因而缺少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
(二)通过“美术作品”的路径保护商标会带来滥用著作权保护的后果
就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犯商标犯罪的定罪逻辑而言,制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罪名选择的范围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并不会特意对注册商标本身是否为美术作品进行判定,亦不会进行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考量。究其原因,著作权与商标权各司其职、各有其权利保护范围和侧重,著作权的核心是美感,商标权与专利权的核心是实用,商标的主要作用并非给人带来美感,而是商誉的体现,并在生产和商业流通中产生实用效果。虽然一些商标具备一定美感,但就其作用发挥而言,更为核心及关键的还是区分商品来源以及商标所附着商誉的体现。本案中,涉案“ ”图样对于一般公众认知而言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商标,其印在产品外包装上的实际用途即区别商品来源,但涉案图样案发时尚未注册成为我国商标而无法构成侵犯商标类犯罪。但若仅因侵犯商标类型犯罪无法适用就试图寻找适用侵犯著作权罪的入口,将“ ”图样作为作品予以著作权刑事保护不免有滥用著作权保护的嫌疑。
一方面,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后果可能使得图形商标注册毫无必要,因为只要是图形商标或是图形加文字的商标必然会有一定的设计因素,既然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保护著作权,那么注册商标就变得基本无意义。正式商标的获得要经过形式审查与严格的实质性审查审理,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的有关规定,对商标首先要进行形式审查,主要是对申请书件的审查、对商标图样规格、清晰程度及必要的说明的审查;之后再进行关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不得作为商标标志”“商标显著特征”“商标相同、近似”以及关于“三维标志商标的审查审理”等具体内容的审查。而作品著作权因作者作品创作完成时即自动获得,登记机关受理作品登记时仅做材料齐全方面的一般形式审查。另一方面,一旦类似本案的非注册但实质使用的“商标”能够被认定为作品,侵犯这种实质使用“商标”的行为能够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那么今后权利人显然都不会再去申请注册商标保护,而是只会去申请有关商标图样作为美术作品进而几乎“无成本”地实现更加长的保护期限(著作权保护期限系50年,商标保护期限系10年),会导致刑法所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犯罪被架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案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同时因在刑事诉讼阶段涉案标识尚未在我国成为注册商标,因而亦无法构成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类犯罪。此外,本案中扣押的涉案化妆品未发现有商品原料“以次充好”等情形,无法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亦未发现因使用该批次化妆品而发生造成他人容貌毁损等严重后果等情形,因此亦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检察机关综合上述法律分析及全案证据,依法对行为人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法益保护不仅仅通过刑法得以实现,而必须通过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10]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能纳入犯罪刑罚圈中,也无需“想方设法”挤进犯罪刑罚圈。司法者理应遵循立法者搭建的范围和框架而不能有所突破,尤其是知识产权这种侧重于财产属性、民事手段可以较为完善救济的的权利,更应注意把握刑事手段干预的范围与尺度,审慎运用刑罚手段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