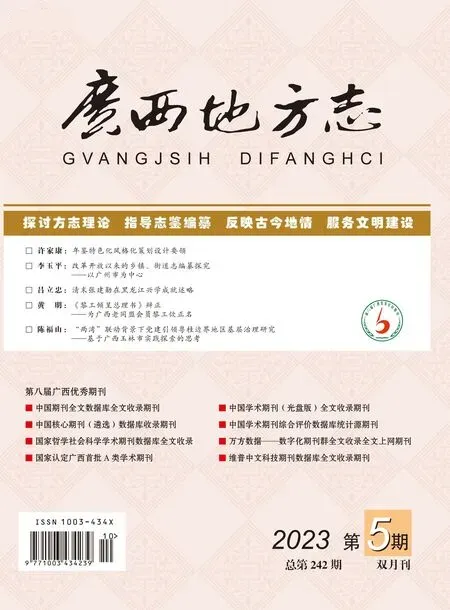霍乱时期的城市防治与乡村失序
——以1942年广西霍乱为例
黄小玲,刘超建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回顾近年国内关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历程,可知关于医疗史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是不断提升,还在质量方面保持着精耕细作,但是涉及1942年广西霍乱疫情问题的研究甚少。就目前民国医疗史中所涉猎到广西霍乱的研究著作来看,其主要以广西发生的大疫为主线,对广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疫情概况、救疗措施、疫病后果等一一作了论述,着力于史事的铺叙,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的疫病资料作深入发掘,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而在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主要聚焦于近代广西霍乱中的政府职能发展历程,普遍忽略了在霍乱疫情里的主要承受者——普通民众,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农民。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1942年广西霍乱作为切入点,利用所搜罗到的史料对其时疫情下当局政府的救疗防疫措施和城乡的各自表现等状况进行探究,以明晰城市与乡村两个不同纬度对于霍乱疫病的应对,从而以更立体的角度来清晰认识广西在霍乱疫情发生的真实样态。
一、1942年广西霍乱的袭来与扩散
霍乱被时人定义为一种因感染郭霍氏之霍乱孤菌而起的急性肠胃病,[1](P1)其大致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经由海上通道传进中国,而后成为我国通行的夏日时疫之一。据考证,广西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即发现霍乱流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中共发生流行35年次,波及市(县)达55个[2](P序1),相关情形已被时人普遍记录在案。1942年,一场异常猖獗的霍乱在广西爆发,并且是在不少群众公共环境卫生意识淡薄和卫生防疫条件艰苦的战时社会背景下倍道而进,致使广西当地遭受了巨大且多重的创伤。
(一)霍乱爆发前夕的预防措施
古称为瘴疠之地的广西,卫生设施至为简陋,终年流行传染病,[3](P195)且在新桂系初期获得权力重柄之时,“军事行动不绝……在全省里面,很少没有遭过兵灾的区域”,[4](P201)战争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秩序,饿殍遍野,病菌可任意滋长与散布。再加上,连年爆发的自然灾害,仅就1932年至1941年间发生的水灾、旱灾及其他灾害所波及的县城数量分别计有119县、126县、289县,[5](P政222-225)大量难民流离在外,人口流动频繁,这亦是霍乱频频发生的缘由之一。据1925年至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广西各地发生霍乱共五次(参见表1),并呈现出霍乱爆发的范围扩大、发病周期逐渐缩短的情形。

表1 1925—1941年广西霍乱疫情一览
新桂系政府为应对频繁出现的霍乱,要求各级政府部门都参与到了防疫之中,全方位地持续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首先,设置专门防疫组织机构。1931年,新桂系政府根据《广西建设纲领》中的计划,设立卫生委员会以负责全省的卫生防疫工作,并于1933年将全省划分为梧州、南宁、桂林三大卫生区,每区设省立医院或卫生事务所,协作、指导各县推行防疫工作。到1940年,“为便利卫生行政之推行起见”,再将全省增加到12个卫生区[6](P1199),每区下设15个巡回医疗卫生防疫队。其次,在全州、梧州、六寨、柳州、天保各设一个临时检疫所。[7]最后,在桂林、梧州、南宁、柳州、百色等重要地方成立防疫委员会,采取各样措施进行预防。如张贴“预防霍乱,第一要打防疫针,第二要喝用开水,第三要扑灭苍蝇”“预防霍乱,要吃煮烫的食物!”“霍乱危险,快打预防针”等霍乱防控标语。[8]这初步形成了以省卫生委员会、卫生区、防疫医疗队、检疫所和防疫委员会为结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
以上各方面措施的实施,可以说是有针对性地预防控制疫病的产生与扩散,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疫病的防控能力,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未能避免霍乱疫情的再次爆发。
(二)1942年广西霍乱的发生与传播
1942年广西霍乱疫情的初次发现地点是在金城江。广西省政府立即派广西省卫生处第二科技士陈联三,并偕同桂林卫生事务所检验主任徐周恩,携带疫苗及检验器材前往该地调查防治。[9]据陈联三述称:金城江霍乱发生后,省政府即派医生前往防治,但防治中医生亦不幸被感染,未及治疗,即毙命;后陆续发病二十余人,死亡10人。该地霍乱均系急性,发病后4小时即毙命,最多亦未超过10小时。[10]由此可知,金城江的霍乱来势十分凶猛,不可阻挡。但有时报称,经过省政府会同金城江当地政府“召集各界组织防疫委员会,力行防疫工作,并对该市环境卫生之整理,尤多致力”且“经各方竭力防治后,疫势稍戢,已不似一般宣传之严重云”。[11]可从后来愈发严重的霍乱疫情可知,这样的防疫措施并没有能够成功阻止霍乱的扩散,反而是“继金城江之后各地霍乱不断出现”。[12](见表2)

表2 1942年5—6月广西省各县市霍乱疫情一览
由下表内容分析可大致得知,在广西霍乱爆发的早期,即5月至6月间疫情在广西各大城市中散播肆虐的情状。起初应是因1942年5月,“气候酷热异常,忽然雨水多而寒凉,伏热被抱住而不外泄,又加寒饮食凉”[13],使得金城江成为1942年广西霍乱的起源地。在疫情暴发之后,霍乱沿黔桂铁路传入桂柳,最后依仗着桂柳两地交通枢纽的可达性,沿着铁路向东、西、南三方散播。总之,1942年广西霍乱整体传播趋势是先在交通便利的核心城市范围以内广泛传染,然后才逐渐扩散至小县城乃至乡村。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当时医疗服务条件及机构匮乏,且统计受限的战时环境下,偌大的广西乡村地区的病例已大约占据整个广西患病人员总数的半数,可见乡村地区的疫情形势的严峻,因而1942年的广西霍乱毫无疑问是一场牵涉多区域的大型瘟疫。
(三)1942年广西霍乱流行的频度与强度
在广西省政府1942年度卫生工作报告中有提到,霍乱自当年5月在金城江流行以来,至11月已蔓延至全省67县,致使36个市县成为疫区,7274人被感染,3553人死亡,[14]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此现有数据应是有所低估。
根据广西省立医学院1942年度工作报告中的《霍乱临时病室之工作报告》一文所载的信息可以推测(见表3、表4、表5),不同性别、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广西民众都有因这场霍乱而遭受到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表3 桂林市霍乱患者年龄及死亡数统计(1942年5月28日至8月8日)

表4 桂林市霍乱患者职业、性别及死亡数统计(1942年5月28日至8月8日)

表5 1942年广西省7月份各县疫情
其一,从患者的年龄阶段来看,患者都有分布在各个年龄层,上至70岁以上,下至1岁以下,而20-29岁间的患者数量居于首位。虽然该阶段的青年群众体质状况较各个年龄层来说,会更为强健且自身抵抗力也较强,但作为活跃在社会底层上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上的流动相对来说会较为频繁,而霍乱染疫的速度迅疾且猛烈,因此这个年龄层染病的比例会高于其他年龄层。
其二,从患者的职业类别来看,以苦工最多,其次是家务之妇女,再次是失业者,从次是商人,而后的学生、公务员、警士等占比较低。我们凭借此信息可得知,因此次霍乱大流行而成为最大冲击的群体对象是苦工、无业者和商人,这三者在当时均是社会地位低下者,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多为恶劣,以致大量人口极易染疫。正如桂林版的《大公报》所评论的那样:“一般平民之罹病致死者,时有所闻,路病路毙之流丐,每日必有二、三起,”[15]而商人的地位虽说不低微,但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要从事商业、集贸贩卖等经营活动,这难免不会增加其染病的机率。其余的阶层由于均有特定的活动场所,因而他们的致病可能性会比较小。
其三,从疫情地区的分布来看,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已从城市转移,并集中在乡村地区,且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都有疫情发生。在5-6月间,桂西地区发生11次,桂中地区发生5次,桂北地区发生4次,桂东地区发生3次,桂南地区发生3次,总计26次。在7月份时,桂西地区发生10次,桂中地区发生4次,桂北地区发生7次,桂东地区发生5次,桂南地区发生9次,总计35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桂北、桂东、桂南地区的疫情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先期流行的桂西地区,各地疫情发生的总次数并未有所下降,还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且疫区与非疫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
总而言之,霍乱患者人数与其社会地位、社会经济背景有着紧密的关联,虎疫来袭后的主要感染者就是下层劳动者、贫民及商人等。如其时《广西卫生通讯》所报道的:“桂林市前后已发生三十人左右,大多数是劳动者,其中有士兵,一个是中学生。劳动者既不识字,生活条件有(又)非常之坏,加以一般抵抗力薄弱,他们得霍乱的机会既多,患了以后,能够救治的希望亦很少。”[16]而这一群体也成为了霍乱得以频发和不断蔓延的条件。
二、广西城市的有效救治与防疫举措
以城市为维度来谛视与解读1942年广西霍乱疫情期间的应对表现,可以看到新桂系政府在人口密度较高、工商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已将切实可行的救治与防疫举措付诸于行动,并且取得最大限度的成效。然而,新桂系政府在重新主政广西之后,属意于确立与完善南宁、梧州、桂林及柳州等重要城市的卫生防疫机制,以致各地资源未能得到平均的分配,导致广西各地在面对疫情时所能够动用的救灾款项与物资截然不同,进而致使疫情的整体控制状态不佳,故本文将选取广西发展量质较高的部分区域核心城市来具体考证。
(一)迅速进行有效救治
面对各地不断爆发的霍乱疫情,作为全省交通枢纽和重点疫区的桂林,其防疫形势异常严峻,因为霍乱一旦流行,以水及苍蝇为媒介,传播迅速,患者如救治不及时,极易致命,“患者上吐下泻、抽搐、数小时即毙命”。[17]所以遇到霍乱发生,第一时间应是救人,“如一星期内能动员防治,尚可望不致蔓延,否则恐怕不可收拾也”。[12]可霍乱流行于桂林已成形势,其由交通线进入市中心,广西当局对此甚感隐忧,遂命桂林省立医院星夜布置传染病舍,次日要即可收治病人。[12]故为遏制此次霍乱,中央卫生所防疫大队即派21位技术人员担任桂林霍乱治疗医院的工作,并即时开始免费收容治疗。[18]并且,桂林市还动员了数家医防单位以及军政部、省卫生处等单位医务人员参加预防注射。[19]可疫情还是甚为猖獗,省政府惟特令桂林市卫生事务所自6 月1 日起暂停总所及分所的门诊,紧急动员全体人员投入防疫。[20]
进入6 月后,霍乱还是日益蔓延,流行不已。柳江也于6月初发现了真性霍乱的踪迹,[21]并在10日间有50余人死亡,霍乱蔓延势头正处于上升状态,尚未得到控制。虽然柳州卫生事务所已与柳州省立医院、柳州军医院及驻柳各卫生机关切实联系,进行防治工作,但是情形愈发严重,惟有急电呈报广西当局,新桂系政府随后立即派卫生处技士陈联三携带500瓶浓缩霍乱疫苗驰往柳州,协助防治工作,[22]并饬令柳州省立医院停止门诊,以专注于霍乱患者的救治。[23]作为沟通桂、粤、港之枢纽的梧州,亦面临着严重的疫势,梧州省立医院病房已不敷容纳,遂将各私立医院病室进行统制,而广西当局也特令梧州当地各卫生机关要全体动员起来以扑杀霍乱。[24]尽管相对于广西其他地区,发展程度较高的梧州、柳州、桂林三地已全力救治与扑灭霍乱中,但是请求增派医护人员的电文还是犹如雪片飞来,广西省政府遂特令省内的妇婴卫生助产士训练班及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停止上课,分批驰往前线进行救治。[23]
1942年的广西霍乱自发生后顿成燎原,广西当局迅速反应,积极调动全省医疗队伍以投入于救治病人的工作中,使大多数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救治。虽然霍乱发生于夏日,但6 月仅是潜伏期,接下来的7 月正属霍乱的大爆发时期,[25]患者数量逐日增加不已。
(二)整合多方救援力量
霍乱流行已逾一月,虽经各方医疗机构的努力救治,但是疫情未见有消停之意,反而有日渐严重的趋势,所以“扑灭霍乱”已不徒是一个口号,而应是当时一桩非常迫切的工作。可医院收治霍乱患者是防止霍乱大流行的最后一道防线,若要从根源上阻止其发生与蔓延,还得做到真正的治本,即为通过严格公共卫生,将役源和传播媒介扼杀在源头里,从而铲除霍乱的根蒂。
脏乱差的卫生环境是霍乱的培育器皿,而恶劣的卫生环境源于民众未能树立良好的卫生观念,继而易进食受污染的食物,最后滋生霍乱。因此,广西当局的相关部门加快了卫生警察、公共卫生护士、环境卫生员等的培训步伐。[3]P(203)另外,还筹划各县卫生警察训练班,向警察进行传染病管理、消毒、急救等方面的技能培训。[26]而各地政府部门都会紧急安排应对策略,例如自霍乱在柳州被发现后,柳州市有关机关立马召开防疫委员会分配工作。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主要有饮水消毒、饮食商店摊担管理、病家消毒与病家劝导四方面。其中,饮水消毒主要是对自来水、井水与河水进行专门的消毒,“自来水由自来水厂消毒,漂白粉由防疫委员会发给,井水由第三防疫大队办理,河水消毒由防疫委员会交警察局卫生科办理”。饮食商店摊担管理的相关规则在起初之时,已由警局长官部拟定,但在办理过程中愈发感觉霍乱流行速度之快,于是取消了一切饮食摊担。病家的消毒与劝导工作,主要是由卫生事务所派专员前往发病各户进行检查与指导消毒工作,后而进行寻找传染原因与传授预防方法。[27]
囿于人物力等资源的分配失衡,造成了公共卫生控制措施的实行偏重于大城市中,而整治恶劣卫生环境的措施却难以真正地在乡村地区得到实行,如此一来,社会整体的卫生环境不容乐观,于是没能以最大限度来堵截住霍乱的传播途径。
(三)严把交通舟车检疫
自新桂系重新主政广西后,经济、文化、军事各项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而在抗战爆发以来,“省外人士迁居桂柳日多,兼以湘桂黔铁路兴筑通车后,交通利便,”[28]大批外省民众涌入广西。所以,由国民政府领导的卫生署决定在这段非常时期间进行交通检疫工作,由各省市卫生所设交通检疫站将霍乱病菌堵截于市外。[29]诚如桂林卫生区卫生事务所所长施毅轩所言:“把敌人引进市区来巷战,谁也知道这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全省的防疫部队,是沿着黔桂路的交通路线步步为营,段段作战,”[30]严防境外疫菌传入市区。
广西省当局于5月28日实施国民政府卫生署制定的《非常时期交通检疫管理实施办法》,其要点有:一是针对霍乱进行检疫;二是在霍乱流行时,一切舟车及步行旅客均由检疫机关公告,实施检疫;三是进行舟车检疫工作之时,发现有感染霍乱之嫌疑人员,立即隔离;四是在舟车检疫时期发现霍乱患者,需就近送达传染病医院进行治疗;五是检疫机关必要时得禁止舟车往返疫区。[31]各市也具体贯彻和落实到位了,比如柳州在南北火车站各设检疫站,凡出入境的旅客均须接受检疫人员检验与注射,甚至派用了军队力量。[32]而在梧州方面,则就市区的各水上要道“举办水上检疫,往来船只,非经检验一律不准出入口,及在江面游弋”。[33]
1942年的广西霍乱基本牵涉到广西各地,多个地方均有爆发霍乱的情况发生,而交通检疫这一策略的实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地降低广西各地霍乱疫情输入与扩散的风险,有效地斩断疫情传播链,防范疫情扩散。
(四)积极推进防疫注射
不管实行内防扩散的公共卫生措施,还是设置外防输入的交通检疫站,对市民个体而言都是筑防线于身外,一旦霍乱发生,仍有威胁人身安全之虞。所以,仍需通过注射霍乱疫苗来对霍乱菌筑起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以有效提高身体免疫力。
1942 年霍乱大流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二十三医防服务队奉命来广西协助桂林市开展霍乱预防注射工作。[34]在该医防队的指导下,桂林卫生区卫生事务所划定“北极路等十街为疫区,疫区内之人民对于挨户防疫注射如有故违,处以10 元以上50 元以下之罚金或1 日以上5 日以下之拘役,至疫区内之街甲首长有协助推行强迫注射之责任”。[35]此外,为了能更多地扩充注射的人数,政府规定除医疗机关内设有注射疫苗处外,还不断增加注射地点。注射站一般设于桂林市区繁华的十字路口,“注射人员共分六队,上午四时至七时一队在花桥工作,下午一时至四时四队人员分别在体育场、十字路、乐群路及正阳路工作,晚间则派人在十字路注射”。[36]据统计,1942 年自5 月下旬发现霍乱开始注射起至7 月29 日止,“经注射者共约11 万余人”。[37]11 万余人虽仅占桂林全市人口三分之一,但加上往年已注射产生抗体者,该市的注射人数规模已属显著。而柳州经过防疫委员会先后三次发动市内各医师出动,前往贫民住宅区挨户强迫居民注射,并通过暂时封锁交通来配合注射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得人口总数仅为10万的柳州,已注射人数过万。[38]
但获得如此成效的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的畸轻畸重,像上述有基本城市设施、市政服务及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梧桂柳等市,其不仅有物力,还有财力和能力来架设和担负防治霍乱的供应链,因而在城市发生的疫情可以快速被扑灭。[39]但医疗条件贫瘠的广大乡村若是发生此疫情,其可能会陷入更为复杂的困境。
三、广西乡村陷入失序状态
当面临各种天灾人祸时,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程度及社会资源占有程度往往会立即在城乡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而发生在1942年的这场波及范围最广的广西霍乱有着最直接的体现。从上文的内容中可以看到,霍乱流行期间广西的有限医疗资源大都投入在城市的救治、防疫与公共卫生控制上,然而周边乡村似乎未被广西当局关注到,这会易使其陷入霍乱所带来的未知慌乱之中,继而造成乡土社会陷入混乱且无序的状态。
(一)乡村失序的医疗卫生背景
乡村社会之所以会在霍乱时期发生大混乱,是因为其时分配不均的医疗资源与恶劣的乡村卫生环境。据记载,“卫生医药,较有设备者,只有桂、梧、南、柳暨及附近各县。如左右江除龙州、百色、田阳、田东、靖西、天保等县稍有设备或稍有中医师中药店外,余皆无之。柳州区各县,如龙胜、三江、罗成、南丹、河池、东兰各县,亦尚无医生医药设备,即中医生中药店亦极少见。”[40](p189)加之,“因县乡工作比省区工作,尤为困难,即以出差费而论,技术人员下乡工作,每日只得出差费三元五角,实不敷一宿两餐之用,与省区人员出差费相差甚巨,故卫生人员对于下乡工作,视为畏途”。[41]
由此可知,除桂林、梧州、南宁、柳州暨及附近各县外,其余之地不仅存在着缺医少药的情况,同时缺乏相关医疗卫生机关与专业人员,从而导致了现代传染病观念和公共卫生观念的匮乏以及卫生条件愈发的堪忧。如桂林海洋乡的乡民发生疾病,“首先的医法就是看花,请郎中和吃药,还在其次。……‘看花’又分为‘阴花’和‘阳花’问题,‘看阳花’又叫做‘问神’,这是圣人有了疾病,或其他的事就去看一朵阳花,问问死鬼是凶是吉,有什么办法没有,可使病好或有其他顺利之法。”[42]而关于广西乡村的卫生环境,也有时人进行描述:
也有比率的野生的茅草,但这野草不是生长在田野上,却生根在颓败的朽烂的屋顶上,或是添塞着那残断的泥土剥落的垣墙。而在那烟熏的黯黑的屋檐下,则是蝙蝠、蜈蚣、燕崔与老鼠的洞穴。在这儿造物者显示了无比的公平:两三间茅蓬里,鸡、鸭、猪、狗、……和人一样,都有着一个安身之所。不分季节地,恶臭便弥布着——从猪栏毗连锅灶的屋舍里,总漂浮着粪便的腥臊,烂苹果的味道,或是都市里阻塞的阴沟的气息。是穷困的地方,是褴褛的地方,是菌毒滋生、疾病蔓延的地方。[43]
因此,乡民“如有普通疾病,多位求神问鬼,如不痊愈,则谓命实为之,瘟疫流行,则安为天灾不能逆抗。”[40](p189)可正出于乡民未能及时接收和消化外界所带来的医疗知识,故而遇上疫情的爆发,乡民们的错乱认知将会让乡村弥漫着恐惧的氛围。
(二)霍乱侵袭乡村后的失序表现
1942年5月始爆发的霍乱,未经多久就横行于广西乡村,“据谓各乡霍乱之流行,较城区尤为严重”。[44]由于乡村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广西的众多农村民众普遍缺医学与卫生的相关知识,所以致使乡村一遇上霍乱猖獗就容易失去原有的常规状态。
在1942年霍乱流行于广西的期间,广西乡村失序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引发大规模恐慌。由于面临霍乱的爆发与流行时,广西大部分乡村地方的医疗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所以对于霍乱的防治均是束手无策。此外,从时间脉络中观察关于1942年广西霍乱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邕、桂、柳三地的地方报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报道频率,且相关词条基本都含有“死亡”“猖獗”“可怕”等字眼,以致无知的乡民会在危机时刻催生出恐惧感。例如天峨县桥头乡的患者经过数小时后死亡,其乡村在数日内死亡人数超过60人,还出现了全家死亡的情况,导致本地人心惶惶,进而选择迁徙流离。[45]但由于疫情发生地纷纷出现流动性群体,向各地纷至沓来,尚未爆发霍乱之地将会受到强力冲击,以致于广西霍乱此起彼伏,始终未得到平息。二是极易受到迷信神权的荼毒。眼看霍乱在广西乡村地区恣意流行,难以控制,无知的乡民们在绝望与迷茫中只能大肆敬拜神明,频频出现“说神谈鬼,相率惊怪,杀猪宰鸡以祭之,广请僧尼以符咒之”等信奉超自然力量行为。[46]就如桂林的各乡镇在刚发生霍乱不久,乡民们就开始进行星象占卜等问神的活动,还公然散发传单进行宣传。[47]同时,亦有人意识到有些假托鬼神、耍弄手法的骗子会利用人们的愚昧以及对霍乱的恐惧心理趁机推波助澜,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48]。由此可见,乡村面对霍乱时所出现的失序行为,不仅是由于乡民自身的愚昧而导致,还因为有些利欲熏心的人会利用迷信活动以攫取更多利益所推动起来的,这不仅极大地妨碍了科学防疫工作的进行,还无形地促进了霍乱的流动。三是涌现大量未得到科学证实的各种医药偏方。譬如《扫荡报》于6月30日为所刊载的廉价草药偏方,即取3条名为“一块瓦”的草药,将其分为1寸长,并放入嘴里嚼烂后,遂用开水将药汁吞服,服至舌头产生麻的感觉为止。[49]亦或是在8月5日所登载的霍乱简易疗法,其主要使用范围是医药难施的广西穷乡僻壤处,此法主要分为防疫和治役这两大方面。其中,防疫方法有6个方面,分别是:“(1)马齿苋晒干,同盥醋煮食之;(2)松叶细切,酒冲服或浸酒服;(3)苍耳嫩叶,阴干收之,临时为末冷水服,或水煎服;(4)豉和白木浸酒常服;(5)明雄黄末少许擦鼻孔;(6)黑豆半升,用新布袋装放水缸内,三四日换一次”;治役方法有12个方面,分别是:“(1)绿豆粉和白砂糖少许服之,或各二两新汲水调服;(2)井水和白沸汤各半碗闻服;(3)锅底墨煤五分、灶额上墨煤五分、白沸汤一盏,搅数千次,以盌覆之,顷刻通口服一二口立止;(4)东壁土,新汲水搅化澄清服之即止;(5)地浆水一升饮之;(6)藕捣汁服之;(7)用桑叶一握煎饮服;(8)木瓜水煎服;(9)滑石四两、藿香一钱、丁香一钱,为末淘米水服二钱;(10)海桐皮煮汁服之;(11)樟树皮之粗皮或樟木煎水服;(12)早备口急散”。[50]尽管现未有材料证明,以上所提及的民间偏方在实际应用中是否对霍乱的治疗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民间偏方的疗效基本会因时令、地域及身体状况的不同而异,所以民间所流行的医药偏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民接受科学的应对方法,不利于霍乱的预防与救治。
由是观之,虽说乡村地区在面临霍乱瘟疫时,丧失了原有的正常秩序,被迫采取一些非科学的自救行为,但这并非没有实际意义。在等待政府缓不济急的霍乱防治措施时,这些非科学的自救举措适逢稳定了乡村地区的社会秩序,以至于乡村地区没有发生与堕入更大规模的动乱中。直至广西当局将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乡村上,这场声势浩大的霍乱疫情才拉下帷幕。
(三)乡村霍乱的治理与平息
当广西各大城市的霍乱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时,新桂系政府对于乡村地区的官方医疗救济与日俱增,逐渐控制住霍乱在乡村的蔓延,这场声势浩大的霍乱疫情才得以拉下帷幕。
首先,新桂系政府为构建起严密的疫情报告网,积极调动村街长、开业医师、警察局、乡镇公所、医院等各方力量,参与疫情报告,从而为政府及时掌握各地的疫情动态,使得各地更加有效地联合起来以防治疫病的蔓延。[51]其次,依照广西省卫生建设计划大纲,逐渐建立县级卫生院及筹设卫生分院与卫生所,并以此负责医药救济和县与县以下的卫生事业,进而实现广西卫生网的建立。[6](p1200)正如在1942年8月30日,平治县乐育乡与邕宁诚志五塘两村发生霍乱,“省府经已饬各卫生院就近派员防治,免致蔓延云”。[52]最后是派员前往乡村地区进行霍乱的预防注射,以控制针对霍乱的发生和流行。就如霍乱在雒容县各乡的蔓延速度愈发加快,该县在召开防疫会议后,立即决定各乡民众一律强制举行防疫注射。[53]可见,官方的医疗卫生体系已开始在乡村地区建立,从人员队伍建设、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官方的医疗救助日趋完善,有利于乡民减少采用非科学的自救行为的次数。
言而总之,在霍乱疫情蔓延至乡村地区之时,乡村地区所采取的非科学自救行为发挥出了自身的独特作用,暂时稳定了乡村地区的秩序,直至晚来的政府医疗救济发挥作用,才得以抑制1942年广西霍乱的持续蔓延。
四、余 论
1942年广西爆发的霍乱,是民国时代广泛传播且造成大规模死亡的一次瘟疫,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不少损失。尽管新桂系政府在广西已经建立起一套卫生防疫体制,能够在疫情爆发的瞬间有效地展开防疫减灾工作,推行了包括公共卫生控制、交通检疫、防疫注射等具体措施,但是由于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分派不到位的原因,获得资源的区域核心城市在抗击疫情上得以产生效力,而没有获得足够卫生医疗救济的乡土社会就此陷入到恐慌的情绪与混乱的秩序中。所以从城市与乡村两个维度来观察它们的防疫应对,发现两者对疫情的应对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也恰好反映了民国时期不同社会层面的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现今利用当时留存的资料对其时城市与乡村的反应表现进行总结与深思,可以了解到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大有裨益,而这也为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带来了不一样的思路,从而更好地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