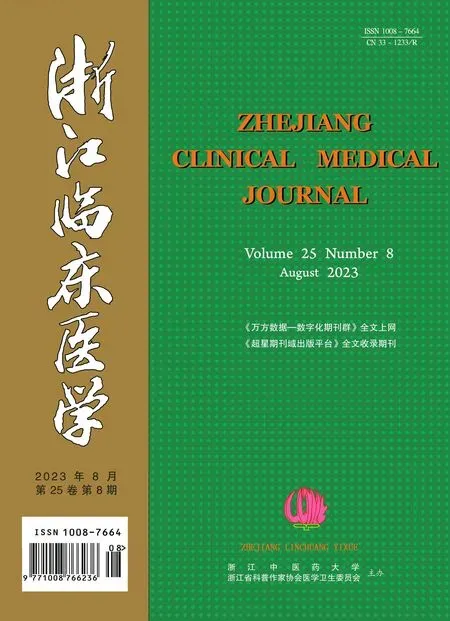婴儿肠道菌群早期定植时间的研究现状
商能欣 刘翠婷
作者单位:321017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金华中医院
肠道微生物群是指由细菌、病毒、真菌和其他影响健康与疾病的微生物组成的复杂集合体,其中,细菌占主导地位,是肠道微生物群的主要研究对象。一百多年前,“乳酸菌之父”伊利亚·梅契尼科夫认为:肠道菌群主宰着人类的健康与疾病。婴儿肠道菌群的建立来源于母亲,母亲微生物组中的每一个细菌都可能在婴儿生命早期,转移入肠道内成为肠道菌群形成的基础。人类肠道内会寄生10万亿个细菌,参与影响机体大脑、消化和免疫系统等发育并介导疾病的发生与转归。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哮喘、代谢性和免疫性疾病等均可能存在一个胎儿起源并与肠道菌群的早期定植变化存在关联[1-3]。因此,明确婴儿肠道菌群的初始定植时间,将有助于我们解密某些成人疾病胎儿起源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并进一步获取疾病可能的潜在治疗靶点。现阶段,人类肠道菌群的定植始于产前还是产后仍存在广泛争议[4],尚无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基于此,本文综述婴儿肠道菌群定植时间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初次定植的时间倾向,为基于肠道菌群而开展的成人疾病胎儿起源研究提供思路与建议。
1 胎儿的物质来源途径
胎儿的诞生始于受精卵,其后受精卵反复分裂形成囊胚,囊胚植入子宫壁,并在此发育成胚胎。胚胎附着于胎盘上,被充满羊水的羊膜囊包被,在受精8周后发育为胎儿。胎儿在密闭的羊水中漂浮,通过脐带和胎盘与母体进行物质交换。因此,羊水、脐带和胎盘作为胎儿的物质来源途径,与胎儿的联系最为密切,此三者的生态变化可直接影响胎儿。
2 婴儿早期肠菌定植理论
2.1 “宫内菌群定植” 肠道菌群定植于产前 人们普遍认为,胎盘具有免疫学特征,可以阻止菌群进入,维持胎儿在宫内环境的稳定与安全,因此,“无菌子宫”理论深入人心。但随着检测技术的日益革新,部分学者提出“宫内菌群定植”假说,逐渐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
1982年KOVALOVSZKI等[5]通过培养353个胎盘发现,16%的胎盘样本细菌培养呈阳性,且无任何绒毛膜羊膜炎的组织学证据。还有报道,属于孕中期阶段的人类胎盘在绒毛膜板内可培养出需氧菌和厌氧菌[6]。第2年也有报道,在人类胎盘中发现了来自母亲肠道的细菌DNA,提示生命早期的肠道菌群定植可能是由母体通过胎盘垂直传递给胎儿[7]。
2012年Isolauri团队利用qPCR技术在29个胎盘和羊水样本中检测出细菌DNA,还发现这些细菌DNA与胎儿肠道中先天免疫基因表达谱的变化相关[8]。2013年华盛顿大学微生物学家Mysorekar和其同事收集195个人类胎盘,对胎盘基板进行石蜡切片与染色,观察到近1/3的胎盘携带细菌,且无明显的炎症痕迹,通过此次观察MYSOREKAR等[9]认为,母亲胎盘基板中的细菌可能是胎儿肠菌宫内定植的来源。2014年Aagaard团队注意到,新生儿第1周肠道细菌与母体阴道细菌并不相似,怀疑肠道菌群的定植可能始于产前,其后他们借助320名产妇的胎盘,在执行无菌和阴性对照的条件下,通过基因测序在部分胎盘中检测出细菌DNA,并提出肠道菌群的初始定植可能始于产前[10],这一发现引起人们对“宫内菌群定植”假说的极大关注。
近几年,“宫内菌群定植”假说得到进一步发展。2016年,芬兰学者在健康产妇的胎盘、羊水和婴儿胎粪中检测出具有共同特征的微生物群,认为细菌在母体与胎儿之间转移,且肠道菌群的定植可能在产前经由胎盘和羊水中不同的微生物群启动[11]。2018年有研究利用正常妊娠小鼠模型,发现孕期(E17)胎鼠肠道内存在细菌DNA,且主要来源于母体胎盘[12];还有研究招募36对阴道分娩母婴和42对剖宫产母婴,共收集包括但不限于胎盘、胎膜、羊水和新生儿胎粪在内的550个样本,通过阴性对照排除污染,发现胎粪、胎盘和胎膜中的细菌组成与分布高度相似,且大约一半的胎盘细菌序列与母体阴道、直肠和口腔样本中的细菌序列相同[13]。2020年有研究分析了39对母婴的羊水、母体粪便、阴道液、母体唾液和首次胎粪,发现胎粪菌群与羊水菌群表现出更多的共同特征,其结果认为胎粪中菌群成分来自母体的多个部位,但羊水内细菌群落贡献最大[14]。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在胎儿物质来源途径的羊水、脐带和胎盘中均发现细菌可能存在的痕迹,也观察到婴儿粪便中微生物群与羊水和胎盘具有某些相似的联系,以上发现在支持“宫内菌群定植”假说的同时,给“无菌子宫”观念带来了冲击。
2.2 “无菌子宫” 肠道菌群定植于产后 二十世纪初,法国儿科医生Tissier断言,人类婴儿在无菌环境中发育,并在通过母体产道时获得细菌,此后“无菌子宫”理论开始盛行[15-16]。目前,虽然存在不少研究支持孕期“宫内菌群定植”假说,但2016年有报道,使用两种DNA纯化方法,通过16S rRNA基因测序和群落分析,却无法将人类胎盘样本与阴性污染对照的细菌群落进行分离[17]。另有研究调查了20名足月分娩和20名自发早产的胎盘样本,通过使用两种测序方法,均未得出胎盘中存在微生物这一结论,研究支持健康胎儿的胚胎期发育是在无菌环境中进行[18]。
2019年剑桥大学Gordon团队分析了537名产妇胎盘,通过使用两种DNA测序方法(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和16S rRNA扩增子测序)及不同制造商的DNA提取试剂盒,发现健康的胎盘中并不能找到细菌物种,他们的结果表明,肠道菌群的最初定植应始于产后[19];同年有研究报道,对29个人类胎盘组织进行细菌培养,除一个胎盘组织可能被污染外,其余28个胎盘组织培养物均未产生细菌[20]。又一项研究对胎膜、脐带和绒毛膜绒毛进行采样,发现只有在胎盘外才有可能分离出有意义数量的活细菌或细菌DNA,宫内细菌或细菌DNA的出现与分娩过程中样品暴露于污染相关[21];还有研究表明,如果去除DNA试剂盒和检测试剂的污染,将无法识别出独特的胎盘微生物群[22];同年,动物(小鼠和猴)实验表明,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基因测序,未发现胎盘和胎儿组织样本中存在细菌定植,研究认为接受“宫内菌群定植”假说尚为时过早[23-24]。
2021年有研究利用直肠拭子,于剖腹产期间和抗生素使用之前,收集胎儿出生前胎粪,通过比较阴性对照和婴儿粪便发现,出生前胎粪中并未检测到不同于阴性对照的微生物信号,该研究认为健康足月婴儿的肠道定植不会发生在产前,并且婴儿胎粪的微生物特征主要反映的是产后获得的细菌种群[25];同年,有报道通过经腹羊膜穿刺术,研究360名早产且胎膜完整的婴儿羊膜腔微生物状态,发现在无羊膜内炎症的情况下,从羊水样本中分离出细菌可能是实验过程中样本受到了污染,而非早期定植或感染[26];另有报道对44名婴儿的羊水、胎盘和首次胎粪进行检测,其结论不支持胎盘或羊水中存在微生物群的观点,首次胎粪中含有的细菌迹象似乎是围产期定植的结果[27];还有报道新生儿胎粪的细菌含量与未含有任何生物样本的阴性对照无明显差异,且其细菌培养也支持这一发现,该研究表明尚无法支持“宫内菌群定植”假说[28]。
综上表明,在严格的取样和检测过程控制下,“宫内菌群定植”假说饱受争议,“无菌子宫”理论仍被认可。
3 “宫内菌群定植”对比“无菌子宫”的研究争议
“宫内菌群定植”假说的兴起,严重考验着“无菌子宫”理论。虽然研究者已在羊水、胎盘、脐带血和胎粪中发现细菌DNA[6-8,10-11,13-14],但仍存在方法学上的缺陷,削弱着“宫内菌群定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宫内菌群定植”研究的现有不足:(1)尚未在胎儿体内发现活菌:“宫内菌群定植”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细菌培养、分子微生物学技术和基因测序等手段,仅检测出细菌DNA而非活菌[6-8,10-11,13-14],故缺少更直接且客观的证据。有报道,通过培养孕期羊水、胎盘及胎粪中的活菌,结果显示与阴性对照并无明显差异[29]。(2)污染:“无菌子宫”支持者认为,羊水、胎盘、脐带血及胎粪的样本收集和相关检测中,缺乏对实验过程的污染控制,导致获取的数据难以真正聚焦宫内菌群。有报道,“宫内菌群定植”研究中相关检测试剂存在污染[17,22,29];另有部分研究,实验设计中缺乏充足的阴性对照设置,故其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7-9];还有研究检测的羊水、胎盘或胎粪样本是于出生后采集,无法排除生产过程及产后菌群定植的可能,故其研究结论需要谨慎认可[6-11,13-14]。(3)方法学缺陷:“宫内菌群定植”相关研究中,检测方法、存储条件等均存在差异,部分研究仅使用一种方法检测样本中细菌存在的痕迹,未进行二次验证[6-9,13],这是否存在检测偏移?且研究中样本获取时间、获取方法和保存途径等亦未统一,致使研究可重复性欠佳[30]。(4)“低微生物量”样品挑战:现有技术虽可以高度灵敏地扩增极微量的DNA,但任何污染都可能超过仅含有极低微生物量的样品中的真实信号,而胎盘、羊水中细菌含量较低[10-11,21],如何避免假阳性结果和污染问题,仍值得思考。(5)样本数据:虽然“宫内菌群定植”支持者收集了几百个研究样本,但仅有部分研究样本支持了他们的观点[6,9-10],且是否存在批次效应有待验证,故“宫内菌群定植”假说还需要更多的多中心、大规模的相关研究支持。(6)临床研究有限:近几年临床中,以“宫内菌群定植”为结果的研究,其数量低于“无菌子宫”,且这些研究未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肠道菌群的定植是由母亲在孕期垂直传递给胎儿。(7)胎儿菌群定植来源矛盾:“宫内菌群定植”研究显示,胎儿菌群定植的微生物来源主要与羊水[14]、胎盘[9,12-13]或者羊水与胎盘[11]高度相关,并未产生统一而明确的结论,故其实验结果有待重复考证。
4 关于“宫内菌群定植”和“无菌子宫”的相关思考
作者发现“宫内菌群定植”面临着众多质疑,因为关于细菌在孕期从母亲转移至胎儿肠道内的证据的可靠度尚不清楚。近几年,较多的临床研究结果侧重支持“无菌子宫”学说,认为肠道菌群的定植应该始于出生后[17-20,22,25-28],但已发现无脊椎动物中共生菌存在垂直传播的现象[16,31],表明母体共生菌传递可能是一种古老且具有进化优势的机制,然而该现象在人类中获得证实还存在诸多困难。
如果接受“宫内菌群定植”假说,随之而来的问题很多:(1)若胎盘、羊水和脐带血内存在细菌,这些细菌是否能真正转移至胎儿身上,并进入胎儿肠道内定植?(2)与健康相关的菌群组成和功能特征尚未明确[32],故出生前胎儿接触细菌是如何规避感染?因为既往研究认为,孕期宫内细菌可能代表感染迹象,这些细菌可激活机体免疫应答,而过度的免疫炎性反应与流产、早产和产后并发症等不良结局相关,甚至可能增加成年时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33]。(3)如果肠道菌群的初始定植时间发生于产前,那么母体是如何平衡肠道菌群与胎儿间的关系?Aagaard作为“宫内菌群定植”坚定的支持者,认为胎盘中可能存在微生物,且这些微生物阻止了致病菌在胎儿体内的定植,但这种观点尚需要更多更充分的研究证明。(4)肠道菌群的定植会对人类胎儿的生长发育产生何种影响?其对健康的胎盘和胎儿是否是必要存在?如果是,肠道菌群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胎儿?随着肠-脑轴、肠-肝轴、肠-肺轴等理论的兴起,微生物又是如何调节复杂的妊娠过程?
“宫内菌群定植”假说冲击着生殖及生殖免疫等领域。目前,作者认为尚无法直接肯定得出婴儿肠道菌群的早期定植时间,但能明确婴儿肠道菌群的广泛定植发生于产后。近期研究多倾向支持“无菌子宫”学说,但要证实孕期宫内无菌也十分困难。明确“宫内菌群定植”和“无菌子宫”正确与否,还需要更多高质量和可重复的临床研究观察。
综上所述,作者建议如需开展母婴肠道菌群与疾病间联系的相关研究,可先立足于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可穿过胎盘屏障),从而避免“宫内菌群定植”和“无菌子宫”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