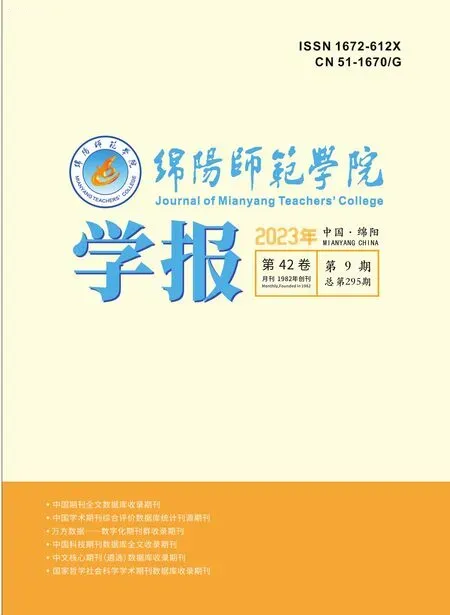战争纪实·民族主义·女性解放
——论庐隐的长篇小说《火焰》
杨昊霖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提到庐隐,人们的第一印象便是“五四”时期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海滨故人》与感伤的女作家形象。作为最早一批觉醒的女学生和女作家,庐隐在“五四”时期初登文坛并大展身手。但随着社会格局风云变幻与庐隐的再次恋情,大众对庐隐私生活的关注反而超过对其文学作品的关注,学界对庐隐文学上的认识也基本延续了茅盾《庐隐论》中的看法:“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的‘发展’也是到了某一阶段就停滞了;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1]不可否认,“哀伤的笔调”是庐隐创作的整体风格,但庐隐“在暑假中炎暑的天气里,挥着汗写成一部长篇战事小说”[2]87,《火焰》却完全摒弃了庐隐“哀伤的笔调”,书写的重心也从“五四”脆弱青年的自叙抒情转移到更具时代性与广阔性的社会与战争,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这部别致的作品却几乎被学界所忽视,不仅研究者寥寥,即便有也是在文中一笔带过,且评价不高。为什么会如此?如何评价这部被忽视多年的长篇创作?特别是当我们将《火焰》置于重新探究庐隐创作转向的原因,还原庐隐更为真实的创作观念和思想立场时,它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呢?
一、基于战争纪实的自叙传体的艺术想象
随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兴起,“人的发现”成为越来越多新青年追求的人生主题。虽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对于刚接触白话文创作与西方文学思潮不久的“五四”新青年来说,以记录与表达自身的身世、经历、思想、情感的方式来创作小说更契合他们的写作理想,自叙传小说遂成为众多青年写作的选择。庐隐便是如此,她是“五四”时期首批觉醒的女作家之一,1921年凭借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经过两年的写作与摸索,庐隐于1923年10月在《小说月报》连载长篇小说《海滨故人》。它不仅奠定了庐隐之后创作自传体小说的色彩基调,也让她摸索到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方式——自叙传体。即使后来庐隐以书信、日记等形式创作,其文本内容也蕴含着她本人极其强烈的主观情感和生命体验。
《火焰》同样是一部自叙传体创作小说,与《海滨故人》有着类似的人物关系设定。小说围绕着主人公陈宣与四位战友的遭遇展开叙述,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出上等兵陈宣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的生命体验,通过刻画陈宣五人在淞沪战争中的经历,来激发读者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面对全然陌生的题材,庐隐选择其写作生涯中最熟悉的自叙传体模式进行创作完全在情理之中,且自叙传体也为作者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提供了文体基础。《火焰》的战争题材和自叙传体的写作方式要求庐隐描述陈宣的作战体验与战斗细节,而战争与庐隐的日常生活经验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庐隐虽没有亲自上战场参与战争,缺乏士兵的第一视角的感受和体验,但并非完全置身事外。战争开始时,庐隐居住在上海愚园坊20号,离闸北一带的战场也仅有十公里左右。淞沪战争爆发后,躲避战难的大量民众纷纷逃往租界寻求庇护。庐隐虽不能体验战场上真实的厮杀和枪林弹雨,却耳闻了战场上中国军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她通过搜集大量时效性与真实性较强的新闻报道等材料,在《火焰》中尽力还原了一个十九路军普通士兵陈宣所亲历的真实战场,并通过陈宣在战争中的亲身体验,具体入微地描写了战斗的情形和中国军人不屈的抗敌意志。如写十九路军对付日军装甲车的方法:“我们老早将手溜弹五六个,拴在一块,把保险栓抽去,并用一条长长的铁丝系住,一条铁丝系上许多炸弹,两旁安置上哨兵,敌人渐渐来得近了,我们把铁丝一松;一阵拍拍轰轰的声音,早见敌人的铁甲车四分五裂的倒在地上。”[3]62同样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如初战告捷击落日军一架飞机、车夫胡阿毛载日军冲入黄浦江、士兵用香烟盒做炸弹等等,力求将一个真实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情形呈现给大家。不仅如此,庐隐在战争纪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想象,让陈宣参与到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如日本轰炸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一事,作家这样写道:
“呀!好大的火哟!……唉,商务书馆遭了殃!”一个瘦个子的广东兵,跑进来说……有几页残稿,被风卷到战壕近边来……“唉,打仗就是一个大毁灭,为什么一些哑巴的书籍,也会遭这样的打劫!”我们的连长愤慨地说。“书籍固然是哑巴,可是他维系着我们全民族的生命呢。当初日本人灭了朝鲜,第一禁止朝鲜人读他本国的文字,这正是日本人斩草除根的狠毒手段,现在想依样的加在我们身上。他们的野心我们很可以明白了。”黄排长说……北望东方图书馆也燃烧起来了[3]63-65。
在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被毁的纪实基础上,作家虚构了陈宣等人的在场,通过想象纸页飞到战壕、众人议论等细节,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信度与代入感,也通过众人的议论侧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陈宣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总被安排扮演一名旁观者,并不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对于较为宏大的历史事件,庐隐是有所顾忌的。她作为战场外的非亲历者,不敢牵涉太多真实的细节,越是宏大的历史事件,细节越难用艺术想象填充,不慎的虚构有可能会因材料了解不足而使作品堕入虚假的深渊。于是庐隐让陈宣参与到一些规模较小的历史事件中,如《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中有一则新闻《班长夺取最新式之机关枪》:
又第二团班长陈友三,于二月十五日竹园墩之役,敌方有连珠枪射来,其势颇异,前所未闻,料为敌之新式枪。当时第五连欲夺此枪,奋勇冲进,因而牺牲者不少。该班长深夜由侧面蛇行斜绕,深入敌阵,自机枪手之侧背,袭击狙杀而夺获之[4]345。
《火焰》中同样也描写了陈宣所在的第五连夺枪之事,但对此事稍加改动:
张权说:“你们听敌人的炮声枪声……那末我们趁这个时候到敌人那里借几杆六五枪,及一两挺轻机关枪来,做纪念也好。只要有四五个人就行了,……老谢,我们去同连长说声好不?”……攻击的时间到了,秦连长率领了我们鱼贯的出了掩蔽部……我们得了不少的子弹,还有六五步枪八杆,轻机关枪一挺,我们砍毁敌人的铁丝网,托着轻机关枪和六五步枪,从从容容的回来了[3]200-206。
小说改写了第五连夺枪失败“牺牲者不少”的事实,而让同属第五连的士兵陈宣与连长等人完成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深夜奇袭。这次胜利不仅渲染了十九路军抗日作战的机智英勇,同时也传达了积极昂扬的抗日爱国精神,激发了读者抗击外敌的民族主义情绪。庐隐为保持小说真实性,尊重宏大的战争纪实事件,选择在较小的历史事件中寻找虚构叙事的空间。作家将短讯信息扩充到几千字的篇幅,充分发挥艺术想象虚构了陈宣等人深夜夺枪的作战经历,完整呈现了第五连战士从筹备夺枪到胜利归来的全过程,在战争纪实与个体虚构叙事之间找到平衡。
小说中对作战细节的还原以及相关新闻材料的应用,在同时期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中独一无二,从这些材料的运用来看,庐隐创作《火焰》时颇费了一番心血。第一次淞沪战争结束后,大批作家创作了相关题材的小说,如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铁池翰的《齿轮》等,这些小说大都在1932年结束前出版,而庐隐并没有赶时间出版,她在自传中提到:“在暑假中炎暑的天气里,挥着汗写成一部长篇战事小说,这本书本想出版的,不过我还要修改一次。”[2]87《火焰》的初稿完结于1932年的夏天,但据庐隐给《华安》杂志主编陆锡祯的信件①,《火焰》的寄出与发表是在1933年的夏天,而庐隐其他小说写作与发表的间隔时间都不曾长达一年之久,这一年的修改时间也从侧面证明了庐隐对此小说的谨慎与重视。庐隐基于战争纪实,以自叙传体书写士兵战争体验的创作手法既不等同于力求真实的报告文学,也与上帝视角描写战争全局的史诗不同。作家以战争纪实为基础展开个人叙事的艺术想象,在虚构中保持宏大历史的真实,这一写作手法在同时代同题材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
二、民族主义立场的矛盾建构
以战争纪实为基础的自叙传艺术想象的写法是新颖的,但小说为何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呢?其主要原因在于陈宣这一人物形象的失策。众所周知,自叙传小说的主人公,很大程度上附着了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而《火焰》中陈宣的许多言行举止与思想情感有悖于角色身份且前后矛盾。虽不排除庐隐将小说修改时间拉得过长,导致作家的思想情感发生变化难以统一,但究其根本,是赋于人物形象上的作者自身的立场与价值观产生了矛盾与冲突。
庐隐在经历“九·一八”“一·二八”等一系列民族危机前,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传入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及在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桑兵曾指出,“五四”新青年一代所接受的世界主义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罗素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5]。三种思想来源都多多少少影响了庐隐的世界主义思想,但严格来说她的立场更偏向于罗素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庐隐作为“五四”中觉醒的作家,曾在北京国立女高师旁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许多新文化阵营的代表人物也在女高师授课,庐隐因此接触到新文化一派从国外带回的新思潮、新学说。且罗素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当时也颇受国内青年喜爱,其1920—1921年的来华讲学影响了一批青年。1920年庐隐曾在校《文艺会刊》上发表了议论文《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以“我”和“他”的界限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家族主义时代”“军国主义时代”和“世界主义时代”。庐隐在文中如是说道:“家族时代,以利一家一族为利己;军国时代,以利一国为利己;世界主义,一旦流行,就必定要利人类,然后才能利己;若到这个时候,利己利他还有丝毫分别么?所以现在人说底利己,不外指家族观念,乡土观念,国家观念,实在是一种偏狭自私底见解,绝不是彻底底议论。”[6]9庐隐早期接受的世界主义思想从此扎根,并对她的人生和创作影响颇深。
世界主义思想也改变了庐隐对日本的看法。她曾于1922年和1930年两度出游日本,第一次出游时访问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戏剧家秋田雨雀,而第二次于1930年去日本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早在1928年日军出兵山东占领济南时,庐隐便作了诗歌《弱者之呼声》和议论文《雪耻之正当途径》谴责日军侵略者,并呼吁同胞团结对外,但庐隐并没有排斥一切与日本相关的人与事。她在1930年的日本之旅中接触到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庐隐在后来的游记中写道:
总之我对于日本人从来没有好感……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了。我就觉得我太没出息——心眼儿太狭窄,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的日本人,当然有些可恨,然而在东京我曾遇见过极和蔼忠诚的日本人……他们对待一个异国人,实在是比我们更有理智更富有同情些[7]21。
开阔的国际视野让庐隐明白,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是由无数复杂且具体的个人构成,日本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其中有侵略者也有无辜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可是“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后,庐隐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两种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首先要澄清的是,庐隐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并无关联,庐隐生平很少涉及政治,她既不倾向于“左翼”团体,也不支持“民族主义文艺运动”。1933年丁玲被捕后,外界传闻丁已遇难,庐隐便写下杂文《丁玲之死》来凭吊同为女作家的丁玲,并在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唉,时代是到了恐怖,向左转向右转,都不安全,站在中间吧,也不妙,万一左右夹攻起来,更是走投无路。唉,究竟那里是我们的出路?”[7]233可以说,庐隐的民族主义是一位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自由作家自发觉醒的思想。张中良也说过:“表现民族主义主题的作品,并不限于来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阵营,也有大量作品出自左翼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倾向的作家以及民间写作。”[8]而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实际源自外敌入侵的压力。民族主义是属于历史范畴的现代概念,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动力:“把中国纳入民族国家轨道上并相应地产生民族主义的历史动力,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9]132中国的近现代史基本是被侵略欺压的耻辱史,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有不同内涵,但反帝爱国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民族主义的重要主题,而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日本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并多次挑起战争,民族主义情绪的敌对目标更加清晰,反帝爱国逐渐变为反日爱国。
庐隐被民族主义激情推动而创作了《火焰》,其小说内容自然要建构民族主义战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但庐隐不得不面临自身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突:一方面,“一·二八”淞沪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自卫反击战,反日爱国的立场不容置疑;另一方面,战场上的敌人也是活生生的普通人,战争意味着死亡与反人性。庐隐不能抛弃原有的世界主义观念,但又要构建小说的民族主义立场,于是陈宣的思想呈现出自相矛盾的局面:
唉,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太短促了……但是我想起敌人无缘无故的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杀害了我们无辜的人民,焚烧我们工人血汗造成的建筑物……他们逼着我们走进战争的漩涡……战争之神,虽是露着可怕的狞笑,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在那可怕的狞笑里找出路![3]39-40
此时陈宣的内心独白虽有挣扎,但通过列举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证明“一·二八”抗战的正义性与正当性,坚定自身作战的信心。可在随后不久的战斗中,陈宣的心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和敌人肉搏时产生了怜悯之心:
有一个敌兵扭住我滚来滚去,结果滚到一个坑里去……我就势骑在他的身上,咬紧牙根,用拳头在他心口用力的捶。突然他喷出血来。我的手莫名其妙的软了,我看见他眼角有两颗晶莹的泪滴。唉,我不能再眼看着他咽气,连忙从坑里爬出来,我的神经错乱了[3]86-87。
听说日本枪决了六百名逃兵后,陈宣感慨道:“唉,我们的敌人,何尝不是我们的朋友呢!只要毁灭了我们中间的障碍,原可以握着手,亲切的互弹心弦中无私的交响曲。造物主创造了人类,何尝希望人类互相屠杀呢?”[3]124庐隐在面对自身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时,并没有找到答案,也没办法处理这个矛盾。随着后期战争的接连失利,陈宣的民族主义情绪愈演愈下,甚至产生了不知往何处去的想法:
我们急切的追逐那各式各样的幻想。这是造物主特予我们人类的权利。只要我们从猛兽的漩涡中扎挣出来时,便不知不觉有了这种企求。但是为了人与人互相残杀的事实继续着;这种企求只是增加苦痛而已。因为我们所追逐的幻想,只要敌人一声炮轰,便立刻消失了。这时候我们只有运用我们的四肢,极力的活动着,从毁灭中找出路。也许就是从毁灭中找归宿。唉,生的希望,有时似完整,有时似破碎的,在不断的向我这时的心灵攻击,使我对于多罪恶的世界发生咒诅声。我这时有一种愿望,假使这世界终有光明的一天,那末我们应当不再继续演那人杀人的惨剧。不然我们应当把整个的世界毁灭。一些空洞的希望,骗人的幸福,都应当宣告死刑,使一代一代的人们,都在战争中扎挣,这是可耻的呀![3]192-193
陈宣所面对的混沌又迷茫的问题同样也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难题,战争中生命的消逝与人类同情恻隐之心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庐隐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可在小说结局,她选择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大笔一挥强行改变了陈宣的立场:“一股热烈的血潮,不知不觉又从颓唐的心底涌起。我忘了一切的苦痛,我也不惋惜我变成残废;至少我在这世界上,是作了一件值得歌颂的牺牲。这种的牺牲,是有着伟大的光芒,永远在我心头闪着亮的呵!”[3]257虽然庐隐在小说结局升华到民族主义的大义主题,但如此强行建构的民族主义立场推翻了陈宣之前所有的思想挣扎与自我斗争,使陈宣的人物形象彻底崩坏,陈宣的思想与他的行动和经历完全脱钩,成了无根之木,最终导致小说的艺术价值失衡。
三、启蒙到救亡:曲线的女性解放
为何庐隐不惜损伤小说的艺术价值也要如此坚决地在文本中建构民族主义立场呢?“一·二八”抗战的爆发无疑是最直接的外部原因。1931年夏,庐隐为讨生活从杭州搬至上海,经刘大杰推荐去工部局女子中学教书,其丈夫李唯建经舒新城的介绍在中华书局任特约编辑,一家四口在上海愚园坊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但好景不长,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后,庐隐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空袭,庐隐在《小说月报》连载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被迫中止,只刊载到第十七章,这对向来不留底稿的庐隐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她在自传中提到:“我写一本十万字的长篇,在《小说月报》已发表了十分之八九,其余的一部份,不幸因国难而遭焚。——如不然这本书在民国廿一年就可以和人们相见了,现在呢,这本书竟成了焦尾巴狗,不知那天才能把它续起来。”[2]87不止作品遭殃,庐隐身居离战场不远的租界,铺天盖地的战时报道和紧张的战争氛围对她的写作也造成极大的冲击。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庐隐只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豆腐店的老板》,小说发表在1932年4月的《读书杂志》。其后庐隐1932年6月15日在孙福熙主编的上海《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登有一篇短文《自白》:“近来对于人生似乎有了新发现……开始写一个长篇,题目还未曾定,但这次上海的炮声确给了我一个大启发,也许写些蕴蓄于我心灵深处的悲叹与欣喜!”[10]苏雪林在悼念庐隐的文章中也说过:“廿一年暑假返上海……她那时正写一本淞沪血战故事,布满蝇头细字的原稿,一张张摆在写字台上,为了匆忙未及细阅。”[11]
从历史背景看,庐隐创作《火焰》无疑是受到了1930年代民族情绪的感染,但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究竟给庐隐的创作观念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庐隐的民族主义立场是跟随时代情绪一时兴起还是立场的根本转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庐隐创作《火焰》之前的写作经历说起。
茅盾曾形容庐隐的创作就像“‘五四’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停滞了”,在“‘五四’初期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动分子。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时候,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的,《海滨故人》集子里牵头的七个短篇小说就表示了那时的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1]。1925年,庐隐的第一任丈夫郭梦良患伤寒去世,此后几年庐隐带着女儿四处奔波,以教书、编辑为生。庐隐称这一时期的作品渲染着更深的伤感,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灵海潮汐》。1928年,庐隐搜集一年来的作品编成散文小说集《曼丽》,她在自序中称:“其中共有十九篇作品,大半都是最近四五个月出产的,是在我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自然光芒微弱!”《曼丽》中昙花一现了诸如《房东》这样的新题材,但大部分作品仍是庐隐悲哀自怜的延伸。随后庐隐的好友石评梅与待她很好的大哥相继去世,庐隐称自己“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一场大病痊愈后,庐隐这一时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归雁》《云鸥请书集》和《象牙戒指》的题材又回到自己友情和爱情的“小阁楼”。茅盾形容道:“庐隐她只在她那‘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以后,她就不曾再打定主意想要出来,她至多不过在门缝里张望一眼。”[1]虽然茅盾的评论带有一定的政治立场,但他的描述基本与庐隐的创作经历相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1920年到1931年这十二年的写作生涯中,庐隐的大多作品仍是其作为女性个体的自我表达,记录着作家作为“五四”时期新女性真实经历的困境。王富仁曾这样评价庐隐:“庐隐在传统的封建家庭里,没有得到象冰心那样多的父爱和母爱,这决定了她对封建传统没有那么多的留恋,对封建意识和传统的审美意识没有那么多的偏爱……她追求着自我的和女性的个性解放,又本能地惊惧于男性的个性解放,因为男性个性意识的片面增长恰恰会给得不到充分个性解放的妇女带来严重的威胁。这种种复杂的意识,庐隐都坦露地表白了出来。”[12]
在创作《火焰》前,庐隐并不是没有想要转变写作风格的意愿,但“五四启蒙运动塑造了新一代女性的心灵,而新文化的个人主义话语,却令她们无法完全表达自己”[13]。庐隐从小被家人厌恶、歧视,第一段婚姻嫁给有妇之夫郭梦良,第二段婚姻则是忍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嫁给比她小9岁的李唯建。庐隐好友石评梅的两次婚姻则都嫁给有妇之夫。正是因为经历过现实中女性解放的种种挫折,庐隐才选择坚持写下女性的痛苦和悲哀,而这也是她作为新一代女性所遭受的真实的痛苦与悲哀。有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艰难处境,使得庐隐女性性别意识的表达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尤其是她对‘五四’主流话语传统的质疑与反思,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体会和对女性现实出路的艰难求索。庐隐的叙事彻底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为妇女解放所编撰的一系列女性神话,代表了女性写作之初女作家自我性别立场的寻找与确立,即以怀疑的目光审视并追寻女性的出路,深刻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男权秩序的现实社会里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14]庐隐作为“五四”觉醒的女作家,从创作伊始到去世前都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出路,这尤体现在她的杂文创作上,如《“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1920年)、《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1924年)、《妇女的平民教育》(1927年)、《妇女生活的改善》(1930年)、《小小的呐喊》(1932年)、《今后妇女的出路》(1933年)等文章,都表明庐隐从未放弃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如果处在一个和平年代,实现女性解放无疑是有希望的,但处于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尤其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战争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让庐隐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先实现民族解放。值得注意的是,《豆腐店的老板》是庐隐在淞沪战争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以第三人称讲述了豆腐店老板在战争中的经历,赞颂了普通百姓募捐物资的爱国精神。上海百姓自发募捐支援十九路军的行为,让庐隐看到了启蒙的可能与希望。而从文本出发,《豆腐店的老板》与《火焰》两部小说中罕见地几乎没有出现女性角色。《豆腐店的老板》中,女性只作为战争的遇难者出现,而《火焰》中,除战争中遇害的妇女外,只有两个未出场的女性角色占了寥寥几次笔墨:远在家乡的母亲和未婚妻。二者形象只出现在信件和陈宣的回忆中。庐隐有意避开女性角色的描写,正是因为在原始野蛮、厮杀拼力气的战争中,女性永远是被压迫的受害者。旷新年指出:“中国现代的各种‘解放’,不论是个人解放、妇女解放,还是阶级解放,都与民族解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个人并不是凭空地获得解放,个人并不是被个人所解放,而是被国家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砸碎家族的枷锁,最终是为了将个人组织到国家的现代结构之中去。”[15]庐隐也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写完《象牙戒指》后,创作风格发生了大转变:
在这个大转变之后,我居然跳出了悲哀的苦海。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2]97-98。
庐隐的《一个情妇的日记》结尾,美娟面对爱而不得的仲谦所寻得的解决方法为“我要完成至上的爱,不只爱仲谦,更应当爱我的祖国!”[16]351932年之后,庐隐增加了针砭时弊的杂文创作,发表了大量尖锐讽刺的作品,如《灾还不够》《屈伸自如》《监守自盗》等等,积极参与时政时事。李唯建评价庐隐这一时期作品已“由酣恣多情的作风一变而为客观的分析的写实的了”[16]146。
四、结语
《火焰》是庐隐创作风格和思想立场的一次重要转向,也是她决心走出“海滨故人小屋子”的标志之作。这部以战争纪实为基础的自叙传小说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激流汹涌的民族主义时代情绪,作品中多处表现战争纪实的细节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庐隐强烈地意识到,民族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故文中构建的矛盾的民族主义立场正是庐隐曲线实现女性解放的策略选择。诚然,《火焰》的艺术并不那么成熟,但并不乏许多同时代战争文学甚至后来许多战争小说都未包含的闪光点,如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等。因此,《火焰》在庐隐的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在战争文学史和史料方面的价值,也有待被再次发掘与重估。
注释:
① 信件由陆锡祯载于《华安》杂志1934年第8期,其内容为:“承蒙惠顾失迎,甚歉!兹由邮寄上拙作《火焰》十章,请查找妥为保存为感,盖敝处无副稿也。其余六章稍迟当续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