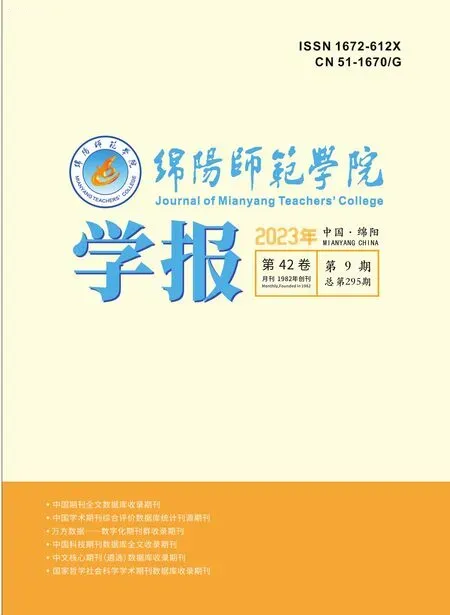明代王门学者王宗沐的文学观
——文道合一
杜 梅
(1.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241;2.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
王宗沐(1523—1591),字新甫,号敬所,浙江临海人,师事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据后人《刻敬所王先生文集序》评价:“先生(王宗沐)自束发登朝,即以古名臣自期,居比部则精研狱律,称名法家,巳督学江岳粤,则倡道东南称名师,飏历藩臬。凡一切条布具为世程,称名方岳。”[1]2可知,他早年立志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人。王宗沐曾授刑部主事,擢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后任右副都御史、漕运总督,疏请复海运,未果。王宗沐一生致力于传播阳明心学,既注重事功实践,也重视体悟个人心性,故为官任上政绩卓著。王宗沐著作颇丰,内容涉及经学、理学、文学、史学、水利、海运等,多具事功之用,如《漕抚奏疏》十卷,见《千顷堂书目》,今天一阁有藏本;《海运详考》一卷、《海运志》二卷,今天一阁有藏本;《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见《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天一阁书目》。今有旧刻本,收录于《四库未收》第1辑。另外,据史志文献所考,他还刊刻《朱子大全私钞》十二卷、《象山粹言》六卷,撰写《攖宁语录》、《敬所续集》八卷、《探匏集》、《十八史略》、《尼山随笔》、《三镇图说》等等,但今皆未见。总之,王宗沐具有深厚的学养和极高的才情,这对其政治仕途、著述内容有引导和指导作用。
王宗沐《吉阳先生文集序》言:“夫疲精苦力之士,仅能工其一事,而李白、杜甫振古之豪才,顾独工于诗而不能兼于序记。而其能者,又往往不合于道,而不可以为教,其为事若是乎。……夫所谓文者,不外于道。所谓道者,不出于心。徒以其气之所极为才,而以其资之所近者为体,不根于心,则不合于道,即有合焉,亦不过一时悲欢,感遇之适。”[1]35首先,王宗沐明确指出人们在创作过程中很难诸体兼备,即使能够诸体兼善,但难以使诗文合于道。他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诗文不合于道,无法发挥教化之用。因为诗文内容应合于道,甚至可以说“文”的本质即为道。其次,他对创作主体提出明确要求,即强调创作主体的心性也应合于道,才可保证创作主体与创作实践相统一。王宗沐所言的“道”,是指符合社会秩序规范之道,属于儒家正统思想体系。王宗沐力图通过文章维护儒家思想体系,复归“仁”“爱”之旨,这一观点影响着王宗沐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
一、文道观之成因
(一)继承阳明先生“修辞立诚”的文学思想
明初,承接并尊崇程朱理学思想。至成、弘之际,阳明心学思想撼动了程朱理学的重要地位。致良知强调心性的纯然状态和良知灵明的自发性,认为心是万物之主导,强调“去私存理”,证悟得“仁体”。王宗沐的思想学术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他在《阳明先生图谱序》中表达了对阳明先生的钦慕之情,曰:“余少慕先生,十四岁游会稽而先生没。两官先生旧游之地,凡事先生者,皆问而得槩焉。”[1]31
王宗沐主动、自觉地追随阳明先生之文风,《刻传习录序》:“先生(王阳明)顾其始亦尝词章而博物矣,辗转抵触,多方讨究,粧缀于平时者,辨艺华藻,似复可恃。至于变故当前,流离生死,无复出路,旁视莫倚,而向之有余者。茫然不可得力,于是知不息之体……事功文词,固其照中之隙光也。”[1]32-33阳明先生早年好词章,曾将渊博的学识和充沛的精力放于辞章,当阳明先生历经政治低潮,在生死边缘悟道后,其文学思想发生转变。他批判溺于文辞的创作风气,故曰:“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2]37并对创作主体提出具体要求,即要求创作主体正心诚意,因为辞诚乃是致知的具体工夫,亦是成圣成贤的基本表现。
王阳明曰:“门人作文送友行,问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费心思,坐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又作诗送人。先生看诗毕,谓曰:‘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2]111王阳明所言的“修辞立诚”可追溯至宋代程颢,他曾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却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业处。”[3]51其实质即是探讨文与道的关系,认为质实之文才可传道。王阳明认为若因作文致使心体浮躁,即使创作出辞章,那所作诗文也并不值得称颂。若辞章之旨与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不一致,这也不符合修辞立诚的观点。
(二)坚守阳明先生的心学思想
《传习录》是集中体现阳明学术精神的重要文献。最初《传习录》仅一卷,是正德七年(1512)由阳明先生的高足徐爱将先生语录内容进行收集和整理而进行刊刻。正德十三年(1518),薛侃在徐爱初刻《传习录》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自己与陆澄手录的内容。薛侃将徐爱、陆澄及自己所录三卷合为一册,后人称该本为《传习录》(薛本),即今通行本上卷和中卷。至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任绍兴知府,他以薛本为基础刊刻《传习录》,以薛本为上册,以选编《答徐成之》等九篇阳明论学书信为下册,两册汇刻成为《传习录》(南本),确定了《传习录》“语录+论学书”的编排模式。自南大吉《传习录》(南本)刊刻以来,阳明弟子纷纷刻印《传习录》。嘉靖七年(1528),阳明先生去世后,钱德洪与同门不断增订、精编阳明语录,力图使各版本《传习录》说法统一,有助于阳明思想“归一”。钱德洪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湖北刻《传习录》。
王宗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至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在江西任上刊刻《传习录》。他在钱德洪版本基础之上刻印《传习录》,合续本凡十一卷。他之所以向前辈一样积极热衷于刊刻《传习录》,原因有二:
一方面,江西乃阳明先生“提戈讲道处”,他以阳明讲学于江西却无刊本甚为遗憾,正如他于《传习录序》所言:“《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而江右实先生提戈讲道处,独缺焉。”[1]32因此他在江西任上,借职务之便立马组织修缮阳明祠堂、积极刊刻《传习录》,传播阳明心学。他历任江西按察副使、江西参政、江西按察使,后升江西右布政使,掌一省之政令与财赋之事,这为他组织刊刻《传习录》提供了职务之便。《传习录》刻成后置于学宫,供众生阅览传播[1]32。
另一方面,在传播阳明心学过程中,出现了偏离阳明旨归的讹误情况,其原因是学术思想借助语言形式进行传达易于产生偏差,故阳明后学在传达阳明心学过程中也难免出现许多讹误。王宗沐意识到上述问题,在刊刻《传习录》过程中是极为谨慎、细致的,正如他于《与钱绪山先生》言:“《传习录》就梓已完,讹误未别,尚须役便。徐生特遣送阳明先生像去,谨此附问,驽身未鞭,进退寸尺,成物切励,本公素旨,幸有以教之。”[1]229他力图通过致力于刊刻《传习录》来还原并传承阳明心学旨归。故王宗沐《刻传习录序》曰:“先生之所以得者,岂尽于是耶?嗣后一传,百讹师心,即圣为虚无漭荡之论,不可穷诘,内以驰其玄莫之见。而外以逃其践履之失。……今袭先生之语以求入,即句句不爽,尤之无当于心,而况不能无失乎!心不息,则万古如一日;心不息,则万人如一人。”[1]32-33有的阳明弟子一味溺于文辞,而未能真正领会阳明心学之旨,从而曲解了阳明旨归,误传了阳明心学之旨。因此,王宗沐在刊刻《传习录》的过程中对文字表达方面表现得尤为谨慎,力图客观地传递阳明心学思想。王宗沐组织刊刻《传习录》的背景渊源和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他思考如何处理文与道之关系,影响了他的文道观的确立和定型。
二、文道观之表现
(一)著述内容:于人伦庶物中述道
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泰和人,师从阳明先生。据《四库全书存目》可知,著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南野文选》四卷。欧阳德作为王阳明高足,坚守并传承师说。阳明先生曰:“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4]8欧阳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哲学范畴的“致知”延伸至文学观念领域,他认为文学创作亦属于人伦庶物、日用之间的范畴,正如其《答徐少湖·二》曰:“今之志于学者,往往多谈繁说,而于真心实地上,未能着实磨砺锻炼,去偏祛蔽,故施为往往乖戾。”[5]22人们应于日常言行处磨练心性、克服私欲,然而这往往被当时人忽视。他进一步指出修撰文字亦是在磨练心性,修省言辞是致良知功夫论和本体论的统一结合,修省言辞即是致良知的工夫。故曰:“则凡言语文字,莫非实理;知识见闻,莫非实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带水也。”[5]61所谓“实理”“实得”就是源自于个人体验的实闻和实见,这些实闻和实见皆源于日用人伦,若将日用人伦庶物之事的反思和感悟落实于文辞,才能避免创作沾泥带水的空洞之文。
王宗沐作为欧阳德弟子,继承了欧阳德将良知与日常人伦庶物相结合的文学观点。王宗沐于《南野先生文集序》言:“南野先生固王氏高第,夙抱异质,从其师说而守之,以信本则自得,而非一时之意象,其诲人虽不出《中庸》之慎独、《论语》之改过,流转对治,……其幽远深微,而未尝遗其日用。继往开来,囊括万物。其言明白深粹,受之无不得力。而无一说自主之,无所不行,而皆足以垂于后世。予谓先生之教之书,则固不贰于孔子之家法,其斯以为可传也。”[1]34-35因此,王宗沐的许多文章皆结构规律,文章开头多由自然风景、具体日常物象等起兴,然后展开对儒家思想的探求和思考,文章结尾再次回到当时社会和个人生活中,阐发个人继承圣人之志、坚守儒家之道的决心,或表达个人情志和胸襟抱负。如《乾乾亭记》,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宗沐于广西任上与众人一同拜谒靖江王,众人留宴于靖江王府的藏经楼。朱元璋为巩固明朝统治,采取了“众建宗亲以藩王宗”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将诸位王子封为各地藩王。朱元璋侄孙朱守谦封为第一代靖江王,封地位于广西,而王宗沐拜谒的是第九任靖江王朱任昌(康僖王)。在文献记载中,朱任昌袭爵在位共七年,爱游山玩水,后人评价其较为平凡。不过透过王宗沐这篇文章,却可展现了这位郡王更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宴会期间,王宗沐留意到宴席房间东边的小径,沿着小径穿过树林,他发现一座小亭子,小亭子“上覆以茅,不彩不斫,环以众木,居之幽然,盖若山林焉”[1]162。靖江王见王宗沐十分欣赏这处亭子的隐秘幽静,于是命王宗沐为这个小亭子作文记述。但王宗沐十分谦虚,未敢为之撰述。居一年后,王宗沐又同众人再次拜谒靖江王,而靖江王再次请王宗沐为文记之,并且对王宗沐说:“‘予未尝不终日乾乾也。’某因拜而进曰:‘忆王之东偏亭,以为独不贵势也,乃今则进于道矣。’夫终日乾乾,周公系乾九三爻词后之言者,皆以为《易》之理,而不知此公后之心也。”[1]163当王宗沐听到靖江王引用周公之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而为亭子命名,他体察到靖江王继承周公圣心,心忧天下之精神,于是欣然为文。一方面,他在《乾乾亭记》一文中对周公的崇敬,曰:“盖抚盈成之运者,有敝坏之防,居极隆之势者,有降殄之虑。故尝观之成王继立,悲彼家难,幼君天下,稼穑未知,且将有侈心焉,公所为陈《无逸》也。二叔不谅其精白之心,流言以间上下之交,东征绥辑,犹顽民是或惧乱,公所为赋《鸱鹗》也。……是其忧劳之心,虽非疑忌,祸福之间而公所以任天下之重,继绝学、开太平,以心王室者,固有不容自遑者矣。盖《易》曰‘终日乾乾’,则公之心夫,则公之心夫!”[1]163另一方面,文章末尾赞美靖江王以天下为重,继承先人之志。文章以记述靖江王府内东边朴素的小亭子起兴,引发出他对圣贤之道的真切体悟,对辅佐君王的贤者的崇敬之情。文章通过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自然而然地传达圣贤之道,并且能做到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在普通日常事物中体察和传承圣人之志,并非一味抒发个人情绪和私欲。因此,文章能够呈现出述道、传道的一面。
(二)著述结构:融景、情、理一体而述道
王宗沐所撰《敬所王先生文集》三十卷是本文的基础文献研究资料,卷一至卷十收录有序、记、柬;卷十一至卷十四为诗歌;卷十五至卷二十三收录有论、碑、赋、说、传、策问、祭文、行状、墓表、讲义、奏疏、恩疏;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收录有杂著;卷二十七至卷三十收录有公移。尽管,明代的文体样式已完备,各种文体近六十种,不过王宗沐文集的文章篇目多于诗歌,其中所载文章多以序、记、柬为主,赋、传、说、策问、行状、墓表、公移次之。
王宗沐的文章擅长将议论、抒情和传道熔铸为一体。即使是游记体之文,他所撰写出的艺术性高于普通涉笔成趣的小品文。他能够协调处理好文章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选择适于传道的文体形式而著述,从而达到经世致用之目的。王宗沐的游记体之文不仅细致地记述游玩的过程、游玩之地的景色细节,还善于勾连历史、前代圣人等,其情感融入于景色,达到情景融合、情理融合的境界,富有情趣和哲理意味。
王宗沐早就听说过罗浮山胜景之美,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冬公务闲暇之余登上罗浮山。《游罗浮山记》:“日亥,抵山下冲虚观,道士皆惊有官长来,鸣钟鼓,出迎入。坐定则既秉烛月东出,步行殿上转拜葛稚川仙翁祠。见太白在西,光芒逼南斗,与月争明,踌躇久之。出视王简亭,景泰中以王简埋于殿前,筑亭其山上……出大门,则人静声寂,池光漾沉。而门西,诸山岚在树中哄哄若涛鸣,时杂远村鸡犬声,始觉尘世隔。还坐室中,宦虑稍稍尽矣。”[1]171王宗沐善于合理架构立体空间来描摹景色,将其游玩的时间点和路线描述得十分精细和具体,内容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空间感。他将视觉感官和听觉感官相融合,呈现出月夜游玩山林的空寂画面。此外,他也透露出身处山林的心境和感受,认为在深林之中心境宁静,洒脱自由,公务的焦虑感似乎尽除。透过对这些山林景物的描写,可以感受到王宗沐希望远离尘世、忘怀于山林的愿望,因为处深林之中心境宁静,洒脱自由,能够减轻公务的焦虑感。然而文章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传达隐逸愿望,而是于文章结尾之处升华主旨,转而追溯先贤孔子、大儒罗(罗从彦)李(李侗)。宋代理学家杨时(1053—1135,二程一传弟子)、罗从彦(1072—1135,二程二传弟子)、李侗(1093—1163,二程三传弟子)传至朱熹。孔子、罗从彦、李侗都不曾为官,但都致力于授学传道,对后人思想精神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此,王宗沐的文章能够将情、景和理熔铸一体,通过情景的感发而阐发出理,即向先贤大儒表达仰慕之情,从而隐晦地传达其个人继承圣人、述道传理的决心。
三、文道观之评定
(一)上承欧阳修道胜文至的文学思想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与唐荆川先生》:“今征书甫下,缙绅动色相庆。盖不惟恬澹之踪,可以抵障颓澜,而石画之才且当扶植危构。自宋氏以来,儒者受不适于用之诟久矣。门下天挺命世,昭然建立,一为昭雪,非百年快睹,吾道将兴耶?惟门下勉,惟社稷加强饭也。”[1]231王宗沐除了赞扬唐顺之的治世之才,还肯定其文学主张。因为,唐顺之早年推崇先秦两汉文章,后因受阳明心学思想之影响而发生转向,强调文章要直抒胸臆,反对一味拟古,主张以“本色”示人,力图创作思想内容充实、风格简雅之文。而这一文学思想与宋代文豪欧阳修的文学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观点,并且有所创新和发展。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6]134欧阳修在这封信中论证了文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品德高尚、心中有“道”的人,才能创作出好的文章。韩愈倡导圣贤之道,彰显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而欧阳修发展了韩愈所言之“道”,将道落实于社会现实,关注百姓民生,应因真情所感而创作,不可为文而文,应重道而为文,文辞应质朴充实,形成了道胜文至的文学主张。明人归有光早意识到这一点,故《欧阳文忠公文选》评语卷三云“文本于道,道乃生文,其识深而论却”[7]1887,即是指欧阳修强调文道统一。
王宗沐同唐顺之一样,继承唐宋文章之遗风,有师法欧阳修的文学倾向。王宗沐的多篇文章也是有感于人伦庶物而展开论述的,文章内容落实于世俗生活,具有一定教化功用,协调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从而发挥文字传道的功用,这与欧阳修道胜文至的文学观点相类似。正如后人《刻敬所王先生文集序》评价王宗沐:“先生(王宗沐)之于道,可谓深矣,故其宣诸制作、藻泽仁义、经术,曲中事理,委纡汪洋,透其意之所之,而止神采所旨,冲然色相。蹊径之外,殆镕匠欧阳氏法,而上逼贾、董,所谓至理,辞达超乘而上,非邪?是足以传矣。”[1]2后人的点评是比较中肯的,一方面明确指出王宗沐继承了欧阳修的文章文法。所谓欧阳修的文章文法,即是指诗文内容涉及百姓之民生日用。这可追溯至汉代贾谊、董仲舒,他们心忧百姓,期盼君主实行仁政,即以传达敬天爱民之志为文章内容;另一方面,揭示出王宗沐文章风格与欧阳修、先秦两汉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追求说理透辟、直抒胸臆、晓畅自然,即呈现出质实的文章风格。
即使是传递心学思想一类的文章,王宗沐的文字是文从字顺、不事雕琢的,简洁、明了地传达出心学思想。王宗沐于《刻象山粹言序》曰:“则文字训觥从其烨,然譬之古人,画蛇添足,而今更为之鳞爪也。粉饰弥工,去真弥远。凡若是者,质之于禅,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谓,五古不如荑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非吾党之过而谁执其咎乎?”[1]27他批判当时的人们热衷雕饰文辞之风,认为雕饰文字实为画蛇添足,只会造成“粉饰弥工,去真弥远”之弊病。这里所谓的“真”,即是指抒发人之本心、人之本体、纯然之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直抒胸臆、说理透辟,从而呈现出文风晓畅之特征。故笔者认为,王宗沐同唐宋派一样,同样推崇并效仿欧阳修之文风。
(二)下启“后七子”文道质实的文学观点
明代文坛最早扛起文学复古大旗的是“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文学复古,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他们力图变革台阁体华靡卑弱的文风。明中后期以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后七子”继承了明初文人及“前七子”的创作主张,他们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8]102尽管“前后七子”主要是诗歌改革的流派,但是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后人有重要影响。
王宗沐早年与“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等人结识,参与谢榛、吴维岳、李先芳、李攀龙、袁履善等人的诗社,他们唱和交游,以诗文相友善,王宗沐与李攀龙交往甚密。《与李沧溟郎中》:“吾兄专笃之志,且又处省中久,时取兄旧作及相赠遗者,读之一字一法,……沛若河海,秋高水落,涯涘立出,其行于世,宁能自已乎?”[1]194王宗沐十分赞赏李攀龙的文采,肯定并支持“前后七子”复归文道、情理融合的创作主张。
王宗沐更是直接肯定了传道说理的文学主张和质实的文风。正如他《象山集序》言:“心之体也,见庙与墓而兴者,应也。体无所不具,则无所不感。无所不感,则无所不应,因其应而为之文,于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仪,仪立而其心达,而仪非心也。此所以为圣人之学也。”[1]24可见,王宗沐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包,当心体受外物之影响而有所感应,心体受到感应后则会激发出创作文章的动力。因此王宗沐认为创作文章功用有二:一是抒发喜怒哀乐之情;二是阐明祭祀等仪礼制度,传递圣人之学。所以,王宗沐认为文章的功用主要以传道、教化为主,以抒发人之性情为次。可见,王宗沐“文道合一”的文学本体论思想并未忽视文章的教化功用,即文以载道、文以传道。
后人于《敬所王先生文集序》对王宗沐的评价:“始则刘文成(刘基)、宋文宪(宋濂)并为之,……弘治间敬皇帝右文朝,士大夫竞尚儒术,则比地烨然称盛焉。时王文成(王阳明)起于句余,监刘宋而润色之,遂有阳明子之文,此三先生者,皆用事业显,才可以命世,为帝者师。……文以载道,立言者,不废也。……先生(王宗沐)结发对公车,辄以文名震世,即一变至道,曾不以其故废所就业。”[1]4明初学者刘基和宋濂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如以刘基为首的浙东学派,学术思想深受理学传统的金华学派之影响[9],他们凭借才能辅佐君王治国。至明中期,王阳明反思程朱理学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流弊,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力图通过转换学术思想来巩固儒家传统社会秩序。刘基、宋濂、王阳明三人不仅在中国学术思想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具有极高文学素养。后人将王宗沐与这三位学者相提并论的目的是称颂王宗沐同样以道自任,有命世之才,极富文学才华。尽管此说法有序体文章的夸饰之嫌,但据王宗沐文集所载文章来看,确实能看出其文章风貌与三先生有相似之处:文章既应与日常事物结合,又应复归儒家道统,以反映社会现实作为文章内容,以情景交融作为表现手法来传递圣人之道,从而形成内容充实、说理简明的文章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王宗沐的文章寄情于景时不似李白那么直白,而是更接近杜甫那样沉郁的风格,他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对自己施以克制力和约束力,其原因在于他已将礼制内化于心,因此在抒发情感时也比较克制和内敛,符合儒家的中庸思想。可见,王宗沐虽不自觉地身处于文学流派的不断变革历程之中,但据说理观点的看法和实践创作来看,他不同于纯粹的文学家,而是基于儒家思想的立场来思考文与道的关系、处理议论方式与议论内容的关系,因此形成了质实的文章风格。
从文学流派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王宗沐的文道观呈现出历史特性:一方面,他继承唐宋派文以载道的创作倾向,又开启了“后七子”文道质实的风格特点;另一方面,他重视议论抒情、笔法简洁生动的文笔特色,可将其视为晚明小品文的先行风格。
四、余论
本文透过王宗沐可以看窥探到,阳明后学既是理学家,也是明代中后期文学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在统一的学术思想影响下,其文学思想观点也具有一定趋同性。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后学也是明代文学各流派演进过程中的一派力量,甚至是某一时间段的主要参与力量或发挥着引导作用。据本文研究可推测出,阳明后学群体的文章创作实践为唐宋派向“后七子”、晚明小品文的过渡架起了一道桥梁。至于这座桥梁是如何搭建而成、如何发挥作用、实际影响程度是如何的,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阳明后学个案研究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