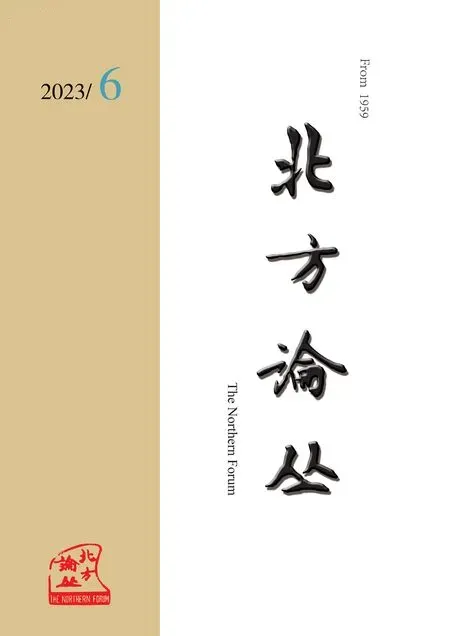论红学是文艺学
丁广惠
《红楼梦》是什么?红学研究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科?这是一个问题吗?从脂砚斋到今天的两个世纪中,红学已经历了前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众多的不同流派和学科分支,具有前人所未掌握的大量的宝贵文献和资料,拥有一支由专家学者和爱好者组成的庞大的研究队伍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日益发展的具有国际性质的显学。在红学研究如此兴盛繁荣的今天,《红楼梦》是什么,红学研究的性质、内容及其所属学科是什么,还会成为一个问题吗?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却在红学论坛上真实地出现了。《红楼梦》是什么?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常识得不能再常识的问题。
一、《红楼梦》是文学作品,不是秘电码
《红楼梦》是小说,是长篇小说,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但是,在漫长的红学发展史中,有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和数量众多的人,并没把《红楼梦》当文学作品。他们或者把它当作隐私文学,而考证它究竟影射明珠、和绅,还是顺治皇帝;或者把它当成政治纬书和《推背图》,索隐其中隐藏的满汉种族对立,康雍乾三朝间的宫廷斗争;或者把它当成玄理图书,勾索其中的卦文易理……直到最近,还有人直截了当地把它当作类似秘电码的东西去破解秘码,还有人说它是北大未名湖一带的寻宝图。当然没有谁当真拿着《红楼梦》跑北京大学去寻宝。
这些论者,都没有把《红楼梦》当作小说去研究,《红楼梦》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神秘,它和《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一样,都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上述论者赋予的那些功能和特点。
这些论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摄其要,是考证和索隐;溯其源,分别承袭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研究方法。既然《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不是“经”,就应该顺理成章得出以下结论:不应该以经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红楼梦》,而应该按文学作品的特点去研究《红楼梦》。
二、文学作品却用了经学的研究方法
不管论者承不承认、自不自觉,他们的研究方法来自经学,而且红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和经学挂钩。

不仅形式源于经学,具体的研究方法,旧红学之索隐,新红学之考证,分别承袭了经学今文学派、古文学派的研究方法。溯其源,还和秦皇汉武扯上关系。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书殆尽。汉兴,叔孙通率儒生为刘邦制定朝仪,遂尊儒术并访经书。济南伏胜,将授《尚书》,汉文帝时,伏胜已八十多岁,乃派晁错前往受经。由伏胜女儿口授,晁错用当时文字汉隶记录,是谓今文《尚书》[2]3603。
景帝时,鲁恭王刘馀扩建宅院拆毁孔子住宅,从墙壁中得到《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经书,都是用先秦文字篆文书写的,是谓古文经书[2]2419。后来河间王刘德又蒐集呈献一批,也是古文。至汉武帝,朝廷设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处于在野地位。今文经学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为大一统观念服务,并杂以“天人感应”。至两汉之交,又杂以谶纬之学。至东汉,逐渐衰落,清末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其余绪。旧红学索隐派亦宗微言大义,从《红楼梦》“微言”中,蔡元培揭示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得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3]的“大义”。寿鹏飞则揭示出“盖是书所隐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的“‘康熙季年宫闱秘史’”[4]的“大义”。而具体索隐某事则使用与今文经学合流的谶纬之学的手法,即文字笔画拆合法和同义相训法,如蔡元培说王熙凤影余国柱,说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囯”,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相连也[3]。这和汉献帝时京都童谣表达方法相同:“‘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青青草,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2]3284千里草(草字头)合起来为董;十日卜,合起来为卓,这是拆字法。青青训暴盛,谁为暴盛,只有权倾朝野的董卓可当。这是词义转训法。
蔡先生也使用此法,它先训红为朱,即红与朱都是红色同义相训。朱又是姓,朱姓王朝是明朝,而明朝又是汉人政权,这样辗转相训,得出书中“红”字影射汉族的结论。他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又说:“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馀也。”“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完全是今文经学支流谶纬之学的研究方法。
古文经学则认为经籍为上古遗留的典章文献,以训释字词、考证文物典故来解读经文。至东汉马融、郑玄,成绩斐然,取代今文经学成为学术主流。至清代,承其文风,形成乾嘉朴学。在考据学术风气影响下,一本《红楼梦》,有人考证出是写“明珠家事”或“纳兰成德家事”(1)陈康祺《燕下乡脞录》,钱静芳《红楼梦考》等。,有人考证是写“顺治帝与董小宛事”[5]……但手法亦用“影射”,于索隐无异。至胡适,始将红学考据从索隐派独立出来,形成新红学学派。他信奉杜威实用主义,但他的治学方法,“大胆怀疑”是来源于赫胥离的进化论,而“小心求证”却是乾嘉朴学论必有据的治学原则。他挖掘收集整理了一批关于《红楼梦》的材料,考证了曹雪芹由盛到衰的家世、曹雪芹晚年的交游和卒于壬午年、后四十年为高鹗所续、甲戌本和庚辰本的考辩等,但却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6]的结论,从而混淆了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与现实中人物的区别,其“将真事隐去”与索隐余绪的“掩盖”说、“障眼法”殊途同归了。
旧红学的索隐,新红学的考证,都如经学家一样,把《红楼梦》当成索隐、考证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去分析和评价。
三、历史没为小说准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文学作品不用文学的研究方法而用经学方法,这是历史的错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地位有关。
小说之兴,其源甚古,考其源流有二:一曰文言,昉自先秦。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先秦小说,自列一家,与先秦诸子并列,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2]1745“说”,学说、道理。“小说”,小道理,而且是稗官——乡长闾长之类小官[7]收集的“道听途说”的文字,其地位与讲大道理的先秦儒家经典、诸子著述是不能相比的。汉代称之谓“残丛小语”。至魏晋南北朝,发展成以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为代表的志怪、志人的笔记小说。至唐宋,小说更为成熟,出现了《古镜记》《柳毅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长恨歌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一批传奇作品。延至宋代,称之为唐宋传奇。至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是文言小说的高峰,其后林纾之作《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金陵秋》,则其末流。二曰白话小说。先秦两汉,口语与书面语一致的。至魏晋,口语发生了变化而书面语仍保持文言,直至清末。但唐宋的寺院和勾栏瓦肆,则以口语讲述经文故事和说书,他们的讲述底本,称为俗讲和话本,俗讲的文字本或称为变文,《舜子至孝变文》《大目莲救母变文》……等开了说唱文学的先河,《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快嘴李翠莲》《碾玉观音》等话本,促进了明代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至清代,《红楼梦》的出现,标志小说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
中国传统小说形式多样,历史悠久,但其地位,特别是白话小说极其低下。论文化层次,它属于下层文化。论社会功能,他不如经书政论律诗可以进入科举考试而使士子飞黄腾达,只能作为茶余饭后消遣之用。在文学范畴里,诗词是高雅的,小说是低俗的,甚至被加以“诲淫诲盗”的罪名而焚毁。
小说的晚熟和社会地位低下,导致它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缺位。孔老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8]2524重视的是诗经,而不是小说。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是指“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9]125,是宏著大论,也没有涉及小说。刘勰《文心雕龙》是最早的古代文论专著,号称“论古今文体”,书中所论,遍及经书、诸子、诗、骚、赋、乐府、史传、论说,甚至包括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等应用文,却没有小说一体。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下的诸多诗话,亦限于诗词的技巧品评鉴赏。及至清代,金圣叹把《水浒传》抬了一下,将其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加《西厢记》而称“六才子书”。在批《水浒传》中,观点触及人物形象问题,他说《水浒》的成功,“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2)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贯华堂课本,第一回前批。。他还注意作品的写作技巧和行文方法,称之为夹叙法、倒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等。继其后者,有毛宗岗之批《三国演义》,张竹坡之批《金瓶梅》,在方法上都未能超越金圣叹。
但是金圣叹的理论只是散见于夹批、回前批的一个个断片,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被董含(3)董含:清华亭人,字阆石,顺治进士,观政吏部,以奏销案被黜。讥为杂乱无章,并未形成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也就是说,直到《红楼梦》问世,中国还没有与之配套的系统的文艺理论,更不要说解读长篇小说的理论了。及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蔡元培先生苍茫四顾,历史并没有为他准备下应手的文艺理论,只好从今文经学那里拿来“微言大义”和索隐方法,从《红楼梦》中解读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目的服务。与其效仿者形成旧红学派。蔡先生索隐的“三推法”被新红学的主帅胡适讥为“猜谜”“笨伯”。但他一转身便和古文经学家把经书文本当作考证对象一样,也从文学作品的《红楼梦》中考证出贾宝玉即曹雪芹、《红楼梦》即作者自传的结论。于是新旧红学殊途同归,都陷入经学方法的迷途。
四、按文学作品特点研究《红楼梦》
新旧红学和现代红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告诉读者《红楼梦》写了什么内容,它有什么意义。既然《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是经书,而用经书的研究方法去求索,结论自然南辕北辙。是文学作品就应该按文学作品的特点去研究。和音乐之以旋律节奏,绘画之以色彩线条反映现实一样,文学作品是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现实为特点。恩格斯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462文学作品的中心问题是形象问题。解析《红楼梦》应使用形象分析的方法,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一干人物放在作家所塑造的大到贾史王薛联络有亲的社会、宁荣二府的生活,小到大观园的典型环境中,研究他们的性格的成长过程和人物间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探讨作品思想意义,从而给读者以正确的回答。形象分析应该注意:
第一作者是以具体的真实的形象的言行和生活细节来塑造他的人物形象的,因此《红楼梦》文本是形象分析的唯一根据,而不是研究者猜想与臆断,不需要文本外的任何细节,不需要索隐与考证,文本写了什么就是什么。以秦可卿的艺术形象为例,只要扣紧文本描写,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个养生堂的弃儿,被清寒的郎中秦邦业收为养女,由于她的美丽和教养,成为贾府长重孙媳。她小心处事并对家族的衰败有着清醒的头脑,却有着诸般的不如意,最后因病医治无效而亡。这些都是作品文本中明明表白写着的。至于她因病而死,有张太医的脉象、症状、处方可按,有病势发展的日期可循。如七月开始停经,八月二十日添症候,九月初五左右家塾风波,次日症状转重,九月初六张太医来诊,九月初七凤姐宝玉来探病,从九月初八到十一月三十凤姐最后一次探病并嘱预备后事,年底前某日半夜逝去。除高鹗所续第一百一十回,秦可卿以吊死鬼身份引导鸳鸯自缢外,曹雪芹前八十回无一个具体的细节写过她与曹赦私通和上吊而死。这有文本可查,她不是淫荡的事败自尽的少妇形象。
第二,作家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一个过程,当他对所反映的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时,会不断地修改预定的写作计划和塑造的形象。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是经他手亲自修改了五次。这五次中就有对秦可卿形象的修改。探索这一修改过程,可以解决某些红学家的困惑。
书中明确写的是她因病而逝,为什么太虚幻境册子“画一高楼,上有一美人悬梁自尽”并有“情既相逢必主淫”?还有《好事终》那支曲子?由此可以断定,曹雪芹最初塑造的秦可卿是个淫荡风骚的贵族少妇,并有脂靖本脂批说有“遗簪”“更衣”情节为证。其结局是高楼自缢。但是,现存脂本《石头记》为什么没了这些情节和结局呢。畸笏叟在甲戌本《石头记》第十三回回后批说,是他让曹雪芹删去的。至于删去理由且不要管他,总之淫荡自缢的情节没有了。删去的,就是作者不要的不承认的。连作者都不承认的东西,一些红学研究者还有什么理由说秦可卿因奸败露而自缢呢?修改后的秦可卿就是现在呈现于书中的这个样子,是一个美丽随和头脑清醒的少妇形象。通过给凤姐托梦嘱托置茔产、兴家塾的后事,曹雪芹把她从一个淫荡少奶奶升华为对家族前途有清醒认识的少妇形象,从而与协理宁国府指出五种弊病的凤姐、权理荣国府“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行开源节流专司其职的贾探春、“小惠全大体”的薛宝钗等成为“补天”计划人物形象系列。这些人物的措施都没有挽救大家族的衰败,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比一个荡妇的形象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在中外文学创作中,作家修改人物形象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如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初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形象是个“趣味恶劣……智力非常低下,毫无同情心,卖弄风情”的女人。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对人物和沙俄伦理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定稿时修改成为一个热情、纯正、意志坚定而又有自省能力、鄙视庸俗环境而对爱情热烈追求的女性形象[11],从而使《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性、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他的《复活》中的玛斯洛娃形象,更修改了二十次才定稿[12]591。
既然曹雪芹已经彻底修改了秦可卿的形象,为什么还保留了正册图像判词和《好事终》曲子?甲戌本第一回脂批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则《红楼梦》至曹雪芹逝世还是一个没写完的未定稿,所以书中还有一些当删未删与当补未补之文。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只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句,夹批:“删却!是未删之笔。”瑞珠触柱而亡句的夹批:“补天香楼未删之文。”(4)曹雪芹撰《脂砚斋夹叙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影印平装本。第七十五回,“赏中秋新词得佳谶”,庚辰本回前总批:“缺中秋诗,俟雪芹。”(5)曹雪芹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据北大图书馆藏本缩印平装本。中秋诗和秦可卿的判词、曲子,不比散文易写,须费时日,结果未及补换,雪芹便泪尽而逝了。
以上情况说明,只要承认《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按文学作品的特点、创作规律等研究去探讨,《红楼梦》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根本没有什么不解的谜的存在。
五、拨红学返归文艺学正途
把《红楼梦》看作小说,按小说的特点去研究《红楼梦》,从理论系统说,它属于现代文艺学,最早使用文艺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红楼梦》是“撤头撤尾的悲剧”(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美学上之价值》,收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之《静安文集》。。郑朝宗说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术史上以资产阶级美学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论文”[13],但他的文艺观点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其后则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佩之的《红楼梦新评》,但较为可观的则是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兴起,出现了李希凡、兰翎的《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刘梦溪《红楼梦新论》等一大批论著。文艺学理论为红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他们都十分重视《红楼梦》的本体研究。
新旧红学家虽然辗转于经学研究方法的迷途,但他们毕竟都是功底深厚的学者,和现代红学家们先后在“曹雪芹身世”“《石头记》版本”“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脂砚斋”批语等四个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红楼梦》的本体研究很有帮助。尽管如此,但他们还不是《红楼梦》的主体研究,是准备学科,还要再进一步用到主体研究上才显出它们的重要。而一些红学家就此止步,说这“四大支”就是真正的红学。说用“一般小说学”亦即文艺学去做文本研究和本体研究不是红学,而且“一点也不是”[14]。本来“四大支”都是十分锐利的羽箭,但却盘弓跃马、把玩摩挲而拒绝射向立在辕门的大戟。
红学仅限于“四大支”,还是文艺学?胡经之先生说:“‘红学’,理所当然,应该把《红楼梦》作为文艺学术来研究。对《红楼梦》作历史的、文献学的、考据学的研究,也不能忘记它是文学艺术,时刻以此为前提。‘红学’,它首先是文艺学。”[15]
以文艺学研究《红楼梦》并不排斥“四大支”。文艺学认为,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作家又是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曹雪芹身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生活的变化和世界观形成与发展,也有助于了解作家所处的现实与作品素材的关系。文艺学还认为,艺术创作 是个过程,作者在典型化的过程中对描写的现实认识不断加深,而不断修改原定计划,对“《石头记》版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增删修改情况,“八十回后”和“脂砚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整体构思与规划。“四大支”是我们研究曹雪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重要材料。但在红学文艺学学科体系中,它仍服务于《红楼梦》的本体研究,属于重要的辅助学科。
文艺学的红学以本体研究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方面如社会文化学的研究、传播学的研究。在本体研究内容中,包括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典型环境、情节结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语言特点等的研究。在社会文化学的研究内容中,包括《红楼梦》所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在比较学研究内容中,包括作家比较、作品比较,创作方法比较和其他比较。作家比较包括与中国作家,如和施耐庵、罗贯中等的比较,与外国作家,如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的比较。作品和创作方法比较,包括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及创作方法的比较,如《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水浒》《金瓶梅》,现代的《家》《金粉世家》以及西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比较;《红楼梦》青埂峰、太虚幻境等浪漫主义因素与《西游记》《聊斋志异》《神曲》等作品的比较。传播学的研究,包括各种版本的传抄、整理、在国内外的出版,发行、焚毁,论著查阅目录索引及其历史的研究;包括中外学者对《红楼梦》批评鉴赏历史的研究;包括对文学的续书、仿作等自身门类的影响;包括对戏剧、绘画、民间文学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及其历史的研究等等。流传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
文艺学的红学研究终极目的是阐释《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在这个终极目的统帅下,除了使用形象分析方法外,还可以使用审美心理学、精神分析美学、层次结构学、原型批判学、审美鉴赏等分析方法。根据需要,还可以使用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如研究作者身世和时代背景,采用考据学方法,考辩新发现的文物,则借用金石学、辩伪学的方法。对脂本,则使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方法。对文本词语、典故的注释,则使用训诂学的方法,甚至既用新红学的音训法,如对“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元(原)、迎(应)、探(叹)、惜(息)”的训释,也用旧红学的拆字法,如对“一从二令三人木”的训释。因而文艺学的红学研究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和新旧红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文艺学的红学将红学研究从经学研究的迷途引向正途,极大地拓宽了红学研究的范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现代红学,从而使红学得到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