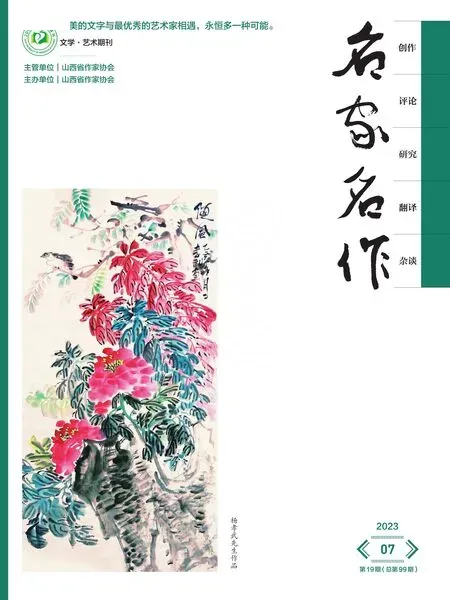叙事技巧与伦理取位
——《我辈孤雏》的叙事学视角探析
张路雨
一、聚焦者、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
小说的叙述情景为班克斯的第一人称叙述,属于斯坦泽尔区分的三种不同叙述情景中的第二种,即“叙述者就是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在班克斯对童年的回忆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其中一种叙述眼光是年幼的班克斯;另一种叙述眼光是当前的班克斯追忆往事的眼光。两种叙述眼光共存造成了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的分离,因此,当班克斯转而以从前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叙述时,就有必要区分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因为两者来自两个不同时期的班克斯。而对比小说开头,班克斯采用其目前的眼光,则没有必要区分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因为这两者统一于作为叙述者目前的“我”。
这种叙述手段可以起到的作用是“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1]。所以,当前的班克斯以成年人的心智和世界观来重新审视幼稚的班克斯的叙述眼光,从而了解当年父母离奇失踪案的真相。
叙事聚焦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于1969年在《修辞格Ⅱ》一文中提出,而美国叙事学家费伦的双重聚焦理论与热奈特的双聚焦、布斯的双重焦点存在本质的区别。费伦的双重聚焦涉及感知,强调叙述者可以作为聚焦者。“费伦的双重聚焦则是指称叙述者的感知与人物感知的同时性。”[2]笔者取费伦的双重聚焦观点,可以理解为小说中有两个聚焦者。这两个聚焦者分别是:目前的班克斯和年幼的班克斯。在小说开头,目前的班克斯既是叙述者又是聚焦者,因为班克斯同时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和叙述者存在。当目前的班克斯观看年幼的班克斯的时候,年幼的班克斯作为人物而不是叙述者,承担故事中聚焦者的角色,而此时追忆往事的班克斯仍然是叙述者。“必须指出的是,当人物聚焦开始时,叙述者聚焦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叙述者聚焦包含了人物聚焦。”[2]因此,双重聚焦在巴克斯开始观看年幼的班克斯的时候就生成了。
二、隐含作者与叙述距离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隐含作者(作者的‘第二自我’)——即便是那种叙述者未被戏剧化的小说,也创造了一个置于场景之后的作者的隐含的化身。”[3]刘月新将文学创作过程与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进行对比:“文学的创作是一种想象力的游戏活动,创作语境的呈现就是游戏情境的建构。创作语境由作者、对象、读者三方构成,同游戏活动中的游戏者、他者、欣赏者一一对应。作家是创作主体,对象是创作客体,读者是作者设想的未来作品的读者,‘隐含作者’在三者的碰撞与征服中逐渐生成。”[4]从以上隐含作者的概念和对比阐释中可得知隐含作者和现实作者的区别。艺术创作过程是由现实作者生成隐含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受到现实个性的局限。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作者能以超脱的视角和态度去个性化,从而达到艺术个性和审美个性。而这个生成的隐含作者还需要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才能转化为现实,才具备艺术生命。总之,隐含作者生成的情景包含三个要素:作者、对象、读者。
此外,艾略特的去个性化理论对理解隐含作者的生成也极具启示意义。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传统对于个人才能生成的作用。由此可知,艺术个性的生成还可以通过对传统的模仿,因为传统是经过历史的洗涤保留下来的,具备极强的艺术生命。对文学传统的揣摩和模仿也能生成隐含作者,从而造成现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分裂,这也是有些艺术家的现实个性与艺术个性有较大差距的原因。
“叙述距离是美学和文艺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来的。叙述距离是小说叙述主体(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是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各种叙事技巧精心创造出来的,它的有效控制是读者审美距离形成的必要前提,所以,距离控制是小说最根本的修辞目的;而陌生化是小说叙述距离的修辞本质。”[5]在小说开头,班克斯作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故事中的人物是有距离的,表现为班克斯自以为融入和适应了伦敦的圈子,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他儿时所说的那种英国化,对父母失踪和童年生活的真相也充满现实主义幻觉,以致他虽然从小到大都有伦理角色意识,却一直都没有完成对自身伦理角色的确立。作者有意拉开叙述距离是出于为主题服务的考量,作者似乎在提醒人们明确认识并且承认自身视角的局限性,挣脱现实主义幻觉的束缚,明确自身伦理判断和承担真正的责任与使命。班克斯迟迟不能确立自身伦理角色的一大原因,就是对当年父母离奇失踪案真相的含混,以及其对童年生活的现实主义幻觉和美化。班克斯只有打破那个束缚自己的童年幻觉,才能肩负起作为儿子的家庭伦理使命,还原当年的真相。故事开始的叙述距离不仅拉大了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距离,还直接影响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这表明叙述距离是审美距离的必要前提。叙述距离随着真相的逐渐揭露而缩小,也同时意味着班克斯的“心结”慢慢解开,认识逐渐接近真正的现实,而不是现实主义幻觉。读者也从一开始的被蒙在鼓里到豁然开朗。久病还需猛药,这味现实的药虽然黑暗、残酷,看似无法接受,但是对于精神失衡、伦理缺位的班克斯来说却是无法避免的。
三、不可靠叙述者
不可靠叙述者的概念是韦恩·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的,布斯的学生詹姆斯·费伦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至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布斯的理论。一是他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或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沿着这三大轴,相应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6]
根据费伦的理论,在事实轴层面上,班克斯对当年发生的故事的叙述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比如,他没有目睹父母在餐厅争吵的场面,而是躲在重门后面通过只言片语推测门后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也只有在我父母按捺不住,音量失控的时候,我才听得见整句话。我约略可以从母亲愤怒的声音里听到义正词严的语气,就像那天早上她对卫生督察说的话一样。”[7]因此,班克斯对当年的叙事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得到的信息是片段的、不完整的,而且还很不确定,充斥着现实主义幻觉。比方他对于这次争吵发生的时间的叙述就很模糊:“我不记得那次在餐厅里的争吵发生在卫生督察来访之前还是之后。”[8]这属于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
在价值轴层面上,文中有一个颇让人意外的角色菲利普叔叔。隐含作者对菲利普叔叔的判断是,此人是引起国共两党分裂的叛徒,是阴险狡诈的“黄蛇”,是出卖班克斯母亲导致班克斯母子悲剧的直接因素。然而,在班克斯追忆当年经历时,他和母亲对这位菲利普的评价则是相当高的:“他基于‘自身与雇主对于中国该如何成长的看法,有极深鸿沟’的理由,辞掉了公司的职务,这是母亲每次描述的用词。等我年纪渐长,知道了这号人物的存在时,他已经在经营一家名为‘圣木’的慈善机构了,宗旨是要改善上海中国人区域的生活条件。”[9]甚至连父亲都没认出菲利普的真面目,对菲利普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这位高贵的菲利普叔叔在关键时刻,其兽性因子克服了其人性因子,铸成大错。由此可见,上述这些对他的判断并非隐含作者对其的价值判断,属于“错误判断”。
在感知轴层面上,班克斯感知的偏差表现在他与亨明斯小姐的关系上,对于自己对亨明斯小姐的爱情的感知他一直不明晰。起初,班克斯以为亨明斯小姐是追名逐利的势力者,一心以攀上名人为人生目标,后来他发现自己对亨明斯小姐的感知并不正确。“我要嫁,就要嫁给真正有所贡献的人。我是指对世人、对于改善世界有贡献的人。这样的抱负有什么不对?我不是来这种地方找名人,克里斯托弗。我是来这里找杰出的人。”[10]后来,班克斯在追寻所谓的使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否认自己对亨明斯小姐的感情,这也为他最终依旧在使命和爱情间选择使命,背弃对爱情的诺言埋下了伏笔。最终,班克斯出于不违背来上海调查真相的使命以及不违背伦理秩序的考量,背叛了对爱情的诺言,导致其最终的伦理悲剧。班克斯没有早点认清自己对亨明斯小姐的心意,低估了爱情的价值导致自己错过爱情,这属于不可靠叙述中的“不充分解读”。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费伦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疏远型”和“拉进型”的二元区分。[11]《我辈孤雏》的不可靠叙述属于“拉进型”不可靠叙述。尽管班克斯在三个轴上都有偏差,但是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他在三个轴上的叙述比起以前的状况体现出某种好的变化,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故事、接近人物。而“疏远型”叙述则相反,随着叙述推进,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距离则是拉大的。
四、人物的伦理选择以及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的影响
在班克斯探查当年真相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的伦理情景发生了变化,随着叙述距离的不断缩小,班克斯的感知逐渐从不靠谱到靠谱。班克斯知悉父亲当年并非死于政治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的冲突中,而是背叛了社会道德伦理和家庭伦理,而他在伦敦获得的身份地位是用母亲的牺牲换来的。成年后的班克斯在面对亨明斯私奔的要求时,也面临和他父亲当年类似的伦理选择,但他选择了调查父母离奇失踪案真相的使命。然而,他的这一伦理选择却没能导向一个好的结果,从这一点看,班克斯的伦理命运是悲剧的。父亲的伦理选择对班克斯母子的悲剧造成的影响是间接的,直接造成班克斯母子悲剧的是导致国共两党分裂的人物“黄蛇”,而他竟然是班克斯小时候敬仰的菲利普叔叔。菲利普叔叔在进行伦理选择时,做出了违背社会道德伦理的极其下流无耻的事情,直接导致了悲剧。
伦理取位是修辞叙事学尤为关注的一个理论维度。费伦的伦理取位观强调了伦理取位的四种伦理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认为四种伦理情境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双重聚焦的影响。尚必武进一步指出:“就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所产生的影响而言, 这四种伦理情境之间既互为因果关系,又互为时序关系。”[12]用这种逻辑关系阐释《我辈孤雏》中的伦理取位可以理解为:随着真相浮出水面,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的伦理情景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作为人物的班克斯的伦理情景发生变化。随着作为叙述者和人物的班克斯的伦理情景发生变化,读者会去有意识地推断隐含作者的伦理情景。笔者在阅读结局时感叹班克斯的伦理悲剧,在考虑他的伦理选择是否值得的同时也对真实作家的经历和意图产生了兴趣。石黑一雄在一次访谈录中是这么解释的:“我碰到过许多缠绕在极端事物中的人,比如写作。如果要他们在使命和家庭之间选择,他们总是选择使命。即使从那些表面上过着平衡的生活的人们身上,我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于是我想,其实他们是幸福的,他们不必选择。”[13]因此,在读者感慨“克里斯托弗·班克斯是不幸的,他的使命感并没有将他引向一个好的结果。而它又是如此强烈,浪费了他的生命”[13]时,隐含作者除了激起读者关于虚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自我判断和伦理取位的思考外,还表达了一种更为开阔和宽容的观点。即隐含作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同的伦理选择,有些人是在没有认清真实自我的情况下牺牲于虚幻的使命感,有些人则是在痛苦的反复挣扎中认清自己的真实内心,但是无论最后他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无论在外人眼里看来是幸或是不幸,对其个体而言都是合理的。笔者对隐含作者意图的猜测体现了读者伦理情境的变化,至于这是不是隐含作者有意安排、有多少接近隐含作者的真实想法则有待探讨。
五、结语
石黑一雄(隐含作者)通过各种叙事技巧的巧妙安排,一步步引导受述者感受这个故事所表现出的道德伦理,并激发受述者的理性思考。随着叙述距离的一步步拉近,读者和叙述者、读者和人物、读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也逐渐缩小。通过叙述距离的变化,作家成功地向读者传达了其价值观念,并通过距离控制促使受述者从情感、理性和审美上更加接近隐含作者,从而对受述者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