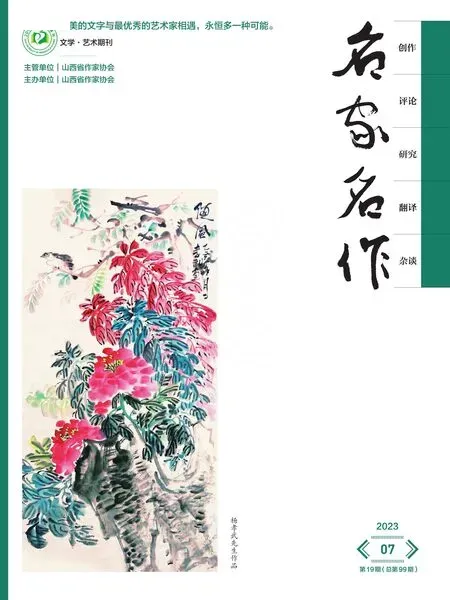生命之思的诗化呈示 现代诗质的多重探寻
——王立世诗歌创作艺术浅析
王 鹰
王立世的诗,晓畅而隽永、简洁而凝练、哲思而深情。读他的诗,就像观一个天然美人姗姗走来,不招摇,不弄姿,清新素雅,招人喜爱,细品则发现胸有沟壑、内心玲珑、深有风骨,绽放出一种绘事后素的惊艳,令人不由得追寻和沉醉。
一、美人在皮: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能不能进入一首诗,首先看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而新诗受人诟病最多的地方往往是语言:要么晦涩、要么直白。新诗自诞生以来,急于与传统割裂,一味求新求怪,于是语言粗鄙化、极度散文化、低级趣味化、文字游戏化、极端诡秘化等现象充斥诗坛。还有一些诗歌写作者弄不清什么是诗,把诗写成了分行散文,使广大读者对诗歌产生了绝望情绪,当代诗歌写作沦为诗歌圈子的自嗨。广大读者缺席的诗歌,是不会有蓬勃生命力的。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又符合大众审美习惯的道路,这是当代诗人一直在探索的课题。而王立世在这一点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并给我们树立起一个标杆。
王立世的诗歌大多短小精练、惜字如金,一般不超过十行。他很少使用繁复的意象,不用长句和形容词堆砌,节奏明快、通俗易懂。
倒立了一生/每天都在感叹/那些容易弯曲的事物——《感叹号》
这首诗明白晓畅、简洁凝练,但语意丰富、回味无穷。“倒立了一生”是一种精神姿态,一生都这样谈何容易,用动态的不平衡先声夺人。“每天都在感叹/那些容易弯曲的事物”,全诗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抒情中蕴含思考。“那些弯曲的事物”象征着背离初心而为名利折腰的人。“感叹”一词用得极妙,抒情主体只是“感叹”,什么也没有言说。“容易弯曲”暗含褒贬,诗人不置一评,把是与非、善与恶的评判留给读者。读者刚刚开始思考,诗歌就戛然而止,言已尽而意无穷。诗人用“倒立”“感叹”“弯曲”三个动词使一个标点符号脱胎换骨,完成了“感叹号”这个意象的重构,激起了读者探求的兴趣。
面对高山/我有点胆怯/不是怕它陡峭/而是怕爬上去了/云里雾里/再也找不到自己——《爬山》
这首诗选取的题材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爬山,但是我们既看不到传统美景的描绘,也没有“一览众山小”的英雄主义情怀。这里的意象不再是传统的“理想”寓意,而是象征着爬上高位而失去了自我。诗人用寻常题材却翻出了和古人完全不同的新意,以纯净、自然、不枝不蔓的语言抵达了内在情绪的深处,将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蕴含其中,完成了寻常生活不寻常的升华,具有隽永的哲学诗意。
早在唐朝的新乐府运动中,白居易就提出了“文章合为诗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他在创作中重视对“俗”的追求,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叙事场景上。“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他强调诗歌语言的质朴通俗、形式的流利通畅。王立世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这一优秀传统,并融汇于现代语言中,不追求视觉效应,不附和辞藻华彩,在诗歌里融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深邃的玄理思考,将凝练、富有张力的语言融合在一起,既告别了内涵的浅白,也远离了表层的晦涩,显示出平和蕴藉的诗歌魅力。
二、美人在意: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
王立世的诗中,最常见的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其实象征在新诗中并不新鲜。在新诗向西方学习之初,就多以西方的象征主义为比附,注重意象本体的象征性和暗示性,追求世界与主体之间的神秘契合。而中国传统的“托物言志”和《诗经》中“兴”的运用,实际上和西方的象征主义相通。诗歌要通俗,但又不能白描、议论,王立世显然是掌握了这一密钥,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得炉火纯青。
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搬走/下地狱时/又有人把它搬回——《这倒霉的梯子》
“梯子”是平凡的事物,搬梯子的场景也常见,但是诗人不说“上房”“上楼”“下房”“下楼”,而是“上天堂”“下地狱”,化平凡为神奇,赋予司空见惯的事物以深邃的诗意。在这里, “梯子”象征了通往高尚/卑鄙的道路:想做一个高尚的人却无路可走,通往卑鄙堕落的途径却摆在眼前。这个社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何其难,而引向罪恶的诱惑却无处不在。诗人对于两个生活场景的瞬间捕捉,目击式的言说、游离在诗歌文本外的客观观照,引发读者对“搬梯子”含义的深层思考,将诗意拓展在诗外。而题目用形容词“倒霉的”形容样子,不仅委婉地抒发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还使“搬梯子”超越了生活场景转化为诗的艺术,在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既对立又联系的艺术空间中扩展了诗歌的张力。
钓鱼者/常常被鱼/钓走/这世界/弄不清/谁在钓谁/一池春水/眼睁睁地看着——《钓鱼》
诗人在体制内工作,对各种贪腐受贿行为比普通人有更深刻的认知。“钓鱼者/常常被鱼/钓走”“这世界/弄不清/谁在钓谁” ,诗歌采用象征的手法,暗示了无法言说的社会思考。“一池春水/眼睁睁地看着”,在唯美的画面中,传达出嘲讽、憎恶等欲说还休的复杂情绪。
他没说一句话/就背着太阳/上山了/在山上/他没觉得自己有多高//他没说一句话/就背着太阳/下山了/在山下/他没觉得自己有多矮——《上山下山》
这首诗极具建筑美,完美地达到了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读起来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富有音乐的美感。“太阳”象征着光明、希望;“上山”象征着年轻时步入社会,从底层打拼,一步步升到了很高的领导位置。“他没说一句话”表明“他”是一个实干笃行的人;“背着太阳”象征着“他”怀揣理想、心向光明、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山上/他没觉得自己有多高”,即使达到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仍然牢记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二节“他没说一句话/就背着太阳/下山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没有任何抱怨,不改本色,继续发光发热。“在山下/他没觉得自己有多矮”,回归平凡,“他”依然自尊自爱,内心坚定从容,人格臻于至善。这首诗诗形整饬、诗意呼应、意象丰富、“兴”味蕴藉,给人以灵魂的温暖和精神的振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辉。
三、美人在骨:知识分子的良心自省
一切文学皆人学,诗歌也不例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作者健全人格的体现。任何诗歌本质都是抒情的,这是诗歌的起源,亦是诗歌创作的动力。郭沫若说:“我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因此,将丰富的现实经验和生命体验共同纳入诗歌的表达,追求“灵肉调和”的现代人格建构,是诗歌不可回避的主题和深层次的开掘。
诗人一直在体制内工作。众所周知,体制内的工作氛围和世俗追求与诗人热情纯真、敏感细腻的气质是相悖的。这种精神追求的背道而驰,时间久了对诗人来说就是一种慢性消耗。而诗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像对抗地心引力一样,他也一直试图与这种状态保持着对抗。
如果我这盏灯突然灭了/我怕灯口生锈/美丽的玻璃碎裂一地/钨丝永远黑下去/灵魂再不能发光发热——《我这盏灯》
“灯”是光明的意象,在这里喻指诗人高尚的人格和理想追求。诗人居安思危,拟想光明熄灭、理想坠地的生存处境,传达出焦虑和忧怖的情感体验,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自觉。
我后悔一生的是/不能从汗水里/晒出更多的盐/不能从骨头里/提取更多的钙/不能从抑郁的心海里/捧出一颗理想主义的太阳——《心迹》
这里的三个意象“汗水里的盐”“骨头里的钙”“心海里的太阳”具有同一指向性——都是奉献社会、济世安民。这些意象连续出现,相互呼应、互相凝聚,形成一种律动的诗情,承载着诗人遗憾、悔恨的心灵自省。这首诗虽然是直抒胸臆,但是在象征的修辞肌理之中,诗意层层推进,达致精神的净化和提升。
有人说我病得不轻/不要紧,这病不影响/我在尘世活着/不要命,只要/我的苟且偷生/还惠赠免疫力/我拒绝上医院/在这浮躁的尘世/只想用尖锐的文字/一个人刮骨疗毒——《病》
“有人说我病得不轻”,开篇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紧张感。但是诗人表现得很达观,“不要紧,这病不影响/我在尘世活着/不要命”。“病”不是现实层面的身体生病,而是诗人不愿与不良社会风气同流合污,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浮躁的社会所鄙弃。从这个视角看来,诗人是“有病”的。从“不要命,只要/我的苟且偷生”可知,诗人貌似达观,实则无奈,传递出一种无以言说的无力感。但是诗人拒绝改变,“我拒绝上医院”“只想用尖锐的文字/一个人刮骨疗毒”,个体的力量难以改变社会,为了五斗米多少人不得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和“苟且偷生”,但是诗人内心又是矛盾的、抵触的,诗人试图用文字来对抗黑暗、拯救灵魂。
自古以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的政治理想和家国情怀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中,然而现实和理想的悖论必然会造成挫败的人生和痛苦的感情。歧路彷徨、寻找出路、自我坚守、精神寄托等复杂而丰富的深层次的内心体验如果要找到一个倾泻的出口,那必然是诗。“物不平则鸣”,古代那些优秀诗歌无一不是这种精神困境的回响。屈原、阮籍、陶渊明、苏轼、辛弃疾……这些伟大的诗人无一不是以文字为刀刮骨疗毒,在诗歌里挣扎、救赎,最后破茧成蝶。而王立世用最现代的语言诠释着最古老的风骨。他的诗,是屈原的美人、陶渊明的菊花、鲁迅的野草。他把一根肋骨卸下来,燃成火把,小心翼翼地在暗夜里行走。而那微弱的光芒也烛照了我们浮躁的心灵。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王立世的感怀诗总是温柔敦厚地兴观群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平和含蓄。他的诗,是深刻的自我内省,是菩萨低眉式的悲悯,而非金刚怒目式的鞭挞。无论是金刚怒目,还是菩萨低眉,皆是六道慈悲。
四、美人在巧: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取材,挖掘新的意象
王立世善于观察生活,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提炼新意,进一步拓展意象的选材范围。他虽然也选用高山、大海、明月这些传统的意象,但总是别出心裁,赋予了意象和传统内涵完全不同的新意。例如这首《山》:
这座山并不高/更不是高不可及/也没有什么风景/上去的人如天上的云/风一吹就不知去向/我没有什么烦恼和遗憾/因为我从没想上去/也从没上去过/我只是在山下/看了看/就去干别的了——《山》
在传统诗歌中,“爬山”的意象蕴含了人的崇高和超越体验,“山”更成为生命意志上升勃发的象征。而王立世的《山》,则赋予“爬山”以仕途攀爬的意味。在诗人眼里富贵如浮云,“这座山并不高/更不是高不可及/也没有什么风景”,诗人不屑一顾,也志不在此,“我没有什么烦恼和遗憾/因为我从没想上去/也从没上去过/我只是在山下/看了看/就去干别的了”。
王立世更擅长挖掘新的意象,那些微小的、习以为常的事物,诗人都能托物言志、寄托幽情。例如《夹缝》系列:
缺水、缺氧、缺光/说开就开/低着头,像一个/不多说话的君子/给这个狭小的世界/留下美和香/凋谢时/也没有一点遗憾——《夹缝里的花》
一束生动的光/经过多次折射/才抵达潮湿的夹缝/夹缝兴奋了许久/那些灰暗的草木/开始欣欣向荣/那些憔悴的鸟儿/开始鸣翠柳——《夹缝里的阳光》
我们喜欢歌颂广袤的原野、险峻的高山、辽阔的大海,谁会把目光投注到不起眼的夹缝呢?但在诗人眼里,那些卑微的生命——“夹缝里的花”“灰暗的草木”“憔悴的鸟儿”都是可敬可爱的,即使环境恶劣,“缺水、缺氧、缺阳光”“狭小”“潮湿”,依然生机勃勃、心向阳光。这些意象寄托着诗人对社会底层深深的怜悯之情。在诗人心中,众生平等,没有什么尊卑高下之分,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都可以引发心灵悸动和哲学思考。
诗人为什么能有这种共情心呢?因为他也处于生存困境之中。他在《夹缝》中写道:“夹缝里的草弯着腰/夹缝里的花低着头/夹缝里的空气异常稀薄/夹缝里的鸟鸣已变调/夹缝里的阳光都被折射过/夹缝里的风如箭/夹缝里的雨像子弹/夹缝,夹缝/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由己及人,天人合一,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分。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佛教讲“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故“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
故此,毛毛虫、大拇指、感叹号、穿山道、帽子、体检报告等再平常不过的事物,王立世都能信手拈来,点石成金。这背后,一定有日复一日对自然的沉浸和对生活的超越,才能培养出如此深刻的观察和联想能力。诗人通过类比的技巧提炼,创新性地把大自然的原材料和表面的生活经验转化成诗的艺术表达,拓宽和丰富了中国诗歌的意象领域,对现代诗质的深层探索、开掘和建构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王立世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所在。
五、美人在韵:内蕴丰富、多姿多彩
王立世的诗歌表情是丰富的:可哲思、可悲悯、可幽默、可深情,好像姿容姝好的美女,一颦一笑,风情万种。
我一辈子/没有像雷那样/大声说过一句话/却像埋在路上的雷/谁踩了/才知道我的厉害——《雷》
这首诗中出现的两个“雷”,分别代表不同的喻体:第一个是自然现象打雷,第二个是地雷。诗人要表达的是“我”这一辈子虽然不会和人大声争执,但是“我”并不是好欺负的,“我”是有原则和血性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词义的悄然转换使诗意呈现出一种跳跃性的律动,读者在恍然之际不禁叹服诗人的机智。结尾一扫其他诗歌的深沉内敛,带着孩子气的勇敢和率真,让人心领神会又忍俊不禁。
我胆小、怕事/上帝悄悄放了几块小石头/为我壮胆//我多愁善感/上帝怕我受伤/又在肝上包了一层薄薄的脂肪//我多嘴,看见不平事就想多说两句/上帝怕我祸从口出/在右侧甲状腺安了一个结节//遇事,我爱激动/常常热血澎湃/上帝,让我的心跳放慢了速度//上帝都是为我好/要不,他一狠心/就会让我痛不欲生,或者早早完蛋——《体检报告》
看到体检报告,一般人的反应是紧张焦虑的,但是诗人却用轻松诙谐的语调消解了这种紧张焦虑,把痛苦的疾病调侃成上帝对“我”的“爱护”,用戏谑的口吻传达出生命的达观和清醒的自我认知。他将生病的“悲”与“上帝都是为我好”的“喜”强烈碰撞和缠绕,对立的因素均衡、共存,一方面以突兀转折、逻辑对立、深层语意扩张了诗歌的包容性,产生了整体的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语言的幽默也使诗歌具有反讽的意味,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余地。
我在桃花源里种菊/你在天上种星星/我们种的都是爱情/因为你想在午后采菊/我想在夜晚看星星——《菊与星》
王立世很少写爱情,但是偶一为之就惊艳绝伦。这首《菊与星》构思新巧、自然流畅、跌宕有致、温情脉脉,在王立世的诗歌中独树一帜。诗歌的意象很美,颇具童话色彩。诗歌中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沛的感受成功地表达了缠绵的深情,具有浪漫主义风格。诗歌前面是实写,后面是虚写,虚由实生,彼此密切衔接又层层深入,空间的反复对照和时间的回环跳跃,纵向拓展了诗歌的张力。
小时候/让妈妈用拴风筝的线/给我拴月/妈妈漫不经心地说/长大了/自己会拴的/现在/拴风筝的线丢了/月/比我童年/还遥远——《月》
诗歌中的“月”渲染了幽冷凄清的情绪氛围,增添了诗篇的朦胧感和神秘感。诗歌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一是时空上的对比:小时候,“我”和妈妈在家乡快乐地游戏,表现了轻松愉悦的亲情;“现在/拴风筝的线丢了/月/比我童年/还遥远”,表现的是成年后对故乡亲人深切的追思和寂寞失落的惆怅。小时候有多温暖现在就有多冰冷,欲抑先扬的手法加深了痛苦的心灵体验。二是态度上的对比:“妈妈”的漫不经心和现在的“我”的深深怅惘。“妈妈”对“我”的美好希冀和成年后“我”面对命运的无力感形成了反差,最终酝酿出无以言说的心灵呜咽之声。诗人的表达十分节制,避免了“井喷式”的抒情,对情感采取冷处理的艺术手段,巧妙地把忧伤的情绪隐藏在文字背后,然而人世的悲怆却可触可感。“月”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前者是物象,后者是意象,二者相互映衬、相互化合,在虚实交错中控制着情感的运行和变化,使主观自我的情感抒发与客观自然景象的意蕴达成完美的契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诗人半生的积淀和历练已使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经验方式、精神气质都转化为与众不同的精神长相和坚定笃行的内心力量,不断滋养着每一个文字,最终在诗歌中开出花来,构成了他诗歌丰富的审美体验、多彩的艺术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王立世将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落实于诗歌写作中,在继承和发扬诗歌优秀传统的同时,实现了生命感悟和诗歌写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写出了符合“新时代”精神和当代读者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的诗篇,建构起了新的诗歌美学形态。随着时间的大浪淘沙,他的诗歌的艺术价值还会被发现和重估。